古典到前卫从未消失的现代性
——夏皮罗的中世纪美术动态研究
文/图:董雪莹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2019 级博士研究生
一、夏皮罗的中世纪艺术研究方法
夏皮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四卷美术研究文选之中:《罗马式艺术》(Romaneque Art,1927)《现代艺术:19 与20 世纪》(Modern Art:19 and 20 Century,1978)《古代晚期、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艺术》(Late Antique,Early Christian and Medieval,1979)以及《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Style,Artist and Society)。[1]1929 年,夏皮罗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第一个美术和考古学博士学位。1931 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莫萨克的罗马式雕塑》(The Romanesque Sculpture of Moissac)发表在《艺术公报》(Art Bulletin)上,为中世纪艺术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批评视角。从20 世纪20 年代陆续出版的论文集到1973 年发表的《词语与图画》[2]系列单行本著作,中世纪美术的研究几乎伴随了夏皮罗的一生。这既是夏皮罗美术史学研究的起点,也是贯穿他的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条经线。[3]
关于夏皮罗的中世纪研究方法的概括与提炼,从欧洲中世纪史学家迈克尔·卡米尔[4](Michael Camille)所提出的风格、社会、自我这三个关键词中可见一斑,他的治学风格和方法反映在其研究谱系中所对应的三个价值尺度中,它们分别是:夏皮罗对于艺术视觉品质持续的关注,并伴随着艺术家的共鸣所形成的一种随性而开放姿态;他认识到形式、内容和社会环境必须一起评估,从而拥有更宽阔的研究手法和途径;风趣幽默充满智性的性格,包括他狂热的,甚至神经质的博闻强记,以及对细节严苛关注的名声。[5]这些都是成为一名横跨古今、打破研究壁垒的美术史学家所具备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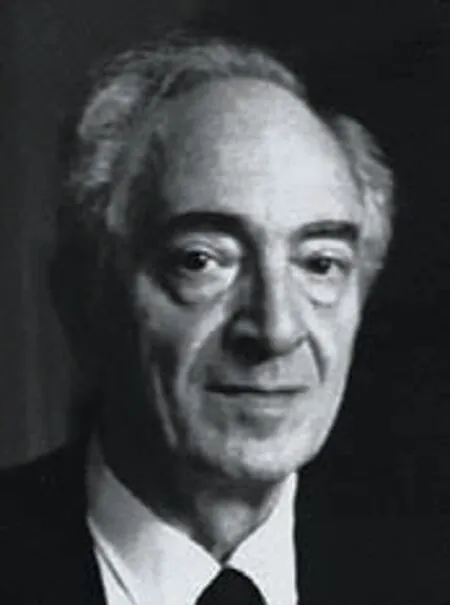
夏皮罗
如果我们细读夏皮罗的原文会发现,描述对象的改变并不会使他放弃对现代术语的使用。事实上,他的研究不仅贴合当前的[6]视觉实践经验,而且直接源于他对古典图像创作的兴趣,甚至是地点的兴趣。在夏皮罗的笔下,罗马式雕塑、比图雅斯启示录手抄本(Beatus)、早期基督教绘画与19、20 世纪的作品并无区别,它们甚至是可以共同使用同个问题、同个术语。于是,罗马式风格得到了彻底的复兴,从而挑战了陈旧的欧洲模式。我们在一段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近似疯狂追逐动态形式而不断变化的文字运动:
雕刻家认为对比既是一种排列的原则,也是一种对立或分裂对象的行为,这一概念也出现在对魔鬼之脚的描绘中。它们在这两集里是不同的,好像在暗示魔鬼前进的步伐,事态在行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起初,它长着一只贪婪的四足动物的爪子;这样,两只脚就彼此区别开来:右脚像鸟的爪子,左脚像人的脚。这种内在的变化与已经观察到的本尼迪克特和彼得的脚形成对比;但在第二场中,魔鬼的内在不对称实际上是魔鬼形象逐渐显现的过程,是它本性和丑陋的最终体现,就像它头部形状的改变一样。[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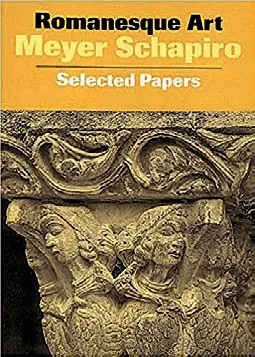
《罗马式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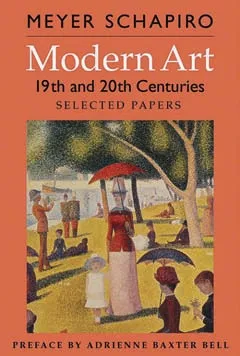
《现代艺术:19 与20 世纪》

《古代晚期、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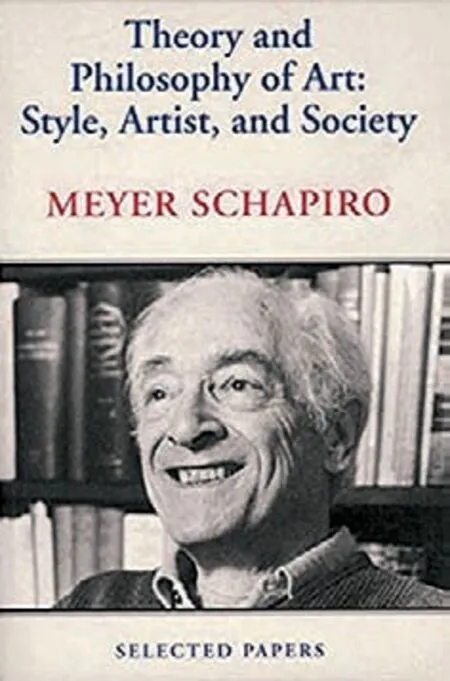
《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
这种形式和叙事效果的结合是身体的共鸣和对材料的直接理解,与20 世纪30 年代关于中世纪艺术文章中常见的静态形式主义语言相去甚远,即严格的形式主义和线性设计导向的“定律”。在那个由谦逊古板的古物研究从业者和图像学代表人物所控制的中世纪艺术领域,夏皮罗的研究方法显得格外的时髦与叛逆。这也就足以说明作为一名两栖学者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所具备的前瞻性和探索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把对中世纪物品的审视视为理所当然,所强调的也不是历史事物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而是碎片化和差异性。
此外,他还论证了苏雅克修道院的雕塑[8]在中世纪时期美术发生了世俗化的转变时指出浮雕画面的内容与样式设计与社会演变有关,此时期的教会已开始向世俗阶级和机构屈服,它培养了一种更能反映人类经验的风格;锡洛修道院[9]在风格之变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风格以及“全新的主题”都是来自转型时期的文化体现。而“早期罗马式美术中所保留的穆莎拉比(Mozarabic)的风格特征[10]既可看作是文化转向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看作是教会扩张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11]夏皮罗旨在通过风格研究以确立图像的形式和意义将会与某个时期、地区之间产生某种关联。从而,以此论证艺术并非是自己变化的,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环境折射。他从对中世纪艺术的图像语言研究找到了一条称之为“符号”的线索,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贯穿古今与20 世纪现代艺术的形式分析法、精神分析、符号学、马克思社会主义、精神分析法结合,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视觉语言符号学。[12]
二、对中世纪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态度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夏皮罗的一生都在中世纪与现代艺术之间穿梭。他与现代艺术的接触使他更容易接近和理解那些曾在艺术史学中被忽视或不被接受的“旧艺术”现象。他在罗马式雕塑和现代绘画中发现了“完美、连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的问题,并对每一种艺术都进行了精确的描述与分析,他注意到莫萨克、苏亚克和塞洛斯的雕刻家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重要决定。同样,他也能够用敏锐和批判的眼光,在印象派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中发现创造力的笔触和色彩在画面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夏皮罗在阐述现代艺术作品的价值时总是以形式分析为例回应那些认为在这个时代的作品中缺乏形式、混乱或无意义的评论家们。他关于中世纪艺术研究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论罗马式艺术的审美态度》(On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Romanesque Art)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反对者最直接的回应。现代主义反对者将虔诚的中世纪艺术家服务于教会的浪漫主义概念用于批评现代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脱节。
显然,克服来自大众最初的质疑或不理解的行为是现代主义史诗般历史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它反映在:当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在《第一夫人》(Woman I)的创作过程中被夏皮罗说服后决定保留这张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作品时;当批评家们批评蒙德里安的作品是“极其死板,与其说是情感的产物,不如说是理论的产物”[13],夏皮罗积极地为其辩护之时。在他的眼中古典与现代是相通的,其理论即可用于古典研究,也受用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的研究方法。换言之,是源于对对象非常现代的关注模式直接导致他对中世纪和现代艺术在文本阐释上的契合。事实上,现代艺术家所遭遇的种种困境都能够在夏皮罗的中世纪研究过程中再次上演。首先,他挑战了来自传统中世纪研究者所善用的图像学方法,将视野扩展到形式分析和新的风格标准上,以证明了那些被早期艺术史学家视为笨拙、偶然或原始的特征,恰恰是这些作品中最有意义的元素。遗憾的是,夏皮罗对罗马式雕塑开创性分析方式并没有得到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们的认可,他们不认为这些风格是有效的,也不承认对其进行视觉扩展分析是有价值的。其次,夏皮罗所使用的视觉分析方法是将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的,依赖于对中世纪艺术的制作、意义和观看的假设,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批判性反思。他对每一个视觉细节的关注都是对整体构成和意义的独立贡献,这与超现实主义兴起后产生的现代艺术有着明显的联系。战后纽约的画家对艺术意图的理解与12 世纪的雕刻家或修道者截然不同,同样中世纪的观赏者可能也以不同的观看方式阐释自己的作品。因此,夏皮罗将形式和内容联系起来的开创性尝试引发了对中世纪艺术创作和意图的进一步研究。最后,夏皮罗比较和发现中世纪与现代艺术联系,有助于现代艺术家确信他们的作品是具有当代意义的。在对锡洛手抄本的研究中,他发现手抄本中的绘画形式竟然与纽约前卫绘画有相似性。夏皮罗经常带艺术家去参观摩根·贝特斯(Beatus)的手稿,其中包括罗贝托·马塔[14](Roberto Matta)和弗尔南多·莱热[15](Fernand Legor),后期夏皮罗声称看到了这次参观对莱热艺术的影响。想象一下:一个中世纪的艺术家,习惯于研究死去的无名艺术家,用他古老的主题来启发活着的当代艺术家,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命题。正如迈克尔·卡米尔(Michael Camille)所说的那样,艺术世界日益扩大的地理和文化传播阻止了当今任何一个中世纪史学家发挥类似的作用,即使他或她有这种能力或愿望。
夏皮罗的作品为当代艺术史提供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另类谱系。正如对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对当代艺术创作影响的评价一样。夏皮罗在过去20 年里的地位也有所上升,他的方法论为艺术理论铺平了道路。因此,夏皮罗的美术史研究著为那些不愿与传统形式主义或肖像学方法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史学根源。
三、研究的语境和思考
在概述了一些夏皮罗在艺术研究中的方法后,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些其背后的一端倪。但是要想完全的理解夏皮罗是从中世纪跨越到现代艺术背后的驱动力,我们有必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做一个简单介绍,旨在勾勒出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以此建立起讨论所需的思考语境。
夏皮罗所处的20 世纪美术史研究正值美术史学科的转向时期,一方面是来自于地域上的转向,战争给当时的英美世界带来了一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知识迁徙。大量德奥语系的学者们,不得不从欧洲向英美转移。美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了二战后国际美术史研究的重镇。以潘诺夫斯基为首的德语系研究者在美国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夏皮罗也是其中之一。[16]另一方面,是20 世纪70 年以来形成的新美术史对传统美术史发出的挑战。所谓的“挑战”并不涉及图像本身,主要来自于多种人文学科介入后对传统美术史学研究所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因此,在这种学术氛围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夏皮罗既受到欧洲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的熏陶,也受到现代美术发展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20世纪的史学研究整体发展趋势是构成夏皮罗学术体系发展的外在因素之一,那么对精神分析法的痴迷和马克思主义语境的回归算是给了夏皮罗学术转向的临门一脚。这门学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和各种女权主义的深远影响,在长期以赞助为形式的肖像研究系统以及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之后,有开始回归艺术史的趋势。遗憾的是中世纪艺术由于没有名字和签名的个性,总是特别容易产生千篇一律的分析形式。但是夏皮罗关于研究早期罗马式艺术的作品是最令人兴奋的,文中充满了对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颂扬,他把艺术家个性与社会和历史变化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对于艺术史而言,最重要的是夏皮罗将中世纪图像创作的边缘因素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联系起来。夏皮罗笔下描述的“怪兽”们是舍弃了智力系统后的个体,是非理性的幻想,是单一的思想和感觉。这些奇形怪状和充满兽性的战士有着个性化但又边缘的特征。夏皮罗就站在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中间,就像封建主义占据着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位置一样,以包罗万象的开放姿态挑战权威。
如果夏皮罗的形式主义带来的是对客观对象在空间和结构中的启发,那么他对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等概念的使用,也同样能帮助我们关注当下。如同30 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夏皮罗在马克思身上发现了理解历史的强大思想,但是夏皮罗的理论并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和社会原则等纯粹理论坚持,而是把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则与客体结合起来。早期的文章之所以如此成功,不只是因为对视觉形式的严格关注,而是将目光锁定在历史的每一个变革节点上,最终形成了一张反映社会关系与实践的地图。夏皮罗在描述历史过渡时期和内容形式转变的文章,《从摩札布尔到塞洛斯的罗马式》(From Mozarabic to Romanesque at Silos)中攻击在巴尔特鲁沙伊蒂斯(Jurgis Baltrusaitis)[17]的作品中存在着机械的辩证法,因为用这种方法根本无法解释风格和形式的变化: 我们无法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发现一种新的风格是如何产生的,或者罗马式艺术究竟是如何变化的。它不是对一个活跃的历史过程的解释,严格地说,也不是黑格尔或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方法。巴氏的辩证法的一个关键弱点在于内容在艺术作品的形成中所起的消极、中立的作用;它不允许意义和形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仍然是最主要的和永久的。[18]
无论激进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是好是坏,夏皮罗这样的人所看到的是历史形式发动机的内部。他在三四十岁走向成熟,像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大众”娱乐下滋生的“文化产业”。然而,在这个时代艺术已不可能如此干净地与商业文化隔绝。所以,当代艺术不再包括德库宁(De Kooning)的裸体画框和马瑟韦尔(Motherwell)的抽象作品。如果夏皮罗能够用美国的前卫艺术来定义罗马式艺术的视觉机制,并且学会培养那些刚刚有欣赏“新事物冲击”意识的观众,那么,当代文化和中世纪艺术之间所建立的辩证联系就将是另一番景象。对于未来的艺术史学家来说,这种辩证联系可能来自于新兴媒体和人工智能。但对于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的我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视觉形式不是艺术,而是信息、广告和各种空虚的娱乐指南。那么,如果是你,会不会将这些物品和图像与中世纪的圣物匣、祭坛、石雕、手稿和大教堂做为比较?

贝叶经
注释
[1][美] 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 与20 世纪[M].沈语冰,何海,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2]全名为《词语与图画:论文本插图中的文学系和象征意义》《词语、手稿与图画:视觉语言符号学》两本单行本著作。
[3]王春辰. 夏皮罗中世纪美术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07.
[4]迈克尔·卡米尔(1958-2002),芝加哥大学玛丽布洛克教授,欧洲中世纪艺术历史学家。他在《纽约如何偷走了罗马式艺术的灵感:迈耶·夏皮罗的中世纪、现代和后现代》一文中指出夏皮罗在中世纪艺术领域对这三个问题的探索——我们可以称之为风格、社会和自我——远比“现代主义”标签最初所暗示的要复杂和狭隘得多。他在文章中宣称要说服那些对夏皮罗的罗马艺术作品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主义学生,以及还没有读过这些作品的人,并让他们相信对于此类作品持续关注的价值。
[5][美] 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 与20 世纪[M].沈语冰,何海,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6]指20 世纪40 年代。
[7]See Meyer Schapiro,Romanesque Art: Selected Papers ,1977,George Braziller Inc,page11.
[8]苏雅克修道院位于法国西南部,建于1075-1150 年。夏皮罗于1939 年发表《苏雅克修道院的雕塑》一文中对苏雅克圣母修道院西门门廊门楣提奥菲勒故事的九块浮雕进行研究。
[9]锡洛修道院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布尔高省,始建于929 年。
[10]莫兹阿拉伯建筑,公元711 年阿拉伯人入侵后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伊斯兰教装饰主题与形式的同化,如马蹄形拱门和肋状穹顶。
[11]See Meyer Schapiro“From Mozarabic to Romanesque in Silos”,in Romanesque Art: Selected papers,1977,George Braziller,Inc,page 64.
[12]此方法是夏皮罗终身研究的核心命题,其中反映了他对图像与文本互动关系的研究与思考。
[13]See Meyer Schapiro “Mondrian: Order and Randomness in Abstract Painting,” in Modern Art: 19th and 20th Centuries,1978, George Braziller,inc,page 233.
[14]智利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是20 世纪抽象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开创性人物。
[15]费尔南·莱热 (1881-1955 年) ,立体派代表画家之一,受到塞尚的艺术影响,1910 年结识了毕加索和布拉克。
[16]尽管帕诺夫斯基和夏皮罗在学科研究上非常接近,但乍一看,他们的职业生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然而,一些联系也是可见的。夏皮罗在梅洛德祭坛上的论文引用了帕诺夫斯基关于范·艾克的名作《阿尔诺菲尼肖像》的著名文章,而帕诺夫斯基则在1964-65 年中反过来称赞夏皮罗对《阿尔诺菲尼肖像》的诠释是“杰出的”。两人也有过私人接触:比如,帕诺夫斯基感谢夏皮罗在他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及其艺术宝藏》(1946 年首次出版,第二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年,P231)一书中所提供的参考书目中更有暗示意味的提到并称赞伯纳德的《克莱沃的自辩》是对罗马式雕塑的敏锐描述,他说:“一个现代艺术史学家会感谢上帝赐给他写作的能力……如此真切地唤起人们对‘克莱尤尼亚风格’装饰式的描述;deformis formositas ac formosa deformitas 这个短语提供给我们很多关于罗马式雕塑精神的提示,而不是单纯的风格分析。尽管夏皮罗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但人们很容易认为,他至少是帕诺夫斯基心目中的“现代”艺术史学家之一。夏皮罗在第二年发表的《论罗马式艺术中的审美态度》(On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Romanesque Art)一文中,把伯纳德的文本放在一个很关键位置;帕诺夫斯基再次感谢夏皮罗在他的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Latrobe, PA:Saint Vincent Archabbey,1951)一书中所作出的贡献。两年后,夏皮罗又以“风格”一词为索引间接地提到帕诺夫斯基的书。他写道,“从思想中获得风格的尝试往往太过模糊,只能产生启发性的想法:这种方法滋生出类比性的推测,而这种推测在详细的批判性研究中是站不住脚的。”哥特大教堂和学术神学之间的类比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两个当代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百科全书式的完整性和对无限的追求,以及辩证方法(最后一段提到了帕诺夫斯基的作品),P85。这些接触的信息可以证明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位都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历史学家,这样的研究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关于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艺术史的信息。
[17]巴尔特鲁沙伊蒂斯(Jurgis Baltrusaitis)立陶宛籍艺术史学家、肖像学重要代表之一。他对罗马式雕刻中的装饰纹样逻辑进行了精彩的研究。
[18]See Meyer Schapiro,Romanesque Art: Selected Papers ,1977,George Braziller Inc,page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