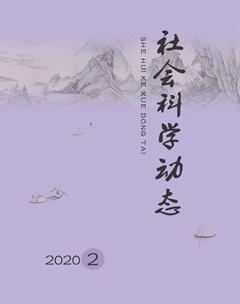城乡文化影响下的欲望和执念
摘要:在小说《花满月》(方方著)和《直立行走》(宋小词著)中,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怀着各自的欲望和执念。这欲望和执念的萌发,既体现出人类生命主体的自由,也受到时代环境的约束,更有城乡文化的潜在影响。小说中的人物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中选择、浮沉和坚守。作家通过对人物欲望与执念的叙述,反思了个体生存方式的多样化,审视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呈现了城乡文化语境中不可调和的现实矛盾。
关键词:方方;宋小词;城乡文化;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2-0103-05
方方是著名的当代湖北作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底层小人物,他们常常呈现出一种固执、刚烈、坚韧不屈的性格特质,作家通常在简明而流畅的表述中,对这些小人物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中辅以悲悯的亮色抚慰,进而表达其深邃的人生思考,呈现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北京文学》2017年第1期上,刊发了方方的中篇小说《花满月》,故事主要讲述一位叫花满月的落难地主小姐,她嗜赌如命,在社会变迁和政治洪流中颠沛流离,在无法把控的命运沉浮中,麻将成了她的信仰和依靠,令她有了超然物外的精神力量,也因此写就了她獨特的人生传奇,故事更多让人感叹的是世事的沧桑、命运的莫测和人生的多彩。几乎与此同时,《小说月报》2017年第1期上选载了湖北籍80后女作家宋小词的中篇小说《直立行走》,这篇小说原刊于双月刊《当代》杂志2016年第6期。故事以城市房屋拆迁为主题,在城市底层平民期望改善生活向上爬的挣扎过程中,极为冷静地表达着小人物的命运与尊严。作品以底层人物的恋爱婚姻悲剧、委曲求全的性格缺陷、一波三折的叙述节奏、直面生活的姿态书写深刻地展示出主人公杨书福等人现实生活的困境与伤痛。让笔者产生兴趣的是,两位女作家分别在这两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塑造了怀有欲望和执念的人物形象。换句话说,在《花满月》与《直立行走》里,故事的主角都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式的欲望和执念。
一、个人与家庭:欲望和执念的两种存在形式
在《花满月》开篇,方方通过有限的全知叙述,就描写出女主人公花满月在麻将牌桌上专心致志,置生死于度外,也为下文她遭遇家人分离、下嫁车夫、隐姓埋名等一系列生活变化,却依旧坚守自己的欲望和执念作了铺垫。花满月的牌瘾是与生俱来的,她从小到大的唯一爱好就是打牌。为了打牌,她在民国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活得心无旁骛,对家里大小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她在麻将桌上得到的痛快,是其个人享乐方式的一种极致。及至兵临城下,她不顾父母劝说和反对,一定要打完最后一百圈才肯收手。正是这种个人式的欲望和执念,让她错过了与家人一起逃亡的机会,而这一错过,竟改变了她的一生。“一定要打完最后的二十八圈”的执念,让她在此后的社会动荡变迁中幸存;使她在政治运动风暴面前毫不妥协;支撑着她“好死不如赖活着”走过了六十多年风雨,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她的日子纵是水深火热,可她却一直怀着念想。一个人心里倘有念想,就不会觉得日子难过”。①
探究花满月的欲望和执念是如何衍生的,可以发现,这与她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分不开,也和哺育其成长的市民文化有关。民国时期,花满月一家生活在城市,母亲是城里有名的全职太太,经常在家聚众赌博,或者出门打牌时也带上她。母亲身上所体现的市民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花满月的性格习惯,无形中也养成了花满月嗜赌如命的癖好。有牌可打的舒服日子曾伴随花满月二十多年,但这纸醉金迷的好日子终究逝去。造化弄人,内战爆发,花满月与家人分离,为了生存,她只得下嫁给从农村来的车夫王四。丈夫一家所秉持的乡村文化与花满月习染的城市文化格格不入,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家庭文化背景的不同,直接成为花满月与王家人之间接连不断的矛盾导火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城乡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生活冲突,反而让一念执着的花满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欲望:“一个人光是赢钱有什么乐趣?打麻将就是一个赌,跟别人赌,也跟自己赌。”
在《直立行走》的开篇,宋小词通过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叙述了主人公杨双福与周午马在情人节的约会情景。作者选取生活中一个片段来切入故事,但并未交待约会的来龙去脉,这为下文两人之间无爱的婚姻交易埋下了伏笔。杨双福拼命考上大学,实现从农村来到城市,毕业后选择留在城里工作,独自一人过着苦逼的私企职员生活,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稍微宽敞点的房子,跟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生个孩子把他养大,然后寿终正寝。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前者暗藏着令人向往的物质文明与严格的社会层级,素朴的乡村文明在与前者的比较之下显得相形见绌。从乡村走向城市,杨双福以其天生的乡村文化基因面对全新的文化形态的审视和过滤。她不断地努力向所谓的城市文化靠近,并由此生发出个人式的欲望和执念。为了让自己在这座城市能扎下根,她想嫁给一个城里人的方式来改变出身,让自己拥有城市户口,过上稳定且不愁温饱的生活。在杨书福的内心深处,始终潜藏着一种作为乡下人的天生自卑感,“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的”。② 这种感受就像高科技芯片一样根深蒂固地植入她的大脑,逐渐形成她的日常观念,影响支配她的行为活动,让她在面对城市青年周午马时,主动选择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以致最终丧失了平等的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即使在追求这种平反生活的过程中,周午马一次次地把她当成性工具对待,她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这无疑是都市文化对杨书福个体生存的一种暴力侵蚀,也是对其人性的一种扭曲。她试图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努力融进周家人所期望的家庭生活,甚至容忍男友及其家人联合起来利用自己,使她身陷拆迁补偿骗局,最终违法犯罪失去自由。杨书福嫁到周家后所做的种种改变,看似顾全大局为了周家,尽到为人儿媳之本分,但实际上还是在为了让自己早日在周家站稳脚根,获得一家人或者说城里人的一种身份认可。那种蝼蚁一样在生活重压下的尴尬和疼痛,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直立行走》中不仅有杨书福个人式的欲望和执念,还存在一种家庭式的欲望和执念,即个人执念来自于整个家庭欲望的满足,并试图通过个体行为使得家族成员能从中受益。周午马的父亲便是这样的人。周父这一人物的出场,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旁观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之间的反差,间接通过杨双福的眼光来作出近距离观察。作为一个肺癌晚期病人,他虽人之将死,但依然想给妻儿争得一套宽敞舒适的房子,他在家里的床上顽强地硬撑着,“有病都不敢看,没钱,经常为了报销药费得罪一大堆人,最后,便都自觉地用身体来与病魔作斗争”。③ 为了在拆迁后能多分30平米面积,周父硬撑着一口气,一家人串通起来欺骗邻居和政府。换房子的欲望和执念,让周父可以直面死亡,而一旦欲念得以实现,一直徘徊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生命也随即消逝。周母和周午马的欲望和执念也是关于这个家庭的几十平米房子。为了房子,周母规劝儿子尽快找个人结婚,尽管儿媳不是自己理想中的贤妻良母,她也能够忍气吞声;为了房子,周午马尽管心中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主动“追求”杨双福并将她带回家。母子二人的欲望和执念,相较于周父和杨双福来说,表现得不是那样突出和深刻,但正是这母子二人的陪衬下,更凸显出周父和杨双福两人念想之执着、欲望之强烈。
在两部小说中,既有故事外的叙述者,也存在故事内的聚焦人物,如花满月、杨双福等。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不再统一于将主人公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以上两个不同主体之中。不论是花满月,还是杨书福,主人公个人式的欲望和执念,都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她们各自的命运。杨双福和花满月的人生故事在结局上也具有相似性,二人都失去清白之身,最后人财两空。但其本质上却又有着区别,《花满月》重在写“执念”与“欲望”本身;而《直立行走》中“执念”与“欲望”只是一种手段,是为其他人生目的服务的。两篇作品内核各异其趣,两位女主人公诉求的具体对象不一样,诉求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杨双福虽然嫁给周午马,赢得了同事的称羡,但她一直活在别人的看法里,百般忍气吞声也没能让自己过上满心期待的生活,最后还与家人彻底决裂,想住进周家新房亦属不可能。花满月虽对现实生活比较钝感,面对变故不断妥协听天由命,最终却又似乎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并把生命也送到了麻将桌上。这倒应了作家余华在小说《活着》里的一句话:“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从两部小说结尾来看,如果仅用“封闭式”或“开放式”这种简单贴标签的方式来评价,是不恰当的。《花满月》的结尾,作者安排花满月倒在了麻将桌上,完成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结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她若再活着,生命意义何在?有学者认为,“死亡是最为让人困惑、最为开放的结局。它以最为神秘的戏剧化方式表明,结尾作为整个故事清晰度的基础和跟据,总是逃遁后退,消失不见”。④ 花满月的死亡意味着故事的终结,也意味着欲望和执念的不复存在。《直立行走》的结尾,杨双福被前夫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打晕。这不禁引起读者猜想,若周午马和其现任妻子发现被打昏的人是杨书福,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办?是像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装作不认识旧爱鲁侍萍,不与杨双福相认,然后将之轰出新居?或者报警,将杨双福再次送入警察局?作者在小说的结尾留下了诸多可能,在解结的同时又打了一个新结。
二、主体的自由与客体的约束:欲望和执念的悖论
卢梭曾言:“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人的欲望和执念也一样,其产生与实现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或者说,既有主体萌发的自由,又受到客观现实环境的制约。“在方方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宿命制约着人的生存,外部世界对主体的生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掌控,人生的种种磨难和进退维谷的生存焦虑有着外部环境的操控,而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⑤ 小说《花满月》中,主人公花满月无时无刻想着就是麻将,这一欲望和执念支撑着她从民国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她走过六十多年时光,也让其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便是饱受物质上的困顿,但精神上却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常。城市解放之际,家人纷纷逃难,家产被查抄,花满月变得一无所有,被迫留在西月巷,时移世易失去了打牌的机会,其后是社会整体风气的变化,使其打牌的执念不仅面临现实的责难,欲望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花满月却从来没有把这欲望和执念寄托到别人身上。她下嫁车夫王四,忍受着王老太太裹脚的臭味,学会干“腌菜厂腌萝卜”的粗活。她随遇而安,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镇定地接受了自己遭遇的生活种种变化,甚至是丈夫的饿死和婆婆带着儿子的离开。改革开放后,已改名换姓的花满月无意中发现城里新修了一家“福来棋牌室”,但当她想进去打牌时,老板嫌她又老又穷而将其拒之门外,“这是岳满花人生最沮丧的日子。这份沮丧,比得知一家人都忽然不见的消息来得更沉重”。⑥ 面临生活的种种挫败,她却并没放下这关于麻将的执念和欲望。欲望的坚守使她终于迎来了生活的转机。一次是其居住的老房子将被拆迁,可以获得十万元以上的拆迁费。若真能如此,她就有了打麻将的本钱。可儿子很快得知消息,立即打消原本要跟母亲断绝来往的念头,要与她争夺这笔拆迁费。这让花满月的希望落了空,拆迁费最终换成了房子。第二次转机是逃难的亲人衣锦还乡,从台湾回到大陆认祖归宗,寻找到花满月这个唯一的大陆亲人后,慷慨解囊给了她三万元生活费。这一次她的欲望终于可以实现了,在牌桌上打完二十八圈牌以后,她一头倒在了地上,不再醒来。人生的阴差阳错往往在顷刻之间,生活环境的限制与生命主体的局限,都不曾把花满月击垮,因为她心存执念,这执念可以让她看淡六十多年的生活苦难,把人生活成一场赌博;这执念焕发出一种光芒,照耀了花满月曲折的一生。方方在结尾处写道:“花家屋大小姐花满月的故事不久也淡出人世,不再被人提及,盡管她觉得自己这一生很是辉煌。而实际上,这辉煌只要她自己觉得照耀了,就已足够。”⑦ 个体纵然渺小与卑微,但正因其在不可掌控的时代气候面前坚持自我的追求,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坚持自己的执念,似乎又让她这一生活得灿烂辉煌,最终达成了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
在《直立行走》中,宋小词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叙述,直接通过杨双福的眼光来观察人事,使读者对个人与社会时代之间冲突能够获得更为切身、强烈的感受,从而强化了“欲望和执念”这一主题。在城乡文化二元对立下,在新世纪的都市气候里,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中,杨双福的执念逐渐生发出来,欲望逐步获得满足。她克服了自卑心理,赢得了同事的称羡,以自己的身体、单纯和顺从实现了想嫁给城里人有稳定生活的愿望。她原本以为尘埃落定,殊料好景不长,现实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她的城市梦遭到无情地毁灭。在拆迁冲突过程中,由于冲动和不理智,杨书福发生袭警行为,致使一位警察双目失明,结果因故意伤人罪被判除有期徒刑一年,还需赔偿25万元人民币。周家人在她陷入绝境时不仅不出面相帮,反而落井下石,在狱中她收到周午马送来的离婚协议书。这让她的欲望彻底变成无望,那些执念看似五彩斑斓,但太阳一照就灰飞烟灭。可以说,杨书福想通过嫁得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选择寄希望于别人,这种扭曲的执念是其最终不幸的根源,“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在人性的层面,决定于人物的既定性格——它是人物生活经历、文化遗传、观念意识和时代烙印的产物——人物也许能够摆脱某些外来的阻碍,却由于强烈的自我遮闭而难以超越自身”。⑧
杨双福和花满月同为女性,两人各自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执念,却都没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意识,没有存在主体追求精神自由的意志。花满月在丈夫患病死后,与儿子和婆婆闹掰,一个人生活看似独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她在没有麻将、没有亲人陪伴的日子,也去找寻曾经为她家做过饭的厨子聊天;当她在文革中偶然得到113张麻将牌之后,麻将再一次支配了她的人生,她被麻将所异化、控制,完全无法自拔。而杨双福也不能没有周午马,否则她的欲望将无所寄托。她入狱后,周午马提出离婚,她直接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周午马身上。在杨书福的潜意识中,付出就应得到回报,自己为周家辛苦付出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在她心里变成了强烈的怨恨。周家人用算计、玩弄辜负了她的期望,但她也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也不认为是自己的轻浮、无知、冲动、贪婪,直接把自己推入不幸的深渊。人性本无绝对的善恶之分,却都有着自私的本性。杨双福和周午马带着各自的小算盘结合在一起,目的不同,三观也不合,身份更有差异,一旦利益发生冲突,结合必然变为分离。最为致命的是,因为没有独立的个体生命意识,不能靠自强自立的奋斗来完成自身的欲望,无数的“杨书福们”最终也必然会因遇见“张午马”“王午马”而掉进不同的生活陷阱。
三、城市与乡村:欲望和执念背后的社会意蕴
在《花满月》与《直立行走》中,两位作家通过人物的命运选择,传达了对个人生存方式的深刻反思,表达了对社会现实、时代环境的理性审视,揭示出城乡文化的语境下城市与乡村的内在矛盾冲突。方方和宋小词都生活在武汉,有着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也对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冲突都有着深切的关注。两部小说的写作对象都是女性的情感、家庭、婚姻。方方笔下的小人物,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尽管出身经历不尽相同,但都在日常繁琐无奈的生活中挣扎,表现出外部的社会变化与内部的人性惰怠之间的冲突,进而展现出一种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原生态世俗生活。“全城一条街,花家的店铺占了半条,街名都叫了花半街”,花满月就出生在解放前这样一个地主家庭,过着城里大小姐的生活,从小看母亲打牌长大,打麻将就是她的存在方式。但在社会的动荡和命运的变幻无常面前,听天由命也是花满月的一种豁达与通透。一个视赌博为生命的女人,一生被社会变动和政治浪涛所裹挟。家人逃难台湾,丈夫患病死去,婆婆带着儿子搬回乡下,与她反目成仇。不仅如此,碰上政治风暴,只能隐姓埋名地活着。在无法把控的命运中,赌博成了是她的信仰和依靠,令她淡泊亲情又坦然应对挫折。花满月的存在方式是与社会、时代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动,都无法撼动她、摧毁她,自身的欲望和执念为她提供了一份精神支撑。“小说对花满月的人物描写,超越了一般典型描写的有关阶层的价值判定,没有纠结于人物的社会定位,而是观察描写出人物独特的活法,写出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这就是文化与生存、生命的关系。当一种文化成为人的信念和生活始终的一部分时,它也就是生命、生存的一部分,并使生存有了一种动力,任何艰难的克服和生活创造都是一种文化目标下的活跃。”⑨ 在题材的选择上,无论是书写乡村还是城市,“新写实小说”在直面人生、呈现生活原生态时,都倾向于以“零度情感”的方式,描写普通人贫困的生存處境。可以说,《花满月》是方方在新世纪对“新写实小说”的回归与承继。
宋小词笔下,杨双福也是在城乡差异的逼迫下,对个人的生存方式作出了被动地选择。作为一个乡下人,杨双福上大学后,只身来到城市打拼,残酷的现实让她相信:“付出就有回报、勤劳就能致富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⑩ 只有“依靠姣好的面容和身材俘获有钱男人”{11},才能过上有房有车的幸福日子。关于这一点,早在大半个世纪前沈从文先生就提出了担忧:“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2} 历史进入21世纪,杨双福和她的同事依然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像背负着血海深仇一样从乡野进入城市,每天如鸡一样,两只爪子得在地上刨出血来才有一爪食吃”{13}。杨双福和周午马走在一起,依然是彼此各取所需。杨双福要的是城市户口和城里人的家庭生活;周午马除了满足他的性需求外,还想利用杨双福为自己家多争取30平米的房子面积。他们之间通过物质和身体维持的关系终究是不可靠的。杨双福迫切想改变自己刻着泥土烙印的卑微身份,通过婚姻实现了身份上的解困,但其精神上却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肉体也一次次在婚姻内外被征用。与当下许多农村女性一样,杨书福在都市不断遭遇挫折和冷眼,为了过上城里人世俗眼中舒适安逸的生活,她们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以社会和时代粗暴地强加给她们的价值观苟活着,哪怕这种生活无处不映照出盘附于人性隐匿角落中的团团晦暗。小说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思:当个体生存方式面临城市与乡村的严重对立时,如果完全跪拜臣服于现实的困境,个体命运也必将受社会环境的控制和吞噬。
此外,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一种文化现象。城市文化往往掌握着话语权,乡村文化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受都市文明浸染长大的花满月,尽管在解放后落难,但在夫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而从小受乡村文明影响的杨双福,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在周家都一直处于弱势,没有地位可言。两篇小说都以关注女性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虽然生活在不同时期却面临着相似的选择,个人与时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在城乡中国这一大背景下,女性对自己的婚姻、家庭的选择,依然难以实现独立自主、平等自由。花满月和杨双福一生的痛苦悲喜皆来自自身的欲望和执念,这似乎无关对错,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选择,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其背后是时代和文化的渗透浸染。恰如有学者指出的:“城乡之间的流动迁徙、文化冲突、身份尴尬、农村的土地荒芜、传统价值解体、家庭伦理失范等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耗尽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作品成为类型化的现实镜像或社会学记录。”{14}
注释:
①⑥⑦ 方方:《花满月》,《北京文学》2017年第1期。
②⑩{11}{13} 宋小词:《直立行走》,《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
③ 宋小词:《我们蛰伏在严寒的冬天里》,《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
④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⑤ 陈琴琴:《异化的生存现实与反抗苦难生活的理性思索——论方方小说中的悲剧性叙事》,《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⑧ 方方:《只言片语》,《小说月报》1991年第10期。
⑨ 路侃:《坚持不懈的敏锐与关怀——读方方近年几部中短篇小说》,《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12} 沈从文:《长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4} 王鹏程:《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新世纪城乡书写的叙事伦理与美学经验》,《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平,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