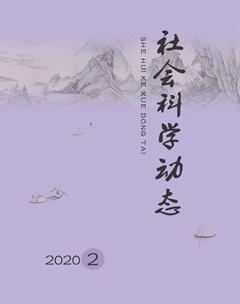英美菲尔丁研究近期动态述评
朱宾忠 杨文慧
摘要:本文搜集了英美学术界关于菲尔丁研究的近期(2016—2019年)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认为近期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前辈权威逐渐淡出前沿阵地;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增长较快,但研究话题和研究对象有待拓展;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们用更新的材料,以更新的视角和理论研究菲尔丁,从小说艺术、社会伦理和哲学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新见,促进了菲尔丁研究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关键词:亨利·菲尔丁;英美研究;动态;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2-0078-07
18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20世纪20年代之后,克罗斯和布兰查德等学者们有力地否定了所谓的“菲尔丁传言”①,肯定了菲尔丁及其作品的道德性,成功为作家恢复了名誉。此后,日益丰硕的研究成果使菲尔丁获得了应有的崇高声望和稳固的文学地位,为他赢得了“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② 之美誉。
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菲尔丁研究着力于从小说艺术和哲学思想两方面论证菲尔丁作品的深度,由此出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声势浩大的菲尔丁小说艺术之辩,以及世纪末以综合性论著为主要呈现形式的关于菲尔丁思想研究结论的反思与修正。本世纪初的研究以更宽广的文化维度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呈现出“总结归纳和创新开拓并重的局面”③。
近年来,菲尔丁研究依旧保持着相当的热度。根据笔者在Project Muse和Jstor数据库里检索的结果统计,2016至今涉及到菲尔丁的研究成果共有41项,其中学术期刊论文25篇④,著作中的专章或论文集论文12篇⑤,专著5本⑥。本文拟以这些成果为对象,从研究者现状、研究对象与话题、重要论著的观点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之走势,评估论说之得失。
一、研究者现状
衡量一位作家研究是否繁荣的标志,首先体现在有一定人数规模的研究群体,有不断增加的新生力量,有一批在同行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量级学者。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菲尔丁研究队伍虽然不乏新人加盟,但是力量有转弱之势。尤其最近几年,卓有所成的前辈大牌学者中,除开唐尼(J. A. Downie)和罗森(Claude Rawson)偶尔发声之外,大多逐渐淡出前沿阵地。他们或者已经辞世,如谢里丹·贝克和马丁·巴特斯廷;或者不再发声,如南希·梅斯、罗纳德·保尔森、约翰·芮歇蒂、吉尔·坎贝尔等人自2012年以后均无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当前菲尔丁研究的主力军要么是新入行的青年学者,要么是专攻其他作家而偶尔涉足菲尔丁研究的中年学者,如特伦斯·鲍尔斯、多萝西·伯克、安德鲁·布里克、大卫·戴蒙德等人。这批人当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有斯科特·布莱克(Scott Black),瑞吉娜·简恩斯(Regina Janes)和罗杰·麦欧利(Roger Maioli)。但无论就成果的厚重,还是影响力的重大,他们都还难以望前辈学者之项背,尚不足以在菲尔丁研究领域执牛耳。
二、研究对象与话题
罗伯特·休漠曾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菲尔丁研究者都是小说研究专家,他们倾向于要么忽视,要么轻视他的剧作。”⑦ 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观,但变化不大,近期研究成果主要还是聚焦于菲尔丁的小说。关于《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阿米莉亚》、《江奈生·魏尔德》⑧ 和游记《前往里斯本纪行》等单部作品均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而以研究《汤姆·琼斯》的成果最多;针对其戏剧、政论、法律论文的研究,成果较少,范围较窄,话题主要涉及其政治司法实践以及他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关于他的生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则只有1篇论文。除单个作品的研究外,更多的是就多部小说进行的综合研究或者比较研究,在所统计到的42项成果中,这类研究成果有25项,占比达到近60%,这显示综合性或者对比性研究正成为大趋势。就研究话题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比较研究。就菲尔丁的小说和戏剧等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虽然一般来说也是研究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但彰显的是不同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些共性,因此宜单独作为一类来看待。这方面主要有如下话题:菲尔丁与萨拉·菲尔丁和夏洛特·伦诺克斯小说中的标题设置问题、菲尔丁的剧作《大拇指汤姆》与约翰·盖伊的剧作《阿基里斯》中的戏仿手法、斯威夫特与菲尔丁创作中对于英国内战的描写与指涉、亨利·菲尔丁、威廉·戈德温和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中的宗教信仰问题,以及菲尔丁某部作品与其他作家的某部作品的整体性对比研究。
第二,小说研究。在小说研究方面,话题可以分为五类。一为主题思想研究,主要涉及到菲尔丁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审美与伦理观念、他对自然科學的态度、作品中人物的暴力与男性气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二为艺术形式与特色研究,主要涉及到小说的史诗性、小说与史诗的关系、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与个性化问题、审美判断与小说形式问题、菲尔丁的创作与传奇文学的关系、菲尔丁的小说风格问题、表现形式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三为小说理论研究,主要从小说的演进历程中研究菲尔丁的小说,概括出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四为小说的改编问题,主要是《汤姆·琼斯》的戏剧改编问题。五为菲尔丁小说的教学方法论问题,这个话题还刚刚成为关注点,但它意味着菲尔丁小说已经在大学的文学教学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教学内容。
第三,戏剧研究。戏剧研究主要是主题思想研究,如《女丈夫》中性别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大拇指汤姆》中的喜剧性与社会历史真实性的关系。
第四,其他作品及生活史研究。这些话题一般涉及菲尔丁的政论类、法律类写作,或者他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经历。主要话题包括:菲尔丁对其他作家的批评、菲尔丁的司法实践与相关新闻报道的特点及倾向、社会和政治作用、涉菲尔丁史料研究。其中《追寻菲尔丁的脚步——一封失踪的来自莱德的信件》研究了该失踪信件的来历及其意义,指出该信件除了史料价值外,还同时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能帮助读者认识菲尔丁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人转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可以看到,菲尔丁的研究话题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主题思想研究和艺术形式与特色研究。这三个方面的选题大多是在原有选题上横向拓展,例如菲尔丁、戈德温和艾米莉·勃朗特作品中的宗教信仰问题;或者纵向上的深入和细化,例如菲尔丁的宗教观念、他对不同教派的态度,以及各种宗教理念在其作品中的反映。研究者的探索路径越来越宽,运用的理论越来越多,采用的视角越来越新。有些话题,如《汤姆·琼斯》中的暴力与男性气概之间的关系、主人公的自信问题等,为菲尔丁研究开拓了新的选题空间,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或者其他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略为遗憾的是,鲜见不同研究者就同一个话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提出诘难与反驳,这意味在研究者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性。
相对而言,小说理论、改编问题、教学方法论等方面的选题较少。菲尔丁小说理论研究是一个老话题,学界对其小说理论已经有基本共识,在缺乏新的方法论前提下,恐怕暂时难以有所突破。但小说改编问题和小说的教学方法论是崭新的领域,可供选择的话题很多,而现有的话题涉及的问题都很特别,角度很新颖,极具启发性。
三、重要论著观点述评
在40余项论著中,有近10项以视角新颖、观点独到或者理论性强而对菲尔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进或者引导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笔者对这些论著的主要观点予以概述如下:
在文体研究方面,玛丽·博克(Mary Bock)的《菲尔丁小说风格面面观》是一部理论性强、分析细致、见地独到的专著。作者运用韩礼德功能主义文体学、雅克布逊语言诗歌功能理论以及巴赫金对话与复调理论,以艾迪生和斯威夫特的创作为参照,研究了菲尔丁《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两部小说中的文体特征、美学和修辞效果及风格流变。作者指出,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菲尔丁从无处不在的自我反讽与文体模式的交互影响的风格向更自信、更严肃的作者声音风格的逐渐转变;菲尔丁的文体实践、讽刺模式、叙事风格,及其在小说序章中对理论问题的讨论,证明了他对语言和叙事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因此应将他置于18世纪关于小说语言与本质的大讨论中来看待;他倾向于将句子的并列部分写成音节和韵律数量大致相同的单位,使句法平行与语义平行相匹配,通过具有对比性和反向期待式的彼此嵌入并彼此生发的联想关系句展开段落,这使其文字看起来比斯威夫特的更典雅;他惯于给修饰语、插入语以及评价性分句披上一层意义的伪装,使语义更富歧义;他强调心理过程,反复提醒读者用自己的意识去过滤文中所表述的事实和个人观察,为此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以避免叙事者主体意识的过度张扬,寻求在叙事者与读者之间构成一种对话;其古典文学素养所造就的审美意识使他倾向于使用响度更高的对仗句和更为华美的文体,以切合他对人物思想和动机的表现、对读者情感的调动和对道德共鸣的激发;菲尔丁的语言既符合当代惯例,又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其小说语言的当代性、风格的多样性和文体意识的开放性使他对小说这一新兴文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小说理论方面,麦欧利(Roger Maioli)的专著《经验主义与早期小说理论:从菲尔丁到奥斯汀》可作为一个杰出代表。作者研究了经验主义对文学的挑战及其对18世纪小说理论的影响。他认为,一般而言,从培根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有一种观念:不认为以想象力为特征的文学可以成为可靠的知识来源。但从菲尔丁到奥斯丁的小说理论家们都认识到了经验主义的这种观念及其对文学构成的挑战,并拒绝认同和屈服。麦欧利追溯了作家们在对小说的反思中如何试图在经验世界和想象力的产物之间建立理论联系,从而在经验主义盛行的时代为文学提供富有时代性的辩护。作者认为,经验主义对文学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反应标志着长期以来关于文学与知识辩论的一个转变,是经验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持续冲突的又一个回合。
菲尔丁小说的影视剧改编问题是一个新话题。罗法尔迪·艾力(L. faldli Eli)在《屏幕上的菲尔丁:〈汤姆·琼斯〉中的作者-叙事者》一文中比较了小说《汤姆·琼斯》的两个影视改编本,即1963年由托尼·理查森制作和导演的电影和1997年由梅廷·侯赛因改编的BBC系列电视剧。作者注意到改编者一方面需要靠原作者的声誉来获得权威性和商业号召力,另一方面还必须为改编作品创造独立的艺术品格和价值。作者指出,由于《汤姆·琼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突出的“作者-叙事者”角色,因而凸显出三个概念(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作者对文本的所有权、文本自身的权威)的重要性。但在小说改编过程中,这三个概念的表达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叙事者被等同于作者,作者的身份以一种非常具体可感的方式被具象化;另一方面,作者对文本的所有权被表达得更具隐喻性,而文本的权威性则成为至始至终被关注的问题。在理查森的电影中,作者作为叙事者的角色不如在小说中那么突出,“作者权”被部分地“夺走”了,作者仅以评论性画外音的方式出现;而在侯赛因的电视里,片头的简介部分就出现了原作的封面页,以表明原作者对作品具有所有权,暗示原作者与改编者是新作的共同拥有者。作者最后指出,两个改编本对三个概念的不同处理揭示了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作者身份”的不同观念。
作品主题研究是菲尔丁小说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这方面,德怀特·科德(Dwight Codr)的《风险规避与审慎节约》一书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中的经济问题与17、18世纪晚期英国宗教、经济、伦理和文学之间的复杂交叉点。科德认为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鼓励追求经济利益并承担经济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都反对谋取“有保障”的高额利润,因为根据早期现代反高利贷文学传统和新教伦理,经济交易只有在其结果不确定时才被视为道德的。科德进一步揭示,18世纪围绕高利贷话语的核心伦理不仅具有文化上的传导性,而且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更好地理解18世纪文学主要作品的透镜。特伦斯·鲍尔斯(Terence Bowers)的《菲尔丁的奥德赛:〈汤姆·琼斯〉中的君子、新人与暴力问题》一文探讨了公共暴力与男性气概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菲尔丁作为伦敦负责处理犯罪问题的地方法官,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暴力及其破坏性对18世纪英国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而这种暴力大部分源于以男性荣誉为中心的冲突,于是在作品中塑造了汤姆·琼斯这样一种新型男性气质典范。汤姆孔武有力,与人打斗几乎战无不胜,但是除非为了捍卫正义或者维护自身安全,从不主动惹事,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欧洲骑士,被荣誉准则所驱使,为了“男性荣誉”动辄诉诸武力,从而对公民社会造成威胁。菲尔丁将汤姆塑造成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暴力冲动所驱动,更能适应后荣誉社会的现代英雄,一个西方文明传统下理想的新人,建构了新型男性范式,批判了傳统的荣誉文化,表达了他对英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期待。比尔·莱特(Bill Knight)在《菲尔丁的王尔德:庄严的场面和兽性的崇高》一文中研究了菲尔丁的《江奈生·魏尔德》,他以德里达的思想为指导考察了小说中君主、罪犯与野兽的结合方式,指出这三者的结合与互相吸引成为现代社会衰落的致命症状,使人们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崇高。论文认为该作品是对现代社会伦理与审美价值的衰落所给予的毫不留情的讽刺性评价,宣告了文化转型时期审美价值观的转变。马修·瑞斯林(Matthew Risling)在《蚂蚁、水螅虫和汉诺威老鼠:亨利·菲尔丁与大众科学》一文中就菲尔丁对18世纪逐渐“热”起来的实验科学的态度进行了详细考察。他指出,17、18世纪的文学家们一般对实验科学都不以为然,认为它是反宗教的,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加以讽刺和挖苦,甚至对从事实验科学研究者进行污名化描写,表现出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斯威夫特,而菲尔丁也是同道中人。但根据对《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及其他论著的详细考察,瑞斯林认为,与比恩、斯威夫特、约翰逊等人不同,菲尔丁其实对实验科学并不反感,他对当时的热门研究话题“水螅虫”的调侃只是幽默的逗趣而已,其作品中对实验科学的调侃是温和的、善意的;他本人科学知识丰富,对实验科学家们固然有所批评,但只是批评其中一些人的实验没有产生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批评其学术活动的内在价值;在菲尔丁看来,即使有些研究是“轻飘飘的”,但也能让人寄托性情,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知性乐趣。论文作者最后指出,虽然应该承认菲尔丁对实验科学的态度是同情的,但是也不要把他看成实验科学的积极拥护和推进者,他是一个趣味保守的人文知识分子,其态度的两重性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科学态度总体上的矛盾情绪。
作家的宗教思想研究是菲尔丁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在《世俗的菲尔丁》一文中就《汤姆·琼斯》和《阿米莉亚》中的人物所代表的宗教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这些人物身上单一的正统宗教的约束力很弱,因为在菲尔丁看来,宗教与很多东西相关,其中很多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况予以考虑,不断调整,而不可以拘泥于单一的、正统的宗教规范和理念,这种复杂性包含了宗教思想的世俗性,而菲尔丁小说世俗化的倾向也一直在形塑着小说的历史。朱迪丝·斯塔齐纳(Judith Stuchiner)在《圣经的真理与英国小说》一文中对比研究了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葛德文的《凯勒·威廉姆斯历险记》和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三部小说中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书写的价值,指出这些小说接受了同时代的布道、宗教小册子、新闻报道和《圣经》经文的影响,吸纳了其中的思想观念,因而不仅是小说,也是社会宗教和历史文本;许多有争议但在讲坛上无法辩论的宗教问题,如信仰与理性、信仰与善行、《圣经》的权威和真理性等问题,往往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更为自由充分、更具建设性的表达和探讨。在教会的权威性正在走下坡路的时代,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特别适合探讨那些容易撕裂英国圣公会教会会众的一些宗教问题,如《圣经》是“真理”吗?它是完全正确还是仅部分正确?人们如何通过信仰或理性来获取《圣经》的“真理”?如何以权威或民主的方式传达这些“真理”?如何看待《圣经》中记载的某些奇迹事件(例如复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同时代宗教文学的道德表述复杂化和世俗化,因此可以说早期的英国小说是18世纪英国从宗教世界向世俗世界过渡的重要一环。
对菲尔丁的哲学思想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展的领域。安德鲁·布里克(Andrew Bricker)在《曼德维尔之后的菲尔丁:美德、自利及“善良品格”的基础》一文中研究了菲尔丁的人性观,指出其中包含着曼德维尔人性观。作者指出,菲尔丁相信人性利他,因此无论在小说还是在论文中,都对持人性利己观的曼德维尔痛加指斥,这使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与曼德维尔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他还是深受其影响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他尝试自行定义“良善天性”时。菲尔丁和曼德维尔对于善行动机的理解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都以“自利”作为善行的出发点,而分歧在于是否把这种出于“私利”动机而做出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视为善行。在曼德维尔看来,一切善行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哪怕这种利益仅仅表现为行善时获得的一种内心满足感,而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不可称为善;同时,也不可从行动所产生的好结果来判定一个行为是善的,例如,偷窃富人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创造了治安人员的就业机会,但是偷窃显然不能被视为善行。而在菲尔丁看来,“自利”确实驱动着人类的行动,但过于强调行动的动机,则是在着眼点上犯了错误;如果行动产生了善的后果,那就是善,假如行动者从善行中得到了内心满足,那这正好证明此人天性良善。纯粹以动机判断行为,不仅抹煞了善行,也破坏了人类相互同情所产生的重要社会纽带。菲尔丁关于人类行为受私利所驱动的思想显然是在他在驳斥曼德维尔时不知不觉所接受的,而《汤姆·琼斯》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他所赞赏的沙夫茨伯里人性观与他所厌恶的曼德维尔人性观相结合的情况。
结语
近年来,专攻菲尔丁研究的前辈大牌学者陆续淡出前沿阵地,较少发表新作,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以及偶尔涉及菲尔丁研究的“客军”正成为菲尔丁研究的主力军,但他们大多尚未能确立自己在菲尔丁研究方面的学术权威和学界影响力。不过正因为如此,研究者较少受到既有研究成果的羁绊,更能够寻找新的材料和研究视角来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话题,增加其多元性和丰富性。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既有细部的比较,如菲尔丁与其他作家的小说标题设置、菲尔丁的剧作与其他剧作家作品中戏仿手法的关系,也有整体性比较,如就菲尔丁某部作品與其他作家的某部作品进行多方面对比研究等。对菲尔丁戏剧、政论类、法律类写作的研究仍然冷清,研究对象少,研究话题窄,对其小说的改编与教学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菲尔丁思想研究和小说风格研究话题丰富,探讨深入,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就代表性论著而言,博克论证了菲尔丁文体的演变及其文风的华美和独特之处,肯定了菲尔丁的文体对小说这一新兴文类的贡献,将对其创作艺术水准的评价推上了新的高峰。麦欧利从经验主义与知识的可靠性出发,提出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和理论促动了文学与有用知识之间相互关系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菲尔丁小说的艺术价值。罗法尔迪对《汤姆·琼斯》中的“作者-叙事者”角色、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作者对文本的所有权、文本自身的权威等问题的研究凸显了菲尔丁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独特性。鲍尔斯发掘出了汤姆·琼斯的 “新人”形象,彰显了菲尔丁对新型男性范式的建构和对传统荣誉文化的批判,凸显了主人公的社会伦理价值。莱特关于《江奈生·魏尔德》是对现代社会伦理与审美价值的衰落所给予的毫不留情的讽刺性评价这一观点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现实批判维度,把读者的目光引向现代社会伦理与审美价值的变化,具有突破性意义。瑞斯林指出菲尔丁对实验科学的批评旨在批评其实验没有产生有用的知识,而非批评其学术活动的内在价值,这种态度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科学态度的一般矛盾情绪,此说一反传统认知,起到了扭转方向的作用。斯塔齐纳指出菲尔丁的作品不仅是小说,也是社会宗教和历史文本,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时代宗教文学的道德表述复杂化和世俗化,此说厘清了菲尔丁的创作与当时的宗教活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以上这些观点增加了菲尔丁研究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深化了菲尔丁研究。但是有些观点虽然新颖,论证不是很有力,如科德指出在《汤姆·琼斯》中作者鼓励追求经济利益并承担经济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反对谋取“有保障”的高额利润,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力的证据。同样,布里克曼关于菲尔丁不自觉地接受了曼德维尔人性观的论断也还欠缺足够的论据和有力的论证,难以服人,有待深入论证,这当然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驳论目标。总之,这些新的研究在保持菲尔丁研究的热度、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达成研究共识方面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注釋:
① Wilbur L. Cross, The History of Henry Fielding, Vol.3,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3, p.136. 据此传言,年轻时的菲尔丁脾气暴躁,爱与人争吵;放浪不羁,常厮混于女人之间;酗酒、抽烟,是为钱折腰的雇佣文人、政治上两边倒的墙头草以及收受贿赂的法官。
② Ernest Albert Baker,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ovel, Volume 4,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67, p.191.
③ 韩加明:《菲尔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④ 期刊论文如下:Andrew Benjamin Bricker, Fielding after Mandeville: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 of “Good Nature”,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ECF), Fall 2017, 30 (1), pp.65-87; Bill Knight, Fieldings Wild: Sovereign Spectacle and the Beastly Sublime, Eighteenth Century, Spring 2018, 59(1), pp.45-63; Claude Rawson, Theatre and the Novel from Behn to Fielding, Restoration & 18th Century Theatre Research, 2016(1), pp.125; Claude Rawson, Epic into Novel: Henry Fielding, Scriblerian Sati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 Spring 2016, 28(3), pp.603-607; David Diamond, Secular Fielding, ELH, Fall 2018, 85(3), pp.691-714; David Lemmings, Henry Fielding and English Crime and Justice Reportage, 1748-52: Narratives of Panic, Authority and Emotio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Studi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pring 2017, 80(1), pp.71-97; Dorothee Birke, Direction and Diversion: Chapter Titles in Three Mid-Century English Novels by Sarah Fielding, Henry Fielding, and Charlotte Lennox,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33; Frederickg Ribble, In the Footsteps of Henry Fielding: A‘LostLetter from Ryde,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39-40; Jakub Lipski, Bodily Spectacle and the ‘Curseof Traveling in Henry Fieldings Journal of a Voyage to Lisbon,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36-37; Judith Stuchiner, Fieldings Latitudinarian Doubt: Faith ‘versus Works in Joseph Andrews, Studies in Philology, Fall 2017,114(4), pp.875-895; Kathleen E. Urda, Escaping type: Nonreferential Character and the Narrative work of Henry Fieldings? Tom Jones, Philological Quarterly , Spring2017, 96(2), pp.219-2; Lisa OConnell, MumBudget: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rticulations of Audibility, Republics of Letters, 2017, 5(2), pp.1-10; Lfaldli Eli, Staging Henry Fielding: The Author-Narrator in Tom Jones On Screen, Authorship, 2017, 6(1), pp.1-14; Matthew Risling, Ants. polyps. and Hanover Rats: Henry Fielding and popular science, Philological Quarterly, Winter 2016, 95(1), pp.25-44; Nancy A Mace, Refashioning the Epic for Eighteenth-Century Consumers in Henry Fieldings Novels,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018, 42(1), pp.121-123; Przemyslaw Ski, The Mocking Theatre: Parody in John Gays Achilles and Henry Fieldings Tom Thumb, The Scriblerian and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87-88; Regina Janes, Henry Fielding Straddles a Moving Theme,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35-36; Roger Maioli, Empiricism and Henry Fieldings Theory of Fiction,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37-38; Sarah Nicolazzo, Henry Fieldings The Female Husband and the Sexuality of Vagrancy,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 2017, 49(2), pp.6-7; Scott Black, Epic into Novel: Henry Fielding, Scriblerian Sati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Autumn 2016, pp.130-132; Shaun Regan, Epic into Novel: Henry Fielding, Scriblerian Sati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17, 40(3), pp.466-467; Stephen Rayni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Novels of Henry Fieldin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pring 2017, 14(1), pp.113-114; Sunardi Sunardi, Darman Sitepu, Zulfan Sahri, Self-Confidence in Henry Fieldings Novel Tom Jones, Language Literac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2017(1), pp.141-162; Terence N. Bowers, Fieldings Odyssey: The Man of Honor, the New Man, and the Problem of Violence in Tom Jones, Studies in Philology, Fall 2018, 115(4), pp.803-835; Yuko Engetsu, Is the World a Masquerade or a Theatrical Stage: A Study of Henry Fieldings Criticism of John James Heidegger, Scriblerian & the Kit-Cats, Spring 2018, 50(2), pp.17-20.
⑤ 此類论文如下:Elena N. Penskaya, Fieldings Farces: Travestying the Historiosophical Discourse, IN Jo-achim Küpper, Jan Mosch, Elena Penskaya (eds.), History and Drama: The Pan-European Tradition, De Gruyter, 2019, pp.101-111; J. A. Downie, Clarissa and Tom Jones IN Thomas Keym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Novel in English: Volume 1: Prose Fiction in English from the Origins of Print to 1750, Oxford UP, 2017, pp.563-578;John Richetti, Formalism and Historicity Reconciled in Henry Fieldings Tom Jones IN Liisa Steinby, Aino M?覿kikalli (eds.), Narrative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79-97; Jukka Tiusane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Faction: Civil War in Swift and Fielding IN Mihaela Irimia et al.(ed.)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Memory, Brill, 2017, pp.173-187;Michael McKe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allenge to Narrative Theory IN Liisa Steinby, Aino M?kikalli (eds.), Narrative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9-77;Monika Fludernik, Perspective and Focaliz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Descriptions IN Liisa Stein by, Aino M?覿kikalli (eds.), Narrative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99-119; Rebecca Tierney-Hynes, Epic into Novel: Henry Fielding, Scriblerian Sati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Studies in the Nove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37-138; Regina Janes, Incipience: Inventing Genres; Or. Henry Fielding Makes It a Habit IN Crowe, Nicholas J.(eds.), The Ways of Fiction: New Essays on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ewcastle upon Tyne, England: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8, pp.108-130; Richard N. Ramsey and Robert M. Otten, Henry Fielding, IN Critical Survey of Drama, 3rd Edition, 2017, pp.1603-1615; Scott Black, Henry Fielding and the Progress of Romance IN Downie, J. 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Oxford, England: Oxford UP, 2016, pp.237-251; Thomas Trzyna, Henry Fielding and the Problem of Forgiveness IN Karl Popper and Literary Theory: Critical Rationalism as 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7, pp.80-100; Vivasvan Soni, Judging. Inevitably: Aesthetic Judgment and Novelistic Form in Fieldings Joseph Andrews IN Brodsky, Claudia (eds.); LaBrada. Eloy (ed.); Inventing Agency: Essays on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Production of the Modern Subject,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pp.201-223.
⑥ 专著如下:Dwight Codr, Risk Aversion and the Economization of Prudence: Fielding, Gambling, Gifts, Raving at Usurers: Anti-Finance and the Ethics of Uncertainty in England, 1690-175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6; Henry Knight Miller, Essays on Fielding Miscellan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59(1); Mary Stewart Bock, Aspects of styl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Fielding,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16; Roger Maioli, Empiricism and the Early Theory of the Novel: Fielding to Auste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Judith Stuchiner, Scriptural “Truth”and the English Novel: Henry Fielding, William Godwin, and Emily Bronte, Fordham University, 2017.
⑦ Robert D. Hume, Fielding at 300: Elusive, Confusing, Misappropriated or (Perhaps) Obvious?, Modern Phil-ology, 2010, 108(2), p.224.
⑧ 菲爾丁的小说“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Joseph Andrews”,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Amelia”有不同译名,本文取最简单的译名,分别为《江奈生·魏尔德》、《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阿米莉亚》。
作者简介:朱宾忠,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杨文慧,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