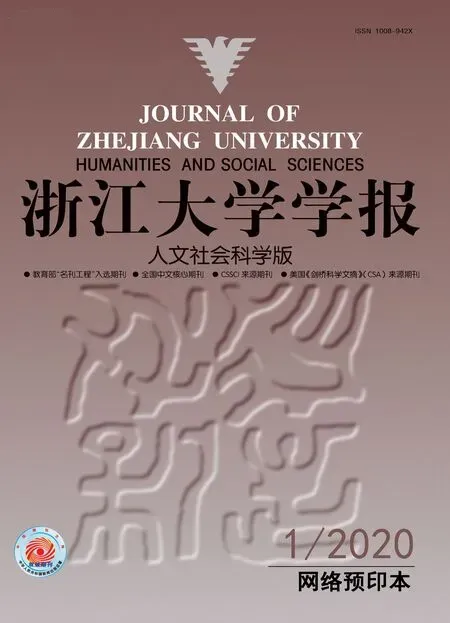俄国形式主义在法国的早期接受及其影响
曹丹红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015年10月8日至10日,纪念俄国形式主义诞生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召开。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帕维尔(Thomas Pavel)、皮尔(John Pier)、谢弗(Jean-Marie Schaeffer)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2018年11月,《交际》(Communications)杂志第103期出版专号“俄国形式主义一百年后”,刊发了由德普雷多(Catherine Depretto)、皮尔和鲁森(Philippe Roussin)编撰结集的研讨会论文。这两起事件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揭示了当代法国诗学(1)受字数限制,本文不拟对“当代法国诗学”的外延与内涵展开讨论,具体可参见笔者所撰《今日诗学探索之内涵与意义》(载《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第153-160页)、《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综述》(载《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第90-96页)等论文。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深刻关联。回顾法国文论发展史,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形式主义对法国当代诗学诞生与发展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最初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接受,法国诗学就不可能形成今日的局面。本文将以这段最初的接受史为考察对象,就俄国形式主义对法国当代诗学的主要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
一、 两位摆渡人:列维-斯特劳斯与托多罗夫
德普雷多、皮尔和鲁森在《交际》专号的卷首“介绍”中指出,“形式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运动,‘形式主义’这一术语指称的是某个整体,这一整体内部的人物之间及研究成果之间均存在极大差异”[1]7。从起源看,1915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起成立莫斯科语言学小组,1916年,什克洛夫斯基(Viktorklovskij)、蒂尼亚诺夫(Iouri Tynjanov)、艾亨鲍姆(Borisjxenbaum)、托马舍夫斯基(Boris Tomasševskij)等人创建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形式主义就此诞生(2)有关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时间存在诸多争议,也有学者认为形式主义起源于1914年左右,参见Wellek R., ″Preface,″ in Erlich V., Russian Formalism,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p.9-10; Robel L. et al., ″Présentation,″ in Tynianov I. (ed.), Le vers lui-même: Les problèmes du vers, traduit du russe par Jean Durin et al.,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7, pp.7-33。。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三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交际》杂志第103期刊发了三人未出版过的通信录,这些信件表明,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末俄国形式主义行将终结之时,他们仍在雄心勃勃地规划形式主义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也解释了两个团体的成员及其研究往往被相提并论的原因。形式主义本身在俄国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加上一段时期内世界格局及欧洲政治气候影响了学术交流,导致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法国等西欧国家熟悉。
对于形式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列维-斯特劳斯与托多罗夫二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列维-斯特劳斯是法国学者中较早接触到形式主义的。1941年,他在纽约遇到雅各布森,在与后者的交往中了解到音位学与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民间故事研究,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真正走上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之路,极大地推动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1960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结构与形式》一文,对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进行深入解读,并对普洛普在其中提出的理论假设予以高度评价:“如此丰富的直觉,它们的洞察力——它们的预见性——令我们赞叹不已,为普罗普赢得了所有那些并不认识他的追随者的忠诚。”[2]126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普洛普从此进入法国学者视野,在20世纪60—70年代对格雷马斯(A.J.Greimas)、布雷蒙(Claude Bremond)、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托多罗夫等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列维-斯特劳斯等学者的推介下,雅各布森尤其是普洛普的思想已被法国学者所熟悉。普洛普其实并不属于俄国形式主义团体,列维-斯特劳斯对此心知肚明,例如他在《结构与形式》一文中提到《故事形态学》时指出:“该书的思想与大致从1915年到1930年这一短期间内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思想非常相近。”[2]115但他很快便不顾这一说明,将普洛普完全当作形式主义者的代表。不久之后,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认识,这部著作便是托多罗夫编选、翻译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1965,以下简称《文学理论》)。
托多罗夫是令俄国形式主义真正传入法国的摆渡人。1965年,托多罗夫在列维-斯特劳斯、本伍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人创办的《人类》(L’Homme)杂志发表长文《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遗产》,详细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托多罗夫认为,形式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将语言学概念与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例如将文学视作一个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并通过系统概念来思考文学要素的意义与功能,借助语言学的区别性特征和语言功能概念来分析词语意义、寻找文学基本单位、划分文学类型、揭示类型之间的转换规律,运用计量的方法来分析诗歌的韵律与节奏等等[3]。托多罗夫还将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与当代语言学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前者的超前性,并思考了其对语言学及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启示。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由托多罗夫编撰的《文学理论》也出版面世,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方法论遗产直接呈现于法国读者面前。《文学理论》是托多罗夫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国对形式主义者的‘发现’始于《文学理论》的出版”[4]54。在这部文集中,托多罗夫选择翻译了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人的14篇论文,并对文选的作者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中还收录了普洛普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神奇故事的衍化》。尽管这14篇论文只是形式主义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这是法国公众第一次看到这些作者的成果被集中在一起出版,他们被冠以‘形式主义者’的称呼”[5]41。《文学理论》的出版为当时的法国文学及理论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打开了法国学人的视野,促使他们“从此能够对某段并不久远的过往有所了解,法国学者虽直接继承了这段历史留下的遗产,却奇怪地对这段历史本身一无所知”[6]13。
在列维-斯特劳斯、托多罗夫等学者的推动下,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成果陆续被翻译成法语,除上文提到的《故事形态学》(1970),还有什克洛夫斯基的《马步》(1973)、《散文理论》(1973),雅各布森的《诗学问题》(1973),蒂尼亚诺夫的《诗歌语言问题》(1977),以及多篇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这些文章和论著被译介至法国后,很快被法国学者模仿、改造、吸收,成为法国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促进了叙事学的确立与文学类型研究的发展。法国学界对形式主义遗产的吸收不仅体现于对其文学研究核心概念和主题的拓展与深入,更体现于对其研究方法及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一转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决定了法国诗学的特征与走向,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二、 叙事学的诞生
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分支,因诞生于巴特、托多罗夫等人的诗学研究中,故而常常被等同于狭义的诗学。亚当(Jean-Michel Adam)在著作《叙事》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普洛普、托马舍夫斯基、艾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奠定了叙事学的基础[7]3。形式主义者的这一贡献至今也没有被否认,例如皮尔发表于《交际》杂志的文章《叙事的世界与符号域》开门见山地指出:“毫无疑问,20世纪60—70年代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叙事文结构分析从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接受中获得了重大推动力。”[8]265
亚当提到的形式主义者中又以普洛普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佛克马(Douwe W.Fokkema)与易布思(E.Kunne-Ibsch)对此有较为深入的分析[9]67-78。亚当也描述过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界的普洛普热:格雷马斯于1963—1964年在亨利·庞加莱学院开设语义学课程讲授普洛普的理论,并于1966年出版讲义《结构语义学》;布雷蒙于1964年在《交际》杂志发表《叙事信息》;托多罗夫于1965年编《文学理论》;奠定叙事学基础的《交际》杂志第8期出版等[7]5。普洛普热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在其影响下取得的成果包括格雷马斯的《论意义》(1970)、热奈特的《叙事话语》(1972)、布雷蒙的《叙事逻辑》(1973)以及托多罗夫的《诗学》(1968、1977)、《〈十日谈〉的语法》(1969)和《散文诗学》(1971、1978)。在此过程中,“叙事学”一词被创造,一门新的学问终于有实有名。
关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普洛普的吸收与改造,前人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不再详述。普洛普对法国叙事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功能”理论。他对前人收集的几百个俄罗斯民间故事展开分析,找出了其中的不变因素与可变因素,进而对不变因素也就是角色的功能展开研究,最终提炼出31项功能,认为其囊括了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所有功能。这种从表面形式繁复的材料中归纳出不变因素,或者说从整体中提取结构的做法给了法国学者以巨大启发,促使他们在借鉴、批评、修正、发展普洛普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例如布雷蒙将普洛普的单线程模式改造成“多声部合唱”,并强调了被普洛普忽略的人物行动及心理元素,使分析模式能适用于更复杂的文学文本。格雷马斯提出施动者(或译行动元)概念,系统化了普洛普提到但并未重视的“角色”概念,将普洛普的31个功能缩减至3个基本功能范畴(契约、考验、交际),又提出一个颇具特色的转换模式来分析施动者的状态。施动者模式与转换模式的提出使得格雷马斯能超越民间故事素材,对更为广泛的叙事文、其他符号体系甚至文化的基本结构、深层意义及其价值展开分析。
不过,普洛普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虽大,却不是后者的唯一来源,如巴特、托多罗夫与热奈特的研究便体现出普洛普以外的俄国影响(3)《文学理论》收录的是普洛普的《神奇故事的衍化》,而非当时影响更大的《故事形态学》节选。1970年《故事形态学》法译本面世,托多罗夫翻译的《神奇故事的衍化》也被收录其中。国内学界关注更多的也是普洛普对法国诗学的影响。例如,张寅德在1989年出版的《叙述学研究》“编选者序”中已富有洞见地将叙事学研究分为叙事结构研究和叙述话语研究,但张寅德仅指出普洛普理论对叙事结构研究的影响,没有提及俄国形式主义对叙述话语研究的影响。。巴特发表于《交际》杂志第8期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往往被视作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奠基之作,除普洛普以外,文章不断提及托马舍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贡献。
再看托多罗夫与热奈特的研究。两人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很容易解释:热奈特属于托多罗夫初到法国结识的第一批学者,两人志同道合,合作密切,热奈特全程参与了《文学理论》的素材选择与翻译出版工作。《文学理论》选译的托马舍夫斯基的《主题》一文对两人的影响超过了普洛普。在《主题》中,托马舍夫斯基对“本事”与“情节”这组对立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整个一部作品里,我们获知的彼此相互联系的全部事件,就称为本事。本事可以按事实因果关系的方式,按照自然的顺序展开,也就是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顺序展开而不受任何安排事件和写入作品的方式的制约。本事和由同样事件构成的情节是对立的,但是情节遵循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顺序和表明事件的材料的连贯。”[10]238-239对这段话,托马舍夫斯基添加了一个注释:“简单地说,本事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情节是读者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10]239同一部作品之所以可以从本事或情节的不同角度去理解,是因为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作品是最小主题单位“动机”(motif)(4)或译“细节”,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的组合,动机可按两种方式进行组织,一种按事件发生先后顺序和因果逻辑组合成本事,另一种按动机在作品中出现的顺序组合成情节。如果说本事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不受作者叙述影响,那么“情节则完全是艺术性的结构”[10]240,因为它是作者对动机的重新编排。
《文学理论》出版后不久,托多罗夫在《文学叙事的范畴》一文中特别提到托马舍夫斯对本事与情节的区分:“俄国形式主义者最先提炼出两个概念,将其命名为‘本事’(‘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和‘情节’(‘读者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第268页)。”[11]126-127尽管托多罗夫没有采用托马舍夫斯基的术语,而是受本伍尼斯特影响,将这组对立概念另外命名为“故事”与“话语”,但他对“故事”与“话语”的界定基本沿用了托马舍夫斯基的定义。
在提出本事与情节的区别后,托马舍夫斯基又分别对此二者进行了探讨。在本事方面,他列举出一系列与本事发展关系或密或疏的动机。在情节方面,他提到叙事时间与本事时间之间的错位,以及作者、叙述者、人物之间的认知差异等问题,几乎可以说确立了一种叙事学的雏形。托多罗夫在《文学叙事的范畴》中正是从叙事的故事方面和话语方面发展了托马舍夫斯基的理论,对于前者,他用“行动”一词取代了托马舍夫斯基的“动机”,并归纳出故事的几种行动逻辑;对于后者,他细分出叙事的时间、语态、语式等几大范畴。有关这些问题,托多罗夫在两年后出版的《诗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叙事学框架,并对热奈特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热奈特在1972年出版了之后成为经典叙事学奠基之作的《叙事话语》。
三、 文学类型研究的发展
文学类型或体裁划分也是托多罗夫提到的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之一。文类研究在西方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说是对悲剧与史诗两大文类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对文类的思考一直在诗学与美学领域占据中心位置。至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的发展促使文类研究的地位被文学史和文学社会学取代。俄国形式主义可以说实现了文类研究的复兴。法国当代诗学在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在文类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而这些新进展在托多罗夫看来是古典诗学未能成功实现的。
实际上,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本质与功能的思考往往是基于某种特定文学类型展开的,艾亨鲍姆指出,“从一开始,诗歌语言体系和散文语言体系之间的区别便决定了形式主义者的研究工作,后来又影响到许多根本问题的讨论”[10]28-29。毋宁说,对形式主义者来说,思考文学类型本质与思考文学本质是同一个问题,蒂尼亚诺夫的名篇《文学事实》即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类型”[12]212这两个问句开篇,《论诗句》(托马舍夫斯基)、《论散文理论》(艾亨鲍姆)、《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诗歌语言问题》(蒂尼亚诺夫)等名称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从这些文章和论著中管窥到俄国形式主义文类研究的下述特征:首先,托多罗夫批评“古典诗学一直没能成功地对体裁进行逻辑分类”[13]10,这一缺陷在形式主义文类研究中得到了弥补。形式主义者尝试从文类内部提取区别性特征,或者说尝试寻找“类型基本构成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14]37,将其作为文类划分的依据,这种方法总的来说是描述式的,与规约式的古典诗学有着根本区别。在当时,雅各布森、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对诗句构成要素的思考,普洛普对民间故事结构的探索,什克洛夫斯基对叙述方法的类型划分等,都体现了形式主义者探索文类基本结构的努力[10]7-8。其次,形式主义的散文研究明显侧重对叙事情节发展机制的探索。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研究即是一个典型例子。从《文学理论》收录的论文看,什克洛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结构》和艾亨鲍姆的《论散文理论》探讨了长短篇小说在情节结构原则方面的差异,托马舍夫斯基的《主题》一文特别提到侦探小说这一类型,启发托多罗夫写出名篇《侦探小说类型学》。实际上,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对侦探小说情节结构机制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散文理论》法译本出版时间虽晚于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但托多罗夫在《文学理论》“编选说明”中已提及这部著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散文理论》启发了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及其他文章和论著。最后,形式主义文类研究体现出一种体系观。提出这一观念的是蒂尼亚诺夫,他明确指出:“如果脱离文学类别处在其中并与之类比的体系,是不可能研究文学类别的。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不仅仅和扎戈斯金的历史小说进行类比,而且和他同时代的散文进行类比。”[10]107也就是说,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学类型没有意义,因为文学类型的区别性特征或者说功能是文学体系赋予的。由体系观又衍生出两种观念:演变与差异的观念。从演变来说,文类特征并非一成不变,这点不难理解;从差异来说,“人们从来不脱离文学现象的类比来考虑文学现象。我们举散文和诗歌作例子。不言而喻,我们都认为有格律的散文仍然是散文,没有格律的自由体诗依然是诗歌,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在某些文学体系里就很难自圆其说。这是因为散文和诗歌是互相类比的”[10]107。这种体系观也体现于其他形式主义者的研究中,比如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在探讨长短篇小说结构法则时,采取的都是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
形式主义的文类研究观念和方法得到了法国诗学研究者尤其是托多罗夫的继承与发展,后者的《散文诗学》或许正是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的呼应。在类型研究中,托多罗夫也往往借助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大的类型来看,在《叙事文的两大原则》一文中,他通过对比叙事与描写探讨了前者的结构特征。他认为叙事与描写的最大差异在于对时间的处理:“开头的描写确实处于某种时间背景中,但这一时间是不间断的,相比之下,叙事特有的变化将时间切分成彼此不相连的单位。纯粹延绵的时间与事件性的时间形成了对立。”[14]64他进而将叙事变化归纳为“接续”与“转换”两种[14]66。从次级类型来看,他的侦探小说研究、奇幻故事研究也都遵循同样的思路。《侦探小说类型学》按“犯罪的故事”与“侦破的故事”在小说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侦探小说分为推理小说、黑色小说与悬疑小说:推理小说重前一个故事,吸引读者从结果出发还原犯罪经过,找到犯人解开谜团;黑色小说重后一个故事,吸引读者关注侦探的活动及命运;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悬疑小说。此外,《侦探小说类型学》认为侦探小说是按照从推理小说到悬疑小说的进路发展的,充分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演变观的影响。在《奇幻文学导论》(1970)中,作者为界定奇幻文学这一类型,将其同另两个类型即怪谈与神奇故事进行了对比,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当故事确实涉及超自然因素,文本便属于神奇故事类型;当完全不涉及超自然因素,所有怪异现象均能得到科学解释时,文本便属于怪谈类型;而模棱两可、兼具此两种解读可能性的便是奇幻文学。这两种研究也是托多罗夫对体裁进行逻辑分类的尝试。
与形式主义散文理论一样,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也偏重叙事研究,更确切地说,正是在探索散文区别性特征的过程中,产生了最初的叙事学建构。《散文诗学》收录的文章大多有关叙述进程与情节结构。此外,托多罗夫还受普洛普等人的“转换”理论启发,思考了“叙事转换”与文本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可以根据某种转换的数量或质量优势确定文本性质”[13]162,“转换的概念……能帮助建立基本的文本类型学”[13]162。以中世纪民间故事《圣杯的寻觅》为例,在故事中,“一方面,所有发生的事都是被预言的;另一方面,事情一旦发生,便得到一种新的阐释”[13]162,这两方面涉及圣杯故事的叙事转换特征。与此同时,根据托多罗夫的构想,可将此类叙事转换占主导地位的文本都视作《圣杯的寻觅》的同类型作品。
托多罗夫的努力促使文类研究成为当时法国诗学的显学,除他本人的《散文诗学》《话语类型》(1978)外,热尔(André Jolles)的《简单形式》(1972)、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的《自传契约》(1975)、杜布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的《论自我虚构的文字》(1977)、热奈特的《广义文本导论》(1979)和文集《文类理论》(1986)等相继出版,且大多被收入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主编的“诗学”文丛。直至今日,文类研究仍然是法国《诗学》杂志与“诗学”丛书中最常见的一类研究。与此同时,20世纪60—70年代文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又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影响。例如,巴罗尼(Rapha⊇l Baroni)的《叙事的张力:悬念、谜团与意外》(2007)是近年来法国诗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著作对叙事张力也即故事对读者的吸引力进行了考察,将张力来源归结为情节发展所制造的悬念、谜团与意外等,明显体现出什克洛夫斯基和托多罗夫的影响,也体现出形式主义文类研究思想与方法的生命力。
四、 “文学性”研究的复兴与“理论”建构的盛行
法国当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学性”的关注与探索,这一点明确体现于其对“诗学”的界定中:“诗学不同于具体作品阐释,它并不试图点明意义,而是尝试去认识在每部作品诞生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普遍法则;诗学也不同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因为它尝试去文学内部寻找这些法则。”[15]19正因其研究对象是“普遍法则”,故“诗学这一科学不再关注现实的文学,而是可能出现的文学,换句话说,它更关注赋予文学事实以特殊性的抽象属性,即文学性”[15]19-20。从文学内在法则来研究文学,这种主张早已有之,在现代法国至少体现于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瓦莱里(Paul Valéry)等人的诗学思考中。只不过,上述定义中,托多罗夫对“文学性”这一术语的使用及对“文学性”概念的理解恰恰都承袭自俄国形式主义。佛克马与易布思也曾指出,“托多罗夫的方法比其他学者的更多涉及文本。除此之外,他不断地做出努力去确定文本的文学性,这是一项我们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熟悉的工作”[9]76。“文学性”一词首次出现应是在雅各布森写于1919年、出版于1921年的《俄国新诗歌》中,雅各布森在其中称:“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某个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6]16在法国,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文学理论》编选的艾亨鲍姆文章《“形式方法”的理论》,之后被托多罗夫引用在《诗学》中(5)托多罗夫之后节译《俄国新诗歌》,发表于他与热奈特主编的《诗学》杂志1971年第1期,不久后又将其收入雅各布森文集《诗学问题》,该文集于1973年作为他与热奈特主编的“诗学”丛书之一出版。托多罗夫的长文《诗学》发表于1968年,比他节译的《俄国新诗歌》的发表早三年,但他在为《文学理论》撰写的“编选说明”中介绍了雅各布森的《俄国新诗歌》一书,并指出这部评论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著作翻译难度很大。这可能是著作片段没来得及被选入《文学理论》的一个原因。。而对“文学性”的兴趣在法国学界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6)最具代表性的是热奈特的研究,参见Genette G., Fiction et diction, Paris: Seuil, 1991。。
不过,法国学界对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接受并非简单地引入“文学性”等几个术语与概念,从更深层次说,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意图。“科学”是形式主义者笔下常出现的一个词,它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明确性(文学科学的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借用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甚至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既不神秘化也不庸俗化研究对象)。这些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支撑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学者向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发起挑战,提出更为科学、客观地研究文学的主张,促成了20世纪60—7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巴特在1966年出版的《批评与真实》中提出建立“文学科学”的设想,他援引雅各布森的言论,将旧的文学批评视作“一种亲切的漫谈”[17]40。这一言论出自《文学理论》收录的雅各布森论文《艺术中的现实主义》,雅各布森原话为:“就在不久之前,艺术史尤其是文学史还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causerie(漫谈)。”[10]79他随后考察了传统艺术理论家在使用常见术语“现实主义”时的随意性,呈现了传统艺术史为何不是科学而是“漫谈”的问题,同时也间接表明了建立“科学的术语”[10]79的主张。此外,雅各布森为《文学理论》撰写的序言题目为“诗学科学的探索”[10]1,文中反复提到“科学”一词,不断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我们不难在雅各布森与巴特的主张之间看出一种连续性。
其次,是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形式主义者或多或少受过语言学的影响,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借用直言不讳,且有些学者主要从事的就是语言学研究。因而,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诗学也深深烙上了语言学的印记。我们已在《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遗产》一文中看到托多罗夫对语言学方法的重视,他本人的叙事文研究也借助了大量语言学术语与概念。巴特也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到,要对叙事话语进行分类和描写,首先需要建立一种理论模式,“如果我们在入手时就遵循一个提供给我们首批术语和原理的模式,就会使这一理论的建立工作得到许多方便。按照研究的现状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似乎是适宜的”[18]4-5。为此他建议在叙事话语和句子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借用通常只用来分析句子成分的语言学术语与方法对超越句子的话语展开分析。
这一时期对法国学界影响最深的还是雅各布森及其《普通语言学论文集》。这部著作的法译本由语言学家鲁威(Nicolas Ruwet)从英文版译出,于1963年在子夜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为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界带来一场思想革命,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甚至认为这部著作对法国学界的影响超过其他所有形式主义者的成果[19]。在该著作中,雅各布森发展了由索绪尔提出但直至那时还不为人熟知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历时与共时、联想关系(选择/相似性/隐喻)与句段关系(组合/毗邻性/换喻)(7)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使用的术语,今人所熟悉的术语纵聚合与横组合由耶姆斯莱夫(T.L.Hjelmslev)在索绪尔研究基础上提出。等,同时提出了语言功能、对等原则、平行结构等振聋发聩的概念。著作出版后产生很大反响,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特都为其撰写了书评,并将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概念和理论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例如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在区分叙事话语中的“功能”与“迹象”这两种功能单位时,借用了雅各布森的横组合/换喻、纵聚合/隐喻的概念,在分析“催化”功能、叙述者/读者关系时则借用了雅各布森的语言功能理论。从巴特等人的研究来看,雅各布森提出的语言六大功能、选择/组合等理论确实成为当时法国诗学研究者进行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时的重要工具。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迫切性。语言学方法并不是当时法国诗学研究者运用的唯一方法,例如热奈特更多借鉴了修辞学,里夏尔(J.-P.Richard)更多借鉴了精神分析学等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研究者几乎都表现出对理论的信心,以及进行理论建构的迫切心情。巴特即指出:“为了对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进行描写和分类,必须要有一种‘理论’……当务之急就是去寻找,去创建。”[18]4实际上,贯穿当时文类研究的也是同一种理论建构的尝试。这一倾向既自发地产生于科学研究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所致。形式主义者对理论的追求甚至体现于其文章和论著的标题,例如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小说理论》、艾亨鲍姆的《论散文理论》、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等。托多罗夫后来提到,“我认为在形式主义者的作品中读到了一种‘理论’的构想,即建立一种诗学”[20]94。他与热奈特之后确实将这一理论研究命名为“诗学”,同时在1970年创建了《诗学》杂志并主编“诗学”丛书,杂志与丛书的创立相当于给法国当代诗学颁发了一张“出生证”,极大地改变了法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促使“文学研究的整个概念框架重新确立”[21]7。
历史地看,《文学理论》出版之前,“理论”对当时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很陌生的字眼,他们更为熟悉的是“文学史”“文学批评”甚至“生理学”。正如托多罗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那样,他初到法国时,想学习“文学理论”“文体学”或“文学形式研究”,却被告知法国大学并无这样的学科与课程[22]72。《文学理论》出版后,瓦尔(François Wahl)为其撰写的书评发表于《文学半月刊》(Laquinzainelittéraire)的“文学史”栏目,因为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栏目。从这个角度看,恰恰是《文学理论》的出版将“文学理论”这一术语与概念引入法国,无怪乎今日仍有不少法国学者将“文学理论”理解为20世纪60—70年代盛行的形式主义文论,并因其过于追求科学性与系统性、抹杀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而对其持有负面评价。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赋予文学理论更为明晰的外延与内涵,促使其最终能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实践并举,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其贡献与价值不容抹杀。
五、 结 语
以上我们从叙事学、文类研究、文学科学构想等几个方面简要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传入法国之初被法国学者接受、继承与发展的状况。需要注意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要比这批法国学者理解得更为丰富。仅从研究对象来说,托多罗夫等人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但鲁森在回顾形式主义的法国接受历程时指出,“形式主义者共同聚焦的实际上不止一个对象,而是几个对象”[23]74。比如,形式主义者曾写下大量谈论电影的文字,催生了最早期的电影理论。埃斯帕涅(M.Espagne)因而指出,“形式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总的来说非常具有局限性和选择性”[24]147。
这种局限性与选择性深受20世纪60年代法国本土学术环境及政治环境、法国语言学及文学批评传统、译介者身份与立场甚至文献材料获得难易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过来,最初翻译、介绍与阐释俄国形式主义的法国学者也塑造出法国式的“俄国理论”。以《文学理论》为例,被引进法国的“俄国理论”深受译介者本人的视野与思想影响,最终结果是“赋予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宣称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的诗学及文学理论以一个历史,一种谱系。俄国形式主义者成为结构主义者和文学先锋派的先驱”[19]。
然而,尽管存在译介与接受的局限性和选择性,俄国形式主义无疑对诗学在当代法国的复兴与发展起过巨大作用。对这段接受史进行全面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法国诗学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途径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吸收,以便厘清当代法国诗学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廓清当代法国诗学的外延与内涵,理解其理论与方法的适用性,认识其问题的根源及可能的解决之道,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解读俄国形式主义,从而在当下实现对法国诗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更为有效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