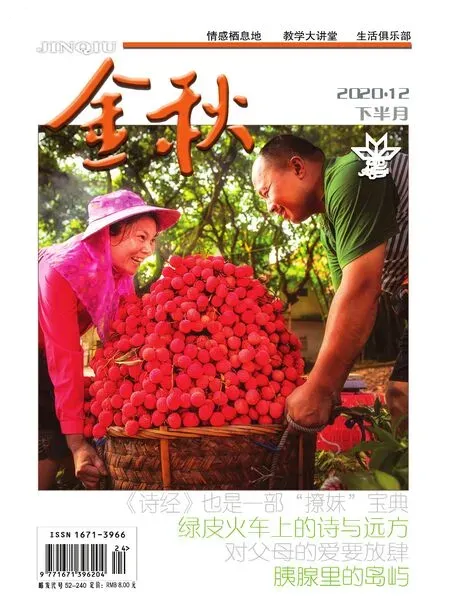魂牵梦绕老院子
文/刘世河

人老多健忘,唯不忘故乡。最近两年,我梦见最多的就是老家的那座老院子。从呱呱坠地到初中毕业,整整14个年头,我都是在那个院子里度过的。
老院子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院龄”要年长我好多岁,早在父亲将母亲娶进门的那一年就建成了,设计和建造者是爷爷。爷爷这一辈是单传,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所以后继要有人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夙愿。当父亲、二叔、三叔相继出生以后,奶奶说爷爷原本有点微驼的背竟然越来越挺拔了。弟兄仨年龄相差无几,一转眼就都长大成人了。爷爷说,三个儿子就是三个小家庭,加上他和奶奶,一共四家,每家三间屋,正好一座四合院。四个小家聚在一起抱团过日子,又热闹又有人气,尤其到了晚上,我从窗户里往外一看,四个屋里都亮着灯,多好!
四个屋里都亮着灯的情况,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最小的三叔也已娶妻,就住在东厢房里。二叔一家住北屋,我们家住西厢房,爷爷和奶奶则住在南屋里。南屋爷爷特意留了后门,为的就是走动方便。房子都是一样白灰到顶的平房,东厢房的南墙正好对着大门口,从墙根到大门口是一条将近二十米长的甬道。大门也是白灰到顶的门楼,虽然白灰里面都是土坯垒就的墙,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座院子在我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村里已经颇为壮观了。甬道的东边是一个园子,我们叫它东园子,园子里有十几棵枣树,一到秋天,满树红彤彤的枣儿煞是喜人。枣儿除了过年蒸年糕,还有一种吃法堪称绝妙,那就是母亲亲手制作的“醉枣”。制作此物选枣很重要,不能有半点破皮儿,需爬上树一颗一颗地摘,而且还得是七成熟,留下的那三分要在坛子里边慢慢膨化慢慢熟。等到腊月底,母亲掀开坛盖,那可是儿时最幸福的时刻。西厢房的后边也是一个园子,我们叫它西园子,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小菜园,有七八棵香椿树、两棵石榴树,其余的空地用来种一些时令的青菜。
南房的前边还有一个小院,院子里有一棵洋槐,树冠很大,树荫差不多能罩住大半个院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爷爷常在树下喝茶,而我就喜欢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爷爷喝茶。那时候,我记得别人家用的一般都是那种又胖又高的粗瓷大提壶,抓一把茶叶末撒在里边,然后倒在大碗里两手捧着喝。爷爷用的却是那种很精致的青花细瓷茶具,水也必是刚烧开的,而且是专门用那个生铁的炉子烧。爷爷说,喝茶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所以不能跟刘姥姥似的海饮,要慢慢品才行。还对我说过许多诸如“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之类的话。彼时年幼,直听得云里雾里。如今人到中年,才终于恍然,爷爷其实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后来我常想自己现在之所以有了这个不可一日无茶的嗜好,定是得了爷爷的真传。
除了在洋槐树下看爷爷喝茶,还有一件糗事记忆犹新。当时不知为什么,二叔家的大水缸偏偏放在院子里,而且一半在地底下,一半露在外边。有一次,我突发奇想,便趁大人们都不在家的空当,将二叔晾在窗台上的一双臭鞋扔进了水缸。当大人们下地回来,要舀水做饭时,便发现了水缸里的鞋子,好端端的一缸水就这样被我糟蹋了。母亲气坏了,抄起烧火棍就要打我,我鬼哭狼嚎地赶紧跑到院子里,正好与二叔撞了个满怀。我心想,这下完了,俩大人这是要联合起来收拾我呀!没想到二叔却说:“男孩子嘛,就是皮,一缸水算个啥,正好舀出来浇菜,顺便我也刷刷缸。”
就这样,二叔非但没有收拾我,还保护了我。随后还真刷了缸,又“呼哧呼哧”地一口气将水缸蓄满了水。那水是要到村西头的老井里去挑的。看着二叔一趟一趟地挑水,我的心里可不得劲了。
不过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困惑,就是爷爷虽然很喜欢四合院,但他却极少去那个院子里转悠,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前院的洋槐树下,或者大门洞里。终于憋不住,便问了母亲。母亲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小孩子,你懂个啥?那是你爷爷仁慈,碍于自己老公公的身份,不方便。”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默默地点着头,可我知道爷爷的心里无时不在惦记着那个院子,因为我隔三差五就会睡在爷爷屋里,每次睡觉前,爷爷都会从窗户里往后看看,并自言自语地说一句“都亮着灯哪,睡吧”!然后才钻进被窝酣然入梦。
直到我14岁那年,因为大哥要娶媳妇,需盖新房,不得已爷爷只好咬咬牙将家分了。西厢房以及那个西园子属于我们家,于是母亲就拆掉了西厢房,然后又买了些木料砖瓦,在西园子里重新盖起了五间北房。紧接着,三婶也离开老家去部队成了随军家属,闲置的东厢房不久也拆掉了。自此,壮观了30多年的四合院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爷爷尽管有些失落,但似乎并不怎么难过。他说:“四合院虽然没了,但我们家的‘四合’家风却传了下来。”
我顿时一头雾水,问爷爷:“四合家风?哪四合呀?”
“婆媳和、夫妻和、兄弟和、妯娌和。”爷爷一边喝茶,一边一字一顿地说。
我细细一想,还真是这样。我们这个大家庭,老少加起来足有二十几口,这么多年,不管是父子婆媳,还是兄弟妯娌之间,抑或堂兄弟姐妹之间,虽然不能称相敬如宾,但至少没怎么红过脸。平日里不管哪屋有事,都能看到全家人一起忙碌的身影。难怪村里人都说,你们这个大门里的人啊,才配得上“一家人”这三个字,一团和气!
可是,我依然还是很怀念儿时的那座老院子,年纪越长,离家越远越想,怀念那些白灰到顶的房子、二叔的大水缸、东园子里的枣树、以及洋槐树下爷爷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品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