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重大疫情时期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
牛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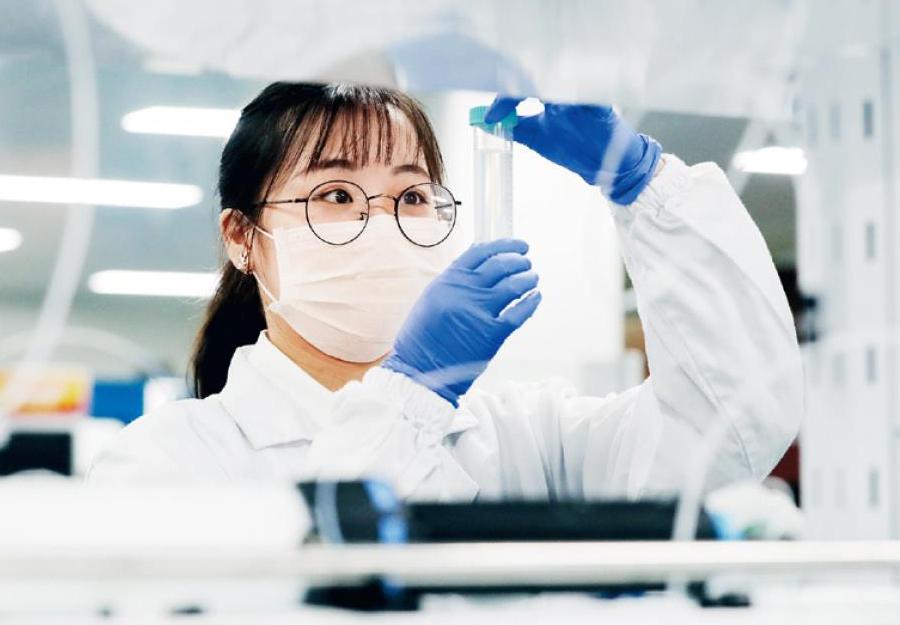
摘 要:谣言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产物,其传播机制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现代社会中,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媒介工具的多样化加速了谣言的产生与传播。重大疫情时期的谣言主要呈现出内容的虚假性、传播的即时性、主体的匿名性、参与的广泛性四个主要特征。谣言不仅阻碍了真实信息的传播,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谣言治理要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谣言;社会治理;治理进路
2020年伊始,国内突然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是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疫情是风险社会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检验。疫情出现后,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投入到疫情防控的战斗中,不仅为国内夺取抗“疫”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世界疫情防控中展现出了高度负责的大国担当。
然而,伴随特殊时期暴发的不仅有肆虐的病毒,还有层出不穷的谣言。作为一种新型具有极强传染性的疾病,新冠肺炎的防治比一般疾病多了一层社会学意涵,即纯粹的医学努力难以遏制它,它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应对系统,即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效能。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离不开对谣言的治理,谣言治理水平反映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谣言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一、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机制
谣言作为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以不同的形式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德国学者洛伊鲍尔曾指出,谣言既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化身,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承载着历史的呼应,与历史随行。比如在中国,早在《战国策》中就曾记载了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等相关的谣言;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也曾研究了中国在1768年流行的一种被称之为“叫魂”的盛世妖术,当时波及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12个省份,造成了近2亿人口的社会大恐慌。[1]
针对谣言的概念界定,最早在1947年由Allport和Postman[2]定义“谣言是借由民众口语传播且无公开证据支持的一种表述或信念”。这一概念忽略了谣言传播途径的变化,经过时代发展与技术更迭,1998年Pendleton[3]在此基础上把谣言的范围扩大为“未经可信来源证实的信息表达”。我国学者在其概念的界定上虽有差异,但都主要围绕“未经证实的”和“虚假的”两个关键来解释谣言。因此,可认为谣言是一种人们私下流传的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事情、事件或未经证实的阐述和解释。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根据研究,总结出谣言产生的经典公式:R=I×A。“R”是Rumor的缩写,表示谣言流行的强度和广度;“I”代表Importance,表示事件对某一群体的重要性;“A”代表Ambiguity,表示事件的模糊性[4]。据此公式可见,决定谣言的因素包括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两个方面,当I与A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谣言随即产生。而且,事件对公众的重要性越大、模糊性越高,谣言传播的效应就会相应扩大。同时,依据这个公式中的比例关系可知,只要重要性或模糊性两者中任一因素趋于零,谣言就无法产生或持续蔓延。
谣言的传播历程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传统方式将谣言发展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消亡期”三个阶段。潜伏期时,如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公众的心理稳定感遭到破坏,以致急需获取信息来平衡内心的恐惧,如若缺乏相关信息的报道而产生一段时间的“信息真空”,人们就倾向于接收小道或者虚假信息,因此便为谣言“流窜”提供了条件;爆发期时,谣言借助各种传播渠道大肆扩散,经过多重传播和夸张渲染,原始谣言可能变异或失真,衍生出更多的版本;消亡期时,政府、相关部门或媒体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信息和辟谣,使公众脱离紧张不安的状态,从而失去对谣言的兴趣,谣言热度降低,进入消亡阶段。因此,信息在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人们迫切地为了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就会产生确认偏误[1],从而导致谣言的广泛流传。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以后,谣言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与传播媒介的发展和进步保持同步,从单一的人际传播演变为多元的媒介传播,进而发展成为互动式、多中心的传播方式。以传统媒介为中心的局面彻底打破,并朝着“去中心化”的趋势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频率更高。
重大疫情的暴发作为一种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与民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新冠肺炎为例,病毒的传染性强、来源和传播途径有待进一步确认,极易引发大范围的社会恐慌,为各类谣言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谣言的主要特征
现代社会,谣言借助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的发达,在信息生成、更迭变异、传播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尤其像在SARS和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时期,各类谣言纷纷四起。总的来说,这些谣言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1.内容的虚假性。这是谣言的本质特征。谣言本身即是“未经证实的”和“虚假的”信息,在事实面前其非真实性暴露无遗。但是,在“全民麦克风”时代,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轻而易举,这降低了制造、夸大虚假信息的“技术门槛”。如若信息发布者和傳播者是非理性的或有所意图的,就会产生大量失真信息与谣言,信息接收者并不会严谨地考证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以致造成“沉默的螺旋”[5]。
2.传播的即时性。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谣言的传播是一个快速且连续的过程,自源头出发后,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到最广泛的公众之中。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使得信息传播的“短平快”特征更加显著,从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一对多”的简单传播模式发展成为“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而且,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介质,更使得谣言散布如虎添翼,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台中迅速被大众分享。尤其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短时间内谣言便能大规模的迅速蔓延,甚至可以波及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3.主体的匿名性。网络时代中,几乎人人皆可匿名发布任何信息,一般只需所谓的“据听说”或者“据传闻”,再加上几张吸睛的照片,便可生产出一则谣言。而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造谣者的身份往往难以确认,谣言经过多重传播之后,真正的信息源头就会被完全淹没,难以追溯;其中最为积极活跃的传播者,大多是距离信息源头和事实真相很远的人。
4.参与的广泛性。谣言之所以可以获得广泛受众,是因为一般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谣言都是无意识集体创作的结果,而非单独个体所制造。参与者会根据自身偏好,不自知的成为传播链上的一环,进行信息累加、协同删改,再经过层层“传播筛选”,谣言就会以更符合大众胃口的面貌出现,攫取更多人的“信任”。如今的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可以快速集结大众,组成“围观”集体,使人们在暗示、从众、想象和社会传染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变成无意识的“乌合之众”[6],陷入非理性的旋涡,享受“集体狂欢”的快乐。
三、谣言的社会功能
一些学者的研究将谣言过分“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个体行动和社会整合方面具有的客观功能。实际上,存在即合理,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环,是为了试图定义那些关键却模糊的信息而产生的社会行为。谣言既是一种自发的叙事,又是一种民间的集体行动;既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性手段,也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必要部分。通常情况下,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并非故意又非谋划。因此,用辩证地视角看待谣言,可以更加理性的认识到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发挥合理的社会功能。
1.个体情绪的发泄渠道。奥尔波特和波兹曼认为谣言是“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个体和社会行动中都包含着相对理性的成分。在现代生活的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下,人们个性中压抑、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日益放大,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个体情绪若不经适当的渠道加以宣泄,极易造成人们个性的扭曲,甚至形成反社会人格,这是现代犯罪的重要心理诱因之一。谣言即是一种个体情绪的表达或投射,使得参与其中的个体不仅可以交流信息和观点,还可以释放情绪、表达态度和诉求。
2.集体行动的合作方式。谣言的传播过程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是合作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谣言具有巨大魅力,可以迅速吸引公众视线,使许多无意识的群众自发的参与其中,形成和拓展了具有某种意见倾向的集体,同时遵循着集体行动的准则,在整个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进行不断的互动合作,以期达致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完全出于无意。
3.社会意见的整合过程。谣言是在“不断的建构”中的,当公众需要得到某一事件的解释,而官方渠道却未有明朗的表态时,公众即会自发的去寻找答案,谣言便甚嚣尘上。当某种解释获得部分群体的认可后,便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协同修改的过程中,谣言历经层层扩散、解释和评论,求得了对某一事件的“一个满意答案”,或许也是一个无限逼近真相和添加事實细节的过程。因此,谣言内容不是简单的对信息进行删改、歪曲和添加,而是一种公众意见达成一致、实现整合的过程,是一群人“智慧”的结果。
4.政治权力的监督途径。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当公众认可官方信息的合法性来源时,即是承认了官方对于所有信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谣言总是跑在官方来源之前。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催生真相的监督方式。实际上,谣言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发声”,是对某一事件提出一种假设或是解释,迫使官方迅速做出回应、进行调查、拿出真相、公布大众,更好的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四、谣言的社会危害
重大疫情时期,有关疫情的谣言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热点,一直处于社会话题的舆论中心,吸引着广泛的社会关注。某些谣言的传播和扩散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危害不容小觑。
1.混淆信息真伪,干扰真相传播。谣言的存在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边界。谣言产生的过程只是因为有人愿意相信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于是便告知周围“圈子”里的人。只有当人们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才可能证实信息的真实与否,但绝大多数人只会选择盲从听信,而不会耗时耗力去寻找真相。所以,谣言的流传与真实无关,只是建立在人们主观意识上,取决于个体的价值偏好。而信息越不全,人们就会不自觉的想挖掘的更深,斟酌其中的含义,用记忆中的片段或是经验中的事例加以解释,进一步加深了对谣言的主观情感,导致人们对后至的真相缺乏关心,极少核实信息的真伪。
2.操纵舆论导向,影响社会稳定。谣言是舆论的特殊形式,也是引导舆论道路上的绊脚石。谣言会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意见群体,在猎奇、从众等心理的影响下,个体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意识被淹没在集体中,人们更加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染,以致被一些谣言蛊惑和煽动,选择盲目跟风或者采取非理性行动。如果谣言被有所企图的造谣者、传谣者利用,操纵信息源、加工信息内容、增删信息核心要件,就会形成不良的舆论风向。一旦这种谣言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不仅会扰乱人心,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秩序。
3.损害政府权威,增加社会风险。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信息交互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给谣言的大量产生和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使得政府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当谣言爆发时,国家与政府存在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可能,即使及时出面辟谣,民众也有可能认为政府在说谎,导致辟谣效果大打折扣;当某些人存在不满情绪或利益受损时,还可能趁机发表刻意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论,诱导群众情绪,衍生出各类社会群体性事件;加之自媒体的不断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更加激化,增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一些网络大V和公众人物可能会不加甄别的传播谣言,用流量带动和影响舆论的发展,从而有损官方“发声”的效力,增加了谣言治理的难度。
五、谣言的治理进路
重大疫情的谣言伴随着特定疫情的出现而产生,谣言的泛滥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互联网时代中,公众拥有更多发声的渠道,舆论更加自由,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激增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爆发率。在重大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如不能把谣言约束在可控范围内,会对社会稳定、政府形象和国家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谣言治理至关重要,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谣言治理的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
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改革遵循的根本逻辑。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我国谣言治理的价值旨归。
首先,谣言治理离不开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而社会的公共屬性决定了治理谣言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如果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谣言便会肆意流窜、无所顾忌,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即是一句空话,无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次,谣言治理需要依靠人民。谣言治理也不例外,必须依靠人民,广泛调动人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谣言是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表面化。因此,在治理谣言的过程中,不仅要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全体人民的充分参与。最后, 谣言治理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我国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于更好的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决定了谣言治理必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要通过有理有据的解释和说明,引导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疏解民众的情绪,让全体人民共享治理的成果,真正的实现“为人民服务”。
2.谣言治理的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在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这就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从不同角度出发,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协作对谣言进行精确化、高效化的治理。当前,社会治理模式已经由单一治理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所以重大疫情下的谣言治理应遵循社会治理的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国家、政府、各类组织及公民个人皆需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意识,这对谣言的提前预警、及时发现、合理引导、正确处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国家和政府层面
国家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谣言采取系统治理、全面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方式,不仅要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制,更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通过制度优势体现治理效能。
第一,坚持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网络时代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言论自由,也带来了谣言的泛滥。由于谣言的匿名性、即时性等特征,具体的规范准则难以面面俱到,存在着一定的“真空地带”,因此要不断坚持和完善法律规范和惩处机制。对于性质恶劣的造谣者和传谣者进行严厉惩处,不仅可以起到辟谣的作用,使谣言失去效力,还可以对他人产生威慑,减少传播频率,增加造谣的违法成本。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辟谣既不是“尚方宝剑”,也不是官方“护短”,应当在法律范围内,尊重事实、认真取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避免“李文亮事件”的重演。
第二,坚持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根据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谣言公式可见,事件越重要,透明性越低,谣言的破坏性就越大。而重大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是当下公众最关切的热点话题。当此类突发事件发生时,若缺乏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就会导致信息不够透明,激发民众强烈的好奇心,“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谣言沸沸扬扬,官方与民众间的信息鸿沟难以填平。谣言的后续效应也不可小觑,如若官方不及时出面辟谣,未来再度辟谣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治理谣言的最佳方法是让谣言传播速度低于信息公开速度,如此一来,谣言的可信度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及时回应社会聚焦,发布权威消息,避免谣言发酵变异,畅通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第一时间进行舆论监控和引导,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
第三,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各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导致各种重大风险、矛盾问题尖锐复杂,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另一方面,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普遍增强,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诉求更加强烈。因此,首先需要着力改变过去“强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断推进扁平化发展,为信息对称创造可能,最大程度提升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瓦解谣言背后的利益助推。其次,政府要熟知各类媒体信息载体,掌握传播规律,实时把握舆情动态。面对谣言做到迅速识别、精确判断,对于公众诉求主动回应、尽力满足,增强信息回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还要提升政府的谣言治理能力与公职人员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公职人员的媒介素养,加强对谣言和舆情的研判、应对以及与民众沟通的能力,建立更加深厚的官民信任,避免出现“信谣不信官”的尴尬局面。
(2)媒体层面
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平台的产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提升了谣言的蔓延速度。媒体作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在谣言治理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加强自身职业素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不仅要对信息进行严格的筛选、甄别、取证,过滤谣言;还要及时调查清楚事件的完整信息,不能为了博取关注与点击率罔顾事实真相,推波助澜,散布谣言,要严守媒体人的职业操守,客观传达给民众迫切想要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信息。
第二,统一发布权威信息。协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辟谣,提高信息透明度,使真实信息占领舆论的制高点,特别是主流媒体要把握舆论主动权,及时报道真相,引导舆论风向,更好的消除出于猜测而引发的谣言。
第三,善用媒体传播功能。媒体每天都要处理交换数量庞大的信息,具有其他社会组织难以企及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在谣言的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其传播职能,将澄清谣言的内容在最大范围内传播,以此降低网络谣言的不良影响。
(3)公民层面
公民是谣言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既是谣言的受众,同时也是谣言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在治理谣言时,公民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是建立谣言传播“防火带”的关键。
第一,提升媒介素养。有些公民缺乏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的技巧、知识和能力。实际上,媒介提供的只是发表和传播言论的平台,其中并非均是具有可靠来源的真实信息,有些仅是为了博人眼球。所以,公民亟需了解媒体运行和发展的规则,从而具备甄别谣言的“慧眼”,才能避免自己受到谣言影响或成為新的传谣者。
第二,培育公民理性。互联网使得信息高度开放,公民需要在充分考虑信息真伪和广泛传播的社会影响之后,再理性发布或转载消息。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信息来源无法核实,就要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等待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发布官方权威消息。
第三,增强法律意识。大多数人对于散布谣言不屑一顾,这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抱持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甚至认为网络是“法外之地”。面对这种问题,更要重视公民的法制教育,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公民对待法律的敬畏之心,真正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自觉约束自身行为。
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其本质就是打破各种壁垒和障碍,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增加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形成上下联动的谣言治理体系,及时公布真实信息、坚持和完善相关制度、改善信息生态环境、提升公民认知水平,可以进一步营造全民抵御谣言的氛围。
六、结语
南宋人彭龟年曾说:“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实际上,谣言不会完全消失,它会与人类社会一直共存,并随时伺机而出。谣言治理不是钳制言论,而是科学引导舆论,关键在于善用社会治理的制度和理念,时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同时避免产生“寒蝉效应”,找到与谣言共生的最佳平衡点。
注释:
[1]confirmation bias,无论是否合乎事实,只偏好获取符合自己认知的信息的倾向。
参考文献:
[1]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2]Allport G W,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omo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2):171-173
[3]Pendleton S C.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J].Language & Communication,1998.18(1):69-86
[4]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5]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何道宽(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光明日报,2012(4)11-16
[8]Soroush Vosoughi,Deb Roy,1 Sinan Aral.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Science,2018(3):1146-1151
[9]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