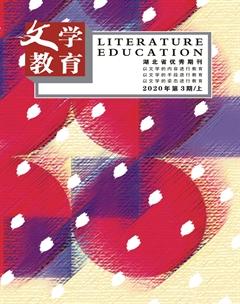散原诗“不用新异之语”辨
内容摘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言及同光体诗人陈三立时云:“其诗不用新异之语”,然而在散原诗中出现的“异常新警”之语,来自他对于世界十分敏锐的感受,亦可看出其对传统意象及其文学趣味的有限度的反叛。对于以泰西新名词、新材料入诗的问题,散原亦多有关注,在诗歌创作中更不是一味排斥之。所谓新旧之辨,在他看来都是寻求革新的手段,从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中寻找出路以出新,才是目的。
关键词:陈三立 散原诗 新异之语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言及同光体诗人陈三立时云:“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1]后人多据此语,论断陈三立诗歌不做新异语,但以旧诗为其一生成就耳,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四公子之结局》条中有“先生一生成就为旧诗”[2]之语,其后又有刘纳的《陈三立·评传·作品选》认为他是“‘代表旧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诗人”[3]。然从散原老人的诗作本身进行考察,真的“不用新異之语”吗?换言之,散原诗与新异语,确实如梁启超所言是截然对立的吗?后人依梁启超此语将散原诗成就限于旧诗,这样的理解又是否存在偏误呢?
依旧识观之,散原之为同光体代表人物,其被视为江西后继的“避俗避熟”早已为人所道,时人云“其造句练字之法,亦异常新警,多为前人所未道过。……光彩陆离,奇思警响,此才洵不多观。”[4]并且随着散原写于戊戌(1898)前的早年诗稿《诗录》的发现,学者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一文就谈及在《诗录》中,散原尤其对诗风转变后的诗稿修改频仍;这些诗作多追求新奇与陌生化的遣词造句,乃散原于光绪十七年(1891)以后所作,与戊戌后《散原精舍诗》中被人视为宋诗派的诗格有明显的趋同倾向,而这一修改“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他对这一转变的重视”。[5]照这么说,锻炼字句本身就是一种造新异之语的事情,是不是反而证明梁启超所言之失呢?但梁氏所言,可能确实意不在指其炼字上由于避俗避熟而显出的“异常新警”。
然而,观散原诗,其复杂精细处在于随着《诗录》这一文学史料的发现,证实了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诗歌风貌呈现出了差异。其早年诗作中,不乏一部分“以音调流美、出语婉转、诗风清丽为特色的作品”[6],代表作如《春日游蜕园歌》、《鹭儿曲》,基本集中在光绪十七年(1891)之前,虽然在圆美流转的同时亦能看出锻炼痕迹,但是确实无太多新异之语,或者说这部分诗作并不以新异之语为突出特征,即使存在,它也是在一般诗歌创作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远没有像后期被视为江西后继的诗作那样甚至被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读出了“自然在朝着诗人挤压、覆盖而来”[7]的感觉。那样的“异常新警”之语,来自散原对于世界十分敏锐的感受,但同时他又位于中国古典诗歌长链的末端,属于他个人的新警感兴在落实笔端时再怎么躲避熟烂都是有限度的,如“夭阏”“睒睗”“眄睐”这样的冷僻用字,确实有可能会对诗性造成损害。但是,在“不肯作一习见语”的背后,亦可看出散原对传统因袭的拒绝,特别是当面对既有的文学传统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意象时,以“花高柳大”“乌鸦鸱枭”代之“柳暗花明”“紫燕黄莺”,这样书写新物象的新异之语,虽受到陈衍后来的批评和嘲讽,然其中亦可看出其对传统意象及其文学趣味的有限度的反叛。并且,对于散原用奇语而能真气磅礴而出的地方,陈衍称其“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8]、“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境,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9]可以看出,对于新异之语,陈衍在真正进行宋诗运动的学术总结时,对此是持了保留意见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评散原之语后面接连记录了其《寄黄公度》一诗:“千年治乱于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久更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巾。”[10]此诗“不用新异之语”,甚至无需要用“新异之语”,而其中流露出的人生悲感之深重,当是散原本色,真正是“境界自与时流异”了。梁启超所言,当重在此。
此外,对于以泰西新名词、新材料入诗的问题,散原亦多有关注,在诗歌创作中更不是一味排斥之。在发现的《诗录》中,卷一所收的早年拟古之作《有所思》中,就已经有“翡翠来巴黎,珊瑚贡琉球”这样融入新名词的句子,在《散原精舍诗》中亦然。这么说,岂不又与梁启超所言“其诗不用新异之语”矛盾?然而尚不必如此轻率得出结论。实际上,散原在与黄遵宪的交往时,也对新名词、新材料怎样才能解决和旧诗格律“明而未融”的问题颇多探索。所谓“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对于当时的诗歌创作来说,展现“域外之观”的新名词、新事物入诗,固然拓宽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但由于这些物象不像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缺乏漫长的文化传统积累,对诗境界的表现无法像意象一样具有如此丰满的内蕴,并且其运用也意味着舍弃了传统的用典使事,因而如何去突破“明而未融”、“不伦不类”乃至使诗歌意蕴单薄的缺憾,实非易事。诗歌本身作得好坏,很难说取决于所谓的新材料与旧材料这样的字句之末,龚鹏程《论晚清诗·云起楼诗话摘抄》中就指出:“诗家搜罗物象,本无之而不可,所谓牛溲马勃,尽成雅言,岂有新材料旧材料之说?……唐宋人写秋千写玻璃,又岂非当时事物耶?……若散原敬观也,则依仁义行,非行仁义,不揭此为标榜也”,并亦举梁启超之言,认为“实则散原非不用新异语,用之妥帖,人不以为新异耳。”[11]要文从字顺,不以词害意,龚鹏程所言极是。从散原诗的实际创作来看,与其说梁启超所言与其不符,不如说是“用之妥帖,人不以为新异”,抑或是理解为即使以“新材料”入诗,亦无损于诗的境界,“与时流异”。
梁氏之语,正是看到了散原在诗歌新旧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而这却是后人在武断的理解下所忽视的。作为一个历史在场者,他做出了有担当的探索,尽管对他个人而言,大概其中是少不了精神痛苦和怅惘唏嘘的。散原作诗讲究独创不因循,而散原诗之所以能使新名词入诗而不突兀降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诗作中,新事物亦被赋予了属于诗人独特而敏锐感受的象征意味和审美价值,面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诗人在其中的情感是十分复杂微妙的,譬如1915年写在火车上观落日的《仁先自沪来视和其车行看落日之作》:“金焦亘古插斜阳,凄入精魂与扬簸。……孰云伤心画不成,宛拾劫灰散吟座。侵夜山风戞杉桂,搜揽怪啼奏楚些。且凭酒椀送今昔,莫占天步自摧挫。帛图丹石已纷纷,世外胡床容措大。”[12]同样是看落日,此时此地恐怕没有一个古代诗人能够与他有同样的心灵体验,而在他之后的现代人,亦不会再有。这样的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非只是“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作,和新诗派中人黄遵宪的《今别离》一比,两者在诗歌中所表达的这种情感交织,是共振的。所谓的新诗旧诗,这个划分或许本身就是多余的,并不是以新名词新事物入诗就是新诗,散原的探索使其旧体诗也具有了新诗境。但观其一生诗学思想的流变,加上学人考察其后期诗作已较少地使用新名词[13],散原还是把诗歌创作创新的内在原动力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文化精神的本色。他的这一思想,与梁启超《新民说》所言“全其旧以日新”在文化主张上是有通达之处的。所谓新旧之辨,在他看来都是寻求革新的手段,从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中寻找出路以出新,才是目的。
注 释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0页。
[2]见张慧剑:《庚子说林》,上海书店,1997年,第77页。
[3]刘纳:《陈三立·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4]南邨:《摅怀斋诗话》,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7页。
[5]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第112-114页。
[6]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第110页。
[7][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6页。
[8]陈衍:《石遗室诗话》,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2页。
[9]陈衍:《近代诗钞述评》,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2页。
[1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0页。
[11]龚鹏程:《论晚清诗·云起楼诗话摘抄》,见《近代思想史散论》,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第205页。
[12]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1页。
[13]可参见孙老虎:《陈三立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34-235页。
(作者介绍:戴铭,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