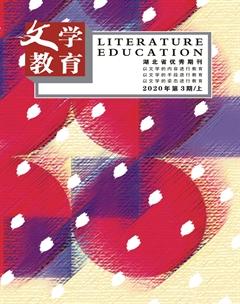上海动物园
赵挺

1
我写完那本庸俗的新书,是一个阴郁的下午。我走在街上,想吃点什么。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伟大的文学性”。我挺喜欢王小波、加缪、塞林格,也挺喜欢炸鸡腿、麻辣烫、热咖啡。我只想赚点钱,以此舒服地度过每一个管他是阴郁还是灿烂的下午。
我吃完饭,没事情干就往回走。一个大爷躺在路中间,旁边停着一辆汽车,路的对面放着大爷的一只鞋子。我想我也做不了什么。当我再次没事干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大爷、汽车和鞋子依旧老样子在那里。出于一名写作者的关怀,我把那只鞋子捡起来递给了大爷。大爷瞪着我说,谁让你捡的?给我放回去吧。我又把鞋子放回了原处,大爷说,有这么近吗?再放远一点吧。
幸亏我现在三十岁了,十年前我会过去踹他两脚,然后二话不说拿起鞋子扔进垃圾桶。现在我不会了,哪怕一辆汽车碾压了他,这又关我什么事。我三十岁了,越来越成熟了。别人的三十岁,除了吃喝,也就盯着漂亮姑娘的胸部多看幾眼,其他一切云淡风轻,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杂念较多。譬如还偶有“写作者的关怀”等虚妄之念,说明心理还没发育健全。
我把大爷的鞋子往后挪了点,实在没事干,就打电话给老虎。三天时间,老虎已经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有接。老虎是个软件工程师,一直在致力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开发。在更早之前,我和他一起见了一个投资人,老虎告诉投资人,将来人工智能将接管你的生活甚至工作,市场潜力巨大。投资人说,要不先给个五万块试试?老虎借口上厕所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和投资人聊了十多分钟的人生和理想,最后我把单给买了。
老虎接我电话的第一句话是,还活着?然后告诉我他在开发一款写作软件。这个想法来自于我。他看我写作太辛苦了,经常连续写几天,打无数个电话都不接,就跟死了一样。这款智能写作软件,致力于把全球所有作家的作品都纳入数据库,进行杂糅、拆分和重组。以后我们写作,脑子里只需有个想法,然后输入百分之十海明威,百分之三十加缪,百分之三十五王小波,百分之十五博尔赫斯,甚至输入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如果对作品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继续输入名字和比例进行调整,也可以人工逐字逐句调整,你只要输入一个数字,他就能生成一篇相应数字的文章,一小时能生成一亿字。
老虎的意思是,我就别写作了,帮他来完善数据库,将海量作家的作品导入这个数据库,并且不断地保持更新。我说那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作家了吗?老虎说,一方面我们不停纳入那些还在进行自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软件创作出来的文章也纳入数据库,这就叫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法。
老虎在挂电话之前告诉我,用不了多久,我们只需要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的操作员就行了,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作家了。
这话让我有点忧伤,如果这个世界真不需要作家了,那我能去干什么?我在这条大街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本质上这是一种职业解放,或者说劳动解放。而我们一直觉得动点脑子写出来的东西总显得比不动脑子写出来的东西更有意义,我们对自己的脑子是否有一种低级的迷信?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被不平的路砖绊了一脚,终于想起了小佚。
我打电话给小佚,她挂断了。她回我信息,在开会。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可以。我说那就吃日本料理吧,小佚说这个昨天刚吃过,我说那就吃火锅,小佚说最近上火,我说那就吃海鲜吧,小佚说还没吃腻吗?我说那中山东路等你吗?她说快结束的时候再联系。我说几点结束?她说现在也不太确定。
2
我花了一个上午,驾驶着我那辆灰蒙蒙的汽车开了三百多公里,不停地从城市的东边开到西边,再从西边开到东边,也不知道往返了多少次。这期间我听了很多音乐。譬如十年前很喜欢的主唱已经死了的林肯公园。只有一首歌好听的Patrick Nuo。某一时刻深入骨髓的FM Static。烂大街的Busted。还有开车让你睡着的卡拉布吕尼。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也听不懂意思的音乐。
我这么来回开的原因是,我汽车的水箱漏水了。比起大店一千多块的修理费,在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家只需三百块就搞定的小店。年老的修车师傅,捣鼓了一阵,在十几平米阴暗的修车铺里点着烟对我说,你先开个十天半个月大概三四百公里试试,到时候再来看看有没有问题。于是我一个上午就开了三百多公里,最后伴随着卡拉布吕尼昏昏欲睡的声音,将车停在了阴暗的修车铺前。老师傅看了几眼说,还是漏水。换了一个水箱之后说,再去开三四百公里看看。我在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又开完了三百多公里。老师傅端着饭碗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了一会儿说,要不明天再说吧。
我急于把车修好,是因为我要开着车和老马去西藏了。这在以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现在干的人多了就变得比较庸俗了。现在我也想不出什么特别酷的事情,只是觉得庸俗其实也是挺酷的。
我和老马在一个游戏群里认识,我们都属于特别庸俗特别酷的人。连游戏我们都不好好打,经常瞎扯淡。在这个几百号人的群里,老马半夜突然会发一句,明天有人骑车去云南吗?只有我回,有。知道尼采唯意志论是什么吗?只有我回,知道。八尺龙须方锦褥,下一句是什么?只有我认真瞎编,四根狗尾圆破絮。你知道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吗?我说,吃喝嫖赌。说完这话,我和老马双双被踢出了群。我们就这样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我和老马玩游戏的时候,经常在游戏的对话框里谈论哲学、人生以及宇宙的奥义。别的队友经常迫于无奈破口大骂,但是因为不雅词汇被屏蔽,所以经常会有一大堆星号出现。只有我们这种高大上的词汇,才会源源不断呈现在一款无聊幼稚的游戏里。
我和老马认识两年多,玩游戏的时候,我们投敌无数,坑队友没商量,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将游戏游戏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老马说,这才是真正的游戏哲学,你亦我,我亦你,敌亦友,友亦敌,输则赢,赢则输。我说,老马你做什么工作的?老马一本正经的回三个字,哲学家。我说,哲学家一个月多钱?老马说,钱越多越庸俗。我说,那就不谈钱了。老马回,两千。我说,那你一点也不庸俗。老马有时候问我借五千,有时候我问他借三千,有时候他又问我借两千五,有时候我也问他借个三千五,来来回回无数次,我都忘了我们到底谁欠谁钱了。
老马提出要开车去西藏的时候,我觉得老马还是挺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老马比我想象的还要酷,因为老马连车也没有。
在我花了一千五将汽车漏水问题解决之后,我开着车去找老马,准备接上他就往西藏方向开去。我和老马都是很酷的人,所以在出发的前一天,我才想起来和老马说,要不见一面吃个饭聊聊,毕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老马说,明天都要出发了,明天见吧。老马说,明天在天一广场的二号门前等我。
我到达天一广场的二号门前,看见老马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袋,一头长发,穿着一件破旧的皮夹克,瘦小黝黑的脸庞,嘴巴上斜叼着烟,这一切无不在告诉周围的人们,老子我要驾车穿越中国去西藏了。这牛逼哄哄的样子和这个城市特别格格不入。
我摇下玻璃窗,大喊一声,老马,这里。
老马晃荡着巨大的旅行袋跑过来,想和我说两句又或者想分我一根烟。我说,这里不能停车,上车再说。老马一屁股坐到副驾,将旅行袋往后座一甩,撩了一把長发,一股几天没洗头的酸腐味扑鼻而来。车上正随机播放着一首名叫In the morning light的歌,我说,这歌怎么样?我将这首歌名翻译成,沐光之城。老马一脸无所谓操着一口极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可以,然后说,得劲,得劲。老马掏出一款过时的破手机看了看说,太慢,上高架。我说,不赶时间。老马被风吹得眯着眼睛说,赶。我说你包里都带了些什么,老马说,破衣服。老马的确是个哲学家,有点人狠话不多的感觉。我说,从网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个哲学家。老马叼着最后一根烟说,过了过了,前面掉头。我调了一个头说,去干吗?老马扶着门说,停停停,就这里,我买包烟。下车的时候,老马给我五十块说,都是这个价。我说,老马,怎么了?老马一扭头,还叼着明灭不定的烟屁股说,谁是老马?我说,你不是老马?老马一下车,踩灭烟蒂说,谁是老马?我说,不是去西藏?老马将旅行袋一扛说,去河南。
我看看手机,老马没有一点反应,我试图联系他,也没有任何回复。我重新将车开回天一广场的二号门。因为大门前不能停车,于是我不停地绕圈,每绕一圈我就看一眼,总看见一群行色匆匆的人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绕了五六圈之后,我将车停在大门口,警察马上过来示意我开走。
我边踩油门边用手不停联系老马,就像在联系一位远古时期的哲学家,一直没有反应。此刻,我发现水温又高于一百五十度了,警示灯亮起,这说明水箱又漏水了。我将灰蒙蒙的汽车往那个阴暗的小店铺开去。此时,曾经钟爱的绿日乐队在唱着那首俗不可耐的歌曲When I Come Around,我英文不太好,隐约知道有周而复始的意思。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好久没有联系小佚了,虽然可能才一天,但是她也没联系我。于是我发了一条信息给她,在忙吗?一直到太阳西斜,年老的修车师傅开合引擎盖无数次之后,小佚回我,还好。
3
鱼龙搞了一支摇滚乐队,希望我帮他找一个排练的地方。我说,那就我家吧。鱼龙说这排练的声音比装修声音还大。鱼龙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个鼓手和一个贝斯手,每当鱼龙说什么的时候,另两个人就负责说,对对对,是是是。鱼龙说,作为一支乐队三个人就是一个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披头士乐队,再不济也要成为滚石乐队,底线是皇后乐队。十年前我也组过一支乐队,我的最高目标只是成为来自台湾的五月天,这是一个在很多眼里整天唱口水歌的乐队。鱼龙问我当初我们是在哪里排练的。我告诉他我们搞乐队最大的问题不是排练场地,而是人都凑不齐。
在这个城市里,找个摇滚乐队的排练场地确实有点困难。摇滚乐队排练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既不能影响别人,也不能受别人影响。但是这一切如果有足够的钱,并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试图去这个城市最高的地方。我们爬了很多写字楼的楼顶。有时候我们上去了,被保安不留情面地赶下来了。有时候我们在大厅连电梯都进不去。于是我们试图去这个城市最低的地方。我们去找了很多地下车库,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地下三层,都不行,只有一个物业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如果有地下十八层,那你们就排练吧。鱼龙听了这话,就要跟物业的负责人干起来,我拼命拉住了。鱼龙说,我们可是搞摇滚的。我说,搞摇滚的搞不过保安。
如果是十年前,我可能要试图加入这个乐队,但是现在,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搞一支摇滚乐队不太现实。除了搞摇滚乐队,三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譬如开一家奶茶店,一个负责做,一个负责收钱,一个负责外送。或者不想干活,纯粹想消磨时间,那坐下来玩斗地主也比玩摇滚乐队靠谱。鱼龙听我这么说的时候,睁大眼睛瞪着我。我第一次发现鱼龙的眼睛竟然这么大。
第一次听到了鱼龙乐队的排练,同样是在一个阴郁的午后。在一个敬老院偏僻空荡的场地内。鱼龙给每个老年人买了睡眠耳塞,不要听的可以塞上耳塞。出乎意料的是,在鱼龙排练的时候总是围着一大群老年人,他们都一脸认真地坐在椅子上,仔细聆听。鱼龙他们有时候完整地演奏完一首歌,有时候中途停下来重来。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鱼龙他们演奏了一首叫《I Wanna Hold Your Hand》的歌。这是1964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在美国演奏的歌曲,被誉为“英国入侵”的代表作。歌词的核心意思就一句话,我想拉起你的小手。整首歌都在反复着这一句话。
外面的天气依旧阴郁灰蒙,周围的很多老年人依旧坐在小凳子上认真听着。鱼龙他们改编演奏了好几遍,唱了四十多遍“我想拉起你的小手”。台下一片安静。
快到饭点的时候,鱼龙他们演奏了一首《茉莉花》,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然后就是凳子拖动的声音,年老的人群慢慢散去。
鱼龙每周四都要在这个偏僻空荡的地方,给老年人演奏一些院里规定的曲目。一个月里他们演奏了《回娘家》《绣红旗》《打靶归来》《歌唱大别山》《伟大的北京》《翻身农奴把歌唱》等歌曲。
三个月后,他们就从敬老院出来了,去参加了几个音乐节,演奏了几首他们的代表作。赞美他们的人没有,骂他们的人也没有。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点像厕所上面贴的那些小标语。
鱼龙准备重新找排练场地,一切想要的重来的时候。我递给他一只烟,装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鱼龙说,你别劝我开奶茶店。贝斯手和鼓手都说,对对对,是是是。我说,你就一个人弹弹吉他,唱点民谣,这样你在我家里就可以排练。这一次贝斯手和鼓手没有说,对对对,是是是。
我说你弹唱几首轻缓一点的民谣歌曲,《九月》《米店》会不会?鱼龙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响起轻缓的歌词和旋律,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空空的米店……贝斯手和鼓手像木偶一样站在后面,好像从此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打电话给小佚,想让她听一下这些现场版好听的民谣。电话没有人接。我说,鱼龙,一会儿你给我喜欢的姑娘弹一些民谣,我给你钱,或者给你找个好点的能排练摇滚的场地。鱼龙抱着一把我以前买的两百块的木吉他说,好。
我和鱼龙、贝斯手、鼓手四个人一直在等小佚。后来我们就这慢慢睡着了。
4
我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达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的地方。我记不住这个活动的名字,总之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艺术聚会。有很多所谓的艺术家甚至古董收藏家。我是写作的,很荣幸,也成为了这帮伪艺术家中的一员,上台莫名其妙发表了一番艺术感悟。吃饭的时候,一个中年大叔坐我旁边,我看不出他是搞哪门伪艺术的。他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还问我喜欢哪个作家,我咬着大蟹脚说,加缪。我想这下应该没什么可聊了。大叔吧唧着嘴,抑扬顿挫地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敏锐的感受力,外加优秀的笔头功夫,还有勤奋努力的态度,加上孜孜不倦的精神,那就一定能成为像加妙一样的作家。我吐出蟹壳说,缪,纰缪的缪。大叔说,对,加缪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加缪,一个优秀的作家那是经过时间和经验的凝练,个人经历和阅历的积累,等等,最后才成为加缪的对吧?我咬着第六个大蟹脚想说一句,你妈的。然后说了一句,是的,老师。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小市民,我吃了八个大蟹脚,四个北极贝,两只梭子蟹,三对深水虾,两条秋刀魚,一盆杂螺。就这样吃了一堆庸俗不堪的海鲜,聊了一通毫无意义的狗屎。最后他们给了我八百块发言费。讲莫名其妙的废话就能拿钱,作为一名伪艺术家,我真希望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能多一点。如果一切都没有了意义,那我可能就要发财了。
我拿着八百块钱去看我外婆。我发动那辆开了十年的雪佛兰破车。车已经很脏了,这说明很久没有下雨了。北方已经开始烧煤供暖,大量的尘埃南下,空气越来越差,我的车也和这个世界一样越来越灰蒙蒙。
我外婆住在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七零二房间。她的症状是失眠、头晕、腰酸背痛、有气无力,医生说,年纪大了就是这样,正常的。当所有的症状成为常态,这就让我外婆感到了衰老的恐惧。
我被二院楼下的烧饼香味吸引,买了两个准备给外婆吃。医生嘱咐外婆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但是我和外婆的想法是,管他呢,想吃就吃。于是在还没进电梯的时候,我就把两只烧饼吃掉了。我想,算了,老年人还是要遵医嘱。
外婆见到我很激动,立即从床上坐起来,嘘寒问暖了一分钟后,提醒我嘴边还留着一抹葱。我擦了擦嘴巴,掏出六百块钱给外婆。外婆拒绝了一番,拿出两只葱油饼给我,说隔壁阿姨买的,还没冷掉,我们一人一个吃掉吧。我打了一个饱嗝,又吃掉了一只葱油饼。
一天就这样过了一大半。窗外路上的汽车渐渐增多,高峰期马上就要来了。护士进来,又在数落外婆。外婆一言不发看着窗外,乖乖让护士将针扎进皮肤里。之前的一天,一个著名剧团来这里演出,外婆一个人走出病房,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看演出,结果错过了打点滴时间,为此护士对外婆格外头疼。外婆喜欢看各类戏剧。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带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戏剧。现在我成了一个作家,外婆认为很大原因是她小时候带我看戏剧激发了我的写作才能。其实带给我回忆的是,看戏时外婆给我买的各种零食。还有就是走不动的时候,外婆抱着我边走边给我讲故事。故事一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走不动被外婆抱着的感觉真好。多年以后,外婆大概不会知道,被她从小用戏剧滋养熏陶的外孙,最后成了一个伪作家。如果我不成为一个伪作家,连六百块钱都给不了外婆。
外婆看着吊瓶里的液体往下滴,问我,最近出去过吗?这点我和我外婆很像,不管有事没事总喜欢到处走。我自认为去过了很多地方,但是这个世界上却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婆始终没有走出过长三角,但她也自认为像我一样去过了很多地方。
吊瓶的液体下落的很慢很慢,外面的高峰期快要过去了。我和外婆说了再见,准备去见小佚。
临走的时候外婆喃喃地说,上次戏没看,花了这么多时间,是找不到地方了,剧场就在久久天桥旁边,怎么都找不到久久天桥。我说,久久天桥已经拆掉了。外婆看着吊瓶,好像瞬间睡着了。
我在一家小吃馆里吃了一份廉价的鸡腿饭。顺便等小佚结束饭局。这期间,我用手机打开了邮箱看了一份合同。我是一个没有组织和单位的人。只是有想赚钱的公司看中了我写的那些烂俗的文字,所以和我签约,决定要好好做我的书。
我擦了擦嘴巴,关掉邮箱。我不知道小佚什么时候结束饭局。我去咖啡店买了两杯热美式,然后将车开到天一广场附近。
车内播放着Holly Throsby的一首歌曲,翻译成中文歌名叫,为什么我们不将心中的爱意告诉对方呢?歌名很长很庸俗,但好听。我单曲循环了十多遍,小佚还没有结束饭局。我再次打开邮箱,对着合同想补充些什么,小佚发来了信息。她说晚上太晚了,要不明晚再见吧。我说我就在天一广场,她说我送了一个朋友到了柳汀街,这个时候我已经发动汽车往柳汀街方向开,热咖啡还没有完全变冷,我说我很快就到了。她说,回家还有点急事,要不今晚算了。我开着那辆灰蒙蒙的雪弗兰汽车穿过柳汀街,然后说,好的,注意安全。
之后的两天我们依旧保持着联系,联系的内容是她还是挺忙的,空了会告诉我。编辑打我电话说,邮件显示已读两天了,看了没?我说,没意见,都很好。Holly Throsby还在循环那首单曲,这首歌的主旋律和歌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将心中的爱意告诉对方呢?很长很庸俗又很好听。
5
我找了一份写文案的工作。他们觉得我是一名作家,所以认为我很能写。其实我完全不懂那些东西,所有的文案我都是按照网上的模版来写的。有时候甚至直接抄一段。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可能是过腻了不朝九晚五的生活。
上班一个月,唯一确定的是这是一家破公司,待在这这里的人就这样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我大部分时候待在高大上的玻璃幕墙内,灰蒙蒙的阳光照进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地有希望。这时候我会把那些废纸搂成一团,学习那些伟大的球星,将废纸投进垃圾桶。我曾经多么想成为那些伟大的歌手,球星,作家,我的梦想就是成为那些无法成为的人。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这样,譬如我们公司的总监,他做梦也没想过会成为一家破文化公司的总监。
总监非常忙,他也希望我们非常忙。我经常将废纸投进纸篓这个动作重复好几遍。譬如我特意将垃圾桶放得远一些,学习詹姆斯和科比的投篮姿势,如果投进了我会将垃圾桶放得更远一些,我的命中率可以让我将垃圾桶放到总监座位附近,这已经是最远距离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可以命中。这破公司真的太小了。在这里我对于投废纸渐渐失去了兴趣,以至于觉得上班越来越无聊。
总监让我送一份材料去北仑。出发之前我下载了许多歌曲,里面有很多冷门好听的乐队。总监打电话问我,快到了吗?我在办公室的另一头偷偷说,快了快了。出门的时候我选了一条最远的路,到达北仑的时候,那些歌还没有听完,于是我又在马路上绕了两圈,把所有的歌曲听完我才停下汽车。
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太阳灿烂,天空清澈。我不禁在大街上游荡起来。我就这样晃荡了一下午,等到暮色渐浓,天空灰暗,我才发动汽车。我往公司的方向开,去下个班,然后回家。
到公司的时候,我就被总监大骂了一顿。他说你这是去北仑还是去北京了?等了你一下午打了十多个电话。最后表示要辞退我。我想既然这样那就走吧。我面無表情地说,好的。总监突然换了一种语气,扶了扶眼镜说,其实,你知道你活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作为一名伪作家,我对这种话和语调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我没说话。总监坐下来说,人活着是需要有自己的价值的,价值的体现就在工作上,对工作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浪费时间,就是在谋财害命,你说你是不是在谋我的财害我的命?你是一个作家你应该知道高尔基先生也说过一句话……我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总监皱着眉头看着我说,怎么了?我还没说完你就不耐烦了?我说没有,生理现象。
总监说,你先走吧,扣一星期的工资。
我说,我要辞职。
总监说,没让你辞职。
我说,我要辞职。
总监,巴金、老舍,还有那个海明威都说过……
我说,我要辞职。
总监说,你知道辞职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我要辞职。
总监说,都容忍你玩投废纸这么无聊的游戏了。
我说,玩腻了。
总监说,玩腻了你还可以玩点别的
我说,什么都不好玩。
总监说,你走了公司怎么办?
我这样投废纸能投半天的人,竟然能对公司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这说明这已经不是家一般破的公司了。我都很难形容我自己,更不愿意待在一个很难形容的地方。总监好说歹说要请我吃个饭表示挽留,我欣然接受了。等吃完晚饭,我毅然表示要辞职,并且二话不说开着那辆灰蒙蒙的汽车走了。
月亮已经很高了。我开了五十公里的车,给小佚送了一杯咖啡。我们聊了一些我记不太住的话,小佚更加记不住。日后回忆起来的是,那杯美式热咖啡还没有冷掉,外面的夜色比咖啡还浓郁。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小佚没有把咖啡喝完。我只记得她说了谢谢,以及临走前我们都说了,再见。
6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汽车都已经无法发动。老虎让我去做导入全球作家作品的工作,于是我走出了门外。我发现旁边已经变成了一片工地,如果要去公交车,就要去绕一大圈。于是我尝试着从工地穿过去。在尘土飞扬的工地,我突然觉得我可能要失去作家这个身份了,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伟大的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操作员。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这么想的时候,个头戴安全帽的说,快过来一起推钢筋。于是我过去和他一起推着一车钢筋走了。推了好几车钢筋,我累得瘫坐在旁边,等稍稍恢复一点,我拿出手机玩了两把游戏,没有老马的配合,玩游戏也只是输赢而已。我看了看周围,突然发现其实鱼龙可以来这里排练,工地的声音肯定能盖过摇滚那些微不足道的声音,完全不会影响任何人,如果能戴着安全帽演奏披头士乐队的歌曲,那比任何事情都酷。
我站起身,继续往前走。老虎的软件实在太可怕了,祖国可以解放,人民可以解放,劳动力可以解放,甚至性都可以解放,但是作家怎么能解放呢?我犹豫了一下,就在路上转入了二院的病房,顺路去看一下外婆。外婆已经转到了另一个病房。
我看见病房里外婆并不在,我问护士,我外婆呢?护士告诉我,自己走在外面去了。她告诉我,再过个两年左右,外婆可能会忘记很多东西,会说不出很多话,会更容易迷路,再过三年的话,外婆可能连我都会不认识,她会忘记一切,会漫无目的地游走,很容易就这样失踪。我说你们算的这么准。护士说,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就是这样,你好好看住你的外婆吧。
我到达老虎公司的时候,老虎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一张我的名片。上面写着我是公司的总监。除了总监就没有其他人了。我想以长者的姿态语重心长地去教育一个人的机会都没有。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个世界上所有作家作品不停地导入一个黑洞一样的数据库。我夜以继日地做着这样一件事情,将那些作家的作品填入一个大熔炉,把他们分解,也包括我自己。
间隙,我给小佚发了一条消息,在忙吗?什么时候有空见见吗?在我导入一万多名作家作品之后,小佚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再见。
(选自《收获》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