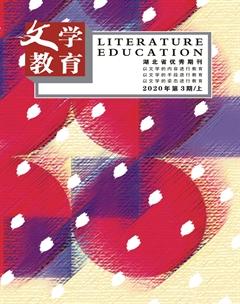一次精神的长旅

女作家艾英的行走,不是简单的游玩,去赏风景,解除世俗中的压力。她是在寻找,追寻另一个女作家萧红的脚踪。
艾英是东北人,本名张乃英。她的家乡距离呼兰河不算太远。在北京读完大学,毕业后,她留在江南常州生活。对于漂泊的感受,她和萧红有相同的感觉。当女作家艾英返回东北,去寻访萧红的时候,心情发生与众不同的变化。萧红在文坛上热了又冷,冷了又热,寂寞和她形影不离,不是什么人都能读懂的。萧红是原生的创作者,她不会拉开架子大放议论,点评人生的苦难。萧红的主题如同蔓延的野草,一层层的丰富,她所写的人,不是停留物质的生与死,而是关注灵魂的归宿地,對人性深刻的感触,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的。美国哲学家A.J.赫舍尔,在关于人的问题时说:“他并不寻找自己的起源,而在寻找自己的命运。”
艾英刊发在《朔方》的文字,写了访萧红故居的感受。这篇文章写得厚重,每一个字沉甸甸的,抒发对萧红的敬畏。断片式的写作,形成一支庞大的组歌,献给早逝的天才女作家。朴白的描写,只是把情感表达出来,没有故弄玄虚的做作。“萧红对呼兰来说,不是一个平凡的名字、普通的作家,而是代表这方水土最动人的一个文化符号;因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呼兰河这条松花江的支流被世人知晓,偏远闭塞的呼兰成为中国地图上一个鲜明的文化坐标。呼兰河滋养和养育萧红,萧红在乱世和困境中创作,这些风格独特的作品超越时空,超越时代。呼兰河,因萧红作品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永恒的魅力。”
阅读一个经过苦难磨砺人的作品,才懂得笔下小人物的真诚、可爱和深刻,明白故乡的含义。浪迹者在遥远的异乡,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带着强烈的爱与恨,在凄美的回忆之中,记下小城人的生存状态。
萧红是值得尊敬的作家,“而坚硬、凛冽,是不是来自于那些鲜活的生命生活地、悲惨的场景发生地西后院?这些文字读来有时令人愉悦,有时让人揪心般地疼痛,这正是萧红的文字具有的意义和力量。童年的生活、饱满的感情烙印在她灵魂深处,她的文字落笔故乡高远的天空、厚重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苍天之下、厚土之上,那些卑微的穷苦的、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
《淮南子·齐俗训》有云:“傲世轻物,不污于俗。”说的是坚持高洁的品行,轻视社会环境。萧红没有翻身跳跃,逃出尘世的苦海,而是紧密的和受苦难的平常人贴近。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悬空虚构,却是双脚踩在大地泥土中。萧红没有借物喻志,发一些个人的小牢骚,宣泄内心积压的情感。她有一颗悲悯的心,同情那些小人物,有二伯、团圆媳妇,这些在社会是产值得一提的人,构成多维立体的历史记忆,一幅黑土地上的风俗画卷。
每个人有独立品格,不是虚情假意赏玩标本。萧红的文字不是“倍清谈”,她经受太多的苦难,寻找个性的解放,又以悲情结束一生。评论家谢有顺指出:“散文就是一种味道,精神的味道,以及文字的味道。如果一篇散文没有味道,没有语言个性,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谢有顺说的味道,是流动在文字中的精神分子,它决定每一个字的重量。如果文字中没有这个味道,那么就是说,这个字是瘪字,不存在精神的核。如果一个人染上世俗的气味,他的灵敏度降低,甚至消失,没有嗅觉。染尘沾俗,是一点点侵入骨髓,难以清除干净。评论家清醒地说出,好散文无语言个性,没有精神散发的味道,那么这篇文章存在和不存在,都无任何意义。
以世俗的眼光看,萧红的一生,热闹而又滥情。人们更多的是拿着放大镜,截屏似的裁取一部分,夸大张扬。女作家丰富的内心,柔弱的身体中,流淌朴素的安静。她的文字不带一点脏污,过于浮夸的描写。很多人读的是喧嚣,不是去勘探女作家的心灵史。
艾英写的是真实的萧红,没有强迫在人物身上涂抹色彩,乔装打扮。她的生活来自于原生态,有着野性的力量。萧红懂得从生活中汲取什么,提炼的过程,体现一个作家的风格,和文本的形成。
真实,真情,这是创作的最高标准。许多拙劣的写作者,在此面前败下阵来。这种寻找,对于作家艾英,不仅是对萧红的敬爱,而是一次精神的长旅。留下的记忆,会时时影响她的创作。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哪怕是被我们称作次要艺术的东西,它们在散文中也能找到共鸣。散文为自己唱歌,为自己跳舞,为自己朗诵:散文中有踩着妙曼舞步的文字韵律,表达的思想就像剥去外衣,露出堪称典范缸的真实感官,散文中还有伟大演员的微妙手势,文字带着一种节奏,将宇宙中的无形奥秘转变成有形物质。”艾英的文字应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说法,文字中含有内容,每一个字不是空壳,它们形成鲜明的节奏。这不是装腔做势,而是作家成熟的表现。
艾英的创作进入一个变化阶段,读过这篇文章,发现她在寻找与决裂中的再生。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每天都在与自己作斗争,与语言作斗争,找到新的表达形式。不是标语似的口号,也不是花拳绣腿的表演,而是心灵的熬炼。
读艾英的文字,看到她的安静,也感受朴来的散文气息,这样的文学不仅好看,而是耐读的。
高维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诗集三十余种,主编“大散文”“独立文丛”等书系,现居山东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