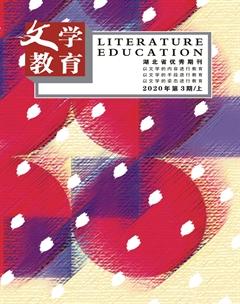多面而合和的批评世界
邱婕

总有这么一类文字,使手中的笔还没开始述写时便已重若千钧。围绕着刘大先的文学批评而展开的批评,俨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名初入文学批评茅庐的“九零后”萌新,意图描画一位已颇负盛名的“七零后”批评家的批评世界,听起来颇有“蚍蜉撼大树”的意味。因此,自立题以来,我便常常深陷于一种悖论式的困境中:一方面我唯恐自己笔劲不足,不能描摹出刘大先批评精彩面貌的十之一二。另一方面,随着对刘大先批评著述的深入探究,我又屡受触动,迸发出为之言说的冲动。在这惶然与奋然的纠葛中,刘大先批评世界的魅力终究助我鼓足勇气,愿倾以十二分的心力为之作注。
刘大先批评体系的建构元素无疑是繁复的,这既给我等后辈提供了极其值得珍视的学习体验,但同时也给其关键词的提取以及主要形态的描画增添了相当的难度。思来想去,我决定暂时摒弃从刘大先批评中获得的千头万绪,老老实实追述我“认识”刘大先的心路历程。一直很羡慕与所描画之批评家相交甚笃的评述者,可以从容且有底气地在叙议交融、庄谐相和中挥洒而出批评家的批评面貌。但是,我必须坦言,就社会关系这一层面而言,刘大先与我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我与他的“认识”是一场由我而他的精神层面的单向活动。其时还在读硕士的我,在武汉的夏天里偶遇了刘大先的著作《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作者简介中平常无奇却又掷地有声的二十一个字给我带来了极深的印象:“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及影像文化”。这种颇具跨度的研究方向,对于竭尽全力却感觉依旧有一脚在学术门槛之外的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震撼。当如今的我试图对刘大先的文学批评进行素描时,当时的那种震撼感便迅速裹挟着夏日的腾腾热气扑面而来,于是,我在构思与试笔时便曾倾向于秉持第一印象,以“多情的批评家”来形容刘大先。但是,当我进一步较为深入且系统地了解刘大先的批评世界:从《时光的木乃伊》到《文学的共和》,从《无情世界的感情》到《未眠书》,再至其浩瀚的学术论文体系,才恍然醒悟,用“多情”来概括刘大先的批评显得过于单一了,“多情”又“专情”的形容可能更合适一些。在这些“渐欲迷人眼”的著述中,刘大先往往以“跨越学科”之名行“消融边界”之举,在上下求索中寻找并坚持自己批评的初心——做一个学者型的批评家,创造出一个多元素共生、多主体共存的合和的批评世界。
一.“随波逐流”的“读书种子”
当明晰了刘大先批评世界的外延与内核后,一个问题便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刘大先所拥有的融“多情”与“专情”于一体的批评形态,其起点在何处?在对其批评历程作一个知识考古式的追溯后,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答案。刘大先曾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做过简短又清晰的绍介:“我之前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教育,硕士读文艺学,博士攻现代文学。因为工作的关系颇多着力于少数民族文化,在游学中又对比较文学和社会学多所用力。”就此而观,刘大先批评“多情”面貌的成型与刘大先的学术教育历程及其人生路途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
说到此处,我不禁要先感叹一句,刘大先着实是一个谦逊之人。因为当我还没来得及为刘大先“跨界”与“转向”的勇气与胆识击节赞赏时,便发现,刘大先早已自觉自发地对自己进行了祛魅式解读。刘大先无意在自己的学术履历上添金描银,在我等旁人看来是如此曲折又精彩的学术建基之路,在刘大先的眼中,不过是切合实际的选择结果罢了:本科时期,“属于浑噩的大多数”的刘大先,在面临保送读研的选择专业时,只因为“有个室友随口说了一句文艺学”,他就选择了文艺学;对于博士攻读专业的选择,刘大先称自己当时并没有过多的学术自觉;博士期间之所以选择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这个研究话题,也与其“正在从事的工作息息相关”。但是,若进一步返回现场进行深究,便会发现,刘大先的这些选择看似随性,其背后却反映着刘大先对于文学、文化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对文艺学专业的选择根源于刘大先对当时文学生态的困惑;对现当代文学的转向是因为“如果真要建立自己的学术根基,可能还是需要一块比较‘实的领域”;现代中国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向的确立已经初显刘大先勾连不同学科的雄心。刘大先曾用随波逐流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学术建基之路,因此,此处给“随波逐流”一词加上“引号”,是我等后辈对刘大先过于谦逊之态度的小小抗议。可以说,这些看似随性、实则颇富深意的学术选择使刘大先的批评拥有了多维多元的绚烂底色。
作为经历了专业学术训练的批评者,刘大先对当下愈发细密与专业的学科分类显然并不陌生,也因此,他对自己“多情”的批评面貌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曾直言,自己的多个研究方向“虽然都在‘文学这个笼统的范围之中,在现代学科的严格分类中它们却经常遭遇壁垒森严的门户。”但是,走在立体多维的學术建基之路上的刘大先非但没有手忙脚乱,反而从容逡巡于各个学科之中,建构着自己的批评观念与理论体系,使自己的批评向“专情”方向进发,其根本原因在于刘大先有着一颗纯粹的追慕知识与思想的心,而其获取知识与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阅读。刘大先从来都不吝于表达对于阅读的深厚情感,“很小的时候我就爱读书,乡里的邻居有时候与我父母闲谈时,往往称赞一句‘这是一个读书种子。”青涩懵懂的乡野少年、躬耕于求学路上的求知学子、投身于现实工作的批评精英,无论身处何时、身在何地,刘大先总是能与读书厮守缠绵,相伴相依。就阅读经历而言,刘大先无疑是幸运的。长期的、不设限的阅读习惯使刘大先形成了阔大绵延的知识谱系与思想版图,也因此给其消融学科边界的批评走向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诚如其本人所言,“读书的诱惑却超然于学科之上,无数今人古人智慧与神思的结晶游荡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让人心驰神往。这种诱惑足以让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对知识与思想的追索使刘大先倾向于在更为阔大的视野中寻找文学存在内核、研究文化建构基因、探求人类精神密码,这是其批评“专情”面貌形成的原生环境。“多情”与“专情”交织与共,是刘大先批评世界走向合和的厚重基石。
二.成为一名学者
如果说既“多情”又“专情”的批评基调给刘大先的批评之路埋下了走向合和的伏笔,那么,刘大先相当自觉的批评身份认知则将其批评向着合和的理想状态推进了一大步。毋庸置疑,刘大先是一个批评家,但是,刘大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描摹刘大先批评面貌的关键。所谓“文如其人”,文学批评自然亦不例外。文学批评好似一条棱镜,能在某种程度上完整地映射出批评家的本真身份。秉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再对刘大先的批评世界进行探究时,会惊奇又惊喜地发现,刘大先是一个如此“多面”的批评家。
如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的意象与现实》中,刘大先便呈现出近乎“分裂”的批评身份:“这个前兵营、消费型官僚城市在岁月中面目婉转,却如同年深日久的老照片,被时光腐蚀晕染的容颜影影绰绰,幽灵一样成为语言的浮城,在人们心口胸间盘旋不去”之优美缠绵的语言功力与抒情散文家相比也不遑多让;“18世纪、19世纪世界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是乡村与都市的冲突,在二元对立式的书写中,乡村和都市分别被赋予了简约的价值内涵,而这种建构与非建构起来的紧张在新世纪北京被欲望自身消解,或者说在消费文化下主动和解了”以严谨的逻辑与理性的表述告诉我,这是一篇学术性的批评文章;“风清日朗的时候,北京的夕阳是值得观看的景象。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会坐在卧室的飘窗上眺望西北天际的火烧云……我曾经在朝阳和通州交界的杨庄住过六年”等贴近现实又带着无限感慨的语句又会使我产生在读作者自传的错觉。
三种表述风格的出现分别彰显了刘大先的三种批评身份认知,即文艺青年、学院派、现实中的“我”。此三种身份认知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刘大先对自己作为“文艺青年”的身份毫不避讳,在追述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日子时,他便将自己整日里躲在家中读书看片的生活称为“典型的文艺青年的生活”。作为“文艺青年”的刘大先有着灵动活泼又敏感多情的书写秉性。对于接受了专业批评训练的刘大先来说,“学院派”是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身份标签,刘大先本人对这一身份也进行了“官方认定”,他称“事实上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学院中的一员”。专业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刘大先严谨理性、审慎厚重之批评特性的来源。但刘大先又并非是空想一派,漂泊而奋进的人生路途给了他“走出象牙之塔”的机遇与勇气。所以在刘大先的批评中,很少见到“空中楼阁”的建构之举,而是多立足于实证批评态度的务实之言,所谓“知行合一”,大抵如是。
文艺青年、学院派、现实中的“我”三种身份并非是独立分裂的,而是互相映衬、互相作用的关系。正是此三者的交相辉映,给刘大先的批评世界灌注了极为丰富的书写元气:灵性的文字、严谨的逻辑、务实的体验,以及与之相伴的渊博的知识、深远的思想以及充满爱与力量的人间情怀。由此,刘大先批评中批评家的主体地位获得了相当的上升。对于刘大先来说,所要研究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来阐释与建构理论体系的客体。而“融合了知识、经验与思想的实践者,是苟日新、日日新,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永远在不断进行自我启蒙与自我反思的主体”便是刘大先向往并想成为的批评身份——学者。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批评家,刘大先一直在路上。
三.“月照万川又万川映月”
既“专情”又“多情”的学术建基之路与成为一名学者的“执念”使刘大先创造出合和的批评世界。刘大先曾思考过批评的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心中花树”,第二维度是“壳中之魂”,第三个维度,亦即刘大先认为的理想的批评,为“月照万川又万川映月”,即指“文本、批评者以及包孕前者的天地,繁星满天,白云点点,在这个意向性的关系之中,文本的内与外、批评者的知与行都贯通一气、生意流注,如盐入水,成为彼此各别又浑然一体的自然对照。”其实这便是一种讲求合和的批评观念。依托于此,刘大先不断的创造并完善着多元素共生、多主体共存的批评世界。
多元素共生是一种融合学科的学术意识,这种意识在刘大先的批评中萌发极早。在做博士论文的那几年,刘大先便尝试着“通过‘六经注我式的综合,将文艺学、现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思想史的内容提炼为一套解释系统,来对一种边缘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知识考古、现状描述和理論前瞻。”在刘大先此后的批评实践中,这种学术意识更是进一步演绎为消弭差异、走向共和、重寻集体性的思想导向。
此种思想导向在刘大先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便有着突出的呈现。刘大先的名字一度乃至于一直都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密关系。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使刘大先既幸运又不幸地掉进了“颇有名气”的坑里,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代言人。为了消除自己所拥有的这种刻板印象,刘大先曾经不惜亲自“下场”为自己做辩护:“少数民族文学不过是我言说的一块领域,而我并不想使自己成为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刘大先其实有些多虑,因为任何一个系统地拜读过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著述的读者,都不会将其限制在单纯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一领域中。
刘大先批评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其不仅仅指向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影像、文献史料、文学文本、田野记录等。在具体的批评中,刘大先会将笔触深入至促进并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语境中,从而在内外相和中探寻少数民族文学的真实面貌。至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目标似乎已经达成。但是,刘大先并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域下对现代文学、现代中国、全球化等相关概念进行解读与阐释。而随着言说的行进,少数与多数、一体与多元、差异与共和等具有普适意味的研究命题便自然而然鱼贯而出。刘大先批评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就好比一轮弯月,在由内至外的皎洁月光中,批评家的所思所想所为与包孕这轮弯月的千象万物皆得以昭示。但刘大先的批评之路亦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真实面貌的揭示以及具有普适意味之命题的探究,会反过来促进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代表的边缘文学或者说边缘文化的研究。如此,刘大先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便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边缘”、“民间”、“地方”的限定,成为可以言说主流文化、想象公共空间的重要存在。此时,“知行合一”的批评家与包孕“少数民族文学”这轮弯月的千象万物便以独立却合作的方式共存,为映衬、铺洒出月光的皎洁而努力。这是属于刘大先的、和合的批评世界。
刘大先的批评世界无疑是极具魅力的,停笔良久,我才缓了缓心神,从其中慢慢走出。时间总是不饶人,刘大先所做出的青涩懵懂又诚恳执着的学术选择似乎还在昨日,但是几乎就在一晃眼间,当年那个“读书种子”就已经成为被我等后辈仰望的批评界的“高山”。作为后辈的我无意也无力于对刘大先的批评世界进行定性。此处,我只是尽己所能书写出刘大先的批评世界带给我的那份悸动与感触。刘大先的批评历程与批评世界,是始终值得我们深挖与学习的富矿。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刘大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兼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国家图书重大出版规划项目等多项,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情世界的感情》《时光的木乃伊》《未眠书》等。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