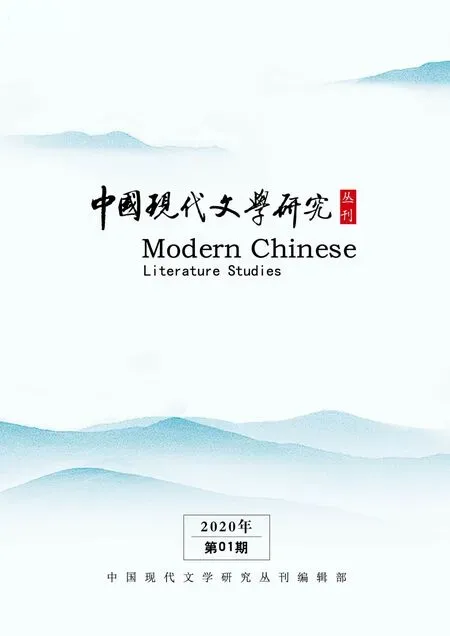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探寻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可分解为“故事”“圆满”“清官”“扣子”“绰号”“可说性”六大元素,正是由于对它们的创造性融汇,赵树理成功地创立了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评书体小说,标志着新文学从“西化”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蝶变。
学步外国文学、在欧风美雨滋润下茁壮起来的新文学曾是赵树理的文学模范,他一度创作过《到任的第一天》《悔》等“欧化”的作品。但新文学与底层民间几乎绝缘的现实,使他真切地认识到:“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①赵树理决意另辟蹊径,力争写出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又闪耀着时代思想光芒的通俗新文学。要写出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新文学,路在何方?毋庸置疑,只能回到中国的传统艺术的土壤中去。从1934年起,赵树理在创作中自觉融入大量的民族传统艺术元素,以契合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创立了一条新文学大众化之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新评书体小说。具体而言,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主要有:
1.“故事”元素
以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完整故事取胜,无疑是中国传统叙事类文学的一大法宝,或悲壮如《赵氏孤儿大报仇》,或凄美如《孟姜女哭长城》,或惊奇如《牡丹亭》,或缠绵如《西厢记》;或波澜壮阔如《三国》《水浒》,或短小精悍如“三言”“二拍”;或言世俗人生如《金瓶梅》,或述神鬼世界如《聊斋志异》;或民间故事如《田螺姑娘》,或文人之作如《红楼梦》……纵然内容各异、形式千般、风格悬殊,但莫不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可以说,喜听故事、爱看故事是中国百姓,甚至是全人类的天性,哪怕时至今日,即便是一字未识之儿童,面对一个个有趣的儿童故事,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不少儿童养成了在故事声中进入甜美梦乡的幼年习惯。在创作时,赵树理始终铭记老百姓爱听故事的传统,总是不遗余力地将故事元素融入作品,哪怕是篇幅极少的短篇小说,也坚持把故事讲得曲折、完整。如《田寡妇看瓜》,尽管也就是千余字而已,却也把田寡妇“土改”前为什么要看瓜、“土改”后刚开始也坚持看瓜、最终决定不再看瓜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总之,注重写好故事是赵树理小说的一大特点,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刊行时便被标注为“通俗故事”,有学者把赵树理小说的结构特点概括为:“大多为纵向型的故事体,整体上是一个有头有尾、首尾相顾的圆形结构”②,具有强烈的故事性。
2.“圆满”元素
学者杨春时说:“中国文化出于对理性主义的信任,对社会人生采取了乐观的态度,认为理性主宰世界,人性本善,正义将战胜邪恶,形成了所谓的‘乐观文化’,中国文化充满乐观精神,它惩恶扬善,宣扬善恶有报,并且形成了‘大团圆’模式。”③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涵养之下,赋予事情结果以一个圆满的结局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显著共性,哪怕现实中是个悲剧性事件,写入作品时,也要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比如,《孔雀东南飞》中,恩爱夫妻焦仲卿与刘兰芝,尽管生前被棒打鸳鸯,难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死后也要化成鸳鸯,比翼双飞;《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尽管遭人陷害而被斩杀,但“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三桩誓愿一一实现,最终是冤情得以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以死刑,贪官知府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因为传统文学过于追求“圆满”的结局,以至于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一度将这种“大团圆”文学贬斥为“说谎”的文学、“瞒和骗”的文学:“做书的人……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④;“中国人的精神,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⑤。传统文学这种浓得化不开的“圆满”情结,造就了中国百姓钟情“大团圆”的审美取向,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赵树理充分尊重中国百姓钟爱“大团圆”这一审美趣味,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将“圆满”元素保留了下来,其作品差不多都是以进步战胜落后、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而告终,在作品结构上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这便是:‘团圆’式的喜剧结尾”⑥,家喻户晓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将一个现实生活中自由恋爱的悲剧改写成了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故事——故事原型岳冬至、智英祥两情相悦,自由恋爱,最终不但没能结秦晋之好,岳冬至竟然因之活活被人打死,而作品中,二黑、小芹历经磨难后终成眷侣,为村中第一对好夫妻。
3.“清官”元素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传统文学之中,“清官”文学无疑是一个华美缤纷的耀眼星群。在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淫威之下,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创造出一种广泛而‘有效’的心理补偿机制,试图通过对清官的企盼、幻想、艺术张扬等神化方式,以使自己得以在心理上勉强抗衡周围无处不在的黑暗与腐败。这种机制造就了亿万下层国民心中的清官情结和通俗文艺中许许多多的清官故事”⑦。例如,在百姓心中,名列一号的清官非“包青天”莫属。包拯,庐州合肥人,北宋名臣,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称誉古今。早在宋代戏剧中,就已出现了包公戏,至元代,包公戏迎来了一个高峰,13种公案戏中,包公戏就占了11种,元代杂剧奠基人关汉卿就创作有《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两部包公戏。明清两代的传奇中也有不少关于包公的剧作,晚清民初则是包公戏的爆发期,涌现了大量的包公戏剧目,至今仍在演的就不下数十种,其中《秦香莲》《狸猫换太子》《铡包勉》《赤桑镇》等剧目更是盛演不衰。可以说,历史上,清官文学正是以其既能给匍匐于地的万千普通民众以一定的心理补偿与疗救,又能部分地填补其精神享受之空白的双重功效,深深扎根在了中国广大百姓的心中,散发出无穷魅力。
细察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不难发现,赵树理不仅将“清官”元素引入小说之中,而且在小说结构上也大胆套用了传统“清官”文学的叙述模式。赵树理明确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是将工作中遇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通过文学的形式加以呈现并探讨解决之道。传统清官文学的情节结构大致由“苦主蒙冤—清官审冤—冤案昭雪”三大板块蝉联而成,“清官审冤”是整个案情的转折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也由“问题生成—清官干预—问题解决”三大部分一气贯通,而问题的解决也是全赖于“清官干预”,只不过在传统清官文学中,“清官”都是清一色的人——朝廷大臣,而赵树理的小说中,“清官”可以是人——党和政府的干部,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区长”,也可以是某项政策制度,如《登记》中新公布的“婚姻法”使得艾艾、燕燕的自由婚姻所遭遇的来自家长、村民事主任、区助理员三方面的阻力彻底瓦解。正因为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是这般的“如出一辙”,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被有的学者称为“拟清官文学”。
4.“扣子”元素
在古代,说书是一种广为民众所喜爱的民间艺术,说书艺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如茶馆、妓馆里面为消费者说书的,另一类是走街串巷随时找个地儿说上几段的。但不管是哪类说书人,都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因此,有固定场所的说书人最希望的是听众这次听了下次还来,而走街串巷的说书人则希望听众能坚持听完而不是中途离场。那么,怎样才能牢牢吸引住听众呢?那就要好好地“卖关子”,让听众欲罢不能。关子亦称“扣子”,指在故事叙述到某个紧要处时,突然中断不讲,另起炉灶,先插入别的内容,或者让听众“且听下回分解”,其根本目的是制造悬念,黏住听众。可以说,“扣子”艺术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俯拾皆是,且不说数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长篇章回小说形成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固化模式,即便是寥寥数千字的短篇小说,也不乏“扣子”艺术。如冯梦龙《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写的是富家子弟曹可成为所欲为败尽家产、最后又在报恩的妓女赵春儿的引导下重创家业的浪子故事。整篇小说设置了不少“扣子”——曹可成吃喝玩乐败尽家产,只能在坟场终其一生了吗?赵春儿感念昔日赎身之恩,带着丰厚积蓄嫁给可成,再次拥有殷实之家的可成从此安分守己了吗?可成恶习不改,再次败尽财产,曹家还有希望复兴吗?可成真心悔恨乃至自残后,赵春儿还有妙招重振曹家吗?浪子回头的可成,最终有了怎样的结局?“扣子”一个接着一个,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赵树理小说在当年之所以不胫而走,产生轰动效应,笔者以为一是靠内容吸引人——小说所反映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二是靠艺术魅力吸引人。在赵树理小说艺术的众多魅力因子中,“扣子”具有重要意义,他自称常常“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⑧。正因为大量“扣子”的设立,才让读者(听众)欲罢不能。如《求雨》,写的是金斗坪村抗旱救灾的故事。解放前,凡遇旱灾只能组织人员去龙王庙求雨,而今“土改”后又遇上了大旱,还是像从前一样去龙王庙求雨吗?以老贫农于天佑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求雨抗旱,以党支部书记于长水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开渠引水救灾,究竟是选择求雨呢还是选择开渠呢?求雨与开渠各干各的,最终是谁胜了呢?当开渠遇到“拦路虎”石崖无法进展、不少人跑到了求雨队伍中去时,开渠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当开渠引水的成功近在眼前,连最顽固的几个老农也陆续退出了求雨队伍,只剩下于天佑一人时,他最终又会怎么做呢……如此环环“设扣”,着实让读者难以释手。
5.“绰号”元素
绰号,又称外号、诨号,即根据某人身上的一些特征给其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号,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一个恰当的绰号,往往是画龙点睛,能极生动形象地凸显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或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鲁迅曾喻其为传神的写意画:“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缺点,却更知道这是谁。”⑨在我国,绰号由来已久,《吕氏春秋》中就称夏桀是“移大牺”——其力气大得可以把牛移动。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一个有趣的绰号,如西汉甄丰因喜欢夜间谋议被称为“夜半客”,东汉崔烈以500万钱买官被称为“铜臭”,唐代温庭筠因容貌丑陋被呼作“温钟馗”,骆宾王写诗因多用数字做对子被称为“算博士”,南宋赵霈担任了谏议大夫之职却大谈禁杀鹅鸭被讥为“鹅鸭谏议”,明代程济因博学而被称为“两脚书橱”。而在我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绰号是刻画人物的一种特殊手法,《水浒传》在绰号的运用上堪称登峰造极,梁山泊108个好汉,人人有绰号,如“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等。可以说,绰号艺术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
赵树理十分钟爱绰号艺术:“外号这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你听得多了,会觉得农民的智慧的确很丰富,取的外号挺适合这个人的性格,我不过是把这些人物每人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罢了!”⑩赵树理古为今用,将古老的绰号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如《三里湾》中,袁天成老婆是村里有名的惹是生非的货,用她的那套处世哲学做人做事,往往是闹得鸡飞狗跳,“能不够”这个外号形象地说明她不是“能”得“不够”,而是能得“过了头”,简直到了让人痛恨厌恶的地步。在赵树理笔下,“铁算盘”“常有理”“翻得高”“使不得”“糊涂涂”“二诸葛”“三仙姑”“气不死”“小腿疼”“吃不饱”“小飞蛾”等一个个趣味盎然的外号,在刻画人物方面,出色地发挥了鲁迅所言的“写意传神”的作用。
6.“可说性”元素
“说唱文学可算是一种庶民文艺,一种乡土市井间的逸乐文化。”⑪作为一种古老的讲唱结合、韵文散文兼用的民间文艺,早在《史记》“滑稽列传”所载之“俳优”活动中便可见说唱的身影,四川成都出土的“说书俑”挥鼓作艺的姿态更是形象地展现了汉时说唱的动人风采。至唐代,印度佛教传入所带来的讲经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说唱的定型,宋代的百戏杂陈、瓦舍做场更是明证了说唱的一度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对此有着生动的记录。历经元明两代的再发展,至清代,传统说唱艺术终于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并穿过历史的重重关山烟云流传至今,成为不死的艺术精灵。毋庸置疑,对于历史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化程度低下的普通百姓而言,说唱艺术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和不少社会时闻、大众话题等,正是借助这种艺术形式得以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说唱艺术已深深融入了寻常百姓的血脉之中,以至于有学者如是言:“对于文人墨客、馆阁大臣来说,儒家经籍是其走向事业和人生巅峰的文化依托;对于民众而言,说唱小曲是可以沉浸其中的感性文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⑫
立志“要做一个真正为广大农民所热爱的通俗文学家”⑬的赵树理,从传统说唱文学中创造性地继承了“可说性”元素,努力使小说“成为能说的”⑭,以实现“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⑮初衷。为达到“可说性”标准,着重进行了三方面努力。首先是语言高度“口语化”,让人听得明白。他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真正达到了“言文一致”,“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恰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⑯。即使是给农民读者“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⑰。其次是内容突出“故事性”,让人听得有味。在情节的剪裁上,他一般采用顺叙法,单线索,不跳跃,不至于因为头绪纷繁或者颠来倒去的碎片化而把人听得稀里糊涂。追求故事的完整性,来龙去脉一概说清楚,不留悬念,不因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人式审美趣味而致使故事“残缺不全”,如《小二黑结婚》中,二黑小芹好事多磨终成眷属之后会怎样呢?人们难免意犹未尽,作品中“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寥寥数语,便把二黑小芹自由婚姻的终身幸福写尽了,确保了故事的完整无缺。最后是叙述力求“快节奏”,让人听得解渴。基本上是为说唱文学所熏染的中国底层民众,对充满着大量冗长心理描写和注重环境描写的外国小说是相当隔膜的,他们习惯于欣赏情节紧凑的故事。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⑱,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主要是通过其自身的行动及语言来彰显性格,这就使得赵树理小说总体上显得简洁明快,动作性强,扣人心弦。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某些元素业已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们救国心切,“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19,致使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因严重“西化”而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赵树理“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⑳,使得中国普通百姓一接触赵树理之创作便有老友重逢之感,倍觉亲切,爱不释卷,以至于当年有《小二黑结婚》一经刊出,半年间发行四万册的传播“神话”,赵树理本人也被美国记者贝尔登称誉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㉑。融入了众多传统艺术元素的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标志着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终于实现了从“西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华丽蝶变。
注释:
—— 陈廷敬
——狄仁杰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