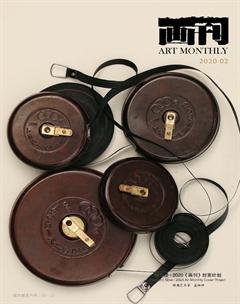实验之殇
“实验艺术”这个词,追溯起来,和范景中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的《艺术的故事》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这一本可能是中文世界最为畅销的西方艺术史话中,贡布里希(E.H.Gombrich)用“实验性的艺术”一词去概括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艺术革命。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词今天在中国的艺术语境中,不仅使用广泛,而且还成为教育部艺术学中一个学科的命名。这意味着在艺术各个门类中,其中一个分类叫“实验艺术”,高等美院因此而建有“实验艺术系”或“实验艺术学院”,有专门从事“实验艺术”的艺术家和教授在其中任教,有本、硕、博建制完整的教学体系。在极富创造力的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这可能是一项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我一直怀疑,如果贡布里希知道“实验艺术”在中国居然产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作用,他可能会瞬间昏厥。事实上贡布里希终老都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基于保守的立场,他在面对内心持有异议的艺术革命时,机智地发明了多少有所中性、在解释上或许会有所散漫的“实验性的艺术”这个词,试图说明20世纪初开始的一系列超出古典范围与常识判断的艺术变革。其实,睿智的贡布里希很清楚自己的意图,这个浸淫在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中、信奉波普证伪主义哲学的伟大学者,在面对纷繁的新艺术时,谨慎从事成为他一贯的风格。这有点像贡布里希强调“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一样,“实验”这个词会让他在面对汹涌而来的艺术革命时,留下一种从容描述的态度。
“实验”这个词首先和科学相关,而不是艺术。实验是科学得以向前发展的关键环节。按照波普所描述的原则,实验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因此实验对于科学结论具有判决性的意义。姑且不讨论证伪与证实相互依赖的关系究竟如何,就实验来说,其成立的前提却是理论本身。也就是说,所有实验都必须基于一种理论、一套逻辑,以及一个或若干个具体的问题才能成立。实验是对问题的判决,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实验,应该叫作失败的实验,或者干脆就不能叫作实验。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实验中所遗留或者逸出原先的实验,因而暂时无法解释的事实,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实验的起点。反过来说也一样,设计实验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先行,否则对实验的设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我们把实验理解为有明确目标的观察,那么,波普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了。他强调先有理论、后有观察,而不是相反。相反的观察不叫观察,没有理论指导的观察不称其为观察,那只能叫胡乱扫描。
现代科学的发展最令人眩迷的一点是,我们发现许多科学结论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所眼见的,以及所触摸到的现象相悖离。这一点对人的创造性思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现代主义艺术本身有很多内在或外在的动力,否则它无法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现象。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刺激无疑受到了科学发展的鼓舞,让艺术家滋生出一腔热血,努力让艺术也呈现出无愧于科学的面貌。科学结论超乎人的意料之外这一事实,也让艺术家获得了极大的精神鼓励,让他们在形式和风格上作更为大胆的尝试。贡布里希认为,促成艺术革命的其中一个因素“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现代科学思想往往显得极其深奥难懂,然而事实证明它们有价值”。所以,“艺术家和批评家过去和现在都对科学的威力和声望深有印象”,由此“产生了信奉实验的正常思想”。不过,更重要的是贡布里希随之指出:与此同时,艺术家和批评家“也产生了不那么正常的思想,信奉一切看起来难解的东西”。
我们应该把贡布里希在这里所作的描述理解成他对自己所使用的“实验性的艺术”的说明,他其实深刻地看到了现代艺术革命的两面,正常的一面和非正常的一面,更看到科学与艺术的根本差异。他想明确的意思是,艺术从科学中所获不少,但科学却和艺术没有关系:“不过遗憾得很,科学不同于艺术,因为科学家能够用推理的方法把难解跟荒谬分开。”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很重要:“艺术批评家根本没有那一刀两断的检验方法,他却感觉再也不能花费时间去考虑一个新实验有无意义了。如果他那样做,就会落伍。”贡布里希想说的是:对于艺术来说,是否属于实验不重要;重要的是,伴随着艺术革命而来的是一种广泛流行的风气,那就是害怕“落伍”!贡布里希大概没有认为整个现代艺术是一种“荒谬”,他一直在其漫长的研究中耐心地寻绎其中的真正价值,并试图用人们可以理解的理性描述去说明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因,比如某种有效的心理动机和整体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就是说,在现代艺术的语境中,害怕“落伍”比从事“实验”更重要。如何才不会“落伍”?这可能意味着,艺术家和批评家几乎不分原则地必须去赞美所有新出现的尝试,不管是新的风格还是新的荒谬。有意思的是,贡布里希把这一现象看成是一条“经济原则”:“在经济学中,一直告诫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否则就要灭亡。”“没有一个实业家能豁出去,不怕戴上保守主义的帽子。他不仅必须跟着时代跑,而且必须被人家看到他在跟着时代跑。保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最时髦的作品装点他的董事会办公室,越革命越好。”[2]
用经济学原则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则,比如美学原则,甚或哲学原则,可以简单解释为什么艺术界中人躲避“落伍”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从这里出发,把解释再往前延伸,我們就恍然明白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及的“象征交换”究竟意味着什么。1998年,我曾经阅读了布氏的一些著作,对此问题有所领悟,并通过对广州前卫艺术小组“大尾象”和侯瀚如的成功合作,探讨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是如何把“反抗”转变成“利润”的,其中的中介就是“名声”[3]。“名声”要保证永不“落伍”,好维持一个“先锋”的形象,本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的确需要睿智,更需要机遇。
今天“实验艺术”也具有同样的经济学功能,它是一个地盘、一块观念高地、一套体系,但其中的理论尴尬却是不言而喻的。结果是,乐意引用贡布里希的说法为“实验艺术”正名,只讨论艺术如何借鉴于科学,却不讨论科学如何相异于艺术,甚而至于,以此为理由,把艺术的先锋性悄悄地和高科技作一个隐晦的联系,好让实验艺术获得科学的支持。从理想角度看这无可厚非,只是我担心,艺术等同于高科技的同时,也是艺术寿终正寝的日子。毕竟,艺术仍然极大地相异于科学,其价值目标也无法和纯粹的科学相等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目标——艺术毕竟以广泛的伦理价值为先导,以具体的社会针对性为方向。
2020年2月5日草于温哥华,时中国正经历严重之疫情,亲人身在其中,心系念之。
注释:
[1]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林夕译,北京三联,1999年,15页。
[2]引文同上,613页。
[3]杨小彦《反抗的利润:跨文化的艺术现实及共获利方式》,见《天涯》杂志,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