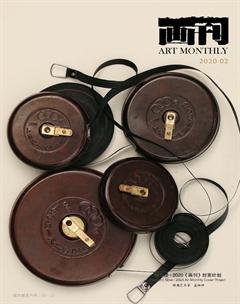“星星”在1979:展览和语境
巫鸿

在討论“星星”时,学者们经常引用王克平的雕刻作品以强调这个群体的政治性和颠覆性,而很少提到这次展览以及1980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中的其他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审视这两个展览的话,我们会发现,王克平的那种直言不讳的政治作品只占少数,其他作品则隶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组以黄锐的“圆明园”系列和尹光中的《春天还是春天》为例,以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意图促进当下的社会政治转型。这些图像把“文革”表现为过去的噩梦,同时为国家设想了光明的未来。数量更多的另一组作品包括风景、静物和肖像画,与“无名”及其他同人画展中的作品接近。正如前面谈到的,这些非政治性的形象也带有政治目的性,所挑战的是当时仍然存在的“文革”式官方艺术。
在“星星美展”中,这三种作品(包括王克平的政治寓言)并不相互对立或互为排斥。事实上,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可以隶属于多个类别。由此,王克平的雕刻也包括轻柔的女裸体,黄锐的作品中也有以轻松的后印象派方式描绘的派对场景。一般来说,我们不应该把“星星”展览和“星星”艺术简化为单一的姿态或维度。艺术家希望表达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一致观点,而是将这个展览作为个人作品和观点的表达渠道。这个观点在“星星美展”的前言中表达得非常清晰:“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尽管如此,“星星”与其他同人群体和展览仍有区别,即它对创作自由更明确的承诺。在1979年的中国艺术中,不仅王克平对政治权威的抨击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作为最初的街头公开展览,这个展览为“后文革”时期的另类艺术树立了一个标杆。随着艺术院校的重建与非政治主题的普及,“无名”和其他诉求“艺术为艺术”的团体不再是官方主流艺术的真正反对者。但通过与其他激进团体的合作以及对艺术自由的直接要求,“星星”挑战了当时艺术中的折中倾向,保持了另类艺术的棱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星星”可以被视为广义“政治前卫”(political avant-garde) 的一个实例。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群体,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其“前卫”的身份。当时的情况是:政府本身也正在经历一场至关重要的变革,并且江丰和刘迅等“改革派”文化官员也和“星星”成员一样,有着对更加自由开放的政治制度的渴望。“星星”与体制因此不是完全对立的。“星星”之所以是政治“前卫”,是因为它在1979年比其他任何人,包括思想开放的干部以及其他同人群体,在促进民主和艺术自由上走得更远。它所发动的活动是前所未有的:街头展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而王克平也在公开讨论毛泽东的“错误”的几年前就创造了《偶像》。
然而,作为一个组织松散的同人群体,“星星”的性质是不稳定的,也因此容易接受妥协。1979年11月23日,在北京美术家协会的赞助下,“星星美展”转移到了北海公园画舫斋。虽然它继续引起轰动,在10天内接待了2万多名观众,但它已不再是对主流艺术机构的挑战——这个活动已经合法化,甚至连《人民日报》刊登的展览报道也采取了赞同的语气。“星星”的合法地位在1980年夏天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其成员——那时已近40个——正式成立了一个“画会”,并申请加入北京美术家协会。申请通过后,第二届“星星美展”于当年8月20日至9月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内举行。在这个过程中,“星星”从“外部”转变为“内部”,因此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第二次展览后,它的许多成员移居国外。他们在国内当代艺术界中的消失,将由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和艺术运动填补。(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