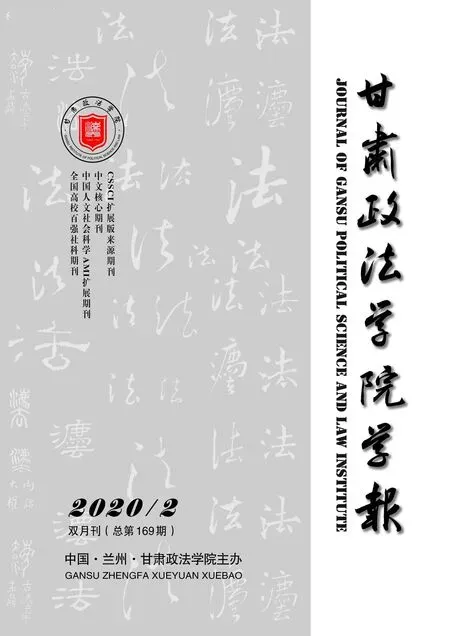程序/实体: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性质分析
曹云吉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学者对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间关系的研究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为正当当事人的规定。(1)张卫平:《正当当事人:内涵与基础》,载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1页。同时指出正当当事人是实体问题。这一结论的理论逻辑是“实体权利义务人=实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不过,非实体法律关系主体亦有成为正当当事人的情形。(2)同前注〔1〕,第107-108页。还有学者指出,正当当事人为诉讼要件,是法院依职权予以调查之事项。(3)[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因此,其应为程序性事项。该种见解下的逻辑为“程序性事项=诉讼要件=正当当事人”。从上述角度来看,关于正当当事人“程序/实体”性质的判断,至少涉及如下概念间的关系,即“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和“诉讼要件”。
如果假设第一个逻辑“实体权利义务人=实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成立,亦假设“程序/实体”为对立之范畴,那么由于“程序性事项≠实体性事项”,因此以正当当事人为连接点的两个逻辑就不能形成“全等”。同样,假设“程序性事项=诉讼要件=正当当事人”成立,获得的也是同样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正当当事人为诉讼要件,且正当当事人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均为理论研究中的多数学说。既然存在以正当当事人为连接点的两个概念,那么至少可以说,在诉讼要件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若假设“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正当当事人=诉讼要件”,同时又要坚持“程序/实体”为对立存在之范畴,则可待商榷。换句话说,以“程序/实体”之对立存在为出发点获得对立的结论,即为“诉讼要件=程序性事项≠实体性事项=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那么若“诉讼要件=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成立,则“程序/实体”的关系将会被重构,进而再以“程序/实体”为界定正当当事人性质的标准,则有待商榷。
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下问题,即若上述“诉讼要件≠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那么以“程序/实体”的对立为前提而对正当当事人性质的界定就不存在问题。但若“诉讼要件=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成立,那么“程序/实体”这一对立的范畴的关系将被重构,再以其作为定性正当当事人性质的标准,则存在问题。那么必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正当当事人性质以及其为何种性质。
二、“程序/实体”概念的关系
继受罗马法而形成的德国普通法时期,诉讼(actio)体系逐渐向实体权利体系转变,同时作为权利保护体系的民事诉讼法也逐渐从作为权利体系的实体私法中分离。由于当时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尚未成为独立的诉讼类型,学问体系当中被作为研究对象的仅仅是给付之诉。 进而只有权利人与权利侵害人这样的实体法律关系主体才具有正当当事人资格。 那时并没有现在的诉讼实施权的概念,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标准被称为“本案适格”。本案适格指的是以系争权利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权利归属主体资格。 在那时,本案适格是本案审理前的问题,即属于今日所说的诉讼要件层面的问题, 进而与作为本案问题的系争权利本身的有无相区别。(4)不过,在19世纪中叶以后,学者们提出本案适格不应是先于本案审理的诉讼要件,而应当是诉的理由的一部分,因此应当是本案问题,欠缺本案适格时,应当以原告请求无理由而驳回诉讼请求。自此,本案适格被作为本案问题又重新回归到本案审理当中。 而伴随这一过程而产生的便是实体当事人的概念。该实体当事人指的是“主张及被主张自己为实体法律关系主体”之人。进而由其填补了本案适格回流之后所留下的“正当当事人资格”内容的空缺,进而成为新的正当当事人资格的判断标准。
从上述的资料来看,“正当当事人=诉讼要件=实体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确实出现在仅有给付之诉的年代,而且目前我国学界亦有支持此见解的观点。(5)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虽然这样的逻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曾作为诉讼要件发挥程序功能。因此,若从诉讼要件与实体权利义务人并非完全不兼容甚至存在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可作为诉讼要件这一角度来看,“程序/实体”并非是截然对立存在的范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关系,进而使得程序性的诉讼要件可以与实体性的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兼容。那么究竟“程序/实体”概念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
沿袭德国法系的法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即概念的抽象性。概念每归纳一次,就被“抽象”一层。实体法中如此,诉讼法亦是如此。从诉讼法学说史的角度讲,诉讼法学经历“归属于实体法”“附属于实体法”“独立于实体法”和“超然于实体法”四个阶段。伴随于此,程序法概念也经历了从实体法概念中脱离、进而独立、再进而超然于实体法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实体法概念的机能逐渐从“决定程序法概念之性质”向“确定程序法概念之内容的标准”转变。而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因“程序”在纠纷解决机能中的作用逐步凸显,进而导致在决定程序法概念之内容的标准方面产生了不同于实体法的标准,为了统合这些不同的内容标准,使得程序法概念相对于实体法概念被进一步抽象。
从实践或制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纠纷均可通过同种诉讼程序予以处理。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即不同的实体法概念可通过相同的程序法概念予以涵括。进而同一程序法概念几乎可以包纳多种在实体法上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如当事人概念,几乎所有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纠纷的主体在诉讼程序中均可被称为“当事人”。另外,在诉讼担当的情形,非法律关系主体亦可被称为“当事人”。因此从这个角度亦可以说明程序法概念相较于实体法概念更具“抽象性”。
从上述来看,随着学说史的发展,程序法概念从实体法概念的下位概念逐渐转变为实体法概念的上位概念,两者的关系是在“纵向”层面而非“横向”层面发生变化。如果说在诉讼法归属于或附属于实体法的时代,程序法概念无论是性质还是内容均从实体法中寻求,进而即认为该程序法概念的性质即为实体性质的话,则当诉讼法独立于甚至超然于实体法时,是否可以说程序法概念的性质为“诉讼性质或程序性质”呢?
分析这一问题,必须存在一个理论前提,即“程序与实体”不能在同一程序法概念中“兼容”。否则,如果“兼容”,讨论程序法概念究竟为实体抑或程序性质则失去了意义。而恰恰程序法概念是可以“兼容”实体与程序“两性”的概念。从上述程序法概念与实体法概念间关系的发展过程来看,当程序法概念超然于实体法概念时,实体法概念从“决定程序法概念之性质及内容”的地位转变为“确定程序法概念之内容的标准”的地位。仍以本文讨论的“正当当事人”予以说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理论通说,正当当事人为诉讼要件,而诉讼要件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程序性事项,但是在判断何人为正当当事人时,则以“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为标准,而这就好比在“正当当事人”这一“理论空盒”中装入了“实体权利义务主体”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正当当事人判断标准的学说演变来看,其经历了“事件适格——实体当事人概念——管理权——法的利益——期待说——争点适格论”的演变。(6)事件适格指的是主观权利归属资格,即实体权利人。参见[日]中村宗雄:《訴訟遂行権の系譜的考察》,载《民事訴訟法学の基礎理論》,敬文堂昭和32年版(1957年),第116页。所谓的实体当事人概念指的是主张其为构成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能动主体(权利人)的人及被主张为侵害权利之人。参见[日]松原弘信:《民事訴訟法における当事者概念の成立とその展開(一): ドイツにおける学説の変遷を中心に》,载《熊本法学》1987年总第51号,第97页。所谓管理权说,依照赫尔维希的见解,诉讼实施权由财产管理权的所在确定。由于通常情形下,财产管理权归属于财产主体,因此诉讼实施权通常也是由财产主体所享有。参见[日]山本弘:《権利保護の利益概念の研究(三)》,载《法學協會雜誌》1989年第106卷第9号,第1556页。法的利益说指的是关于作为诉讼标的之权利关系的存否以本案判决的形式予以确定时,何人作为当事人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参见[日]兼子一:《新修民事诉讼法体系》(增订版),酒井书店1965年版,第158页。所谓期待说指的是应选择可被期待充分实施诉讼之人作为适格当事人,进而使纠纷能够彻底解决的学说。该种学说最初是由谷口安平教授针对公司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而提倡。参见[日]谷口安平:《判决效扩张与当事人适格》,载[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88页。争点适格论是由日本井上治典教授提倡的,其以“程序保障第三波学派”独有的程序保障观为依据,以“辅助参加利益”为突破点,进而建构出作为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之争点适格论,即对于诉讼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事项,谁更适合作为当事人实施诉讼。参见[日]井上治典:《多数当事者の訴訟》,信山社1992年版,第166页。这种演变过程展现出来的便是“实体标准”向“程序标准”的转变过程。如果判断标准的实体或程序性质能够决定程序法概念的性质,那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当判断标准为实体标准时,正当当事人就为实体问题,进而就成为本案问题;而当判断标准为程序标准时,正当当事人则成为程序问题,进而发挥诉讼要件的机能,进而正当当事人性质本身也就发生了从实体到程序再到实体这样的演变”。如果正当当事人本身也发生了实体、程序的交替演变,那么很难想象,当其作为本案问题时,是如何发挥诉讼要件机能的呢?一个诉讼要件事项又如何同时又是本案问题呢?而且,如果要坚持正当当事人的诉讼要件性质,那么根据该种逻辑,其判断标准必然只能是纯程序性的,而不可能具有实体性,因为一旦具有了实体性,就会变为本案问题,而这样的逻辑与学说史不吻合,因为学说史上出现过如事件适格、管理权等实体性的判断标准。
因此,上述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实体到程序的性质转变”。那么,正当当事人概念本身是否也存在着这种转变呢?
应当说,民事诉讼程序是在以“民事诉讼目的或功能”为指导而形成的以“诉权论为起点、既判力理论为终点”的“轨道”上运行的“纠纷解决装置”。“轨道”上的任一“站牌”所形成的理论节点均与诉讼目的或功能“勾连”,进而在一个“横向”的程序过程中予以展开,而这个过程与上述的程序概念与实体概念的“纵向”发展不同。
界定某程序法概念性质的目的在于确定该概念在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即其属于起诉程序中的概念还是审理程序中的概念。进而根据其存在的不同程序阶段,发挥不同的程序功能。对应不同的程序阶段,在诉讼法理论上存在着起诉要件、诉讼要件、实体本案问题等界定程序法概念性质的范畴。这些概念范畴是与诉讼程序阶段相衔接“横向”排列存在的。需要探讨的只不过是应当将正当当事人置于“何种范畴”之中以发挥相应的程序功能。
因此,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程序/实体”的性质界定标准应当适用于“程序法概念之判断标准”的界定,如将实体权利义务人作为正当当事人的界定标准时,仅仅是正当当事人的界定标准具备了实体性或程序性,而非正当当事人概念本身;二是从程序本身出发,正当当事人作为程序法概念,是与相应的程序功能“挂钩”的,进而对其性质亦应从“程序进程”的“横向”视角予以界定,即其应为“起诉要件”“诉讼要件”还是“实体本案问题”。因此以“纵向关系”为主的“实体/程序”标准不适用于“横向定位关系”的“程序概念”。
那么,接下来需要探讨的便是处于“横向”定位关系的程序法概念的正当当事人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要件。
三、正当当事人性质与诉权机能
(一)诉权机能的转变——“起诉——判决”
应当说与本文所要论述的正当当事人概念关系最密切的概念为“诉权”。从现在的理论通说来看,正当当事人是诉讼要件,而诉讼要件理论是在诉权理论演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7)[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而且,正当当事人也被纳入到了诉权利益概念之下。(8)[日]同前注〔3〕,第175页。因此,要研究正当当事人的性质问题,需从诉权问题入手。
诉权理论经历了私法诉权说、抽象公权说、具体公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等学说演变,(9)[日]同前注〔7〕。高桥宏志教授对诉权学说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论。该演变趋势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把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诉权学说的发展实际上主要体现的是诉讼法与实体法、诉讼法与以宪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从学说史的发展来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无疑是整个诉权学说发展的主旋律。
从微观的层面把握,那么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诉权的内容层面及机能层面。从机能上来讲,诉权概念所要处理的无疑是与起诉、判决的关系,(10)关于诉权因何而生,参见中村宗雄:《訴權學說と訴訟理論の構造》,载民事訴訟法學會:《民事訴訟法講座》(第一卷),有斐閣1954年版,第45页。相同观点参见[日]齋藤秀夫:《民事訴訟法概論》(新版),有斐閣1982年版,第37页。即诉权的机能在诉权学说史上发生了从起诉机能向判决机能的转变。从内容上来看,诉权所要处理的无疑是与请求权或实体私权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不同的诉权学说下,请求权或私权是否先在或既存;二是请求权或私权中是否内含有“诉权”。
据此,可将请求权先在与否以及内在于实体权利或请求权与否作为变量,画出如下图示。

诉权的机能层面与诉权的内容层面并非是决然无关的两个层面。诉权概念是基于“为何可以起诉”这一问题而生,(11)[日]中村宗雄:《訴權學說と訴訟理論の構造》,载民事訴訟法學會:《民事訴訟法講座》(第一卷),有斐閣1954年版,第45页。相同观点参见[日]齋藤秀夫:《民事訴訟法概論》(新版),有斐閣1982年版,第37页。而“实体请求权内含诉权,进而其先于诉讼而存在”则成为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初答案,此即私法诉权说。(12)[日]富樫貞夫:《ドイツ訴権論の成立過程--とくにその前提条件を中心として》,载日本民事訴訟法學會:《民事訴訟雑誌》1965年总第11卷,第115页;[日]奥田昌道:《請求権概念の生成と展開》,創文社昭和五十四年版(1979年版),第45-46页、第63-64页。而后的抽象公权说则是与私法诉权说完全相对立的“解释论”,即因为实体请求权是于判决生效时产生,因此诉权并不内含于实体请求权,而是独立于实体请求权而于诉讼前既已存在。(13)[日]富樫贞夫:《ドイツ訴権論の成立過程--とくにその前提条件を中心として》,载日本民事訴訟法學會:《民事訴訟雑誌》1965年总第11卷,第121-122页。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均为“为何可以起诉”寻求答案,只不过后者认为诉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公法上的权利。(14)同前注〔13〕。处于两者之间的便是具体公权说或权利保护请求权说。(15)同前注〔13〕;[日]富樫贞夫:《権利保護請求権説の形成》,载《熊本法学》1965年总第4卷;[日]奥田昌道:《請求権概念の生成と展開》,創文社版昭和五十四年版(1979年版),第102页以后。从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开始,诉权的机能从起诉转移至判决。而这种诉权机能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诉权无法说明为何诉权在具有起诉机能的同时亦具有“请求胜诉判决”的机能。
之所以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无法同时具备起诉与“请求胜诉判决”两项机能,主要因为如下原因:若权利保护请求权论仅仅关注的是起诉机能,就不能与抽象诉权论予以区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在于对于何时作出胜诉判决,具体诉权论提出了“权利保护要件”,而权利保护要件被作为诉权成立要件。在具备权利保护要件时,应当作出胜诉判决。因此,应当说在具体诉权论下存在如下逻辑:权利保护要件成立——诉权成立——胜诉判决。另外,如果说具体诉权理论同时兼顾起诉与胜诉判决两项机能的话,那么上述逻辑则应当是:权利保护要件成立——诉权成立——起诉——胜诉判决。(16)[日]富樫贞夫:《権利保護請求権説の形成》,载《熊本法学》1965年总第4卷,第6页。因为在赫尔维希的理论里,“请求给付判决、形成判决、确认判决的诉权从事实的角度来讲是基于诉讼外、诉讼前的要件事实而存在,从法律上来讲,是基于法秩序而客观的存在。因此,提起诉讼是在判断原被告究竟何方当事人应当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不过,上述“权利保护要件成立——诉权成立——起诉——胜诉判决”的逻辑存在一个问题,即当原告败诉时,自然是被告能够请求获得有利判决,即被告享有权利保护请求权。那么原告起诉的正当性理由何在?原告为何能够基于被告在诉前成立并存在的权利保护请求权提起诉讼?因此权利保护请求权论必然面临着如何协调“起诉机能与胜诉判决机能”的问题。(17)当然,有论者可能会指出:权利保护请求权根本就不关注起诉问题,仅仅关注胜诉判决如何获得的问题。那么作者提出的疑问是,如果真如论者所言,那么赫尔维希将“诉的可能性”从实体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意义何在呢?即既然起诉机能与权利保护请求权无关,那么起诉的正当化依据在哪里?或者说赫尔维希将“诉的可能性”从实体私权中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将其命名为“权利保护请求权”,进而发挥起诉机能,那么“诉的可能性”又被命名为何呢?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诉的可能性”分离的意义在于将诉权从实体私权中独立出来,进而发挥起诉机能,只不过因为本部分论述的问题,导致向判决机能转化。
从上述逻辑来看,出现问题的是原告起诉的权能与权利保护请求权先在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赫尔维希将起诉的正当化理由归结为“起诉自由”,(18)[日]中村宗雄:《民事訴訟理論の再構成》,洋々社1955年版,第223页。进而将诉权与起诉这一行为本身分离,使得诉权机能后移,由于赫尔维希将一个制度性的“起诉自由”作为“为何可以提起诉讼”的解释学理由,进而也就使得诉权本身从包括起诉+要求判决转变为指向胜诉判决的权利。正如日本学者中村宗雄教授指出:“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最终将为何可以起诉的问题置于其解释之外。”(19)[日]中村宗雄:《訴權學說と訴訟理論の構造》,载民事訴訟法學會:《民事訴訟法講座》(第一卷),有斐閣1954年版,第54页。
其后在德国产生而在日本奠定通说地位的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实际上仍然将起诉委诸于“起诉自由”,而将诉权之机能定位为“请求本案判决”。这种脱胎于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又向抽象公权说靠近了一步。
不同的诉权学说针对“为何可以起诉”“为何可以获得本案判决”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论,进而导致诉权机能从起诉机能转变为判决机能。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便是诉权要件从起诉条件转变为“请求本案判决”的要件。换句话说,随着诉权机能的转变,诉权要件逐渐从“起诉要件”中脱离,在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下形成了以胜诉为目的的权利保护要件。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则是将权利保护要件中的诉讼性的权利保护要件与实体性的权利保护要件分离,将前者改造为“诉讼要件”,形成了以获得本案判决为目的的诉讼要件理论。(20)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上)》(修订七版),三民书局2010年版,第85页。
(二)诉权机能转变与正当当事人性质
需要明确的是,正当当事人性质的演变是随着诉权机能的演变而演变,还是随着请求权或私权的先在或既存与否而演变。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澄清正当当事人概念是与诉权连接在一起,还是与实体权利或请求权连接在一起。因为从诉权学说的发展来看,诉权与实体权利或请求权经历了从“归属——依附——分离”的演变,当两者分离时,正当当事人是随着两者中的何者演变呢?如果正当当事人随着请求权或实体权利的性质而转变,那么就会发生如果请求权或实体权利先在,当事人则应当于起诉前具备正当当事人资格,若请求权或实体权利不先在,那么当事人则于判决后才能确定其是否是正当当事人的问题。这样的演变则与学说史存在极大冲突。在学说史上,正当当事人的判断并非以“实体权利或请求权人”为唯一标准,还有如“诉的利益”“管理权”等标准。因此如果认为正当当事人概念的性质演变是随着实体权利或请求权的先在与否而演变,可以说并不符合学说史上的事实。因此可以明确,正当当事人性质的演变应当与诉权机能的演变相关。只不过在诉讼法附属于实体法的时代,这种关系被诉权与实体请求权的关系所掩盖,而在诉权与实体权利关系相分离后,这种关系便“显现化”。若上述结论成立,则诉权机能的转变会导致正当当事人在性质上的转变。即正当当事人这一程序概念本身的机能亦从起诉转变为判决。
从上述来看,私法诉权论、抽象公权论中诉权的机能在于起诉机能,那么只有享有诉权之人才能开启诉讼程序,这也就决定了开启诉讼之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可以说在私法诉权说下,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是在实体审理之前就需要确定的。因此,其应当为开启实体审理的要件,即起诉要件。此时,当事人概念与正当当事人概念“重合”,当事人概念本身即具有担保当事人正当性的机能,没有诉权就不能成为当事人。
权利保护请求权论下的诉权由于不能兼具起诉机能与胜诉判决机能,最终使得诉权的机能从起诉后移至胜诉判决。进而起诉的正当化依据被委诸于“起诉自由”,那么这就使得起诉之当事人无需具备担保当事人正当性之机能。至此,由于诉权机能后移而发生了正当当事人与当事人概念的分离,因此在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下,正当当事人的性质完成了从起诉要件向以请求胜诉判决为目的的权利保护要件的转变。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实际上是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下的诉讼性的权利保护要件独立为诉讼要件。(21)同前注〔20〕。因此,随着诉权从权利保护请求权转向本案判决请求权说,正当当事人的性质也发生了从权利保护要件向诉讼要件的转变。
(三)小结
从上述对诉权学说的研究可以看出,私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均认为当事人的正当性应当是开启诉讼程序的要件,而之后的审理阶段为本案审理阶段。在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下,由于诉权不再具备起诉机能,因此起诉时无当事人正当性的审查要求,进而在起诉阶段无需对当事人的正当性予以审查。结果便是当事人正当性的审查被转移至起诉之后的审理过程之中,进而使得当事人概念与正当当事人概念分离。当事人则被置于起诉阶段,成为起诉的要件之一,而正当当事人则被置于起诉后的审理阶段,成为诉讼要件之一。
四、我国正当当事人性质的界定
关于我国当事人概念及理论的由来,有论者指出我国当事人概念的形成与前苏联的当事人理论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就是对前苏联当事人理论的移植。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正当当事人或当事人适格的概念,在说明当事人概念时,就赋予了其正当当事人的含义。(22)张卫平:《正当当事人:内涵与基础》,载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7页。相同见解可参见肖建华:《寻求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当事人概念的再认识》,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前苏联及东欧学者认为:“并不是一切有权利能力之人都能成为具体案件的原告,而对提起这项诉讼有法律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原告。并不是一切具有权利能力的人都能够成为具体案件的被告,只有确实侵犯了原告的权利或对原告权利提出争执的人才可作为被告”。进而,民事诉讼中,与案件无实体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成为当事人。(23)肖建华:《正当当事人理论的现代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不过论者也指出:“即便在前苏联,学者也意识到当事人概念在程序上的独立意义,即(1)承认法庭审理的对象是一种推定的或有争执的民事法律关系。争执的相对方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只有在审判之后才能知晓,因而不可能在提起诉讼之初预先解决。有权请求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不仅是确实存在的和确实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而是所有的人,只要他们善意的认为自己确实享有某项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因他人提出争执而需受到保护。而这样的意识实际上是承认了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不一定一致。(2)苏维埃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正当当事人和非正当当事人的概念,诉讼中查明当事人一方属于非正当当事人时,只要对方同意,可准许正当原告或被告替换,替换后,重新开始审理。最初的原告或被告虽然是非正当的当事人,但也不能否认其曾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参见肖建华:《寻求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当事人概念的再认识》,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由此可见,在前苏联,起诉阶段的当事人本身即需具备“正当性”,因而当事人即为正当当事人,两者于起诉阶段“重合”,这与其独特的诉权理论相关。
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认为诉权应有三部分内容,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起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胜诉权)、认定主体资格意义上的诉权,此被称为三元诉权论。(24)关于三元诉权论的内容,详见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8页。另外,前苏联学者对二元诉权论的正当性作了如下论证:诉是一种保护权利的手段。原告在向法院请求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被告提出要求。因此诉区分为诉讼法与实体法两面。其中程序意义上的诉为原告向法院提出的权利保护请求,实体意义上的诉为原告通过法院向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上的请求。而诉权则应当对上述两方面均应有所反应。针对前者的诉权即为起诉权,针对后者的则是胜诉权。参见江伟、单国军:《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另外,基于上述顾尔维奇的理论,前苏联学者多博罗沃里斯基等在所著《苏维埃民事诉讼》一书中提出二元诉权论,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质意义上的诉权。(25)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国理论界对诉权的认识主要受前苏联诉权理论的影响。(26)同前注〔5〕,第180页。在该影响之下,产生了“双重诉权说”。(27)所谓双重诉权说指的是诉权具备双重含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前者指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和被告针对原告请求事项予以答辩的权利,即起诉权和答辩权。后者指的是原告可通过人民法院向被告提出实体上要求的权利和被告可通过人民法院反驳原告提出的实体上请求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即胜诉权和反驳原告提出的实体请求的权利。同前注〔5〕,第181页。正是这样的诉权学说,使得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长期以来被解释为法院审查起诉及决定是否立案的标准。(28)吴英姿:《论诉权的人权属性——以历史演进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双重诉权论实际上具备了上述多种诉权的特点。我国有论者指出双重诉权论实际上是具体诉权论的变种,是将具体诉权论中的诉讼性的权利保护要件与实体性的权利保护要件作为两种诉权分开定义。(29)李龙:《民事诉权论纲》,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二元诉权理论实际上是源于抽象诉权说与具体诉权说,可以说是两者的综合。本文认为,从“二阶段程序构造”来看,实际上二元诉权论更接近于私法诉权论,而从要件的内容来看,则更接近于具体诉权论。而将具体诉权论下的要件即诉讼性权利保护要件独立为“起诉要件”的作法,则是类似于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将诉讼性权利保护要件作为诉讼要件的作法。只不过,二元诉权论下,将诉讼要件装入了“起诉程序”之中。因此,可以说二元诉权论是利用了私法诉权论下的程序构造,利用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权利保护要件,又以类似于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的作法,将诉讼要件从权利保护要件中独立出来,将其“装入”到“起诉程序”之中。
不过,虽然我国诉权理论采“双重诉权论”,但并不代表存在着“两个”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仅是起诉要件。理由如下:首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第1项为“原告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在实体审理过程中,如果明确当事人非正当当事人,那么以“驳回起诉”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判定并非是作出实体胜诉或败诉判决的条件,而是起诉是否合法的条件。
起诉条件设置的本来目的主要是平衡“司法资源”与“诉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防止无益诉讼等耗费司法资源。但门槛过高,不利于诉权保障;门槛过低,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起诉阶段判定当事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而不予受理的做法节约了司法资源,但却使得案件在未进入实质双方对席审理时即不予受理,无法实现“诉权保护”的目的。在受理后的实体审理阶段判定当事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而驳回起诉的做法,并不能终结本案诉讼。因为驳回起诉的案件,当事人在具备起诉条件后仍可再次起诉。因而,从实质上讲,并未完全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窘境”,是因为将“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并置于“起诉阶段”。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存在如下三条:即(1)若仍然坚持“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那么在审查阶段上,应当后移至审理阶段。这无疑就在正当当事人之外独立出“当事人”的概念,并置于“起诉阶段”,进而形成了“当事人+起诉阶段”、“正当当事人+审理阶段”的程序构造;(2)正当当事人仍然为起诉阶段的审查对象,但是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人“解绑”,将对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判定置于审理阶段。这样的结果必然形成“正当当事人+起诉阶段”、“实体权利义务人+审理阶段”,进而正当当事人的概念中要“装入”不同于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内容;(3)“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但将正当当事人的审查“跨越”“起诉+审理”两个阶段。

审理阶段改革路径 起诉阶段审理阶段路径一当事人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路径二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路径三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
上述改革路径的实现无疑是以如下理论为基础:即(1)不同的程序功能应由不同的程序概念予以承担;(2)程序概念与界定程序概念的标准不同一。以此为前提,上述何种路径符合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无疑是选择改革路径的核心因素。无论采上述何种改革路径,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起诉阶段关于当事人资格的审查标准将低于“实体权利义务人”,进而有利于实现“诉权保障”。应当说,第二条路径似乎更为符合民诉法第119条的规定,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的规定的前提是“正当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人”,如果选择第二条路径,就要重新对“直接利害关系作不同于实体权利义务人”予以解释。第三条路径较符合目前司法实践的做法,即起诉阶段坚持“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30)最高人民法院(2014)最高法民二终字第39号“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太原市北晨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中指出:“就本案而言,中银公司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已提供了其与华融太原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表面已证实中银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向北晨公司起诉主张权利,应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且案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实体审理。”即将对“正当当事人”的审查作为“以诉状记载之当事人为起点、以实体权利义务人为终点”的连续体予以把握。实际上在起诉阶段对于当事人资格的审查亦未达到“具备直接利害关系”的程度。因此,第二条与第三条路径于起诉阶段审查当事人资格时,实际上均是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与实体权利义务人分离”。但是,如果对整个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当事人”的规定作体系解释,可以发现,民事诉讼法中确实存在着独立于“正当当事人”的“当事人”概念。(31)曹云吉:《立案登记制下“当事人”的程序构造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5期。因此,无论是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上述三种改革路径均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若仍然将正当当事人置于起诉阶段,作为起诉要件,那么应当明确,“审查标准<实体权利义务人”并不代表“审查标准=0”,即当事人也需具备一定的“正当性”,只不过其无需是“实体权利义务人”。
将正当当事人置于起诉阶段,有可能导致起诉要件的“高阶化”。(32)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但是为了赋予立案受理阶段被不予受理的当事人以程序保障,民事诉讼法赋予被不予受理的当事人以上诉权。这些均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正当当事人置于起诉要件而存在的相应的制度设计。如果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相比较,那么可以做出如下图示: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德国和日本在案件进入诉讼系属前,裁判长仅仅审查诉状是否记载了应记载之事项,并不对相关事项是否存在进行实质审查。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存在“不予受理——上诉”的制度设计,我国学者所谓的“起诉要件高阶化”,在制度设计上也不能谓不合理。不过,存在问题的是“要防止不予受理制度的滥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2条来看,(3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2条:“对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一律接收诉状,出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前,不接收诉状可能是“起诉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不接收诉状,即可不用审查,进而也就无需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那么当事人的上诉权无异于被剥夺。因此,即便存在“不予受理——上诉”的制度设计,也很难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起诉难”的“症结”并不在于“起诉要件高阶化”,而是在于“诉状收——理程序”的不规范。(34)杨会新:《从诉之效力位阶看民事案件受理制度》,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但是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后,在规范了“诉状收——理程序”的基础上,应当防止《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成为“立案难”的新的阻碍点。按照现行法,防止“立案难”回潮的重要救济手段便是对“不予受理”的上诉机制。
但问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对民事案件的不予受理裁定并没有单独的案号,导致实务操作中出现了如下几种做法:一种是立案,进而生成立案号,以该立案号作为“不予受理裁定”的案号。另外一种做法便是立案后,由业务庭来裁定驳回起诉。再一种做法就是由立案庭向当事人释明。如果释明不成功或者是当事人“坚持立案”的,则按照第一种方式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第二种做法实际上较为繁琐,因为如果要业务庭来裁定驳回起诉,则需要在收取诉讼费用后,再退还诉讼费。第一种做法则存在着“以立案的方式作不予立案裁定”的矛盾。而实践中存在的普遍做法则是第三种即释明。(35)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3款:“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由于第三种情形中不一定会作出不予受理裁定,进而对于释明的相关情况无法通过上诉程序予以救济,也就导致了“不予受理——上诉”机制“疲软”。从这个角度而言,将正当当事人置于起诉条件中,则有可能导致“立案难”的“回潮”。
从这个角度来讲,仍然将“正当当事人”作为起诉要件置于起诉阶段会有损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因此,将正当当事人置于“审理阶段”,进而以“当事人”的概念承担起诉阶段的主体资格审查功能,既符合现行法的体系化解释,又有利于降低起诉阶段的审查标准,实现诉权保障功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投诉”由于是类似于“即时抗告”的制度设计,进而也就实现了“低标准+简易救济手段”的程序构造。为了平衡“诉权保障”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之间的矛盾,可以在正当当事人置于审理阶段的基础上,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人解绑,而将低于实体权利义务人的标准置于“正当当事人”的概念之中,进而实现“防止无益诉讼”等程序功能。这样的改革路径会形成如下制度架构,即“当事人+起诉阶段”“正当当事人+审理阶段”“实体权利义务人+审理阶段”的三层结构,进而实现诉权保障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之间的平衡。
五、结语
对正当当事人以“实体/程序”对立的范畴予以性质界定,并不能有效解决“诉权保障”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制度改革路径,是因为未充分理清实体概念与程序概念之间的关系。在理清程序与实体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将程序概念与界定程序概念的标准“解绑”,将程序概念与程序功能“勾连”,方是制度改革的理论前提。在完成上述理论前提后,如何在“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之中“装入”相应的界定标准,进而实现“诉权保障”“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等程序目的,则是今后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而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则在于在“当事人”的概念中装入相应的界定标准,实现诉权保障与防止无益诉讼等程序功能。如此方是缓解目前“案多人少”局面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