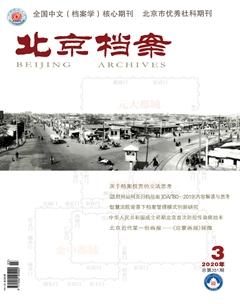对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理论思考
王巧玲 周玲凤 梁传靖 史唯君
摘要:文章在综述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地区丝绸老专家口述档案采集实践,从概念、价值、规范等理论源头对口述档案采集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更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口述档案定义,分析了口述档案及采集工作的特殊价值,以及规范性操作在实践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最后,文章指出,当现有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应该反思理论,给予“新生事物”相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口述档案口述档案概念口述档案价值口述档案采集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le? vant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 oral archives collection practice of silk experts in Beijing area, this paper makes in- depth thinking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oral archives collection practice from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concept, values and norms, and puts forward a more practical and instructive definition of oral archives. It analyzes the special value of oral ar? chives and collection work,and the two meanings of normative operation in practice as well. Finally, this pa? per points out 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theory and give"new things" some developing space, when the exist? ing theory is not enough to help guide practice.
Keywords:Oral archives; Concept of oral ar? chives; Values of oral archives; Oral archives collection
“口述档案”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进入档案学界视野,到现在已有30多年。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显示,国内以“口述档案”为主题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86年,2006年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首次突破个位数,达到20余篇,并自此呈现较为稳步的增长趋势,2012年至今,年均发文量则达到了40篇左右。虽然研究成果涉及概念界定、价值探讨和实操规范等诸多方面,但相关讨论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对其概念、价值和实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更缺乏系统分析。
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中国丝绸档案馆的筹建单位——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苏州工商档案中心)特委托北京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档案系成立项目组,对北京地区的丝绸老专家开展了口述档案采集工作。本文试图结合该实践项目,从概念和价值等理论源头来思考口述档案采集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以期为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指导。
一、口述档案的概念界定是采集工作的基本前提
开展口述档案采集工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概念的界定问题。只有概念被界定清楚,理解和沟通才有可能真正地发生,相关的实践工作才可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究竟什么是口述档案?”也是北京地区丝绸老专家口述档案采集项目组成立时,接受项目培训的档案学专业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目前在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中,有关“口述档案”概念界定的具体文字表述虽各有不同,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三大类。
第一类,是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所编撰的《档案术语词典》中的界定:口述档案,是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
第二类,是2001年刘耿生在《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的定义:口述档案,是指出现文字之前,人们把言传耳闻留下的传说、故事、逸闻等,后人的追记,以及当事者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从以大脑为载体形成的记忆转录为文字材料的一种档案。[1]
第三类,是2015年吕豪杰、王英玮在《口述档案收集抢救规范化流程研究》一文中的表述:口述档案,是指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口述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像形式的,具有佐证历史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的口述史料集合体。[2]
三者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口述档案概念在档案学界出现的源头”,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目的、主体和形成过程,即口述档案的采集目的是为满足研究利用的需要;口述主体是个人;形成过程是有计划的采访。该定义中有关形成过程要素的规定,将个人自己写的回忆录和自传等材料排除在了口述档案之外。
刘耿生的概念界定方式,显然是以档案记忆观为理论基础的。从该定义可以提炼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主体即个人,二是形成过程即记忆的迁移,三是内容即口头传说与个人经历。这一定义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了档案的记忆属性,并通过将人脑视为一种记忆的载体而使口述与档案关联起来,口述档案的实质是存在于人脑载体的原生记忆迁移到其他载体的结果。另外,该定义还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口述内容:口头传说与个人经历——而这通常是后来者提出所谓广义的口述档案概念与狭义的口述档案概念的依据之一,即把两者内容都包括的称为广义的概念,把仅包括后者的称为狭义的概念。
吕豪杰、王英玮的口述档案定义,主要包括四个要素:對象、形成过程、价值和状态,其中的价值要素,其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中的目的要素相似。由此可见,与第一类概念相比,第三类概念的特点在于:(1)价值(目的)方面的表述更为详细具体;(2)围绕事件来界定主体范围,即事件的当事者或亲闻者;(3)形成过程由“有计划的采访”变成了“以标准方法采集”;(4)增加了有关状态的表述,即“口述史料集合体”。从档案学的角度来说,“集合体”是该定义中最体现档案学专业贡献的内容。[3]
第三类概念界定借用“口述史料”来指代采集结果,这与档案概念从诞生开始就与口述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比如,《档案术语词典》中“口述档案”的法文和西班牙文词条虽与中文词意直接对应,但其英文词条却是Oral History,后来很多人据此认为,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原本就指同一事物,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称谓。不过,笔者认为,口述史料不宜用在口述档案的概念界定中,因为口述史料本身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专业术语;且与口述史料密切相关的口述历史,其外延亦存在不确定性,比如学者们对口述历史是否包括口述传统(即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民俗等)就存在争议。另外,该定义将形成过程表述为“以标准方法采集”,从逻辑上推断,应该也与其默认“口述史料”的采集已存在公认的“标准方法”有关。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三类定义都提到了口述档案的表现形式,由于表现形式与媒介技术手段有关,而媒介技术手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笔者没有将表现形式的区别纳入讨论的重点。事实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声像形式目前已成为主流形式。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口述档案”概念呢?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项目组成员的深入讨论,笔者提出的定义为:口述档案,指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依据相关规范与标准,通过有计划的访谈事件亲历者,将其保留在大脑中的个人记忆转换为文字或声像形式的、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记录材料的集合体。
这一定义除综合三类典型定义的优点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修订和调整:
(1)将口述档案记录的内容界定为“事件亲历者的个人记忆”;
(2)增加了对口述档案工作主体的规定即有公信力的機构;
(3)将“以标准方法”修改为“依据相关规范与标准”;(4)将“口述史料”修改为“记录资料”;
(5)将价值要素的表述由“具有佐证历史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改为“具有长久保存价值”。
该概念界定明确了口头传说排除在口述档案记录的内容之外(口头传说反映的是集体记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对于口述档案与非遗档案的关系,笔者将另撰文讨论),避免了定义过宽给沟通理解带来困扰,摆脱了其他学科术语的依赖,更具有独立性,同时也体现了档案留存社会记忆的专业特色;提出了专业机构介入的明确要求,提高了口述档案的产生门槛,确保了口述档案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使其更加符合档案学学科发展和实践工作指导的需要。
对采集工作实践而言,该概念界定的现实意义突出体现在使项目组成员在理解的基础上明确了本次访谈对象的身份特征与访谈的主要内容,即丝绸行业发展的亲历者与他们相关的个人记忆。
二、口述档案及采集工作的特殊价值是采集工作的主要动力
尽管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概念是否成立一直存在争议,对应该如何界定“口述档案”亦未形成一致看法,且口述档案采集是一项十分耗时、耗力、耗经费的实践工作,但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档案部门以各种方式加入到相关实践中来。[4]在国家层面,2010年,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达成合作意向,在云南试点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5]与此同时,省市县高校及部队各个层面都有档案馆陆续开始开展口述档案采集工作。这些采集项目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称“口述档案”,有的称“口述历史”,亦有的称“口述历史档案”,其中还是以“口述档案”者居多。[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呢(鉴于前面有关口述档案概念界定比较混乱的原因,不排除有些项目采集的其实是口头传说)?包括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在内的实践部门,为什么愿意在相关理论认知尚未明晰且投入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就先“做起来”呢?
“丰富馆藏资源”通常是实践部门介绍口述档案采集目的时最常用的一句话,本项目亦是如此。但对于刚才提出的问题而言,以之为答案显然是不充分的。笔者认为,驱动实践部门投入采集工作的最主要动力源自工作结果(即口述档案)与工作自身(即口述档案采集工作)两个方面。
(一)口述档案的特殊价值
口述档案的特殊价值包括记录内容的稀缺性和记录视角的独特性。
1.口述档案记录内容的稀缺性。口述档案记录内容的稀缺性,在相关事件在发生时因各种原因,未以其他方式被记录下来或相关记录很少的情况下体现得最为明显。比方说,因战乱原因没有记录的条件,或是因为相关群体没有记录的意识,或是缺乏记录的工具,如文字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亲历者的个人记忆转换成由相对固化载体承载的记录资料,显然具有填补社会记忆空白的伟大意义。
2.口述档案记录视角的独特性。一般类型的档案,通常是正式组织运作过程的产物,记录的是正式组织视角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口述档案的主体是个人,记录的是个人视角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在档案部门已建立的常规档案资源建设工作机制中,个人叙事视角基本是被排除在记录对象之外。
个人视角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有正式组织视角所没有的温度。人是兼具理性与感性的动物,个人视角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带有人的情感。而组织虽是由人组成的,但它是人理性设计的产物,因此,正式组织视角下记录的社会实践活动注定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
其次,个人视角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有组织视角所缺乏的细节。相对于组织视角的记录而言,个人视角下的记录是叙事性的,有着更加丰富的细节。两者相比,前者胜在连续性,而后者的“故事性”则更加突出。
最后,个人视角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所包含的思想性。口述档案除了可以记录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做以外,还可以记录其所思、所想,即有关个人对事件的感想、评价、期待和建议等集中反映人类情感和思想的活动。比如,在本次口述档案采集项目中,项目组在访谈提纲中就设计了请丝绸老专家谈谈个人对筹建中国丝绸档案馆的看法和建议等相关内容。而这类记忆在档案馆现有资源体系中亦是较为罕见的。
正是个人视角的独特性,再加上口述档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其比一般类型的档案更加鲜活、生动,亦更能贴近普通民众。[7]
(二)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特殊价值
相对一般类型档案的资源建设工作,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创新理念的集中体现,且具有突出的外显性特征。
1.创新理念的集中体现。在最初的档案资源建设工作中,进馆的档案资源都是“接收”来的。“档案征集”的开展率先打破了原来被动的工作模式,而口述档案采集则将档案馆在相关工作上的主动创新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档案馆不仅要突破传统禁锢,参与档案的形成过程,还要积极探索如何在此过程中实现与相关主体的有效合作模式。比如,本项目就是苏州工商档案中心与外地高校首次合作开展口述档案工作的尝试。
可以说,口述档案采集工作集中体现了国际著名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倡导的后保管时代下档案工作者角色转型理念。该理念认为档案工作者应从詹金逊式的被动保管者与中立守护者角色中解脱出来,积极参与社会建构与文化塑造,在强调档案系统和档案标准客观性的同时,不要逃避其主观性倾向。[8]
2.具有突出的外显性特征。由于口述档案采集工作需要更多地与外部相关主体的合作,因此,与一般类型档案的资源建设工作相比,口述档案采集工作更容易为上级部门和外界所感知。与此同时,口述档案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采集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多种创新要素,以及因个体生命有限性而赋予口述档案采集项目的“抢救性”意义等,则为档案实践部门的对外宣传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新闻点”,從而使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外显性特征得以进一步强化。
三、采集工作的规范性是口述档案价值的重要保障
30余年来,口述档案的概念界定之所以未能在学界达成一致意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口述”与传统的档案定义存在一些“不相容之处”,“口述档案”作为“档案”合法身份仍受到颇多质疑,梁淑情在《口述档案概念的合理性辨析》一文中对正方双方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问题的焦点在于:口述档案是否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及口述档案的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9]
口述档案形成过程的特殊性,是其身份地位受到质疑,甚至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它不是组织日常运转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经有计划的采集形成的,因此,为保证口述档案的可信度、相关度与独特性,采集工作的规范性非常重要。
2017年8月2日,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DA/T 59—2017)作为档案行业推荐标准,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使用的术语虽是“口述史料”,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它的确为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规范性提供了系统、权威的参考指南。本次北京地区丝绸老专家口述档案采集项目的设计实施就主要是以其为参考指南的。
另一方面,项目实践经验亦显示:确保采集工作的规范性,参考标准很重要,参照标准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亦同样重要。从理想状态来说,口述档案应是最优秀的采访者与最合适的口述者,在最佳状态下密切合作的结果。[10]但这样完全的理想条件,现实中往往不存在。因此,只有心怀人文关怀,对口述档案采集工作充满热情和勇气之人,才能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使其在现实的局限中向最理想的结果无限贴近。
四、结语
如前所述,“口述档案”概念的出现虽已有三十年历史,但同美国、新加坡等国相比,口述档案采集工作在我国还属“新生事物”,有关其身份之合法性的争议仍未停止。但笔者认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当现有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应该反思理论,给予“新生事物”相应的发展空间。
*本文系“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2018)”支持的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8.
[2]吕豪杰,王英玮.口述档案收集抢救规范化流程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5(4):49-53.
[3]王荣声,王玉声.档案是一个集合体概念[J].档案学研究,1995(2):8-14.
[4]首小琴.我国档案馆口述档案资源采集模式及其比较[J].北京档案,2018(6):29-31.
[5]李文栋.国家档案局加强口述档案培训[N].中国档案报.2015-11-30(1).
[6]吕豪杰,王英玮.口述档案收集抢救规范化流程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5(4):49-53.
[7]张威.浅谈档案馆口述档案的价值及征集途径[J].北京档案,2013(5):19-21.
[8]闫静,徐拥军.后现代档案思想对我国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基于特里·库克档案思想的剖析[J].档案学研究,2017(5):4-10.
[9]梁淑情.口述档案概念的合理性辨析[J].档案, 2018(6):13-16.
[10]汪长明.记忆不可靠性视域下口述档案的身份重构[J].档案与建设,2016(10):12-16.
作者单位:1.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4.苏州市工商档案中心(中国丝绸档案馆)3.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