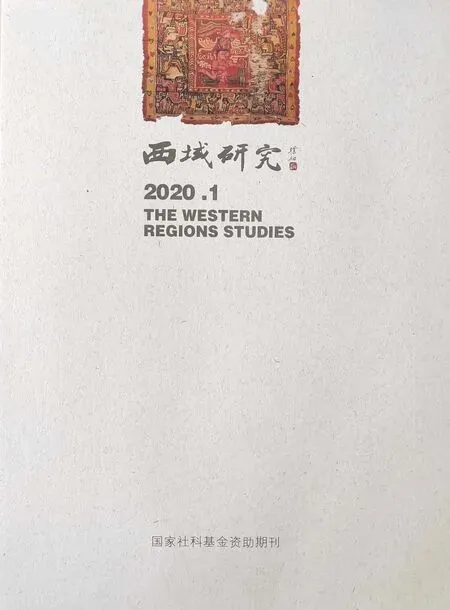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身世考①
杨栋娟
内容提要: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加紧了对和卓子嗣的搜寻与清查,以期消除隐患,在此过程中遗漏了大和卓一子,名萨木萨克。清代汉文史料有关此人的记载较为混乱,似乎有多个同名之萨木萨克。满文档案有关萨木萨克的记载中,有两同名萨木萨克且皆为大和卓之子,一为其妾所生,后被送往京师安置;一为大和卓之妻所生,被人携带逃至中亚各地,成为漏网之鱼,此人在乾隆中后期逐渐活跃起来。本文厘清了史料中两萨木萨克的关系,进而探讨乾嘉两朝对萨木萨克的态度转变过程,以加深对清王朝治理回疆特点的理解。
萨木萨克乃大和卓布拉呢敦(1)不同文献中关于布拉呢敦的写法不一,《清实录》写成布拉呢敦、《平定准噶尔方略》中写成波罗泥都,本文统一采用《清实录》写法。之子,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为防止和卓后裔扰乱,大规模访查和卓子嗣并安置京师,这一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清查过程中,遗漏了大和卓一子萨木萨克,使得和卓家族得以延续。到嘉庆末年,萨木萨克子张格尔、玉素普等人开始不断侵扰南疆,成为后来的张格尔之乱、玉素普之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等一系列和卓后裔动乱的祸根。但是,清代汉文史料中对于这样一个关键人物记载却比较混乱,先后出现过几个不同的萨木萨克。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界,佐口透、潘志平、潘向明、王希隆、王力等前辈学者都先后探讨过,但结果也莫衷一是。(2)佐口透认为送到北京的萨木萨克并非布拉呢敦之子,爱什阿哈察也并非布拉呢敦之妾,而逃亡中亚一带的萨木萨克才是布拉呢敦之子,但并未提供材料佐证其观点(〔日〕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7~109页)。潘志平也指出“清史料中关于萨木萨克的信息相当混乱,似乎有三个萨木萨克和卓:椿园、海明、舒赫德都报导过,海明报导说已查出并解送北京,但后来在中亚继续有萨木萨克的活动。”(《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9页)。潘向明与佐口透先生持相同观点,认为被送到京城安置的萨木萨克为假冒之人(《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王希隆认为史料中出现的两同名萨木萨克均为大和卓之子,只是由不同妻妾所生,但是缺乏具体史料佐证,对笔者的行文有较大启发(《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9页)。王力对两萨木萨克的关系提出了假设,认为“(一)两人确是同名之人,而且都是波罗泥都之子,只是由不同妻妾所生、具有不同影响而已;(二)海明查出的萨木萨克确实是假的,他只不过作为一个‘替代品’,来掩盖真萨木萨克的潜逃行为,从而混淆视听。”(《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98、99页)随着大量满文档案的整理出版,为萨木萨克身世研究提供了全面翔实的档案材料,基于此,本文即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汉文及满文文献,对清代文献中出现的两萨木萨克及相关问题略陈己见。
一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及探访和卓子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已归附清朝的大小和卓在南疆起兵叛清,此时清廷正用兵准部,无暇顾及天山南路。随着天山北路局势逐步稳定,清廷开始全力讨伐大小和卓。和卓兄弟见大势已去,遂分别从喀什噶尔、叶尔羌败走巴达克山,大和卓妻所生之子萨木萨克一同出逃,而其离异之妾所生之萨木萨克等则留在喀什噶尔。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将小和卓霍集占首级交与清朝,清朝在伊西洱库尔淖尔立碑纪功。至此,清朝完成统一新疆大业。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为彻底消除隐患,立即展开对和卓子嗣的清查。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清朝俘获大和卓之妻爱兰,得知布拉呢敦“尚有出妻托和齐、鄂和拉在喀什噶尔等处……又据提督董孟查报,托和齐系英噶萨尔旧阿奇木尼雅斯之妻,为布拉呢敦所夺,后复离异”(3)《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八,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辛酉。。潘志平通过研究发现,“小和卓霍集占无子,而大和卓确有子多人,流亡在巴达克山等地。”(4)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可见布拉呢敦妻妾子女较多,且偶有离异现象,清廷也加紧了对大和卓子嗣的搜寻工作。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获知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藏身于博罗特索丕家中的消息,在给乾隆帝的满文奏折中,详细说明了这一萨木萨克的身份:
大和卓木刚到哈什哈尔时,杀了伊克玛耶尔阿訇,娶其女爱什阿哈察,爱什阿哈察怀孕后,又将其赏给玉素布,后生一子,名为萨木萨克。后来爱什阿哈察杀了玉素布,大和卓木很生气,把爱什阿哈察吊死。大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时,这孩子被达什哈让带到伯什克勒木抚养,迈喇木叛乱中达什哈让死了,伯什克勒木的人们都逃散了,如今这孩子在阿尔瓦特村的博罗特索丕家中抚养,阿尔瓦特村的人们告诉我确实听说了此事。(5)《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奏闻查获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4页。伯什克勒木,位于新疆疏附县东北,见钟兴麒编:《西域地名考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清廷立即命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等搜寻博罗特索丕的下落,清廷抓获博罗特索丕后,据其供称:
我是看守大和卓木家祖坟的索丕,萨木萨克系爱什阿哈察所生,他的母亲因杀了玉素布,也被大和卓木吊死,后来这孩子被交给伯什克勒木的摩罗瓦斯抚养……我向爱苏尔什询问叶德格尔bibii和萨木萨克的情况,她告诉我叶德格尔bibii把萨木萨克撇在色达村后逃跑了,我想这是大和卓木所收的女人生的孩子,就去了色达村,确实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抚养。(8)《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奏闻查获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0册,第311页。
清廷立即派人前往博罗特索丕家中寻找萨木萨克,并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将“布拉呢敦离异之妾爱什阿哈察所生子萨木萨克,将伊乳母及收养回子博罗特索丕解京。”(9)《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清廷认为,“萨木萨克尚属童稚,不应缘坐,送来京师,惟加恩养育可耳。即博罗特索丕留养旧主之子,情亦可矝,俱著照例安插。”(10)《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并传谕永贵将萨木萨克已安置至京一事晓示南疆回众。(11)《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此后,清代汉文史料中便再无关于这一萨木萨克的记载。
笔者认为,此处海明所提到的解送至京之萨木萨克应该是大和卓与离异之妾爱什阿哈察所生之子。正如王希隆先生所指:“此萨木萨克及其母亲、乳母、收养之人皆有查明上报之实名,而且已奉乾隆帝谕令送往京师‘加恩养育’,如果确实是冒称作假之人,当有严加处理之相关记载。”(12)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9页。后来并未发生追究之事,足以说明此萨木萨克为大和卓之子无疑。时值平定两和卓叛乱不久,清廷正不遗余力追查大小和卓家眷,此时当无人胆敢冒充布拉呢敦之子萨木萨克,因而假冒的可能性不大。
此后不久,清廷又得到“闻布拉呢敦尚有二子,或藏匿回地,亦未可定”(13)《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的消息。便派人继续访查大和卓子嗣的下落。到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舒赫德奏报:“臣等风闻波罗尼都(布拉呢敦)逃入巴达克山时,曾将幼子三人携往。今据素勒坦和卓赎回之叶尔羌回人台里卜和卓,密告臣额敏和卓云,波罗尼都(布拉呢敦)三子,一名和卓阿什木,一名阿卜都哈里克,一名和卓巴哈敦,现在巴达克山居住,所有照管养育之人,俱甚穷苦,且虑伤害。”(1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一,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丙寅。这一重要的线索使清廷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乾隆帝随即谕旨素勒坦沙:“今闻布拉呢敦三子俱在汝处,其三子将来稍长,安保不别生事端。”(15)《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三,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己未。几度要求交还和卓之子,均未能如愿。后叶尔羌都统派人秘密潜往巴达克山侦探消息,得知“布拉呢敦尸骸潜瘗于牌租阿巴特”(16)《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零,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在清廷的强烈要求下,乾隆二十八年(1763),素勒坦沙“于二十三日遣密尔咱阿达里卜等同到埋瘗布拉呢敦尸骸处所,眼同掘出。并将伊妻一名珠赉哈,系回人,生子和卓阿斯玛;一名巴特玛,系厄鲁特人,生子阿布都哈里克;一名额尔克扬,系布鲁特人,生子和卓巴哈敦;俱全行查交。”(17)《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零,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布拉呢敦之尸骸及查获的家眷被一并带回且遣送至京城,随后清廷把这些外逃人员给与各功臣之家为奴。
在各方面的协作下,乾隆访查和卓子嗣初期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布拉呢敦还有一子萨木萨克,被伊里雅斯夫妇偷偷携带逃往中亚各地,其母便是厄鲁特人爱什阿哈察。也正因此,白山派和卓家族得以延续,成为后来和卓后裔多次动乱的渊薮。
二 潜逃中亚各地之萨木萨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潘志平先生就注意到清史料中记载着两个同名的萨木萨克:一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就已经被安置至京城的萨木萨克,而另一个萨木萨克早年逃往中亚各地,并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始不断骚扰清西部边境。潘先生梳理清代文献后指出:“大和卓布拉尼敦(即布拉呢敦)之子可能有同名之人,亦或有真有假:一是海明访求到的准备送至京师的萨木萨克;一是舒赫德、椿园、永贵、旌额理等人报导的流窜在中亚的萨木萨克。”(18)潘志平:《清—浩关系中的萨木萨克问题》,《中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31页。在潘先生看来,如若确实不存在另一萨木萨克,和卓信徒们可能也会造出一个假的萨木萨克来。但是囿于材料,先生未能提供材料佐证这一观点。《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的整理及出版,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材料。
先前大和卓四子均在巴达克山,其中一子名为萨木萨克,伊里雅斯夫妇盗走布拉呢敦尸骸之际,带萨木萨克逃往衮图斯、塔拉干、伊玛木拉等地……彼时萨木萨克方才两岁,如今已经四岁。萨木萨克系厄鲁特人爱什阿哈察所生,此母子均与伊里雅斯夫妇同在一处。哈什哈尔亦有一回子名为爱什阿哈察,先为摩罗米奇特阿訇之妻,大和卓杀了摩罗米奇特阿訇,并纳爱什阿哈察为妾,继而又将这个女人给了玉素布,后来听说回子爱什阿哈察杀了她的丈夫玉素布,大和卓很生气,把她带到街上绞死,爱什阿哈察怒骂道:“如今我已怀孕,且这孩子是你大和卓之子。”(19)《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查实萨木萨克是否是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1册,第196~197页。
王希隆先生认为两萨木萨克为不同妻妾所生,遗憾的是当时未发现文献档案作为支撑和订证。(20)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9页。上面这份满文奏折为两萨木萨克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可知曾有两同名之爱什阿哈察:一为厄鲁特人爱什阿哈察,为布拉呢敦之妻,另一回子爱什阿哈察,被布拉呢敦纳为妾,二人所生之子均名为萨木萨克。由于和卓家族在起名时受宗教文化影响,导致重名现象极为普遍。(21)如玛哈木图·阿杂木的第三代世系中有一名为阿布都拉,但是第五代世系中又出现名为阿布都拉的人;第三代人中出现墨敏、木萨,而到第五代、第四代世系中分别出现一名为墨敏、木萨的人;第四代中出现名叫霍集占的人,而第五代中也有一名为霍集占的。参见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前文已经提及,大和卓占有爱什阿哈察两三个月后即与大和卓离异,并被大和卓赏给玉素布,此时后来被送至京城的萨木萨克尚未出生,因而其名并非大和卓所取,因此同名之萨木萨克的出现似乎也能解释。
另外,前文已提及,先前舒赫德听闻布拉呢敦有三子在巴达克山,而此处又提到大和卓携带四子出逃,因而可能除了前文所述乾隆二十八年(1763)被解送至京城安置的三子阿斯玛、阿布都哈里克及巴哈敦外,还有这个萨木萨克。该萨木萨克可能在两和卓出逃巴达克山之际就已经被伊里雅斯夫妇偷偷携带出逃,加上此前已有一同名之人被解送至京,因而时人鲜有注意到外逃的萨木萨克。
此外,从其他文献中,也依稀可见出逃萨木萨克的蛛丝马迹。《西域闻见录》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布拉呢敦之子萨木萨克逃至其地,其汗留之。”(22)椿园七十一著:《西域闻见录》卷三《外藩列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布拉呢敦子萨木萨克与其党羽千人突围走退木尔沙(23)佐口透推测可能是阿富汗杜兰尼朝的阿哈默特沙的儿子退木尔沙和他的领土。,退木尔沙汗留之。”(24)椿园七十一著:《西域闻见录》卷三《外藩列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可见,除了解送至京之萨木萨克,还有另一萨木萨克逃往中亚一带确有其事。
至此,海明和舒赫德分别查出两个同名的萨木萨克,清廷方才意识到尚有一外逃的萨木萨克,于是寄信舒赫德“现经查出之萨木萨克护送到京,妥善安置抚养之处降旨宣谕回众。而随伊里雅斯出逃之萨木萨克尚在巴达克山以外,若专为此事派人寻找,回子等转至疑惧……惟此期间,不时派人巡查其茔地,或暗访下等回子,也许可得实信。”(25)《寄谕参赞大臣舒赫德著留心查访大和卓木之子萨木萨克》,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16~617页。令舒赫德等人继续访查外逃之萨木萨克的藏身地,以期早日将其招降。但正如潘向明所指出,“另一名为萨木萨克者,却始终未能查到,以至于张冠李戴,贻误时机,为后来留下一严重祸根。”(26)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成为日后清廷经营西北过程中长期无法摆脱的祸患。(27)此是另一议题,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
三 余论
综上,清王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天山南北最终纳入清王朝统治版图。为维护新疆的统一局面,清廷加紧步伐严密清查和卓子嗣,并采取积极措施将其安置至京师。富有戏剧性的是,大和卓布拉呢敦有两同名之子萨木萨克:一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海明奏报送至京师之萨木萨克,其母为回子爱什阿哈察,被大和卓纳为妾;一为舒赫德查访得知流亡中亚之萨木萨克,其母为布鲁特人爱什阿哈察,为大和卓之妻。
当清廷得知两个萨木萨克的关系后,便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乾隆三十三年(1768),乌什参赞大臣永贵派人前往帕米尔以西一带探查萨木萨克的下落。当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建议“用计剿除”萨木萨克时,乾隆帝驳斥道:“将萨木萨克诱来尚属可行,至用计剿除,则非天朝体统,亦非边疆大臣办事之道。”(28)《清高宗实录》卷一二零二,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丙辰。认为若真查到其人,也只需送到京师,从宽安置即可,并宣示清廷的招抚政策,称如若萨木萨克能主动归降,即“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2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零六,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但是,该萨木萨克出逃时方才三四岁,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均处于沉寂状态,因而这一时期的清代史书中不见这一萨木萨克的相关记载。
乾隆四十九年(1784),外逃的萨木萨克派遣托克托索丕等二人潜入喀什噶尔给默罗色帕尔等五人送信敛财,被地方官员发现,其通信对象还包括一些有权势的伯克官员们,信中言辞悖逆,清廷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令“务须不动声色,酌派干人,将萨木萨克所使二回人严查拿获,并将默罗色帕尔等五人明白审讯。”(30)《清高宗实录》卷一二零零,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丁酉。以“寄信敛钱案”为界,清朝一面严厉打击萨木萨克与境内和卓信徒的联络,一面谕旨浩罕等外藩首领协助擒拿萨木萨克,乾隆帝表示“如能擒获,朕当加恩”(31)《清高宗实录》卷一三零七,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卯。。清廷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萨木萨克的活动,此时萨木萨克并无归顺之意,因而终乾隆一朝,清廷未能如愿招降外逃之萨木萨克。
嘉庆帝即位之初,在外流窜多年的萨木萨克一度请求前来归降,就在萨木萨克呈表文欲投降之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采取了不当举措,错失了招降萨木萨克的最后时机。此后,清朝再未能与其有正面接触。而伊犁将军松筠为迎合嘉庆帝的心理,制造了荒谬的“玉努斯”冤案否认萨木萨克的存在。尔后,清统治者彻底放弃对和卓后裔的防范态度,和卓后裔得以凭借和卓家族在南疆的影响力与境内的和卓信徒联络并积蓄反叛力量。
逃亡境外的萨木萨克病故后,留下了三个儿子:长子玉素普、次子张格尔和三子巴布顶。嘉庆以后,清朝国势日益衰弱,加上内地起义不断,无法顾及每况愈下的南疆局势,导致从嘉庆末年起,萨木萨克后裔便屡次扰乱回疆地区,成为清中后期西北边陲长期不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