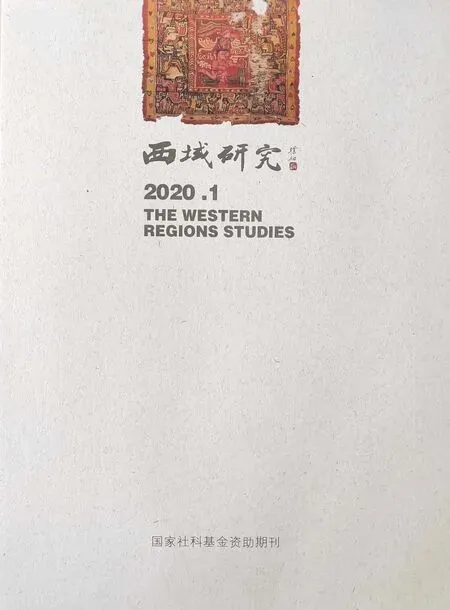于阗国名对音补论①
向筱路
内容提要:关于于阗国名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段晴先生撰写了《于阗王国之名新考》,提出了新的见解。本文着重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段文中的相关看法做进一步的论证和补充。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斫句迦国》载:“从此而东,踰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玄奘自注:“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玄奘对于阗国名的这段记载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段晴先生利用新近刊布的犍陀罗语、于阗语、梵语等多种语言书写的文书,撰写了《于阗王国之名新考》一文(下文简称《新考》,见本期),在前修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段先生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论证和补充。不当之处,敬乞方家教正。
1
汉文史籍中很早就有了对于阗国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汉书·西域传》:“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颜师古注:“阗字与寘同,音徒贤反,又音徒见反。”“窴、阗、寘”是异体字关系,可见,至晚在汉代,于阗国就称作“于阗”。
伯希和(Paul Pelliot)曾探讨过汉文史籍中“于阗”的词源,他发现“于”几乎不出现在佛经对音中,反而经常用来对译匈奴语词汇,因此他认为玄奘记录的“于阗”对译的是匈奴语*’Odan,并且这个对音发生在汉代;后来由于受到阿尔泰语言元音和谐律的影响,*’Odan音变为*’Odon,于是玄奘在7世纪时改用“于遁”来对。(1)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aris:A.Maisonneuve,1959,p.412.

“于”字《广韵》注音羽俱切,《集韵》还收有邕俱切的读音,释义为“大也,《礼》‘况于其身’”,这两个反切的声母有别。原本《玉篇》残卷给“于”字注音禹俱反,宋本《玉篇》同,可见“于”字在中古的惯常读音是于母。清末民初的音韵学家曾运乾在1927年发表《喻母古读考》,认为“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4)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年第2期,第58页。,即所谓的“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这两个说法影响很大。如果从青年语法学派的历史语言学观点来看,“喻四归定”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样会造成澄母和以母(喻四)在中古无条件分化的后果,所以后来学者大多认为以母和定母在上古只是音值相近。至于“喻三归匣”,则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承认,例如王力就说,“于母(喻三)在上古应属匣母,直到唐初也还属匣母”(5)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2014年,第23页。,隋—中唐音系中匣母和于母仍然是一类。以上是就音类分合来说的。
从音值的角度来看,于母和匣母在上古如何构拟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邵荣芬对学界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同时综合考察谐声字、现代汉语方言、梵汉对音、通假字、异文和《说文》读若等材料,认为匣母在上古应该分为两类,“匣1跟群母相同,都是浊擦音g,匣2跟云母相同,都是浊擦音”(6)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0页。。在邵先生利用的这些材料中,只有梵汉对音可以直接反映音值,这对于古音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因此我们这里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于”在上古归鱼部,这是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达成的基本共识。(9)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从对音材料来看,上古鱼部的主元音应该是a,支娄迦谶就用“于”对过ha。(10)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第300~302、319页。郭锡良把“于”的上古音拟作*ǐwɑ。(1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8页。
根据恩默瑞克的研究,于阗语中h的音值是喉擦音[h],这主要是基于和亲属语言的比较,于阗语的h是从古伊朗语的h发展来的,例如于阗语hunä-和阿维斯塔语vohunī-“血”对应,于阗语hauda和阿维斯塔语hapta“七”对应。(12)Ronald E.Emmerick,“The Consonant Phonemes of Khotanese”.In Monumentum Georg Morgenstierne I,Leiden:E.J.Brill.1981:205.Ronald E.Emmerick,“Khotanese and Tumshuqese”.In Rüdiger Schmidt (ed.),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Wiesbaden:Dr.Ludwig Reichert Verlag.1989:213.而hv也直接是h加上半元音v,(13)Sten Konow,Saka Studies,1932,p.37.可以用国际音标表示为[hw]。同样是参考恩默瑞克的研究,早期于阗语中的a和是长短音的对立,a的音值是[ɑ]。(14)Ronald E.Emmerick,“The Vowel Phonemes of Khotanese”.In Bela Brogyanyi (eds.),Studies in Diachronic,Synchronic,and Typological Linguistic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B.V.1979:248.
这样看来,用“于”字来对于阗语的hva-是合适的,那么我们再来看“阗”字的情况。
“阗”《广韵》注音徒年切,上引《汉书》颜师古注音徒贤反或徒见反,声母是定母。段晴《新考》在恩默瑞克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进一步论证于阗语中-t-的音值是[d],因此汉语用浊声母的“阗”对tan在声母上是非常合适的。由此也可以证明,于阗语中元音间的t浊化为[d]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发生。从押韵和谐声来看,“阗”字上古无疑应该归真部。俞敏根据译经对音材料将后汉三国的真部构拟成in、en,这是因为很多真部字的主元音都对过i和e。(15)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第295页。不过从文后所附的对音字谱来看,也有中古先韵系字主元音对a的例子,如“先”对chan、sa,“填”对dyan,“怜”对ran等。柯蔚南早年根据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的两汉韵部系统,把这些字归入真部;后来认为用汉代用韵作为后汉三国对音的参照并不合适,进而采用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的处理意见,将这些字归入元部。从拟音上来看,柯蔚南前后的处理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主元音分别是和(16)South Coblin,“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p.151.South Coblin,“BTD Revisited -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al Dialect”,第924页。
不过正如俞敏所指出的那样,后汉三国中的译名词只有数百个,再加之梵语的元音数量本来比较贫乏,因此用它们来归纳韵部比较困难。(17)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第287页。因此我们这里不在采用哪一时期的韵部系统以及如何拟测韵部音值等问题上纠缠,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具体字的对音上。为了进一步扩大材料范围,我们可以参考西晋时期的译经资料。根据刘广和的研究,西晋译经对音中,中古的仙先韵字对过an、a、n、ayan、yn、ran、al、il,尽管对音形式多样,但主元音不出a、i两类,并且对a是主流。刘先生进一步认为,“仙韵禅、先韵田都对dhyn,跟田同音的填对dayan(=dyan)、先韵连对lyn,让咱们非得把仙先合成一部不可,仙韵旃字对can又对cin提示主元音不是十足的a,可以拟成ɛ。”(18)刘广和:《西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音韵比较研究》,第199~200页。可以看出,将这一时期的仙、先韵的主元音拟成ɛ,一方面是为了解释它们主元音还对过i的客观现象,但同时也是考虑到和《切韵》音系的衔接。在《广韵》中,“阗”和“田、填”等字同音,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在后汉三国时期也可以对an。还需要说明的是,“阗”等字在中古是四等字,从对音来看,“纯四等字对音东汉就有i介音,两晋增强,唐宋大备。”(19)刘广和:《介音问题的梵汉对音研究》,《音韵比较研究》,第219页。不过i介音的有无对于整个音节读音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用四等字“阗”对tan还是可以做到语音近似。
可见,至晚在后汉三国时期用“于阗”对于阗语的hvatana在音韵上是完全可能的。
2
开头我们引用的《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说“俗语谓之汉那国”,这里有一处异文。《大唐西域记校注》:“《古本》、《建本》汉作唤;《宋本》、《资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径山本》及《慈恩传》、《翻译集》引并作涣。《赵城本》及《华严钞》引作汉,同此本。”(20)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1页。“汉”《广韵》注音呼旰切,晓母翰韵。“涣”《广韵》收二音,泰韵呼会切:“涣,水名,在谯。又音唤。”换韵火贯切:“涣,水散。又音翙。”宋本《玉篇·水部》:“涣,呼换切,水盛皃。”可见“涣”在中古的惯常读音是晓母换韵,它和“汉”只有开合的区别,读音很近。郭锡良给“汉”、“涣”的中古音分别拟作xɑn、xuɑn。(2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296、346页。
伯希和所据《大唐西域记》本写作“涣那”,继而认为它对应的是晚期于阗语形式hvana,早期于阗语hvatana-中位于元音间的-t-在7世纪上半叶同化为了n,变成*hvanna之类的形式。(22)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411.
段晴在《新考》中引用了她曾经刊布过的一件于阗语案牍,前后20年间“于阗”分别被写作hvatana和hvanä,(23)段晴:《于阗语大案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3~375页。段先生进一步结合恩默瑞克的研究讨论于阗语中元音间的-t-音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研究于阗语的前辈学者都曾做过说明,例如柯诺夫(Sten Konow)很早就指出,元音间的t会浊化为d,但是在文字上仍然写作t,这个d音很早就失落了,只是在文字书写中仍保留下来。他举出的例子有*vta>bta“风”,*pith>päte、pye“父亲”,byehäte、byeye“他得到”(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词根byeh-),等等。(24)Sten Konow,Saka Studies,p.26.总之,不管是从文献材料还是从于阗语的语音演变规律来看,早期的hvatana音变为hvana等形式应该毫无问题。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汉”、“涣”读音很近,相较而言,“涣”对hva要更准确一些,用它的合口成分去模拟于阗语的v[w]。用“汉”来对音也可以得到解释,按照生成音系学理论对语音特征的分析,[x]和[w]的发音位置都是舌体(dorsal),部位靠后,在这种情况下,[x]和[xw]在听感上的区别将会减弱。“那”在中古是泥母歌韵系字,玄奘用它对过na、n、a、、nya、ns等形式。因此用“涣那”“汉那”对晚期于阗语的hvana等形式也是合适的。同时也从汉语的角度证明,于阗语中元音间的t音失落至晚在玄奘时代就已经发生。
3
玄奘说“旧曰于阗,讹也”,类似的表述在《大唐西域记》中很常见。玄奘给很多梵语或其他语言的词做了音译,并时常引用前代音译形式以资参照,有时甚至直接说旧译“讹也”“略也”。关于玄奘这样做的用意,刘广和曾对《大唐西域记》中注明“讹也”的条目进行过初步分析,将其细分为八种情况,其中有两种是“旧译跟唐译分别对了不同的梵音”和“旧译对了唐以前的汉语古音,新旧译的不同正反映了汉语的音变”(25)刘广和:《玄奘译音夹注“旧曰……,讹也”考》,“第十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北京)会议论文。。这些意见为我们分析玄奘此处的记载提供了启发。
先看第一种可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正文中记载的于阗国叫作“瞿萨旦那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gostana的音译。如果以此为标准形式的话,那么在唐代“于阗”的读音与之相去甚远,因而被玄奘认为是“讹也”。第二种可能较为复杂。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于阗”对的是于阗语的hvatana,这个对音至晚发生在后汉三国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于母合口字和匣母合口字的对音表现相同,“于”字在当时可能读作ǐwɑ。假使玄奘知道“于阗”所对的原词是hvatana,那么在唐代“于阗”或许已经不能准确地读出它的语音了。
于母字几乎不出现在唐代对音当中,这在玄奘、义净、不空的译经中都是如此,而匣母字已经基本与晓母字混同,都可以对梵语的h。玄奘改用晓母字“涣、汉”对于阗语的hva,这就暗示出当时于母字不适合用来对hv。从韵母来看,“于”字在《切韵》音系中属虞韵,郭锡良把它的中古音拟作ǐu。(26)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178页。玄奘对音中,模、虞韵字对梵语的u和o,施向东把虞韵系音值拟作[ju]。(27)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这与hva的主元音a读音差距较大,不能准确对音。当然,这两种可能的解释都还只是推测,目前还难以确证。
4
根据玄奘的记载,于阗国“印度谓之屈丹”。关于这个说法,学者们也曾有过讨论。
斯坦因提到,在尼雅出土的公元3世纪的佉卢文书中,有kustana、kustanaka等形式,当然更为常见的是khotana,在脚注中斯坦因说kustanaka的形式是由拉普逊(E.J.Rapson)告知的。(28)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154.伯希和也认为玄奘所说的“屈丹”并不是某个梵语词的对音,而是当时在西北印度使用的一种口语形式。而由于中期印度语中没有音,只能用读音最近似的kh来替代,并由此推测出“屈丹”对应的词形是*Khutan或*Khǒtan。(29)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411.这实际上仍然是将它们的源头追溯到hvatana上去。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暂且比较谨慎地认为,“屈丹”有可能是对梵语、犍陀罗语的khotana等形式。
5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汉文史籍中的“于阗”是早期于阗语hvatana的对音,这个对音至晚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第二,玄奘记载的“涣那”“汉那”是晚期于阗语hvana的对音,之所以玄奘将旧译“于阗”判定为“讹也”,可能是由于于阗国名本身有不同的源语言形式,也可能是由于汉语自身的语音变化。第三,“屈丹”有可能是梵语、犍陀罗语khotana等形式的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