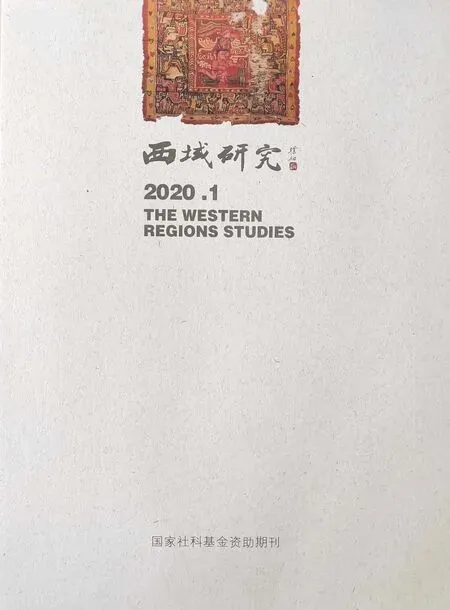唐西州契约的基础研究①
裴成国
内容提要:唐西州契约是吐鲁番文书中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料,本文研究了前人关注较少的契约的书写、形制、画指、随葬等问题。唐西州契约的形制与高昌国时期一脉相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书写、形制上的变化和画指的流行既是契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结果,也汲取了官私文书形制上的合理因素。唐西州契约的保管期限因类型不同而有差别,契约废弃之后被收集积攒用于墓葬明器的制作,专门随葬的契约很少,左憧憙墓葬随葬契约并非为供冥界继续追讨之用。西州契约具有典型性,因而是我们研究唐前期基层社会的宝贵资料。
契约是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因其数量大、内容丰富、与基层百姓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百余年来备受学界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既有契约文书的整理释录,(1)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Contracts(B) plates,the Toyo Bunko,1986;Contracts(A) Introduction & Texts,the Toyo Bunko,1987.Supplement,Contracts(B) plates,the Toyo Bunko,2001;Contracts(A) Introduction & Texts,the Toyo Bunko,2001.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也有借助敦煌吐鲁番契约研究契约形制或梳理契约发展演变史,(2)池田温:《契》,池田温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收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第160~188页。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上编《契约史研究》前四章,中华书局,2008年。王旭:《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第四章《经济关系的券契及其发展》,中华书局,2017年。还有学者运用契约研究中古时期的社会生活。(3)童丕著;余欣,陈建伟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徐秀玲:《隋唐五代宋初雇佣契约研究——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包含丰富的法制史内容,因而从法制史角度入手也是一个重要视角,这方面也积累了大量成果。(4)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 土地法·取引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 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Valerie Hansen,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鲁西奇中译本:《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罗彤华:《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契约因为此前笔者已经作过研究,本文将主要探讨唐西州契约。
此前从文书学角度对吐鲁番契约作过整体考察的有陈国灿先生和吴震先生。陈国灿先生《由雏形走向定型化的契约——谈谈吐鲁番出土契券》一文揭示了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的契约内容和条款的演进和变化,分别从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土地租佃契约入手具体比较和梳理了契约条款逐渐成熟和定型的表现。(5)陈国灿:《由雏形走向定型化的契约——谈谈吐鲁番出土契券》,《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第24~30页。吴震先生在《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的表层考察》一文重点从形式和语词的发展与演变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他将吐鲁番出土契约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晋—十六国时期;第二期为高昌国时期;第三期为唐代,自贞观十四年(640)起。唐代又分为初唐(Ⅲⅰ,包括武周,止于睿宗朝)、盛唐(Ⅲⅱ,开元、天宝年间)和中唐(Ⅲⅲ,至德至大历年间)三个阶段。吴震先生归纳第三期较第二期的变化包括:1.立契年次下省去干支岁次;2.自贞观末年起,券文内券主双方姓名上冠以所属乡名(Ⅲⅱ期后或省);3.由于画指节习俗逐渐流行,券末之“各自署名为信”,改为“获(画)指为信(记)”;4.券主双方并列署名于券后;5.券后并列之关系人中“倩书”署名移后,永徽以后渐省,Ⅲⅲ期偶见,作“书契人”;第二期之“时见”作“知见”;增加“保人”联署,其位置在券主之后,“知见”人之前;6.券主与关系人署名并画指节且书其年岁,Ⅲⅰ期仅买卖契上一见,Ⅲⅱ期渐多,Ⅲⅲ期更为普遍;7.买卖、夏佃券契中,首列标的物于契文之前,自Ⅲⅱ期始;8.有些契纸背面可见契合文。(6)吴震:《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的表层考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收入作者:《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吴震先生归纳的以上变化大都正确,但也有个别地方需要修正;另外,限于文章的结构,契约形制的演变不是吴震先生论述的重点,因此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画指问题等。至于契约的用纸、书写、废弃等基本问题都未论及,因而仍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一 唐西州契约的典型性问题
在进入文书学的研究之前,笔者想先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即唐西州契约的典型性问题。像大多数敦煌吐鲁番文书一样,地域特色是绕不开的问题。也就是说唐西州的契约文书反映出的只是西州一地的情况,还是在全国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就内容而言,既然是边疆地区出土,一定会有一些地方特点的内容,比如雇人上烽契在唐西州契约中数量不少,但在全国其他地区不一定会有。那么笔者此文重点讨论的书写和形制问题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唐朝是律令制社会,契约文书作为一类法制文书,必定会有统一的规范。西州确实执行了唐律令规定的诸多基本制度,但既有的研究也表明,西州在执行唐朝制度之时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中宗朝之后西州均田制执行的是每丁十亩的标准;根据贞观户籍,西州丁男一人的租调是租六斗、緤布二丈,与唐赋役令规定的租二石、调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的规定不同。那么就契约的形制而言,西州契约与全国其他地区是否相同呢?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寻找唐西州之外地区留存的契约进行比较方可。P.4053《唐天宝十三载?(754?)道士杨神岳便粟契》、P.4053《唐天宝十三载(754)龙兴观道士杨某便麦契稿》(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6~77页。、S.5871《大历十七年(782)霍昕悦便粟契》、S.5870+S.5872《唐大历某年女妇许十四举钱契》、S.5867《建中三年(782)马令痣举钱契》(8)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38~140页。6件契约(契稿)时间都在敦煌陷蕃之前,契约或完或残,但可见部分都与同时期西州契约几无二致,如有的契约中出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并且当事人画指,名字之后记有其年岁等。与唐西州契约稍有不同的就是有部分敦煌契约末尾的用语“两共对面平章,画指为记”,西州契约中没有“对面”二字。可以说,沙州契约与同时期西州契约形制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否仅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沙、西二州呢?我们还需其他地域的契约来证明。
吐鲁番文书中非常难得地保存了一件洛州的契约,即阿斯塔那204号墓出土的《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以下简称《桓德琮典舍契》)。先迻录文书如下以便分析。


4 坊正、坊民令遣两人和同,别立私契。
5 其利钱,限至八月卅日付了。其赎宅价
6 钱,限至九月卅日还了。如其违限不还,任
7 元隆宅,与卖宅取钱还足,余乘(剩)任
9 负钱人 桓德琮 琮
10 男大义 义
11 同坊人 成敬嗣
12 嗣
13 坊正李 差 经
从内容来看,这件文书并非一件普通契约,而是契约订立之后债务人未及时偿还债务引起纠纷,债权人向河南县提起诉讼,经坊正李差经、坊民调解,限期还钱,两人合意二次订立的契约,吴震先生认为应题作《桓德琮负典宅赎价限期偿还契》,(9)吴震:《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的表层考察》,《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第429页。池田温先生题作《唐贞观廿二年八月十六日洛州河南县张元隆等索钱契》。(10)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16.就基本格式来说,这件契约与同时期的西州契约,如同年十月西州订立的《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索善奴佃田契》(1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7页。(以下简称《索善奴佃田契》)几乎完全一致,(12)可能由于《桓德琮典舍契》是产生纠纷之后二次订立的,所以格式与普通契约也还有不同,如末尾的“坊正”的出现。不管是程式化的语言,还是末尾的画指,甚至证人的人名之后画指的指节之间另书人名中的一字,也都一致。这件契约的债权人张元隆,应是贞观十四年高昌国灭之后被迁居中原的高昌人中的一员。贞观末年唐朝开放西州和中原移民之间的人员往来,已经去世的张元隆的骨灰被同族人带回西州下葬,同时随葬了这件很可能是张元隆生前遗命要求随葬的契约。(13)裴成国:《唐朝初年西州人与洛州亲属间的几通家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6~348页。这件洛州河南县订立的契约,是债务纠纷引起诉讼之后经调解重新订立的,当事人理应遵循通行规范,可以看作当时中原订立契约的一个标准样板。值得注意的是契约末尾证人的人名之后画指的指节之间另书人名中的一字,这种做法此后并未流行,很可能只是画指执行之初,百姓不清楚具体的操作办法而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的一种做法,但巧合的是同年订立的西州契约《索善奴佃田契》上也出现这种情况。总之,洛州《桓德琮典舍契》与西州契约在格式上的高度一致性,充分证明了西州契约的典型性。
如前文介绍吴震先生研究认为,吐鲁番出土唐代契约可分为三期,第二期(开元、天宝时期)的显著变化有:首列标的物于契文之前,契约末尾当事人人名后书其年岁,这种变化在西州之外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如出自于阗的《唐大历十六年(781)杰谢合川百姓勃门罗济卖野驼契》是一件汉文于阗文的双语契约,首行书“野驼壹头父拾岁”,末尾当事人人名后书其年岁,(14)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234页。与同期西州契约完全一致。前文所举敦煌陷蕃之前的六件契约因并非买卖、夏佃契约,所以首行未列标的物,但末尾当事人都书有年岁,也与西州契约相一致。由此,我们可知当时唐朝整个帝国版图之内,包括四镇地区契约书写格式都是统一的,变化也是同步的。唐西州契约的典型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 唐西州契约的概况
吐鲁番墓葬文书除一少部分专门随葬的以外,大多数被制成明器埋入墓葬。(15)除墓葬出土之外,还有少量出自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台藏塔等地面遗址。文书来源有官府、私人、寺院等不同途径,与墓主人有关或无关,入葬具有偶然性。制作明器的形式包括经裁剪制作成鞋、帽、腰带、纸衾、纸棺,以及不需大幅裁剪铺设在停尸席上。用于制成明器的官府文书应当得自官府废弃的文案,包括户籍手实、田亩簿、赋税征收簿、帐簿、行政文书、馆驿文书等,还有民间的寺院文书和百姓私人文书,包括寺院破历、名籍、百姓纳税证明、契约等。就数量而言,官府文书和民间文书约略相当。契约只是民间文书中的一种,留存也具有偶然性。
墓葬中纸质明器文书出土的数量多少并不均衡,这与不同阶层的葬具差别有关。社会上层采用棺木、死者穿戴都用丝绸等实物,使用纸质明器的机会很少,(16)目前吐鲁番发掘的等级最高的唐墓应该是阿斯塔那336号墓和哈拉和卓383号北庭副都护高耀墓,阿斯塔那336号墓葬具葬式不明,没有出文书,高耀墓有棺木,也未出文书(也有可能是墓室深,环境潮湿没能保存下来。)其次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等级也很高,虽然出了文书,但文书大多拆自舞俑身上,而非纸质明器。反而社会下层百姓会更多使用纸质明器,如迄今出土文书最多的阿斯塔那506号张无价墓,用文书制作了一具纸棺。就契约的使用而言,社会底层的百姓比社会上层的机会更多,因为社会底层的百姓才需要经常性从事借贷、租佃、雇佣等经济活动,所以使用纸质明器的平民墓葬出土契约的几率也较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与契约的密切关系。
吐鲁番出土的各类文书中,契约是数量很大的一类。吐鲁番出土契约已经公开发表的共有320件,(17)这里的统计只包括汉文文书。唐西州以前143件,唐西州契约177件。(18)遗书和市券的性质与普通契约差别较大,为研究方便,本文暂不讨论。唐西州时代的177件中,集中收录情况如下:《吐鲁番出土文书》收录141件;《大谷文书集成》收录13件;(19)《大谷文书集成》收录的许多文书之前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利用和发表过,为方便统计,此前单独发表的情况都不计,而以《大谷文书集成》的集中收录为准。特此说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收录1件;(20)《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按契约类型集中收录了大量唐西州契约,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大谷文书集成》大多重复。为方便统计,凡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大谷文书集成》者,《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统计均不计入。需要说明的是,集中收录契约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第三册出版要比《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早;《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增补卷出版也比《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早。《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收录6件;陈国灿先生《鄯善新发现的一批唐代文书》一文收录13件;(21)陈国灿:《鄯善新发现的一批唐代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第123~141页;后经修订收入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3件。吐鲁番文书中真正随葬的完整文书主要包括随葬衣物疏、功德疏、买地券、告身等,大多与百姓的丧葬观念有关,数量并不大。已经出土的契约虽然数量不小,但绝大多数都是经过裁剪制作成明器随葬的,所以完整的契约仅占很少部分。据笔者统计,177件唐西州时代契约中真正完整、没有裁剪痕迹的契约只有16件,(22)其中阿斯塔那35号所出的《唐咸亨四年(673)杜队正买驼契》边角部位稍有残缺,且纸面有印渍,应是陪葬墓中朽烂所致。不到十分之一,其中有10件都出自阿斯塔那4号墓。契约存纪年者最早为《贞观十四年(640)张某夏田契》,最晚的是《唐大历三年(768)僧法英佃马寺契》。
选取完整的契约文书测量,我们可知用纸的纸幅大小。笔者测量了9件契约,数据如下(23)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数据并非据文物实测,而是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图版测量所得。(左右×天地,单位:厘米):
1.《唐龙朔元年(661)龙惠奴举练契》:35×28
2.《唐麟德二年(665)张海欢、白怀洛贷银钱契》:39.58×29.17
3.《唐乾封元年(666)郑海石举银钱契》:40.83×28.96
4.《唐乾封三年(668)张善憙举钱契》:38.75×28.33
5.《唐总章三年(670)左憧憙夏菜园契》:41.09×28.91
6.《唐总章三年(670)张善憙举钱契》:40.43×30.21
7.《武周长安三年(703)曹保保举钱契》:42.05×29.78
8.《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35.42×28.75
9.《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39×28.75(24)《桓德琮佃舍契》右半部边角残缺较多,但不影响测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完整契约的纸张边缘也不整齐,不同位置尺寸相差2、3毫米是很常见的。观察以上数据,我们发现,9件契约的左右长度相差超过7厘米,相比较来说,天地的尺寸相差基本在2厘米以内,基本上都接近唐代一尺的标准。(25)关于唐尺,研究者大都认为一尺约合今30厘米左右。现今搜集到的唐尺已达30余支,大尺尺度也参差不齐,其伸缩范围在29~31.8厘米之间。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5~146页。第9件洛州河南县订立契约的尺幅数据也说明西州契约与中原的相当。值得一提的是,第5、6两件契约订立时间相差仅一月,纸张尺幅也有差别。在没有机械化作业的唐代,民间文书的尺幅精确可能也不是当时人追求的目标。
尺幅之外,书写的情况讨论文书正背面、合同契和书手三个问题。
唐西州官府文书正背两面书写是常见情况。如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文书中,《唐麟德二年(665)张玄逸辩辞为失盗事》和《唐憙安等匠人名籍(一)》等文书粘接之后背面书写了《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2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7~246页。《唐郭阿安等白丁名籍》背面书写了《唐田绪欢等课役名籍》;(27)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49、254页。阿斯塔那35号墓《武周证圣元年(695)前官阴名子牒为官萄内作夫役频追不到事》背面书写《武周阴仓子等城作名籍》;(2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519~520页。阿斯塔那230号墓《唐开元九年(721)里正记雷思彦租取康全致等田亩帐》背面书写《唐馆驿文书事目》,《武周沙州敦煌县田亩帐》背面书写《武周牒为镇果毅杨奴子等娶妻事》,(2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9、81、83页。例子很多,不备举。百姓的文书也常见正背面书写的情况,如阿斯塔那93号墓文书,《武周西州高昌县顺义乡人严法药辞为请追勘桑田事》背面书写《武周长安二年(702)西州高昌县顺义乡人苟仁辞》。(3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30~431页。作为法制文书,唐西州的契约会正背面书写吗?我们先关注一下此前的高昌国时代的情况。
高昌国时代契约正背两面书写以及两件契约书写在同一纸同一面的情况并不鲜见。2013年刊布的新疆博物馆新获高昌国时期15件契约,契约被剪裁做成纸鞋,都有残缺,有纪年的6件为和平(551~554)、建昌(555~560)年间书写。这些契约有4组11件为正背关系,其中有两件契约写在一纸上的情况3例,还有一件契约背面书写了《高昌立课诵经兄弟社社约》。15件契约中8件都明确是涉及同一人“郑凤安”,另外几件契约可能亦为此人所有,研究者推测这批文书应出自郑凤安的墓葬。(31)陈国灿:《对新出一批高昌券契的认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311页。其中正背书写的一组《高昌和平二年(552)四月王文孝从郑凤安边举麦券》和《高昌建昌四年(558)某人从郑凤安边夏田券》(32)《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第202、205页。时间相距仅六年,《高昌和平三年(553)郑凤安买田券》与背面书写的当为建昌四年(558)的《高昌□寅岁六月苏法□买马券》时间相距仅五年。目前墓葬所出建昌年间文书较少,但同出自阿斯塔那169号墓时间当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以前(33)该墓葬出土了《建昌四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墓葬文书下限由此可以确定。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的《高昌僧僧义等僧尼财物疏》和《高昌僧僧副等僧尼财物疏》,《高昌写本〈孝经〉残卷》和《高昌书仪》,都是正背两面书写。由此可见高昌建昌年间官私文书、百姓契约正背面书写应当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建昌以后,两件契约写在同一纸上的情况虽然继续存在,但明显减少,(34)阿斯塔那365号墓所出的《高昌延昌二十八年(588)王幼谦夏镇家麦田券》和《高昌延昌二十九年(589)董神忠夏田残券》连写在同一纸上,两件契约租种的都是镇家田;同墓所出的《高昌某人夏树(或葡萄园)残券》与《高昌某人从孟儁边夏□残券》也连写在同一纸上,“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推测第一件的出夏方可能也是主簿孟儁,出夏的标的物应当也归镇家所有;阿斯塔那34号墓的《高昌延和元年(602)隗某举麦残券》和《高昌延和元年(602)□□宗从左舍子边举大麦券》也接连书写在同一纸上,推测两件契约的债权人应当是同一人。而利用背面书写其他契约的情况似乎未见。到唐西州时代,尽管官府文书正背两面书写,二次利用的情况很常见,但契约则不然。
唐前期未见契约正背两面书写,或者两件契约写在同一面的情况;出现两件契约写在同一纸上的情况要晚至天宝年间。目前所见的两例都出自阿斯塔那506号墓,即《唐天宝十三载(754)杨堰租田契》和《唐天宝十三载张元举男方晖租田契》。细读两件契约,发现两件契约的标的物都是沙堰渠部田贰亩,且都是天宝十四载租种。第二件契约首句不写时间径直写“张元举男方晖于杨晏边领得沙堰渠部田贰亩”,说明张方晖实际是从杨晏处转租了这块土地。(35)《杨堰租田契》中租田人的名字写作“堰”(未及检阅原卷,文书图版模糊不清,录文写作“堰”),而第二件写作“晏”,可能因第一件契约田地位置中有“沙堰渠”,书契人因以致误,实际上是同一人。这两件契约写在同一纸上是因为没有第一件契约,第二件契约无以自明,所以必须如此。第二例是《唐至德二载(757)杨晏租田契》,在第1件契约之后接连书写了两行内容,“□交□小麦二斗于白如奕边租取□□渠□分部田一亩,其契准上。 田主 白如奕载卅”可知,后件契约的租田人也是杨晏。另外,用使用过的文书背面书写契约的,管见所及仅有一件,即阿斯塔那184号墓文书《唐家用帐》的背面书写了《唐道士梁玄忠便钱契》,文书整理组根据“玄忠”之名又见于同墓所出文书《开元十二年(724)残书牍》,推测本件亦当是开元年间契约。总体来看,唐西州契约一契一纸几成规律,绝少出现两契写在一纸上的情况,后期稍有例外。
入唐之后,之所以一契一纸成为定制,一方面因为契约涉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凭证,客观上需要妥善保管,另一方面也与契约制度有关,即契约背面需要书写用于验真的“合同”文。
唐代对民间契约采取“任以私契,官不为理”的态度,确立了政府不主动干预私契的放任原则,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涉及的契约政策又有差别。对于土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买卖,民间订立私契之后,必须经官府批准给以市券,方为合法,对没有及时订立市券的要处以刑法。对民间的租赁、借贷、雇佣、抵押、典当等经济活动的契约,官方不予干预,但法律承认并保护私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才由国家政府出面予以解决;对“契外掣夺、违法积利”等违犯公法规则的行为,则予以干预,用立法手段保护契约当事人的权力。(36)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基于官府的态度和法律环境,民间契约的订立尽管以诚信为基础,但也需要有避免纠纷的防范措施,如在契约背面书写用于检验真伪的“合同”,在契约末尾署名画指等。
关于合同契的问题,张传玺先生指出,隋唐以后,合同契主要使用于租赁、借贷、雇佣、抵押、典当等契约中,在买卖关系中使用的已很少,一般买卖关系多使用单契。(37)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50~51页。那么唐西州契约中合同契有多少呢?根据目前文书刊布著作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找到8例,(38)2001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文书《唐吕致德租葡萄园契》,契约中记“契有两本,各捉壹本”,但契约背涂墨,不清楚是否存“合同”文记,论理应当亦有。同墓所出《武周吕□□佃田契尾》残文也可见“契有两”原文应该也是“契有两本,各捉壹本”,文书残甚,背面情况不详。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70、372页。罗列如下。
1.大谷文书2828号《唐显庆四年(659)张君行租田契》,背面款缝写有“合同”二字的合体字,存右半字。契约中没有提到“契有两本,各捉壹本”。
2.阿斯塔那337号墓《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张海隆夏田契》,纸背可见折缝处所写的“合同”文记,本件存所书左侧。契约中有“契有两本,各捉一本”。

4.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张小承与某人互佃田地契》,背面下部中间有“合同”二字左半。契约中有“契有两本,各执一本”。
5.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孙玄参租菜园契》,背面中间有“和同”二字之左半。契约中记“契□□本,各执一本”。

7.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武周天授元年(690)西州高昌县武城乡张文信租田契》背面有合同类文记左半,契约中记“契两本,各执一本”。(40)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9~240页。

因为绝大多数唐西州契约都是经过裁剪、残缺不全的,所以原本应当有更多的契约订立时就是同时书写两份,折叠之后对接并在折缝处书写“合同”二字。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书写两份的也并非都背书“合同”二字。情况到底怎样呢?
以上8件中,除第3件是博换契约之外,其余7件都是租佃契约,租佃契约是使用合同契最多的一类。8件当中,比较特殊的是第8件,从残存的“各执壹本”可以确定契约写有两份,但“合同文”写在正面却是罕见的情况。另外7件都背书“合同(和同)”,并且第2到第7件的契约正文中也写有“契有两本,各捉(执)壹(一)本”。第1件契约从背书“合同”来看必定是同时写有两份,但从基本完整的契约内容中确实看不到“契有两本,各执一本”这类声明,这说明立契时同时书写了两份的也未必会在契约中声明“契有两本”,没有在契约中说明“契有两本,各执一本”的,也未必就不是书写了两本的。我们可以从阿斯塔那4号墓所出的左憧憙契约中作一考察。该墓所出15件契约中,有左憧憙的2件夏菜园契、1件夏葡萄园契、1件夏田契。在这四件租佃契约中,左憧憙都是租佃方,契约中约定租佃期限往往超过一年,租金也是分期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土地主人一定要持有契约,作为日后收取租金的凭据。尽管四位土地主人的那一份契约今天没有保存下来,尽管契约中无一例写明“契有两本,各执一本”,尽管完整的租佃契约背后也未见“合同”字样,我们确信这4件契约书写之时都是书写了两本的。这个墓葬中还出土了1件《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这是左憧憙为之前租佃的赵廻□的一所葡萄园而向县司上的辞,为了向县司说明葡萄园租佃的相关情况,我们确信左憧憙在给县司呈辞之时,必定要把这份租佃契约一起呈上,尽管墓中随葬的15件契约中没有这1件(保留下来的葡萄园租佃契约园主是王输觉,并非这一所),但我们确定左憧憙身前曾持有过这件契约。用这个例子,笔者想证明,合同契的数量必定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得多,大量没有保存下来的契约是真实存在过的。尽管今天留存的唐西州契约中找不到2件是同时订立的合同契,但当时一式两份的合同契必定不会少,尤其是在租佃契约中。
标准的合同契理应同时书写两份,在契约中专门注明“契有两本,各执壹本”,然后折叠拼合,在接缝处书写“合同”二字,以备日后验证。上文列举的第1例背书“合同”而契约中未记“契有两本”之语,第8例“合同文”写在正面,都是实际操作中贯彻不严的表现,但契约的效力并不会因此受损。
契约的书写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订立契约首先要备好纸。高昌国时期当地就有“纸师”,唐西州还有“纸坊”,(42)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385页。西州当地应当可以造纸,官府用纸质量上至少分两种。(43)大谷文书5839《开元十六年(728)请纸牒案》所记河西市马使请纸分案纸和次纸,《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第208页。从天宝二载交河郡市估案我们看到大量内地产品在西州市场行销,外地纸张也有条件进入西州。(44)此次研究过程中未得机会检阅文书原卷。从文书图版来看,洛州河南县订立的《桓德琮佃舍契》所用纸张为白色,与大多数西州契约用纸颜色迥异。订立契约除了买纸以外,请人书写应当也需要花钱。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的《唐家用帐》记载“五月五日,六十籴面,卅买酱,十八买酢”,也记载“伍拾文为缘勋官事文辞用”,在识字率低的时代,普通百姓订立契约、作家书或者向官府呈辞等都需要专门请人代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经常需要订立契约的情况下,请人代笔可能也是普通家庭的一笔常规性支出。契约的形式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书券”“倩书”的退出和“保人”的加入。唐西州时期的契约虽然极少见到末尾注明书契人的例子,但大多数百姓的契约继续需要请人代笔,则是一定的。高昌国时期的契约书手有两个特点。其一,道人(僧人)充当契约书手是高昌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僧人是当时的知识群体,大多能识会写;其二,个别俗人也充当了契约书手,但这些人在自己订立契约时却必须找人代笔,这主要是高昌国时期契约“署名为信”的规定使然。唐西州的契约末尾依次列名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保人、证人,一般不会写上书手名字。幸运的是,有几件契约的末尾保留了一些信息。阿斯塔那40号墓出土的《唐保人安不六多残契》的末尾注明“书人甯欢保”(4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301页。,《唐天宝五载(746)闰十月十五日某人从吕才艺租田契》末行书“倩书人浑仙”(46)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59.;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乾元二年(759)康奴子卖牛契》末尾最后一行注明“□契人高元定”(47)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549页。,大谷3107号《唐开元廿四年(736)二月张某从佐小礼租田契》末行书“倩书地主□□□”。四例中的最后一例引人注目,“倩书地主”的写法表明地主自己书写了该件契约。由此件契约不难想到唐西州的部分契约可能是由当事人自己书写的,唐西州契约在程序上的“画指为信”取代了之前高昌国的“署名为信”,为契约当事人自己书写契约扫除了技术上的障碍。
三 唐西州契约的画指及形制演变
唐西州的契约较之前高昌国时期契约在形式上的另一个变化是契约末尾的“画(获)指为信(记)”取代了之前的“署名为信”,也就是画指节代替了之前的署名。回顾十六国至唐代吐鲁番地域的契约形制发展史,作为民间文书的契约,其形制发展中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占据主导,官方的介入也提供了助力。十六国时期契约的书写材料始变为纸,书写格式和用语都不固定,但却孕育了后来形制规范的高昌国契约。《前凉升平十一年(367)王念卖驼券》(4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页。《前秦建元十三年(377)赵伯郎买婢券》(49)徐俊:《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年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211页。《高昌建平五年(441)张鄯善奴夏葡萄园券》(50)王素:《略谈香港新见吐鲁番契券的意义——〈高昌史稿·统治编〉续论之一》,《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5页;收入作者《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的末尾都注明了契约书手姓名,称之为“书券”,并且书手还担有证人之责,(51)契约中注明书券也“共知本约”。《高昌建平四年(440)道人佛敬夏田券》中明确写明“各自署名”。《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末尾写作“请宋忠书信”,契约中没有提到署名,但买卖双方和末尾的四位证人都署了名。麹氏高昌国初年的契约《高昌承平八年(509)九月廿二日翟绍远买婢券》末尾记“倩书道护”,文中写“各自署名为信”,且契约第1行买主翟绍远确实有署名,这件契约缺少末尾的证人,但主体内容已经是非常规范的高昌契约。和之前的张祖买奴券相比,“倩书”名称的出现以及此后一百多年固定为高昌契约对书手的称呼,令人想到这可能是麹氏高昌立国之后官府基于民间已有的做法,对契约的形制和用语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内地的契约《北魏正始四年(507)九月十六日北坊民张神洛买田券》砖券的末尾写“画指为信,书券人潘藐”(52)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2.,这件北魏契约提示我们高昌国契约6世纪之后开始与中原契约出现明显的形制差别,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又过了一百多年,当地契约中出现“画指”的做法,而当时还在麹氏高昌国时期,这一点也值得特别关注。
高昌国契约中写明“各自署名为信”,但因为大多数契约末尾的列位中并无契约的当事人双方,所以署名是在契约一开始首次提到两位当事人时。通检契约发现,双方同时署名的仅有数例,债权人或债务人仅有一方署名的有17例,契约残缺不清楚有无当事人署名的占到不少,当事人双方俱存但无署名的有15例。可见“各自署名为信”在大量契约中并未得到贯彻,原因之一应该是许多人并不能识文断字做到自己署名。
契约末尾画指节的做法在高昌国末期就已经出现,但数量不多。阿斯塔那117号墓所出的《高昌延寿九年(632)十一月廿二日曹质汉、海富合夏麦田券》(以下简称《曹质汉夏田券》)(5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89页。的末尾除海富之外的四位当事人都用“指节为明”的方式画了指。大谷文书《高昌延寿十五年(638)六月一日周隆海买田券》(54)《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册图版,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7.末尾周隆海的名字之后也有“指节为明”,但仅限周隆海一人。高昌国后期的画指文书不只以上两件,(55)还有大谷文书1494+3462+1500+1492+3470+3457《高昌延寿十五年(638)前后买田桃券关联断片》中明确记载“以兄欢伯妻手不解书,指节为名”、“以员海伯妻手不解书,指节为名”,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p.8-9.阿斯塔那117号墓也出土了另外一件,不过纪年残缺,需要考订。

高昌国后期画指契约的出现背景是当时唐朝和高昌国存在民间交流(商人可能助力颇多),具体原因则是契约形制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署名为信”的规定对大量百姓而言缺乏履行的基本条件,就像契约中陈述的“手不解书”;另一方面契约基本上还是民间文书,官府干预得少,所以形制的演变也一定程度上允许其自发性来主导。“画指”被接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较“署名”简便易行,因而可以说,画指取代署名成为表达个人信誉的方式。吴震先生概括唐西州契约“券主双方并列署名于券后”“券主与关系人署名并画指节”,洵非事实。那么唐西州契约中的画指情况执行得如何呢?
总体来说,与契约末尾无一例外地写明“画指为信”相比,画指真正在契约中执行的并不严格。理论上来说,唐西州契约的末尾列位中当事人双方、保人、知见人都需要画指,画指应以食指或中指三个指节位置划线示意,理论上每个人手指长短不一,指节长短也不一,指节线长短具有唯一性,因而画指就是个人信誉的承诺。但在契约中,当事人是否全都画指、在哪里画指、怎样画指在执行中都做不到严格统一。以下详细举证。首先讨论谁该画指的问题。上文提到的《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张海隆夏田契》是一份标准的合同契,契约末尾田主和佃田人都有画指,但总体来看,这种例子为少数,大多数契约债权人是不画指的(一些契约末尾债权人连名字都省略未写)。除当事人双方,保人和证人画指也是契约确保效力的客观要求,但实际上保人和知见人该画指而未画指的例子很多。在文书的哪个位置画指,不同契约也不尽一致。常见的画指位置是在人名之下,依次画三个指节印,但也有契约指节画在人名中间。从文书图版来看,指节画在人名中间基本上都是因为书写人名之后空间不够在余白处画指,这本身也说明画指的位置民间并无严格规定和清晰统一的认识。前文提及的洛州河南县的《桓德琮典舍契》和西州的《索善奴佃田契》既有画指,又署有人名的一个字,形式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当时不管洛州还是西州,尽管契约都需画指,但画指的具体做法可能都不统一。关于所画指节的精确程度,不同契约也差别较大。早期的画指契约如高昌国末期的《曹质汉夏田券》《唐显庆四年(659)张君行租田契》等所画的指节印都是平整的短横线;还有很多契约如《唐乾封三年(668)张善憙举钱契》所画的指节像是随意点画的接近圆形的顿点,仅具示意作用,谈不上精确。
以上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契约画指的具体状况,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状况下画指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呢?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当时画指这种做法实施的环境。画指的做法从高昌国末期传入吐鲁番地区之后,逐渐在唐西州流行开来,被普遍地运用到了官私文书中,用来表示当事人认可、承诺、保证、同意等含义。如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的《唐麟德二年(665)张玄逸辩辞为失盗事》首行书张玄逸姓名年龄,之后有画指,画指应是张玄逸确认证词真实无误。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商人康义罗施等人的姓名年龄之后也有画指,这是确认身份之意。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的《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末尾译语人何德力也有画指,应当是保证翻译和书写内容真实无误。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武周天授二年(691)老人王嘿子等牒为申报主簿高元祯职田事》末尾有两位老人的画指,牒文末尾称“如后不依今状,连署之人,请依法受罪”,所以老人的画指也是保证之意。此类例证多有,不赘举。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举文书中本身都没有提到“画指”;尽管画指的含义各处不尽相同,但也毋需特别说明。总之,唐西州在官文书中需要画指的场合非常多,百姓对于画指极为熟悉,广泛接受。从阿斯塔那91号墓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何射门陀案卷为来丰患病致死事》中“节义坊正麹伯恭”署名且画指的情况来看,画指在契约之外的场合被使用自唐西州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唐西州在契约和官私文书中都广泛使用画指的方式,其效力必定具有广泛的认可度。与以上官私文书不同的是,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专门用于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契约末尾列名的当事人双方、保人和证人都有明确的履行和维护契约条款的义务,因而尽管有些契约中画指执行并不严格,但并不影响契约效力。在契约末尾均详列保人的情况下,保人的存在也是确保契约执行的有力保障。
唐西州契约在开元年间开始出现的两个重要变化,契约末尾的当事人书其年岁和买卖、夏佃契约首列标的物于契文之前,可以肯定这是受当时其他官私文书做法的影响。重要的当事人书其年岁,这在西州官文书中颇为常见,如西州初年的文书《唐贞观十七年(643)何射门陀案卷为来丰患病致死事》《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勘问梁延台、雷陇贵婚娶纠纷案卷》中已然如此。至于最早书写年岁契约的出现时间,则尚需稍作考辨。
阿斯塔那117号墓出土的另一件有关吴海儿的契约是《某人用练买物契》(以下简称“《用练买物契》”)。此件契约末尾共有六个人名,其中“吴海儿”在第四列,应该也是“知见人”。契约末尾六个人名不仅画指,其中四个人还在人名之后书写了年岁,“吴海儿五十”。这件契约也残缺较多,断代殊为不易。文书整理组没有给出意见,《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第三册定名为《高昌或初唐年次未详某人用练买物券》(59)Tatsuro Yamamoto,On Ikeda co-edited,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Ⅲ,(A),p.9.也未作出判断。《买葡萄园券》和《用练买物契》同时裁剪制作成鞋子下葬,将两件契约中的“吴海儿”判定为同一人应当是稳妥的。根据墓葬解题,该墓所出文书有纪年者既有高昌国时期,也有唐西州时期,最晚为唐高宗某元年。吴震先生根据残存程式将此件契约定为第三期的初唐契约,并指出买卖契约画指并书其年岁,此期仅此一见。(60)吴震:《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的表层考察》,《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20、433页。笔者也同意吴震先生对契约的断代意见,并且愿略作补充。高昌国时期银钱的使用非常普遍,除小额交易的场合使用粮食作为货币(61)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货币研究》,《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62~67页。之外,罕见使用其他货币。唐西州前期因为军资练的流入,帛练成为一种重要货币,文书中也时时可见,如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唐龙朔元年(661)左憧憙买奴契》和《唐支用钱练帐》即是明证。《用练买物契》的例子说明尽管人名后书写年岁开元天宝时期渐多,中唐时期才普及,但其萌芽实际早在唐初就有了。从这种做法出现、增多、普及的历程来看,应当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非出于官方推动。
将标的物列在文书首行,在《唐永徽三年(652)士海辞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这类文书中也是习见做法。总之,开元年间契约的两种新变化反映了在汲取官私文书合理因素的背景下,契约形制和内容向着更严密、更明晰方向发展演变的能动性和自发性,是契约文书自我发展完善的表现。
四 契约的废弃与随葬
绝大多数唐西州契约都是经裁剪制作成明器随葬的,在制作明器之前,契约必定已经废弃。本节尝试对契约的废弃期限、文书转让和随葬作一探讨。
唐代的官府档案有定期废弃的规定,“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62)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中华书局,1983年,第351页。契约文书的保存时间应当是依类型不同而长短不一。相比较而言,雇佣契约如雇人上烽契等,一般涉及的就是上烽十五天,时间既短,雇佣价格也仅为银钱数文,因而只要受雇人按时上烽归来,雇主结清剩余部分雇价,(63)多数雇人上烽契都是即时交付雇佣价格,也有个别契约规定上烽归来再支付剩余部分雇价,如《唐张隆伯雇范住落上烽契》即是一例(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199页)。契约就算是履行完毕。上烽契当然还需要保留一段时间以备日后官府查核,但期年之后应当即可废弃。租佃契约保留的时间应当更长一些。一则租佃契约期限最短一年,时间长的比如一些葡萄园、菜园租佃契约则有四五年的,(64)如《武周吕懃子从和行本边佃葡萄园契》(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69页)期限为四年;《武周长安三年(703)严苟仁租蒲陶园契》(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32页)期限是五年。并且唐西州时期很多租佃契约是前一年就订立好的,这样一来,契约履行的时间就长,在此期间契约当然需要妥善保管。二则,目前出土文书所见契约订立之后履行过程中的纠纷由土地租佃契约引起者数量不少,为预防可能产生的纠纷,契约也需妥善保管。买卖契约因标的物不同,情况不同,契约保管时间长短亦应有差别。奴婢、大畜买卖契约因为有呈报官府另给市券的要求,短期即可获得官府的正式认定,所以私契不一定需要长期保管;奴婢因为要上户籍,而造籍之年以三年为期,所以最长三年即可将买来的奴婢登入户籍,因此私契的保管亦应不必太久。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契约废弃和制成明器埋入墓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间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差。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百姓,尤其社会中下层使用纸质明器陪葬相沿成俗。对于许多普通百姓而言,废弃的收据、契约也不会随便丢弃,为自己或家人终将来临的葬礼积攒收集用于制作明器的废弃文书,应当是大多数家庭的习惯做法,而契约是普通百姓最常使用的为数不多的私人文书,自然是积攒收集的重点。阿斯塔那10号墓是傅阿欢的墓葬,他由高昌国入唐西州,大概在唐高宗永徽之后去世。(65)墓葬出土仅刻“傅阿欢”三字的墓砖一方,因而可以确认墓主。男尸纸鞋所出纪年文书最晚者为永徽六年(65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01~211页。他的墓葬中留存高昌国义和四年(617)他自己的条记文书,还有他永徽四年(653)的夏田契约,显然是长期积攒的结果。废弃契约除了供自家之用,也常常会用在家族成员的墓葬中。如阿斯塔那337号、338号墓因为有墓志出土,得知是范阿伯、范乡愿的墓志,两个墓葬中出土了多件卫士范欢进的契约,有雇人上烽契、买马契、买奴契、赁车牛契,(6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21~246页。应当是范欢进在族人去世后拿出自己积攒的契约助葬的结果。类似的例子还有阿斯塔那40号、42号墓。(67)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110、145、295~300页。阿斯塔那40号墓无墓志,但出土了杜定欢的契约5件,很可能即为杜定欢墓葬,契约中有一件《杜定欢赁舍契》,舍主为证圣寺三纲僧练伯;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了永徽二年(651)《杜相墓志》一方,同墓也出土了一件《杜定欢赁舍契》,舍主为郭海柱。应当也是同族亲属助葬的原因,杜定欢的赁舍契约埋在了杜相的墓葬中。我们在傅阿欢和范阿伯、范乡愿的墓葬中还看到孙阿父师、赵明儿等显然非同族人的契约,应当是应墓葬明器制作之需,无偿或有偿获得的。
真正以没有废弃的契约随葬的较为罕见。左憧憙墓葬因为出土了十余件契约,且大多完好,被人认为是刻意随葬用于冥界讨债之用,此处作一澄清。
出土完整契约最多的阿斯塔那4号墓,因为有墓志出土,可以确认系左憧憙的墓葬。该墓葬总共出土契约15件,其中10件都是完整契约。契约中有6件左憧憙出借银钱,2件出借大练,(68)最近吕博也研究了相关契约,参见吕博:《唐西州前庭府卫士左憧憙的一生》,《唐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9~423页。可见左憧憙善于经营,经济实力雄厚。韩森注意到左憧憙先后在668年和670年向张善憙出借银钱,期间又曾在670年早些时候夏取张善憙的菜园,韩森认为左憧憙以租田的名义多次纠缠张善憙,张善憙欠左憧憙的债越来越多。由此韩森认为左憧憙刻意随葬契约还想去冥界找所有没有还债的人,把他们所欠的银钱和练索要回后,在冥界中使用。尽管该墓葬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但其中没有提及契约出土时的情况,韩森论文中提到主持墓葬发掘的吴震先生告诉她墓葬的情况,并说契约是完整地卷在一起。(69)韩森:《为什么将契约埋在坟墓里》,收入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0~546页。从契约的完整性来看,墓葬刻意随葬契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韩森对原因的解释令人疑惑,以下试作分析。
左憧憙两次向张善憙借钱的利息是每月百分之十,虽然很高,但却是当时西州民间借贷的一般利息率,是普遍接受的“乡法”,(70)参阅罗彤华著:《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之第五章《借贷之期限、数量与利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246页。又参见孟宪实:《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99~105页。如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同一时期的《唐麟德二年(665)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举钱契》,利息率也是月息百分之十。左憧憙六次借钱其中五次都是按照百分之十收息,仅有一次要求月息百分之十五,是向崇化乡的郑海石收取。从文书来看,左憧憙和张善憙之间没有存在不良债务的迹象,所谓张善憙欠债越来越多,以致左憧憙要带着契约去冥界讨要,并无根据。其次,如果15件契约都是要带到冥界去追索的凭据,数量如此之大,坏帐和纠纷如此之多,在当时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目前发掘的墓葬情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这只是特例,那么按照乡法借钱,又善于经营的左憧憙反而有大量欠债追讨不回,这也是情理不通的。如果再看契约的情况,15件契约中还有5件是残缺较多的,基本可以确定下葬的时候应该已经残缺,那么残缺的契约还能作为去冥界讨债的凭据吗?显然是有问题的。实际上,15件契约中,还有左憧憙的两件夏菜园契(1件完整、1件残缺)、买草契(完整)、夏葡萄园契(残缺)、夏田契(残缺)、买奴契(残缺)、1件残缺太甚难以确认性质的契约。至少性质明确的这6件,左憧憙都是买方和租赁方,根本不可能牵涉到对方欠钱的问题,带这6件契约到冥界,也无债可讨。契约订立之后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这并不鲜见,因为契约纠纷而给官府呈送的辞也发现了多件,如阿斯塔那19号墓所出《唐咸亨五年(674)王文欢诉酒泉城人张尾仁贷钱不还辞》。(7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69页。左憧憙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残缺的《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涉及的葡萄园主人是赵廻□,与张善憙无关。如果左憧憙和张善憙之间真的产生了债务纠纷,左憧憙应当会在生前就呈辞诉诸官府;(72)左憧憙在总章三年(670)的三月十三日和廿一日分别给张善憙和白怀洛出借银钱肆拾文和拾文,距左憧憙咸亨四年(673)五月廿二日去世还有三年多时间,不会存在来不及追讨的问题。左憧憙墓志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551~552页。官府解决不了,左憧憙不得不去冥界追讨的话,作为债务纠纷的见证和重要环节,左憧憙理应保留给官府的辞并完好地随葬。我们在墓葬中并没有发现涉及与张善憙债务纠纷的辞。
契约作为法律凭证,是债务纠纷牵涉诉讼时必须向官府出示的。如果按照韩森的理解,左憧憙要求把没有追回欠债的契约随葬,是要去冥界讨债,这也就意味着彻底放弃现世和未亡亲属的追讨权力。左憧憙真的有可能会这么想吗?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人的冥界财富观念。中古时期吐鲁番绿洲百姓虽然大多信仰佛教,但与冥界相比,他们更注重现世的利益。比如高昌国男子流行骑射之风,弓箭为家家必备,男子的随葬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比例也极高,但墓葬中未见真正随葬实用弓箭的情况;(73)裴成国:《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2页。又比如随葬衣物疏中大多会登载随葬丝绸万段、银钱万文,比如左憧憙墓的《生前功德及随身钱物疏》中就有这两项,但墓葬中顶多放置象征性的绢片;一般墓葬中随葬的陶器也都是专门烧制的比较粗糙的明器,而很少将实用器物随葬,对大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这样。墓葬同时牵涉生死两界,在生者看来,写在衣物疏里就算是给亡人陪葬了;而未亡人自己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借贷、买卖契约中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条款“若身东西不在,仰妻儿偿上”,即便债务人去世,也可以向其亲属追讨。左憧憙如果真的要求把尚有纠纷的契约随葬,也就意味着放弃现世的追讨权力,左憧憙的亲属应当不会答应,(74)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随葬的契约是重新抄写的复制品。而他们才是主导左憧憙葬礼的人。
左憧憙墓葬随葬的这些契约真的牵涉债务吗?当然不是。因为律令和乡法的保障,西州的借贷、买卖、租赁市场总体上应该是秩序井然的。左憧憙虽然偶尔放高利贷,但也在乡民容忍和接受的范围之内,否则他不可能经营致富。那么他为什么会遗命随葬15件契约呢?契约有完整的,也有残缺的;有他向人放贷取利的,也有他租种别人的菜园、葡萄园的,是他经营起家的真实写照。左憧憙作为普通百姓,却能积累大量财富,主要得益于他善于经营,当然也需要律令和法规保障的良好环境。在当地百姓都有积攒废弃文书以供将来制作明器之用的环境中,左憧憙生前的契约也大多保存完好。和普通百姓情况不同的是,左憧憙非常富有,随身衣物似乎无需使用纸质明器制作,(75)纸质明器在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墓葬当中使用较为普遍,这些明器绝大部分是实物的替代性用品,随葬应该与物资匮乏有关系。参见陆锡兴:《吐鲁番古墓纸明器研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50~55页。明器也不是所有墓葬都会使用,并且同一墓葬的个体也有差别,如2006年发掘的阿斯塔那604号墓葬两个个体,其中男性个体身体包裹白色绢单子,里面穿着麻布衣、裤,脚穿一双纸鞋;女性下身着夹裤,表面是丝罗,内层是红色绢,脚穿一双紫色翘头绢鞋,内有一双红色绢袜。从随身所穿衣物看墓主人显然生前较为富足,虽然是同一墓葬,男女两个体也有穿纸鞋和绢鞋的区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44~45页。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契约埋入墓葬,只能是出于他的遗命。左憧憙遗命将这些已经废弃的契约收集起来随葬,或许是想以此纪念自己勤劳致富的人生,他可能也希望在冥界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76)町田隆吉认为左憧憙墓葬随葬契约可能反映左憧憙希望来世也可以继续从事这些契约关系代表的经济活动,町田隆吉《「唐咸亨四年(670)左憧憙墓誌」めぐって——左憧憙研究覚書(2)》,《国際学研究》第4号,2013年,70頁。同墓出土的左憧憙墓志中称“财丰齐景,无以骄奢”(77)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51~552页。,说左憧憙堪比很会敛财的齐景公,但却不奢侈。(78)町田隆吉也注意到这两句话在一般的墓志当中未曾见过,表现了左憧憙这样的新兴庶民阶层的自负心理,并希望自负心理来世也能得到满足。町田隆吉《「唐咸亨四年(670)左憧憙墓誌」めぐって——左憧憙研究覚書(2)》,《国際学研究》第4号,69頁。在这方颇多溢美不实之辞的墓志中,这两句写左憧憙财力雄厚虽然夸张但也还是有根据的。“财丰齐景,无以骄奢”这两句颇为个性化的描述应该视为家人对左憧憙的描述和评价,或许也道出了左憧憙自己的心声,在家人心目中的左憧憙正是“勤劳致富”的代表,所以会遵照墓主人遗命随葬这些相关契约。
西州的市场也并非全无纠纷,左憧憙的墓葬中就出土了一件《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即是一例。墓葬中也确实有因为纠纷未能解决而将相关契约随葬的,就是前文引用的《桓德琮典舍契》,迁洛高昌人当时居洛州河南县的张元隆去世时纠纷尚未解决,而他也已经知道将有机会与亲族重返故土西州,现世的追讨已经不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未知的冥界了。(79)裴成国:《唐朝初年西州人与洛州亲属间的几通家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第346~348页。这种情况毕竟太特殊,此件契约毕竟是特例。大多数契约都是废弃后被剪裁,缺损严重,较为完整的也不一定就是刻意随葬的。如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开元廿一年石染典买马、驴契,一件完整、一件稍残,但实际都是拆自纸衾,并非专门随葬,只是因为裁剪较少,保存较好而已。
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商贸发达,经济繁荣。契约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平台和保障,契约自身也在频繁的经济活动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本文对唐西州契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书写、形制、画指、随葬等作了研究,填充了此前研究的一些薄弱之处。唐西州契约形制演变与之前高昌国时代一脉相承,又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新的发展。高昌国时代契约末尾的“署名为信”对许多不具读写能力的普通百姓而言没有可操作性,唐西州演变为“画指为信”更加简便易行;唐西州契约末尾列位中“保人”的加入为契约增加了一重保障;一纸一契和合同契更为普遍;开元年间之后当事人书其年岁,租佃、买卖契约首行标明标的物。以上变化都使得契约内容和形制更加合理、严密和明晰。高昌国末期画指契约的出现,初唐契约中偶见的当事人书年现象都说明契约自身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汲取官私文书的合理之处则是契约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尽管契约中的画指情况执行得并不严格,在画指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契约的效力并不因此受损。不同类型的契约保管期限差别也较大,当地百姓有收集积攒废弃文书制作明器的习惯,所以契约废弃和埋入墓葬的时间可能会相差很大。左憧憙墓葬的契约文书是他经营致富的写照,但随葬并非为了去冥界追讨欠债。
唐前期的契约文书保存最多、资料最丰富的就是西州。从形制来说,唐西州契约与中原、敦煌、安西四镇地区都具有一致性,典型性毋庸置疑,因而西州契约是研究唐代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宝贵资料。唐西州契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律令制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边界,看到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井然秩序,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