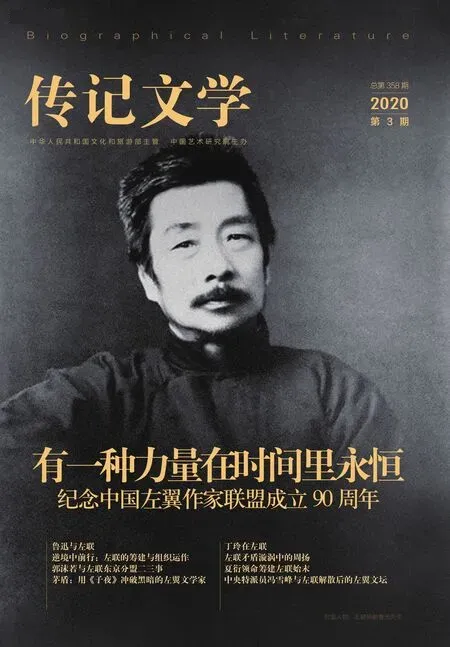为明国粹大道 不惜继晷焚膏
——我的戏曲研究之路
安 葵 口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李志远 整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安葵先生,本名王安奎,亦作王安魁,笔名安葵,1939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戏曲研究》主编、《中华戏曲》主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安葵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学术理念,时刻关注戏曲创作实践的发展,对作品、剧作家、创作现象的研究贯穿始终,同时致力于当代戏曲理论体系建设,并在戏曲美学领域进行了不懈的研究。2020年春节期间,80岁高龄的安葵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戏曲研究之路。
因热爱文学 与戏曲结缘
我出生在辽宁省盖州市(原来叫盖县)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一个老寿星山,老寿星山下就是头道沟村。祖父王文林中过秀才,但没有再“进步”,只在农村教书,并且家境越来越贫穷。我没有见过祖父,我出生时他早就去世了,但我看过他留下的一箱线装书。父亲王肇远弟兄四人,他行大,只念过几年私塾,很小就务农。山里没有多少耕地,父亲主要侍弄果树,房前屋后嫁接了多种水果树。我的家乡很美!一到春天,山坡上就红红火火开遍了映山红,一团团、一簇簇,远看像燃烧着的火焰。映山红谢了,便有杏花、桃花、梨花、苹果花等开放,这些花谢了,赤、橙、黄、绿各种颜色的果子挂满枝头,那是父亲劳动的结晶。我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他们都很聪明好学,但没有条件多读书,哥哥们很小就外出工作,三个姐姐都早早嫁人,四姐读了师范,加上勤奋自学,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教师。我读书时新中国已建立,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因此得以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父母在家里辛勤劳动,上中学后两位哥哥负责了我的生活费用,姐姐们对我也非常关心,因此我永远感恩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我的小学离家五六里路,天不亮就要去上学,母亲每天都站在院墙边看我走远,直到看不见为止。中学则是到四五十里以外的熊岳城盖县第二中学住校,高中是在熊岳高中。
我走上戏曲研究之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小没有看过戏曲演出,对戏曲也不了解。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各门功课是“全面发展”的,考初中时是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的,还成了三里五村的大新闻。但我更喜欢文学,小学时写作文,宋庆鸿老师曾写批语:“有造之才,勉之勉之。”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中学时期,夏鸿明、郭增益、宫凤阁等语文老师水平都很高,学校也都有很浓的文学气氛。初中时学校有一份《学习生活》油印小报。开始是苏芳桂做主编,发表了我不少小文。苏芳桂毕业后(他后来到了广东惠州,是优秀的小说家),我接任了主编。高中时,宫凤阁老师曾出作文题:写杜甫《兵车行》的评论,把古诗《十五从军征》改写成新诗的形式等,都激发了我评论和创作的热情。还曾听盖县的剧作家田心上(本名由志正,辽宁著名剧作家)在文化馆的讲座,因此便萌生了当作家的梦想。1960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艺术院校提前招生,一些喜欢文学的同学就相约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两院校联合招生)。说起来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东北地区是在沈阳集中考试的。复试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克莹老师问我:“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你读过莫里哀的剧本吗?”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她说:“入学后得多读一些书啊!”这似乎是一颗定心丸。不久,我就接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的中国戏曲学院是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组建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地址在东四八条52号。开始国务院任命张庚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后来撤销中国戏曲研究院,合并到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是梅兰芳,副院长是张庚、晏甬、罗合如。在“大跃进”之后,国家实行调整政策,许多高等院校被撤销。中国戏曲学院的牌子又被摘掉,恢复中国戏曲研究院建制。我们也提前于1963年毕业,叫作“实习在外”。我们是“文革”前唯一的一批正式的戏曲专业的大学生。
开学时,梅兰芳院长和张庚先生都对同学们讲过话,不久张庚先生下放到江苏沛县,教学工作主要由晏甬副院长负责。张庚、晏甬提出按延安鲁艺精神办学,进行学院式教学。戏曲文学系系主任是郭汉城先生,副主任是张为先生,先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有王彤、吴琼、简慧等老师。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大部分是本院的研究人员:吴琼、简慧、王芷章、刘念兹、林涵表、王淑兰、余从、黄菊盛、李振玉、邓兴器等,并请了外面许多专家来讲课。郭汉城先生给我们讲过一次话,内容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你们要“多读书,少生气”,当时很不理解,并且觉得挺奇怪,后来渐渐觉得这句话,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是很有深意的。老师们认真负责地进行教学。吴琼老师指导我们写剧本,刘念兹老师用“笺注”的方式讲《牡丹亭》,简慧老师细致地解析《雷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剧名著。记得学习期间曾到双桥农场参观,回来后同学们写诗,我写的一首“五律”的头两句是:“农村旧印象,今日一扫光”,王芷章老师给我改为“农场陈印象,今日扫来光”。使我开始意识到写诗需调整用字以符合平仄规律。读书期间正值国家开放传统剧目的演出,因此得以观摩了京剧和各地方戏的许多优秀传统剧目,使我的文学梦与戏曲艺术逐步结合了起来。我曾担任班干部、团支书,还担负着辅导3 个越南留学生学习的任务。同学相处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尽述了。毕业前,班里的调干同学王登山、张巧兰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晏甬副院长参加了我的入党讨论会,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同志们也都对我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3年毕业后,我留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秋天,我与谭志湘、苏明慈等青年同志(后来邓兴器也加入)被安排到山西“学毛著”先进典型地区绛县南柳村和昔阳大寨去“劳动锻炼,体验生活”。临行前晏甬副院长与我们谈话时说:“劳动锻炼很重要,也要强调体验生活。你们趁年轻时要好好体验生活,为今后的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在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很愉快。我从小就参加劳动,上中学后,假期也与乡亲一起干活。在家里干活时,父亲常说我笨,到农村却常常得到宽厚的乡亲们的称赞。老乡们不但有丰富的生产知识、自然知识,而且能讲出很多人生的哲理。这一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在绛县过的“革命化的春节”。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我到北京观摩会演,之后又返回南柳。当年冬天河北发洪水,水灾过后,文化部布置写抗洪剧本的任务。我随郭汉城先生等人到河北、天津等地采访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我先写剧本初稿。初稿写成后,又有新的任务来了。领导说,剧本放一放,先搞“四清”去。于是,我们先后到北京郊区楼梓庄、延庆和河北邢台等地搞“四清”。在南柳,我还担任了生产队的副指导员,“四清”时担任过副队长。在这些农村工作中,我与当地的农民结下很深的感情,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更多切身体会,也向他们学习到很多东西。接着就是1969年秋天开始,下放到“五七”干校七八年时间。干校后期,劳动之余,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前在读中学期间,我就读了《毛泽东选集》的一二三卷,毛泽东同志热情、雄辩的语言和强大的逻辑力量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干校后期“待分配”期间,我开始抓紧时间读书,向本所的姜永泰同志(他是郭汉城先生60年代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借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希腊悲剧、喜剧剧本来读,并读了鲁迅杂文的全部单行本。“文革”期间批判周扬、林默涵在《鲁迅全集》的注解中做了“歪曲”,所以那时出版的鲁迅著作的单行本都没有注解。我借来老的版本对照读,并把某些注解抄到单行本上。当时虽然没有失去信心(我曾写诗说:“自知不是经纶手,亦不甘为酒饭囊。”),但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当时读这些书都还不能有深刻理解,但对我的学术修养来说是重要积累。
弥补光阴逝 明晰研究路
“文革”后,文化部组建了“艺术研究机构”(后改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中国戏曲研究院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所。我是1976年春回到戏曲研究所工作的,从这时起才开始正式搞专业工作(此前只发表过粤剧《山乡风云》的评论等一两篇文章)。
这时张庚、郭汉城先生在全国招收研究生,我对张庚先生说,我想考您的研究生。张庚先生说:“你不要考了。我们招研究生主要是想从外边招一些人来,扩大戏曲研究的队伍。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你。”于是,我便没有报考。
根据戏曲研究工作的需要和各人的特长,戏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在不同的研究室组,开始我是在当代戏曲研究室,此后便重点研究当代戏曲、戏曲文学、戏曲创作,也做评论。
回顾我的学术道路,有一些与前辈相同的特点,即并不是单纯地搞研究,而是与戏曲创作的实践紧密结合,具体地说,是与教学、编辑、评论等工作相结合。20 世纪80年代,《剧本》月刊刊登一些剧作家、理论家的照片,并要各人写一句话。我写的一句话是:“从实践中探真知,经积累而求建树。”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和遵循的道路。
这一期间,我参加的重大集体项目是张庚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戏曲》,编写组主要由戏曲研究所一批青年同志组成,我担任编写组负责人。张庚先生对中国戏曲史论体系有完整的构想,《当代中国戏曲》是继《中国戏曲通史》之后,这一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后来我们又编写了《中国当代戏曲史》;《中国近代戏曲史》因故这时没有完成)。新时期以来,全国和各地的戏曲活动较多,相继成立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中国戏曲学会、中国近代戏曲文学研究会、中国昆曲研究会等组织。我积极参加这些学会的工作并撰写论文。我开始是受戏曲研究所指派担任与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的联络员,后来则担任了研究会的编辑委员、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先后担任秘书长和会长的何孝充同志为人很好,善于听取和吸收大家的意见,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从1980年研究会成立到现在,几乎每一届年会我都参加了。期间我为大家服务,也从各地从事戏曲创作演出和研究的同仁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具体感受到现代戏的发展进步。在中国戏曲学会,我继龚和德先生之后,担任了秘书长,再后担任了副会长。除日常工作外,还和湖南的同志一起,连续组织和举办了数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剧坛寥落正彷徨,弦歌扬,起潇湘,杜鹃如火,烂漫遍城乡。”(安葵《江城子》)民间戏剧确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1980年开始,我对陈仁鉴、翁偶虹、范钧宏、马少波、黄俊耀、杨兰春、王肯、胡小孩、顾锡东、徐进十位在当代戏曲史上影响较大的老一代戏曲作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总结他们从现实和历史中提炼素材创作剧本方面的经验和对戏曲传统挖掘整理方面的经验,撰写成《当代戏曲作家论》一书。我读他们的作品,观看演出,访问他们本人和相关的人,使我对戏曲创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打下了我研究戏曲创作论的基础。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与这些老剧作家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这十位剧作家中只有胡小孩健在了!那些已故去的老剧作家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我的眼前。

1997年在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题字留念
在研究戏曲作家的过程中,对戏曲创作的规律、特点逐步有所了解后,使我认识到戏曲创作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如汪曾祺先生说的“用韵文想”,因此可以叫做“戏曲思维”。我感到要真正把握戏曲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单独研究戏曲还不行,还得进行戏曲艺术与姊妹艺术的比较研究,于是就撰写了《戏曲“拉奥孔”》一书。
此后一段时间,我将所写论文辑为《新时期戏曲创作论》和《戏曲理论与戏曲思维》,尝试把当代的戏曲创作研究与古代的戏曲创作研究贯穿起来,试图在古代戏曲理论和创作里梳理出与当代戏曲创作相对应的理论命题,以期更好地推动当代的戏曲创作,并通过把古典戏剧创作论与当代的创作结合起来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民族戏剧理论体系。

安葵著作
研究戏曲理论必须研究戏曲理论家和戏曲艺术家的理论贡献,因此我结合一些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先后撰写了论述王国维、吴梅、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俞振飞、欧阳予倩、张庚、阿甲、郭汉城等戏剧家的文章,特别是对张庚先生的研究,撰写了《张庚评传》一书。因为多年的战乱环境,张庚先生解放前的很多文章和作品都找不到了,为了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我到各大图书馆查阅,还利用出差的机会访问张庚先生工作过的地方,查阅当地有关资料。先后到过长沙、武汉、泉州、上海、延安、张家口、哈尔滨、佳木斯、通化、沈阳、大连等地,访问了与张庚先生共过事的人,如吕骥、赵铭彝、陈锦清、干学伟、陈明中、石凌鹤、姚时晓、葛一虹、钟敬之、张水华、田川、张玮、胡沙等在现当代戏剧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访问和阅读的笔记记了十几本。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这不只是张庚先生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进程,通过写这本书,使我对现当代戏曲的发展进程和老一代戏剧家的杰出贡献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服务戏研所 往事可追忆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郭汉城先生。他与张庚先生一起,在“文革”后领导大家重建队伍,拨乱反正,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开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二任所长是苏国荣先生。他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他与沈达人先生一起,主编了“戏曲史论丛书”,组织和推动戏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拿出第一批个人研究成果。我的《戏曲“拉奥孔”》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那时出国考察的机会很少,他与院外事处的同志一起与文化部积极联系,争取到去印度做学术交流的项目。事后我知道他是很想去的,并做了很多学术准备,但最终他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别人,让沈达人、余从、我和孙玫四人去了。我参加了这次学术考察,收获很多,在历史文化的比较中加深了对中国戏曲和东方戏剧特点的认识。苏国荣之后,余从担任所长,我担任副所长;余从退休后,我担任所长。在此期间,我努力学习和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限于水平,成绩不大。日常的工作很多,特别值得回忆的有几件事。一件是与河北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了“东方戏剧展和学术研讨会”。1987年张庚、郭汉城先生曾策划召开了“中国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中国的戏曲研究与海外学者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我们举办“东方戏剧展暨学术研讨会”是想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当时邀请了印度、日本等国的戏剧团体演出了印度戏剧、舞蹈和日本的能剧和狂言,研讨会邀请海内外戏曲专家共同探讨东方戏剧的特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件是连续举办了8 届戏曲编剧培训班以及戏曲导演、戏曲音乐、戏曲舞美各一届培训班。新时期以来,各地都有提高本地剧作家、导演等创作水平的迫切要求,我们办培训班正是适应这种要求。我担任培训班的班主任,吴毓华、陈静担任副班主任。我们请来北京的戏剧、文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专家来教学,组织学员观摩剧场演出和重要作品的录像。对于外请的专家,我都在门口迎候,并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学员们因为有很强的使命感,学习都非常努力,颇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氛围。每一届培训班都组织游览一次长城,我和大家一起登长城。一幅幅长城上的合影,记录着大家共同学习的欢乐和友谊。这些学员中有很多人此后都成为各地创作的骨干力量。他们确实认为,在“前海”的这一段学习对他们的创作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工作也继承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举办戏曲演员讲习会和编剧讲习会为全国的戏曲创作服务的传统,加强了戏曲研究所与各省同志的联系。这一阶段还有与台湾及香港、澳门同行的学术交流。在与台湾的交流中,薛若琳副院长做了很多工作;在与港澳的交流中,田本相同志做的工作很多。我作为戏曲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也承担了相关的任务。我曾带台湾的戏剧家到大陆观摩戏曲演出,并推荐大陆的剧团到台湾演出;作为副领队和大陆学者一起到台湾参加学术研讨活动等。在这个过程中,大陆的戏曲研究者与台湾的同行结下了友谊,也推动了两岸戏曲研究交流的开展。

1998年,与编剧班学员合影,前排左一安葵,左二张庚

后排左起:安葵、郭汉城、刘厚生、龚和德
这期间,中国戏曲学会还组织了一些大型学术活动。1990年,中国戏曲学会与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活动,我担任学术组副组长(龚和德任组长)。2001年,中国戏曲学会在南京举办了纪念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50周年学术研究会,我作为秘书长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并撰写了《推陈出新五十年》及《戏曲研究五十年》等文章。
为了激发青年学者研究戏曲的热情,我们还与浙江的同仁一起举办了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的评奖,吸引了海内外很多青年学者参与。我退休后,后面几任所长都继续了这一活动,现在已举办了8 届,这些参评的论文从一个侧面记录着戏曲研究前进的足迹。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各国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化部向全国各文化厅(局)发了通知,要各地认真准备申报材料。文化部又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评审。我国符合条件的项目有好几个,最后根据专家和文化部领导的意见,确定要申报昆曲,并组织专家组进行了多次讨论。我当时任戏曲研究所所长,具体负责昆曲申报文本的撰写工作。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录音录像室的同志,对于文本的翻译和相关的录像资料,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协助。文化部外联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及时地转达教科文组织有关专家的意见,我们再根据意见修改补充。2001年5月18日,昆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的全票通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1年6月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大家对昆曲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意义和今后昆曲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文化部公布了《文化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我为能参与这一工作深感荣幸。昆曲申遗的成功,是由于中国的昆曲艺术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全体昆曲人的努力,我所做的只是一项“职务创作”。此后,我还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化部非遗评审、督导和调查研究活动。

与所指导的研究生合影,前排安葵先生和夫人,后排右起谢拥军、何玉人、魏强、柯凡、朱俊玲
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集体项目有我与余从共同主编的《中国当代戏曲史》,这是在张庚先生的直接指导下由我负责组织大家共同完成的。2007年,我与薛若琳共同主编了《中国当代百种曲》,这是中国戏曲学会根据刘厚生先生的提议经集体讨论确定选目后编辑而成的,我撰写了“前言”。通过这些作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曲创作的成就和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
教学方面,我1995年开始带研究生,先后指导了硕士生谢拥军(她之后又随郭英德先生读了博士)和博士生何玉人、朱俊玲、柯凡,艺术硕士生魏强。退休前我曾担任戏剧戏曲系主任,除给本院研究生讲课外,还给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讲课,并给中国戏曲学院的贯涌老师、郝荫柏老师、中央戏剧学院的彭隆兴老师的研究生上“小课”。教学相长,学生们活跃的思维、睿智的思考对我常常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编辑方面,我先后担任过《戏曲研究》的副主编、主编,《中华戏曲》主编。

授课中的安葵先生
退而未曾休 心怀使命感
2002年退休后,很想过清闲的生活。我曾向朋友们散发我写的一首打油诗:“老骥伏枥,慢慢吃草,烈士暮年,不能快跑。不贪事多,不嫌钱少,随遇而安,怎么都好。”但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对我很关照,给了我一些学习的机会。如文化部的一些观摩研讨、评审等工作,使我退休后仍没有脱离戏曲人奋斗的实践。直到2015年,我每年都应报刊之约撰写本年度戏曲状况的回顾、总结性文章。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也都撰写了回顾、总结的文章。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总结历史经验是很重要的,只有充分肯定取得的成就,才能坚定我们的自信;只有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进。退休后,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又让我担任了《昆曲艺术大典》的副总主编兼历史理论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第三版副总主编兼戏曲文学分支主编。除了参与设计整体结构、认真审读所负责部分的文稿外,我自己也撰写了一些文字,在工作中得到学习和提高。这些年,我也承担了文化部“国家昆曲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的很多工作,昆曲研究也成为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昆曲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

全家福
戏曲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不能放弃思考。如戏曲理论体系的建构、戏曲美学的研究,都是张庚先生等前辈的未竟之业,需要我们继续尽力。因此这些年,我又撰写了关于戏曲理论建设和戏曲美学范畴的文章。我认为,现代戏曲理论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戏曲的实际,以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为主要资源,吸收借鉴外国的戏剧理论,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我撰写了《中国现代戏曲理论的构成和新的建设》《如何对待西方戏剧理论》等文章,后者获得了中国剧协的理论评论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戏曲美学范畴既属于话语体系,也是建设戏曲美学体系的必需的一环。我把戏曲美学范畴梳理为形神、虚实、内外、功法、流派、悲喜、雅俗、新陈、美丑、教化十个范畴(已结集为《戏曲美学范畴论》,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述是否符合戏曲艺术的实际,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退休后所以还能做一些事情得益于我有很好的家庭环境。老伴王秀琴与我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她从中国医科大(沈阳)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能对我的健康“保驾护航”。几十年来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有一女一子,都是普通劳动者,包括女婿和儿媳,他们都勤恳工作,全家团结和睦。现在我的外孙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大孙女读初中,二孙女在幼儿园。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不断进步给我带来欣慰和欢乐。因此可以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学术研究。
八十初度,我曾写一首诗(步叶剑英元帅韵)表达自己的心情:
八十欣逢国运兴
龙腾虎跃涌新人
开山荜路仰前辈
继晷焚膏步后尘
须教园花齐绚丽
谁言国粹向沉沦
浑然不觉黄昏近
大道精深尚未明
耄耋求精义 心得赠后学
因为有很多成绩卓著的老前辈,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后生晚辈,但看到比我年轻的一代学者的成长,更是感到十分欣喜。如前所述,我是年近四十才真正开始专业工作的,现在不少四十岁的同志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了。我也深知现在的青年学生和学者有与我们那一代不尽相同的生活压力,社会的竞争也更激烈,所以要让他们完全做到“心无旁骛”是不容易的。但我希望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还是尽量能“心少旁骛”,趁身体好、记忆力好的时候,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研究包括我们的戏曲研究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做下去的。我在读《张庚日记》后曾写下这样一段感想,写在这里与大家共勉:
学术的发展要靠积累,但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理论,研究的成果体现为一种认识的水平,它存在于个体的学者的头脑之中,老一代的学者不可能直接把这些成果传给下一代;年轻一代的学者必须从头学习,并能体会到老一辈的心路历程,才能把老一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承继下来,变成自己的积累。所以要“站到巨人的肩上”是不容易的。张庚先生 用毕生的心血把戏剧研究事业推向了前进,但艺术研究工作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想在张庚先生等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就不仅要学习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
最后再补充一点:李学勤先生谈治学说,对于重要的学者,需要读他们的全集。我认为很重要。只有读了他们的全集,才能全面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也才能从他们的新贡献中认识学术的进展。张庚与郭汉城先生,我都是读了他们的“全集”的;在撰写其他戏剧家的研究文章时,我也尽量多读他们的著述,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甚多。当然这是苦功夫。如同做考据一样,不能指望每读一篇资料都会得到想要的结果。有人把考据和义理(思想)的关系比做蚕吃桑叶和吐丝,只吃桑叶不吐丝没有意义,但想不吃桑叶或吃很少的桑叶就吐出很多的丝来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