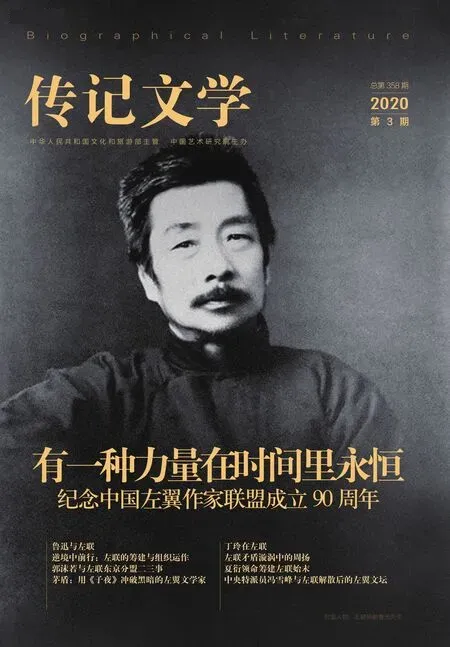群星当年耀黄湖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三)

家书里的家族叙事——《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绎读(上)
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作了重要指示,后被称为“五七指示”。此后,“五七”干校便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干部被下放到这里接受改造和锻炼。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创办“五七”干校。4月15日,著名作家叶圣陶的长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叶至善随大部队来到黄湖。此时,叶圣陶已经75岁,叶至善51岁。

1970年1月4日,叶圣陶与三个子女合影,右二为叶至善
叶家可以说是人丁兴旺。叶圣陶有子女三人:长子叶至善、次子叶至诚、女儿叶至美。叶至诚定居南京,至美出嫁,叶圣陶与叶至善一家生活在一起。但是,在叶至善下放黄湖农场时,留在北京东四八条71号的是年迈且患有心梗的叶圣陶和叶至善患有糖尿病的妻子夏满子、叶至善的长媳姚兀真和她的两个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叶圣陶想念远方的儿子,叶至善牵挂家中的老小,双方只能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从1969年5月 到1972年12月,叶至善在黄湖农场工作生活了3年零8个月。这段时间是叶至善离开父亲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段时间。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叶至善回忆说:“我去了潢川干校,有话要跟父亲和满子说,全靠写信。离家的前夜说定,每十天写一封。实测了两地邮程,往回一次只需六天,于是掐准了一星期写一封;最后缩短至三天一封,偶尔也有一天一封的,让此来彼往的信件在邮路上擦肩而过。”[1]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叶家父子一直保持密切通信,单单保存下来的就有446 封。2006年,叶小沫、叶永和将其中的300 封整理为《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由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2014年,潢川县政协又将其作为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文史资料专辑整理为《潢川黄湖干校家书叶圣陶叶至善(1969-1972)》[2]。“这次爷爷和爸爸互相保留下来的通信,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了,整理下来竟有近七十万字。可见爷儿俩彼此都很珍惜这信件,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3]

偌大的叶家常常只有这老幼三人:叶圣陶、夏满子,还有叶圣陶的重孙女阿牛
“这信中的爷爷就是那个时代的爷爷,这信中的爸爸就是那个时代的爸爸,还有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真实得没法再真实,确切得没法再确切。”[4]“这本家书,反映了叶家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对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价值。”[5]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书信在叶圣陶、叶至善的其他文献中都很少收录。因此,就了解叶圣陶、叶至善,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叶氏家族而言,这些书信不能不说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天南地北的牵挂
叶圣陶要求自己的儿子经常来信,哪怕只言片语,也能告慰家人的思念之情,保持家人之间的信息畅通。1969年7月25日,叶圣陶嘱托儿子说:“以后望你多写信,短些不要紧,以免挂念。”8月18日又说:“看信是我们的一大快慰。”对于二儿子叶至诚(乳名“三官”)不能及时来信,叶圣陶跟叶至善发牢骚说:“我也曾以同样期限期望三官(因为我连去几回信老无回信),问他能不能这样约定,最近他总算来信了,可是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在北京,他们在南京,见面时间少,以后恐怕也不会常见面。唯有信来信往,哪怕三言两语,一张半张,不痛不痒,无关宏旨,总算彼此没有失去联系,要是连这点联系也没有,太寂寞了。”叶圣陶之所以如此在意两个儿子的及时来信,一是出于对孩子的牵挂,同时也表现了叶圣陶晚年的寂寞。这就像他在1970年6月24日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没有谈话的对象,确是最苦的事”。12月13日,听说叶至善要回京探亲,叶圣陶就给他写信说:“希望你作个在家若干日的计划,和我谈些什么,……日子不多,要珍惜着过。”老人对儿子的期盼、对相聚的珍惜之情,读来令人动容。想一想也的确如此。因为年迈,身体又不好,叶圣陶已经很少出门。家里尽是些妇孺老弱,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叶圣陶满肚子的话去跟谁诉说呢?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叶圣陶喜欢给儿子写信。1970年8月21日,叶至善告诉父亲:“我的来往信件,别说全连,就是全校,恐怕也是最多的。”做儿子的也理解父亲的寂寞,就在同一封信中,叶至善又说:“我总怕爹爹惦记,怕爹爹寂寞,所以有空就写。”对于儿子的这份心意,叶圣陶也心知肚明。1971年8月17日,叶圣陶告诉儿子:“你近来写信更勤,我了解你的心意,知我寂寞,不能见面,就凭纸笔多多叙说。我非常感激你,真的。”父子之间的这种心意相通、相互体谅,读来让人心生温暖。盼望儿子来信的叶圣陶总是嫌信来得太慢。于是,叶至善几乎在每封信的开头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什么时候收到来信,这封信大概什么时候寄出,父亲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收到。1970年2月25日,叶至善就提前给父亲解释说:“今后雨水逐渐增多,公路汽车可能有时停开,如果接不到我的信,不要着急,很可能是被雨阻挡了。”体谅父亲到了这种程度,我们不能不感佩叶至善的仁孝之心,也不能不对他们父子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心生羡慕。
如果到了该收到信的时间没有收到,叶圣陶总会问起原因,叶至善也必然会在下一封信中详细解释。1969年10月11日,叶圣陶抱怨说:“大概是遗失了你的一封信,叫我们等得苦了。”“满子精神本来不大好,为了没来信,老是控制不住,想想就想到你不来信总有缘故。我是口头不说,心里也老想,不过还不至于睡不着。”“直到下午四点过,总算接到你的六日写的信了。看了之后,知道一点事儿也没有,大家这才放了心。”也难怪一家人担心,社会形势瞬息万变,叶至善毕竟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从北京下放到条件艰苦的黄湖,一开始如果长时间没有音信,家里人不免会胡思乱想。可能是收到了家人的电报,就在同一天,叶至善给父亲写信时解释说:“我每隔十天总写一封信,如果收不到,那就是遗失了,不会有别的原因。”“我以前信上说过,如果真害了病,倒有时间写信了,所以接不到我的信,决不是我身体不好,不能写信的缘故。”对父亲的那种体贴,对家人的那种牵挂,满溢于字里行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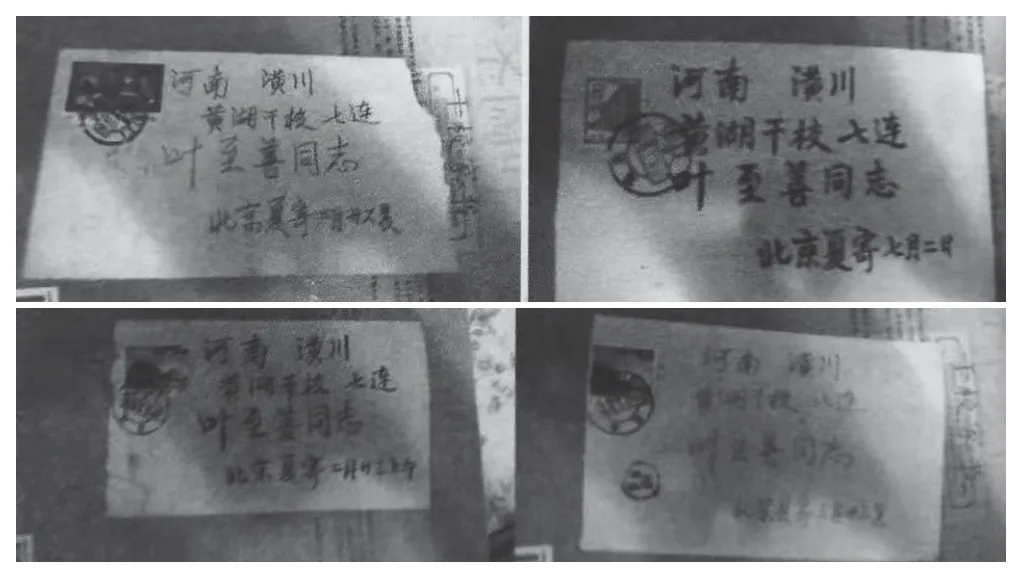
叶圣陶给叶至善所寄信的部分信封
身体健康的关心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叶至善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完成了37 万字的长篇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叶氏父子虽然长寿,但是,从这本《干校家书》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叶家也的确有不少人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在这些家书中,讨论家人身体的内容占有不小的篇幅,其中又以讨论夏满子居多。
1967年9月,叶圣陶患上心脏病,需要长期服药,无论走到哪里都须随身携带。1969年6月16日,叶圣陶给叶至善写信汇报:“你叫我出去必须带硝酸甘油片,你放心,我是一向带的,玻璃管里装两片,放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因为患病,叶圣陶一点儿重活也干不了。1970年7月11日,叶圣陶给叶至善写信,汇报他干活以后的感受:“说起擦电扇,那一天也不过弄了个把钟头,忽然觉得‘肝阳’发作,恶心,有些晕,与以前用心改稿时候发作的相似。于此可见我搞轻微的体力劳动也不行了。”就是因为父亲患病,叶至善经常在信中观照他多加小心。1970年10月18日,叶至善嘱咐父亲:“爹爹入冬以后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去浴室洗澡,要选好天,出浴室前要多坐一会儿再出来,要戴上口罩。”嘱咐得如此详细,好像在跟一个小朋友讲话,那种关心、那种体贴,恐怕很少有哪个儿子能够做到。

1971年1月19日,叶至善第二次回京探亲时与父亲合影
插队子女的教育
在叶家父子的《干校家书》中,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主要是叶小沫和叶永和,占有很大比重,300 封家书里面,专门讨论或提到他们工作学习情况的竟有70 余处。他们父子二人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两个孩子,一是因为他们年龄较小,二是因为他们都在偏远地区上山下乡。叶小沫1947年生于上海,叶永和1952年生于北京,在叶至善下放黄湖时,他们也不过20岁出头,甚至还不到20岁。1967年12月,正在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附中读书的叶小沫报名参加上山下乡,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插队。叶至善表示支持,并且说:“十年前我就打定主意要改换门庭,不支持子女继承父辈祖辈尽干笔墨的营生。”[7]基于这种思想,叶至善的四个孩子在20 世纪60年代都成了工人和农民。长子叶三午到密云水库林场当了工人,次子叶大奎先是在黑龙江泰康县团中央生产基地农业中学读书,学校停办后在泰康县印刷厂当临时工,女儿叶小沫到黑龙江军垦农场插队,幼子叶永和到陕北延长县农村插队。

叶小沫在黑龙江插队时留影
叶小沫、叶永和刚开始插队的时候,情绪都很高涨,工作上积极进取,思想上追求进步。1969年4月26日,叶小沫给家人写信,汇报“活学活用毛著讲用会”的情况。她写了两份材料,“都引起了营首长极大注意,一再帮我们提高认识,帮我修改,耐心极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深受感动”。她又把这两份材料寄给家人,“想让你们看看。当然要从思想和政治上来衡量,也可以帮我修改修改,如果不累的话。看完了寄给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改法,爷爷爸爸批在上面寄还给我”,要求进步的心情扑面而来。叶永和在农村的工作也十分扎实。1970年7月,他被派作民工参与修路,“劳动强度很大,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叶至善却“很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生产队把他们当作社员一样看待,他自己也把自己当作社员看待”;“这种集体劳动和生活,是他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极好机会”;“对锻炼思想和身体大有益处”。叶至善是真心实意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接受锻炼的。后来,虽然经历了选拔工人未果、同伴逐渐调离等切身影响,但是叶永和的情绪一直表现得很积极,这让叶至善很受感动,甚至认为自己应该向孩子学习。在1970年11月4日的信中,叶至善就真诚地对父亲说:“小弟的信看了很使人感动,我实在不如他。”

叶永和在陕北插队时留影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两个孩子的情绪还是不可避免地低落了下来。叶小沫先是经历了工作调动,后又因为生病想调回北京,中间经历了诸多波折。叶永和先是招工未成,后来又是考学未果,直到叶至善调回北京时,他的工作还未能确定下来。这些具体而却又涉及自身的事情,再加上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两个青年人的思想不免会发生波动,甚至出现“看穿”的情绪。这些都让两个老人感到十分忧虑。1972年1月28日,叶圣陶告诉叶至善说:“这回听小沫和永和的言辞,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有些‘看穿’。我不甚赞成‘看穿’,可是我无能劝说他们,为此心中怅然。”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消沉情绪,叶圣陶没有办法,叶至善也同样给不出主意。1972年春节,叶至善回京探亲,回到黄湖以后,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说:“这回回家,说实话心里不很舒畅。好像处处都是矛盾,许多问题想不通,心烦得厉害,因此发闷发呆。青年人那种对什么事情都看穿了的想法,我也看不惯,很发愁,但是又拿不出道理来批驳。”两位老人之所以无力解决,主要是因为这不只是孩子们的个人思想问题,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去分析社会现实而是拿一些大道理来劝说他们只能是适得其反。1972年3月7日,叶至善向父亲发牢骚说:“小沫和永和初去的时候,的确有一股劲,后来却逐渐消沉了。”“正因为缺乏斗争的毅力,这些青年必须再受教育。我又在说大道理了,大概也解决不了他们的思想问题。”1971年12月6日,叶圣陶告诉叶至善,说永和也对他们提出了意见:“他批评我们家里人,包括我和你,还有三午、大奎、小沫等,都不知道外面的实际情况,只是抽象地认为一切都好,一切都得从理论出发。”叶永和的这种观点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思想状况,而这种思想状况在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特殊时期的读书学习
作为书香门第,叶家父子自然不会不在家书中讨论读书学习的事情。据笔者统计,在这300 封家书中,他们父子讨论读书学习的内容多达120 余处,主要涉及购书寄书、理论学习、文坛现状以及如何作诗填词。
叶家父子都是读书人,生活中自然不能离开读书,但是在黄湖农场,图书资源十分缺乏,所以在书信往还中,叶至善经常让家人给他购书寄书。1969年5月2日,叶圣陶写信说:“我告诉满子,出外时经过书店,可买几本《红旗》寄与你与小妹小弟。《红旗》目录前天登出,但是书店未必就有。我又想人民出版社或许会出单行本,如果出,一定多买几本寄出。”同年5月21日,叶圣陶又告诉儿子:“《红旗》真不容易买,机关里集体购买,书店发行,每日一早排极长的队。前天满子出去的早,见书店运进的《红旗》多,就排了队。买了三本,一本寄你,一本寄小弟,一本我留下。”这两段话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叶家人虽然书生气很浓,但是也时刻关注时势的发展,而且还似乎把这个作为一种家风;第二,虽然早已退休在家,但是作为退休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叶圣陶依然能够比普通人更早了解一些文艺动向;第三,当时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都比较吃紧,不能及时买到,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资的紧缺程度。

1972年1月,叶至善从河南、叶小沫从黑龙江、叶永和从陕西回京过年,与夏满子、姚兀真合影
读书当然不能仅限于了解时事的报刊,叶至善也经常阅读一些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1971年5月7日,叶至善写信给父亲要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我仍旧希望能各有一本。”至少在干校期间,叶至善始终没有放松对革命理论的学习,经常向父亲索要各种理论著作,得到之后就会在以后的书信中与父亲进行探讨。1972年叶至善读书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文学与诗词,这时候他索要的书籍就更多地是一些文学著作。1972年4月12日,叶至善对父亲说:“我想要一本平装的《新华字典》,还有张允和编的那本韵书。《唐宋名家词选》在三午那里,我也想要来作参考。解闷,还是在学填词。”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报刊书籍充实了叶至善的下放生活。

1971年6月,夏满子随团中央“五七”干校家属参观团到黄湖参观时与叶至善在黄湖农场合影
进行理论学习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对于下放黄湖的团中央干部来说更是如此。叶至善在黄湖期间不仅参加干校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文件传达,而且自觉通过阅读理论书籍、与父亲进行讨论以及自己反思总结提升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1971年4月11日,叶至善给父亲写信汇报自己读书学习的情况:“《法兰西内战》,我还没有,是借别人的来翻了一下,看到中间引了许多当时的史料,感到很有趣味,仔细读的话,其趣味可能不在读战争小说之下。我想先读《共产党宣言》,第二本读《法兰西内战》,如果还能买到,就寄一本给我。”“读这几本书,我想最主要目的是在区分真假马列主义,区分唯物论和唯心论。”“读了这几本书和毛主席的著作,应该可以大体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列宁怎样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怎样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叶至善不仅通过读书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时刻在政治学习、生活实践中反思自己的思想。1970年12月26日,叶至善在信中反思自己说:“回顾到‘五七’干校来了二十个月,思想革命化方面的收获很少,实际上是‘劳动省心’,干活、吃饭、睡觉。”“追求心地平静,回避思想斗争,这个毛病不改掉,是改造世界观的一大障碍。”叶至善的这种理论学习和反思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他们的这种学习和反思都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实现思想的革命化,改造原来的旧思想,早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叶家父子毕竟是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依然不会放弃对当时文艺现象的关注。当然,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无外乎那个时期仅有的几个作家和几部作品,如浩然,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牛田洋》《草原烽火》等。1970年1月29日,叶圣陶评价当时的文坛说:“《文汇报》近来批判《早晨》[8],批判‘四条汉子’[9]……我看大多一般水平,不能说没有东西,也不能说有过硬的功力。批判文章精而短的,真正击中要害的,究竟不大多。”叶圣陶不仅对这些批判文章看不上眼,对当时的文坛评价也很是失望。1972年3月1日,浩然去叶家向叶圣陶请教,除了自己的作品,“他还说起今年五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文艺界真是够寂寞的了”。作为一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路走来的著名作家,面对当时文艺界的凋零与衰落,叶圣陶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作家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是浩然与叶圣陶之间的交往以及叶家父子对《金光大道》的评价。在1972年2月17日的信中,叶圣陶说:“我准备用二十天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册六百二十九页,每天看三十多页,不算多。小问题的确有,他叫我尽量从严,我就见到即批。”这是《干校家书》中第一次出现浩然和他的《金光大道》。查《叶圣陶年谱长编》,1972年2月13日,“浩然、李学鳌来访。”[10]据此推测,浩然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第一次到叶家请叶圣陶帮他审阅《金光大道》。3月1日,叶圣陶阅毕,浩然再次到叶家请教。“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页面都不甚干净。”“这部小说真是比历史还要切实生动。我不大佩服人,对这个人我真有些佩服了。”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浩然创作《金光大道》并非只有当时流行的“三结合”“三突出”等创作原则在支配着他,“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源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上述细节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叶圣陶对《金光大道》评价颇高,竟至于“有些佩服了”。叶圣陶如此,叶至善也同样如此。“浩然的短篇,看过一些,觉得也平常;这一本真是大有进步,不论从内容和语言来讲,都拿得出手。”(1972年5月31日)“有人看了说:这是目前的长篇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浩然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公允的。”(1972年6月9日)叶家父子的这些评价应该是受到了当时文坛主流倾向的影响,但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光大道》的创作水平和当时的文坛对这部作品的基本认知。
样板戏是那个年代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叶家父子的《干校家书》自然也会有所涉及,其中包括样板戏的普及方式、剧本创作、舞台表演以及对不同戏曲的不同评价。样板戏的演出剧种十分多样,《干校家书》提到的就有京剧、豫剧、川剧、粤剧、锡剧,还有话剧,这当然是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的欣赏习惯。戏曲的最初形态是舞台演出,但是普及范围太小,在与叶至善互通家书的那几年,叶圣陶这样的在京退休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都没能欣赏过现场演出。叶圣陶欣赏的主要是电影。1970年10月30日,叶圣陶写信说:“《智取威虎山》彩色片看了,非常满意。我虽然没看过舞台上演,我相信比看舞台上演好得多。”11月9日又写信详细解释说:“第五场《打虎上山》开头,杨子荣的唱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是在幕后唱的。看舞台表演,只看见雪林的死布景。影片则使观众以杨子荣的眼与心情见到骑马驰骋之际的活动环境。唱‘穿林海’的时候是无边的森林,唱‘跨雪原’的时候是广阔的雪原,镜头都推进得极快。待唱‘气冲霄汉’,则镜头一直向上,拍那高入云天的松树林。这比在剧场里听幕后唱胜过十倍了。就这具体的一例,足见此片之制作真是用心得很。”他们父子对《智取威虎山》评价很高,但认为其他几部样板戏则似乎不大尽如人意。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以后,1971年12月5日,叶至善写信给父亲说:“觉得这部片子拍得不太理想,镜头较乱,与《智取威虎山》相比,差得远了。似乎功夫下得不够。”1972年2月13日,叶至善又告诉父亲,觉得“《海港》改得比以前好多了,但仍不如前三个”。1972年3月22日,叶圣陶在信中评价说:“《龙江颂》的唱与白几乎全是概念话,实在不敢恭维。”叶家父子的这种交流,一方面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样板戏在当年的普及过程,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戏曲作品的不同反应。

1971年6月,夏满子随团中央“五七”干校家属参观团到黄湖参观时与叶至善在他居住的草屋前合影
“九一三”事件之后,干校的管理逐渐松懈,这从叶至善写给父亲的信件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叶至善在家书中讨论诗词创作的内容逐渐增多。从1971年10月22日叶至善第一次与父亲讨论诗词,到1972年12月21日的最后一封家书,叶家父子在《干校家书》中讨论诗词创作多达50次。在1972年的一些书信中,讨论诗词创作甚至成了主要内容。1972年3月19日,叶至善给父亲写信说:“对学填词,我最近有点入了迷。天老是下雨,实在闷得很。牛棚里人少,我也不习惯找人聊天,就自己‘冥思苦想’。”4月16日又写信说:“为了解闷,还是想填词。”这种现象在他前三年的家书中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的。那时候更多的情况是没时间写信,“挤时间写的这封信,字迹实在潦草,爹爹看起来一定很费力,但是一定很高兴”(1970年5月13日)。“没时间多写了。字迹潦草,可见我心里是多么急。”(1970年11月13日)对于儿子的诗词爱好,叶圣陶是支持的。1972年3月22日,他回信说:“你有兴作词,我有兴谈词,也算是找到了共同点。”

2014年7月,潢川县政协主席涂白亮(左二)到北京叶圣陶旧居拜访,受到叶小沫(右一)叶永和(右二)的热情接待
关于填词,他们谈论最多的是遣词造句和声韵格律。1972年3月25日,叶至善在信中写道:“平仄和韵,我看最好是通过熟悉的诗词来辨别,看前人是怎样用的,把它们归起类来。从前作韵书,想起来也是这个办法。靠查字典,实在太麻烦,还不一定靠得住。”在学习填词时,叶至善大概将王力的相关著作当成了工具书,但是在参考过程中,他却对王力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4月6日,他告诉父亲:“王力的词谱,是否靠得住,的确有点难说。”4月16日又说:“王力的书上对平仄的‘拗’‘救’‘黏’‘对’的规律讲得很繁琐,我看了也不明白。”后来他竟至于专门挑起王力著作的错误来。4月18日,他在信中很高兴地告诉父亲:“王力的书,又给我挑到了一个岔子。”填词作诗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雅兴,声韵格律又是填词作诗的专门知识,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也就止于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更为深入的内容大概也只有专业的爱好者做专门的研究了。
(待续)
注释:
[1][7]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78页、第376页。
[2]作为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的一部分,本文所引用的家书均以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潢川黄湖干校家书叶圣陶叶至善(1969-1972)》为本,引用时仅在第一处标注文献出处及所在页码,以后均不再另注。
[3][4]叶小沫、叶永和:《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叶圣陶、叶至善:《潢川黄湖干校家书叶圣陶叶至善(1969-1972)》,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2014年版,第1页,第2页,第1页,第2页。
[5]涂白亮:《千里传家书 只为黄湖故》,叶圣陶、叶至善:《潢川黄湖干校家书叶圣陶叶至善(1969-1972)》,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2014年版,第2页。
[8]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9]“四条汉子”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此说法源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10]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四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八)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