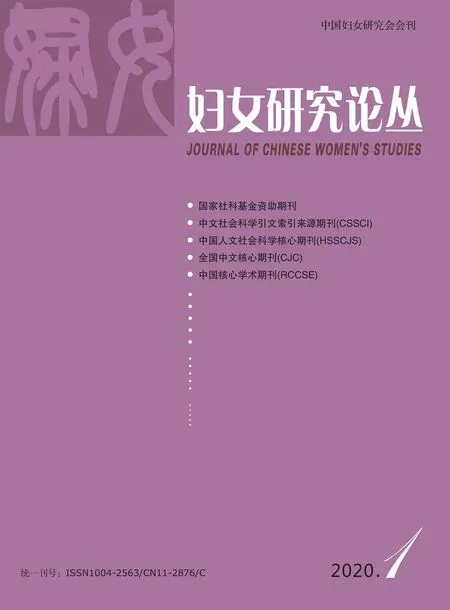闺媛与国事:戊戌六君子遗孀的生命际遇
宋 雪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光绪戊戌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宣告训政,并发布上谕,是为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9月28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被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这一惨烈的方式戛然而止。
“六君子不惜头颅,不惜身命,不顾家室,了然以一身为国家之牺牲”[1](P 1764),其志士精神百余年来被屡屡称说;而这“不顾身家”之死带来的六个家庭的破碎、丧偶失父的伤痛、世态炎凉的悲苦,历来却鲜少有研究者关注。随着菜市口刑场的屠刀落下,戊戌六君子的生命在暮色中消逝。观者陆续散去,史家对六君子的叙述通常到此为止。壮士横刀向天笑,抛头颅洒热血,自是历史上最为慷慨壮烈的一刻;而当夜幕降临,亲友家属各来收殓之时,死者长已矣,生者的情绪其实难以为外人体察。在纷纭复杂的社会舆论之外,六君子遗骨先后出都返乡,各家返榇营葬之事大多只能从友朋亲属的记述中获得些许片断;志士捐躯以后,留给未亡人的只有寂寞身后事。透过重重历史云烟,考索六君子遗孀的生命际遇和内心世界,发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女性故事,亦可见清季闺媛与国事之间丰富的历史张力。
一、维新谢幕之后:京华返榇的历史记忆
按照儒家传统,死生事大,叶落归根,官商亡殁远方者,应设法扶柩回籍,归葬故里。六君子喋血京华,虽为国事“要犯”,但为其料理后事、收殓回乡,仍是亲友责无旁贷之事。六位被难者皆非京都人氏,山水迢遥,再加上风声鹤唳的时局气氛,返乡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六君子身后京华返榇、归正首丘的历程,无疑是一种极具时代感的创伤记忆。
根据报载新闻,行刑之后,“各犯亲属闻信俱至,将尸首缝合,舁回棺殓”[2](P 2),惟“康广仁之尸竟无敢收殓者,由行刑之人随便弃置”[3](P 3)。《申报》报道,“康弟广仁之死,至无敢收其尸者,其衣衾棺木,悉由南海会馆长班代办,迟至日暮,始由长班潜往棺殓舁去。都中旧有广东义园,值年京官为杨少司马颐,因康系钦犯,不许康弟寄埋园中”[4](P 2)。
康有为事后记载,“幼博就义时,衣短衣,南海馆长班张禄,既得吾衣物,乃为缝首市棺,葬于南下窪龙爪槐观音院旁,立石树碑曰‘南海康广仁之墓’”[5](P 64)。南下窪是北京城的丛葬地,“蓬颗累累,坑谷皆满,至不可容,则叠瘗于上。甚且掘其无主者,委骸草莽,狸猃助虐,穿冢以嬉,髑髅如瓜,转徙道路”[6](P 23)。故虽经营葬,实非长久之计,甚至在时人眼里等同于“入万人坑”[7](P 2)。因此,逃亡中的康有为先是致信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请其代收遗骨,转寄香港,后又令门生陈介甫、梁元理入京收骨,皆未成[8](PP 414-415),直到1900年春,康有为派梁铁君入京寻弟墓,“得于北京宣外南下窪龙树寺之旁,携遗骸以归”[9](P 3),停厝于镜湖医院。1913年11月,流亡归来的康有为将亡弟移柩还乡,与亡母劳太夫人合葬南海县西樵山,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门生旧友挽诗颇多,辑入《哀烈录》[10](P 16)。七年后,1920年,又迁葬江苏句容茅山,并请陈三立撰墓志铭[11](PP 66-67)。1973年毁墓,现不存[12](PP 120-122)。
杨深秀被难后,留下的史料记录不多。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所编《山西献征》“忠义”篇所收《侍御杨仪村先生事略》,略记其归葬事:
身后藁葬京中,宣统二年诏先朝党事被祸诸臣听归葬,于是故人太平刘观察笃敬厚赙归葬于乡。民国三年,令山西省长官具先生事状付史馆,且优邮同乡,更议为先生建祠事,未举,先奉其主于闻喜会馆焉[13](P 17)。
因杨深秀长子韨田、次子墨田均避难未归,故灵柩返乡后暂厝于仪张村关帝庙,直到1926年方才安葬[14](P 48)。杨深秀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下阳乡仪张村南,碑额“戊戌志士杨深秀之墓”。1996年立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P 90)。
据《清稗类钞》记载,谭嗣同死时未瞑目,“李铁船京卿徵庸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耳’。始瞑目”[16](P 283)。浏阳会馆长班刘凤池与罗升、胡理臣二仆同往刑场检收遗骸,为之涤血缀元,殓后棺存僧寺[17](P 34)。
谭嗣同入京之前,曾充任江南筹防局提调,戊戌年其家属一度暂居南京。凶讯传来,谭家即于南京公馆设位成服,进行祭吊,旋派人北上迎接尸棺。“旧日同寅,无一人前往吊唁者”[18](P 2),世态炎凉,莫过于此。当年11月1日,灵柩归乡[19](P 142),权厝于郊外茂坪之墓庐中。“开吊之日,一切简略,吊者亦寥寥,仅挚友唐才常烈士及亲戚辈与时务学堂学生共十余人而已。”[17](P 36)1901年始葬牛石岭,墓有碑记,题曰“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20](P 75)。浏阳城中另有谭嗣同祠(建于1914年)和谭嗣同故居,现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林旭殁后,同乡林开謩(贻书)等[21](P 297)为其收殓,灵柩暂厝清慈寺,郑孝胥(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林开謩(时为翰林院编修)等在京官员曾前往祭吊[22](P 686,P 689)。10月12日,林旭灵柩起程,由仆人朱德贵护送离京返闽[22](P 689),21日过沪[23](P 1),11月抵闽,停柩于金鸡山地藏寺,“主(李)拔可家中,人皆礼重之”[24](P 156)。1901年秋,林旭岳父,时任淮扬海兵备道的沈瑜庆告假回闽,“营生圹于福州北门外义井,葬林晚翠夫妇左侧,题碣曰:‘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妙词。’又曰:‘北望京华,累臣涕泪;南归邱首,词女倡随’”[24](P 164)。墓今已不存。
杨锐、刘光第皆蜀人,被难后,同乡李徵庸(号铁船)出资为二人收尸[22](P 693)。黄尚毅、乔树柟为杨锐具棺装殓,停厝于清慈寺,郑孝胥等曾前往祭吊。10月10日,杨锐之子杨庆昶与门人黄尚毅扶柩出京[25](P 14),辗转运回四川绵竹,先停柩于南门外精忠观,后于南轩祠侧安葬,1958年毁墓[26](P 82)。绵竹县城关另有杨锐祠,落成于1916年,现改建为纪念馆[27](P 639)。
刘光第殁后,李徵庸、乔树柟代为料理后事,寄柩莲花庵,“朝官公车,无一人不来吊,外省来吊亦百数十人,皆相向痛哭”[28](P 5)。10月10日,遗孀张云仙携子女,在刘光筠(字南村)、廖湛华(字问渠)陪同下,扶棺归里,10月28日抵汉口,当年冬抵富顺县赵化镇(1)陈琴阶:《刘光第生平事迹》:“戊戌八月廿五日,张恭人携子三人,女三人出都,以运先生灵柩回富顺,有南村、问渠两公同行,九月十四抵汉口,十月某日抵富顺赵化镇”。转引自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按:笔者曾于2018年11月5日致信大连大学王夏刚教授请教,王教授11月23日回信告知此书系稿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仅有卡片目录。因未能通过馆际互借获得该书副本,此处暂作转引,并对王教授的回信表示感谢。,葬于赵化镇外罗汉寺旁。墓曾被盗,1987年迁葬富顺县西湖[29](PP 90-96),1991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30](P 1)为国事在京相逢的六位士人,生命与“百日维新”一同谢幕,遗骨各自舟车返乡,归葬故土。在六君子身后的祭吊、营葬、追悼、纪念乃至毁墓之举,也折射出百余年间时代风气与舆论思潮的变迁。
由上述材料,为六君子收殓营葬的,多为各人同乡旧友,而罹难诸人的妻室至亲,在如此横祸面前,似乎多数是缺席的角色。在清季乱世中,未亡人丧夫失偶的内心伤痛,其实难以被男性视角下的历史书写所详细体察;关于她们的命运和选择,时人也存在诸多道德评判与政治误读。
二、曲解与误读:“烈女”形象的生成
考证六君子的姻亲关系和子女情况,简列如下:
杨锐,夫人孙氏,生一子三女,1908年卒[25](P 15)。
杨深秀,原配李氏,1851年生,闻喜县城人,1863年5月嫁与杨深秀。有三子,韨田、墨田、弧田,1907年卒[14](彩页图录)。另有一妾莫氏,生年籍贯不详,无出,1926年卒[14](P 130)。
谭嗣同,夫人李闰,字韵卿,1865年生于湖南长沙,为咸丰六年进士李寿蓉(字篁仙)之长女,有家学渊源,擅诗词,1883年5月嫁与谭嗣同[31](P 96),1889年生子传择,越年即殇[32](P 54)。系“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1914年创办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自任校长,1925年去世[20](P 65,P 52)。
林旭,夫人沈鹊应,字孟雅,1877年生于福建侯官,为两江总督沈葆桢孙女,沈瑜庆之长女。曾受业于陈衍、陈书兄弟,工诗词。1892年嫁与林旭,1900年春“毁殉”,无子女,有《崦楼遗稿》存世[24](P 128,P 148,P 162)。
刘光第,夫人张云仙,1858年生,四川富顺人,粗识文字[33](P 252)。1877年嫁与刘光第,生四子(鹏年、凤年、长安、鹤年)五女(稚云、秋姮、茂萱、桂馨、荷生),其中长安和秋姮早殇。张氏卒年不详。
康广仁,夫人黄谨娱,生卒年不详,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孝友通达,且甚才,持节茹苦。”有一女名同荷,“毕业于日本女学,明锐有父风”(2)康有为:《康烈士广仁传》,《哀烈录》卷一,《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第16页。按:梁启超《康广仁传》(《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本《清议报》,第1册,第331页)作“黄谨娱”,康有为《哀烈录》作“黄娱谨”。由康有为在家书中称黄氏为“谨如弟妇”(马忠文:《黄元蔚家书所见康梁活动史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98页),而广州话(南海县属方言划分中的粤海片,粤海片以广州话为代表方言)“娱”和“如”二字同音,均记为jy21(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313页),推知《哀烈录》系误排。。
除林夫人沈鹊应和谭夫人李闰外,其他数位女性留下的材料极少,甚至无从查考杨锐与杨深秀夫人的名字。六君子慷慨赴死,以志士身份留名青史;而在他们身后,承受着毁家丧夫之痛的女性,在历史上只有模糊的身影。
在传统社会,女性的“贞”与男性的“忠”相对应,作为未亡人,大抵只有守节与殉节两条路。六君子以“国事犯”身份被清廷处决,虽然此案并未株连,但“犯属”身份无疑给了遗孀们更大的舆论压力。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求死似乎成为时人眼中最为“合理”的选择。根据报刊新闻、时人日记乃至在华西人回忆录,当时坊间传闻杨深秀之妻妾、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之妻悉皆自尽,方式包括自缢、仰药、投水、自刭等,情状惨甚。郑孝胥在日记中哀叹“闻刘光第之妻缢死,五子,长者才八岁耳”[22](P 686),《新闻报》《申报》《亚东时报》则报道了杨深秀妻妾的死讯:
杨深秀家有一妾,痛夫情切,于十四日乘间自缢身死[34](P 2)。
杨深秀之妻闻变,自缢而死[35](P 2)。
闻其(杨深秀)妻亦仰药殉之云[36](P 20)。
关于林旭妻沈鹊应与谭嗣同妻李闰之死事,报道最多,传播最广。二人均系名门之女,通晓诗书,堪称才女。贤媛殉节的故事,似乎最为引人关注。
沈鹊应之死,最早揭载于《新闻报》,记述甚详:
(林旭)妻沈氏,系沈文萧公族女,秉性贤淑,颇知大义,适林未逾三载,尚未生有子女。日前得耗之下,哀痛异常,誓以身殉。亲属善劝,且步步随守,未能遂志。嗣于某日人定之后,乘人睡熟,暗取紫霞膏吞服。比闻呻吟之声,知必有异,设法灌救,奈受毒已久,一缕贞魂,竟随夫地下而去。其情实惨,其志堪嘉,是当志之以彰柏节者也[37](P 2)。
这段报道,写法颇近于传统的“列女传”,以“其志堪嘉”“以彰柏节”点明文旨。此时距离六君子被难,只有二十余日。虽然其中有一处史实错误(此时林沈二人结婚已六年有余),但由其叙述细节之详尽,读者其实不易察觉其中的问题。随后,日本报人山根虎之助将这一传闻写入林旭小传:
(林旭)妻,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也,得报痛不欲生,传闻已仰药殉之云[36](P 20)。
对于消息真伪,山根虎之助可能并不十分确定,故以“传闻”述之。而当《六士传》经历了中日之间的文本旅行,回译成中文发表时,此处文字变成了:
其妻沈氏,字文萧,沈公葆桢之孙女也。得报痛哭不欲生,乃仰药以殉[38](P 10)。
相较于山根虎之助的原本,这里发生了两处变动,一是误将沈葆桢之谥号“文肃”当作沈鹊应之字,二是把传闻更易为事实,坐实了沈氏之死。查《日本》所刊《清国殉难六士传》,此处表述为:
其妻沈文蕭は葆公楨の孫女なり。報を得て痛哭生くるを欲せず。藥を仰で之に殉せりと云ふ(3)《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年11月28日,第3版。感谢狭间直树教授寄赠原刊影本和业师夏晓虹教授的帮助。。
由此可见,两处误植均出自日文本,《知新报》翻译时照录。根据狭间直树教授的研究,将《六士传》译成日文,再回译成中文的过程,与在日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密切关系[39](PP 195-218)。根据梁氏当时的日语水平,汉译日的执笔者大约并非梁启超本人。不过,由翌年《清议报》所刊《林旭传》,将沈鹊应之死定作已发生之事实的,很可能就是梁启超:
(林旭)妻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入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40](P 456)。
由文字上的相似性,梁启超在写作中很可能以《六士传》为底本。梁文加入了沈氏拟入京收骸骨之事,较之日文的记述,情节上更为生动具体,烈女形象也更加突出。同时,由于梁启超的维新同人身份和《戊戌政变记》的巨大影响,沈鹊应殉夫自尽之说流传甚广,日后李提摩太撰写回忆录时,亦提到此事:
The betrothed of Lin Shio,on hearing the news of his execution,at once committed suicide.[41](P 267)
在沈鹊应仰药殉夫之事屡见报端的同时,谭嗣同的遗孀李闰也由“节烈”之举,登上了新闻。1899年3月2日,《国闻报》刊发长文《谭烈妇传》,述其“幼娴《内则》,博极群书,议论明达”,且由明代杨继盛(号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凸显李氏性格之刚烈执着。该文详叙谭嗣同死后,噩耗传来,李闰悲恸求死之事:
是月复生父谭公罢鄂抚,携眷南归。复生噩电适至,总督命录其语为椷交谭公幕僚,约到湘始发。舟次湘阴,语泄。烈妇自船窗跃入河,逾时救起,息未绝,至长沙复苏,舆以入城。过自巡抚辕门,烈妇下舆伏堂大恸哭。陈公命婢媪掖入内室。烈妇跪地哭,语不可晓。陈公长跪语之曰:“汝夫之死,吾欲为之营救,而朝廷以为吾罪,且逮治吾。大臣义不可辱,行将与汝夫相见于地下”。语未既,烈妇袖中出寸刃自刭,血溅陈公襟袖,阖署大惊,医者梁生出良药封创口,舆归寓次。次晨,烈妇忽若欲语状,婢倾听得其语,问视杀吾夫者谁,或告之曰,大学士某。烈妇捶床大呼某某,创破,血直射丈许,两眦皆裂,遂死。及殓,双手交握,不可开。齿尽碎,血流胸前成刀字,拭之愈明。呜呼,烈矣!(4)《谭烈妇传》,《国闻报》1899年3月2日,第1-2版;《游戏报》1899年3月15日,第1-2版;《清议报》第10册,1899年4月1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本《清议报》,第1册,第593-594页;《知新报》第82号,1899年4月1日,第7-8页。
这段记述中,李闰先是投水,继而自戕,再而捶床,最终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自杀成殉。《谭烈妇传》以传统纪传体行笔,情绪丰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此文刊出后,《清议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皆予以转载,且《清议报》将其置于《戊戌政变记》的叙述框架之中,李氏之殉节获得了与六君子之殉国同等的地位。与《新闻报》所刊沈鹊应之事相比,虽然二文均细写女性死节之惨,然沈氏之死意在彰其“贞”,李氏之死更加重其“烈”。“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42](P 298),在历朝正史“列女传”中,节妇烈女向来是重点书写的对象。沈李二人皆出身宦门,青年丧夫,且膝下无子,以旧道德的眼光来看,在此情境下,或许唯有一死。因此,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后,对于遗孀自尽殉节的新闻报道,时人除慨叹“哀哉”“烈矣”之外,似乎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根据史料,杨深秀妻妾和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之妻自尽的消息,其实都是假新闻。在传闻与史实的巨大反差之间,不仅有政治宣传的考量,也尽显晚清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
男子死忠,女子死节,皆为古代名显千秋之事。纵观维新同人的戊戌书写,文本多有强烈的现实政治隐喻。史学家已经考证出康、梁对政变许多关键性细节的伪造行为,维新报刊中对沈鹊应和李闰殉夫情事的书写和建构,亦存在类似的因素。维新同人在辩白六君子之忠君爱国的同时,大力铺叙各人遗孀殉夫自尽之情状,以女子之贞烈衬托壮士的忠义,以此获得舆论的同情和海外的支持,实际上仍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不过,恰是与这些列女传式的故事相对照,六君子遗孀的现实境遇,反映的才是新旧转换时代女性所面对的真实世界。
三、求死与臾生:未亡人的内心世界
根据现有的史料,变法失败之时,六君子中只有刘光第携家眷寓京中,张云仙也是唯一得以亲理亡夫丧事的遗孀。1888年,刘光第携眷入京,生活清贫,“其境遇困苦,为人所不堪,君处之怡然”,“其夫人自入都至归,凡十一年,未尝一出门与乡人眷属答拜。宅中惟一老仆守门,凡炊爨洒扫,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在长年的劳动和子女的拖累下,40岁的刘夫人已如同老妪,“帐被贫窭,乃不似一官人”[28](P 5)。刘光第死后,“其夫人自缢数次,均经家人救活”[43](P 1)。除去遇救得不死[16](P 283)的因素之外,此时他们京中尚有子女五人,长子鹏年九岁,季子鹤年只有三岁,张氏实有“死不得”的苦衷。在寓京十年之后,张云仙携儿带女,舟车迢遥,扶柩归乡。没有文字记述这位昔日的四川农家女是以怎样的坚韧意志,间关万里,返榇归葬,抚养子女。其长子鹏年后改名长述,曾加入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从事新闻工作。由其1906年弃学回家侍奉寡母之事[44](PP 25-28)推知,张氏卒年当在1906年以后。
政变发生时,杨深秀之发妻李氏仍在山西,在京府中服侍他的是妾莫氏。杨深秀被难后,莫氏自杀未遂,辗转回到闻喜,与李夫人一同“守灵抚孤直至寿终”。1926年,夫妻妾合葬[14](P 130)。
关于林旭之妻沈鹊应自杀殉夫的传闻虽不确切,但在哀恸中度过了一年半以后,1900年春,她还是“毁殉”而亡[24](P 162)。林纾曾以小说笔法摹写林旭在缇骑到来之前的心理活动,“自念身受不次之擢,年未三十,死以报国,亦无所愧”,唯挂念“娇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从吾死,不期酸泪如绠”[45](P 39)。这一霸王别姬式的场景虽出自想象,却道出无限悲凉。林沈感情甚笃,二人曾同拜于闽派诗人陈书门下。林旭宦游期间,夫妇以诗词相唱酬,互诉衷肠,被推为文坛佳话;政变噩耗传来,沈氏以极其悲痛的笔调填词悼亡,并终以身殉,“合葬闽山阳,歌哭见风谊”[21](P 298)。李宣龚曾作联挽曰“淮水东流,语怨不曾伤小雅;夕阳西匿,魂归何以慰孤忠”[24](P 162),悲慨二人的凄凉谢世,亦点出沈氏的诗词造诣。
在“孤嫠泣淮水”[46](P 300)的年月里,沈鹊应留下了多首悼亡诗词,其中尤以《浪淘沙》最为文坛推重,“字字沉痛,传者哀之”[47](P 231):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48](P 312)。
上片哀夫君赍志以殁之憾,下片叹己身命运沉浮之悲,数语之间,道出心中无限哀伤。与传统闺怨诗相比,这些文字所叹的不只是一己之际遇,更饱含着国难中的惨淡心情。林旭就刑前,曾赋诗“慷慨难酬国士恩”[49](P 281),沈氏一方面理解丈夫的报国宏愿,另一方面“翻悲罪人妇”[24](P 162),空叹离合悲欢之无常。身为未亡人,她翻检亡夫遗稿,追怀往昔旧事,“掩镜检君诗,泪痕沾素衣”[50](P 313),“遗编和泪叠,字字是华严”[51](P 317)。她以琴曲遣怀,“暗坐悲君泪不禁,聊将诗卷谱桐琴”,然而“凄凉曲罢声声血”,唯有“拥鼻妆台学苦吟”[52](P 318),借诗寄托心中万千愁绪。除夕之夜,在万家团圆之时,沈氏设奠祭祀,写下凄凉哀绝的断肠文字:
空房奠初夕,对影倍凄然。
守岁犹今夜,浮生非去年。
心随爆竹裂,眼厌灯花妍。
况是无家客,银筝悲断弦[53](P 317)。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哀伤和凭吊中,词女“病骨寒将断”[51](P 317),最终追随亡夫而去。其父沈瑜庆为《崦楼遗稿》所作题词,道出爱女在板荡流离中的心境: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难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能无诗,此崦楼之诗所由作也。过此以往,以怨悱之思,写其未亡之年月,其志可哀,其遇可悲[54](P 305)。
与报端刊载的“仰药殉夫”故事相比,沈氏真实的境遇,其实少了几分刚烈,多了无数深情。其心中书写不尽的凄凉悱恻、一往情深,并不为一般时人所知晓。
谭嗣同夫人李闰,虽系出名门,实一生坎坷。她幼年失母,25岁失子,29岁丧父,33岁丧夫,命运的打击接踵而来,她却以不寻常的坚韧承受了一切。在谭嗣同为维新事业奔走时,李闰亦身体力行,参与倡办女学会,赞助湖南不缠足会[55](P 8)。谭嗣同殉难后,李闰由亡夫“忍死须臾待杜根”之句,自名为“臾生”,继承丈夫遗志,捐资办学,1914年创立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以昌明女学、开通风气;又倡办育婴局,以绝弃婴恶习。在这一意义上,李闰可谓一代“新女性”,亦无愧于“巾帼完人”的称号[31](PP 96-99)。
谭嗣同曾在家书中写下“夫人亦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56](P 530)之语,但当政变遽作,噩耗传来,忽为孀妇,李闰胸中自有千转愁肠。根据记载,她每当朔望,必焚香燃烛祭奠,以寄哀思。李氏曾作悼亡诗稿一本,“凡二百余篇”,惜已不传[57](PP 89-90),所存仅一首七律,可谓字字泣血、肝肠寸断: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31](P 99)。
与沈鹊应的悼亡文字相比,李氏虽同在慨叹亡夫壮志未酬之遗恨,抒写嫠妇寂寞孤灯之苦况,但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对国难家仇的悲愤,而非己身命运的悲凉。在“死”与“生”之间,沈鹊应选择了“求死”,“药炉经卷在,即此了吾生”[58](P 317),以死亡作为解脱烦扰之道,以期与亡夫黄泉相会;李闰则选择了“臾生”,“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着,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31](P 99),在伤悼忆往的同时,与乖蹇的命运作抗争。死生之间,并无对错之分。在晚清政治失序的历史背景下,沈鹊应和李闰的生命际遇,体现了志士形象背后,女性身上少为人知的苦难;而她们在文学中的世运关注与自我呈现,也表现出变局时代闺媛复杂的内心世界。
四、结语
作为世纪之交最为悲壮的历史事件,戊戌六君子的死难具有多重历史意涵。在政治史、革命史的话语之外,以个体生命的视角透视晚清社会,可见在戊戌之秋的政治高压下,其实涌动着复杂的时代情绪。这场失败了的维新运动,虽未能完成“新国新民”的期许,然其在政治体制、文化思潮、社会舆论诸方面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亦昭示着国家未来新的可能。
六君子的死难,在国族命运的象征意涵之外,于六个家庭而言也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孤儿寡母的凄凉、道德舆论的压力、乱世流离的苦况都压在未亡人心上。在此情境下,“求死”抑或“臾生”对她们而言都同样艰难。在她们模糊的身影背后也折射出新旧之间的历史转向。女性个体生命在清季变局时代的多元选择,在六君子的下一代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杨锐之次女绯云“字吕氏,未成婚而婿殁,誓不他适”[25](P 15);而康广仁之女同荷,则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校[59](P 53),甚至在东京“开会演说,鼓吹革命”[60](P 4)。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传统的“贤媛”形象最终被新女性所取代。作为戊戌六君子之妻女,李闰、康同荷的人生选择其实也代表了维新运动与革命思潮对女性的影响。同时,透过百年历史云烟,打捞六君子身后这些少为人所知的女性故事,钩沉“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概背后“低徊哀歌”的伤痕记忆,亦有助于体察被长期以来的烈士书写所遮蔽的儿女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