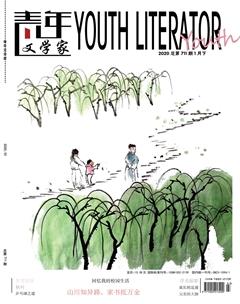从“情”的逝去到“情”的回归
摘 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源远流长,在这种传统里,文学艺术家们不仅局限于抒发个人情感,也借由抒情观照历史,反思家国兴衰、社会剧变。白先勇在《游园惊梦》里表达了代表着“情”的传统的消逝,而借由青春版《牡丹亭》召唤“情”的回归,这种姿势本来就是抒情傳统的一部分。白先勇用一种抒情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爱情、生命、往昔、家国以及传统的复杂情感,“情”与“抒情”得以完美统一。
关键词:情;抒情;传统复兴
作者简介:姜智慧,女,湖南安乡人,华东师大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3-0-02
(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1]”1945年的上海美琪大剧院,梅兰芳一曲婉丽而妩媚的《游园惊梦》将经历了八年战争离乱的人们从恍如隔世的噩梦中唤醒。而就在那一刻,昆曲的优雅与凄美触动了九岁的白先勇内心深处的某一种情愫,这种情愫在他此后的人生履历中不断丰富与复杂,即便到了人生的晚年,他竭尽全力也要将这曲戏所代表的抒情审美意境再一次生动地还原。
(二)游园招魂,“情”的逝去
二十年后,经历了民族的危难分裂,家族的过眼繁华,亲人的离散永别的白先勇,把对家国传统的依恋、人世沧桑的无奈之情,抒发在小说《游园惊梦》里。而他在兹念兹的昆曲,则成为这部小说创作的动机。他曾说:“由于昆曲《游园惊梦》以及传奇《牡丹亭》的激发,我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两出戏的境界,这便是我最初写《游园惊梦》的创作动机”[2]。昆曲《牡丹亭》是潜藏在小说中的一个潜在文本,白先勇借助于梦境连接过去与现在,表达了他对于往昔的依恋与召唤。《游园惊梦》里一群经历了家国丧乱流落异乡的南京贵族,依然活在往日民国政府的繁华记忆里。在一场如梦似幻的的盛宴上,当年红极一时钱夫人蓝田玉因一曲《游园惊梦》忆起往事种种,一时哽咽失声。她在这一次“游园”中“惊梦”,顿感世事变迁与人生无常。《游园惊梦》所惊醒的,不仅仅是钱夫人一个人的梦,而是整个没落贵族阶层的美梦。
昆曲曾经从明朝中叶起盛极一时,后于乾隆年间,被通俗浅易的花腔取而代之。因此,小说里钱夫人的今夕感触以及往昔凭吊,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游园惊梦》不仅仅是一部蓝田玉等一群人身世的沧桑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阙挽歌。昆曲这种精美的艺术形式,曾经是贵族阶层辉煌时期精致生活的体现,也是一个繁华时代的象征。《游园惊梦》将昆曲百年的变化浓缩于一夜,小说末尾,钱夫人感叹:“变多喽。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的高楼大厦。”这一“变”字,道出了白先勇内心对于传统消逝的怅然。他在小说里尽情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以“情”主导,象征着生命、灵性与希望的往昔消逝的一种感伤。面对繁华的陨落,传统的衰败,白先勇借着《游园惊梦》叩问:一场宏大的,关于时间重整的冒险,怎么就让过去如此“陨落”了呢?那么丰富的文明,那么繁华的景象,怎么就不由分说地都失去了呢?[3]也许,白先勇借助于今昔对比所要表达的,是他对于个人、家国、传统以及时代文明的反思,他徘徊在时间的两岸,想通过写作这样一种抒情的表达,为他所处的60年代招魂,这种召唤实际上也是他寻求文化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达。
(三)牡丹还魂,“情”的回归
小说《游园惊梦》中白先勇对于传统与青春美好伤逝的困惑,以及对于传统文化失落的反思与叩问的解答,是他之后的生命道路中一直探寻不止的梦。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文化救赎与往昔再现的旅途。《牡丹亭》中汤显祖思想的伟大之处不是情对理的反抗,而是理必须以情为基础。黎湘萍[4]认为:杜丽娘的苦,不是来自于礼教的压迫,而是来自于为情所苦。在《牡丹亭》中,礼教并不构成压抑人性的迫害力量。汤显祖是想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在所有礼教、政治、理和道所构成的人世风景里,最不能或缺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乃是“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在汤显祖看来,“诗言志”无他,“情”也。 我们不必追问情从何而来,我们只要懂得这个“情”是中华传统里“安顿生命与文化的绝对信念与姿态”[3]210,它可以跨越时空,超越生死。《牡丹亭》所承载的人性与生命意识,正是生活在工具理性时代的现代人所缺乏的。白先勇将《牡丹亭》命名为青春版,是想从现代的视角,重新塑造一个纯粹、干净、雅致与唯美的现代版《牡丹亭》,与传统遥相呼应,并让传统在现代重生,唤醒当代人对于诗性的追求与至情的向往。他曾经在与符立中的对话中谈及:如果要给《牡丹亭》一个定位,可能是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从《诗经》、《楚辞》一以贯之——的巅峰[5]。因此,白先勇以“抒情”作为青春版的制作总原则,一切努力都以“情”的展演为核心。
(1)以“情”为主线的剧本整编
《牡丹亭》原著作的情节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柳梦梅和杜丽娘反礼教的主线,另一条是陈最良和杜宝等代表封建势力的主线。两条线索形成一种张力,体现了情与理的对抗,对当时明末礼教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而青春版《牡丹亭》面对现代观众,封建“理”的线索不复存在,因此主要围绕着“情”的主线展开,除了杜、柳之间的爱情之外,还有一条隐形的“情”的线索,即杜、柳两家与其家人、仆人等的情谊,这一显一隐两条“情”的线索,构筑一个爱情、亲情与友情交织的完美世界。全剧分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三部分,“由情真、情深、层层推进到情至的境界;也由情与自我、情与他者、逐步扩展到情与社会的关系”[6]。整编中为了利于情的推进,青春版对于二十七个折子戏的整理也是进行了适当的串联与剪裁,对于原著的折子戏顺序进行了部分的调动。全剧从杜丽娘的故事开始,引起观众对“情”的期待,唤起普通大众的情感共鸣,唤起日益功利化的现代人原始生命情感的复苏。
(2)突出“抒情”的舞台演出
舞台演出如何让“情”生动地展现与传达是青春版《牡丹亭》的核心。青春版《牡丹亭》着重打磨与渲染男女主人公的抒情唱段。为了突显杜丽娘一往情深的诗人气质,突出了原著中“驚梦”、“寻梦”、“写真”、“离魂”等旦角表演的抒情唱段,使得“千古第一有情人”的形象得以凸显与丰满。柳梦梅在 “拾画”中因为游赏花园,触景生情,唱起“锦缠道”,用半小时的独角生角戏把柳梦梅的痴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男主角游园与寻梦的情景和上本中女主角游园寻梦两相呼应,构造了一个纯粹诗意的有情境界,男女主角在这种浓厚的抒情氛围里尽力展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极好地呼应了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杜丽娘因情而死,花神出场为之护送,“回生”里杜丽娘在花神的围绕中复活,最后大团圆的场景里,花神簇拥而舞。花神是杜丽娘的守护神,也是青春、生命、美好的象征,杜丽娘美丽的梦境与花神的表演充分地诠释了《牡丹亭》“情”的主题,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3)为“情”服务的舞台呈现
传统的昆曲演出,舞台上没有布景,一桌两椅,剧中情感的体现完全依靠演员的歌唱与身段表演。而青春版《牡丹亭》运用的却是现代的大型舞台,如何在现代剧场里展现传统昆曲的美?白先勇以“尊重传统,却不因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为原则,“在舞台装置、服装道具、舞蹈技法、书画布景、灯光设计等各个方面有所变革,既保持写意、抒情、象征诗化的传统意境,又放手打造古典与现代相互交融的舞台场景”[7]。青春版《牡丹亭》里没有具象化的舞台背景,而是利用书法、绘画以及投影营造了一个写意、简约的空间,演员服装的水袖以及服装颜色的搭配都适合昆曲传统的审美标准,唱腔的配乐、配器皆依照现存昆曲曲谱, 新配的音乐、过场都体现了传统昆曲音乐的特点。所有现代元素的运用,恰恰更好地彰显了古典的雅韵。青春版《牡丹亭》,正是白先勇面对21世纪的当下,对现代粗鄙的机械复制与商业潮流的批判,他想借着青春版《牡丹亭》,重现中国古典的人文精神。
(四)“情”与“抒情”的完美统一
从《游园惊梦》到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用一种抒情的方式展现了“情”的失去与“情”的回归。白先勇在写作中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最精美的就是抒情美典,中国文学最悠久的就是抒情传统。这样一个召唤过去的姿势,本身也就是一个抒情的姿势。通过这一姿势,他在尽力弥补海峡分割造成的巨大缺憾,以及现代对于传统的巨大断裂[3]214。21世纪,置身于工业繁荣、科技发展而传统逝去的现代化语境里,白先勇又用青春版《牡丹亭》这种抒情的表达方式,以中国抒情传统的巅峰之作,唤起情的回归,这种努力何尝不是中国文学里伟大抒情传统的一部分。白先勇在多次访谈中强调,自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给与了过分的关注与书写,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声音,这种声音既能融合中国古典,又能体现现代。《游园惊梦》用一种现代的写作手法表达传统的失去,青春版《牡丹亭》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呈现传统的回归,二者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古典意义上的抒情倾向。因此,《游园惊梦》和青春版《牡丹亭》可以说是白先勇用一种抒情的方式回归中国文学艺术抒情传统的努力,同时也是他从抒情的视角,表达对于抒情传统里“情”的尊重与探寻。白先勇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自西学东渐开始,中国人不仅与传统文化割裂,对传统肆意破坏,更是在长期“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霸权话语下,失去了文化自信。白先勇借由《牡丹亭》建立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以此重建他心中的传统家园,唤回传统文化的青春。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无处不谈启蒙与革命的史诗年代,和今天商业文明与的科技革命的大场景里,《游园惊梦》与青春版《牡丹亭》的抒情召唤显得尤为可贵,当这个时代过去,回头再看时,这种抒情之音也许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2]白先勇《白先勇文(五)》[M].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6页。
[3]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08页、210页、214页。
[4]黎湘萍 闻玄歌而知雅意—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文艺复兴[A].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M].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5]符立中《对谈白先勇—从台北人到纽约客》[M].现代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6]华玮 情的坚持—谈青春版《牡丹亭》的整编[A].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M].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7]吴新雷 青春版《牡丹亭》的独特创意与成就[J].华文文学,2005(6):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