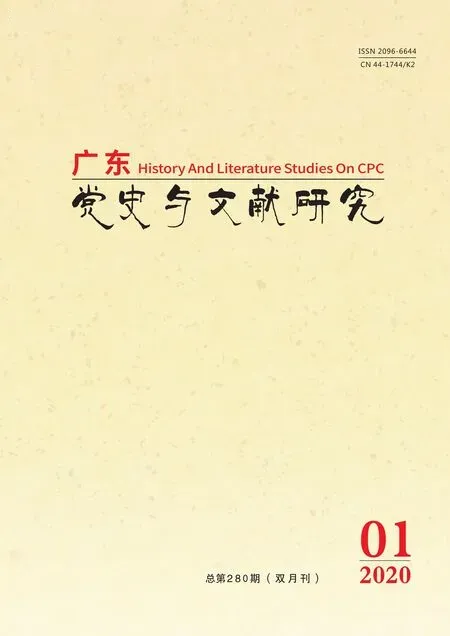再评罗章龙与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岳 梅 李永春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对于分析、认识“左”倾错误,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在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完全改造中央,又在与王明的斗争中陷入宗派主义,甚至组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等组织,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学界在罗章龙与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关注的是罗章龙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组织策划“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等组织、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的过程,批判其“同党闹分裂”的行为,及其错误的政治路线,①主要研究成果有:《罗章龙分裂活动考》,《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安子敬:《关于罗章龙问题的若干史料和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5期;卢庆洪、刘晓鸣:《罗章龙策划中共首次分裂始末》,《广东党史》2008年第3期;曹仲彬:《罗章龙谈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9年第9期;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而往往忽略了对其在党的三次“左”倾错误期间的思想脉络的梳理,从而割裂了其思想演变的整体过程。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罗章龙思想的三次转变为主线,研究中共三次“左”倾错误发生期间罗章龙的思想主张,客观评价其与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探析罗章龙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思想转变轨迹,更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罗章龙,还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共“左”倾错误产生和纠正的历程,总结历史教训。
一、从执行到批判“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来不及深入思考和研究,尤其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导致后来出现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当时党内普遍存在“左”的思想和情绪,作为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在思想上也出现“左”的因素,在行动上执行了盲动主义政策。
罗章龙在1928年2月著文指出,国民革命之后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时期,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在客观上已经走到直接革命的时期,而敌人的统治极端动摇,军阀间的混战、政治经济的危机,即将总爆发。因此,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兵士组织赤色先锋队,准备武装总暴动以根本消灭敌人的统治营垒,“自己动手推翻资产阶级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统治,自己动手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①真君:《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的意义》,《布尔塞维克》第19期,1928年2月27日。罗章龙在1930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仍在宣传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暴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城市是敌人经济命脉所在,革命运动“只有在中心城市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领导之下,才能尽量适度的发展”。②《庆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劳动》周刊第34期,1930年6月7日。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思想,实际上忽视了其他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在武装斗争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定了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罗章龙接受和宣传过“左”倾错误的许多观点,提出了革命“不断高涨”的主张,号召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总暴动。
不仅如此,罗章龙也执行了中共中央“左”的错误政策。受中央指派,罗章龙参与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他和毛泽东等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制定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计划。按照部署,罗章龙留在长沙后方,等部队打下萍乡、浏阳、平江、醴陵,围攻长沙时,来个城市暴动,里应外合,占领长沙。然而,秋收起义失败了。此后,罗章龙继续坚持城市武装暴动政策,在工人中宣传城市工人暴动和革命高潮论。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中共在城市和农村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害,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除毛泽东、罗章龙等人领导的湖南秋收暴动以外,上海、江苏、天津、湖北、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暴动无不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及时发现“左”倾盲动错误,罗章龙也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积极参与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斗争。
一是批评盲动主义的主要危害。罗章龙结合自身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经验指出:在湖南秋收起义以前,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将革命毁坏了,湖南“党的组织百分之九十是完全消灭了,工会组织除安源外没有一个群众的组织了。农民协会存在者也是极少数的”。然而,在机会主义还没有消除之时,中央又陷入“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完全没有注意到暴动的必要条件”,决定在湖南举行秋收暴动。在罗章龙看来,当时湖南党的组织、工农民众的组织脆弱不堪,暴动的主观条件远远不够,“除安源尽力之所能及发动一千余工人群众,在粤汉铁路做一些破坏骚扰(炸铁路,毁车等)的工作以外,是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于是不得不迁就革命的布置,以求孤注一掷的胜利。这一次暴动的结果,除死伤四五百工人外(农民没有参加),昙花一现的失败了”。暴动失败以后,湖南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省委领导王一飞却提出“只要有一点力量,便尽量地运用他发动一个暴动”。在盲动主义的思想的指导下,湖南继续不断暴动,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将我们党少数团聚的力量完全毁坏,党的干部及工会的干部直到后来死亡净尽(只剩下极少数人逃生的)。另一方面,在农村暴动中形成失败主义,即大烧大杀主义,甚至将整个的城市(如永兴县)烧毁了”。可以说,在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影响下,“湖南党的组织和工农组织便完全崩溃了,几十万工农群众无代价都牺牲在党的错误政策领导之下了”。鉴于此,罗章龙要求肃清盲动主义的倾向,建立无产阶级意识的正确政策。③《第三十二号罗章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600~601页。
二是分析党内盲动主义出现的根源。第一,自中央到地方的机会主义没有完全肃清;第二,党的理论还不成熟,不了解革命的内容和性质,容易走到错误上去;第三,党组织脱离了群众,实行“畸形的中央集权制”,党员的群众意识很难反映到指导机关去。①《第三十二号罗章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601页。罗章龙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也要为盲动主义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是中共革命盲动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他“不惜用强迫命令方式,实行持续不断的暴动”,使得中国革命元气大伤,延缓了真正革命的来临。在罗米那兹的指导下,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进展是“不断高涨”,要求不断采取暴动的手段来革命,明知暴动胜利无望,仍然“为暴动而暴动”。②罗章龙:《参加中共六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因此,“以前过分夸张的乐观估量是错的,不问条件的直接行动为暴动而暴动的政策是更应该改正的。革命固然是向前发展,但是距一般成熟的条件还是远的”。要消除盲动主义倾向,就必须“重新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夺取成千成万的群众,主要的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注)的工人群众,在群众斗争的发展中去认识暴动政策,不要像盲动主义时代只一味的瞎干,傻干,毫无目的的糊(胡)干,弄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以至(致)于消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完全不组织暴动,而是积极领导乡村游击战争及群众自发的暴动,“因为只有这样长期的争斗,才能使未来的总暴动更加快实现”。③《第三十二号罗章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601页。
罗章龙从领导秋收起义的经历中感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较早发现和认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分析盲动主义错误出现的根源,这对于全党认识盲动主义错误、纠正盲目暴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罗章龙是在盲动主义造成重大损失之后才真正认识到其错误的,因而在挽救这种“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他对“左”倾错误的分析与研究也远远不够,他认识到了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但是没有有效地采取应对手段与方法。何况,罗章龙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来批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这意味着他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的认识只是感性层面上的,在其内心深处,基于中心城市暴动理论和革命高潮理论的“左”倾思想仍然存在。
二、从保留意见到全面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
中共六大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中共六大虽然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一些做法,却未从根本上克服“左”的错误。基于中心城市暴动理论和革命高潮理论的“左”倾思想逐渐滋长扩大,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在1930年3月20日至28日的全总特派员会议和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章龙与何孟雄、林育南、林育英、张昆弟、吴雨铭等人表达了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不同的意见,认为目前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暴动和同盟罢工的时机还不成熟”。④刘万能编著:《张昆弟年谱》(1894—193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但是,他们的意见被李立三指为“右倾”。据王明说,到7月的中央工作人员会议时,罗章龙没有表示反对意见,⑤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报告中也说罗章龙“在12月底以前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过任何斗争”。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摘录)(1931年2月22、23、25、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事实上,在中央整个工作方针都“左”的大背景下,罗章龙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不满,但是在共产国际的“七月指示”到达中国以前,他总的态度还是拥护的,并没有公开提出反对立三路线,而且他在这一时期宣传的革命理论,执行的革命策略,也是按照李立三和中央的精神来展开的。
罗章龙明明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政策,但还是宣传和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与李立三的强硬态度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央工委、全总与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以及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都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批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都遭到李立三的压制和打击,被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以至受到组织处理。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1l页。何孟雄被指为在七个根本问题上犯有“调和主义路线”。③《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罗迈同志在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1930年9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9—1934.8),1987年内部编印,第285页。李立三等还以“右倾机会主义者” “小组织者”等罪名,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给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尽管罗章龙觉察到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主要问题,但是在遭受批评后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甚至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支持“左”的做法。作为中央委员,他没有坚持原则,争取对党有利的革命方针策略,还参与决策了一系列“左”的决议,实际上成为“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因此,对于立三路线,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直到共产国际“七月指示”到达中共中央之后,罗章龙才开始公开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罗章龙发言批评向忠发、李立三的政策错误,认为他们从来不知正视革命利益,建议党的政策改弦更张,将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对此,瞿秋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工作中不应有第一位主义,如果把群众工作当作第一位,那么其他(意指武装暴动)工作就不是第一位了。罗章龙因此认定六届三中全会只是在原地踏步、打圈子,中央政策并没有挪动一步,认为“此会大可不开,决议有等于无”,进而在三中全会后联合全总党团、江苏省委,以及北方党与工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史文彬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要求筹备召开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清除“左”倾错误路线。⑤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下),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页。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来信严厉地批评李立三提出的政治路线,指出立三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⑥《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352、357页。据此,12月,罗章龙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召开中共七大,改造党的领导,解决党的路线问题。他也估计召开中共七大的阻力很大,于是退一步向共产国际提出召开紧急会议,并建议原有犯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不得参加紧急会议,而加入由各部门、各基层组织推选出来的“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积极分子”。他还要求完全废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重新通过正确决议案。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领导全总党团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革命”,而“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根本缺乏领导革命的能力与阶级的忠诚”,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召集紧急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各项问题”。他们还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引进“工人同志及群众组织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参加工作”。①《全总党团决议案——关于对中央九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1931年1月1日),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章龙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主要是在批评李立三“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观点,批评李立三不遵从共产国际指示的行为,以及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不彻底,而并不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认清“左”倾冒险主义在革命形势、革命路线、斗争策略等方面的根本性错误。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罗章龙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的决议和指示来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而共产国际本身的“左”倾错误贯穿在他的思想认识中,使他在革命高潮论、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总暴动等问题上仍然是“左”倾的。这也使得罗章龙即使尖锐地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也始终无法触及“左”倾错误的根本,代表不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三、在与王明的党内斗争中从发展宗派到分裂中央
在罗章龙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时,王明等人也在反对立三路线。他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李立三犯了右倾的错误,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与决议,也都宣称“拥护国际路线”,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的要求。但是,随着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并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他们的思想发生分化,在行动上开始对立起来。
米夫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声称他已报告共产国际,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就否定了罗章龙等人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王明转而服从米夫,认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于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中央问题上,王明与罗章龙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见,进而发展成为不同的意见集团,形成党内派别。“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摘录)(1931年2月22、23、25、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117页。
米夫声称,王明把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旧领导的优秀部分)聚集和团结在自己周围,而罗章龙等人“把党内所有最坏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到一起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实际上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斗争”。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摘录)(1931年2月22、23、25、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118页。于是,他执意把王明、博古等人推向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其中王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在罗章龙看来,米夫扶植王明、博古的做法,是在为他们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准备条件。“如果召开紧急会议,则由于王明、博古根本未参加过国内革命斗争,在会议上必然全局失败,难逞私图,所以米夫一伙坚决反对紧急会议,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破坏紧急会议”。④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59页。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当时如果召开紧急会议,罗章龙一派人很可能取得中央领导权;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在指定列席人员的问题上拥有更多的操作权和自主权,从而使原中央领导人的多数留任,并保证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层,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班子。①于吉楠:《关于罗章龙分裂活动的几个问题》,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这意味着,罗章龙与王明之间的派别斗争由思想领域开始转向了政治领域。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四中全会突然召开,会期又只有四五个小时,这种“闪击式”会议使得罗章龙等人没有机会准备和在会上提出他们的意见,而且在会上他们的企图又全部落空,这使得罗章龙等人极为愤慨。在罗章龙看来,王明“书本理论比我们读得多一点,但他在莫斯科学习,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一点都没有”,而且“王明上台到处受到反对,上海、武汉都反对四中全会,苏区的毛泽东也反对四中全会,大家都认为王明上台,会比立三还左,中国革命将遭到更大损失”。②唐韵超:《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依据这些理由,罗章龙联合王克全、林育南、李求实、唐韵超等人提出“为召集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四中全会,阻止王明上台,却一步步走上了公开分裂党的道路。
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二天,罗章龙、何孟雄、王克全等人召开秘密会议,会后联名写信给米夫,重申六届四中全会为非法,会议一切决议及违法选举应宣布无效。请米夫转达共产国际,采纳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分歧。
米夫收到上述信件后,不得不为争取罗章龙等人的同意做最后努力。他通过秘书找到罗章龙,提出举行一场座谈会,出席一方为给共产国际写联名信的二十六人,一方为共产国际代表三人,双方真诚坦率地交换意见。罗章龙等人经过讨论,决定同意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会议。
然而,这场被罗章龙称为“花园会议”的座谈会最终不欢而散,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激化了党内矛盾。罗章龙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在花园会议上,米夫宣布开除包括他在内的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党籍,他们才走上了另组“中央”的道路。笔者认为,口头宣布与正式发文是具有根本差别的。即便当时米夫在口头上做出了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威胁,但毕竟没有发布正式文件,并不能算真正的开除党籍,这不足以构成罗章龙等人另组“中央”的原因。而且,在正式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以前,中共中央也为争取他们做出过许多努力,而罗章龙等人却表示要“争百年是非”。③罗章龙:《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下),九歌书坊、浏水工作室2015年版,第851页。
花园会议以后,罗章龙等人进一步从事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米夫、王明路线的活动。他们召集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举行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 (1)反对四中全会的人,以‘全总’党团名义包括不了怎么办?(2)怎样使上海以外党的组织和国际方面知道我们反四中全会是什么理由?”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发表反对四中全会的宣言。但是据陈郁所言,当天的会议“仅原则上通过这两件事情举办而已”,并没有具体的名单和宣言的内容。④《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会后成立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干事会”。接着,发表《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大纲彻底否定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执行铁的纪律”,给予“严重的处罚”。大纲还抨击四中全会“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提出要“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推翻六届四中全会全部决议,召开紧急会议。⑤《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1931年 1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466~469页。这一大纲是“非委”的行动纲领,实际上是企图重新组织中央领导机关。
随后,“非委”成立起来,设执行委员22人、候补委员15人,组成中央机构,“继续领导革命工作”。①罗章龙:《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下),第604页。“这实际上就是另立中央,也就是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②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4 辑,第 97~98 页。“非委”成立之后,为争取获得共产国际和中共各方的支持,分别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和各苏区,并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指责米夫践踏党章,认为六届四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称左派,诬人为右,全党人人自危,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一切革命斗争工作陷于停顿状态”,③罗章龙:《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下),第 797~799页。要求广泛开展反米夫、王明路线及其御用组织临时中央的斗争,筹备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根本解决一切有关中国革命政策上的重大问题。这表明,罗章龙、史文彬等人全面开始了与临时中央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并已制定较为完善的方案来推行反对临时中央的方针。
从罗章龙开始全面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从事推行分裂中共的活动起,中共中央就采取了多种方式来争取罗章龙。夏曦、柯庆施、周恩来先后找罗章龙、林育南、王克全等人,希望他们尽快承认错误,回到党的工作中来。但是,罗章龙态度强硬,表示必“争百年是非”。④罗章龙:《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下),第851页。在此情况下,王明领导展开了“反右倾”斗争,对罗章龙等分裂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和严厉的组织制裁:凡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团、工会等各种组织一律实行改组与重建;对凡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员一律进行无情打击,立即停止发放生活费,开除党籍。
1931年1月15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指斥郭妙根、何孟雄、彭泽湘等人利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实际上批评了罗章龙等人。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1931年1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第22~24页。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人在全总党团的职务。⑥《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 476~477 页。21日和25日,中央点名斥责罗章龙借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之名,“作分裂党捣乱党的活动”。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1931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3页。26日,王明起草《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扩大的四中全会总结与上海党的目前工作决议案》,指责罗章龙等人“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帜之下进行反国际路线的言论和行动”,“应该受到全党的指斥和反对”。⑧《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扩大的四中全会总结与上海党的目前工作决议案》(1931年1月26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9—1934.8),第371~372页。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宣布“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⑨《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4~68页。此后,中共中央还陆续通过多项决议,开除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宏经等人的党籍。
为了彻底瓦解罗章龙派和“非委”,2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六届四中全会经过,并报告罗章龙“公然进行反国际及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的情况。⑩《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514页。向忠发也向共产国际陈述了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以及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斗争始末。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罗章龙等人组织右派小组织,分裂党的活动的情形,并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王明激烈的“反右倾”斗争下,“非委”工作难以展开与延续。各地“非委”的活动陆续遭到失败,一些参加活动的人开始转变态度,纷纷宣布脱离“非委”,陆续开始揭发罗章龙等人的“右派”活动。在此情况下,罗章龙情绪低落,很少参加“非委”的活动,于1931年冬被开除出“非委”。张金保接任“非委”主席。但是,“‘非常委员会’既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孤立无援,又反对不了王明,肩负不起领导全国人民的任务,困难重重,无法维持”,1932年2月13日,张金保召集全体会议,决定解散“非委”,把它的基层组织全部交给了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①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至此,罗章龙另组“中央”的活动彻底失败。
四、余论
罗章龙在中共党内纠正“左”倾错误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他在领导秋收暴动的实践中较早发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加以批评和纠正,为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较早地察觉到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并试图与李立三做斗争,有利于其他党员干部及时发现与批评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左”倾错误同样贯穿在罗章龙的思想认识之中,他在革命高潮论、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总暴动等问题上,一直是“左”倾的。他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作右倾来反对,把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 “左”倾冒险主义的批评说成是犯了右倾“调和路线”的错误,不仅没有达到反“左”的效果,反而越反越“左”。
罗章龙另立“中央”的行为,对中共中央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罗章龙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全总的主要领导人,在跟随他参加“非委”活动的人中,有相当多是全总党团的党员干部和工人运动的活动骨干。为了尽快解决这一事件,减少负面影响,使党的工作快速步入正轨,中共中央将这一部分人开除出党,但也因此失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先锋,多年来建立的工人运动队伍和工会组织系统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导致中共在工人中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都一蹶不振。
此外,罗章龙表达反对王明上台、反对米夫控制六届四中全会的意见是正当的。但是,他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借反对立三路线与王明争夺中央领导权,甚至不惜采用分裂的办法,组织“非委”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种不顾大局和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罗章龙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却又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原则,违背了党员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给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罗章龙另组“中央”的行为,必然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斥责,得不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最终必然要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