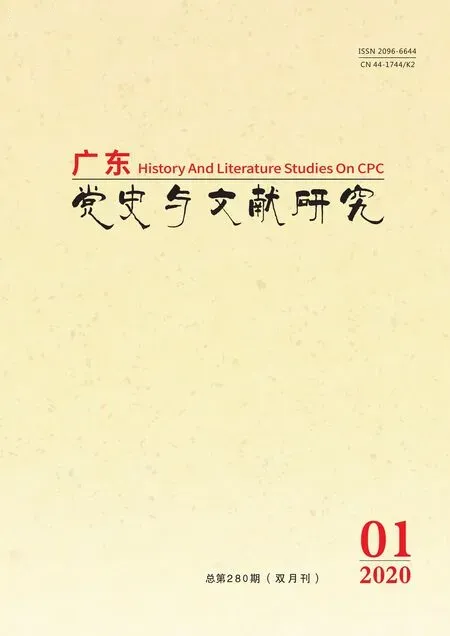彭述之宣传思想再认识
——以《向导》为中心的考察
周鹏飞 单 越
彭述之是中共四大选举的党内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的五位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部长)。他从1924年9月在《向导》写稿始,至1927年4月离开《向导》主编位置止,先后在《向导》上发表各类政论文章73篇,其中1925年10月至1927年4月担任主编期间共撰文44篇。彭述之在主编《向导》期间,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在关注国内时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唤醒和发动群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较系统的宣传思想,有些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但目前学界对此尚很少挖掘研究,亟需弥补。①相关研究成果仅见周鹏飞:《论彭述之的爱国民主思想》,《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李永春、岳梅:《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再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3期;傅小平:《彭述之国民革命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等。不能认为彭述之有所谓“托派”问题,就不挖掘、研究、利用其宣传思想的有益成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向导》为中心,考察彭述之的宣传思想,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背景与条件
彭述之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和宣传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宣传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环境、共产国际的指导及编辑《向导》的实践,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时代环境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使得促进民族觉醒、推动民族解放事业成为有识之士必然的历史使命。近代以来,地主阶级有志之士推行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士大夫知识阶层主推戊戌变法,唤起知识阶层的觉醒,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民族觉醒提升到共和的高度,新文化运动使劳苦大众进入人们视野,五四运动使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成为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当时中共自身建设不够成熟,在宣传对象、宣传力量、宣传经费、宣传内容、宣传方式与手段等方面存在重重困难。为了开创中共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彭述之等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进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探索。
(二)进步报刊的感召
彭述之青年时就十分关注国家前途命运。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是读报,1912年在长沙读书时,学校露天墙壁每天贴有大量报纸,他从这些报纸中了解很多新鲜事件。1918年,同乡罗云庆从安徽寄给他《时报》《申报》等刊物,彭述之系统了解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随后他密切跟踪巴黎和会进展情况和五四运动情况。1919年7月,彭忠泽等带给他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刊和整套《每周评论》。彭述之特别喜欢《每周评论》中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很有震撼力。彭述之对《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等内容非常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冲破传统习俗、反对妇女贞操观、文言文转白话文等观点对他影响很大。通过阅读这些报刊,彭述之深刻感受到报刊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力量,在唤醒发动民众运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共产国际的指导
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的有关指示,是彭述之宣传思想的来源之一。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宣传的党性原则,包括:“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还要斥责其帮凶;党一切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刊、出版机构都应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的党的政策”。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3页。共产国际三大提出“到群众中去”的行动口号,号召共产党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把大多数群众的思想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加以具体化。共产国际四大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总纲领》特别说明:“首先就表明要支持他们创办以本国语言出版的出版物和机关报;第二是要使党的政治机关报成为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集体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第三是资助中共中央创办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并且使《向导》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组织广大群众实践党的纲领、口号的舆论工具。”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同时共产国际强调《向导》宣传的内容要切合中国实情,要依据马列主义理论,面向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进行持之以恒的宣传,掀起革命大高潮。在《向导》编辑队伍方面,共产国际要求必须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派遣马林等代表来华参加编辑工作。在党报的宣传管理和组织纪律方面,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执行。192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要设宣传鼓动部等基本部门。
彭述之在莫斯科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掌握了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宣传的有关规定,深刻认识到党的宣传工作必须贯彻党的意志,具有极其严肃的组织性、纪律性。在宣传对象问题上,要求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比如理论研究时期宣传对象应该倾向于知识分子;但随着革命向纵深发展,为了扩大和巩固群众基础,则需要重点面向工农群众。郑超麟回忆,“彭述之书读得多,好读理论”。③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陈碧兰认为彭述之“在旅莫支部作过很好的贡献,曾为他们作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报告,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④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代序)》,《彭述之选集》第一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 年版,第3页。彭述之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五大等重要会议,聆听了列宁等领袖人物的报告和演讲。从1921年至1924年三年之间,彭述之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逐步锻炼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的素养。彭述之还研究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思想与政策,考察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办报办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报刊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据郑超麟回忆,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会按期收到党内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在回国前,彭述之“就已经打算回国占领党内宣传阵地”。①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5页。
(四)编辑《向导》的实践
1924年8月彭述之回国,中共中央指定彭述之等人组成宣传临时班子,集中精力编辑《向导》。9月3日彭述之在《向导》发表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据陈碧兰回忆:“我认识彭述之是在1925年,但我认识他的思想早在认识他本人之前。我还在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时,就从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上读到他的文章”,“他将义和团运动定性为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驳斥了所谓“拳匪之乱”和“野蛮排外”等传统观念,胡适称“这是推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观念,这是翻案了”。②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代序)》,《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1~2页。由此可见彭述之这篇文章的思想性和影响力。
1925年中共四大上,彭述之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五位委员之一,随后就中央宣传工作提出建议:要按时出版党的刊物;要担任对革命积极分子的训练任务;要担任对更广大公众的宣传工作;在日常任务内还包括有系统地收集不可或缺的资料,以便同志们在面对某些现实问题或总体性的政治问题以及写作论文时能及时在场作参考。③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录》下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0页。中央接受这些建议,并指定其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从1925年10月至1927年4月担任《向导》主编期间,他共撰文44篇,刊登在《向导》头版头条的有近20篇,这些文章密切关注中共对时局的主张,极力宣传中共的中心工作。彭述之编辑《向导》,在宣传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其宣传思想最重要的源头。
二、内容与特征
《向导》将革命行动与革命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彭述之在此宣传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宣传思想。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彭述之认为中共的宣传工作、教育方针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明确要在党内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要使《向导》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宣传阵地。他在主编《向导》期间,发表瞿秋白撰写的文章,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能够准确地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之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起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强大的革命中枢,而实现打倒资本帝国主义”,④瞿秋白:《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51期(1926年5月1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26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⑤瞿秋白:《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51期(1926年5月1日),第1428页。
一方面,《向导》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动。1924年11月《向导》刊发文章,指出暴动成功必须依赖三个条件:一是先进的阶级和政党;二是民众革命潮流高涨;三是暴动必须在革命历史的转弯点进行。这篇文章中还提到真正革命之军需就是物质和精神,指出必须制定适合的党纲草案,“和平给民众、土地给农民、取缔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恶”。⑥郑超麟:《马克思主义与暴动》,《向导》(影印本)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753页。
另一方面,《向导》积极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彭述之策划《向导》刊发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共发表《列宁与中国》《列宁不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等专题文章。彭述之成为《向导》主编之后,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密切联系群众,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要收集各种材料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特别关注国民革命理论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翻译。
(二)坚持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彭述之认为中共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应该发行刊物、出版书籍,造成思想影响,使党报真正成为“全党的思想教育机关”,正确阐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要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党报还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主张进行批评斗争。①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录》下卷,第10页。中共四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指出,针对一些党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不满和误解党的政策的言论,今后要加强组织和思想建设,以真正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②《对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页。针对陈公博在《广东群报》和《珠江评论》公然偏袒陈炯明叛变的观点,与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政策相对抗的言行,《向导》公开批驳陈公博言论,认为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③记者:《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第771页。《向导》与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象作坚决斗争,不仅维护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发挥了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政治作用。
彭述之紧紧围绕《向导》的党性立场来撰写文章,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拥护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他通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百姓的各种迫害现状,揭露其凶残的阶级本质。同时他指出:“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实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就是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建设革命的国民政府,此外绝无他法。”④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的解释》,《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3期(1924年12月3日),第778页。
彭述之十分注重对工人阶级和群众组织的宣传,认为“只有军事行动,而无群众的宣传与组织,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⑤彭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694页。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推动和宣传党的思想路线,使无产阶级不断了解贫困根源,加速了革命觉醒,扩大了革命影响。维经斯基曾报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其对群众的效果确实在扩大。我们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尽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查封,但其印数已经超过3万份,而且还在许多地方翻印。例如,在北京,党的地区委员会每周翻印《向导》3000份”。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6页。可见,在彭述之等人的努力下,《向导》向工农群众广泛宣传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三)坚持独立批评的原则
彭述之把中共宣传的独立自由原则和党的组织独立性原则始终联系在一起,坚持《向导》编辑方针的独立性。《向导》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代表中央的态度,对外力争《向导》不受或少受国民党的牵制,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言行保持独立自主的批评态度。1924年9月起《向导》连续刊发了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和《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两篇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办报的精神,明确答复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贵会并非本报上级机关,本报言论方针,自有权限,绝不容贵会干涉。”⑦记者:《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第772页。
彭述之坚持《向导》的独立批评原则,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马林曾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①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这一主张显然违背了中共宣传工作独立批评的原则。但马林也曾鼓励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希望通过共产党员去引导国民党执行国民革命的相关政策。马林曾就国民运动问题严厉地批评国民党,他说:“我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维经斯基强调共产党保证“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来影响国民党,强调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要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主张为基础。他批评国民党没有利用当时的工人罢工、军阀枪杀工人和镇压学生等素材来进行宣传,吸引广大劳动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的斗争。所以共产国际五大强调,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必须保持彻底的独立性,批评了在联合战线中“左”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
(四)坚持中共言论出版自由
《向导》坚持中共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之解放之唯一关键。”③《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第766页。彭述之在《向导》第93期撰文,认为:“‘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这种对内政治上的解放,与以上对外的解放同等重要,如果此条不做到,人民终无发表政治主张之余地,国家将永为军阀官僚压迫人民、戕杀人民之工具。什么国民政府,国民会议,绝对是空话。”④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主张的解释》,《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3期(1924年12月3日),第778页。由此可以看出,彭述之高度重视中共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和主张。他指出北伐军应该发表对于北伐的政纲,在这个政纲中应该表明北伐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应具体规定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各种应有的自由权,应发布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以收拾将来的时局。⑤彭述之:《中国政局大变动之前日与民众之责任》,《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7期(1926年8月15日),第1674页。
《向导》坚持揭露帝国主义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钳制。瞿秋白在《向导》刊文指出:外国人的政府取缔印刷品,压迫租界内的言论自由,遭到书业商会、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公所等中国市民的公开反对,但工部局却回答“租界已经不是你们的领土,由不得你们,你们若不愿意,滚出去吧,亡国的上海人民”。⑥巨缘:《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外国人的政府》,《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61期(1924年6月16日),第490页。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言论出版没有自由,还需要向外国人(工部局)诉苦。“一切印刷品——报纸、传单、小册、小张招贴以及带有公众事项评论意见等报纸”,其“发行、主使印刷、主使发行者,均需要向工部局将姓名住址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他号召国人将争取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不懈努力。⑦双林:《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向导》(影印本)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9期(1925年4月5日),第1001页。《向导》办刊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上海总巡捕房得知《向导》周报在上海大学刊印发行,曾派探员到该校购买《向导》,搜查书报流通处,查询《向导》出售、印刷情形,并没收新出杂志和有关书籍。
《向导》坚持揭露国内军阀势力对民众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向导》刊发蔡和森的文章:“省宪不规定一些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但是十一月七日湖南市民对苏俄革命五周年纪念之集会被赵恒惕令军警解散”,“湖南人民要从赵恒惕这个军阀的伪自治中洗刷出来,便应猛烈的起来争自由呵!”①蔡和森:《赵恒惕与湖南自治》,《向导》(影印本)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第79页。1927年1月,彭述之撰文指出,巩固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的策略,并再次呼吁要有允许人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抗租的自由。②彭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阵线问题》,《向导》(影印本)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期(1927年1月27日),第1961页。可见彭述之和《向导》对民众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直在努力争取和贯彻执行的。
彭述之在《向导》工作期间,其宣传思想涉及面广、特点鲜明,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革命暴动;坚持中共宣传的党性与阶级性原则,使党报真正成为“全党的思想教育机关”,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凶残的阶级本质;贯彻中共宣传部门独立批评的原则,阐明共产党独立办报的精神,展现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精神;高度重视中共的言论出版自由,揭露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势力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
三、作用与影响
彭述之在《向导》时期的宣传工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不仅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推进了中共理论宣传工作的探索和发展。
(一)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是宣传十月革命,鼓舞中国人民。彭述之非常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通过宣传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鼓舞国民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在《向导》一共发表了三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中,彭述之援引托洛茨基的经典设问开头,“谁是列宁?列宁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然后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俄国的意义,称“在十月革命里,不但八百万纯粹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得从俄罗斯资产阶级之统治底下解放出来,而俄罗斯之一万一千万农民和六千万弱小被压迫民族,也从这个革命里得到新的生命”。③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0期( 1924年11月7日),第746页。在彭述之看来,这就是十月革命之总成绩,就是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十月革命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之开端。他呼吁中国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起来!”,实质上是呼吁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在《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一文中,彭述之将十月革命喻为“将帝国主义之整个的铁网撕毁了一大块”。④彭述之:《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747页。他指出:在经济问题上,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而乡村经济则恢复得更快,工农业间“剪刀差”问题也得到解决。在政治问题上,从前比较混乱的民族问题在苏共十二大后已完全解决。而所谓的政治问题主要就剩下外交承认问题了。在外交上,苏俄逐渐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承认,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此外,苏俄国内工人农民逐步加入工会农会组织,共产党员数量增加,质量上不断提高,而同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末运”。在殖民地问题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纷纷觉悟,现在已经继续不断地起来反抗了。最后,彭述之探讨了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断言“苏俄之巩固与发展蒸蒸日上。资本主义经济绝没有复兴可能;资产阶级政治已到穷途末路”。⑤彭述之:《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747页。彭述之歌颂十月革命,以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困境反衬十月革命的辉煌,号召中国人民努力学习和仿效十月革命,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是宣传列宁主义,提出中国革命原则。彭述之主编《向导》期间,非常注重收录与列宁主义相关的文章。比如刊登陈独秀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的《列宁主义与国民革命》、郑超麟的《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等文,明显看出其宣传列宁主义的积极态度。彭述之还亲自撰文宣传列宁主义。彭述之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指出:“列宁主义不仅是解放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唯一武器。被帝国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民族只有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才可以解放出来。”彭述之分析当时的中国国情指出:第一,帝国主义极其野蛮地压迫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二,封建军阀最无人道的压迫中国人民;第三,资本家极其残忍的压迫中国工人。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矛盾冲突的焦点”,这些矛盾突出的“总和之表现便是现时‘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驳斥了所谓中国特殊国情不适合列宁主义的论点后提出:“中国的革命特别用得着列宁主义全部的理论和策略——从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认为只有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彭述之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的德谟克拉西,必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①彭述之:《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向导》(影印本)第五集,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第1948页。他号召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民族斗争,争取民族解放。
(二)扩大中共政治宣传的影响
彭述之强调宣传工作是中共的“生命线”,宣传工作必须围绕中共中心工作来进行。北京政变后,为了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向导》刊发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彭述之随后撰写《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主张之解释》一文,对中共政策主张进行解读:一是英日帝国主义有分裂中国的倾向,美帝国主义有实施道威斯计划共同管理中国的阴谋;二是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中国共产党赞成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成立预备会议筹备国民会议执行一切临时政权;三是中国共产党代表被压迫民族向国民会议提出几点要求。他解释“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实行彻底的国民革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建设革命的国民政府,此外无他法”。②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主张之解释》,《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3期(1924年12月3日),第778页。他特别强调民众最为需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
彭述之十分注重对群众的宣传。他认为革命是有一定步骤的,革命必须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才能够成功。他指出第一步是宣传,宣传使革命群众充分了解自身的痛苦、痛苦的来源以及解除痛苦的必要和方法。其实质就是要使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和真正的敌人,了解革命的必要及革命的方法。③彭述之:《我的北伐观》,《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第1722页。
首先要注重对工人的宣传。彭述之在总结“二七”失败的根本教训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与工人群众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组织还没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如果京汉各路的工人群众当时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真正的指导权,在京汉路作指导工作的人受到党的支配,那二七斗争的失败,绝不至于如此。”④彭述之:《目前政局与工人阶级》,《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94期(1924年12月10日),第788页。换句话说,彭述之认为那时中共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没有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党还没有完全掌控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所以要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力度。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工人相对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容易受到政府控制和帝国主义镇压等。另一方面,工人注重生产劳动,但轻视文化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导致工人文化素质较低,思想政治觉悟有待提高。这些分析都是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同时这种分析也进一步彰显了党的宣传工作的紧迫性,特别是对广大工人群众宣传的重要性。
其次要注重对农民的宣传。彭述之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要想国民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的力量。在阶级利益上农民与工人阶级最为接近,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与农民建立联盟,因此要大力宣传农民运动。彭述之指出水灾、旱灾和米荒是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从东三省到河南、陕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至四川,发生灾害,大量饥民饿死,导致平民抢米风潮,上海工人因米贴罢工,军阀借此封闭总工会,军阀不仅不参与救济,反而增加苛税,彭述之鼓励农民起来反抗。①彭述之:《军阀统治下的灾荒和米荒》,《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4期(1926年7月21日),第1627页。在湖南,城乡居民积极支持北伐,他们为革命军做向导,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截断铁路,阻止吴佩孚部队前进,有的为北伐军运输粮食、侦探敌情等。②葛特:《北伐声中之湖南》,《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2期(1926年7月14日),第1607页。对此,《向导》也予以大力宣传。192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共要取得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进行。”③《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7页。
再次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彭述之贯彻和运用共产国际的经验,“广泛利用学生党员,为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④《学生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21页。认为这是发挥知识分子宣传作用的一条好路子。知识分子不仅能够成为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人群众的桥梁,同样可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群众的纽带。通过知识青年在农村中演讲、散发传单等宣传手段,送政策到农村、到农民。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本身就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革命宣传,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的影响。如发掘乡村教师组织联合会,使乡村学校成为中共思想传播阵地和信息中心;在农村开展反抗地主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宣传中共对于农民的政策和纲领。
由于中共早期缺少宣传经验,宣传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忽略宣传对象的阶级差别和个体差异,导致中共的宣传内容不能与群众的思想接轨。比如有些人一搞宣传就只会讲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试想在农村采取这样的宣传方式,完全忽略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民对这些所谓的主义根本不懂,宣传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共中央在1926年《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⑤《农民运动决议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9页。有时为了方便工作,宣传者还须将自己的生活农民化。在宣传方法上,还要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等多种形式,目的就是为了把对农民的宣传搞上去。在彭述之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的宣传手段在不断地改进,创造了一些流行词汇,遴选了一些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美与热爱。有读者称《向导》“是暗黑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口号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⑥雅零:《读者之声》,《向导》(影印本)第三集,第104期(1925年2月28日),第872页。也有群众来信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替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革命道路”的唯一报纸,是“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①《读者之声》,《向导》(影印本)第一集,第34期(1923年1月1日),第258页。
(三)推动国民革命发展
一是推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在“二七”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彭述之策划《向导》“二七”专刊,刊发彭述之的《二·七斗争的意义与教训》、陈独秀的《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工人力量》、瞿秋白的《1923年的二·七与1925年的二·七》等三篇文章,评论、分析和声援这次斗争。彭述之认为1923年的“二七”斗争是中国革命无产阶级跨入历史舞台的伟大时刻;指出京汉铁路工人表现了中国年轻的无产阶级卓越的革命气质,预示了其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将成为世界革命洪流的一条支流。彭述之指出“二七”罢工失败的原因:第一是没有充分加强工会支部对下层群众的训练和组织,没有帮助他们排除不能自制的原始性的盲动,使他们在遭到镇压后失去了方向。第二是中国共产党还在形成阶段,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真正联系较少,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组织还没深入工人群众,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指导权。第三是没有看清吴佩孚军阀的真实面目,没有看清军阀与工人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②彭述之:《二·七斗争的意义与教训》,《向导》(影印本)第三集,第101期(1925年2月7日),第844页。彭述之对这一事件性质分析和革命认识是清晰的,对革命失败原因分析客观准确。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在战略方针问题上认识高度一致,这对全国工人运动来说是最好的福音,是最大的鼓舞,直接影响到上海小沙渡纱厂的联合罢工,这次罢工在组织上、纪律上,成为1925年4月青岛日本纱厂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导火索。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再次兴起,1926年6月就有一百零七次罢工,有七万人参加,在各生产部门,如纺织、铜业工人、船坞、港口、公用事业等均受到影响……7月初到16号,新的罢工潮触及四十个企业,即四万人。③施英:《四论上海罢工潮》,《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4期(1926年7月21日),第1632页。
二是揭露封建军阀真实面目。彭述之指出:“我们要趁此机会唤醒国民,外国帝国主义是怎样地贿买军阀,军阀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努力训练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军,准备将来之大举,此外无他。”④彭述之:《江浙战争与国民党》,《向导》(影印本)第二集,第84期(1924年9月24日),第680页。他在《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一文中,希望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进行国民革命。1926年1月14日彭述之在《向导》写道:“此次反奉唯一武力,本以国民军为中坚,而国民军的首领冯玉祥始终采取犹豫态度。而在行动上,冯玉祥始终只顾他个人的军事计划,始终按兵不动,以致失去很多机会。如果冯玉祥在郭军反戈之时,与国民军二三军一致行动,急速结束李景林,结束张宗昌,进而全力助郭,则奉张虽有日本帝国主义之帮助,亦未必幸免。至少郭松龄不至于一败如此。如郭松龄不败,则直系自不敢遽然与奉张妥协。而反奉战争,未尝不能达到最后目的。”⑤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的责任》,《向导》(影印本)第三集,第142期(1926年1月14日),第1288页。接下来彭述之又在《向导》上撰文,一方面主张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军,另一方面提醒要警惕国民军的某些军阀将领,因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有可能恢复正统军阀的面目,并特别提到冯玉祥、岳维峻是大野心家。这一预言在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下令对北京广大爱国群众的血腥枪杀惨案中得到了证实。彭述之表达了对国民军的极度疑虑,如果国民军被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消灭,中国的恐怖时代是必会到来的,中国的民众和广州政府必将受到重创。⑥彭述之:《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向导》(影印本)第三集,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第1363页。
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在帝国主义推动下,孙传芳个人野心膨胀,局势变幻。彭述之提醒全国民众密切关注孙传芳的态度,严密监视孙传芳的一举一动,做好军事应对准备,针对孙“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鬼话,希望孙二十四小时以内以事实答复国民军的条件。①彭述之:《政局变化中孙传芳的态度》,《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6期(1926年8月6日),第1657页。但孙传芳暗中调兵遣将,唐福山援助叶开鑫,周荫人将其队伍调入江西,王普将孟昭月的队伍调入江西,并且封闭浙江江苏的国民党党部等。彭述之指出,孙传芳枪杀五卅运动的刘华、砍杀拥护江苏农民利益的周水平、镇压上海总工会等暴行才是其军阀本质,号召江浙人民起来反抗孙传芳。②彭述之:《且问孙传芳的保境安民》,《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8期(1926年8月22日),第1688页。彭述之撰文揭露孙传芳希望借助军阀武力攻打国民革命军,排斥苏俄、铲除共产党以坐收渔翁之利的企图,提醒国民革命军的同志特别加以注意。③彭述之:《读了孙传芳致蒋介石书以后》,《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69期(1926年8月29日),第1712页。
三是指明革命前途、步骤和力量。为了廓清北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意义,避免主观上的夸张和轻视,彭述之适时发表《我们的北伐观》一文,指出革命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才有胜利的可能。第一是宣传,使群众认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革命的方法;第二是组织,必须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为战斗力量,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第三是武装暴动,以群众的武装解除压迫阶级的武装,夺取政权。④彭述之:《我的北伐观》,《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第1722页。随着北伐取得进一步胜利,彭述之分析当时中国政局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北伐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得靠民众的拥护、内部的团结和正确的政治主张,并在具体的军事策略上要取保守态度,在政治上则应采取积极的建设态度,从而为夺取北伐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他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停留在南方革命势力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层面,就不能够完全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应该是各阶级的革命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求解放。⑤彭述之:《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向导》(影印本)第四集,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第1737页。
总之,作为中共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彭述之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适合中国的,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革命道路理论、国民革命理论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因其自身的局限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客观来讲,彭述之过于夸大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天然性,从而使得运动中无产阶级忽视了领导权的主动性,在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途径问题上没有提出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因此并没有真正的掌握领导权。
彭述之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贡献,但在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右的错误,发出“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的责难,对农民革命的前景持否定态度。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观点,使得他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出现矛盾的认识,既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又不希望农民运动开展过于迅速以致失去控制。认为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会影响国共统一战线,尤其是北伐途中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彭述之竟然斥之为过火,拒绝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上发表。他不支持农民运动继续发展,认为这不利于革命的不断发展扩大。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矛盾认识,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这是彭述之又一明显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