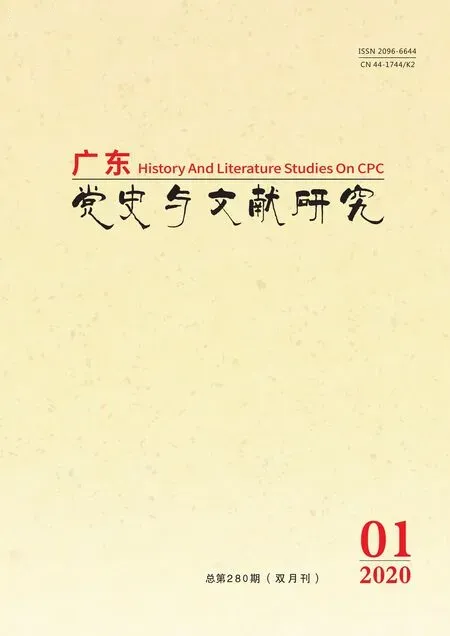毛泽东诠释《忆秦娥·娄山关》探析
王建国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对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极为喜爱,曾三次亲自加以诠释。本文就其中缘由和若干史实进行探讨。
一、注家误判引发毛泽东初次诠释
1957年1月,《忆秦娥·娄山关》作为毛泽东“旧体诗十八首”之一在《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旧体诗的刊发,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发了众多学者诠释毛泽东词作的热潮。由于刊发时尚未确定写作时间,注家差错频出。有鉴于此,1958年12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毛泽东写了如下说明:“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锋(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针对学者对写作时间的误判,毛泽东特地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天头上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9页。批注明确交代了写作时间——“过了岷山”之后,并且告诉读者其中的原因是“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即便取得了“娄山关大捷”,毛泽东的心情依旧是“沉郁的”。换言之,在当时情况下,即便取得了大胜,毛泽东依然没有心思去填词。等到“过了岷山”,红军摆脱了危险,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欣然执笔,追记娄山关之战,这才有了《忆秦娥·娄山关》。就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批注是毛泽东对《忆秦娥·娄山关》的首次诠释。
不知何故,直到1984年,有学者经过“考证”得出的结论却是:“该词作于(二月)二十七日,应该是无疑的了。”③蒋南华:《〈忆秦娥·娄山关〉词试析》,《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4期。时至今日,《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④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红军长征史》写道:“中央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其实,只要根据毛泽东1958年12月的批注,再查证毛泽东翻越岷山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断定:《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不应该早于1935年9月18日。
二、郭沫若误读引发毛泽东再次诠释
1962年4月22日,“突然像天外飞来似的,一份题为《词六首》作为征求意见用的铅印本寄到了编辑部”。收到毛泽东的《词六首》,《人民文学》编辑部成员十分兴奋,一致认为:“5月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词六首》必须在5月号刊物上发表。”对于发表毛泽东词作,《人民文学》十分慎重,“由于主席这六首词是在革命年代所作的伟大的‘诗史’,要去敦请郭沫若同志为《词六首》写一篇诠释性文章,好让一般读者更好地接受词中的教育”。①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1~822页。
受邀的郭沫若心潮澎湃,他认为:“主席是不轻易写诗词的,也不肯轻易发表。目前所发表的词六首和以前所发表的诗词二十一首,我们可以断然地说,正是革命的诗史。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语言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凝铸出来的。”②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就这样,他去中央档案馆查核革命史实,“在短短的三天中便洋洋洒洒写下一万三千余字长文,这便是后来与《词六首》同时发表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③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822页。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写道:“主席的诗词气魄雄浑而音调和谐,豪迈绝伦而平易可亲。人人爱读,处处弦颂。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④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需要指出的是,《忆秦娥·娄山关》本不属于诠释之列,只是郭沫若对它极为偏爱,且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人民文学》约请诠释《词六首》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心得与他人分享。
在明确“今年二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我曾经把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的同志们,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后,郭沫若这样诠释:“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⑤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不难看出,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诠释是相当细心的。他不但和广州诗歌座谈会上的专家探讨,而且还查阅了两种版本的《遵义府志》,认真核实从遵义到娄山关的距离——恰好是一天的路程,并据此推断《忆秦娥·娄山关》描述的是第一次夺取娄山关的情景。
接着,郭沫若写道:“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二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阙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⑥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郭沫若告诉读者:通过细心推敲,发现“西风”“雁叫”“霜晨”应该是秋天景色,自己便赶紧对诠释思路进行重新调整。
郭沫若接着写道:“‘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着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⑦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郭沫若之所以这样诠释,是因为在《忆秦娥·娄山关》发表前不久的1957年11月,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毫无疑问,郭沫若对“西风”的诠释非常符合时代的氛围。
郭沫若进而强调:“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接着,笔锋一转,写道:“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不)管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①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到此为止,郭沫若完成了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诠释。
不过,郭沫若意犹未尽,他说:“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例如屈原的《离骚》里面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或‘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所谓朝夕都不限于一天。”②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不难看出,郭沫若对自己的诠释颇为自得,因为他的诠释完全能够自圆其说。
郭沫若没能想到完全误读了《忆秦娥·娄山关》,更没想到他的误读还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第二次诠释。
三、毛泽东亲笔诠释
1962年5月9日,郭沫若致函毛泽东:“我应《人民文学》的需要,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因为《人民文学》要在十二日出版,今天才送了小样来,没有来得及先送给主席看看,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闻《人民日报》将转载,如主席能抽得出时间批阅一过,加以删正,万幸之至。”③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郭沫若完成诠释的时间是5月1日,不过,他并没有立即送毛泽东“删正”,而是等到清样已出、即将刊印的时候送交毛泽东。很显然,郭沫若自信毛泽东不会提出大的修改意见。出乎郭沫若意料之外,毛泽东亲自动笔对诠释稿进行修改。修改幅度之大,我们只能称之为: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名义对《忆秦娥·娄山关》进行亲笔诠释。
毛泽东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做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阙一次,第二阙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在明确指出写的就是一天的事情后,毛泽东接着重点强调:“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毛泽东明确告诉读者:《忆秦娥·娄山关》写的就是第二次攻打娄山关。针对郭沫若关于气候方面的疑问,毛泽东还颇具针对性地强调:“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在进行上述修改后,毛泽东这样总结:“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只要略加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基本上否定了郭沫若的诠释。
由于发现郭沫若的诠释不够理想,觉得自己“有说明的责任”,毛泽东于是对诠释稿进行彻底修改。而要进行彻底修改,必须对《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有深刻的记忆。如果像《词六首》那样“通忘记了”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85页。,修改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娄山关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仗,是四渡赤水期间的辉煌胜利,毛泽东自然难以忘怀。对“过了岷山”之后的创作激情,毛泽东时隔多年记忆犹新。在批注诠释中,毛泽东就对《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进行过介绍。此次亲笔诠释,毛泽东特别强调:“词是后来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97~98页。这实际上是对批注诠释的补充说明。细数毛泽东词作,描绘长征途中战斗的仅此一篇。从特地强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自以为颇为成功”来看,《忆秦娥·娄山关》的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对《忆秦娥·娄山关》亲笔诠释。
考诸史实,笔者发现毛泽东的亲笔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出入。如“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就存在差错。红军第一次占领娄山关的时间是1935年1月9日,遵义会议召开是1月15日—17日。换言之,红军占领娄山关在前,遵义会议召开在后。再如,“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是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开始于2月25日,攻取娄山关是26日。换言之,并非“一战攻克”。陈伯钧日记记载“25日,晨稍雨,即阴,大雾”“26日,阴”。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由此看来,红军向娄山关前进的时候不可能看到“霜晨月”。此外,夺取娄山关与攻占遵义城并不是同一天,战果也不是各消灭敌军一个师。据1935年3月2日《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我野战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克服桐梓,击溃守城黔敌两连,二十五(日)南下攻占娄山关,将黔敌杜旅两个团全部击溃,小部歼灭。二十七日乘胜直下遵义城,击溃王家烈部守城约六个团,消灭一部。复于二十八日击溃遵城之薛敌五十九、九十三两师。”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四、毛泽东亲笔诠释未能如期刊发
毛泽东对《忆秦娥·娄山关》的亲笔诠释居然没有发表,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如前所述,郭沫若在1962年5月9日才将清样送呈毛泽东。当毛泽东完成修改时,《人民文学》5月号已经出刊。据陈白尘回忆:“1962年5月12日……秘书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读了郭老的文章,其中有一句成语的解释想和郭老商榷一下,问刊物是否可以推迟出版……不仅《人民文学》刊物已经装车运出北京,同时转载《词六首》的北京各日报也已经上街了,我便向秘书同志说明具体情况,请他请示主席。几分钟后,主席的指示来了:‘既然北京各报都已出版,那就罢了,以后再说吧!’”所以,《人民文学》刊发的依旧是郭沫若的诠释稿,而不是毛泽东修改后的诠释稿。陈白尘满怀愧疚地写道:“这有如晴天霹雳,将我从狂欢中震醒!为什么郭老这篇文章没有等到主席过目就付印呢?对主席诗词如有丝毫误解之处,这种损失将用什么来弥补呢?而郭老的文章又是在我们催促之下匆匆赶成的,如有疏忽,其过在我,又何以面对郭老的盛情呢?”⑤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823~824页。陈白尘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是“有一句成语的解释想和郭老商榷一下”,而是对《忆秦娥·娄山关》进行了重新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陈白尘写道:“后来,感谢郭老,又写了《‘枯木朽株’解》和《‘温故而知新’》二文,对主席《词六首》中《渔家傲》一首的诠释做了澄清,才算稍稍弥补了我的过失。”⑥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824~825页。从向竺可桢求证娄山关的气候来看,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诠释。郭沫若既然两次纠正对《词六首》的诠释,为什么没有将毛泽东修改稿发表?除了毛泽东说过“以后再说吧”外,合理的解释是郭沫若可能对毛泽东的诠释有所保留。郭沫若有没有发现毛泽东诠释中的前述史实差错,目前已经无从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所强调的“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仍然存在明显疑问。因为云贵川下雪还是比较普遍的,并非“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出生于川南乐山的郭沫若对此自然非常清楚。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进一步向气象学家竺可桢求证。
竺可桢在1962年6月13日日记中写道:“接郭老函,讯问毛主席《忆秦娥·娄山关》词有西风烈,长空雁断(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是否阴历2月现象?……我查日记知1941年2月3日(到)达娄山关时见山顶有雪,1943年4月13日过娄山关遇雪,另一次未查明日期,过娄山关,山上雪、冰载途……可见2月间娄山关是有霜雪,而风向在1500米高度也应是西风或西南风的。去年到遵义,展览馆送我一本红军在贵州纪念刊,其中有夺取娄山关一段说明,红军夺取娄山关是在2月26日。”①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57—1965)Ⅳ,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638页。特地向竺可桢求证娄山关“阴历2月”的霜雪与风向,可见郭沫若对毛泽东亲笔诠释的重视程度。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当年阴历二月对应的阳历日期是3月15日至4月13日,这正是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时段。不难看出,郭沫若是怀疑毛泽东可能把阴历二月当作阳历2月进行写作了。不过,从竺可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娄山关即便在阴历二月也会下雪。郭沫若与竺可桢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竺可桢自然会在第一时间把查证结果告诉郭沫若。既然如此,郭沫若也就有理由认定毛泽东的修改稿的确存在“硬伤”。由此看来,郭沫若没有将毛泽东修改稿公开发表也就可以理解了。
1964年1月27日,在接见《毛泽东诗词》英译者时,毛泽东又这样诠释《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上下阙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这里北有大巴山,长江、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雁叫’、‘霜晨’,是写当时的景象。云贵地区就是这样,昆明更是四季如春。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长江,但是遇到强大阻力。为了甩开敌军,出敌不意,杀回马枪,红军又回头走,决心回遵义,重占遵义。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②参见卢洁:《解诗之难——从毛泽东为郭沫若修改〈忆秦娥·娄山关〉考证解读说起》,《秘书工作》2011年第5期。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口头诠释与亲笔诠释在角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分析山脉走向,进而分析山脉对气候的影响,这正是亲笔诠释所缺少的内容。毫无疑问,口头诠释是对亲笔诠释的补充论证,自然也是为了消除郭沫若诠释稿可能对英译者产生的误导。不过,口头诠释中“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说法很可能存在记忆的差错。
五、缺憾原本可以避免
其实,只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考证,完全可以对《忆秦娥·娄山关》进行较为准确的诠释。不知何故,擅长历史考据的郭沫若对词中景物的描写从气象学的角度进行推敲,却忽视了对娄山关之战史实进行深入考证。郭沫若知道中央红军两次攻占娄山关,却没弄清楚第一次攻取娄山关是智取,并未进行激烈的战斗。他查出遵义距离娄山关是70里,并由此推断“恰好是一天的路程”。可是,他并不知道红四团夺取娄山关是从板桥镇出发,凌晨发起突击,上午就解决了战斗。若能准确地弄清《忆秦娥·娄山关》并非描写第一次娄山关之战,郭沫若就很可能进行较为准确的诠释。
毫无疑问,弄清毛泽东经过娄山关的情况对于理解《忆秦娥·娄山关》肯定有所帮助。警卫班战士陈昌奉这样介绍毛泽东第二次经过娄山关,“主席是晚上到达桐梓的。而且一到住处马上就同周副主席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首长在开会……我们听到娄山关方向有枪炮声传来……东方发白了,主席和其他首长们才从房子里面走出来……十点多钟的样子,参谋处有位首长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要我们把主席唤醒了。只听他说:‘主席,部队已经进占了遵义,战斗全部解决了。’主席高兴地说:‘好嘛!那我们也走吧?’‘您再休息一会吧!’那位首长说。主席说:‘不,不!走,走!’”。①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164页。其实,毛泽东得知红军夺取遵义城的消息不应该是10点多钟。因为在早晨7点钟,林彪就已经报告:“遵义新老城于本28晨完全占领,缴获正在清查中。”②周朝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90页。很显然,毛泽东肯定在第一时间得知如此重要的消息。陈伯钧日记写道:“晨得报,我军已占领遵义新城。”③《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91页。既然陈伯钧“晨得报”,毛泽东得到消息就不可能是“十点多钟的样子”。
桐梓距离娄山关只有16.2公里,急行军每小时10公里,即使一般行军速度也不低于每小时5公里。即使按照5公里计算,3小时多一点也到达了娄山关。如果一接到占领遵义的消息就出发,上午10点多钟就应该到达娄山关。即使10点多钟出发,中午1点左右也应该到达娄山关。既然如此,“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说法就值得存疑。只可惜,陈昌奉没有记录毛泽东第二次登上娄山关时的天气。要弄清当天的天气,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28日,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陈伯钧日记写道:“行军。由桐梓经红花园、娄山关、板桥、四都站到大桥,约80里。”看来陈伯钧这一天的行程与毛泽东相同。陈伯钧记载了当天的天气:“阴,微晴。”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91页。在阴天上午或中午,显然不可能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美景。
值得注意的是,陈昌奉这样记载了毛泽东第一次翻越娄山关所看到的景色:“一月的黔北高原虽不象北方那样寒冷……但是一登上山顶,那风象突然从山林里窜出的猛兽呼啸着冲我们扑过来……我们赶上去,见主席已坐在一座石碑旁的岩石上……主席站起来望着两头狭窄的山谷……转身往我们刚刚上来的山路望去。此时,只见西南方向的天空正弥漫着一抹红霞,把娄山关苍茫群峰,滔滔林海就染成一片透红似血的颜色。”⑥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156~157页。大概就是这种景色,引发了毛泽东“西风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感慨。经查证,毛泽东这次过娄山关是1935年1月22日。同日经过娄山关的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日晴,夜微雨”,⑦《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81页。可见,陈昌奉关于景色的描绘应该是可信的。由此推断,《忆秦娥·娄山关》写的是第二次娄山关之战,景色却很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跨越娄山关时所见。
由此看来,如果查证有关史料并询问相关人员,郭沫若就完全可能对《忆秦娥·娄山关》进行较为准确的诠释。毛泽东实在太忙,他不可能有时间去找出有关文献进行仔细查证,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找陈昌奉、陈伯钧等知情者一一进行核实。否则,毛泽东的诠释就不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
六、余论
毛泽东三次诠释《忆秦娥·娄山关》,都是为了纠正学术界的误读。可是,《忆秦娥·娄山关》毕竟是文学作品,又是时隔半年之后的追记,而毛泽东诠释时距离《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几近三十年之久,且仅凭记忆进行诠释,这就难免会造成与历史事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出入。不过,这倒印证了毛泽东的感慨“解诗之难,由此可见”。此外,笔者发现《忆秦娥·娄山关》很明显地借鉴了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⑧唐圭璋、钟振振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毫无疑问,这也是诠释《忆秦娥·娄山关》应该考虑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毛泽东的亲笔诠释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这份珍贵的文献最终为世人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