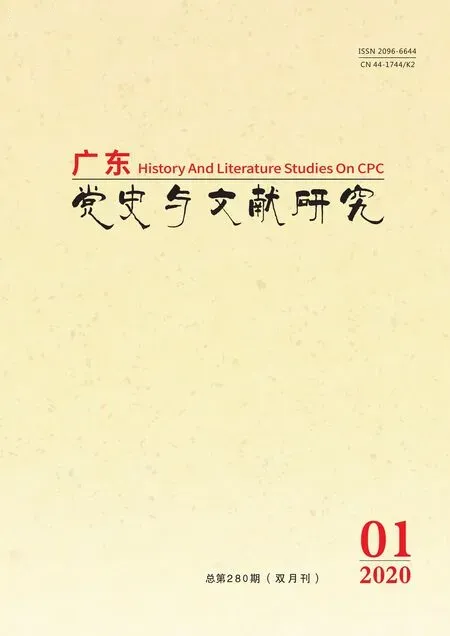身体史视角下的长征:动员、纪律与献身革命
伍小涛
长征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对于长征,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和专著,①据笔者对中国知网粗略统计,发表的论文18000多篇,出版的专著600多部。重要的著作有《红军长征记》(上、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重要的文章有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孙果达:《四渡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唐双宁:《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等。大都是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涉及对长征人物、会议、事件、长征原因、经验、影响、意义和长征精神的研究,但鲜少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解读。作为“在这个肉体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都是以人类身体为渠道表现出来的”②〔美〕布莱恩·特纳著,马海良、赵国新译:《身体与社会》,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的场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把身体当作研究热点。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充分表现革命意志的英雄史诗,自然是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内容。
正如台湾学者黄金麟指出:“以身体作为线索来讨论革命的历史,不但会牵涉到历史的‘应然’与‘实然’辩称,也会将讨论的焦点从旧有的政权更迭与阶级斗争,转移到人的处境与身体的遭遇。这个观看焦点的转移也许不会改写一场革命的全部历史,却能让我们以新的、更贴近‘人’的角度来观看历史的发展,体认客观现实如何限制或激发人的欲想与抗拒,使历史形成预计或为预计的结果。”③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长征,从革命身体的视角来探讨,自然让我们可以对革命的本质与目的、手段与方式,有特定的了解。
一、“革命身体”的提出
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中,尚未见“革命身体”这个专门词语,但把革命与身体联系起来的现象比比皆是。李大钊针对袁世凯对大众身体的摧残,号召大众起来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他说:“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苟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吾人对之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①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因“西崽乐志华。被他的洋主人疑他偷了八百块洋钱,引到虹口巡捕房毒打,‘吃雪茄’,‘浇冷水’,打得血肉横飞,死去三次;结果,英帝国主义者,用种种手段注销两个施刑探捕——加布德和鲍尔庆的罪名,以顾全‘两人在租界内文明和威信’”,②《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页。蔡和森号召大众起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
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蔡和森,都把身体当作革命的媒介和目的。在他们看来,因身体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摧残,必须起来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解放和自由。这一点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向导〉发刊词——本报宣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国的革命就是身体摆脱奴役和压迫的革命。
同时,因为革命必须把身体置之度外,所以,一些仁人志士在革命与身体的二难选择中,选择了革命。方志敏在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④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更是表达了革命者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壮烈情怀。毛泽东指出:面对反革命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这说明在中共早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身体”已经形成。
长征,不但是中共“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9~150页。而且是革命与身体的完美结合。中共长征史,就是一部革命身体史。
二、身体的动员:革命理想的诉求
按照黄金麟的解释,身体动员指的是,人力的调动和利用。这些动员牵涉到的不只是物质和金钱的征集,还牵涉到动员所要解放的人,这也是共产党要有各种方式来征集、调动和政治使用的人。⑦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第 159 页。长征的身体动员沿着两条路径进行。
一方面,维持现有的红军身体。长征初期,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红军内部弥漫着一种对错误军事指挥路线不满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的情绪,逃跑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近来落队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对我之行军计划有莫大障碍”,⑧《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一路上有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搞革命真不容易,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⑨萧锋编:《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这些现象,影响整个红军身体的力量。因此,必须进行身体的动员,“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⑩《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325~326页。基于以上情况,首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地打胜仗。必须根据党中央与中央军委告红军战士书,在连队中利用行军休息时间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讨论,特别要巩固在云、贵、川边境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①《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其次,红军高级领导人深入各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云“在接着的十多天内,同十三师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周恩来“详细询问部队的行军、思想情况,如各连多少人,掉队多少,战士们有些什么想法,生活怎样,粮食好不好解决,等等。……他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要一切为着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排除一切困难。同时,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和前途,要提高信心和勇气,不要被困难吓倒”。③萧锋编:《长征日记》,第11~12页。最后,在红军中下层干部中积极进行身体政治动员。萧锋《长征日记》中写道:“1934年12月5日,二营文书小胡对我说:总支书,你们心里有个底吗?自离开中央苏区,我们整天走,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走到贵州,快走了半个中国了,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我告诉他说,中国那么大,帝国主义分割统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哪里好粉碎国民党‘围剿’,就到哪里去。要相信党和红军的力量,相信红军总会找到创造苏区的地方的。”④萧锋编:《长征日记》,第28页。
对于身体的革命政治动员,产生了一种献身革命的身体政治图式,“上午八时,我们几个团领导决定,马上边行军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全团指战员,并立即启程前进。战士们响亮地喊着‘一切为着革命’的口号,感到浑身是劲,行军速度加快了好多”。⑤萧锋编:《长征日记》,第12页。
另一方面,扩充红军的身体。黄金麟在研究中把扩红作为苏维埃身体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他说:“我们看到身体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正成为苏维埃政权努力想要掌握的对象。”⑥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第 323 页。红军长征时期,承继了这一身体技术。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扩充红军的力量成为长征的一项重要任务。1935年2月16日,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指出:“千百万云贵川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饥寒交迫的中间过着非人生活,拯救他们,发动与组织他们斗争,号召他们起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神圣任务。”⑦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1921—1949)》第1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由于长征中红军所经过的区域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动员少数民族大众参加红军是扩红的主要方式之一。长征初期,《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强调:“批评他们的动摇犹豫与不坚决,推动更左的革命分子走上领导岗位,团结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并从他们中间吸收共产党员。”红军到达川康藏边后,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指出:“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并特别注意与培养自己的干部。”⑧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245页。
经过中共政治部门的宣传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努力,“这两天整训、扩红成绩不小。一营通讯班长陈忠梅兼任营青年干事,工作搞得很活跃,他们扩红三十三名,筹得现洋五千元。七连扩红筹款成绩突出。六连扩红十五名。团部特派员小袁跟三营突击队扩红四十二人。全团扩红三百余人,筹款两万多元”。⑨萧锋编:《长征日记》,第14页。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相反还补充了新鲜血液。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途中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入了红军。⑩伍小涛:《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历程与经验启示》,《桂海论丛》2013年第3期,第102页。
按照现代身体政治学者的观点,身体“作为或多或少可资利用之间,或多或少易于进行利润可观的投资之间,有或多或少生存前景的事物之间,死亡与疾病之间和或多或少受到有用的训练的能力之间的新的易变因素的载体出现”。①〔英〕克里斯·希林著、李康译:《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身体的政治动员,实质上是人力的政治动员。红军长征时期的扩红,实际上是红军身体生产的扩充。通过身体政治动员,红军身体生产的数量,即人口的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而且身体生产的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三、身体的规训:革命纪律的体现
福柯曾指出:“身体规训是一种使人体变得更顺从、更有用的机制、技术和关系。在‘做什么’和‘怎么做’方面,身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即纪律,被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②〔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6页。红军长征途中的身体规训,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进行:
第一,通过决议、布告、条例、训令规训身体。红军长征途中,发布了许多这方面的文件。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出发前夕,《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强调:“在敌人残酷摧残下,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内一些干部中的不坚定分子,可以而且必然产生一些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人持久战争中最危险的倾向……党应该经过许多解释与教育工作,把全党同志和睦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坚持的有毅力的为着中央路线而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和历史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③转引自刘志新:《长征中党的纪律建设》,《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部队的士气,士气的低落就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因此,长征时的身体规训首先是士气的提升,其次是纪律对身体的规训。红军长征途中发布了许多纪律训令,如《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坚决地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④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也指出:“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军的纪律,必须采取严厉办法以保障纪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红军的纪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极大发扬党员间与红色指战员间阶级友爱与服从纪律的精神。”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537页。
通过这些决议、布告、训令对身体的规训,还获取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身体认同,“往时红军所至,人多闻风避走,兹入康后,风趣与传闻者大异。所至保护寺院,尊重习俗,爱惜人命,避免摩擦。诺那解至后,尚给以名义,令向民众演讲。疾病为之医治。死,准其化尸存灰。韩大载请负灰往招李抱冰,亦竟遣之。德格头人夏克刀登被俘,予以优待,冀能为用。故一度混乱后,旋即相安”。⑥任乃强: 《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从而澄清了国民党对红军身体行为的污蔑,“赤匪每遇一乡一镇即召集人民开会,伪称不扰人民,及至人民集聚,乃完全屠戮,钱粮劫掠一空,及退,复将房舍火化”。⑦《赤匪蹂躏下的泸定》,《康藏前锋》1934年第1卷第9期。
第二,通过支部会议规训身体。1927年9月永新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后,支部会议对红军身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红军长征这段艰难的岁月中,支部会议能起到规训红军身体、凝聚红军力量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针对连队支部不健全的情况,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连队组织工作命令》,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地发扬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①《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同时,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针对长征中红军纪律有所松懈的现象下令:“部队中思想散漫、军纪风纪松懈等严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工作没有跟上,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政治工作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地在战斗环境中进行。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弱点,要迅速地有大的转变。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从胜利的战斗中创建新苏区的任务已迫切地摆在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面前。”②《李富春选集》,第19页。根据总政治部指令和李富春的指示,各连队进行了纪律检查,“部队准备打回遵义去,师政首长要我同金行生同志跟一团行动。检查一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部队的反映,以及连队支部的活动情况。晨七时出发,经大圆子、青杠坡、上溪沟到桐梓城宿营,行程九十里。这次回桐梓,精神面貌大不一样,抗日救国的目的更明确了”。③萧锋编:《长征日记》,第56页。红军战士方国安也回忆道:“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④高中华:《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学习时报》2016年10月11日。这充分表明,连队支部在红军身体规训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没有连队支部这个坚强组织堡垒对身体的规训,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第三,通过正反事例来规训身体。红军长征途中涌现了许多遵守纪律的事例。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经过贵州黄平时,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⑤《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红一军团也是如此,据杨成武回忆:“毛儿盖是藏族同胞聚居的中心地区,虽有几百户人家,但要供应我们红军的粮食,还是极端困难的。虽然地里已有不少成熟了的金黄色的青稞,但我们谁也不去动一粒。通过各种宣传、解释工作,我们终于请回了藏民兄弟,并征得他们同意,用银圆购买了一部分青稞麦。可是这也不够吃啊,我们只好用它掺和点野菜充饥。”⑥《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红军是执行革命纪律的模范,同时也表明,红军对身体规训很有成效。但是也有个别违背纪律的现象。《红星报》报道:“红三军团某部上士袁子何,率领运输员一人,故意逗留后面,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自由行动,有意破坏红军纪律。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⑦王强、奉鼎哲、吴满意:《从红军长征铁的纪律看法治中国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3页。通过正反案例,红军身体行为有了一定的标杆和正确的规范。
总之,通过上述身体规训,红军身体产生了质的飞跃。红军再也不是以前的封建旧式军队,而是具有革命理想和革命纪律的无产阶级新式军队。
四、身体的疾病:革命意志的考验
疾病是身体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按照福柯的观点,人们通过疾病,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⑧〔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长征时期由于长途跋涉和物质资料的贫乏,红军干部和战士得病的很多。
长征初期,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好,体虚血亏,王稼祥伤口大化脓。进入雪山、草地后,由于气候条件的恶劣,红军干部和战士患病的越来越多。据《耿飚回忆录》载:“川藏边的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常常于六月雪、七月冰雹。一年四季都是冬。属高寒山区,再加高山反应、氧气稀薄、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过往行人易染消化不良、拉肚子、头昏眼花、胸闷气短、脸上脱皮、嘴唇干裂、头部浮肿、四肢无力。”①《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一些患病严重的红军战士,由于抵御不了寒冷的侵袭,就静静地躺在雪山上了。《童小鹏日记》记载:“此路前面曾有部队过,因冷甚,故因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②《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部队过草地时,“正值春末夏初。气候转热,地气上升,天空终日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由于当地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大部分同志还未来得及换装,部队中病号增加,有的同志突然发病,喘息一阵后就牺牲了。开始,大家以为是中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呼吸了‘瘴气’所致”,③《耿飚回忆录》,第292~293页。“晚上气候,更令人难受。不是刮风落雾,就是雨雾漫天。地面到处是湿漉漉的,部队绝大部分没有帐篷,无处栖身,就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肩靠肩地睡一会儿。好些人带在身边换洗的衣服,在白天行军时被暴雨淋湿了,不能换,冻得无法入睡”,④《罗荣桓传》编写组:《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红军在草地上患病的人太多了。一则长征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当看到这些瘦弱的战友们倒下了,心里更难过,我跑前跑后,招呼医生和卫生员拼命抢救。没有药品,医务人员只好推拿按摩,进行急救,有的病号按摩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我们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滴在战友的遗体上。草地不能久留,只好忍痛告别战友的遗体,扶着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拉一步走一步,顽强地向前迈进。”⑤萧锋编:《长征日记》,第124页。
这些疾病及境遇,对红军干部和战士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意志考验。耿飚当时正患疟疾,病情严重,是留在后方养病还是继续长征?耿飚选择了跟部队出发。他说:“什么疟原虫,见鬼了,我反正不能留在后方。”在他坚强的意志下,“‘疟原虫’顿时无影无踪了”。⑥《耿飚回忆录》,第199、207页。周恩来在过草地前夕,“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六十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361页。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终于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而那些因为身体严重疾病无法前进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也坦然面对疾病带来的身体死亡,“炮连神炮手吴民选班长,江西于都县人,十四岁参加红军。他肚胀、脚肿,两天没吃东西了,走不动,战友们轮流背,背不动,就用木架当滑车拉。这样坚持了两天,实在不行了,快咽气时他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总支书,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快跟着毛主席打出去。有时间给我家去封信,告诉我妈妈、哥哥、姐姐,叫他们好好活着,工农革命一定能胜利的”。⑧萧锋编:《长征日记》,第125页。
因此,身体疾病对于革命者来说,只是革命意志的一次考验。在考验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和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则资料是这样描绘红军长征的:“尽管唇舌被冻得发僵,说起话来不大利索,浑身无力,唱的声音不大,可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歌声像篝火,漫延在无垠的茫茫草地;歌声像火焰,升腾跳跃,温暖着人们的心。在歌声中,红军战士送走了寒夜,迎来了东方的曙光;在歌声中,英雄的部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①《星火燎原·丛书之二》,战士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透过红军的身体疾病,看到的不是老弱病残的身体,而是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身体,如肖华在《长征组歌》所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②《红色经典的记忆·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因此,从这一点来说,红军长征身体疾病史,就是一部红军革命身体史。
五、身体的伤亡:革命精神的升华
在身体社会学里,伤亡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吉登斯认为:“死亡代表着这样一个关节:在一个以成功实现控制为取向的世界上,人的控制宣告终结。通过采取以关注身体的生活规则为核心的生活风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自我认同,这样的能力必然以控制为旨归。”③〔英〕克里斯·希林著,李康译:《身体与社会理论》,第175页。红军长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首先,就伤残来说,长征时期的伤员人数较多。在长征回忆录和长征日记里,不时出现伤员的感人事例。“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⑤《杨成武回忆录》,第158页。“作为领导干部,我们也知道,非战斗减员,特别是伤病员在这样的情况和环境里离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同志都不愿意,不忍心,也舍不得丢下那些曾经生死与共,而今为革命受伤成疾的战友。大家互相团结关心,共同前进,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⑥《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二营六连排长何玉香负重伤,宁死也不愿留下。三营通讯班长刘挺楷,腿被打伤,要把他留下,他打天翻地不干,说爬着也要跟红军走”。⑦萧锋编:《长征日记》,第20页。长征时期有许多伤残的独臂将军和独腿将军,如贺炳炎、晏福生、余秋里、彭绍辉等,他们虽然身体残疾了,但革命的精神一直未变。红军身体因伤致残,成为革命的象征资本,红军身体资本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
其次,就死亡来说,它不只是身体的自然消亡,还是革命精神的呈现。红军长征时一、二、四方面军共20多万人,到达陕北时只有5万多人。除了少数逃跑外,大多数战死在战场上。其中在湘江战役、爬雪山、过草地中红军死亡最多。单湘江战役一役中央红军就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这大量的死亡中,革命身体凸显。
在1934年11月30日的觉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师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聂荣臻回忆道:“敌人从三面向我尖峰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峰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⑧《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而红五军团第34师和第6师在灌阳阻击敌人。红军伤亡惨重,师长陈树湘率余部200多人突围,遭保安团袭击,陈树湘受重伤被捕,他乘敌人不注意,从腹部伤口处把肠子掏出,扯断肠子英勇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易荡平、陈树湘成为革命身体的标杆。
而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许多无名战士,更是革命身体的最好表征。黄克诚在回忆录这样描述爬沙窝山:“每爬行一步,都相当吃力。谁要是放任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尽量不停留下来。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没能坚持住,倒在路旁。一停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倒在一旁的人,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死亡相继,尸体比比皆是,惨不忍睹。”①《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 234~235页。王平回忆过草地时一名红军小战士的死亡情景:“我们团部的一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他就在地上爬。他说,我多爬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离中国革命胜利近一步。我真想把他带出草地,眼看他走不动了,我赶紧把他往马上扶,结果一扶他就倒在我怀里咽气。我心里难过极了。红十一团过草地时,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两百人。”②《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这些倒在路旁的无名尸体,就是一座座矗立的革命身体的丰碑。
六、结论
张闻天曾经指出:“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在奋斗的中间,在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贡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③《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红军长征中所呈现出来的革命身体,是一首伟大的生命之歌。
第一,长征是一首精神性身体之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心是合一的。孟子指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④《孟子·公孙丑上》。精神与身体紧密结合在一起。长征精神与长征革命身体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上有飞机的轰炸,下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正是因为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的支撑,才顺利完成战略转移,红军才战胜了身体的疾病,克服了身体的伤痛,挑战了身体的极限。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曾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⑤〔美〕埃得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页。长征是革命身体与革命精神完美的结合。长征叙事,从某一角度上来说,就是革命身体的叙事。
第二,长征是一首政治身体之歌。按照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世界身体、政治身体、社会身体、消费身体和医疗身体五种身体形态中,政治身体指的是“身体一直在为我们提供着一种语言和政治文本,籍此我们能对抗和反击那些支配我们的非人性因素的力量”。⑥〔美〕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长征是革命政治身体的产物。
长征途中,一直存在着政治路线之争。长征初期,“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⑦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在“左”倾错误政治路线下,红军迎来的是身体的大量伤亡和身心的沮丧和迷茫。遵义会议后执行了正确路线,红军身体伤亡不仅减少,而且身体也得到了愉悦。据资料记载,黄克诚听完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对党在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长期以来紧缩的心情开始松弛下来”。①《黄克诚回忆录》(上),第234~235页。正如刘伯承指出:“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左’ 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②《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页。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战胜错误的政治路线的结果。从身体政治的视角来说,红军长征是一首革命政治身体之歌。它不但开启了身体政治的革命叙事,而且是中国革命身体的重要成分,“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③《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8页。
第三,长征是一首社会身体之歌。根据约翰·奥尼尔的解释,社会身体指的是在我们的身体中,“存在着一种社会的体现逻辑(embodied logic)或一种社会构成成分的体现逻辑,这一逻辑构成了内在于公共生活的深层交往结构”。④〔美〕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第40页。长征中的红军将士的身体,不只是自然性的身体,还是社会性的身体。它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的产物。
无论是19世纪末西学东渐后提出的“身体改造”,还是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身体解放”,其相似点都是为了打造一种“新人”的身体。红军长征时的身体承继了这一发展趋势,而且完美地打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任何时代的革命身体。这种身体,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它的阶级性。长征中红军将士的一言一行无不透露着他们是无产阶级的身体,而非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身体。二是它的革命性。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不抛头颅、洒热血。据统计,红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有10万多人,其中有400多名是营以上干部。⑤徐生文:《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红网,2019年9月6日。几乎每前进300米就有一位红军将士倒下,红军长征之路,是由红军鲜血和生命铸成之路。黄克诚所描写的“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尸体一路不断,后边的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⑥《黄克诚回忆录》(上),第236页。便是革命身体之歌的写照。
总之,长征的革命身体,既表现为革命的精神性身体,又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性身体,还表现为革命的社会性身体,是多种身体形态的综合。这种综合奠定了革命身体的基础,为以后革命身体的张扬提供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