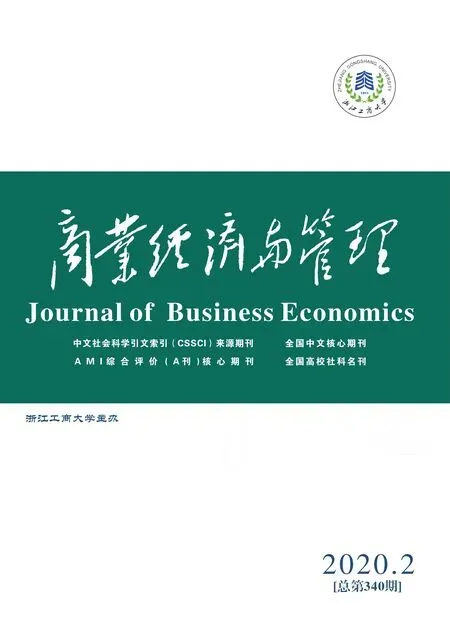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创新现状、辩证价值与未来发展
曹祖毅,贾慧英
(1.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2.武汉纺织大学 管理学院,武汉 430200)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
一、引 言
在各种学科领域中,理论为掌握学科知识以及了解其中的重要关系奠定了基础[1]。理论是管理研究的重中之重[2],不仅可以描述与解释管理现象[3],简化对管理实践的认识[4-5],还可以进行预测[5-6]。理论甚至成为学术领域的“流通货币”[7],好的理论本身就具有实用性[8]。科学系统激励着学者不断做出新的知识贡献,而理论构建在一个完整学科的发展、演化和变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11]。管理学作为一个面向管理实践的特殊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构建与检验是这个系统的核心[12],所以已有众多学者认为,理论创新已经成为管理学科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而核心理论体系的创立是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13]。为此,公认的管理学顶级期刊及其审稿专家大都重视文章的理论贡献水平[14],无论是对理论的新颖性还是连续性[15]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甚至一些著名管理学期刊的审稿人经常以理论贡献不足为由拒绝一些优秀稿源,即使这些探究运用了非常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提出并解决了重要的问题,或是发现了重要的管理规律,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制度顺从几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则。为了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继西方顶级期刊如AMR、AMJ、ASQ(1)AMR是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的缩写,AMJ是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缩写,ASQ是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缩写;下同。等纷纷专门召开研讨会之后,国内管理学优秀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也纷至沓来,希望抓住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力求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如“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管理世界》杂志合作主办,创建于2007年,旨在探索与提炼中国特色管理理论;2019年该论坛的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理论构建”。“管理学在中国”与“中国·实践·管理”(3)“管理学在中国”与“中国·实践·管理”学术会议均由《管理学报》杂志主办,前者于2008年开始,至2019年已召开12届;后者于2010年开始,至2019年已召开10届。二者都非常重视本土管理理论的创新。系列学术会议等。不难得知,在现阶段,期刊、学者、评审人均深谙理论价值对于学科发展乃至科学贡献的重要性,而关注理论创新已然成为国内外管理研究的一种主流趋势。
鉴于理论的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替代的地位[16-17],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数十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必须直面的话题[18-25],不仅攸关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18,26],而且关系着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合法地位,甚至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宏微观管理模式的选择。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管理学在中国逐渐取得合法性的基本要求、主要特征与重要标志[26-28]。对此议题,众多管理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与关注,或强调经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或重视理论成长的内生与外生环境,或从不同的子学科与领域进行比较,或基于纵向的演变视角进行总结[27,29-33]。虽然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与参考价值,但是主要存在以下遗憾:一是缺少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开发(exploitation)与理论探索(exploration)进行系统与全面的考察;二是缺少对相关的理论价值进行辩证性的反思,尤其是对其消极作用缺少思考;三是缺少基于具体的解释逻辑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未来创新路线进行提炼。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基于对理论价值的辩证性思考,试图从开发式与探索式创新的视角[16,17,23,34]出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现状并进一步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本文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创造性地从管理理论的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二者不同程度组合所得到的四个象限(分别是“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的“故事”讲、中西融合与探寻实证规律),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不同层面的回顾与反思,在与现有文献进行学术对话的同时,也指出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四个象限的逻辑关系以及各自的特征,本文阐述了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如果过于追求开发或探索——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主流价值取向——可能会带来的优势与挑战,以及如果不强调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而言所蕴含的重大历史机遇;最后,在对现状进行梳理与对理论价值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必要张力的思想,围绕四个象限的知识创造目的及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崭新的理论命题并构建了相应的发展模型。本研究议题的开展既是总结与提炼管理学科的中国特质的重要使命所驱[35],又应该是每一位中国本土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管理理论的内生与外生创新,还是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交互影响与互相促进[36],抑或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复杂与动态关系[28,37-42],均体现为理论对于管理学科发展与演变的引领与决定作用,故本文必然为洞察管理学在中国过去与未来的科学演进提供重要的价值参考。
本文首先交代了立论的基础与研究目的,并澄清主要的创新点;其次,基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维度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创新现状进行回顾,并从理论的辩证价值出发,梳理与考察四个理论创新象限各自的知识创造特征、存在的挑战以及逻辑与现实基础;再次,基于必要的张力思想,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最后,对相关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的展望。
二、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空间与现状

图1 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空间
理论构建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不仅通过对现有范式的拓展来衡量,还通过对传统世界观的挑战和对变革学科自身概念的更加多样化的轨迹来衡量[9]。管理理论的探索强调新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而管理理论的开发强调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应用与完善[43-44]。因为前者体现学者对理论知识新颖性的重视,后者体现学者对理论知识连续性的强调,二者均是促进管理理论科学成长与获取合法化的重要前提[15],所以本文主要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维度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回顾。一方面,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可以“从距离理论最远”到“距离理论最近”[45];另一方面,学者对新理论的探索也是一个连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20,46]。因此,本文认为,无论是理论开发还是理论探索,均可以区分为“高”与“底”两种不同的层次,故可以从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四个象限——进行考察,如图1所示:
(一) 第I象限:“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随着学术共同体越来越追求与重视理论贡献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价值[42],理论创新的第I象限主要对现有理论——主要是西方——的开发、利用与完善,即“接着西方管理学讲”[47],侧重于在中国背景下运用与完善其他情境中发展出的管理理论,而正在兴起的中国经济环境为验证与完善通用性的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22,48]。因此,这一象限的一个中心议题便是关注管理理论与管理情境的复杂与动态关系[17,49],基本假设是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理论不具有情境专有性,其目的是增加现有管理理论的普适性,从而“借鉴旨在改良”[19]。
在现有的学术制度压力下,这条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的研究方式主导了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17],大部分的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在有限的情境中使用已有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概念[50],而且管理学者比较擅长于增加情境调节变量或者改变现有的理论联系[16]。尤其是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主流的权威管理学期刊——如《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纷纷效仿西方主流的理论范式[42],第I象限顾名思义,已经成为国内外管理学者开展中国管理研究的首要选择,而且学者对其憧憬似乎有增无减,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一象限获得越来越广阔的传播渠道与逐渐强化的合法地位。
然而,质疑与反思的精神是“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产生的前提[47,51-52],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从辨证的视角开始对这一象限进行担忧与反思,或认为虽然可以基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来解释新情境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与问题,但是却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这种理论创新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地方性问题的新解释[19];或认为这一象限缺乏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哲学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舶来理论情境假设的适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管理现象的有限或者是错误的理解[17];或认为如果长此以往,管理学者注定要在科学严谨性(rigor)与实践相关性(relevance)之间有所取舍,这会妨碍对新知识的发现与探索[34]。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其他的理论创新途径。
(二) 第II象限:接着中国的“故事”讲
第II象限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给出解释,强调针对中国的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管理理论[17,49]。这一象限的基本假设是文化具有特殊性和理论具有情境专有性,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53]的演变与变迁,使得那些旨在使用西方的舶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实践的研究议题和套路,可能不适合理解中国的管理与组织[48],因此需要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或者基于转型时期独特的管理实践来构建与创新本土管理理论,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科的世界话语权。从理论创新的现状来看,这一象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47]。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逐渐显露光芒;随着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呼声之高涨[54-56],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不断被国内外管理学者所挖掘,用以构建本土的管理理论。据此,已经有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诞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如和谐管理理论、C理论、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和合管理、道本管理等。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挖掘并不是国内管理期刊的特权,一些相关的优秀成果同样也出现在西方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期刊上(如AMJ、OS等),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管理学主流群体的认同,这些理论成果有关系理论[57]、儒家思想[58]、人情理论[59]等。
二是“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47]。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从管理实践中构建管理理论一直都是管理研究中永恒的时代主题。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部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持续重视,中国管理学学术共同体、本土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期刊也纷纷加入时代的主流,主动成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管理理论构建的弄潮儿,相关的理论成果如“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60]“领先之道”[61]等因此得以涌现。与此同时,为了扎根于中国特殊的管理实践从而构建本土的管理理论与模型,国内的管理学权威与核心期刊也纷纷开设了案例研究专栏,甚至召开专门针对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的主题会议——这些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探索与构建管理理论的重要举措,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然而,从科学共同体学术对话的视角来看[62],无论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还是“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47],目前第II象限的学术成果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其在世界主流的管理学社群中的合法性与认可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一理论创新象限对提高中国管理研究的世界话语权似乎依然任重道远,其学术潜力尚需管理学者进一步深度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挖掘方面,虽然2000年以来本土逐渐诞生了一些崭新的管理理论与模型,而且有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认同,但是现有情况表明,即使对新理论的验证、复制与检验是理论发展与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63-64],国内学者似乎缺少对本土管理理论与思想进行检验与验证的信心,导致并未对其进行有效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近现代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虽然理论的组成要素包括概念(what)、概念之间的联系(how)、解释逻辑(why)和适用边界(who、where和when),而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解释逻辑[14,65],但是2006年之后,本土管理学者构建与探索管理理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案例研究,似乎很少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解释逻辑。同样,这些诞生于本土的理论模型在被提出后,也似乎很少有研究进一步对其检验、复制与完善。
从图1所构建的分类法来看,无论是对理论开发的追逐还是对理论探索的强调,二者应该不能代表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所有空间,而且一些有代表性且有影响力的其他空间确实存在,比如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相结合[22]、实证规律探寻[66]等。因此,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还应该包括同时强调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知识创造空间以及既不重视理论开发也不强调理论探索的较低程度理论研究或非理论研究(atheoretical research)[67]。
(三) 第III象限:中西融合
随着近年来中西方文化更多的交流与学术对话[21]以及学者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更多的关注[68-69],东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整合备受重视[55],如文化双融思想[70-71]因受到不同情境与分析层次的文化观念启迪而得以实现平衡和超越,(4)除了AMR在2014年39卷第2期和2015年40卷第1期的发表与对话外,文化双融得到管理学届广泛认可的一些证明有:陈明哲(Chen,2014)一文在2015年的SSCI数据库中曾被列为“高被引论文”,即根据对应领域和出版年中的高引用阈值,到当年七月/八月为止,其被引次数已将其归入最优秀的1%之列;陈明哲[74-75]、Chen[76]等均基于文化双融思想,同时又推进其合法性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从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每届的举办来看——第一届(2013,清华大学)、第二届(2014,华中科技大学)、第三届(2015,南开大学)、第四届(2016,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第五届(2017,吉林大学)、第六届(2018,西北工业大学)与第七届(2019,上海财经大学)——文化双融思想一直是CMSW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与实践影响力。既涉及中西方理论的融合,又涉及中西方不同情境元素的互动与超越,甚至强调不同文化与情境的矛盾与辨证关系。对此,Leung,Morris、Leung、Ames和Lickel以及Li也提供了重要支持[22,72-73]。
因此,第III象限强调在对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开发与利用时,同时也进行本土新的管理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甚至是实现中西管理思想的整合与动态互动,是对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同时重视。无论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解释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同时对这些理论进行完善,从而增强现有理论的普适性,还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特殊的管理实践来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其背后的文化背景逻辑都是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探索新理论与完善已有理论、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抉择与比较。相对于第I象限与第II象限而言,第III象限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共同追求以及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在横向与纵向的整合。一方面,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有效融合,可以促进中西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理论融合的方法可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22];另一方面,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动态互动可以充分体现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普遍性二者的动态影响:文化特殊性研究可以通过提供新观点来修正和扩展文化普遍性理论;文化普遍性研究可以突出在某一特定文化中被文化特殊性研究者错过的重要理论构念和过程。随着研究的积累,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理论通过不断交流和相互刺激得以完善,进而出现理论整合和普遍性理论的形成[22]。基于其特殊的价值以及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这一象限目前已经开始被国内外众多管理学者所重视,一些优秀的管理研究成果也已经出现在中西方重要的管理学期刊杂志上。目前,第III象限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纷纷做出尝试。
然而,由于第III象限既关注开发现有理论,又同时强调探索新理论,往往要求管理学者对中西方现有的理论与思想要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尤其是需要理解中西方管理思想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情境逻辑。在现阶段,管理学者开展中西文化与理论的整合研究还处于起步与尝试阶段,目前比较擅长在西方现有管理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等方法尝试构建本土管理框架或模型,但是这些新的框架与模型能否经得起实践考验,以及是否能被学术群体广泛接受,还有待未来进一步验证。
不可否认,理论对于学者认识管理实践的价值不可低估。理论满足了人类对现实进行归类和理解的需求[4],学者对开发现有理论、探索新理论以及对二者的同时强调,自然成为管理学获得话语权与合法性的有效途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认可现阶段管理理论在知识创造、学科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已有学者开始对之质疑并认为学术群体对理论创新的过度强调已经到了理论崇拜的境地[77-78],或认为应该暂停对理论创新的步伐,更加关注证据[79]与知识[80]的积累;或认为理论的过度创新导致了远离管理实践[81];或认为理论创新并不是最终目的,若是过度强调就会阻止对管理实践重要事实的发掘,妨碍科学研究理解目的的实现,还可能阻碍管理学科的发展[77]。甚至有学者直接批判理论对于科学新知的创造与传播的价值与作用,认为理论往往限制了可以提问的各种问题,影响可以接受的数据以及决定解释调查结果的方式,从而阻碍了学者对管理实践与现象的准确观察[23,78,82],因为“见如不见”(a way of seeing is a way of not seeing)[83],而且“在科学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学者越是接近理论的中心公理(central axioms),就越可能是不充分的”[84]。Walsham也认为,如果学者只从理论的视角进行窥探并以一种僵化的方式应用的话,就会扼杀知识探索的其他有效途径[85]。而Thomas和James观点可能更为发人深省:“理论——如果爱因斯坦是正确的话——不会诞生新的发现!”[86]。因此,以上三个象限并不成为中国管理学知识创造的全部空间。
(四) 第IV象限:探寻实证规律
结合图1的分类法并基于对理论价值的批判性思考,本文认为第IV象限——非理论研究或理论创新程度较低的管理研究——也可以、也应该成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议题,即使在现有的学术制度下国内外科学共同体对这一象限的认知与尝试较少。正如Miller所建议的一样[78],主流的学术期刊应该给予这种非主流的实证研究更大的比重,只要它们可以:①关注了管理实践的重要问题或检测到了有意义的规律,并至少对一些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②付出了大量的搜寻与努力成本从而探究到了原创性的新发现;③遵守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从而可被复制与检验。Miller认为这种非理论研究已在科学研究中诞生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Fleming突破现有理论范式束缚而对青霉素的发现,以及霍桑试验、Woodward对技术显著影响组织结构的重要发现等[78]。这一象限多起源于对管理实践最为逼真的观察与发现,在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性时拥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即实践相关性程度可能较高),并对后期的管理知识创造与传播产生了——甚至比很多理论——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对此,管理学者也可以从Helfat[87]找到类似的共鸣。Helfat认为这种非主流的研究因为深刻关注管理情境与实践,所以一定是与实践息息相关的,并通过菲利普斯曲线与经验曲线等案例进行了有效的阐述。与之类似,Hambrick鼓励管理学应该向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学习与借鉴,认为除了理论创新可以促进管理知识的贡献以外,报告与关注重要的管理实践现象也可以促进管理新知的有效发掘,并强调“事实必须先于理论”[77]。作为这一象限的有益尝试与例证,Tsang在探寻迷信有助于商业决策的实证规律时,发现迷信可以有效帮助中国管理者应对决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焦虑;虽然迷信经常被视为非理性并缺少现实根据,但是被试者依然相信其预测价值,并依赖迷信进行商业决策[66]。这一研究被Organization Studies称为创刊以来最有趣的研究,并得到了James March(5)关于Tsang对实证规律的探究过程,可参考Tsang[23]的相关论述。的盛赞[23]。类似的,Beamish和Bapujid的实证规律发现[88]在西方对政府与企业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本文认为第IV象限既不重视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与利用,也不重视对新理论的构建与探索,而是可以深刻描述与窥探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虽然这种研究的理论贡献程度很低,但却可以有效地贡献必要的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40]。其实,对于实践规律与事实的提炼与重视,还有类似于“雾霾调查报告”“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等较有影响力并对中国管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理论创新成果,只不过在中国管理研究逐渐向国际化接轨时,学术共同体与制度环境太过于重视理论创新的合法性而忽视了这种非以理论贡献为主要目的、但却可以深刻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管理实践并有效地揭示实践背后的重要规律类型的研究。近几年,随着西方顶级管理学期刊(如审稿要求理论贡献)、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会议对管理理论的重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纷纷效仿,再加上本土管理学者一直想摆脱中国管理研究被西方理论与议题所制掣的尴尬局面[18],直接导致了这一象限的话语权有日益衰减之趋。
综上所述,同时从不同程度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组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空间存在四种可行的空间,每一象限都有自己的知识创造特征、存在的挑战以及逻辑与现实基础。
三、不同象限之间的必要张力与未来的管理知识创造
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揭示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多元化理论创新空间以及在现阶段各自的特征与问题,更旨在基于必要的张力思想,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必要的张力最初被Kuhn用来描述自然科学中平衡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共同价值主张[89],随后被管理学者用以表示对理论范式的收敛与发散的同时追求[90-91],甚至被拓展至维护管理学理论与理论之间[92-93]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上[91,94-96]。因为带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40,97]只能对真实的管理实践与现象提供有限、简约与不完整的内部一致性解释[93],导致每一种理论都只是片面与相对精确的,所以平衡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必要张力有助于对比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及其各自的优势利弊,从而既有利于比较系统地认识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又有助于诞生管理新知与创新洞见[92-93]。与此同时,又因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本身是既竞争又促进的矛盾统一体[94],所以平衡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不仅可以强化各自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还有助于促进管理思想的诞生与理论的构建[95-96,98]。正是由于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必要张力思想在管理学中存在比较广泛的应用基础[28],以及管理学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在中国现阶段有所失衡,甚至还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还有可能继续加剧,故本文主要从上述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本文统称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视角进一步探寻未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造路径。
(一) 第I象限与第II象限:孰优孰劣?
第I象限强调文化普遍性以及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其遵循的价值主张与逻辑是“由外而内”,而第II象限强调文化特殊性以及对新理论的探索,其遵循的价值主张与逻辑是“由内而外”。本文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需要同时兼顾国际化与本土的视野,最终目的应该是创造与传播管理新知并为全球管理知识[17,25,68,99-100]做出贡献,因此需要同时兼顾并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管理学者不应该过于推崇其中的某一象限而忽视另一象限,因为在学者认为第II象限更有利于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以及管理实践构建本土理论时,第I象限也可以通过理论复制与检验来提高现有管理理论的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与预测能力[63],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解决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二者之间的互相竞争与互相依存既有利于解释中国复杂与多维——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管理实践,同时又可以增进不同的理论创新途径之间的情境对话与学术交流;既有助于揭示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不同价值逻辑与优势利弊,也更有利于为中国管理研究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用意并不在比较不同理论到底孰优孰劣,而在于强化每种理论的知识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于理论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理论之间的对话与学习,对于长久扮演‘先行者’角色的西方理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在过去的发展之中,西方理论甚少师法‘追随者’而极其缺乏自省的机会。”[20]由于二者是管理研究知识生产的不同过程,会互相限制与互相竞争[16],若过于重视第I象限除了会继续使管理学在中国的议题被西方所主导外,还可能会限制对中国情境与管理实践的深度挖掘与理解;如果过于强调第II象限的合法性,则可能会导致中国管理学者只关注中国管理情境和实践与西方的差异,而忽视了中西方管理实践中相同的部分[21],从而使得中国管理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产生显著的冲突[24]。因此,本文认为平衡第I象限与第II象限之间的必要张力体现了同时追求理论扩散与理论一致的“保持”[90],故提出:
命题1(P.1):强调理论开发的第I象限与强调理论探索的第II象限均是可行路径,虽然二者各有利弊,知识创造特征也不同,但均是重要与必要的;在学科整体上保持对二者的同时追求与平衡,从而形成必要的张力,既可以成为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崭新来源,又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从而促进管理学在中国的科学发展。
(二) 第I象限、第II象限还是第III象限?
因为第I象限的理论创新价值主张是从西方现有理论到中国情境的应用、开发与完善,而第II象限的理论创新价值主张是从中国本土的文化、实践与情境到新理论的构建与探索,所以二者或情境理论化,或理论情境化,主要遵循线性的理论创新逻辑与思维,因此缺少同时对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互动与整合的关注。相对而言,第III象限同时重视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强调中西方文化、理论与情境的同时互动、互释、整合甚至是超越,从而体现理论与情境的非线性整合价值,旨在既强化中西文化与情境的有效交流与对话,又有利于实现中西方理论与情境的整合与超越,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所以未来可有所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现实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希冀管理理论对动态的管理实践与组织提供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解释是不现实的,因此一个好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对管理实践进行有限的、相对精确的阐述,而不是试图覆盖现实的全部维度,否则势必会失去理论固有的简约性特征[93]。与此同时,管理学者的有限理性特征导致任何管理研究都不是价值无涉的,也不可能实现对真实管理世界的完全反映,所以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进行的理论化阐述,都只能是对实践的一种片面解释,体现了理论构建者个人的价值主观性[40]。因此,同时追求各种不同视角下的理论解释,既重视第I象限与第II象限,又同时注重第III象限,从而实现不同理论价值主张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互相补充、互相揭示,有利于探索中西文化情境的异同与相互影响,有利于从国际化的视角审视本土的管理问题与从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国际化的管理问题,又有利于基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互动视角实现中西管理文化与情境的整合、超越与双融,从而既有助于共同呈现较为真实、较为全面、较为动态的管理实践,又可以帮助中国管理学者更为全面与更为系统地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特殊管理实践与现象进行必要的理论化抽象[92],进而有利于管理新知的创造与传播。
无论是管理研究对“从匀质化到多元化”的呼吁,还是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合法性,对管理实践与现象进行理论化提炼与概括并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与理论,本身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因为抽象与一般化概括能力是人类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固有能力与天生活动,理论建构——开发与探索——作为这种抽象能力的一种方式,是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重要形式[92]。这些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观点之间互相比较、互相竞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产管理理论本身,也不仅仅是探索新的管理理论或是应用、开发与完善已经存在的理论,而是为了创造管理新知与传播更多的科学知识,从而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外部的真实管理实践。因此,本文认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或理论开发——无论是第I象限、第II象限,还是第III象限——本身都是管理知识积累、抽象、规范和合法化[92]的重要体现,学者可以适度加强对其中一种象限的重视,但不应该提倡某一象限将来占据绝对地位而忽视其他象限,因为真正的知识创造来自于不同价值主张下理论之间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必要张力。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2(P.2):无论是强调理论开发的第I象限与重视理论探索的第II象限,还是同时强调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第III象限,均是创造与传播管理理论知识的重要选择;在这三种不同的理论创新路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中国的管理实践与现象,又可以促进理论自身的演进,从而促进管理学在中国的科学发展。
(三) 管理理论是否需要普适化?
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议题需要关注理论是否以及如何普适化的问题[19,24,27]。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形式的理论发展都具有阶段性演变特征[62],而追求普适化是理论成长的高级发展形态[24]。既然诞生于西方本土的管理理论可以被接受,甚至有些已经逐渐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认可,具备了普适性特性;而且全世界的管理学者几乎都在应用诞生于西方的、又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管理理论知识,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或通过第II象限或通过第III象限诞生的管理理论不能像已有的西方理论那样,发展成为被全世界学者都认可的管理理论。Leung的论述——“美国理论起源于文化特殊性视觉并主要采用美国数据验证这些理论,但并没有妨碍美国研究者将这些理论定位为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样道理,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并没有任何理由妨碍中国研究者在中国情境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22]——在很大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其实,从西方管理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不难得知,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基于一定的路线:西方管理理论(主要是美国)——管理学理论(部分理论逐渐被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者接受)——对已有的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应用与开发——其他国家开始借鉴。从理论研究主体的能动性来看,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由个体学者思维开始,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与跨层次制度对话过程[62],这一对话过程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管理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从文化特殊性到文化普遍性,以及从主位到客位的普适性过程。从理论自身的演变特性来看,管理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情境化或情境理论化、理论抽象化以及理论普适化[24]。因此,在现阶段有学者提出追求普适性的管理理论来提高管理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如物理学)——的合法地位,甚至将此视为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本文认为虽然第I象限、第II象限与第III象限都是学者创造新知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贡献的途径,但它们均不是最终目的。无论选择哪一象限,都应该是促进理论创新与成长的一种选择,是理论演变的一种可能形态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管理学者不应只将追求理论普适性作为最终归宿和目的,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101],而是需要将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实现其不断地完善与升华,在各种理论创新象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具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与互相促进,从而促进理论知识的有效创新。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3(P.3):第I象限、第II象限与第III象限都可以发展为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但是这些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特征的不同选择,都只是中国管理学者开展理论创新工作的中间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保持它们之间的必要张力,从而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四) 理论创新是否足够?
相对于以理论创新为导向的第I象限、第II象限与第III象限,第IV象限的管理知识创造逻辑并不重视理论探索或理论开发,而是以直面管理实践问题与发现客观规律为导向,更注重对实践知识[40]的总结与提炼。本文认为,第IV象限也是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重要贡献的有效路径,因此学者应该至少给予同等的重视。
无论是对全球还是对中国的管理学者,理论与实践以及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一直都是学术界与实践界持续关注与争论的话题[28,91],也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与目的。这种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之间的争议难以消除,甚至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均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规范与准则要求,因此是不可弥合的[102],但正是这种争议产生对二者同时追求的共同压力,进而在二者之间产生必要的张力,形成促进管理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91]与正能量[51],充分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103]
需要注意的是,第I象限、第II象限抑或是第III象限都只是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或理论探索的具体表现,这些不同象限的基本出发点都强调理论贡献。虽然中国管理学科需要借助理论发展提高世界话语权与合法性地位,但是对理论价值的过度强调可能会限制不同的子群体之间知识的有效流动与传播,过度地关注理论探索与开发可能会使已有的、已经较为碎片化的学术共同体更加碎片化,这种对理论的过分关注而忽视其他非旨在贡献理论知识的可能性,最终可能会限制管理知识的有效创造[23,92]。其实,关注管理实践、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并不只局限在理论创新上,中国管理学者或可以采取Hambrick学者的建议,即提倡顶级管理学期刊应该给予那些数据有趣和重要的发现相对更高的评价,尽管这样的理论贡献不能即刻显现或是其研究发现不能融入目前的理论架构之中[77];或可尝试Miller和Tsang的建议,寻找与发掘中国管理实践中特殊的实证规律以及开展管理实践背后的深度描述与调查[23,67],因为很多时候一项重大的研究发现往往是基于真实的实践与现象而实现突破,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对人类实践与生活的改善更具有影响力。这样的研究思路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对于管理学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恐怕更是如此。
因此,本文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既应该包括重视理论贡献的研究,又应该包括不重视理论发展但可以更加贴近管理实践的研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是管理学者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的前提条件,因为有效的科学追求是对“知识生产系统共同的、制度性的承诺”[92]。若学者过度强调理论开发或理论探索,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知识创造途径,那么无形中只会导致管理学科出现更加碎片化的趋势,同时可能使得管理范式更加难以建立与保持一致性,也可能会更加动摇管理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合法地位。因此,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更加全局与批判地思考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充分认识到追求科学知识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宝库贡献自己的力量才是为学的最重要目标。管理学者应该承认,对科学的追求以及对知识的创造与贡献,不应仅仅侧重第I象限、第II象限或者第III象限,因为理论只是知识生产这个科学系统的一个产物与反映[92]。任何一种旨在理论贡献的象限都只是知识生产、积累、传播与共享的中间途径与过程,而不是最终目的和归宿,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关注理论对于科学探索与知识创造的价值,但也应该至少同等程度地关注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其他有效途径,这些重视理论创新与不强调理论发展的研究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也相辅相成,维持其间的必要张力是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造使命所然。学者在吸收与消化全球管理知识的同时,也在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从而形成良性的知识循环与生态系统。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4(P.4):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造不应该只强调第I象限、第II象限或第III象限,还应该至少同等程度地重视第IV象限;虽然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均较低的第IV象限不强调理论贡献,但是却可以通过对管理实践深刻的描述、揭示管理实践背后的实证规律等途径更加直面中国转型时期下的管理实践。因此,第I象限、第II象限、第III象限与第IV象限相辅相成,在共同有效推进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造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从而更有利于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价值贡献。
(五) 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
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分别代表不同的知识体系:实践知识是为了知晓如何处理具体的情境问题,往往直接面向真实的实践;而理论知识是为了解释管理实践的本质,更加追求知识的概括性与一般性,经常将具体的管理实践问题视为理论的具体应用,因此越与情境无关,这些理论知识就越具有普适性[40]。
管理学者对理论的重视,是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的具体应用与体现。虽然管理理论的创新对于管理学科的建设乃至世界话语权的获取至关重要,而且在现阶段的制度压力下,理论的诱惑力将使得管理学者或继续对之持之以恒,但是致力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应该知晓在转型时期是否所有的管理实践现象背后都一定蕴藏着构建本土管理理论的重大机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中国独特管理实践与管理现象,其所根植与嵌入的文化情境也一定与西方迥然有别,但是有些比较新颖的现代管理实践很有可能有悖于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设,也未必与时俱进[24],所以这些管理实践可能就不值得、也不一定蕴藏着创造和构建新的本土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无论学者是选择第I象限、第II象限还是第III象限,都不能忽视第IV象限,因为正是不同学者同时追求不同的管理理论创新途径之间,以及追求理论创新与直面管理实践之间,形成了管理学在中国知识创造的必要张力。
因此,本文认为四个象限都应该是创造与发掘管理新知的有效途径,学者没有必要将中国管理研究过于绝对化和局限化,不能只定位在第I象限与第II象限上而导致忽视了其他有效的象限选择;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更加辨证地看待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议题,更加遵循中国管理学科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旨在关注管理理论的贡献,最终目的或是拓展现有理论,追求管理理论的普适性,或是构建新的本土管理理论,但是这些论断是基于一个非常强的前提假设,即当西方管理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时,就应当构建本土的管理理论。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非真命题,因为中国管理研究不只是包含理论创新研究,还应当包括非理论性质或者理论贡献程度较低的探索研究,而且当西方管理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非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当中国管理学者过于追求第I象限时,即使这是通往普适性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也可能会导致中国管理研究被继续掣肘于西方管理议题而失去增强中国管理学科合法性的机遇;当中国管理学者过于追求第II象限时,虽然有利于解决本土管理问题与增强中国管理学科的合法性,但是很可能形成短期导向的问题,从而导致忽视中国管理学科长期发展的问题出现。然而,当过度追求管理理论的探索或开发(第I象限、第II象限或者第III象限)而忽视第IV象限时,也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短板,即由于管理理论的过度繁衍,从而可能会分裂已经支离破碎的管理学科,因为薄弱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既会阻碍好理论的发展,也会妨碍科学的进步[104],甚至一个错误的新理论将会比初期没有这个理论时带来的危害更大[23]。因此,若是过于强调对管理理论贡献的关注而忽视管理研究的其他方面,可能只会让中国管理学科在因为缺乏理论自信而不得不探索新理论以增加世界话语权时,因为不恰当理论的过度繁殖,从而导致中国管理学科更加缺乏自信,甚至很有可能导致管理学在中国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也很有可能在无形中继续拉大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继续动摇中国管理学科的合法地位,甚至是陷入孔茨十分担忧并试图竭力避免的“管理理论丛林”困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综合命题:
命题5(P.5):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知识创造不是在第I象限、第II象限、第III象限与第IV象限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尊重中国管理学科的客观发展规律与历史演进特征,更为辩证与客观地看待不同理论创新空间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在学科整体上保持对四种可行路径的同时主张与追求。因此,不仅需要在不同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途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追求与保持重视理论贡献的第I象限、第II象限与第III象限之间的有机平衡,还需要在强调理论创新的三种象限与可以更加面向管理实践的第IV象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有机平衡,从而创造与传播管理新知并为全球管理知识的更新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综合上述各命题(P.1、P.2、P.3、P.4与P.5),本文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体层面的学者与团体层面的学术共同体,还是对于中国制度层面的管理学术引领力量而言,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过程与未来发展路径应该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四、结论与展望
对于管理理论的开发与探索并不只是中国管理学者必须直面的话题,也是西方(如美国)管理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从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视角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基于对理论价值的辩证性认知与现有的文献,提出相关命题并构建了“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既为国内外的学者未来更为深入地探讨相关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又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洞见,因此同时具有本土化与全球性的重要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的每一象限都需要知晓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与制度特征。管理具有开放性系统的特征,不是一种封闭的活动,管理理论是过去和当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环境的一种产物[53]。鉴于文化环境也塑造了中国管理实践[69],管理理论可能反映并嵌入在中国现代管理实践与现象当中。随着西方价值观与文化逐渐在中国的渗透,中国难以与其传统文化完全割舍,既要面对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又不得不郑重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哲学。“华人的西化经验并非是一种取代性的学习,而是演化性的转变:透过‘中庸’哲学的调和,一方面西方文化价值观顺利地进入华人文化体系内,另一方面华人传统也未受到全面的破坏与毁灭,而与现代价值共存。”[20]因此,中国现代的管理情境与文化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以及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特征的混合体,所以探索与开发的管理理论需要考虑的中国情境不仅需要定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还应该考虑由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复杂情境与现象。因此,无论是对第I象限、第II象限与第III象限的关注,还是第IV象限的突破,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议题未来应该不仅从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发展理论构念、变量关系与解释逻辑,还应该充分反映中国现在的真实情境、文化与实践,探索与开发理论构建与规律探寻的重要元素,从而在关注理论与情境时,更加尊重中国管理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设定既符合管理实践要求又充分体现学科特征的知识创造组合。
本文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的下一个40年或者更遥远的未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征程绝不是事先被西方学者所设定,而是按照“探究自主性”原则[17],结合中国转型时期下制度情境与管理实践的真实特征,甚至应用本文所构建的发展模型,重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从而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科学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