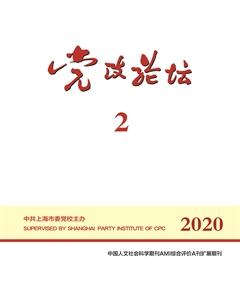论红色文化创建中的三重逻辑
周煜

[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追溯红色文化创建中的具體实践、时代价值、重大意义,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同时,深入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建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有着积极的传承借鉴作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历史创建;实践转化
红色文化作为革命文化的形态表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先进文化。自1921年以来,红色文化的创建与中国共产党的繁荣壮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并肩而立,同轨并行,而其之所以能在各个历史关头发出革命强音、凝聚民族精神、引领时代风气,自有其运行的逻辑。深刻把握、准确理解这种历史逻辑,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准确理解红色文化创建中的群体意识逻辑
纵观党的发展史,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如果除去这些代表性红色文化创建过程的时代与环境差异,都共享一种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一种独特而先进的“群体意识”。谓之独特,在于这种“群体意识”并非是某一群体将基于血缘(宗族)、地缘(村落)、业缘(行会)所形成的某种传统社会群体作为“意识主体”;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在超越传统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对一种崇高政治理念及信仰的认同,自觉将一个先进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意识主体”。谓之先进,在于这种以先进政党为意识主体的群体意识引领下,基层群众逐步开始了由分散个体到团结群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跃升。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创建以党的“初心”为根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创建主体范围也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扩大。曾经革命先驱们的个体意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已扩展转化为了由人民集体承载的先进“群体意识”。从开天辟地、勇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到坚定不移、艰苦奋斗的
“井冈山精神”,再到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长征精神”,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无一不是这种由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扩展、转化、跃升的过程。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具有两重性:既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变革所驱动的现实运动,即
“物”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因思想观念变革所引发的价值转换过程,即“人”的现代性进程。如果分析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不难发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世界,很大程度是由“人的现代性”所塑造的。没有人的理性觉醒、人的精神启蒙、人的主体性确认,人不仅无法认识和决定自身的命运,也无法设定社会变革发展的方向。
近代中国同样如此,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冲击蹂躏后,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方面造枪造炮,开展洋务实业运动;另一方面则主动向西学求“真理”,尤其是在甲午战败后,1897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西方进化论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中国思想界。随后,1898年戊戌变法,1911年辛亥革命,276年的大清王朝在十余年间顷刻覆灭。然大清虽倒,但民族振兴依然任重道远,于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便随之展开。尽管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变革在历史转型中的现实作用和意义,但彼时中西方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是以确认文化的主体性来开启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则相反,是从西学中寻求“答案”。
但殊途同归,中西方近代社会的转型变革都绕不开“文化价值观”的转换问题。历史证明,任何国家、社会的转型都会面对观念变革与文化创新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文化思想是人们认识时代,改变社会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如不能转变为物质力量,则根本无法承担和发挥改变物质世界的作用。文化思想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关键是人,但这里所指的人,不是一个个分散孤立的个人,而是特指具有共同文化认同感以及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广大人民群众。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而今天我们熟知的红船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的“群体意识逻辑”正是如此:人民群众在党的奋斗历程中,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即“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不同革命时期、不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逐渐培育起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并最终把这种崇高的“认同感”,转化为了群体性的无私奉献精神,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比如,“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由此,越来越多的群众能在高度认同党的事业基础上,确立起中国式的“文化主体性”,并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将自身一切与共产党事业融为一体的政治自觉,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个体意识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终将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群体意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表明从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到党群、军民根本利益关系上的“水乳交融”,不仅使人民群众心中有了
“主心骨”,而且也使党的事业有了“生力军”。可见,红色文化创建中的群体意识揭示了党在最艰苦的革命岁月,是如何从无到有,由小及大,由弱变强,最后汇聚成摧毁旧世界的澎湃力量的。
二、深刻把握红色文化创建中的基层动员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无疑称得上是红色政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引领创建的红色文化发轫于革命的特殊时期,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广袤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牢固的思想根基与群众基础。这些诞生于革命老区、形成于特殊时期的宝贵经历启示我们,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是如何借助文化创建实现基层动员的。
基层动员包括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归根结底是要让群众“认同”党的事业。“认同”是任何思想文化建设的根基,“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性的文化价值判断,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特定社会共同体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既是凝聚社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更是延续社会共同体生命的文化根基。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缺乏与外部世界的对等交流。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国缺乏形成“认同问题”的客观条件。1840年以降,西方文化挟着政治、经济、军事强势侵入中国,“认同问题”也随着文化多元以及虚无主义的漫延盛行逐渐产生。更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的“认同问题”产生于被践踏欺凌的现实环境,对其的理解不能脱离“文化自尊”向“文化自卑”的被动性“突变”背景。因此,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问题”虽以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呈现,但究其本质,却从产生之时就远远超越了文化范畴,体现为与“现实政治”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文化认同与中国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从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
近代知识分子就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陷入了“认同危
机”。梁启超提出了“国性问题”,试图以此重建“立国之根本”;章太炎也以强调历史的方式疾呼“史亡则国性灭”;1935年更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希望通过重新倡导文化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面临的严重“认同危机”。结果这一切努力均消失在了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丝毫未能触动国人的心灵。究其原因,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化话题,而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能力,试图以单一的文化动员和精神启蒙化解中国已然陷入的“认同危
机”,如同缘木求鱼。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解决“文化认同危机”时,则是采取了这样逻辑:将文化创建作为人民革命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为价值先导,将拯救中华近代社会危机为最终指向。中国共产党引领创建红色文化绝非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为了“唤起民众千百万”共同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事业奋斗,即把“认同问题”与中国现实矛盾的解决融合为一个整体推进。
正如1942年的“刘少奇之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沂蒙根据地被敌人封锁、蚕食、压缩,刘少奇昼夜调研后曾问山东分局: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同志记下了刘少奇的“按语”: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
这一问一答,始终围绕着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而展开。实现基层动员,从形式看是一个理论宣传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与具体的群众工作,即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直接相关联的。“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一语道出,宣传工作即使吹得天花乱坠,但理论不联系实际是于事无补的。所以,理论不能空谈,“认同问题”也不能空置。希望群众接受和认同一种思想观念,根本前提必须是把先进理论与群众利益的实现密切结合。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革命运动,使贫苦的底层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于是“认同感”由此产生。在当时独特斗争环境中,红色文化在创建中培育了“群体意识”,激发了“认同感”,打造了“命运共同体”。
三、充分认识红色文化创建中的实践转化逻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色文化的创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岁月里的实践机理逻辑与斗争路径:即依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为根基,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最终激发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与党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担负起彻底改造旧中国的伟大使命。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③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放事业成功原因时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④的确,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手中唯一掌握的有力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在中国被西方列强蹂躏践踏,中华文化陷入全面被动甚至自卑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对先进思想的坚定信念,在极其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伟大壮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包括政治家、理论家、党内的优秀成员、军内的指战员,更包括接受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广大基本群众。而“学会了”则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懂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指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又成功轉化为了人民群众可接受能理解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从而实现了党的先锋队意志向民族大众意识的转变;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向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向现实物质力量的彻底飞跃。
从本质上看,红色文化的创建是党完成不同阶段历史任务、培育和建设各个根据地的过程。在与自然斗争、与敌人对抗的过程中,“三要素”起着最鲜明的促进作用,即“人民立场、社会需要、革命实践”。而在理解这种实践机理逻辑的过程中,要对这三要素进行准确把握。
首先,人民立场是红色文化创建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与党的政治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也因这一文化立场决定了红色文化会被怎样的社会主体接受,决定了其文化性质与功能。因为价值取向是“文化特质”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⑤关键问题是谁的利益?对此,党在创建之初就明确回答了,党是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服务的。因为,只有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才能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最大的接受度、认同度。
其次,社会需要是红色文化产生的时代基础。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⑥。理论与社会需求的相关度,实质是指与时代问题的解决程度关联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解决时代问题则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以怎样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决定着满足“社会需要”的实际程度,也决定了社会主体能否最大限度地接受这种思想。因此,思想文化的“社会需要”只要能与解决时代问题相关联,与群众意愿相契合,就能形成强大的思想感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最后,革命实践是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红色文化的革命实践是指党的思想理论在创造转化为红色文化之后,是如何通过人民的实践,由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发挥出改天换地的无尽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⑦利益,尤其是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红色文化创建、发展、传承的基础。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展现出的
“革命实践”,无不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以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势谓何?人民群众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矣。
马克思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⑨历史的现实规定性既来自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又出自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两相结合才能“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人民通过“革命实践”实现的。由上可知,红色文化在创建过程中立足
“人民立场”的基本价值,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放在首位,历经“社会需要”的融合,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⑩红色文化创建于革命年代,是党长期革命斗争的文化留存。红色文化发扬于全新时代,也是党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文化指引。在新时代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历史创建中的群体意识逻辑、基层动员逻辑、实践转换逻辑,进一步增强红色文化自觉,以高度的红色文化自信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②③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0、462、82頁。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⑤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1、104页。
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中共杨浦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