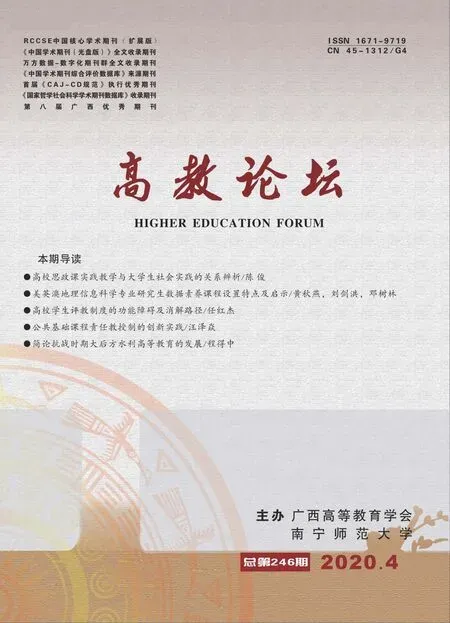西方“娱乐至死”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对策
蒋智华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广西科技大学,广西 柳州 545006)
在人类教育哲学的历史上,由西方开启的“现代性教育哲学”一度占据了20世纪以来的大半个教育思想史,西方现代性教育哲学主张的“主体性哲学”“自由化哲学”“中心—边缘”结构的教育场域哲学等曾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教育变革影响。大概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以马歇尔.麦克卢汉等为代表的一批媒介哲学家开启了从“人—媒介—权力”框架出发批判和思考现代性教育哲学的先河。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1],这种延伸在不同的媒介形态(如文字、印刷术、电视等)尽管具有不同的延伸领域,但是本质上都代表着人的认识与知识的某种扩散。同时,在20世纪中后期由互联网等主导构成的技术媒介形态当中,“媒介即隐喻”[2]也顺之成为“人的延伸”的一种具体表征,在尼尔·波兹曼看来这种隐喻中内含的一种主要文化内核即“娱乐至死”式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灵魂工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
一、“娱乐至死”思潮的主要文化指向
“娱乐至死”思潮或者说作为一种现代性下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走入人们的理论视野,离不开尼尔·波兹曼的建构。波兹曼认为,西方开启的现代性文明无论是在传播学意义上还是在教育学意义上,都带有“泛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后期互联网等新型媒介产生以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作为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守望,波兹曼对西方这种“娱乐至死”思潮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综合现有的理论成果,“娱乐至死”思潮的文化内涵主要指向这样几个方面:
1.价值内核:非理性与非逻辑性
波兹曼在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文化危机时实际上正处于一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转折、过渡的阶段。就产业格局而言,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商业、娱乐业借助于媒介技术(如电视机、互联网等)实现了高度融合,产业边界变得模糊。正如波兹曼所讲,“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35。这种“娱乐至死”思潮借助于泛娱乐化的文化表现形式、无孔不入的传媒技术和后现代主义化的传播方式,将现代性以来确立起来的“中心—边缘”文化结构极大地进行了解构,表现出了其“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价值内核。也即,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的“娱乐至死”思潮在多种媒介构成的传播文化场域中,并不刻意寻求和保持一种“稳定的公共话语秩序”,而是呈现出一种“八卦文化”“狂欢文化”“碎片化文化”“无门槛文化”和“无底线文化”等所谓的“娱乐主张”,当然这些价值本身都带有或多或少的非理性和非逻辑性属性。
2.群体行为:基于注意力经济的消费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理念、思潮和行为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物质基础,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主要社会矛盾制约。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界最典型的一个转向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地位开始呈现出一种蓬勃趋势,“波普艺术”“叛逆文化”“性解放思潮”“去中心主义”“反战情绪”以及基于“消费驱动的营销”开始取代“供给驱动的营销”等都是这一文化的亚文化形态。就媒介属性来讲,自现代性开启以来“电视机”“互联网”等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公共领域,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注意力经济”的场域[3],那些以年轻人群体、叛逆群体、亚文化群体等为代表的群体构成了这一注意力的核心,于是消费主义便诞生了。在我们看来,基于注意力经济的消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娱乐至死”的在群体行为上的主要表现,主要的缘由在于“泛娱乐化”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为这一时代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养分。正如波兹曼所言,“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的话语性质也改变了……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职业”[4],因此“娱乐至死”在社会行为和群体行为的重要表现就成为围绕着“注意力”消费的一种产业形态。
3.交际时空:“全景监狱”式的文化空虚
从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传播革命,即“作为文字的传播革命”“作为印刷术的传播革命”“作为电子传播的传播革命”以及“作为互联网的数字传播革命”[5]。这些传播革命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不同发展时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的延伸”命题。“娱乐至死”对应的传播革命主要指向“作为互联网的数字传播革命”,在这一传播时空中,“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客观世界里,还不如说我们是生活在由自身创造的媒介构筑起的强大迷宫里”[6],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认为,这种由非理性驱使、多样化的媒介传播簇拥、碎片化的进程巩固所构成的公共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全景监狱”,在这里尽管人人看起来都是“自由”的,但是却丧失了文化上的基本理性,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空虚时空。
二、“娱乐至死”思潮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就中西方文化思潮的交流与对话来讲,实际上整体处于一个“西方主导、西方中心”的对话情景当中。“娱乐化”思潮作为一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构成部分,在近些年的传播过程中变异、异化为“娱乐至死”思潮,借助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确立的“中心—边缘”结构,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娱乐至死”思潮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显著挑战:
1.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主导地位
“娱乐至死”思潮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滋生和蔓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运动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信息赋权”的现实可能。在平面媒介时代和电子传播媒介时代,受信息传播的“单向度”特点制约,个体在参与公共场域和公共活动时,在话语权上难以寻获主导地位,只能在“中心—边缘”结构当中充当某种“参与者”的角色。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而言,传统的教育模式尽管带有马克思所讲的“灌输论”[7]特点,但是整体上教育实践的话语权立足于理性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在教育话语权维度上缺乏“歧见”“异见”的干扰。而“娱乐至死”裹挟的媒介技术、消费文化等则在教育话语意义上向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从严肃型”到“娱乐型”转变的要求。尽管这种泛娱乐化思潮不一定对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提出负面挑战,但是它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弱化功能是毋庸置疑的。
2.冲击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体系
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对应的“思想教育”“德化教育”等相近的过程中,“教育知识资源—教育主体—教育介体—教育客体”往往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教育闭环显得具有明显的“教育共同体”特点。而进入后现代主义进程之后,“娱乐至死”及其背后的支配力量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种完整的叙事结构和知识社会化结构,带来了典型的“碎片化”问题。例如,高校学生群体的泛娱乐化思维对原有的德育教育知识提出了“娱乐化”的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很难满足于“被动灌输教育”;在教育介体层面,带有娱乐至死性质的学生的“娱乐狂欢”更在意的是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丧失了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严肃性等立场;在知识获取方面,精于“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的心灵鸡汤”而不愿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性的掌握等,这就从教育过程上破坏了原有的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3.淡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政治实践寻求的基本政治价值之一就是“公共性”,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共同主体性”,它指向的是“相对于私人性而言的……公共性关乎某种共享价值……公共性还意味着某种独立于私人空间的社会空间”[8]。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从人的思想和灵魂角度入手寻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动手段,在根本性的意义上是为了寻求“公共性”的价值。“娱乐至死”就其基本的价值哲学而言,寻求的是“个体性”“自私性”“物欲性”等,尽管它也积极寻求借助于多样化的媒介构建一定的社会交往场域,但是背后承载的却是公共性的“不在场”,主要的表现比如有盲目追求娱乐线索而丧失公共道德、极力挖掘娱乐流量而枉顾公共责任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从思想角度为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设置了不利条件,沉浸于“娱乐至死”中的学生更容易沾染上随波逐流、崇尚享乐、追求浮夸的社会人格。
三、应对“娱乐至死”思潮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策略
综合来看,“娱乐至死”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并外溢性地给思想政治教育等带来挑战是现代性以来市场经济深度调整、工商文明精细化分工和消费主义不断升级、泛娱乐化走向极端的复合作用的产物。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和创新正在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要线索、以“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着,最终的变革目标是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当前我国现有的娱乐环境下,为了矫正过度娱乐化、“娱乐至死”的负面效应,可以尝试这样几个策略:
1.教育过程中的“娱乐生活嵌入”策略
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一经产生就天然地带有分层的属性,例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就是两种明显的分层文化。“娱乐至死”思潮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在根本性的意义上它满足了现代人、后现代人“娱乐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与西哲提到的“人的文化存在”“人的数字化存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娱乐文化来源于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则寻求高于生活。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走向了“极端主体性”“单向灌输性”“理论教条性”“应试导向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在寻求自我高于生活定位的过程中脱离了生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因此,针对淡化“娱乐至死”思潮的观点,我们首要的姿态并不是“筑造防护堤”一味地将娱乐化拒绝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而是要“设置过滤网”将娱乐化的合理内涵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过程中。对此,在教育过程中,本着“德育生活化”的相关理论内核,我们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适度地大胆引入一定的“娱乐生活化”资源,例如采取“翻转课堂”设计,引导学生用时兴的娱乐语言、网络语言等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阐释,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与娱乐生活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自觉提升。又如,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可以学习借鉴央视新闻联播主播以“抖音”“快手”等大众化、娱乐化、通俗化话语方式传播新闻的新样式,以抖音、快手等新兴的“娱乐生活软件”为教学载体,将传统德育课程中较为枯燥的知识部分(例如人的主体性培养等)用相对娱乐化、案例化、网络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实现德育目的。再如,以辅导员为主体的思政工作者,要走进学生、融于学生,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开展思政工作,通过新媒体、微视频、微动画等平台,让学生感觉到辅导员就是自己的真朋友,从而让思政教育更有实效、更有味道。
2.娱乐媒介生态中的“二级传播”教育策略
波兹曼认为,“娱乐至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习惯于拿一切东西来娱乐,而无论它是宗教、法律抑或道德、公共秩序等。同时,由于现代传媒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特点,“娱乐至死”的交往和社会传播带有了明显的“部落化”“社团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对于一个娱乐议题来讲,从议题的设置、议题的传播、议题的发酵、议题的变异、议题的负效应产生等有了更快、更广、更精准的媒介渠道,无怪乎20世纪30年代著名科幻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曾经预言到“工业技术日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不费吹灰之力,在感官刺激的海洋里,不再有人愿意思考。人类对娱乐充满无止境的欲望,不但丝毫没有察觉它正在毁灭我们,反而崇拜和热爱这些使我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最终沉溺于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之中”[9]。从“娱乐至死”的这种传播特点来讲,“病毒式”传播是其主要的表征,而一种打破这种传播形式的重要机制即在于“二级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二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一般也被人们称为“两级传播”、“次级传播”等,最早由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创造,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在受众获得信息的场域中,“信息并不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经过中间的信息通道(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会有效地传递给受众[10]。针对“娱乐至死”所拥有的特定传播社区、阵地或平台等,我们认为既然“非理性”“非逻辑”“无下限”“八卦化”构成了其传播特点,那在相应的传播过程中就应当借助于一定的意见领袖向特定的泛娱乐化学生群体实施精准的“二级传播”,在虚拟交际社区等场域中用娱乐化的语言、娱乐化的口气、娱乐化的思维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引导他们自觉树立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策略又如,在发生区域性或全局性公共危机事件(譬如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时,针对网络虚拟时空中出现的大量社会谣言、政治谣言、生活谣言等,我们的德育工作者可以以“二级传播”带动“三级传播”“四级传播”,从学生队伍中培养学生身边的“意见领袖”,把辟谣、抵制谣言、净化思想政治网络生态环境作为“二级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3.“娱乐在场”导向的参与式教学诊断策略
“娱乐至死”反映着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娱乐化、生活化情趣的追求,构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生活化趋势。在教学管理领域,“教学诊断”(Teaching diagnosis)代表着教育教学实践主体对自身品质和绩效产出的一种管理关怀。教学诊断的本质在于通过对教学过程的评估,不断调试自身的教学过程,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不断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命题。
我们注意到,“娱乐至死”的均衡化配置结果之一就是“适度娱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表现为教学风格的诙谐幽默、教学思路的生活化逻辑清晰、教学过程的交互性平易近人、教学素材来源的鲜活实际等,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评价指标当中可以适当增加这种导向的评价指标,同时又要积极注意收集学生群体对教师授课的“接受度”、“满意度”等,用学生对教师的生活化授课满意度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指标之一。因循着这种逻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诊断”实际操作层面,可以选取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或者班级主题班会、团支部主题团日活动等融合学生党员、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生群众代表等于一体的组织对话的平台,在一种轻松对话、娱乐反思的协商民主议程中实现对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精准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