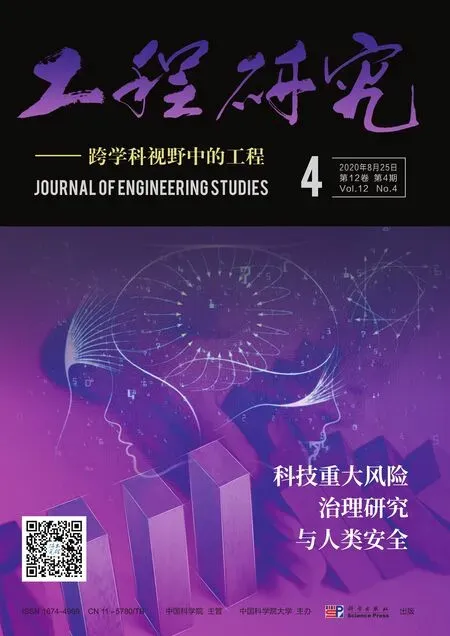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治理——以H5N1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与争议为例
高 璐
“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研究与人类安全”专栏
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治理——以H5N1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与争议为例
高 璐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通过对H5N1禽流感病毒的改造带来争议的分析,并以美国对两用研究进行监管与治理的实践作为案例,来探讨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特征,以及两用研究治理范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尽管美国近年来不断完善两用研究治理体系,从科研经费申请、研究过程到成果发表等对两用研究进行全程管理,但是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以此揭示出生物领域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回顾美国风险治理范式形成的历史与制度逻辑,认为应该拓宽对科技风险的理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和治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两用研究;生物安全;科技重大风险;致毁知识;治理;H5N1
“两用”(Dual-use)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一项技术既能民用又能军用。但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炭疽病毒邮件事件,人们再次认识到科学被恶用的巨大风险,这使得“两用研究”(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DURC)成为一个专有的研究范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两用研究定义为那些本意为了人类福祉的研究成果与知识,但却能轻易地通过知识传播产生滥用,直接用于制造威胁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武器[1]。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随着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技术平台的不断提升,使得我们对基因组的修改能力逐渐提高,相关研究被滥用和恶用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生命科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指向性,带来复杂的治理问题。有学者将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风险归结为三个层面:(1)表面上的民用设施实际上可用于军事或恐怖生物武器开发和生产;(2)可能被挪用或误用于生物武器研制和生产的设备和制剂;(3)可能被用于研究与生产生物武器的科学知识[2]。
两用研究带来的困境源于知识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因为尽管科研过程中充斥着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但随着技术平台的提升与研究数据资源日益开放,使得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距离更短。同时,知识被应用的过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人决定了技术的善恶;从STS的角度来看,科技的价值是由利益分配模式、制度与伦理规范等社会因素决定的。那么,如何确保具有潜在重大风险的知识被恰当地使用,是兼具学术与政策价值的重大议题。国际学界从2004年后开始逐渐关注两用研究的伦理与治理,如Atlas等人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高被引论文中指出了两用研究的三个层面的问题,以及如何从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的角度去消解这些难题。[2]一些学者从已有的伦理规范中寻找适用于两用研究的伦理框架,如起源于环境治理中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两用研究的界限太模糊,这造成了治理中的难题[4]。在国内,较早关注两用研究的学者来自军事医学领域的专家[5],研究内容有科技政策角度的解读[6],这些研究将美国与其他地区丰富的经验介绍到了国内,并反思了我国在建立生物安全体系与监管中的问题。但是,已有研究鲜有从科技哲学、STS角度出发,缺乏两用研究所引发的科技与社会问题的考量,因此也就缺少了对两用研究等新兴技术治理体系的整体反思。如果我们只在监管层面去反思两用研究,而不去回顾这一监管体系的制度逻辑与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很难解决两用研究带来的威胁与困境。
2012年,两篇饱受争议的H5N1禽流感病毒的基因重组研究论文使这种担忧进一步升级[7]。尽管对H5N1病毒的研究本身具有潜在的科学与社会价值,但一些科学家和决策者反对发表这些论文,因为他们担心恐怖分子(或其他别有用心者)可能利用这些研究来制造一种可能危害全球的生物武器。研究H5N1病毒的论文的出现,凸显了科技风险治理的艰难,以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以及国际卫生组织(WHO)为首的研发管理组织逐步建立起两用研究治理的规范,涉及研发投入、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发表与合作等诸多方面。这一案例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8],本文探讨的是美国的治理体系是如何应对H5N1病毒研制引发的两用研究治理难题,以及这一治理体系与实践带来的路径依赖效应。
1 流感百年:对病毒认识的深入
人类历史是一部与病毒斗争的历史,但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才第一次窥见病毒的真容。这种不同于细菌的、能够通过细菌滤器的亚微观颗粒,由简单的核酸与蛋白质外壳组成,只能在宿主细胞中完成生命过程[9]。尽管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H1N1)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导致了5000万人死亡,但当年人们几乎对流感病毒一无所知。一些科学家认为可能是细菌致病,因为在这一时期,巴斯德与科赫的细菌致病说正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们对这一传染病几乎无计可施。在近100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了3次较大的流感疫情,分别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1968年的“香港流感”以及2009年在美国等地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10]。这几次重大的流感疫情都为人类健康与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对比蝴蝶效应,有学者提出了“病毒效应”来表述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与特征,认为病毒可以作为超级支点,给人类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11]。
随着当代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流感等病毒的认知程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与提高。然而,季节性流感以及不同亚型的动物流感的存在,仍在不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直到今日,我们除了流感疫苗,仍然没有十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与此同时,病毒的发展与变异速度非常惊人。一般来说,对流感等病毒的研究通常是对已经发现的病原微生物的结构、生物特性以及流行病学数据进行分析,但也有一部分科学家致力于对病原微生物进行预先“干预”,通过DNA重组技术来制造一些具有新性状的变异,使病毒改变宿主或者提高致病性,以期提前理解病毒的演化——这种研究方式又被称为“功能获得型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12]。这类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为公共卫生和预防工作提供信息,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与生物安全有关的争议。这类两用研究是否应该进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应该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即使制定了管理措施,能否有效落实?两用性研究是否存在着边界?下面我们将从H5N1病毒引发的争议开始,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 旋涡的中心——河冈义裕、富希耶与美国生物安全国家顾问委员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河冈义裕教授(Yoshihiro Kawaoka)是长期致力于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领域的病毒学家,同时供职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担任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病毒致病机理及预防控制研究,在流感病毒的致病、跨宿主传播、抗原研究及疫苗研发等方面做出了不少重要工作,也引起过巨大争议。2013年,河冈义裕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自2008年开始,河冈义裕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下,开展与H5N1禽流感病毒传播的分子特征有关的研究。
2011年8月31日,河冈义裕将论文《血凝素基因突变赋予H5N1甲型流感病毒识别人受体并以呼吸道飞沫在雪貂中传播》投稿到《自然》杂志,在文中披露了通过对病毒进行基因修饰使其获得了更强的传染性。河冈义裕将基因改造的H5N1流感病毒的H5部分替换为2009年流感的H1N1病毒株的H1部分,产生了可在雪貂间通过飞沫传播的H5N1流感病毒[13]。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获得型研究,为了理解病毒的进化机制,给H5N1插上了新的翅膀,让其毒性提高,并且更具传播性。
无独有偶,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Erasmus MC)荣恩·富希耶博士(Ron A. M. Fouchier)也对甲型H5N1流感病毒进行了诱发突变的研究与实验,并于2011年8月30日向《科学》杂志投稿论文《禽流感H5N1甲型病毒的空气传播》。该文指出禽流感H5N1经过部分基因改造可以大幅增加在哺乳动物雪貂之间的传播性,只需要将5种已经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变异,通过基因改造汇聚在一次病毒变异的过程中,就能够实现H5N1病毒的加速演化。在编辑部收到这两篇论文后,意识到这一研究结果和数据的公开存在巨大风险,于是便快速地提交给了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NSABB)。
美国9.11事件以及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生命科学研究恶意应用的可能性。2004年发布的《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呼吁应仔细审查两用研究,明确了解一些研究成果对于恐怖主义的意义。同时,这一报告还提出政府应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措施,建立全国性的生物安全顾问委员会。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启动针对包括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两用性研究监管等在内的生物恐怖威胁的若干举措,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SABB)。这一委员会服务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由不多于25名投票委员组成,职责是为生命科学的两用研究的生物安全监督提供指导和建议。主要包括:为相关学科的科学家、实验室工作人员、学生和受训人员提供关于两用研究的教育、培训与发展建议;就两用研究成果的出版、公众传播提供政策建议;为促进国际社会参与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管理提出战略;对两用研究和研究结果的实施、交流和监督提供政策建议等[14]。
尽管这两个关于H5N1的研究能够提高对流感大流行的监测、预测、预防、诊断和治疗能力,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研究有潜在的巨大的被误用的风险。因此,NSABB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都参加到了对这两项研究的讨论中。经历了5周半艰难的讨论,委员们分析了两篇文章中的数据,衡量公布信息后的风险与收益,最终在2011年11月21日,NSABB建议《自然》与《科学》杂志重新编辑这两篇文章,将关键的结论公布出来,将数据与方法隐去,只分享给那些可信的专家和机构[15]。这是NSABB自200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限制性建议。这一结果引发了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学术审查对科学自由的剥夺;也有一些声音认为,科学的两用性让我们不得不有所取舍。
3 科研伦理与生物安全:争议与磋商
正是因为各界对于NSABB的意见存有争议,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反思这项研究的价值。支持者认为,富希耶研究中的5个基因突变均在自然的H5N1 流感病毒中发现,因此专家认为监测这5 种基因突变有助于早期预警流感大流行。同时,河冈义裕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病毒的传播因素,深入了解病毒遗传进化对人类认识流感有着积极意义[16]。
然而,其潜在的风险也让人难以忽视。首先,实验室存在着泄露的风险,一些专家认为,由于泄露风险一直存在,因此那些使得接触性传染病变异得更加强大的研究不应该做。海恩法则指出,在每一起被曝光的严重事件背后,必然有着29次轻微事件和300次未遂先兆事件,以及1000次事件隐患。尽管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改造病毒对人类的影响程度,但潜在病毒大流行的风险超过了任何可能的研究益处[17]。因此,NSABB的专家强调研究的公开发表可能为敌对分子制造生物武器提供了“路线图”。尽管制备病毒存在着知识壁垒,但公开发表存在着授人以柄的风险。
2012年1月20日,NIH发表了“关于国家安全局审查H5N1研究的声明”,声明中指出NSABB是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关于NIH资助的H5N1流感传播性研究的论文手稿,NSABB认为公布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其他细节,可能会推动那些有不合理企图的人复制此类实验,因此建议不要全文公布这些手稿。NSABB成员还讨论了在研究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是否应暂停广泛传播H5N1的两用研究[10]。也是基于此,卫生部向河冈义裕和富希耶以及提交出版的期刊编辑提供了NSABB的非强制性建议。
同日,河冈义裕、富希耶和H5N1研究界的其他科学家宣布,他们将自愿暂停对H5N1病毒研究60天,等待国际社会彻底地讨论该如何更好地对这一研究问题负责后,再决定是否开启研究[18]。这种暂停适用于增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传播能力,以及任何已经证明可在雪貂中传播的H5N1病毒的试验。
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一争议事件也从科学共同体内部,走到公众面前,变成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公众质疑这种高致病性、高风险的病毒是否应该被主动制造,又该如何进行保存和保护,如何避免被用于不法用途和恐怖活动,研究者和决策者需要考虑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的作恶企图和能力,以及公众的脆弱性等情况。
鉴于这一问题具有全球性,世界卫生组织于2012年2月16日至17日召开了一次初步技术协商会议(technical consultation),其目的是澄清与研究相关的一些事实,并衡量这一研究带来的生物安全漏洞,以及如何更好地获取和传播研究成果。会议邀请了22名参与者,其中包括河冈义裕和富希耶、政府监督人员和公众媒体,当时正处于禽流感H5N1疫情中的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①参会者名单可见https://www.who.int/influenza/human_animal_interface/list_participants/en/ [OL] [2020-6-10]。。与会者回顾了研究中使用的H5N1病毒从实验室外转移到实验室内的时间顺序、有关使用样本的相关协定、研究经历的审查,以及经费方对工作的监督等问题。两位研究者宣读了未发表的研究报告的全文和修订版,并听取了大家对研究结果的意见。与会者认为:基因改造的数据对于改善人类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部门的监测能力具有价值,有助于监测正在传播的H5N1病毒发生重大变异,这些研究结果为病毒在自然界中的进化积累数据,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但是,必须结合社会与政治背景,去判断研究成果是否会带来人们对病毒重组知识的滥用。这也是本着一种底线思维安全观,思考这一研究带来的对全局的影响。为了促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WHO在2月份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深入讨论了生命科学两用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综合了各方的意见,WHO认为这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益处超过风险,建议论文无需删减即可公开发表,并主张设计有效的交流方案,提高H5N1研究的公众认知和理解。同时,他们也对实验室改造病毒的保存与否、在何种时间、地点、环境下进行保存以及后续如何建立生物安全标准、允许进行哪些后续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这些病毒目前所处的设施达到或超过了所需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标准,但代表们一致认为应该提高研究H5N1病毒实验室的相关条件。在研究暂停结束之后,需要就其他研究地点所需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标准提供明确的指导,并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监测系统。
2012年3月29日和30日,NSABB第二次会议审查了之前的会议信息与国际意见,重新审议了出版意见,建议两篇论文全文发表。NSABB同时发布了“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监管政策”(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for Oversight of Life Sciences 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19],指出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定期审查美国政府资助或进行的具有某些高致病性特征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以减少风险、收集必要的信息,从而维护生命科学研究的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滥用此类研究的知识、信息、产品或技术的风险。这项政策补充了美国政府关于持有和处理病原微生物的现行条例和政策,对于研究人员、国家安全官员和全球卫生专家在内的有关群体起到了指导作用。
2012年5月1日,国家科学院科学技术和法律委员会与生命科学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微生物威胁论坛(Forum on Microbial Threats),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公众研讨会[20]。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从研究概念化到出版的可能干预节点”的全周期,并讨论当前对研究的监管和监督,思考如何建立和实施新机制。
2012年6月22日,河冈义裕的论文《H5-HA流感的实验性适应使雪貂的呼吸液滴传播到重组H5-HA/H1N1病毒》发表在《自然》上②研究指出HA中的分子变化使得具有H5-HA亚型的病毒能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研究重组了H5HA(来自H5N1病毒)和2009年大流行性H1N1病毒中的7个基因片段,使得新病毒能够在雪貂模型中飞沫传播。。研究结果强调,有必要为H5HA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潜在大流行做好准备。这些知识将使研究者能够监测正在传播的或新出现的变种的大流行潜力,将工作的重点放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分子变化亚组的病毒上,在这种病毒传播的地区储存抗病毒复合物,并在大流行前启动疫苗生产和大规模生产[21]。富希耶的论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甲型H5N1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宿主体内进化的可能性》也于同日在《科学》上发表,指出甲型H5N1流感病毒只需要5个氨基酸替换或者4个重组就可能通过飞沫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构成大流行威胁。其中两种替换在甲型H5N1病毒中很常见[22],有些病毒可能只需要另外三种替换就可以通过哺乳动物之间飞沫传播。因此,这项研究通过使用宿主内病毒进化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在病毒感染哺乳动物宿主后增加和减少剩余替代物进化概率,来研究该类病毒在自然界进化的潜在威胁。
随着文章的发表,对H5N1研究的紧张情绪逐渐松弛,河冈义裕和富希耶等在2012年10月提出要终止对于甲型H5N1流感研究的暂停禁令,恢复自2012年1月以来的工作,因为人们已经观察到一些自然条件下的突变,这为人类造成了新的威胁[23]。这场有关实验室与自然环境中的病毒的赛跑,在政府和有关机构批准下,又再次上演。至2013年2月1日,河冈义裕等人正式宣告研究恢复[24],宣称由于H5N1病毒传播研究对于大流行预防和了解流感病毒对哺乳动物的适应能力至关重要,但科学家不应在不具备条件的实验室与监管制度下进行类似研究。
2014年7月3日,河冈义裕为了分析H1N1的基因变化,研究绕过人类免疫系统的关键步骤,制造出“超级H1N1病毒”,再次引发极大的争议[25],但河冈义裕针对H1N1以及H5N5等流感病毒的研究仍在继续,自2014年至今仍有百余篇文章发表,不过2018年后的研究成果已经难以检索到。富希耶也仍在呼吸道病毒、禽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病毒学研究领域继续进行研究,自2013年至今仍有约百篇论文发表。
4 难以平息的争议与两用研究的监管
H5N1事件几乎定义了“两用研究”。尽管监管部门应允研究者继续,但在科学界内部,仍不断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NSABB 主席凯姆(Paul Keim)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病原体。我甚至觉得和这种病毒变种比起来,炭疽杆菌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这种病毒因为错误操作而逃逸,势必会造成流行病。虽然这种概率是未知的,但它不是零。需要考虑的场景有很多,从疯狂的孤独科学家、绝望的独裁者到千禧一代的末日狂热分子,生物恐怖分子或一个人的随机疯狂行为。”[26]《科学》的记者恩瑟林克(Martin Enserink)在专栏中写道:“该病毒可能改变世界历史。”[27]美国威斯康星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发文表示:经过十轮实验,病毒才会通过空气传播,感染附近笼子里的雪貂。这种空气传播菌株的基因组与自然中的变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生了最恐怖的突变[28]。有学者通过对H5N1的人工促发突变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三大核心的争议问题为: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风险;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研究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争议;禽流感 H5N1 病毒研究论文公开发表争议[29]。
尽管围绕着河冈义裕、富希耶两人文章发表与否的争议告一段落,但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在美国促成了NSABB对于两用研究的监管革命。2012年3月,NSABB发布了《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监管政策》;2013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研究机构监管政策》。这两项新政策是加强联邦资助的生命科学研究监管的重要举措,美国政府实施该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极其重要的生命科学研究的益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知识、信息、产品或技术误用恶用的可能。两项新政策有助于美国对整个生命科学研究周期(从最初提交资助申请到研究结论和研究成果交流)潜在的误用风险进行管理,对研究进行全周期评审。一方面,明确了政府需要监管的15种重点生物制剂或毒素,以及7类两用性研究类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联邦政府与研究机构的职责,以及如何定期地进行生物安全评审。
在全周期的科技管理中,有三个层面的机构十分重要。首先,是与研究者关系最密切的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Institutional Biosafety Committees,IBCs)。IBCs是20世纪70年代DNA重组技术产生后,由NIH设计出的一个制度框架,与机构伦理委员会一起(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尝试在研究者所在的研究机构中与科学家共同应对人们对基因工程带来的风险的担忧[30]。两用研究带来的潜在威胁促使NSABB考虑进一步扩大IBCs的作用,以监测那些可能对生物恐怖主义有影响的研究。如果一项研究涉及危险病原体(如H5N1、炭疽杆菌、埃博拉病毒等),大学或者研究所的IBCs需要预先对项目进行审议,以确认该研究的研究价值与安全措施,并决定这一项目的危险程度是否需要提交到美国卫生部(HHS)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时,研究人员必须提供符合“加强生物安全的措施”、“提供两用研究的教育培训”、“在机构层面定期检查新兴额外的两用研究”以及“明确沟通形式以确保负责任的两用研究”等八项规定的“风险缓解计划”[6]。如果研究人员无法通过IBCs的审查,那么也无法在HHS与NIH层面参与项目申请。第二个层面,由HHS与NIH为主的联邦机构会从联邦政府的层面审核研究的风险、必要性以及生物安全措施是否完备,做出资助与项目评审意见。美国联邦政府的选择是将审查前置,在资助、项目申请与研发阶段就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避免研究成果完成带来的措手不及。第三个层面,仍然将论文与成果的发布、与研究有关的风险的沟通作为要点,在重要期刊、预印本以及学术会议上,都加强生物安全的考量。在这一要求下,河冈义裕近年来的部分成果未公开发表。
NIH在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前,多次暂停了相关的研究与资助。2012年对于河冈义裕等人两用研究的暂停,以及2014年暂停关于非典、MERS、流感病毒等功能获得型研究资助[31]。由于功能获得型研究能够增强潜在流行病原体的致病性与传播能力,因此直到2017年,美国科学院、NIH以及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分别澄清了功能获得型研究的边界与管理办法,相关研究与新的资助才得以开启。
总体而言,经历了H5N1病毒事件后,美国通过制度、组织与科研管理体系的调节,从一种对于两用研究“应急”似的管理模式,转变到一种深思熟虑的、常规化的管理模式。尽管一些学者怀疑IBCs执行能力,或是独立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等,但通过几次主动暂停,美国联邦政府在两用研究的监管上在尝试给出一个平衡风险与收益的管理体系。同时,随着对研发活动认识的加深,开始从发表物、结果审查转向到全研究周期的管理策略,更尝试通过安全教育、公众意见的反馈来影响研究的内容本身,通过筑高门槛来阻碍一些设计不当的、有其他可选择进路的两用研究。
5 两用研究治理的困境及其可能的破解之道
两用研究风险巨大,其治理绝非易事,治理困境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用研究风险治理在科技监管制度上面临挑战。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或许从未遭遇如此棘手的选择,而监管部门的责任是通过制度引导研究向善的同时,规避一些难以承受的风险。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如何思考》一书中说道,通常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府机构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正在做些什么,而非他们是怎样做或是如何思考的。然而,制度是通过人在进行思维,那么问题就变成,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哪些人在通过怎样的方式思考,进而如何制定政策并影响文化[32]。
反思美国的风险治理逻辑,或许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自1986年里根总统的科技政策办公室做了“生物技术管理协调”的报告后,美国政府依靠分布在不同部门中的咨询委员会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正如贾萨诺夫在《自然的设计》中的分析,美国不同部门中咨询机构的共识是生物技术产品与传统的化学工艺制造的产品没有区别,因此美国将生物技术视为需要普通类型审查的常见产品的供应者,而不是一个对社会造成不确定性的或者危害的特别工艺[33]。因此,美国形成了一个以审查最终“产品”的风险与安全性的风险治理范式。与此同时,生物技术也成为咨询委员会技术专家指导下的决策对象,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的政治事件。对比坚持以“工艺”作为生物技术监管对象的欧洲,美国的“产品审查”逻辑直接决定了其对风险的态度——科学家的自我管制首当其冲,由专家承担责任并做出决策,同时通过政治体系与科学建议对生物技术研究的产品风险进行控制,并通过风险沟通的方式将公众纳入到整个体系之中。自重组DNA技术出现以来,美国对于转基因作物、基因编辑技术、干细胞治疗等新技术的监管方式都是在这样的理念中形成的。因此,在如此的体系之下,两用研究只是一种新的风险管理范畴。尽管联邦政府通过全周期的科研管理来对两用研究的风险进行把控,但是这些程序层面的补救很难妥善治理两用研究风险。同时,即使能够对两用研究从经费申请到研究过程、成果发表的全程进行监管,在美国的科技制度下,也只能对联邦政府的研究机构与经费进行管理,而企业中的私人实验室则几乎不受这一体制的控制。
第二,两用研究风险治理在认知上面临挑战。更进一步地,“两用”的概念是否掩盖了真正可能的风险?两用研究与我们熟知的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两用研究更加强调那些直接能够转化为摧毁性技术的研究,在本文所述案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科学家手中,两用研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病毒的“七十二变”,但如果这些研究被传播出去,就很容易变成走向杀伤性武器的路线图。然而,这些研究是否能够通过已有的管理体系得以完善的管理?面对两用研究产生的重大风险,实际上已有的认知是乏力的,正如刘益东所指出的,目前国际上许多关于重大风险防控的研究,只知其一(风险愈演愈烈、要加强风险防控)、不知其二(忽视了防控措施中存在严重漏洞、忽视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粗放式发展存在严重缺陷)[34]。他提出致毁知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制造毁灭性武器等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各种产品或方案的核心原理、核心技术等核心知识,特别是他关于致毁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伦理法律失灵、核平衡战略不适于生物武器平衡战略等论点[35],对两用研究治理分析极具启发性。两用研究成果是一种典型的致毁知识,研究致毁知识的意义在于认识到当代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产业社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生产出致毁知识或是两用研究的整个社会体系的理解与治理。
美国等关于H5N1禽流感病毒风险的应对,存在三点缺陷:一是两用研究的正负效应不能相互抵消,因此对其益处与害处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功利论层面,关键要探讨其害处能否防控,对于危害巨大的研究领域应该设置禁区,至少应该暂时叫停;二是加强生物技术研究的安全监管和伦理法律并不能约束世界上所有实验室和科技专家,生物黑客、军用研发和一些企业实验室完全不在资助与研发管理的版图之上;三是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得其发展依赖高技术,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使得其选择性地忽略技术发展的禁区。建立在技术与市场联盟之上的社会体系难以应对尖端科技、两用研究带来的风险挑战,科技冷战与军备竞赛使得两用技术在争议中快速发展,科技风险愈演愈烈,即使人们发现其危害和错误,也因陷入边争议、边纠错的“动车困境”而难以纠正错误[36]。近年来,以“防御性”为名的美国《生物盾牌计划》于2004年实施,2004~2013年美国政府为生物盾牌计划拨款约56亿美元[37]。且美国政府机构于2018年底批准了争议巨大、非常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项目,两用研究的不断加强,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其军方的研发。尽管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是,我们现在尚未找到关于两用研究风险的有效应对之策,甚至逐渐走向了贝克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8]。随着生物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或许面临的是对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定位、划界,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两用性或许掩盖了研究本身带来的巨大“危险”,而非风险。
第三,在两用研究风险治理上缺乏明确的指导原则。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迄今为止还缺乏明确统一的两用研究风险治理指导原则,在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既要防控风险又担心失去国家竞争优势。从底线思维考虑,应该以人类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对于国际上“两用研究”治理经验的分析与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构建我国的生物技术治理与生物安全体系。我国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逐渐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同时中国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完备的生物实验室体系,在新冠病毒的测序、疫苗研发等领域,都体现出了高效、高水准的研究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关注类似SARS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其他的功能获得型的两用研究的负面效应的管理。在吸收美国的科研管理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风险治理范式形成的历史与制度逻辑,注意其局限性,应该拓宽对生物技术风险的理解,尝试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生物技术。后疫情时代,民族国家之间在加速分裂、隔离,但是对于新兴技术的治理与应对疫情一样,恰恰需要我们摒弃国家对立之思维,珍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国正在着力制定《生物安全法》,逐步填补两用技术管理的漏洞[39],但是在构建生物安全防御体系的同时,应该积极适应未来科技社会伦理环境,冲出生物技术两用性带来的困境,引领国际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思考与定位。
6 结语
美国近年来关于H5N1禽流感病毒两用研究治理体系的历史实践与现状表明,尽管做出许多有益探索与安全监管,但是总体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底线思维考虑,应该以人类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更重要的是,两用研究风险治理需要建立多要素的治理系统。社会学家古斯菲尔德曾经探讨了酒驾如何从一种个人问题演变为公共问题的过程[40]。当人们还未意识到青少年的偶发车祸是一个公共问题的时候,酒驾只是一种个人的“道德自律”。如果将这一系列行动者放在行动者网络[41]之中,那么汽车(技术)就浮现为一个复杂的道路交通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使得那些之前不可见的行动者——喝了酒的年轻人、酒吧规则、酒驾法律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在这一网络上加以干预,如立法限制速度、严惩酒驾、提高饮酒年龄等,同时重新对技术进行改造(添加新的安全气囊),才能够真正地将技术(汽车)带来的风险加以控制。受此启发,两用研究的风险治理也应该系统解决,仅仅针对科学家进行伦理规范是不够的,需要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到外部社会的有关观念文化、管理措施、体制机制等进行一系列变革,进行系统创新。本文选择一个案例进行研究,缺乏对两用研究治理广泛的考察,应如何针对两用研究的特征构建新的风险治理体系,是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或许只有将技术的网络延伸,将更多的要素纳入到视野中,才能真正改变人们驾驭新兴技术的习惯,塑造技术与人类的共同未来。
[1] WHO. DualUseResearchofConcern[EB/OL]. [2020-6- 23]. https://www.who.int/csr/durc/en/.
[2] AtlasR M, DandoM. Thedual-usedilemmaforthelifesciences: perspectives, conundrums, andglobalsolutions[J]. Biosecur Bioterror, 2006, 4(3): 276-286.
[3] Kuhlau F, Honlund A, Evers K, et al. A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for dual use research in the life sciences[J]. Bioethics, 2011, 25(1): 1-8.
[4] Selgelid M. Dual-use research Codes of conduct: lessons from the life sciences[J]. Nanoethics, 2009, 3: 175-183.
[5] 董时军, 刁天喜. 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分析[J]. 生物技术通讯, 2014(5): 705-710.
[6] 张 琰, 钟灿涛. 美国生命科学双途研究审查协调机制及其启示[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10): 39-47.
[7] Cohen J, Malakoff D. On Second Thought, Flu Papers Get Gohead[J]. Science, 2012(336): 190.
[8] 杨 坤, 刁天喜. 美国禽流感病毒研究监管分析与启示[J]. 中国医药导报, 2015(12): 153-168.
[9] 周 程. 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20(1): 92-112.
[10] 陈化兰. “流感百年”专题简介[J].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2018(12): 1245-1246.
[11] 刘益东. 病毒效应与“直面-回避”问题的决策模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新思维[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20(1): 21-23.
[12] Selgelid M.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Ethical Analysis[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6: 923-964.
[13] NIH. Statement by NIH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M.D., Ph.D. on the NSABB review of revised H5N1 manuscripts[EB/OL]. [2020-04-20]. http://www.nih.gov/about/ director/04202012_NSABB.htm.
[14] NIH. 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EB/OL]. [2020-6-10]. https://osp.od.nih.gov/biotechnology/national-science-advisory-board-for-biosecurity-nsabb/.
[15] Maher B. Bird-flu research: The biosecurity oversight[J]. Nature, 2012, 485(7399): 431-434.
[16] Herfst S, Schrauwen E J, Linster M, et al. Airborne transmission of influenza A/H5N1 virus between ferrets[J]. Science, 2012, 336(6088): 1534-1541.
[17] 董时军. 生命科学两用型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D].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 30.
[18] Fouchier R, García-Sastre A, Kawaoka Y. Pause on avian flu transmission studies[J]. Nature, 2012, 481(7382): 443-443.
[19] NIH.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for Oversight of Life Sciences 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EB/OL]. [2020-6-10]. https://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us-policy-durc-032812.pdf.
[20] Karin M, Annemarie M, Steven K.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with H5N1 Avian Influenza: Scientific Inquiry, Communication, Controversy: Summary of a Workshop[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13: 3.
[21] Imai M, Watanabe T, Hatta M, et al. Experimental adaptation of an influenza H5 HA confers respiratory droplet transmission to a reassortant H5 HA/H1N1 virus in ferrets[J]. Nature, 2012, 486(7403): 420-428.
[22] Pasternak J. Experimental adaptation of an influenza H5HA strain confers respiratory droplet transmission to reassortant H5H/H1N1 virus strain in ferrets[J]. Einstein, 2012, 10(3): 391.
[23] Russell C A, Fonville J M, Brown A E, et al. The potential for respiratory droplet-transmissible A/H5N1 influenza virus to evolve in a mammalian host[J]. Science, 2012, 336(6088): 1541-1547.
[24] Fouchier R, García-Sastre A, Kawaoka Y. The Pause on Avian H5N1 Influenza Virus Transmission Research Should Be Ended[J]. Mbio, 2012, 3(5): 429-493.
[25] Fouchier R, García-Sastre A, Kawaoka Y. H5N1 virus: Transmission studies resume for avian flu[J]. Nature, 2013, 493(7434): 609-609.
[26] Butler D, Maher B. Risks of flu work underrated[J]. Nature, 2014, 511(7507): 13-14.
[27] Enserink M. Scientists Brace for Media Storm Around Controversial Flu Studies[EB/OL]. [2012-01-20]. Science, 2011.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insider/2011/11/ scientists-brace-for-media-storm.html.
[28] Young E.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Publishing Mutant Flu Studies[EB/OL]. Nature, 2012. [2020-06-12]. http:// www.nature.com/news/the-risks-and-benefits-of-publishing- mutant-flu-studies–1.10138.
[29] 董时军. 生命科学两用型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D].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 86.
[30] 高 璐. 从阿西洛马会议到华盛顿峰会:专家预警在生物技术治理中的角色与局限[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6): 28-35.
[31] The White House. U.S. Government Gain-of-Function Deliberative Process and Research Funding Pause on Selected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Involving Influenza, MERS, and SARS Viruses [EB/OL]. [2020-05-28]. https:// 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gain-of-function.pdf.
[32] Douglas M. How Institutions Think[M].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3] 希拉贾萨诺夫. 自然的设计:欧美的科学与民主[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34] 刘益东. 科技重大风险: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视角[J]. 国家治理周刊, 2020(18): 22-25.
[35] 刘益东. 粗放式创新向可持续创新的战略转型研究——科技重大风险研究21年[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4): 75-59.
[36] 刘益东. 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1-15.
[37] 吉荣荣, 雷二庆, 徐天昊. 美国生物盾牌计划的完善进程及实施效果[J]. 军事医学, 2013(3): 176-179.
[38]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2: 260.
[39] 王小理, 周冬生. 面向2035年的国际生物安全形势[N]. 学习时报, 2019-12-20.
[40] Gusfield J.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41]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Boston: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Governance of 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in Life Sci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and Its Controversies
Gao Lu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use research in the life sciences and th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ual-use research governance paradigm by examining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the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and the subsequent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of dual-use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dual-use research governanc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managing dual-use research at all research stages, namely, funding, application, R&D, and publication, the model of “product” as the object of risk regulation conceals the dilemma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dual-use research. Reviewing the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isk governance paradig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biotechnology risk and develop biotechnology responsibly considering the community, emphasizi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biosecu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risks; ruin-caus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H5N1
2020–06–13;
2020–07–14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重点培育项目“科技的社会风险”(E029001101);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科技治理的历史、现状与趋势”(E0290119)
高 璐(1983–),女,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物技术治理、STS、科技政策。E-mail:gaolu@ihns.ac.cn
N01;Q-1
A
1674-4969(2020)04-0355-11
10.3724/SP.J.1224.2020.00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