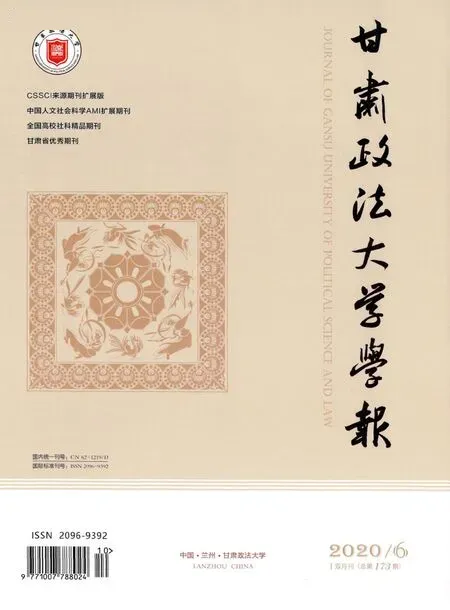瑕疵通知期间规则之借鉴与重构
路成华
司法实践中,标的物是否存在瑕疵几乎是每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58条规定,如果买受人未在瑕疵通知期间即约定期间、发现或应当发现瑕疵的合理期间或者收到标的物后两年或质量保证期内,将标的物瑕疵通知出卖人,则该标的物就被视为无瑕疵,买受人将丧失主张瑕疵救济的权利。因此,瑕疵通知期间的认定成为标的物是否应被视为无瑕疵,进而能否导致买受人丧失瑕疵救济权利的关键,能够直接决定买受人瑕疵救济诉求的成败。但 《合同法》第158条规定的瑕疵通知期间规则过于简单且存在缺陷,〔2〕参见崔建远:《论检验期间》,载 《现代法学》2018年第4期。往往导致实践中的错误认识和适用。如将瑕疵通知的 “两年期间”理解为诉讼时效期间,将 “两年期间”或 “质量保证期间”作为瑕疵通知的 “合理期间”等等。〔3〕同前注 〔1〕,第318页、第323-324页。
为规范司法实务中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适用,201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 《买卖合同法解释》)第四部分 “标的物检验”,以第17条明确了瑕疵通知 “合理期间”的认定规则和 “两年期间”的属性,以第18条赋予法院干预 “过短”约定检验期间的自由裁量权,并细化了质量保证期间的适用规则等。但是,这一司法解释并未厘清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内部构造,没有彻底弥补 《合同法》中该等期间规则的缺陷,约定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和质量保证期间的适用混乱,依然存在。〔4〕参见武腾:《合同法上难以承受之混乱:围绕检验期间》,载 《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尤其是,《买卖合同法解释》第18条赋予法院干预 “过短”约定检验期间的裁量权,使之有权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缺乏理论正当性,而且使相关实务操作更加复杂和困难,并未能够得到司法实践广泛和合理的适用。〔5〕在北大法宝法律资源网,笔者以 “约定检验期间”为关键字全文检索自2012年5月10日 (即 《买卖合同法解释》颁布日期)至2020年2月29日的一审判决,查询到5958份一审判决书,以 “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为关键字进行全文检索,查询到一审判决书168份,其中仅111份一审判决书依据 《买卖合同法解释》第18条认定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占比不到百分之二。有的法院仍然基于约定的收货24小时或2天检验期间已过,而否定买方对需经化验才能发现瑕疵的救济权利,〔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2019)新0203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安定县人民法院 (2019)琼9021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等。有的法院则将约定30天检验期间认定为对标的物型号和数量不符等外观瑕疵的通知期间。〔7〕参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2015)金民二 (商)初字第1308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4)宝商初字第0139号民事判决书等。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 《民法典》),我国由此从民事单行法时代迈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的通过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法典化任务的完成,而民事法律制度完善优化的进程则仍将继续。《民法典》第620条、第621条对标的物检验和瑕疵通知制度的规定,基本上重复了 《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的内容,未见有实质上的改进和修正。鉴于 《合同法》第158条和 《民法典》第621条中瑕疵通知规则的内容,主要继受于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简称CISG)。〔8〕参见王利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我国合同法的制定和完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将基于 《民法典》调整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之际,〔9〕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法办 〔2020〕71号)。有必要在重新检视CISG 的相关规定,对比借鉴主要大陆法国家地区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标的物瑕疵通知期间规则进行梳理和反思,以助益于这一期间规则的改进和完善。
一、标的物检验是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外部基准
在标的物检验通知制度中,直接决定买受人能否主张瑕疵救济的,是买受人是否在规定期间内进行了瑕疵通知,并非其是否进行了检验。〔10〕参见 [德]C.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页。但是,标的物的检验是进行瑕疵通知的前置程序和前提条件,对瑕疵通知期间的确定有决定性影响,也是瑕疵通知期间规则建构的外部基准。在CISG 及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中,均将买受人发现或应当发现瑕疵作为其通知期间的起算点。〔11〕具体可参见CISG 第39条第 (1)款、《德国商法典》第377条、《瑞士债务法》第201条第1款、《日本商法》第526条、台湾地区民法第356条、《美国商法典》第2-607条等,我国 《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也规定,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而这一起算点作为检验的结果,其具体认定则有赖于从检验行为和标的物瑕疵双重角度的审查。易言之,发现瑕疵作为买受人的主观认知,其何时发生或者应当发生,只能从检验行为及其对瑕疵发现的作用上,加以审查和认定。因此,标的物检验行为实际上构成了认定瑕疵通知期间起算的外部基准。而且,标的物的瑕疵能否通过检验而被识别或发现,还决定了对买受人履行通知义务期间的不同要求。对于能够通过检验而发现之瑕疵,无论买受人是否进行了检验,都要求其应当在检验期间经过后不迟延地通知出卖人;而对于不能通过检验而发现之瑕疵,买受人则应当在瑕疵出现后不迟延地进行通知。〔12〕同前注 〔10〕,第691页。因此,标的物检验同时还决定着瑕疵通知期间类型的划分,构成设定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结构的外部基准。为实现标的物检验对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基准功能,需要确立买受人进行标的物检验的一般标准,并区分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
首先,确立标的物检验行为标准是实现检验对于瑕疵通知期间规则基准功能的前提。标的物种类、检验条件、检验技术、买受人的检验能力和检验意愿等千差万别。唯有确立买受人标的物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方能规制买受人检验义务的履行,衡量检验完成期间的合理长度,具体辨别经检验可以发现和不可以发现的瑕疵,从而实现检验对于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基准功能。而且,确立买受人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亦为平衡检验通知制度中买卖双方利益之必需。因为,标的物检验和瑕疵通知本就是施加于买受人的加重负担,其目的在于保护出卖人利益和确保交易效率,〔13〕同前注 〔10〕,第680页、第689页。但其实现应当受到公平原则的制约,不应使买受人因此而承受超出通常情形的检验行为负担,而导致买受人瑕疵救济权利的轻易丧失和对出卖人的过度保护。
在CISG 和德国民法、瑞士债务法等立法例中,通常都在标的物检验通知制度中明确规定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如CISG 第38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进行检验的标准是 “按情况实际可行”,该等标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可以涵摄货物的种类、买方的特定条件、验货地点以及是否转售转送等实际情况,其中应当着重考虑的是货物的种类,因为货物种类的 “实际情况”,对确定买受人检验时间的长短具有决定意义。〔14〕参见 [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3页。《德国商法典》第377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应当 “依通常的营业可能为限”不迟延地检查货物,则提供了界定买受人检查范围的标准,即任何一个具备必要行业专业知识的正常商人可以合理期待的检查范围。〔15〕参见范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页。《瑞士债务法》第201条第1款则要求买受人 “按物的性质”并 “依通常程序”,从速检查受领标的物。台湾地区民法第356条第1款也是要求买受人 “按物之性质”和 “依通常程序”,从速检查所受领之物。当然,该等立法例中所规定的检验行为标准,均可以结合民法中理性人的一般注意标准和特定的交易类型等因素,做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比如,对于CISG 检验通知制度中买方的检验行为标准 (standard for inspection),荷兰学者Franco Ferrari认为,买方 (包括其职员或其授权的第三方)以与其特定买卖合同类似的交易中,理性人所应具有的技能进行检验即可,不应要求买方以超出其通常必备的技术设施和经验的额外努力,去检查和发现瑕疵。〔16〕Franco Ferrari,Specific Topics of the CISG in the Light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Scholarly Writing,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vol.15,1,1995.邱聪智教授认为,台湾地区民法对买受人 “按物之性质”并 “依通常程序”进行标的物检验的规定,明确了买受人对标的物检验的方法,是以按物之性质依通常程序为已足,例如食品之尝味、衣服之试穿、机械之试转、车船之试行等均是,所以,“无论如何,均不必依特殊程序,例如罐头不必经过化验,大量货品,无须全部检验,仅须就同一性质者抽查一部即为已足。”〔17〕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相较而言,《瑞士债务法》及台湾地区民法中 “按物的性质依通常程序”的标准更为具体,而且着重强调了标的物性质因素的重要性,可资借鉴。
在德国、瑞士及台湾地区等民商法的瑕疵通知制度中,均以买受人经检验能否发现为基准划分标的物瑕疵类型,从而对买受人瑕疵通知期限作出不同的规制。《德国商法典》第377条基于第1款确立的买受人的检验行为标准,将瑕疵划分为买受人检查所能发现的瑕疵 (第2款),和基于该等检查未能发现而于 “以后出现”的瑕疵 (第3款)。〔18〕同前注 〔10〕,第691-692页。《瑞士债务法》第201条以买受人 “按物的性质”并 “依通常程序从速检查”为基准,将瑕疵划分为检查所能发现的,和经该等检查不能发现而于 “日后出现”的瑕疵。《日本商法》第526条第2款则将标的物瑕疵划分为买受人按规定检查发现的瑕疵与未能直接发现的瑕疵。台湾地区民法第356条中的划分与 《瑞士债务法》第201条大体相同,即基于 “按物之性质”并 “依通常程序从速检查”所发现的瑕疵与该等检查不能发现而于日后出现的瑕疵。由此可见,前述立法例均对标的物瑕疵进行了二元式划分,划分的基准是买受人通过标准检验行为能否得以发现。针对这两种类型的瑕疵,该等立法例均设定了对买受人通知期间的不同要求,即对于经检验可发现瑕疵的通知期间,买受人应在经检验发现或理应发现瑕疵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而对于经检验不能发现的瑕疵通知期间,则只能待日后瑕疵出现买受人在发现后的合理期间内进行通知。
我国 《合同法》第157条及 《民法典》第620条除规定买受人完成检验的时间要求外,缺少对买受人应当如何进行检验的规制,没有规定买受人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这与作为我们立法继受来源的CISG 第38条,以及 《德国商法典》《瑞士债务法》和台湾地区民法等立法例所提供的比较法经验,均不相符合。而且,由于缺少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无法对标的物瑕疵做出合理的划分,并做出不同的瑕疵通知期间要求,导致标的物检验与瑕疵通知规则之间的脱节。《买卖合同法解释》根据 《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中 “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的表述,首先将瑕疵分为数量瑕疵和质量瑕疵,然后再按照检验的难易程度,将质量瑕疵区分为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试图以此作为确定买受人发现瑕疵期间和通知期间的依据。〔19〕同前注 〔1〕,第280页。按照《买卖合同法解释》起草者的说明,这种划分方式继承自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15条的货物瑕疵分类,〔20〕1984年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15条规定,为细化需方质量异议的期限要求,将货物瑕疵大体划分为三类:(1)产品的外观和品种、型号、规格、花色不符合约定;(2)产品内质量不符合约定;(3)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的内在质量缺陷。其中外观瑕疵是指 “一般包括标的物的表面性能和种类瑕疵,即产品的规格、型号、花色、品种等”,而隐蔽瑕疵则是 “通过通常的检验手段不能知道,需要专门检验或需要安装运行才能发现的瑕疵。”〔21〕同前注 〔1〕,第280页。这种仅仅以客观难易程度为标准的瑕疵划分,与买受人检验行为之间无任何关联,过于简单和僵硬,无法据之确定具体瑕疵经检验是否应当被发现,并进而分别做出不同的瑕疵通知期间规制。
因此,为实现检验行为对瑕疵通知期间的重要基准功能,在我国标的物检验通知制度中,应当借鉴 《瑞士债务法》和台湾地区民法中 “按标的物的性质并依通常程序”的表述,确立买受人检验行为标准,即 “买受人在收到标的物时应当按照标的物的性质,依照通常程序及时检验”,从而奠定进一步完善优化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基础。
其次,对于经检验发现或应当发现的瑕疵,买受人通知期间的起算始于检验期间的结束。标的物瑕疵的检验通知是以保护出卖人为目的,而施加于买受人的负担。因此,基于公平原则和对买受人的对等保护,检验通知制度要求买受人在发现或应当发现瑕疵后的规定期间内,就该等瑕疵有效通知出卖人,就可以排除检验通知制度中标的物无瑕疵的拟定,并不需要发现并通知所有瑕疵。易言之,买受人经检验发现或应当发现一处瑕疵,即应于此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而无需等待发现其他瑕疵。所以,经检验发现或应当发现瑕疵的检验期间,实际上亦于此等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时结束,而瑕疵通知期间则同时开始起算。
检验的完成和瑕疵的发现,受到标的物种类、瑕疵性质、交货场所、检验条件和难易程度、交易惯例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而瑕疵通知行为的完成则基本上主要取决于买受人的主观决定。因此,对于检验行为和通知行为的要求势必存在不同,检验期间和通知期间的衡量标准也就相应存在差异。在CISG (第38条、第39条)、《德国商法典》 (第377条)、《日本商法》(第526条)、《瑞士债务法》(第201条)、台湾地区民法 (第356条)等立法例中,买受人标的物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都是区分开来规定的。在 《美国商法典》中,对检验期间和通知期间同样是分别进行的规定。〔22〕同前注 〔4〕。德国学者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Peter Schlechtriem)在评释CISG 第38条、第39条时指出,“验货期限和通知期限应当被严格地区分,而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期限确定在一起。”〔23〕同前注 〔14〕,第114页。对于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的界分,我国 《合同法》中的表述很不清晰,甚至自相矛盾。根据 《合同法》第157条第二句 “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以及第158条第2款第一句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的表述,在无约定检验期间的情形下,“及时”的检验期间与 “合理”的通知期间应该是两分的。而根据 《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第一句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表述,其中 “约定检验期间”显然是包括了买受人进行标的物检验和瑕疵通知的时间,即在有约定检验期间的情形下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却又是合一的。受 《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应于约定检验期间内完成瑕疵通知义务的影响,我国学界一般将买受人对标的物检验、发现瑕疵和提出质量异议的时间统称为检验期间,大多认为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是合一的。〔24〕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551页;同前注 〔2〕。司法实务部门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无需区分检验期间和通知期间,并将 《合同法》第158条中的 “合理期间”理解为正常检验和通知所需要的时间。〔25〕同前注 〔1〕,第316-317页。但是,如果将检验期间与通知期间合并为一个整体,不仅对买受人更为严苛,使出卖人得到 “加倍式”的保护。更为关键的是,必将导致检验期间原则上 “及时、尽快”的标准与通知期间原则上 “合理”的要求之间的冲突,〔26〕同前注 〔4〕。使这两个各自独立期间的确定和行为评价标准失灵,也无法实现标的物检验对瑕疵通知期间设定的基准功能,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上的混乱。而且,《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将瑕疵通知期间并入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间,有以立法方式强行界定和扩张当事人 “检验期间”约定合意之嫌,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令人质疑。但是,《民法典》第620条和621条基本上沿袭了 《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的内容,未就标的物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界分,作出进一步的修正和调整,实为一大缺憾。从完善我国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角度,应当将 《民法典》第621条第1款中的 “约定检验期间”修改为 “约定瑕疵通知期间”,以与第620条中的约定检验期间相区别,或者将 “约定检验期间”情形从第621条中删除,直接区分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以明确对标的物检验和瑕疵通知行为的不同规制,并实现检验对瑕疵通知期间的基准作用。
二、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内部架构
CISG 第39条第1款规定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第2款规定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从而确立了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整体架构。基于对CISG 第39条的继受,我国 《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也将 “合理期间”规定为确定买受人瑕疵通知期间的一般规则,〔27〕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约定通知期间,从性质上讲,不属于确定瑕疵通知期间的任意法规则。并且规定了特定条件下适用的 “两年期间”及 “质量保证期间”规则。
(一)瑕疵通知 “合理期间”与 “两年期间”的关系
对于瑕疵通知 “合理期间”与 “两年期间”的关系,我国 《合同法》第158条的表述相当模糊,以致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司法实务上则往往将 “两年期间”理解为最长 “合理期间”。〔28〕同前注 〔1〕,第323-324页;孙永全:《关于质量检验期间与质量异议期间的司法认定——对 〈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的理解与适用》,载 《山东审判》2011年第5期。有的法院甚至在确定检验通知期间时,有最小化适用 “合理期间”标准而统一适用“两年期间”的倾向。〔29〕同前注 〔1〕,第318页。但是,“两年期间”就是最长 “合理期间”吗?
CISG 在第39条第1款规定买方应于发现或理应发现瑕疵后 “合理期间”内通知卖方的前提下,于第39条第2款规定了买方应当在实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学者对第39条第2款规则主旨的解释是,一些潜在的或隐藏的瑕疵,即使经过买方受领货物之后的检验仍然难以被发现,而只有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才会显现,但是,该等瑕疵越晚发现,其产生的原因就越难以确定。为避免因此导致的久拖不决,CISG 才设定了这样一个最长期限 (Cut-off Period)。〔30〕Ulrich Schroeter.A Time-Limit Running Wild:Article39(2)CISG and Domestic Limitation Periods,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vol.2017,2,2017.这一最长期限的规定是在制订CISG 的维也纳外交会议上争议最大、辩论最激烈的条款之一,也是与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终妥协的结果。〔31〕参见张玉卿:《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同时,在这一最长期限中,买受人仍然应当按照第39条第1款的规定,于发现或理应发现货物不符合同后的 “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而非等到两年的最长期限届满。〔32〕Franco Ferrari;Ulrich Schroeter.由此可见,“两年期间”并非最长合理期间,而实际上基本是对虽经检验而不得发现的潜在瑕疵的最长发现期间。如果将 “两年期间”称为最长通知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主体为潜在瑕疵发现期间的事实。从瑕疵发现的角度观察,CISG 第39条第2款规定的 “两年期间”与 《日本商法》第526条规定的六个月的最长 “发现期间”,以及台湾地区民法第498 条至第501 条的“瑕疵发现期间”,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台湾地区民法中,第498条至第501条就承揽瑕疵救济,规定了所谓的 “瑕疵发现期间”,即对于一般工作承揽,自工作交付之日起经一年后始发现的瑕疵,不得主张瑕疵救济,土地上工作物或其重大修缮者为五年;承揽人故意不告知定作人其工作瑕疵的,前述发现期间延长;当事人可以约定延长瑕疵发现期间,但不得缩短之等。一般认为,这一瑕疵发现期间的属性为除斥期间。〔33〕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43页;陈自强:《从法律继受观点看承揽瑕疵规定:承揽瑕疵担保之现代化》,载 《台大法学论丛》第42卷特刊 (11.2013)。同样地,CISG 第39条第2款中的两年期限也是 “一个绝对的除斥期间,期间的中断情况将不被考虑。它的到期应获得法院的承认。”〔34〕同前注 〔14〕,第117页。
此外,在德国、瑞士及台湾地区等民商法的检验通知制度中,虽然没有类似CISG 的两年最长通知期间的设定,但是其各自就买受人的瑕疵救济均设有短期时效期间,实际上这两种期间的制度目的和功能大体相同。如前所述,在德国、瑞士及台湾地区等民商法的瑕疵通知制度中,以买受人经一般检验行为能否发现为基准划分标的物瑕疵类型,对于经检验可得发现瑕疵的通知期间,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理应发现瑕疵后的合理期间内不迟延地通知出卖人,而对于检验不能发现的瑕疵,则只能待日后瑕疵出现时买受人在发现后不迟延地或在合理期间内进行通知。当然,该等经检验不能发现之瑕疵的出现,不能遥遥无期。立法者必须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做出决断,以一个明确和固定的期间最终结束买卖双方利益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对此,继承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传统的大陆法国家或地区,一般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中的短期时效制度,实现这一法律效果。比如根据 《德国民法典》第438条的规定,买受人瑕疵救济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从标的物交付时起算,一般为二年,解除权和减价权的行使均受该等期间的限制;而按照 《德国民法典》总则第195条、199条的规定,常规时效则自买受人知道或非因重大过失而应当知道请求权成立的当年年底起算,一般为三年。 《瑞士债务法》第210条规定,动产买卖瑕疵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自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时起算;而根据该法第127条、130条的规定,债权的一般诉讼时效是十年,从债权的清偿期届至时开始计算。〔35〕参见戴永盛译:《瑞士债务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7页。台湾地区民法第365条规定,买受人就物之瑕疵行使解除等救济权利的期间,为其依据第356条进行瑕疵通知后六个月或自标的物交付时起五年;而根据该法第125条、128条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则为从权利可以行使时起算十五年。比较特殊的是 《日本商法》的规定,虽然 《日本民法》第566条已经设定了瑕疵担保责任的短期时效,即 “买受人应当在知晓有隐蔽瑕疵或数量不足时起一年内追究出卖人担保责任”,但是 《日本商法》第526条仍然针对检验不能直接发现的瑕疵,设定了买受人自受领标的物之日起六个月的最长 “发现期间”。〔36〕参见刘成杰:《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29页。原因大概在于,《日本民法》第566条规定的短期时效自买受人知晓标的物瑕疵时起算,而不是从更为确定的交付标的物时起算,不能尽快终结买卖双方因潜在瑕疵而不确定的利益状态,不能满足商事交易的效率要求。
在制订CISG 的维也纳外交会议上,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也正是基于其国内法中的瑕疵救济短期时效制度,而坚持主张在CISG 第39 条瑕疵通知规则中规定最长通知期限的。〔37〕同前注 〔31〕,第267页。CISG 没有采用短期时效期间模式,而是在检验通知制度中直接规定最长通知期间,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执和妥协的结果,更是其国际条约软法属性限制的产物。详言之,各国的时效制度内容和期间长短差别很大,且与各自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紧密牵连,如果设定统一的短期时效,反而可能构成各国立法机构通过并签署CISG 的巨大障碍。鉴于时效问题的复杂性,在CISG 起草过程中,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另行起草了一个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38〕Ulrich Schroeter.但是,签署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国家数量很少,远远低于最终通过并签署CISG 的国家数量。〔39〕参见宋航、赵健:《〈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评介——兼论我国批准该公约的可行性》,载 《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6期;同前注 〔14〕,第3页。因此,对于为避免因潜在瑕疵导致双方利益关系长期不稳定而限定瑕疵救济期间的规则问题,CISG 未能采用德国、瑞士等国内法通常采用的短期时效期间模式,而是在检验通知制度中设立了最长通知期间 (Cut-off Period)。从一定意义上讲,CISG 的这一期间模式也可谓独辟蹊径。
由此可见,瑕疵通知规则中的 “两年期间”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最长合理期间”,其主体部分是瑕疵发现期间,是针对虽经检验而不能发现的潜在瑕疵的最长发现期间,以及应于发现后通知的 “合理期间”的结合。
(二)“质量保证期间”与 “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的关系
根据CISG 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当 “两年期间”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时,以合同保证期间 (contractual period of guarantee)为准。因此, “合同保证期间”优先于 “两年期间”,其与 “合理期间”的关系,相同于 “两年期间”与 “合理期间”的关系,即特别针对经检验不能发现之潜在瑕疵,“合同保证期间”结合 “合理期间”适用,在 “合同保证期间”内买受人应于发现或应当发现瑕疵的 “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40〕参见李巍: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7 页;Fritz Enderlein.Rights an d Obligations of the Seller un 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http://cisgw3.law.pace.edu/cisg/biblio/enderlein1.html#ij.易言之,在CISG 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框架内,“合同保证期间”是 “两年期间”的替代,优先于后者而适用。在我国《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的瑕疵通知期间规则中,采用了 “质量保证期间”的概念作为 “两年期间”的替代,其与 “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的关系未变。但是,“质量保证期间”与 “合同保证期间”相同吗?
如前所述,CISG 第39条中的 “两年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其功能类似于德国、瑞士等国家地区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中的短期时效,而且从法律属性上讲,“两年期间”的适用应当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但是,基于其国际条约的软法属性以及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买卖的特征,CISG 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排除CISG 对双方交易的适用,或者约定减损CISG 相关条款对双方交易的约束效力。因此, “合同保证期间”得以置入CISG 第39条第2款,并且能够优先于 “两年期间”适用,〔41〕同前注 〔31〕,第268页。这是 “合同保证期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当 “合同保证期间”短于 “两年期间”时,只有该等 “合同保证期间”的约定,构成CISG 第6条规定的对救济规定效力的排除或减损时,才能优先于 “两年期间”的适用;而且,其中约定增加CISG 救济的保证期间不影响 “两年期间”的适用。〔42〕Fritz Enderlein.至于专门涉及货物特殊品质或通常性能维持的保质期,不具有 “最长通知期间”的合意,当其短于两年时,也不影响 “两年期间”的适用。〔43〕同前注 〔4〕。可见,虽然CISG 第39条规定了替代 “两年期间”的 “合同保证期间”,但是对 “合同保证期间”缩短 “两年期间”效力的限制相当严格。
《买卖合同法解释》起草者认为,“质量保证期”是指出卖人向买受人承诺标的物符合质量要求或使用性能的期间,其与检验期间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 《合同法》中却被作为异议期间(瑕疵通知期间)看待。〔44〕同前注 〔1〕,第329页。学者们也认为,无论法定还是约定的质量保证期间,仅涉及标的物保持一定品质的时间,并不具有约定瑕疵通知期间的含义。〔45〕同前注 〔4〕;同前注 〔2〕。对质量保证期的这一理解和界定,与 《德国民法典》第443条规定的 “为标的物在一定时期内保有特定的性能”的耐久性担保期,以及CISG 第36条第2款规定的保质期,即 “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目的或特定目的”或保持 “特定质量或性质”的期间,基本上是一致的。CISG 第36条第2款规定的保质期,即质量保证期的功能在于推定该期间内出现的瑕疵为货物风险转移前的瑕疵,从而在免除买方证明责任的情况下使瑕疵违约救济得以成立。〔46〕同前注 〔14〕,第107-108页。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短于两年的质量保证期不能替代 “两年期间”。〔47〕同前注 〔4〕。我国 《合同法》第158 条中的 “质量保证期间”,只相当于CISG 第39条中 “合同保证期间”中不能导致 “两年期间”缩短的保质期。从立法继受的角度,如果 《合同法》第158条中的 “质量保证期间”短于两年,理应不能替代 “两年期间”而适用。其次,质量保证期免除买受人证明该保证期内发生瑕疵为交付前瑕疵的责任,从而对买受人救济更便利、保护更有力。而对出卖人而言,在质量保证期内,其所承担的瑕疵违约责任与质量保证期外并无本质区别。如果将短于两年的质量保证期视为瑕疵 “最长通知期间”,将使在质量保证期最后一刻出现的潜在瑕疵,因买受人无法做出通知而失去救济权利,反而得不到如未设质量保证期时本可得到的救济,显然不合逻辑,也有违质量保证期之本意。最后,如前所述,我国 《合同法》第158条中的 “两年期间”同CISG 第39条中 “两年期间”一样,具有替代瑕疵担保责任短期时效的功能,是针对潜在瑕疵存在或然性以及其出现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交易关系应当尽快清结之间的矛盾,而在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做出的立法决断。而且,德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中的短期时效,均具有强制性,不能被约定排除或缩短。同为国内法,《合同法》第158条的 “两年期间”也不应被约定缩短。所以,排除短于两年的 “质量保证期间”优先适用,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因此,我国 《合同法》第158条以及 《民法典》第621条中的 “质量保证期”,不完全等同于CISG 第39条中的 “合同保证期”。当 “质量保证期间”短于两年时,其不能替代 “两年期间”而适用。只有超过两年的 “质量保证期间”方可替代 “两年期间”,并结合 “合理期间”而适用于潜在瑕疵的通知期间规制。
三、约定检验期间规制之反思
在我国《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的标的物检验通知制度中,“约定检验期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概念。它被前置于第157条的第一句和第158条的第一句而得以突出强调,第157条第一句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然后才是关于未约定检验期间情形的规定;第158条第1款第一句则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以及未按期通知的法律后果,然后第2款是关于未约定检验期间时瑕疵通知的规定。可见,“约定检验期间”不仅适用于标的物检验,也适用于瑕疵通知,相当重要。但是,这一概念无论是在CISG 的标的物检验通知制度中,还是在 《德国商法典》《瑞士债务法》《日本商法》以及台湾地区民法中,却均未见有规定。
首先,由于“约定检验期间”的置入,《合同法》中的检验通知制度,实际上是以有无约定检验期间为标准,而划分成二元结构。如此独树一帜的结构设置,优点是条理分明,有无约定检验期限两种情形前后分列,一望自明,显示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崇,并可以提示当事人重视检验期间的约定,发挥法律规范的行为指引功能。但是,这种先行规定约定检验期间情形的二元结构,将约定检验期间一再地突出前置于检验和通知规则中,挤占了先行确立检验和通知行为一般规则和标准的空间,割裂了检验规则和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内在联系,导致检验规则对瑕疵通知期间的基准功能无法实现。
其次,法律规范应当遵循无矛盾、不赘言、完整性和体系化的要求,其中不赘言就是要求法律不说多余的话。〔48〕参见 [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而《合同法》第157条第一句和第158条第1款关于约定检验期间的规定,实质上就属于多余的话。因为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本就已经决定了当事人约定在不违背效力性强制规定情况下的优先适用性。如此反复地于该等法条中突出和强调约定检验期间的优先地位,的确有些多余。即便需要明确约定检验期间和通知期间的重要性,实现法律的行为指引功能,也完全可以在先行确定检验和通知的一般规则后,再对其做出简要的表述,比如“买卖双方约定检验期间的,以其约定为准”等。
再次,这种二元式划分导致检验通知制度,在检验和通知期间的规则方面产生了体系上的矛盾。如前所述,第157条第一句和第158条第1款第一句中相同的“约定检验期间”表述,显然是包括了买受人进行标的物检验和瑕疵通知的时间,即在有约定检验期间的情形下检验期间和瑕疵通知期间是二合一的。但是,根据第157条第二句以及第158条第2款关于无约定检验期间情形的规定,“及时”的检验期间与“合理”的通知期间却又是两分的。
最后,《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将瑕疵通知期间并入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间,不符合检验期间与通知期间相区分的比较法经验,且有以立法方式强行界定和扩张当事人“检验期间”约定合意之嫌疑,明显缺乏正当性。按照《买卖合同法解释》起草者的说明,该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的主旨在于“规制过短的检验期间,以保护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法权利”。〔49〕同前注 〔1〕,第325页。然而,《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通过对当事人合意的干预,将瑕疵通知期间强行并入约定检验期间之中,恰恰是导致所谓“约定检验期间过短”的原因之一。《买卖合同法解释》第18条第1款,又试图通过授权法官个案衡量并排除当事人约定部分适用的方式,缓解《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强行干预当事人约定所导致的“约定检验期间过短”和买卖双方利益失衡,同样缺乏正当性。而且,授权法官个案衡量“约定检验期间”是否“过短”和能否适用,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确定性。
但是,遗憾的是,《民法典》第620条和第621条在检验通知制度上继续沿用了上述以有无约定检验期间为标准划分的二元结构。
结 语
《民法典》的编纂完成和表决通过,表明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化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内容的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标的物瑕疵通知期间规则,虽然只是 《民法典》合同编典型合同之买卖合同法中一个细小而具体的规则,但是其攸关买受人瑕疵救济权利之得失,应当充分研讨梳理并加以完善优化。而要构建我国更为完善合理的瑕疵通知期间规则,就应当确立检验行为的一般标准,区分检验期间和通知期间,以实现标的物检验对瑕疵通知期间规则设定的基准功能。在瑕疵通知期间规则的内部架构中,买受人应当于发现或理应发现瑕疵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这是瑕疵通知期间的一般规则;对经检验不能发现而于日后发现的瑕疵,买受人应当于标的物交付后最迟两年内通知出卖人,该等两年期间规则与合理期间规则结合适用;标的物法定或约定的质量保证期超过两年的,应当适用质量保证期而非两年期间。买卖双方约定瑕疵通知期间的,以其约定为准,但是缩短或排除前述两年期间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