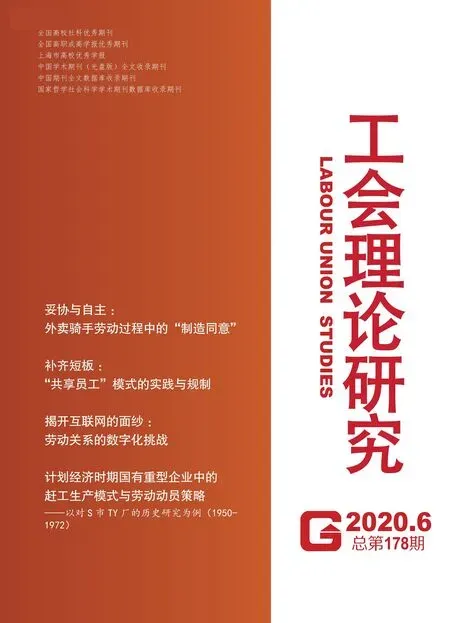妥协与自主: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制造同意”
沈锦浩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为了有效阻断疫情,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对小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区域设卡、交通中断,探亲访友、聚餐出行等活动一律取消,几乎所有城市都处于停摆状态。在疫情当中,广大外卖骑手勇担重任,在武汉市、湖北省和全国各地承担部分医疗物资、医生餐食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物品的配送工作,成为“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摆渡人”。据某外卖平台统计,在武汉封城的76天时间里,该平台的骑手完成订单396万单,送出超过400万个口罩;整个疫情期间,该平台的骑手完成5622万送往全国医院的订单,为援鄂医疗队送餐超9万份。①美团配送:《疫情中的即时配送——2020美团配送抗击新冠疫情行动报告》,http://www.chinawuliu.com.cn/upload/resources/file/2020/05/19/46557.pdf,2020-05-19.他们迎风雨,冒风险,送药送餐送货,有力保障了医疗救治和市民生活,是疫情下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和平安守护者。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研究团队:《“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预印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据业内统计,中国现有近700万名外卖骑手,而且数字仍在持续增长。某外卖平台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5年,该外卖平台骑手人数仅为1.5万人,但到了2018年,仅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该报告还显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82%的骑手为80后和90后。①美团点评研究院:《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5-04/8506105.shtml,2018-05-04.从以上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外卖骑手已经成为许多青年农民工就业的新选择。各类新闻媒体关于“年轻人为何宁送外卖不去工厂”的报道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社会事实。比如,《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宁送外卖不去工厂,年轻人“抛弃”的究竟是什么》一文深刻分析了青年农民工逃离工厂转向外卖行业这一现象。②夏熊飞:《宁送外卖不去工厂,年轻人“抛弃”的究竟是什么》,http://zqb.cyol.com/html/2019-02/26/nw.D110000zgqnb_20190226_1-02.htm,2019-02-26.可以说,青年农民工正由原来的流水线工人逐渐转向“车轮之上的工人”。③沈锦浩:《车轮之上的青年农民工: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载《青年发展论坛》,2019年第5期,第69-76页。
一方面是骑手从业人数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骑手劳动境遇的不容乐观。作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悄然兴起的新职业,骑手还面临着诸多劳动问题。一是受到多元主体的强控制。平台、代理商④代理商就是加盟商,也就是劳务外包公司,外卖平台把区域业务分给代理商,然后代理商自行招募骑手。和消费者对骑手劳动过程的三层监控形成“闭环”,并利用平台技术的远程操作,实行“超视距管理”。⑤赵璐、刘能:《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载《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26-37页。二是劳动关系的弱契约性。平台通过轻资产战略逐渐将劳动力外包,骑手与平台的关系逐渐从正式劳动合同关系转变为通过代理商的劳务合作关系,以及众包模式下的非正式劳动关系,骑手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⑥赵璐、刘能:《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载《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26-37页。三是以罚代管现象突出。当前外卖行业中的奖惩制度严重失调,罚多奖少,超时、差评罚款极为严苛,一次罚款少则等于一天白干,多则等于一周白干。⑦周子凡:《“互联网+”时代外卖骑手薪酬探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96-104页。四是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骑手这一职业处于社会鄙视链的底端,城市居民在与他们互动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⑧邢海燕、黄爱玲:《上海外卖“骑手”个体化进程的民族志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2期,第73-79页。作为外卖经济的担纲者和外卖配送的实践者,骑手对上述劳动问题并非没有切身体会。相反,许多研究表明,骑手对于自身的劳动境遇有着一肚子的苦水。那么,骑手明明对外卖行业有诸多不满,并且有切身体会,为什么还愿意继续从事这一行业呢?或者说,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同意从何而来呢?这将是本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从总体上来看,物流从业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物流业的现有研究更多的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提高配送效率、如何优化配送模式等等。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并对该群体做了更细化的研究,其中快递员成为新的关注对象。201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工部组织开展对快递员工作状态和生活情境的大型调查。调查发现快递员忙碌辛苦,经常超时工作,导致其难以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保持平衡。①周占杰、朱晓宇、张肖婧:《快递员的工作激情与工作-家庭平衡关系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第20-27页。不过,调查同样发现快递员的工作满意度仍处于中等范围,只是年轻、未婚、从业时间短、收入低的快递员工作满意度更低一些。②何玲:《城市快递员离职现象探究——基于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的关系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19页。
伴随着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作为传统快递职业的新分支,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学界对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及其权益保障研究。张瑞涵通过对武汉市多位骑手、商家和顾客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结合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理论审查,提出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处于受劳动法“完全保护”的劳动关系和“完全不保护”的劳务关系中间的灰色地带。③张瑞涵:《互联网餐饮行业中送餐员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2期,第36-42页。谭书卿则认为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具备了一定的劳动关系的认定特征,但从劳动关系认定的严格性出发以及基于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要求,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劳动关系。④谭书卿:《分享经济下用工关系法律界定与制度探索——以外卖配送行业为视角》,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70-78页。闫冬关注的是骑手的劳动报酬保护问题。⑤闫冬:《平台用工劳动报酬保护研究:以外卖骑手为样本》,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年第2期,第114-123页。他认为以骑手为代表的平台用工劳动报酬仍属工资的范畴,传统劳动法的工资保护机制亦是平台用工的现实需要,与劳动关系认定不存在互相依存或冲突关系,应跳出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的思维,将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用于对平台用工劳动报酬的保护。
另一类是社会学界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骑手展开的多维度讨论。赵莉从生活适应、职业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等四个方面来考察骑手的社会适应水平,其研究结果表明骑手的总体社会适应状况较差。⑥赵莉、王蜜:《城市新兴职业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以北京外卖骑手为例》,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50-57页。李升等人关注于骑手的劳动状况和劳动心态,其研究发现骑手的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报酬不高、劳动保障不完善,而且他们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自愿”增加劳动强度。⑦李升、王晓宣、杨昊、许家庚:《利益诉求的表达与消解:一项关于“外卖小哥”劳动过程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99-108页。张玉璞关注的是骑手移动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其研究发现无论是社交导向型,还是工作导向型移动媒体使用,都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黏结型社会资本,但都不能正向预测桥接型社会资本。①张玉璞:《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上海外卖骑手移动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年第1期,第167-198页。冯向楠和詹婧通过对骑手的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强化了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管控,但骑手仍然通过运用多种策略争取劳动的自主性。②冯向楠、詹婧:《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研究——以平台外卖骑手为例》,载《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第61-83页。与之类似,孙萍考察了骑手劳动中的算法运用,发现骑手并非仅仅是受制于“数字全景监狱”的被动实体,相反,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有机算法”。③Ping S. “Your order,their labor: 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in everyday laboring 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9,4(2),pp.1-16.
不可否认,辨别或是确认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对于其权益保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并非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问题,而是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考虑更多社会因素。相比较而言,社会学者的研究更为多元,关注到骑手的方方面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骑手的工作与生活图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骑手独特的劳动过程以及其中新的控制方式和回应方式,但并未对其中的同意产生过程加以解释。
在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布若威(Burawoy)的突出贡献是将工人的主体性带回劳动过程之中。布若威认为,劳动过程研究应当去考察工人的体验,即工人对剥削的“同意”。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工会力量的发展来进行自我改良,缓和阶级矛盾。④Burawoy, Michael.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 Verso,1985,pp. 123-126.然而,将布若威的制造同意理论置于中国本土情境下考察可以发现,虽然“赶工游戏”⑤赶工游戏指的是工人自发在工作中寻找应对严酷工作条件的方式,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游戏的成分,从而使得无聊的工作被重新注入意义。已被各行各业的资本运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但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⑥内部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职位等级结构和晋升机制,通过调配工人的岗位来实现流动,进而控制工人;内部国家指的是企业内部的集体谈判制度和申诉机构,主要是工会。在中国的多数企业中即使存在,也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能找到一份收入满意的工作已是幸事,自然不会奢求在企业中的晋升。同时,广大农民工游离于中国的工会组织之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到外卖行业,骑手的“同意”到底从何而来呢?本文认为在考察“同意”的产生时,既应当注意工作本身的特点,又应当注意工人所处的整体结构。笔者曾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正式入职某外卖平台在上海市的S站点,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亲自从事外卖配送工作。通过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笔者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本文将立足于田野调查资料并结合相关统计资料,从骑手的具体劳动过程及其所面临的结构约束入手,也可以说是从“同意”的主动认可和被动接受两个层面来对“同意”的制造机制加以考察。
三、被动接受的“同意”:结构约束与常态的妥协
布若威认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的不断完善,加上工厂内部“赶工游戏”的意识形态力量,共同塑造了工人的“同意”。虽然布若威并未在书中明说,但其潜在的意思其实是认为工人的“同意”主要是由工人主动形成的。然而,在田野中,笔者发现外卖骑手的“同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工人在结构约束下的被动接受。外卖作为一个以男性青年农民工为主的行业,这些骑手其实都承受着来自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性别关系结构的三重约束,使其不得不妥协于这份工作。
(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工”
报告显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82%的骑手为80后和90后。①美团点评研究院:《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5-04/8506105.shtml,2018-05-04.这说明骑手本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虽然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已有诸多讨论,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农民工在制度上的次等身份始终没能改变。
除非感受到某些可以称之为吸引力的因素,很少人会将主动迁移视为对压力的反应。②Kosinski L, Prothero R.M. “People on the move: Studies on internal migration”,In Kosinski L, Prothero R.M,The Study of Migration,London:Methuen, 1975,pp.1-38.外卖骑手只是数以千万计的城乡移民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之所以远离家乡来到城市谋生,不仅仅是因为参与农村经济活动所获收益难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和更多的人生可能。许多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想趁着年轻出来打拼一下,就算不能改变人生的命运,也能多赚点钱回去。
皮奥里曾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前者具有工资高、就业稳定、工作环境良好、管理与晋升机制规范等特征,后者则相反。③Piore M J. “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In Beer S.H,Barringer R.E, The state and the poor,Cambridge,MA:Winthrop Publishers, 1970,pp.55-59.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以及薄弱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毫无疑问,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因此,服务员、建筑工人或是工厂流水线工人等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流行业。骑手WC曾经在一家毛巾厂工作过一年,枯燥的工作内容、固定的工资收入以及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得那段时间成为他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因此,即使他现在做骑手以后经常受到风吹日晒雨淋,他还是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城乡之间的对立不仅在制度上被建构,而且为农民工所切身感受。带着农村“印记”出来的农民工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不断地“用脚投票”,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业数量是不少,但基本都是密集制造业或低端服务业岗位。他们对自己所经受的不平等待遇早就习以为常,所以他们追求的只是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并且用自己的汗水换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收入,以便留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们能生存得更好一点。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外卖骑手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也是平台经济带动出现的新工作机会之一。
(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体力劳动阶层”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之下,学者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有所不同。其中,职业地位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相对简单的划分依据为学界所认可。李路路等人曾将职业阶层结构粗略划分为高级非体力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①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4页。按照其划分来看,无论是将农民工归为农民身份,还是工人身份,他们都属于“体力劳动阶层”。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这些农民工也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体力劳动阶层”。在问到从事过的工作时,“什么都干过”是骑手们经常说的话。
虽然骑手们“什么都干过”,但是干来干去,干的都是“体力活”。这是因为这些骑手与大多数农民工一样,学历不高、缺少技术,可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对此,骑手GBQ总结得特别好:“我就是没什么学历,也没什么本事,所以只能跑外卖!像我们这样四五十岁的人,做什么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什么都做不了的!”
频繁跳槽几乎是所有农民工都有过的经历,他们的初衷是通过重返劳动力市场,谋得职位更高且待遇更优越的工作。对于工厂体制中的底层农民工来说,工资收入与等级结构往往是相关联的,要想实现工资收入的提升,需要通过晋升机制提升自我在工厂之中的等级位置。但现实往往不如人所愿,无论是从事何种工作,农民工始终被安置在工厂等级结构中的最底层位置,并且受到向上流动中“玻璃天花板”的限制。
在外卖行业中,工资收入与等级结构并不完全相关,多数骑手也没有晋升的想法。这是因为外卖平台对代理商和站点采取KPI考核机制,站长和助理的工资都是根据站点每个月的星级评定结果来发放。达到五星的各项考核指标,站长的工资就有一万五千多,基本相当于站点骑手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可要是只达到一星的考核要求,站长的工资才三千块钱左右,远远低于骑手正常跑单的平均收入。站长及助理收入的不稳定使得多数骑手并不渴望晋升,而是只想着尽量多跑单、多挣钱。
在“体力劳动阶层”这一身份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工追求的只是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相对可观的工资收入。虽然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份前途光明的工作,可对于吃过太多苦的农民工来说,已经是一份令人相对满意的工作了。
(三)性别关系结构中的“男性责任”
报告显示,90%的骑手为男性。②美团点评研究院:《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5-04/8506105.shtml,2018-05-04.这充分说明骑手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杜平指出,当我们在研究男性农民工时,往往只关注到其农民工身份和社会底层位置,而没有关注到他们作为男性所承受的来自性别结构的压迫与束缚,以及在认同和塑造自我性别身份过程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这其实是性别研究与农民工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男性盲视”。③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如果从性别关系结构来考察骑手这一职业时,可以发现传统家庭文化中赋予男性气概的“责任意识”支撑着骑手们的繁重劳动。①赵璐、刘能:《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载《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26-37页。何明洁曾提出“性别化年龄”概念来概括“社会文化传统对男女两性给予的与年龄和生命周期相关的、男女有别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②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9-176页。将这一概念用来检视外卖这一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可以发现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以及造成的男性家庭责任的差异。
“建房子”和“娶媳妇”是农村男性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两宗大事,也是农村社会中影响男性个人声望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成就。③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随着农村“婚姻挤压”现象的愈演愈烈,“建房子”又成为“娶媳妇”的前提条件,再加上高额的聘礼和婚礼相关费用,使得大量农村青年不得不通过外出打工来积累资金。在S站里,挣够钱回家买车、买完车回来继续跑单、再多挣点钱回家相亲几乎是不断重复上演的连续画面。对于许多农村男青年来说,娶妻生子既是整个家庭的期待,也是自己的阶段性使命。
如果说“建房子”和“娶媳妇”是未婚男青年的头等大事,那对已婚男青年来说,“挣钱养家”又是成家后的新压力。正如杰华所指出的那样,迁移对于男性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努力承担养家糊口责任的途径,而女性在这方面不用承担太多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她们能够在迁移过程中相对“自由”地追求更多的个人目标。④Tamara J.“Finding a place: negotiation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Beijing”,Critical Asian Studies, 2005,37(1),pp.51–74.在外卖行业中,这种背负着沉重家庭责任的男性十分容易辨别,因为他们往往是骑手中单量最多的那部分人,也往往是工作时间最长的那部分人。
总之,在田野中可以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骑手有着不同的压力:年龄较长的骑手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只能拼命加班争取“超额”;年龄较小的骑手渴望着成家立业,也在努力工作以积累资金。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骑手大军,“痛苦并快乐地”坚持着。从家庭责任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性别分工中的男性担当。正是由于“男性责任”的存在,骑手才会愿意接受这份遭人轻视的工作。在访谈中,骑手CQ的话说出了许多骑手的心声:“反正哪样有前途,我就往哪样发展,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总要养活一家人!”
四、主动认可的“同意”:主体能动与适度的自主
以男性青年农民工为主的外卖骑手虽然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性别关系结构的约束,但“同意”的产生必然不可能仅仅来源于被动接受,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个主体能动的选择过程,因为他们始终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如果本身没有对工作的主动认可,他们的劳动也不会持久。在田野中,笔者发现骑手的主动认可主要来自于外卖配送工作的工作特点,这具体体现在外卖配送中的灵活性、公平性和透明性。
(一)工作本身的灵活性
外卖骑手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工作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工作模式的灵活性和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工作模式之所以是灵活的,是因为平台采用的是“专送+众包”的模式,骑手们可以根据个人情况从中任意选择。专送模式主要由系统派单,受代理商及站点管理,且要求骑手只能在同一平台专职从事配送工作。众包模式主要靠自己抢单,在正常跑单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受到平台的管理。其出发点是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骑手既可以专职,也可以兼职,既可以在同一平台接单,也可以在多个平台接单。工作安排之所以是灵活的,是因为平台工作是以“订单”的方式分配任务,骑手的工作流程大致可分为接单、到店取餐、送单三步,平均每完成1个订单的时间大约在15-20分钟。众包骑手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上线开始接单或是下线停止接单,专送骑手虽然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配送区域,但是在多数时段依旧可以通过短暂下线自我安排时间。
事实上,大多数骑手选择这份工作也正是看重它的灵活性。报告显示,有42%的骑手认为,高收入比稳定更重要;上班时间灵活是他们选择做骑手最重要的原因(32%)。①美团点评研究院:《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5-04/8506105.shtml,2018-05-04.笔者对多位骑手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统计结果。比如骑手WX就说道:“跑外卖嘛!挣多挣少都在你自己……这个就看每个人的态度了。”
总的来说,骑手们选择外卖行业的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有些骑手选择跑专送,是因为专送订单的单价高且无须抢单。有些骑手选择全职跑众包,是因为众包主要依靠自己抢单,只要自己手速够快、路线够熟,就可以挣得更多。有些骑手选择兼职众包,是因为本身已有工作,跑众包只是在闲暇时挣外快的手段。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平台工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骑手的需求。不管骑手是选择专送模式或是众包模式,也不管他们成为骑手的动机是否有所差异,工作本身的灵活性为骑手产生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准入/退出机制的公平性
平台经济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经济,②闻效仪:《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6522,2018-12-10.并无过多的学历、技术要求,这就决定了互联网平台用工中准入/退出机制的公平性。准入机制的公平性首先体现在外卖骑手招聘过程中的低门槛要求。基本上只要是拥有健康证、会开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的中青年都可以轻松成为骑手。
其次,体现在骑手培训的低形式化。由于平台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传统雇佣关系中的正规培训也就不再需要,不管是专送骑手还是众包骑手基本都是如此。对于专送骑手来说,入职后组长仅会花半天左右的时间带其熟悉主要商家和App操作流程,之后就是骑手自己跑单。虽然专送骑手每天都会开晨会,但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走个形式。对于众包骑手来说,只需下载App,上传个人用户资料和健康证,自配电动车,参与线上培训并通过考试(仅20道选择题,可无限答题)即可上岗。
再次,体现在计酬机制的无差别性。“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一直是平台和代理商的宣传口号。在专送模式下,每单的单价是相对固定的,即使当单量达到相应门槛后,单价会有所增长,可单量门槛对站点的所有骑手都是统一的,因而骑手的收入主要还是取决于单量。在众包模式下,每单的配送费都是由平台通过大数据计算而定,不会因骑手个人发生变化,因而骑手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抢到订单的配送费和数量。基本工资是如此,活动奖励也是如此。
此外,退出机制同样具有公平性。对于专送骑手来说,在无不良记录的情况下,要想离职只需要提前一个月在“钉钉”上打报告,经过站长审批同意,代理商基本都会同意,工资则照常结算。对于众包骑手来说,根本没有辞职的手续,只需要不再上线或是卸载App即可。总体而言,准入/退出机制的公平性使得骑手对平台工作产生了主动的认可。
(三)劳动报酬的透明性
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欠薪问题,长期以来屡遭社会诟病,成为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①于建嵘:《农民工欠薪难题何解》,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19期,第73页。农民工付出辛苦劳动却拿不到报酬,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②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2017-04-28.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不怕辛苦劳动,就怕付出得不到回报。拖欠工资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计,成为农民工最为忧心的问题之一。外卖骑手则没有这样的担心。事实上,劳动报酬的透明性也是吸引骑手加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是专送骑手还是众包骑手,基本配送费、补贴、奖励都是公开的。专送骑手的基本配送费和单量门槛以及时段补贴通常会在入职前讲明,众包骑手的基本配送费和各项补贴都会在系统发布订单时标明,只有价格符合心理预期,骑手才会抢单。针对两者的奖励活动,两者都能在各自对应的App推送消息中看到,平台对这一信息是完全公开的。虽然骑手有时候会嫌弃订单的配送费太低或是奖励的单量门槛要求太高,但是公开的计算规则使骑手首先产生了“多劳多得”的满意感。
计算规则的公开是透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单量乃至收入在App上的直观变化则是透明度更直接的表现形式。众包骑手的收入结算周期是以天为单位,通常情况下当天的配送费(包括补贴)在第二天凌晨就会发放至骑手的账户,相比于按周结算或是按月结算,这种结算方式使得骑手更安心。用骑手WDG的话来说就是,“我每天挣多少钱都是看得见的!”专送骑手的收入结算周期虽然是以月为单位,但是骑手在第二天就能够看到昨天的单量以及本月的累计单量,这样对个人的收入能有基本的预期,而且万一平台统计有误时也能及时发现。
在传统用工模式中,工作量统计结果不及时公开以及下月发放工资的形式一直为工人所诟病。对骑手来说,透明的计算规则和即时可见的劳动报酬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双方的信任度。这就使得骑手们更加自觉、快速地对平台规则产生了好感,也更加深了他们对外卖配送工作的主动认可。
五、结论与讨论
布若威《制造同意》一书的重要理论发现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通过意识形态支配实现的。在书中,布若威详细分析了制造同意的三大机制: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内部国家。①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页。然而,在本文研究的外卖行业中,赶工游戏的效用固然存在,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处于明显的缺位状态,他们的同意更多来自结构约束下的自助意识和工作本身的自主意识。这两种意识混合生产出了外卖骑手的劳资共识。
外卖骑手是一个以男性青年农民工为主的劳动群体,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他们倾向于通过进城打工来改善生活,社会阶层结构使得他们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得收入,性别关系结构使得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面对长期存在的三重结构约束,骑手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不敢奢求国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福利保障,而是将希望寄于自己身上。正如笔者在田野中常常听到的:“不送外卖能干什么”“社保不一定有用”“总要养活一家人”。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反映了骑手的自助意识,即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结构约束与自助意识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如果说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是从正面推动了工人同意的生产,伴随着结构约束而生的自助意识则是从反面逼迫着工人不得不同意。
当然,外卖骑手的同意并非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其中也有着主动的认可。平台工作本身的灵活性、准入/退出机制的公平性以及劳动报酬的透明性使得骑手产生了一种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至少包括两种内涵:自由意识与纯劳动意识。自由意识指的是骑手通常认为送外卖想做就能做,不想做就能不做,可以拼命做,也可以轻松做,非常自由。骑手SY说道:“送外卖真的是自由,干了这行你就不想换了”。可见,自由意识的作用多么强大。纯劳动意识指的是劳动者卖的是具体化的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其直接表现是“多劳多得”意识。②谢国雄:《纯劳动:台湾劳动体制诸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116页。骑手的报酬主要来自一单一单配送费的累加,因而骑手们普遍认为送外卖是公平的、透明的,全凭个人努力,送得多就赚得多。自由意识与纯劳动意识共同构成的自主意识对骑手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产生了相对满意的感觉。总的来说,骑手劳动过程中的“同意”既有被动接受的成分,也有主动认可的成分,其中夹杂着自助意识和自主意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外卖骑手“同意”平台的劳动控制,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面临的诸多劳动问题。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外卖骑手的劳动境遇不容乐观。因此,如何有效保障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就政府而言,应当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卖骑手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就工会而言,应当扩大工会覆盖范围,努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积极推进集体协商制度,使工会成为外卖骑手愿意依靠的组织。就企业而言,应当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适当提升工资水平,使外卖骑手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就社会而言,应当培养公民平等意识,加强公民劳动教育,倡导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态度,让外卖骑手成为一份有尊严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