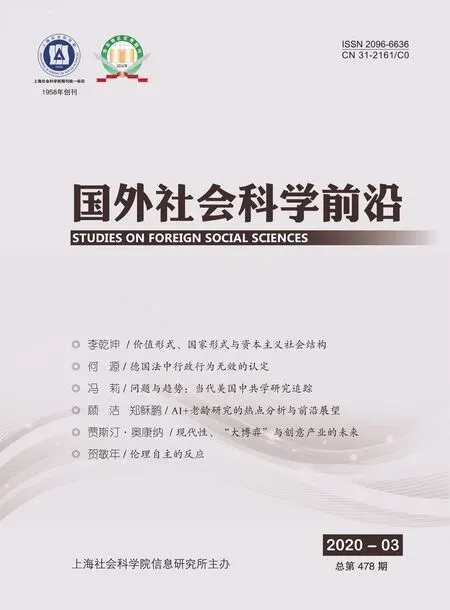医学话语、权力逻辑与治理机制
——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三维度 *
刘 黎
内容提要 |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是一种异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述自由、平等、所有权、身份等范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这也标志着福柯思想进程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再到“生命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转变。福柯从医学话语、权力逻辑与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来筹划其生命政治理论,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生命之间的隐蔽关系,也展现出了医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深度融合。这种聚焦于探讨政治权力技术与生命关系的话语体系已成为现代政治哲学、西方左翼激进思潮中的热议话题,为反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提供了异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模式。
福柯虽然没有创造“生命政治”概念,但是,他在不同的著作、讲座、访谈等场合针对这一议题的大量散论,却展现出了一条相对系统而又富有逻辑性、连续性的研究生命政治思想的线索,这让他在生命政治话语讨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解读有如下特征:第一,生命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领域具有广泛性,政治哲学、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相互交织,相互利用,尤其是医学与政治技术的相互渗透,从而改变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语境;第二,福柯摆脱了前期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的迷恋,执着于从其擅长的权力关系理论角度出发,来解剖生命与政治的关系,努力追问权力机制发生了何种深刻的变化,权力技术装置是如何运作于社会,运作于生命的;第三,生命政治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社会现象,通过仔细观察“不正常”领域所发生的事件,从而揭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邪恶本性。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进行追溯,会发现其中充斥着诸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反复性,这就是福柯的写作风格。对此,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我的想法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说,我的书就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如果我要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在开始写作之前的想法,我可能没有勇气开始。我要写一本书仅仅是因为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所思考的问题,我想要去思考的更多。”1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p.239-240.正是这些模糊性与不稳定性揭示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一、生命政治的医学话语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福柯将批判地矛头指向了传统医学知识,将医学话语置入政治哲学权力关系之中,试图展现医学、医疗手段、权力技术及社会管治模式等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从而质疑服务于个体身体健康的传统医学观。福柯生命政治范畴出现在医学语境中始于20 世纪70 年代。1974 年10 月,福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州立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生物医学中心,举行了三场论社会医学的讲座,主题分别为“医学危机或反医学危机?”、“社会医学的诞生”1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p.134-156.、“现代技术纳入医院”2Jeremy W.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eds.), Space,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141-151.。 虽然,福柯对医学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其权力理论那样广泛与细致,但这是其生命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后来成为罗伯特·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卡洛斯·诺瓦斯(Carlos Novas)等人的核心研究领域。
在讲座“医学危机或反医学危机?”中,福柯重点谈论了18 世纪以来现代医学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医学权威的出现不再局限在知识权威之中,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权威;医学干预不再局限在疾病与病人意愿之中,而更多地转向了环境因素,医学干预正在逐渐转变成一种社会干涉;集体医疗场所的引进,不断引入先进的医学技术知识与装备;医学管理体制不断革新。3Michel Foucault, The Crisis of Medicine or the Crisis of Antimedicine? Translated by Edgar C.Knowlton, Jr, William J.King and Clare O’Farrell, Foucault Studies, No.1, 2004, p.13.医学不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紧密结合,医学领域也不再只是关乎疾病的研究或者病人的治愈问题,而是在社会之中无限地拓展领域,将其纳入自身的管辖范围之内。因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未定义的医学化领域,进而成为政治斗争、政治权力技术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下,残忍的是,当我们想提到医学领域以外的领域时,我们发现它已经被医学化了。当一个人想要反对医学的不足,它的缺点及其有害影响时,这是用一个更完整、更精炼和广泛的医学知识来完成的、实现的。”4Michel Foucault, The Crisis of Medicine or the Crisis of Antimedicine? Translated by Edgar C.Knowlton, Jr, William J.King and Clare O’Farrell, Foucault Studies, No.1, 2004, p.13.医学化无处不在。虽然在这次讲座中,福柯并没有提及生命政治,但是他对医学史发展问题的描述,尤其是对医学治疗目标的转移的分析,即从对个人清洁问题的关注转向个人及集体健康的关注,以及最后将人体生物性生命问题直接纳入考量范围,这些都体现了生物性的生命成为了不只是医学关注的核心,也成为了政治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信号,这意味着人的生命在现代社会之中面临着危机。
福柯在讲座“社会医学的诞生”中,更加详细地展现了现代医学危机的问题,并且第一次提出了“生命政治”术语。“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是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而且这也可以在身体之中以及用身体来实现社会的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就是生命政治,即生物性的身体、躯体、肉体最为重要。身体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的策略。”5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137.这就是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着重于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生命的考察,进而将生命政治的背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制度之中,以及关注医学社会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现代医学是一种以社会机体的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医学”,6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136.福柯从不同国家的医学表现出发重现了这种转变:其一是,出现在18 世纪德国的“国家医学”,即“正式的医学知识的组织,医疗职业的标准化,医生从属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最后,把不同类型的医生整合成产生一系列全新的受国家控制的医疗组织,这些特点可以被称为‘国家医学’。”1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141.在这里,国家充当了“医学警察”的角色。其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医学。法国的城市医学对象不是以国家结构为基础,而是与城市的扩张相结合。它的主要目标是对城市区域内的拥堵、无序和危险区域进行科学分析,建立和控制水和空气的良好循环,最后组织好城市格局与水流的分布与排列。2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p.142-151.其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劳动力医学。这种社会医学类型的对象是劳动力、工人或者穷人,因为穷人在19 世纪慢慢体现出了一种医学危险,他们威胁着上层阶级的生活与健康。同时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由于他们比较熟悉城市的基本功能,又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此,需要对他们实施医疗控制。两年以后,福柯再一次表达了对18 世纪医学的深度思考,这一次他不再强调现代医学是一种社会医学,而是认为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疾病分类政治学的时代。3汪民安主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46 页。
福柯在讲座“现代技术纳入医院”中,仔细考察了18 世纪末医院开始被视为一种治疗工具而出现的情景,他发现从18 世纪末开始医院展开了一系列的新型实践活动(调查医院、对医院进行系统与比较观察),正是这些崭新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医学研究理论充分地表现出医院与现代技术的融合。福柯注意到18 世纪前医院最初是作为对穷人的援助机构(分离与排斥机构)而运行于社会生活,它最初的基本功能与其说是治病救人,还不如说是一种执行临终关怀的慈善机构,其目标是使那些患者获得灵魂救赎而不是使其免受疾病的威胁。在这个时期,他发现医学与医院是两个与众不同而又相互分离的领域,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医学的概念。直到18 世纪末,医院空间在其目的与效果方面开始被医学化,随着规训权力技术的不断涌入,使得医院无论是在其位置选择以及内部空间分配方面,都注入了广泛的医学化知识。与此同时,医生的权力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强化。除此之外,医生会系统性地组织记录病人发生的任何情况,这使得病人完全处在医生的监控之下。因此,在医院转型过程中,个体逐渐转变为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干预对象。
很显然,福柯在1974 年引入的“生命政治”术语,重点不在于传达生命政治思想,毕竟在这三次讲座中,福柯只提到了一次生命政治,相比之下,此时的福柯更加关注的是医学问题。然而,对于医学问题的探讨,他并不想提出反医学或者抵抗的形式,而是要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阴险面。但是,生命政治出现在医学话语背景之中,对于其之后相对系统性地阐述生命政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纵观福柯已出版的著作或讲座集,谈论医学问题的资料是相对比较多的,但是把医学主题与生命政治结合的文献则相对较少。此时,医学话语的建构成为了生命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他对医学的科学性与效应、医学领域的拓展以及种族主义政策的分析,为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与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医学与政治权力技术的结合,使得医学权威逐渐在国家、城市、人口中凸显出绝对的至高性,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考虑,使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延伸到都市空间、环境保护等领域。最后,医学内容主要关注的是个体或集体的健康与卫生状况,这种视角使得医学对身体的关注不断地微观化与细化,直至将目光直接转向人的纯粹的生物性存在,甚至是人体的基因组成状况。但是,福柯第一次表达“生命政治”概念,与其后对生命政治理论的阐发有很大的差异性,最为明显的就是,医学话语逐渐地处于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权力话语的到来,生命政治理论的政治色彩愈加鲜明,从而向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发起挑战。
二、权力逻辑的辩证转化
福柯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追随尼采的步伐转向权力谱系学研究,从而逐渐偏离了60 年代思考现代知识体系的考古学研究,这一转变旨在探索知识和权力关系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隐藏的重要变化,即权力技术在现代性中的运作过程与实质内涵。他首先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和“旧制度”时期主权范畴的历史分析,深刻地批判了作用于法律主体的否定性的、消极的传统主权权力技术模式。然而,当社会发展进入现代性之后,福柯认为,我们必须从主权者的残暴统治权中抽离出来,必须在具有压迫性和镇压性的权力效应中思索权力的生产性与积极性。原来拥有对被统治者绝对至高性的主权权力,随即被聚焦于个体肉体的规训权力技术所取代,这种个体化的权力技术试图在纪律、标准、规范等制度下塑造个体形象与功能,从而使之成为驯服的肉体。而在生命政治时代,权力技术既不是作用于法律主体,也不是直接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整体意义上的人口,这是以确保人口生命安全与健康为首要目标的生命权力。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技术既是生命政治治理的权力运作机制,也是理解与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崭新视角。
从一开始,福柯就强调要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权力关系的“司法—制度”模式,即“一种由法律理论家和君主制所描绘的权力—法律、权力—君权的形象”。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59 页。这种权力形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古典时期国王的统治权,即王权或主权者的权力,它既具备法律价值又体现政治功能。比如,统治者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威,维护统治地位,往往以采取暴力、血腥的酷刑方式来告诫民众,违犯君权,就是迈向死亡。统治者用这种惨无人道、极其严苛的统治方式,不仅宣告了统治者地位的至高无上性,也让违反统治策略的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这也震慑了其他民众而使其能安分、老实地臣服于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从而维护了统治秩序,保障了政权的稳定性。很显然,在这里,权力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大行其道,并以维护统治者的最高权威为最终目的,它的特点是君主权威拥有绝对的至上性,甚至拥有绝对的生杀特权。因此,“这种权力本质是一种控制权:控制事物,时间,身体,最终是生命本身。它在为了抑制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8, p.136.福柯拒绝的正是这种具有特权性质的统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的“利维坦”模式,宣告要“砍去国王的脑袋”,对权力概念与理论进行重新诠释与说明。
总之,他认为“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3[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25 页。因此,他转向了历史性地分析权力关系的模式,这种权力操作的特点是:首先,不再强调统治权威,不再注重直接而又残酷的压制与镇压等否定性关系,而是试图发现权力中可能隐含的生产性要素以及肯定性的东西;其次,摆脱以法律为模型的权力分析意味着权力要从法律与法则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不再局限于宏观政治性的大型国家制度与机构,而是转向对技术、规范和管理的描述;最后,权力不是局限在政治、经济或生产领域,权力没有中心,它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它是诸多力量关系的体现。
但是,这并不是说权力就没有压制性或否定性的因素,而只是分析路径的侧重点不一样。福柯认为,“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扣除’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只是用来激励、强化、控制、监督、优化和组织其下的各种力量的众多因素之一。这种权力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成长,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致力于去阻碍它们、让它们顺从或者摧毁它们。”1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8, p.136.这种管控生命的权力是由两极构成的,即针对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与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前者对应的权力形式是规训权力,后者对应的权力形式是生命权力,简而言之,就是“肉体—有机体—规训—制度系列与人口—生物学过程—监管机制—国家系列”。2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NewYork: Picador, 2003, p.250.
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从权力作用对象上来看,前者针对的是个体的肉体,肉体卷入政治领域之中,考虑的是肉体的效用性、生产性、可利用性及其所具备的力量,“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 年,第156 页。也就是说,尽可能地挖掘出个体的身体素质,以便更好地使其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进行打压、排斥或消灭。后者考量的是作为类别的、物种的人口的生命,生命进入历史,进入权力与知识技术,进入政治战略以及精打细算的领域之中,4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8, pp.141-142.其主要目标就是承担起生命繁荣发展的责任,不断地投资生命、扶植生命、维护生命、强化生命。
第二,从权力运作方式上来看,规训权力技术学“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 年,第242 页。具体体现为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三种模式的相互配合。通过相应的规则、标准、规范、制度、纪律来塑造与规训个体的肉体、意识、灵魂,从而使其适应规训社会的价值要求。而生命权力“完全不在细节的层面上考虑个人,相反,通过总体机制,来获得总体平衡化和有规律的状态;简单说就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6[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88 页。它把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量化,从而只考虑人口生物学层面的总体平衡,不关注个体的具体发展情况,只把握整体概率的发展方向,比如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人口的繁殖等。
第三,从权力运作的领域来看,规训权力的监控、操练、训练等具体方式需要依托物质性的封闭环境,比如家庭、医院、学校、工厂、军队等,这体现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之中。比如当某个城市发生瘟疫或者威胁全城安全的传染类疾病时,就需要对城市空间与区域进行隔离区分,形成封闭的、精致的、被割裂的空间。此时,任何人都有自己稳定的位置,任何细小的行为活动都会受到监视与记录,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的全景式监狱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象。而生命权力运用人口统计学等方法论学科,以及卫生防疫学、生命社会学或生命科学等科学知识,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总体性的调节与管控,以维护生理常数的稳定,消除威胁整体安全的因素。但是,它也包括国家层面以下的次国家制度,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与机构等。除此之外,它还要对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负责。虽然两种权力形式之间充满着差异,但是,这两种权力形式并不是一种正反题关系,而是既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连结,内在于在不同层面的权力机制之中,而它们两者之间的连接点、中介点就是性机制。因为,“一方面,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化惩戒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这个生物学过程不再与个人的肉体有关,而与构成人口的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1[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92 页。性负责着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协调作用,不仅对身体进行各种力量的调节与规范,还体现了对人口的大规模的统计评估,“性既是进入人身体生命的手段,与此同时,也是进入作为物种的生命的方式。”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8, p.146.
三、生命政治与治理机制的融合
在生命政治的时代,社会机体经历着从保护君主到保护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由此衍生出了国家种族主义的政治体制。然而,这只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生命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而另一个基本维度则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尤其是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之后,在西欧社会掀起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浪潮,涌现了一批福利国家,这一浪潮致使自由主义思想不断扩展蔓延,而这正是生命政治思想的又一本质特征。此时,福柯不再从权力形式的转变历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是从国家政权管理机制方面来剖析权力技术的变更,即国家主权的组织经历了从统治形态到治理模式的转变。国家统治权意味着臣民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统治,这是遵循传统的法律—制度模式,而治理机制则是通过考察人的生物性事实如何成为权力策略与技术的对象,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
福柯提出,“‘治理’并不只是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孩子的治理、灵魂的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家庭的治理和病人的治理。它覆盖的不仅是政治或经济屈从的合法构成形式,它还包括行为模式,这行为模式或多或少地被构思和考量,目的就是仿照他人的可能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是去对他人的行为可能性领域进行组织。”3汪民安主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29 页。福柯追溯了治理术历史的谱系学,他将这种对人行为的引导的治理模式追溯到了基督教以前,以及基督教时期东方的牧领权力。根据福柯的描述,牧领权力在早期有如下几种特点:牧领权力的运作不是在领土之上,而是施加在复杂的羊群身上;羊群的聚集需要牧羊人的指导,牧羊人在放牧过程中承担着聚合羊群的任务;牧羊人需要寻求更好的土地、更充足的食物,让羊群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到了基督教时期,牧领制度变得更加复杂与细致,比如牧羊人要对每只羊的各种行为进行记录,羊群必须服从牧羊人的意志,牧羊人必须形成对每只羊的独特认知,每只羊要以克己的方式存活于现世。从表面上看,前基督教与基督教时期的牧领权力,是为了整个羊群的发展,但正是这种献身与关照让羊群缺失了自我,这可能使羊群处于危险境地。福柯提醒,如果我们的社会“将这两种游戏,即城邦—公民游戏和牧人—羊群游戏结合到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中,结果它就真正变成了恶魔般的社会”。1汪民安主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333 页。
随着现代化阶段的到来,这种指向灵魂救赎、服从真理、充满目的因和人类中心论的牧领权力逐渐被另一主题——国家理性所取代。国家理性在政治权力之中运作的机器是对外的外交(军事部署)与对内的治安,这两套权力装置通过在力量场域之中进行操纵、分配、重建诸多力量关系,来保护与维持国家的发展。前者体现的是军事外交力量的目标筹划与特殊运用,旨在宏观层面上维持各国之间的平衡与均势,缓和冲突与矛盾,以便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与国际局势,避免霸权国家在欧洲的产生。后者则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发展秩序与情况,旨在维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主要包括:掌握人口数量,尽可能让人口数量达到最大值;负责提供人口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关注人口的健康问题等。治安是通过让人们生存的更舒适、更便利、更安全,以体现国家权威而使用的一整套干预手段与方法。与之前的牧领权力相比,治安的目标更加明确,直接把国家强弱的问题锁定在人口要素上。此时,基于国家理性的治理模式虽然把人口与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模式并没有体现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此后,国家治理模式渐渐超越了国家理性,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律来实现自我限制的目标,从而进入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阶段。
福柯认为,“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了”。2[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9 页。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将自由作为政治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经济理论,更是一种对人类行为与实践进行治理的模式。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不是去探寻如何更多地去治理,而是想要去解决如何不过度治理,如何做到有效治理,不再试图将国家的权力最大化,市场、效用与国家间的平衡问题构成了自由主义治理机制的基本特征。
二战之后,出现了德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不是去对国家干预的范围进行甄别,而是需要去“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3[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16 页。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话语之中来批判自由主义对人的治理。他认为,这种治理术对权力的行使不是在法律机制中,也不是在规训机制中展开,而是在安全机制中加以建构的。就安全机制来看,它倾向于向四处扩展,没有中心性;它针对的是整体现象;它会适时进行整顿和修正,防止危险的发生。在福柯看来,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正如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一样,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势不两立的竞争、斗争状态,也不是时间上的依次更迭、相继而来,三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因此,“我们绝对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规训社会代替了主权社会,然后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规训—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1[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91 页。
福柯在自由主义框架中论述生命政治思想之后,并没有对生命政治思想本身进行更加彻底地论述,至于为何会如此,学术界对此有很多猜想,比如阿甘本认为,“福柯的死致使其没办法再进一步发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开展关于它的研究”。2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之后他完全摆脱了对权力政治技术的继续讨论而转向了对自我的治理,即自我的技术。对此,他解释道:“我大概已经给予支配性的技术与权力的技术过多的强调了。现在我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对个体进行支配的技术问题,以及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技术问题。”3汪民安主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55 页。他认为,我们整个社会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都是处在权力的监控与笼罩之下,如果我们要抵制、反抗这种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压榨,就必须塑造出反抗权力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不是法律、政治上的主体,而是要诉诸于个体自身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对逃离权力控制的革命伦理主体的构想。
从整体上来看,福柯主要是沿着两种路径来建构生命政治理论,其一是权力形式的变化,即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再到生命权力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形态经历了由统治权社会、规训社会向安全社会的过渡;其二是国家管理形式的组织,即从权力集中于统治到权力撒播一切领域的治理模式的转变。福柯的分析启示我们:首先,虽然可以透过权力关系来解构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本质,但是这种批判无法提供具体的革命指导纲领;其次,福柯将生命范畴引入批判理论之中,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存状态这不失为一种新的批判方向。最后,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是政体展现政治权威的一种权力形式,而生命政治则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知识系统、一门艺术,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一区分蕴含着让生命政治理论得以丰富与延伸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