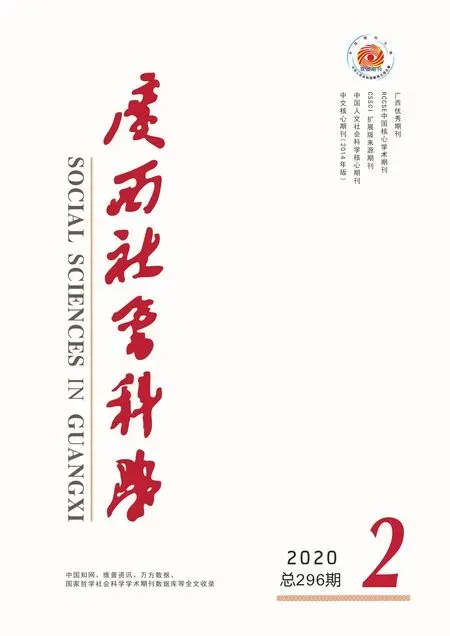从清华简《邦家之政》看早期儒家思想的分化与流变
——兼论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清华简第八辑中有《邦家之政》一篇,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假托孔子之口所作,其内容阐述了治国兴邦的为政观[1]。但作为孔子后学,其治国安邦的方法中,却充满了带有墨家色彩的观念,如崇尚节俭,选贤任能,均分财富等思想,均可以看到墨家思想的痕迹。这无疑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墨思想的相互交融。在以往的传世文献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儒墨思想的相互对抗,儒家抨击墨家,传世文献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并且自视甚高的孟子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自信来对抗杨朱、墨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家对于儒家的攻击也十分的尖锐,在传世的《墨子》一书中,《非乐》《非儒》两篇直指儒家思想的弊端。因此,后世学者更多地关注儒墨两家的相互冲突和激烈对抗,对儒墨两家相互交融的方面关注相对较少。
其实,到了战国中后期,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在相互的对抗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汲取他家之长处以为己用,因此无可避免地会与本流派之外的其他各家思想互相交融。而自家学说内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演变和分化,分化出观点不尽相同的学派分支。单以儒家而言,到了战国中期,其已经分化得极为明显,《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虽然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站在对儒家思想批判的立场上的,对“儒分为八”的论述不太可能客观公正,且后世对此也颇有争议,但儒家在战国中期有所分流,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①有此观点的文章参见:刘光胜《“儒分为八”与早期儒家分化趋势的生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梁涛《孔子思想中的矛盾与孔门后学的分化》,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等。。其所分化的各支流派,都或多或少受到诸子中不同流派影响。如蒙文通所言:“儒之分为八者,正以儒与九流百家之学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法,或取之墨,故分裂而为八耳。”[2]如果说传世的《孟子》等儒家文献,更多地代表战国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正统儒家思想,是与墨家思想激烈对抗的一支。那么简文《邦家之政》一篇的作者,或可看作战国时期儒家分化各个流派之中,受墨学思想影响较大,与墨学思想交融较多的一支。简文所反映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墨家颇有相似之处,反倒与同一时期孟子的治国理政观念颇有不同之处,与稍晚一些的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荀子,也有较大差异。其甚至可以被理解为《荀子·儒效》篇中的“俗儒”,“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通过梳理《邦家之政》简文中的为政观与墨家为政理念的相似性,可以对早期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分化与流变的状态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对早期儒学分化之后,受墨家思想较重的一支,其治国理政的观念有一定的理解。
其实,通过梳理近年来的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对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分化,以及各个分支的面貌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纵观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将儒家类的文献做一个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期儒家分别与墨家,法家,道家思想的相互杂糅与交融,以及同出儒家一派的各个分支之间思想的较大差异。而孟子以及思孟学派,仅仅是作为战国儒家众多分支之一而存在的,是不是战国时期儒家众多分支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还有待商榷。而至于孟子取代颜回成为“亚圣”,这完全是宋元时期的事情。但我们不可就此否认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强大影响力,通过郭店楚简大量篇目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等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孟学派在战国的强大影响。
一
《邦家之政》作为一篇孔子后学表达为政观的简文,与墨家思想的相似性,首先表现为对于“节俭”的倡导。简文曰:“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3]。这种节俭的状态下所导致的邦家状况,因为简文脱字已无从得知,不过按照后文的文章结构,此处所对应的邦家状况当是极为兴盛的。因为与之相反的,“其宫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味集而齐”、“其祭拂以不时”[4],所对应的状态为“邦家将毁”。简文通过对比论证,立场十分鲜明地从正反两个维度,提出了节俭对于为政者的重要性。而节俭具体表现在宫室规模、吃穿用度、丧葬礼仪等各个方面。关于宫室规模的论述,《墨子·辞过》:“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因此,“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而相比之下,“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由此可以看出,简文《邦家之政》中关于“节俭”的为政观,与《墨子》书中所言,几乎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邦家之政》的简文,不仅仅在内容上和《墨子》所言颇有相似性,且其论证的思路也极为相仿,都采用了从正反两个方面相对比,以此达到论证节俭重要性的目的。
至于吃喝用度方面,简文中认为,理想状态为“其味不齐。”也就是说,不必追求十分华美,十分可口的吃喝用度。这与正统儒家的生活状态是格格不入的。正统儒家思想是极为讲求吃喝用度的,认为这一切是维护“礼”的必须。《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其铺张与讲究的主张,与简文所言相比,仿佛不似一家之说。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做的就更为过分,以至于他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孟子·滕文公下》:“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出行的气派实在是非同小可,让人叹为观止。当然,孔子和孟子的铺张都有他非常充分的道德支持。孔子规定了如此繁文缛节的礼仪规范,是为了恪守其礼乐制度。孟子更是以其高度自信的人格,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可食而食之”(《孟子·滕文公下》),是应当应分的合法收入,合法“挥霍”。但作为传统儒者,其观念与简文中所言“其味不齐”是全然不同的。这种为了遵守“礼”而进行“挥霍”以至于奢侈的行径,到了《荀子》中仍没有多少变化。《荀子·富国》有言:“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可见《荀子》中也认为必要的“奢侈”是应该的。在礼乐、衣着、宫室等方面讲求排场并非一味地追求享受,而是为了维护“贵贱”“尊卑”的礼乐秩序,以此来达到国家安定的效果。《邦家之政》简文中“节俭”的为政主张虽与主流儒学大不相同,却与墨学更为相近。《墨子·辞过》篇,关于饮食方面,“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关于衣着,“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由此可见,简文中对于节俭的提倡,明显与墨子所言更为接近。
简文中为政观与墨学更为接近的是其丧葬观念。战国时期正统儒家学者,大多主张厚葬。以大致与《邦家之政》简文同时期的孟子(孟轲生活在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05年,而根据碳十四无字样品的测量,应该在公元前330年,上下浮动不超过30年[5])来说,对于母亲的厚葬,连弟子都忍不住有些质疑,而孟子也对此作了解释。《孟子·公孙丑下》曰:“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赢,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竭尽所能地厚葬亲人,才能寄托自己的哀思。至少厚葬亲人是值得提倡的。而稍晚一些的荀子更是高度地肯定了厚葬的做法,《荀子·礼论》曰:“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丧礼不够隆重,不够讲求规格,是人应该引以为羞惭的奇耻大辱。而只有厚葬才能寄托自己的哀思。而同出儒家的《邦家之政》简文在丧葬观念上却认为,“其丧薄而哀”[6]。这几乎与孟子、荀子的厚葬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相反,简文所言,与墨子“节葬”观念,却颇有相似之处。《墨子·节葬下》曰:“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可见墨子是坚决反对厚葬的,并且对厚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墨子·节葬下》曰:“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但必须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墨家还是儒家的主张,不管是厚葬还是薄葬,丧葬仪式必须表达哀思的要求则是从始至终的。《论语·自张》曰:“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而《墨子·修身》篇也认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墨家原本脱胎于儒家,有“丧礼必须寄托哀思”这一共同的主张并不足以为奇。《邦家之政》简文中所传达的“薄而哀”的观念,可以看作在儒墨两家同时追求丧葬仪式寄托哀思的基础上,受墨家思想影响较重的一支儒家学者的发声。而与孟子、荀子主张的厚葬寄托哀思的观念,有较大的差异。
二
简文中所反映出与墨学极为相似的为政观中,“均分”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简文曰:“其分也均而不贪。”儒家和墨家都从提倡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过“均分”的观念。《论语·季氏》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王制》:“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但是儒家的均分是有条件的,是在承认贵贱等级的基础上的。《论语》中所言,是替“有国有家”者对下人的“均分”,而《荀子》中的均分,更是仅仅让两贵与两贱均分。而贵贱之间是绝不可能平等均分的。相比之下,墨家所提倡的均分是打破等级观念的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墨子·尚同中》曰:“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综合简文全文的文风与主旨思想来看,此处所提及的“均分”与墨子所言均分更为相似[7]。
同样从提倡公平的维度上,简文提出了“选贤”的主张,简文中“其位授能而不外”“弟子不转远人,不纳谋夫”[8]等观点,鲜明地表现了其选贤任能的观念。积极倡导在选贤的过程中,不分内外,不分远近,因此也就不分尊卑和亲疏,积极地选贤任能。这与战国时期的主流儒家的选贤任能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墨子·非儒》曰:“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墨子对于儒家的任人分远近,辨尊卑的做法,所说论述过于偏激,有些言过其实,可战国主流儒家的这种“亲亲有术”的任人标准,倒基本是事实。《孟子·梁惠王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认为,必须通过层层考察,慎之又慎的选拔,才能任用“卑逾尊,疏逾戚”的方式被选拔上来的人才,其任人观念和《邦家之政》的简文中所积极倡导的“不分远近、选贤任能”的观念,差别还是很大的。相反地,《邦家之政》简文中的选贤观念与墨家的选贤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墨子·尚贤上》曰:“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中》曰:“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下》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墨子》中《尚贤》三篇所言,不分贵贱地选贤用能是一以贯之的主张,这几近可以作为《邦家之政》简文观念的注解。如果说唯一有所不同的是,简文中认为血缘纽带关系,在选贤过程中还是十分重要的。选贤时应当“其君执栋,父兄与于终要”[9]。但墨子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墨子·尚同中》曰:“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墨子在此,将“党父兄”的危害说得十分详细。因为简文《邦家之政》的为政观,归根结底代表儒家思想的为政观,不可能与墨学所言完全一致,但其选贤的主张,与战国时期主流儒家选贤学说相差较远,与墨家的选贤观念却颇有些类似则是确凿无疑的。
三
通过对简文《邦家之政》为政观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为政观与这一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主流儒家观念颇有些不同,相反,与墨学为政观念颇有相似之处。《荀子·儒效》中所记载的“俗儒”大体可与之相参:“逢衣解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姑且不论《荀子》中记载对“俗儒”的批评,就《荀子》中描绘的“俗儒”面貌来说,当与持《治邦之政》为政主张的一派儒者相互参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实从近些年大量出土的上博简、郭店楚简、清华简等文献来看,其中有浓厚儒家色彩的简文,其思想观念大多能看到与道法刑名以及墨家等各家流派杂糅的迹象。其中受墨家思想影响较大的儒家类文献,也并不少见。例如将郭店楚简《六德》和《忠信之道》篇与上博简《神鬼之明》相比,便可以看到儒墨思想交融之深是何等的鲜明。在《唐虞之道》以及上博简《容成氏》一篇中,可见儒墨思想杂糅,几近不可分割。郭店楚简《性子命出》一篇,作为儒学类文献的简文,其思想却与道家颇为相似。清华简《心是谓中》一篇虽然是儒家观念的简文,其内容与传世的《管子》又颇有相似之处。出土文献中所反映的儒家与诸子各家思想相互交融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列举。大量的简帛出土材料,给我们了解早期儒家在战国时期的分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通过诸多的简文内容,更直观地了解到儒家分化的状态、程度,以及分化的趋势和方向。
我们知道,孟子以及孟子代表的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仅仅是作为儒家分化之后的一支分支而存在的。孟子成为孔子之后最为正统、最为公认的一派儒学继承人,其主张成为儒家诸多流派中流传最为广远、认可度最高的一派主张,孟子被尊奉为“亚圣”,《孟子》一书超越其他儒家经典,与《论语》一道位列四书,这一切的一切,则是宋代及其以后“孟子升格运动”的事情了①有此观点的文章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夏长朴《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收录于《中国哲学》第24辑《经学今诠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624页;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02页;郭烟《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载《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等等,不在此一一列举。。至于孟子取代颜回成为“亚圣”,也是一波三折,在此不再赘述[10]。
至于在战国时期,孟子以及其所代表的思孟学派,其主张是否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仍是不确定与值得商榷的。因为战国距今年代久远,大量的文献资料缺失,我们已很难准确地探知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的具体情形,而不断出土的新的文献资料,将左右和影响我们的判断。但就如今的出土文献资料而言,我们绝不可就此轻率地否认孟子以及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强大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孟子在当时影响力有限。笔者以为按当前已有的文献资料论,此说值得商榷。单从出土文献来说,郭店楚简有《五行》一篇,同样的《五行》篇还见于马王堆帛书。在不同的出土文献中,同见《五行》一篇,可略见《五行》一篇在楚地流传影响之广远。而这流传广远的《五行》篇,几乎公认是子思一派的作品。马王堆帛书的整理者韩仲民认为其是“子思、孟轲的门徒的作品”[11]。饶宗颐认为:“现在郭店简亦出现与帛书《五行》文字相同的简册,在竹简的开头标记着《五行》二字,大家无异议地承认它正是子思的作品。”[12]《五行》除了“经”的部分,还有“说”的部分,而“说”的部分,一般被认为是孟子其弟子所作,比如梁涛认为:“《五行》说文主张‘动于中而形善于外’,远然是继承孟子思想而来……其观点显然是沿着孟子的‘仁义内在’说继续发展。”[13]
其实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所占的比重甚大,思孟学派所占的比例甚重。郭店楚简除《五行》一篇外,儒家文献还有《成之闻之》《性子命出》《緇衣》《六德》等十三篇,这十三篇文献中,思孟学派的影响随处可见。李存山就认为:“郭店竹简,除《老子》《太一生水》以及《语丛四》外,余皆儒家作品。”[14]李学勤认为,郭店楚简中《緇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六篇,均是子思所作,是《子思子》中的散失之文[15]。李景林也认为:“郭店简儒家类著作应为子思一系作品。抄录于同一形制竹简的四篇文字《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为郭店简儒家类著作的中坚部分,表现了子思一系的‘性与天道’论。其余诸篇,有的较接近于孔子,当为子思绍述孔子思想之作,有的则近于孟子,当为子思后学所述。”[16]当然,陈来等不少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中《緇衣》《五行》等篇目不能全部归入《子思子》[17],但无可否认的是,郭店楚简中作为中坚的十几篇儒家文献和子思与孟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知道,如今出土的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大多都是楚地的文献资料②郭店楚简出土自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上博简与清华简均为收购与捐赠所得,经考证其出土的位置大概在楚国郢都附近。,而子思和孟子主要活动的地区在中原地区,孟子主要的游说对象是齐国和魏国的君主,楚国虽在战国时期,疆域辽阔、带甲百万、国力强盛,但毕竟是思孟学派影响相对有限的地区,子思和孟子本人是否到过楚国,思孟学派的门徒有多少到过楚国,这都尚不可知。而在这一地区仍可以发现如此数量众多的代表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简文,由此可以想见,其在中原地区,在其主要活动的魏国与齐国的影响力之巨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邦家之政》作为孔子后学所作、反映儒家思想的一篇简文,在节俭、薄葬、选贤、均分等各个方面均与墨学为政主张极为相似,反倒与传统认为的代表主流儒家学说的孟子和荀子所言颇有不同。这直观地向我们呈现出了早期儒家在战国时期的分化状态。简文《邦家之政》所代表的儒家一支分支,或可认为是荀子所言的“俗儒”一支,其主要的为政观念受墨学影响极大,与同时期以子思与孟子所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正统儒家学者的为政观有了极大的分别。
近年来,通过上博简、郭店楚简、清华简以及马王堆帛书等大量的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对早期儒家在战国时的分化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对于儒家所分化出来的各个学派所持有的学说,以及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有一个更为直观地了解。通过郭店楚简、清华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等大量的出土的儒家文献与传世的儒家文献相对比,又与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各类诸子文献相互参照,更为鲜明地看出早期儒家进入战国之后,所分化出的各家流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道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的影响。在战国儒家分化的背景下,被后世认为是儒家正宗的孟子及其思孟学派,在当时只是以一家分支的面貌而存在的。但我们不可就此否认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大量的楚地文献作为参照,我们可以想见战国时期,思孟学派影响之巨大、流传之广远。因此,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孟子以及思孟学派,更宜作为在战国时期有极为强大影响力的儒学一支来看待,较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