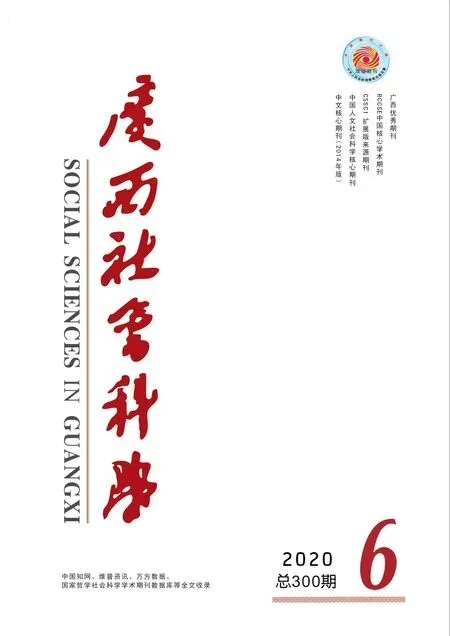正当防卫限度判断的路径修正与视角转换
童伟华,王献英
(1.海南大学 a.法学院;b.特区法制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0208;2.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出现的正当防卫案件,不仅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更牵动着社会公众的神经,引发了民众和理论界对于正当防卫限度的激烈争论。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正当防卫条款,本意是扩大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鼓励社会公众勇于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1],这从我国对有关正当防卫法条的修改中可见一斑。首先,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将1979年刑法关于防卫过当限度的描述由“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扩大了正当防卫可能的成立范围,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获得了广泛支持;其次,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又在第三款中对于特殊防卫权进行了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可以说,我国刑法正当防卫的条文内容对正当防卫限度本无不合理限制,但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正当防卫限度的认定却非常严苛。这与法官在对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及结果限度进行判断时所采取的视角倒置有关。在对行为限度进行判定时,法官倾向于采取侵害人视角,过分强调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所采取的防卫手段应当同侵害行为的强度大致相当。特别是在防卫人运用“武器”对徒手的侵害人进行防卫的场合,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武器对等论”几乎不可能认定防卫人成立正当防卫①例如,在“陈凯故意伤害案”的判决中明确提及“8名徒手的被害人对被告人殴打的危险程度应当与持械殴打他人有所区别,赤手空拳的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与被告人使用刀具导致他人重伤、轻伤、轻微伤的损害后果明显失衡”,借此来认定被告人成立防卫过当。详细参见(2018)黔018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而对于结果限度的判定,法官则青睐于从防卫者视角,围绕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同侵害行为造成或现实可能造成的损害,进行质上或量上简单的比较权衡,这样很容易使法官认定其属于防卫过当。这是由于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重伤或死亡情形下即认为发生了重大损害结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侵害人在防卫者采取防卫措施的情况下往往没有造成现实的损害结果,或只是造成了较轻的危害结果①如果侵害人造成了被侵害者死亡或重伤,防卫者往往失去了防卫能力,正当防卫也就无从发生。因此在正当防卫案件中,简单的结果权衡,会让防卫者处于先天不利的境地。。简单地进行结果比较或法益权衡,会使得法官认为防卫结果与侵害结果严重不均衡从而判定防卫过当,至于侵害行为实施时可能造成的各种危险以及侵害人应当承受什么样的损害结果,往往不是法官考虑的因素。同时在上述两者的判断中,结果限度的判断相对于行为限度的判断对于法官来说往往更为优先,不仅仅是因为“死者为大”“维稳优先”等案外因素的影响,更在于其判断更加直观、简便,双方的损害程度可以通过事后的司法鉴定清晰地表现出来,而行为限度的判断则较为复杂。这就导致了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着唯结果论的倾向以及以结果为核心的判断思路[2]。即以防卫结果为主要考量要素,只要发生了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裁判者往往就认定防卫人构成犯罪或至少构成防卫过当,这就使得我国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变得极其狭窄。尽管理论界对于正当防卫限度的认定不应过于狭窄的呼吁也未曾中断过[3],但司法实践中前述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基于上述现象,本文认为有如下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防卫限度包括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其二者的关系如何,是应当先判断行为限度还是结果限度?第二,二者应当分别采取何种视角进行判断,其考量的具体因素又有哪些?本文将依次分析检讨。
二、防卫限度判断路径之修正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以“防卫过当”“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为关键词所收集的185份刑事判决中发现,法官对于防卫行为限度的判断往往一笔带过,其经典表述为,“行为人造成了侵害人人身重大损害,因此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就说明在司法实践当中裁判者对于行为限度的把握大多来源于对结果是否属于重大损害的判断。而“结果—行为”的判定路径与“唯结果论”相结合,不当地抬高了正当防卫成立的门槛,与正当防卫法条的规范目的背道而驰。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明文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笔者认为,应当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对防卫限度作出解释,而刑法教义学的起点就是刑法规范。如冯军教授所言,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4]。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所确立的防卫过当规范,包括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其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涉及行为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则属于结果限度。两者是相互并列关系,仅在两者都同时得到满足的场合防卫过当才成立。由于当前对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唯结果论”倾向严重,对结果的过分重视必然导致判断过程中先考虑结果后考虑行为的“结果—行为”进路,不但违反了规范本身的要求,而且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以结果为首的判断方式忽视了行为限度在正当防卫判断中的作用。基于“结果—行为”路径,理论界与实务界都从防卫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展开对必要限度的判定,如果结果是不应有的重大损害,一般也会当然认定行为过当。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在对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把握上,其实体标准在于防卫损害是否属于“明显的不应有的重大损害”[5],这就将防卫造成的损害结果当作判断防卫限度的唯一条件,而没有考虑到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问题。还有论者指出,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行为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结果过当而行为不过当”的情形[6],这种见解就使得原本并列的两个条件成了从属关系,从而消解了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于防卫过当的限定意义。针对防卫行为,“在判断是否具有作为防卫手段的相当性之时,考虑结果的严重程度,更会加剧学说中的相当性概念及其判断标准的不明确性”[7]。这种不明确性导致司法实务当中法官受“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以及“维稳优先”的司法导向影响,在面临来自侵害人或者其家属的压力下,对防卫限度的判定过于严苛。
其次,如前所述,从结果入手的思考进路会使得行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就违背了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初衷。“以至于该按照正当防卫处理的却当作防卫过当的案件处理,这极大地挫伤了老百姓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8]要求防卫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尽力保持克制并把握好反击的强度,以期对侵害人的生命及重大身体法益进行保护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被侵害人没有必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防卫尝试的境地,因为防卫是以有利手段将所面对的危险即刻且终局性排除的行为[9]。正当防卫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当法益得不到公权力及时救济时得以私力救助以避免法益受损。尽管依法治国原则要求人们在社会当中保持对他人最低限度的尊重,但将对侵害者利益的考量过分纳入正当防卫的判断当中显然不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应有之义。
最后,这种思考的进路将使得司法人员站在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正当防卫“算经济账”,导致很多在防卫手段上符合必要性条件但造成重大损害的场合被否定成立正当防卫[10]。从事后的角度观察案件事实进而对防卫限度进行判断的做法,必然要求防卫者对正在面临的不法侵害先进行冷静细致的思考分析后再实施正当防卫行为,这就使得防卫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束手束脚。从风险分担的角度来看,防卫过当的本质是对权利的滥用,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含义就在于防卫人以明显违反社会相当性的方式和手段导致重大损害后果[11],忽略正当防卫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过分依赖事后查明的案件客观情况就会使得防卫人承受更多的风险或者轻易对防卫过当进行认定。
因此,对于防卫限度的考量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判断为标准,同时以行为发生时的客观情况为基础进行综合考虑,将对防卫限度的判断从首重防卫结果修正为首先判断防卫行为自身的样态上来,即应当遵循“行为—结果”进路。其一,这符合我国刑法条文对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规定的先后顺序,也是基于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其二,从防卫过当的本质来看,对防卫权的滥用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防卫人实施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紧接着才是“重大损害”这一过当结果的出现。其三,“行为—结果”的判断思路有利于纠正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唯结果论”的倾向,使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的关系回归到相互并列的程度上来,将行为的“必要限度”与“重大损害”在判断上相区分,承认存在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情况的存在,以及行为处在必要限度内但造成了重大损害的场合仍属于正当防卫。
三、正当防卫行为限度之判断
在明确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判断顺序之后,接下来探讨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何判断,亦即应当采纳何种标准及视角。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当中所采取的侵害人视角过分强调防卫人的防卫手段同不法侵害在强度方面要相当,导致防卫人在所能采取的防卫手段上受到诸多束缚。因此,本文认为应当转换视角,从防卫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综合诸多可能影响防卫手段的因素合理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一)判断标准之确立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必要限度的判断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基本相适应说、客观需要说与折中说。基本相适应说所采取的判断标准是,看正当防卫与不法侵害两者的强度是否基本相适应。但在某些场合下,如对强奸犯所实施的防卫中杀伤强奸犯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强度就难以进行比较,尤为关键的是,基本相适应说在判断的角度上采取的是事后标准,这会不当约束公民的正当防卫权[12]。我国通说所采取的标准是折中说[13],认为对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考察关键在于是否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对必需的认定则应考虑侵害行为的强度、所保卫权益的性质以及防卫行为的强度。在折中说看来,防卫行为虽然客观上需要,但当防卫强度与不法侵害强度两者不相适应时仍然不符合必要限度条件,因此,折中说仍旧是以基本相适应说为核心的。
笔者认为,在防卫行为是否属于必要限度的判断上应遵循客观需要说,即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在于其客观需要,而法益保护原则为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详言之,只要社会一般人站在侵害发生当时防卫人的角度来看,该行为是为保护法益所必需的场合,就不应当认定防卫行为存在过当①在此需注意的是,不能以防卫人本人的认识与行为能力作为防卫限度的判断基础。在防卫人本人的认识出现严重偏差的情况下,例如,根据当时的情况在一般人看来只需要轻微的暴力即足以制止侵害的场合,防卫人却认为需要并且采取了开枪射杀的防卫行为,如果对此基于“行为人标准说”认定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普通国民的法感觉会发生严重的对立,也背离了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属性,显然不合适。正当防卫属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而不是责任阻却事由,是否在防卫限度之内,应以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进行客观的判断,才符合正当防卫的属性。如果行为人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导致防卫行为逾越了防卫限度,但根据行为人的个人认知确属难以避免的,可以考虑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很显然,我们无法苛求被侵害人做一位充分保持理性的看客,而应当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将自身置于被侵害人当时所面临的境遇当中[14]。另外,根据法益性欠缺原理,由于不法侵害人在自我决定的前提之下违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的义务,导致其法益值得保护性严重下降,这时法律就要求不法侵害人承担更多的风险。若此时要求防卫行为的强度与不法侵害强度相适应无疑是为不法侵害分子提供不当的保护,反倒使得防卫人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加,这显然不合理。例如,半夜三更侵害人试图从被侵害人位于五楼的房屋窗口爬进来,被防卫者(房屋主人)发现。这时侵害人的意图并不明显,有可能只是偷东西,有可能是入室抢劫,也有可能是入室杀人,防卫者根本无从判定侵害人到底要侵害什么。为了防止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防卫者基于本能将侵害人从窗口推下去,侵害人坠地而亡。此时从防卫者的视角出发,即便后来查明侵害人不过是为了偷东西,也不能认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因为在当时情景下,一般人都会采取这样的举动,不能通过事后回溯性地假设将潜在的不利转由防卫者承担[15]。相反,若从侵害人的视角去观察,以如此剧烈的防卫行为对抗盗窃行为明显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则必然将其认定为防卫过当。正当防卫不同于防御性紧急避险,对防御性紧急避险而言,虽然正在发生的危险是由避险对象引起的,但危险的发生并不是避险对象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对自身所负担的尊重他人义务的违反,因而避险行为受到限度条件的严格控制,对正当防卫行为则不应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行为限度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客观需要。
也许有人会认为,客观需要说无法回答为何不能允许一位只能以开枪射杀小偷的手段来保护自家院子果树上的果实的老人开枪行为?因为此时在老人看来为保护自身利益已经别无其他选择。对此,罗克辛教授是从法确证原则中所推导的社会伦理限制来解释为何此时老人不能射杀窃贼的[16],而持优越利益说的学者则以此行为违反了不能为保护极小的法益而损害不法侵害人的重大法益这一通常性规则来排斥其正当性[17]。但是在笔者看来,只要正确把握“客观需要”的判断标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前所述,以行为人标准对行为限度进行判断会导致认定的恣意性,最终滑向无限防卫权的窠臼。因此,在确定以客观需要说来判断行为限度的同时,标准上宜采用防卫当时社会一般人标准来对行为限度进行判断,而判断的前提素材应当是侵害人当时可能制造的风险。对于行为限度的判断只能以不法侵害发生当时防卫人所面临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为基础,考量社会一般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是否会选择实施与防卫人反击行为强度等同的反击措施[18]。同时,要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其他能够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方案,该方案所应满足的条件不仅在于能够产生与被侵害人实际实施的防卫行为等同的效果,而且当防卫人选择实施该方案时不会使自身遭遇更大的危险。至于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笔者认为,在反击行为的强度小于或等同于不法侵害的强度,以及虽大于不法侵害的强度但在社会一般人看来仍属于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场合,都应承认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要求。面对为何不能允许一位只能以开枪射杀小偷的手段来保护自家院子果树上的果实的老人开枪这一疑问,站在客观需要说的立场,从防卫人的视角出发,根据防卫当时社会一般人标准,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绝大多数人应不会选择以开枪射杀小偷的手段来保护自家院子果树上的果实,因为该防卫行为明显不具有社会相当性。在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法益侵害[19],是具有违法性的行为。
(二)判断因素之展开
基于上述分析,站在防卫人视角的客观需要说能够较为合理地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么接下来所要探讨的就是,何种因素在行为限度的判断中应当得到重视。在笔者看来,以下因素应着重进行考察:
一是防卫者自身的防卫能力。在面对强度相当的不法侵害时,防卫能力强弱决定了其能够采取的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措施的多少。因此,对于防卫能力不同的防卫人法律所允许的防卫手段自然是有所差别的。而被侵害人的防卫能力高低则由如下两方面决定:第一,防卫人自身的体能及格斗技巧,例如男性较之于女性、成年人较之于老人和未成年人、军警人员较之于普通民众,良好的体能及格斗技巧能够有效帮助防卫人选择更加缓和的方式来解决纷争。当同样面对多人徒手围殴时,格斗冠军赤手空拳便能将歹徒击退,而未成年人则可能需要拾起砖块或动用刀子才能有效保护自身法益。在“陈某正当防卫案”[20]中,未成年人陈某在面对持械的9人围殴时,掏出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乱挥乱刺的致三人重伤的行为,检察机关就认为此时陈某借助刀具增强其防卫能力并无不合理之处,同时其挥刺行为符合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需要,不属于防卫过当。第二,被侵害人对于反击不法侵害的准备程度。当防卫人预见到不法侵害即将发生,从而事先进行准备的场合,防卫人拥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对防卫工具、手段进行选择。故此时能够要求防卫人在能保护自身法益的前提下采取危险性较低的防卫手段。
二是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对于防卫者的重要程度。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在现实生活中法益的类型纷繁复杂,并不是为了保护任何一种法益都能够实施一切防卫手段,否则就将落入无限防卫权的桎梏当中。如前所述,为了保护院子里的果实而射杀小偷的行为是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该财产法益对于防卫者来说并不足以重要到以如此强烈的手段来保护。但是当不法侵害针对的是防卫人的身体、生命法益或者是其所针对的对象对于防卫人十分重要之时,对于行为限度的考量应当较侵害轻微法益更为宽松。在“张某某故意伤害案”①见山西省屯留县人民法院(2016)晋0424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在看见自己父亲被两名侵害人徒手殴打之时,持菜刀将二人砍成轻伤的行为,法院认定其构成防卫过当,该结论显然是受到了“武装对等论”的影响。但在本文看来,防卫人所要保护的是自己父亲的身体法益,其排除不法侵害的客观需要较为迫切。即便双方人数和力量上差距不大,但对于动用武器进行防卫的行为也不能轻易认定其偏离了社会相当性。
三是防卫者对于法益侵害风险的合理预见。侵害人对于防卫人的侵害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一个较长时间的危险状态[21]。在该状态下,防卫人对侵害者是否将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会有所担忧[22]。因此,对于防卫者在面对持续侵害时的合理预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此时不能站在事后的角度简单用“武器对等”或“防卫者在造成对方重伤的同时自身没有受到丝毫损害”等理由来认定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基本相适应”的做法无疑是对防卫权的剥夺及对不法侵害的鼓励。在“陆向阳故意伤害案”②见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8)赣05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书。与“盛春平案故意伤害案”[23]中,被告人同样是在持续经历了传销组织“抖新人”的恐吓措施后掏刀进行防卫并致一人死亡。但案件结果却截然相反,其“同案不同判”的根源就在于,在陆某案中法官并未对被告人对法益侵害风险的合理预见予以考量,尽管被告人在其供述中明确表示“我怕其搜到我身上的小刀,我会有生命危险”,但法官还是坚持认为被告人持刀捅刺的行为远超制止不法侵害所需的强度。相反在盛某案中,检察官就充分考虑到了盛春平在当时情形下对其自身安危的担忧,肯定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四、正当防卫结果限度的判断
(一)结果限度判断的基本原则
按照“行为—结果”的防卫限度判断路径,在判断行为限度是否适当后,接下来就是对结果限度的考察。具体而言,在防卫行为已经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场合下,才有必要对结果限度进行判断,如果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无论给侵害人造成何种损害结果,都应认为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有观点认为,在进行行为限度的判断之前应首先判断结果是否能归责于防卫人的反击行为,若结果属于侵害人自我答责的范围内,则应否认防卫行为与防卫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此时防卫行为是无法符合构成要件的,即采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来排斥防卫人的刑事责任[24]。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路径破坏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和三阶层的“阶层性”,因为上述观点认为结果属于被害人自我答责,实际上是在防卫人的反击行为进入违法性评价之前就被认为不能进行客观归责,但是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看来,正当防卫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上述观点将本应在违法性层面进行评价的事由前置到构成要件符合性层面进行判断[25],同时在得到防卫结果不能归属于防卫人的结论后,又运用违法性层面自我答责的法理排除正当防卫行为责任的做法,将会导致犯罪论阶层的模糊化,笔者主张还是应当在严格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讨论这一问题。此外,在“唯后果论”盛行的当下,这样的做法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前面所说的以死伤结果为核心的防卫限度判断路径当中。
那么,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之后,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对防卫的结果限度进行判断呢?笔者认为,对结果限度的判断首先应看结果是否属于“重大损害”的范围,而关于“重大损害”的理解笔者原则上同意通说仅将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包括在内的主张。其次,应基于法益性欠缺原则,从侵害人自我选择并违反互相尊重义务所导致的法益性阙如当中寻找防卫结果判断的基准。对于防卫结果的限度判断,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下降程度的考察,而其下降程度又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风险息息相关。
笔者认为,侵害人实施了不法侵害行为,其违反义务制造了自身法益与被侵害人法益的冲突,并给被侵害人法益造成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这不仅使得其自身法益的价值在法律评价上降低,同时其必须承担消除该法益冲突的义务。而承担义务总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当防卫人在实施正当防卫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时,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让不法侵害人消除风险所应付出的代价。当然代价或成本的大小也要合理,那么成本的大小如何估量?笔者认为,在法益合理下降的范围内防卫行为给不法侵害人所造成的损失即法益损害的结果原则上都应由侵害人承担,因为正是由于其自我选择实施侵害行为,才导致自身的法益在一定范围内要承受被损害的风险,此即合理的防卫结果由侵害人承担规则。当然,侵害人的利益在受到防卫行为损害的同时,他也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当防卫人通过防卫行为有效地保护了自身法益时,侵害人也将因此不纳入刑事评价的范围或仅构成未遂;而当他没有对防卫人造成丝毫损害的场合,民事方面则可能依照“无损害则无责任”原则完全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是,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合理下降的范围”或其应当承受的“合理的防卫结果”该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对结果限度的考虑应当同行为限度一样遵循“情境性”原则,亦即,对于一般人处在侵害人立场下所预料到的可能的防卫结果都在合理的结果限度之内。立于侵害人的立场,明明预料到自己的加害行为可能会招致这样的防卫结果,还要实施该行为,就不得不“自食其果”。虽然实现自身的自由是每个人生来的权利,但权利和责任往往以相互对等的形式呈现,一个人通过自我决定所实现的自由,在侵害他人领域时就应当自我答责[26]。亦即,由不法侵害人所引起的防卫行为和防卫手段中蕴含的典型性危险所造成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身负责[27]。
综上,对于防卫结果的限度问题我们应当从法益性欠缺原理出发,立于侵害人视角,以一般人的标准进行判断,实施该不法侵害可能会遇到何种反击以及会对自身产生何种损害,在此预见范围内的损害结果都应当通过“被害人自陷险境”的法理由侵害人自身负责,不属于防卫结果过当,此即正当防卫结果限度判断的一般规则。
(二)结果限度判断的具体因素
在明确正当防卫结果限度判断的一般性规则后,接下来就是对具体因素的考量,即在正当防卫案件中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下降的程度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防卫结果的具体限度。对此,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因素进行考量:
一是侵害行为的强度。一般来说,侵害行为的强度越大,其所带来的风险越大,防卫人就越可能通过强力的防卫行为来保护法益免受侵害,此时侵害人所应承受的不利后果就越大[28]。而侵害行为的强度则与侵害人是否使用了工具、侵害者人数的多寡以及侵害手段等因素相关。在侵害人使用工具、人多势众或侵害手段较为强烈的场合,防卫人所面对的风险就会陡然上升,其只能通过极易引起侵害人法益重大损害的反击手段取得优势地位以弥补双方的实力差距,此时有很大可能会使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在“王顺义故意伤害案”①见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111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廉某4在与王顺义发生争执后持刀捅刺其腹部与胸部,造成王顺义重伤。王顺义逃跑无果后抢过廉某4手中的刀,骑跨在廉某4腰部并捅刺其胸部数刀致其死亡。本案中,防卫人已经先行逃避而侵害人仍持刀紧追不舍,在身中两刀的情况下,其身体和生命法益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这一风险的始作俑者廉某4的生命法益的值得保护性也应当暂时性地归零。因此,即便王某后续连续捅刺的行为已经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行为限度,但其所造成的结果在一般人看来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侵害人死亡的结果应当由侵害人自行承担。
二是侵害行为所发生的环境。正当防卫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因此在对正当防卫进行考察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环境[29]。为让对法益的侵害更易得逞,侵害人通常会精心选择容易令被侵害人产生恐慌、不安情绪的时间与地点实施不法侵害,这种不安感将会加剧侵害人所面临的风险。此时防卫人会竭尽全力实施防卫行为,通常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又或者是在被侵害人的住所实施的不法侵害,当侵害人毫无理由地侵入并企图伤害被侵害人时,理所当然地会让被侵害人陷入一种自身安全无法保障的恐慌情绪当中。也正因为住宅安宁的重要性,从西周开始就有规定“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周礼·秋官·朝士》),汉唐对“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以及“诸夜无故入人家”的侵害行为,住宅主人均可对侵害人格杀勿论。在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当中,甚至演化和发展出为保护公民住宅权而存在的“城堡法”。科克于1644年提出的“城堡主义原则”,其核心为:某人的住所即是其城堡,为了捍卫其住宅以及当中的居住者的权利免遭不法侵害,防卫人可采用包括杀死不法侵害人在内的一切方式[30]。虽然这些古老的主张存有无限防卫权的偏向而不能为今天所提倡,但足可见住宅安宁对于一个人的重要程度。“侵害住宅安宁”这一情节在今日看来虽不足以论证防卫人能行使任何手段来保卫自身权益,但其足以证明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大幅下降。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入户”这一情节也极为重视,如对“入户盗窃”取消数额限制以及将“入户抢劫”列为法定刑升高的情节即为其适例。在“杨柳故意伤害案”①见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2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书。中,三名不法侵害人于午夜强行闯入防卫人住处并将其拖出进行殴打,后被侵害人杨柳跑回屋内持刀刺向孝某(侵害人)腹部,造成其一人重伤。本案中,即便面对三人的徒手殴打防卫人所实施的持刀捅刺孝某腹部的行为不符合行为限度的要求,但在当时的情形下,防卫人所造成的重伤结果也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理由在于,以一般人的标准来看,侵害人对于其给杨柳所制造的风险是有所认识的,所以对于防卫人所可能采取的强烈反击及可能造成的重伤结果应当有所预见,但其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不能认为防卫所造成的结果超过了必要限度,而让防卫者承担责任。
三是侵害行为所针对的法益。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各类合法利益不受不法行为侵害,不法侵害所针对的法益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侵害行为的性质,也影响着其所造成的风险大小以及防卫行为的难度。例如,针对财产法益的盗窃行为,与针对生命法益的杀人行为相比,杀人行为显然比盗窃对法益的危险更大,侵害人所应承受的防卫结果也就更为严重。这也体现在我国刑法对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中。然而,侵害较低位阶法益的场合,防卫人并非不能损害侵害人高位阶法益,因为即使侵害人侵害的是较低位阶的法益,同样有可能给被侵害人造成巨大的障碍与险境,此时侵害人的法益值得保护性也将大幅度下降。当然,也不能如同李斯特所说的那样,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微不足道的法益也允许杀死侵犯者[31],这是一种无限防卫权的观点,在当今社会难以得到认同,防卫结果也必须在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下降的范围内。笔者认为,如果防卫结果为侵害行为引发的典型性风险的现实化,为侵害人应当预见或为社会一般人所接受,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该防卫结果超出了必要限度。在“任某故意伤害案”②见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12)湖德刑初字第92号刑事判决书。中,任某因欠债被卢某等人带至酒店并限制人身自由,后持刀将卢某刺成重伤。如果仅将防卫人所保护的人身自由权与侵害人身体法益所遭受的重伤进行比较,无疑会认为任某此时手段与目的明显不相称。但从侵害人视角出发,侵害人以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讨债必然将招致防卫人较为猛烈的反击,重伤的结果也应当在一般人可预见的范围内。因此,不能让防卫者承担不合理的过当责任。
五、结语
受对死亡极其避讳的生死观以及个体死亡的群体性意义的影响,“死者为大”的思想在我国刑事判决中根深蒂固[32],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办案思维对防卫案的判决又施加了重要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正当防卫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要防卫行为使得不法侵害人人身遭受重大损害,防卫人一方就立刻在审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发生侵害人死亡的结果时。同时还产生了诸如绝对强调“武器对等原则”“不能为了保护财产剥夺他人生命”以及“侵害人的法益也要被保护”等似乎合情合理的辩护理由。但是,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不仅仅对他人的法益造成了危险,同时还把自身的利益推入险境,如果此时还要求法律对侵害人进行细致周到的保护,这种“唯结果论”的做法无疑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曲解。此外,“结果—行为”的判断进路以及判断视角的倒置使得正当防卫条款有被束之高阁的风险。因此,应当遵循“行为—结果”的判断路径,基于双方视角对防卫人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侵害人应承受的防卫结果进行充分的评判。在行为限度方面,应站在防卫人的视角对其防卫能力及其对风险的合理预期进行充分考量,以确定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只有行为过当时才需要判断是否存在结果过当。而在结果限度方面,对于防卫后果应当认清其本质,不能以死亡结果的出现轻易将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33]。应从侵害人视角出发,对于在一般人看来属于侵害行为所导致的典型性风险或可预见的防卫结果都应认定属于正当防卫的结果限度之内,即便是“重大损害”结果,也不应当由防卫者承担过当责任。
——以美国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