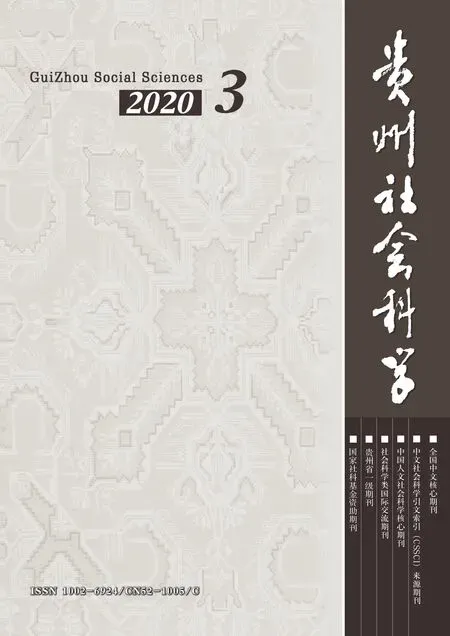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及其批判
陈 伟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西方生态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比较具体地讨论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研究其他物种是否具有和人类相同或相似的“利益”或“权利”,即其他物种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内在价值”。第二个层面则是比较抽象地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自然”并非某种具体的生物物种,而是生物生存环境的整体(除人类社会之外),这一层面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是何种样态,未来又应该向何种样态发展。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些批判性意见。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论
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进一步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总体说来,可以把这些理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存发展之背景或工具的工具主义理论,第二类则是承认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内在价值理论。工具论与内在价值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表述,两者的实质区别是看是否承认其他物种或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自身的价值:承认其他物种或自然自身价值的是内在价值论,否认的则是工具论。
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自然科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另一种则是形而上学、宗教神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前者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人类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只是自然界所有物种中的一个种类而已;而后者则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并不处于同一个等级序列,人因为具有“灵魂”而处于其他物种乃至于自然的上一等级,人类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与自然相分离的精神存在。[1]然而20世纪的社会科学由于强调人类社会的独特性(通过反对自然主义、反对自然科学对人类行动的解释方式)走向了自然科学的反面,反而向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的自然观靠拢了:人类越来越远离自然,在自然之上对自然进行科学主义的操作与剥削。以马克斯·舍勒为代表的德国思想家认为西方与资本主义内在关联的现代性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并且指出西方世界对自然的剥削不仅仅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偶然后果,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必然要求。之后无论是政治上左派的哲学家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右派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都对科学技术持有类似的看法;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中又都存在着为了人类利益而支持工具理性、剥削自然的观点。[2]可见,不能以学术上的激进与否来判断一个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一个固守传统学术理念的人有可能是一个生态整体主义者,而一个声称要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而进行民主改革的人也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坚定拥护者。
虽然整体说来,西方哲学存在着“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把自然当作可以为了人类利益而被合理操作的客观对象”的观念,但这种对待自然的观念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观念。其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并不一致,例如柯林伍德发现,不同时代的人们的自然观念体现在对自然的不同隐喻中,比如古希腊人通常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科学家们则把自然乃至整个宇宙都看作一台巨大的机器。事实上,随着我们身边各种各样具有机械结构的工具的增多,现代人把自然看作具有机械结构的实体似乎是“自然而然”的。[3]通过把自然理解为当时社会背景共识的一种客观结构,工具论才能够对自然进行“合理”操作。随着当代科学研究对进化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推进,作为对象的自然在当代人的意识中则有可能逐渐转变为物种选择或智能生物突破自然选择的背景结构。工具论并非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主流,但很可能是社会常识中的主流,作为哲学中内在价值论的一种对照,其理论的论证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中: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的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甚至唯一价值。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价值论
人与自然的工具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观点,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主流观点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对内在价值论的讨论又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研究其他物种个体的内在价值的个体主义思路,另一种则是把自然作为整体研究其内在价值的整体主义思路。
(一)个体主义思路
个体主义思路主要致力于论证非人个体的利益、权利、内在价值,其共同思路是把西方经典哲学对人类主体为何拥有权利的论证移植到对动物权利的论证。例如,雷根从康德主义的思路出发来论证动物权利,认为动物拥有权利是因为动物自身的原因(与人类平等的内在价值),不能因为动物不具有认知并签订社会契约的能力而得出动物不具有权利的结论,局限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契约根本就不是权利(包括人类权利)的最终来源。[4]辛格则把人人平等的理念推广到所有动物的平等,主张所有动物的平等权利。[5]雷根、辛格还仅仅把道德关注点放在了有感觉的动物(animals)上,古德帕斯特则把道德关怀推向了所有生物,无论是有感觉能力的还是没有感觉能力的,形成了所谓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6]生物中心主义主张尊重所有生命形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感觉能力不过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尊重“感觉能力”这个“方式”从逻辑上就要求我们尊重“所有生命”这个“目的”本身。以树为例,树不仅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拥有内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在人类的实践中几乎没有也不需要得到考虑。[7]更为极端的学者如泰勒,认为所有生命形式都是目的,应该建立一种生命中心主义的理论(a life-centered theory)。他认为,对生态系统与生命共同体固然应该充分尊重,但更应尊重作为个体的生命,这和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固然应该尊重共同体的利益,但首先应尊重个人权利的道理是一样的。[8]
总体看来,对动物内在价值的论证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逻辑缺陷。例如,雷根对动物权利的论证更多的具有宣传上的影响力,而欠缺说服力,因为所谓动物的平等利益、价值和人类的平等利益、价值并不是一回事,动物欠缺对其利益、价值认知的能力。古德帕斯特的生物中心主义仅仅强调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基本道德关怀,而不同等级的生命形式显然应该得到不同程度的道德关怀。蚂蚁和人的生命固然都应该得到最基本的道德关怀,但对人的生命的道德关怀显然应远大于对蚂蚁生命的道德关怀。因此,有学者另辟蹊径,把非人物种的利益或权利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利益上。人类社会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利益,这就有可能在对待动物权利时引入成本效用分析的方法。例如诺顿指出,虽然成本效用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赋予动物以独立的权利却更难证成。对非人类权利(nonhuman rights)的证成需要一个普遍权利理论的支撑,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理论。退一步说,即便我们真的能够赋予非人类以法律权利,也无法在经济发展面前更好地保护它们。这其实就是对非人类物种权利的实用主义看法。[9]这种论证思路其实已经脱离了非人物种的内在价值,又回到经典哲学的人类主体论了。
(二)整体主义思路
基于个体主义的内在价值论证并没有摆脱传统道德哲学中的人道主义伦理学(humane ethic)的束缚。是否可以把对动物的道德关怀从对动物个体的分析上扩展为生态整体?沿着这一思路,发展出了内在价值论的整体主义思路。由于所有物种乃至非生命存在(水、土壤、大气等)都对维持、促进生物共同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审美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生物共同体中所有促进共同体利益的存在物给予道德关怀似乎成为一种合理的考虑。这就大大拓展了道德关怀乃至权利理论所涉及的领域。[10]和生物中心或生命中心主义强调对生命个体尊重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认为应首先关注生态整体的内在价值和利益,强调生态整体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内在价值。[11]
典型的整体主义者如罗尔斯顿,主张把局限于个体的伦理关怀推向生态系统整体,并提出了罗尔斯顿版本的内在价值论。[12]根据他的看法,自然的内在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非工具价值、客观存在的价值、非关系的价值。内在价值论和传统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性(naturalness,即非人类主体的创造)而传统价值论则强调人的价值赋予性。“自然性”这个概念说明了为何我们总是在潜意识里反对那些对自然的拙劣仿造。对自然性的承认,也就是对外在于、高于我们的存在的承认,因此我们又总是反对对自然进行大尺度的干涉,与之相对,我们通常接受对自然进行小范围内的改造,因为后者不容易破坏这种外在于我们的更高存在。[13]坚持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不成问题,问题是这种内在价值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14]卡利科认为,所有内在价值论都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内在价值,因此,罗尔斯顿所谓自然界的客观价值不过是经过伪装的主观价值而已。[15]
即便离开人类,自然也有自己的需求、利益和价值,因为自然本来就在履行生物功能,并提供了与生物进化需求相适应的系统。这意味着,自然有自己的“理性”,套用康德的道德理论,自然是其自身的目的。无机物和有机生命共同构成了作为主体的自然,任何对自然的破坏因此都因为破坏了自然的自主性而是不道德的,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就站不住脚了[16]。有学者指出,从自然界中其他物种存在感觉能力来推导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其实犯了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谬误:我们是从主观上来认为客观存在具有客观价值。而休谟早就道破了这种所谓的客观价值只能够存在于主体之中而不可能到达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对内在价值的论证,不能通过把内在价值等同于自然物的某些固有属性(如感受幸福的能力)而得到证成。因此,对内在价值的论证只有打破笛卡尔的主客二分体系才可能做到。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的基本理论由量子论给出,量子论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并非彼此独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因此无论是人的内在价值还是自然的内在价值都处于一种关系模式之中,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独立的价值主体,内在价值只不过是自我的一种自然延伸,与之相对,自我也不过是自然的延伸。[17]因此,如果理解了人类自我也就理解了自然,理解了自然也就理解了人类自我。如果自然和自我并不是主客二分的两边,而是交互的、连续的统一体,那么说自我具有内在价值也就等于承认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反过来也一样,说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也就承认了自我具有内在价值。[18]也有学者反对把经过误读的量子论引入对内在价值的证成上,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自然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存在都不依赖于人的“观察”,自然界的宏观领域和理论物理学光子理论所揭示的微观领域不具可比性。其他物种拥有为了自身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利益追求,这样的利益完全和人的干涉无关。[19]
此外,整体主义思路下的自然价值论对远离人类社会的荒野自然的价值也进行了研究,承认了荒野自然的内在价值。把自然比作机器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灾害,这使一些学者放弃了机械自然观,而去荒野、原始地带等未被人类文明污染的地方去寻找自然。[20]爱默生指出,在纯粹的荒山野岭中独自与大自然达到完全的交融,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工业文明只不过是由一些看似严肃却没有意义的琐事构成,而所有的发明创造、城镇宫殿对真正的生命而言也就失去了看似重要的价值。[21]但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荒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人类的文化建构,很多学者只是用经过浪漫主义处理的荒野来反抗现代性而已,激进的环境主义者试图保存的荒野往往是他们脑中幻想的荒野,而绝非现实的生态系统。这种逃避现实的做法恰恰构成了深层生态学的环境伦理及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看法的特征。[22]
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中的新视角
无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论还是内在价值论,其方法论都主要是借助于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而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些运用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乃至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这些研究视角既可以用于对工具论的论证,也可以用于对内在价值论的论证,下文介绍三种较为典型的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以增进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了解。
(一)视觉的视角:风景画
自然与社会、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仅仅只是生态哲学关注的领域,环境史学、环境社会学以及环境人类学对此问题也有深入研究,生态哲学可以借鉴这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通过对风景绘画的研究,可以较为客观地描述历史上特定时期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风景画记录了外部自然在人类视野中变迁的历史,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变迁的比较“客观”的反映。
例如,科斯格罗夫(Cosgrove)揭示了透视画法源于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几何学理论的重新发现与修正,透视画法与地图绘制、土地勘测、制图术和航海术等社会实践密切相关,而这些技术是威尼斯海上实力和商业发展的基础,[23]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技术手段。米切尔(Mitchell)则认为风景绘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特定技术。尽管风景画体现了特定的绘画技术和风景内容,但它同样表达了社会和文化价值。米切尔考察了帝国权力对被征服领地的视觉重建,他认为风景画是权力形式的直接表达,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关于风景的概念只能形成对大地的敌对态度。[24]奥尔维格(Olwig)则把介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风景绘画的争论扩展到了性别问题上。他认为在美国文明中女性被赋了和大地同样的屈服地位,风景画因此主要是白人成年男性的视觉文化。[25]对风景绘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研究揭示了西方的文化艺术与殖民主义和对自然剥削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听觉的视角:卡鲁里人
菲尔德(Feld)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鲁里人的听觉中心主义文化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西方人对自然的视觉中心主义态度(如风景绘画在西方艺术中的基础地位)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原初关系。西方人习惯于从客观的立场观看外界自然,这是一种站在自然远方而疏离自然的主客二分法。而卡鲁里人则身处自然之中聆听自然,自然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外在的landscape而是内在的soundscape,卡鲁里人用自然界中不同的声音(如鸟鸣、蛙叫、昆虫声、不同的水声等)来标记一天中不同的时段、一年中不同的季节、节气等。卡鲁里人正是通过自然界的不同声音来理解、认识自然的多样性的。[26]这类研究显然大大拓展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面向,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中心论的片面性。
西方文化对自然的视觉中心主义理解隐含了精英统治主义和男性主导主义,对视觉中心主义模式的批判因此既可以为个人自由的解放,也可以为更加广泛的环境政治运动提供动力。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进路使一些学者意识到,对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然意象进行深入分析可能对理解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大有助益。
(三)文学的视角:浪漫主义
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另外一种新视角。例如贝特认为,当代的环境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直接遗产。尊重地球的生态主义态度、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批判观点“直接来源于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以华兹华斯、莫里斯、拉斯金、缪尔、梭罗等为代表。如华兹华斯的《湖区指南》(Guide to the Lakes)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生态学的代表作品,这本书深刻考察了人类与其物质环境的关系,并十分注重人类对待环境的态度及环境管理。就其研究了居民与其居住地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言,浪漫主义似乎又成了生态区域主义的理论先声。[27]
浪漫主义文学在现代观念对自然的重构,如“地方虚构”(place myths)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厄里(Urry)指出,浪漫主义语言不仅在指引游客的导游宣传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保护荒野景区的话语中也影响甚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护荒野和宣传旅游本就是相互矛盾的。具有诸多价值的自然完全是通过环境主义者和绿色话语制造出来的产物。以英国的湖区(Lake District)为例,对英国西北部湖区的描述话语与管理方式完全体现了英国南部一定社会群体的观念。[28]对作为浪漫主义概念的“壮丽”(sublime)之欣赏在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区域主义中也得到了具体的表达,自然壮丽的景观往往令人产生一种震惊的体验,而有资格经历这种体验的人往往并不是普通大众而是社会精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壮丽的体验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体系,并在环境保护和绿色运动中得到了体现。[29]这种话语体系无疑缔造了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独立价值的并超越于人类社会的实体的形象,在对自然错综复杂的认识迷径中,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似乎越来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自然价值论:一方面把自然表述为社会历史的建构结果,另一方面则强调自然独立于人类社会而拥有内在价值。
除上述三种视角之外,西方生态哲学还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例如吉尔贝特(Giblett)检视了沼泽、湿地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的地位,他认为沼泽、湿地在西方文化的想象中具有双重特性:既被设想成为生命提供富饶的资源又被设想成令人窒息的、散发着恶臭的死亡之地。而后者似乎成为我们重建沼泽意象的主导方面,这种意象又为我们合法地开发、征服沼泽地提供了合理性证明。[30]毕肖普(Bishop)则以植物的符号、文化学意义为切入点,分析了植物灵魂的隐喻。植物世界在西方文化的想象中也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是活力、精力、生长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静止、呆板、单一甚至死亡的世界,西方文化显然更为强调后者。这表明了西方文化是一种积极的、进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重视死亡的意义、无法容忍失败、害怕体会深切的情感。[31]毕肖普因此呼吁一种为“绿色意识”提供基础的生态学,通过这种生态学来重新连接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而费尔南德兹(Fernandez)认为,自然界的象征意义有时比语言和经验的理解力更为强大,正是通过自然界的象征性,环境经验与环境价值达到了辩证统一,而文化和自然在发生根源和人类实践上才达到了双重统一。经验世界的象征体系对于道德和共同体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作为象征性的“树”可以赋予社会生活以生命意义,并使得把共同体想象成为富有活力的整体得以可能。[32]对隐喻和象征的研究、考察,目的都是为了从对自然的操作主义中逃离出来,重建人与自然的本真的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
四、批判性超越:作为生态整体的“人-社会-自然”
事实上,无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论、内在价值论还是方法论的新视角都未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生态文明需求的理解。其理论上共同的失败是割裂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图景。不仅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整体,“人-社会-自然”更是一个扩展了的生态整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学者认为只要理解并实践了马克思本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这其实是一种对早期马克思论述的理想主义态度。[33]事实上,实践马克思的论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基本都是片段式的箴言,而非如资本论那样成熟系统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生态危机时代中进一步完善、发挥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此外,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误解为卢梭的浪漫主义,因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理论,已经是在人类科技高度发展下的更高层次的统一,而非人与自然那种原始社会中的虚假统一。因此,马克思绝不可能主张我们放弃现代文明的成果赤裸裸地返回原始社会。[34]基于这两个理论前提,可以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合理重构。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不可能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论提供存在空间,因为马克思过于强调了人对自然的超越而非自然自身的独立。[35]然而,本文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论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并不矛盾。自然固然具有内在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消失而消失。但在一个没有理性存在物存在的世界上,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具有认知意义,自然内在价值的(认知)意义只能来自自然自身的理性进化(人或其他理性存在者)。说人与自然统一不是要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恰恰是要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找到意义,这个意义当然是相对于理性存在而言的,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理性存在的生存论基础就是自然,因此这个意义其实是自然通过自身而提供的。把自然内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看法,其实是现代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典型特征,因此有学者指出,要正确继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洞见,必须“摧毁现代性的科学主义文化及其形而上学基础。”[36]汤因比也指出,虽然“在思维法则中,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37]思维与存在、意识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因此只能是共生的。
按照青年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也就是说,“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社会”是人与自然相和谐基础上的社会。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终“和解”的理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消亡的基础上的,“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这种看似悖谬的表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相。“人是自然的人”,以现象学的方法给出了人的存在样式,人的主体性是其与自然的关系在某一程度上的表达,一切先验的设定都只是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的主观想象。在意义先行的真实世界中,意识哲学的大厦欠缺一个牢固的地基:自然。理性的可能性条件并非孕育在先验逻辑构想出的时空、因果性和范畴之中,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人在自然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因果性其实是自然的因果性(而非主体的先验构造)。“自然是人的自然”并非认识论命题,“自然是人的自然”与“人是自然的人”同样都是存在论层面的命题,是一个在朴素唯物主义和意识哲学中难以被恰当地理解的存在论命题。由于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不过是在它自己的意识中展示自身,“自然是人的自然”真实含义:自然是它自己——而非被异化的非人的“自然”——“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8]
正是在此意义上,才能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下述经典论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9]187由于人自身就现实的包含着自然界积聚的所有潜能,即人不过就是无机自然有机化(有机化这一过程本身也是自然的)的最高形态,因此人的真实本质中必然蕴含着自然的从而生态的稳定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将被社会(共产的、非异化的人类社会)扬弃,形成“人-社会-自然”的生态整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