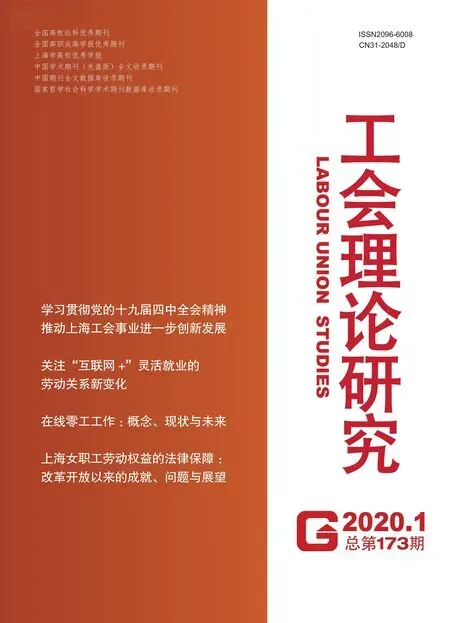关注“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新变化
肖 巍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和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特别是促进充分就业都有重要作用,而其中的灵活就业颇为引人关注。“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组织编写)。按照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灵活就业)主要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和临时就业等形式。http://www.mohrss.gov.cn/fgs/syshehuibaoxianfa/201208/t20120806_28571.html.已经不是一个陌生概念。根据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的《灵活用工业务现状与趋势报告》(2017年),灵活就业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12.9%)、互联网行业(11.2%)和批发零售行业(9.5%);从岗位上看,使用率最高的岗位依次为前台(49.6%)、IT人员(46.12%)和办公室行政人员(45.69%);从地域上看,上海、北京和广州的灵活用工比例最高,全国一半以上的灵活用工出现在那里(57.5%),其中又以上海最高(35.9%)。无论是专业型岗位(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近两成),还是通用型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也超过半数),4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都超过了八成。②叶赟:《灵活用工时代到来》,载《劳动报》,2019年4月8日。灵活就业工作及其结构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应该予以认真关注。
一、“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新经济新业态的“标配”,原来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灵活就业形式也搭上了网络平台的班车。以往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临时工、固定期限的合同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和老年工,而现在“互联网+”灵活就业或利用网络平台的灵活就业,则是通过“平台—个人”或“企业—平台—个人”等连接方式进行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不断扩大。这种灵活就业方式也是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经常被表述为“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或“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的主要劳动形态。区别于传统就业,“互联网+”灵活就业利用网络技术配置劳动资源,具有就业方式灵活、工作时间和场所不固定和“去组织化”等特点。
2017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指出,全球范围零工经济劳动者占劳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16%(2005年是10%);2016年,欧美15个国家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有1.6亿人,还有20%-30%的人或多或少也从事独立非传统的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在建筑、交通、家政和个人服务领域,医疗、法律和创意产业也是吸引他们的地方。①MGI,Independent work:Choice,necessity,and the gig economy,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independent-work-choice-necessity-and-the-gig-economy.MGI估计中国现有300万个零工经济从业者,到2025年这个数字可能增长20多倍,将突破7200万人。根据《2018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的数据,美国有超过40%的劳动者受雇于“非传统用工安排”,包括临时工、兼职或者零工,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要求受访者预测2020年其所在企业的员工构成时,有37%的受访者预计合同工会增加,33%预计自由职业者会增加,28%预计零工会增加。迫于改善服务、快速应变和发现新技能的压力,人力资源和企业领导正在加快重新规划以优化劳动力生态系统。②《德勤2018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human-capital/articles/global-human-capital-trends-2018.html.
“互联网+”灵活就业颇受年轻人欢迎,他们喜欢网络直播、付费阅读的创作和编辑、视频制作和分享,以美国Viemo、法国Dailymotion、快手为代表的视频制作和分享平台参与者每天数以千万计,快手注册用户超过了7亿,每天生产1000多万条内容,每天活跃用户也超过了1亿。我国网络直播用户已将近全国网民的一半,超过3.4亿,许多人通过网络平台和移动终端,在快递、交通、家政、维修等服务行业从事灵活工作。灵活就业的种类不断丰富,覆盖领域不断扩大,不但有劳动密集型工种,也有中高端技术类工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的应用对后者有很大需求;还有法律、财务、人力资源等专业性较强的职能型工种,如兼职的讲师、律师、短期合同工、执业顾问等。有报道称,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PWC)宣布于2019年2月开始,在香港、内地和澳门正式全面落实灵活工作制度。③《普华永道明年2月起执行“灵活工作”制度》,http://news.esnai.com/2018/1217/183846.shtml.全球各地还有不少全职工作者也在从事灵活工作,他们注册网约车司机,在网上进行二手货交易、远程教育、民宿出租等。
“互联网+”平台和应用不断向传统产业领域渗透并重组有关资源,催生新的经济业态、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新的灵活就业方式,并将传统“企业—员工”雇佣方式转变为通过网络平台转包或外包给自由职业者或小型团队做。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网约车用户的普及率由26.3%提高到43.2%,在线外卖用户普及率由16.5%提高到45.4%,共享住宿用户普及率由1.5%提高到9.9%,共享医疗用户普及率由11.1%提高到19.9%;网约出租车客运量占比从9.5%提高到36.3%,网约车服务收入年均增速为35.3%,是传统出租车服务的2.7倍;共享住宿收入占比从2.3%提高到6.1%(年均增速为45.7%,是传统住宿业客房收入的12.7倍);在线外卖收入占餐饮业收入的比重从1.4%提高到10.6%(年均增速为117.5%,是传统餐饮业的12.1倍)。近三年来,这种新业态对出行、住宿、餐饮等行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分别为每年1.6、2.1和1.6个百分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29420亿元(比上年增长41.6%),从市场结构来看,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三个领域的共享经济交易规模位居前三;从发展速度来看,生产能力、共享办公、知识技能三个领域增长最快(分别较上年增长97.5%、87.3%和70.3%);共享经济参与人数为7.6亿人(2017年超过7亿人,2016年超过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的数量为7500万人(比上年增长7.1%,2016年约6000万人),平台员工数为598万人(比上年增长7.5%)。共享经济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快速增长和消费方式转型的新动能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18年底,全球305家独角兽企业中有中国企业83家,其中具有典型共享经济属性的中国企业34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41%)。①《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http://www.sic.gov.cn/News/568/9906.htm.由此可见,在灵活就业工作密集的共享经济领域,无论新业态参与者还是服务提供者的增长速度都相当可观。还有研究表明,平台灵活就业者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传统灵活就业者,年轻化趋势更加明显,灵活就业方式更容易被女性所接受,对外地户籍的劳动者也更有吸引力。②詹婧、王艺、孟续铎:《互联网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第134-146页。
“互联网+”经济大大增强了就业的灵活性,体现了新经济形态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为此,国际劳工组织(ILO)已不再坚持原来的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的单向倡导,鼓励正规就业也可以转向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也大幅度改变了原先较低技能的属性,加快融入高附加值、高透明度的创新企业和商业模式。许多公司的研发现在已是通过外包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来完成了。当然,劳动和资本各自所理解的灵活性是很不一样的,雇主关心的是可以更灵活地雇佣或解雇员工,随行就市地支付劳动报酬,而不必承担社会保障费用;而对于劳动者来说,灵活性带来了更多选择性和更大自主权,但他们同时也要面对充满变数的不确定性。
二、雇佣劳动者,还是自由职业者?
冷战后期,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福利负担日益沉重,经济不景气更导致失业问题严重,迫使这些国家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改革,主要措施就是推行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场所等非正规就业和提高领取退休金门槛,以缓解就业压力。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并产生较强的示范性,逐渐形成全球劳动力市场改革趋势。我国近年来的新增就业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灵活就业。与以往灵活就业不同的是,“互联网+”的灵活就业主要是在网络平台进行,就业方式有用工主体与从业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自营模式”,平台作为中介的“信息服务模式”,具有合作特征接受平台管理的“新型共享模式”以及平台采取直接雇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新型用工等形式进行的“多元混合模式”。①参见刘燕斌主编:《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去组织化”(deorganizition)特点主要是通过在线平台(on-line platform)提供产品和服务表现出来的。“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就业方式,还是以技术的根本性变革为基础的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技术进步为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方式。”②刘剑:《实现灵活化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对雇佣关系的影响》,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年第14期,第77-83页。除了少数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名副其实的“零工”,大多数灵活从业劳动者是将零工专职化,“例如,共享出行的司机从原来的空闲时间从事此类工作转变为专职化的从事共享经济按件式的、接单式的劳动。此时的用工形态即应当表现为劳动提供者专职化的、固定化的‘打零工’的形态。”③于莹:《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49-60页。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提供的数据,滴滴出行平台已经为去产能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职工提供了393.1万个工作和收入机会,为复员、转业军人提供了178万个工作和收入机会。在生活服务领域,截至2017年底,美团外卖配送活跃骑手人数超过50万人,其中15.6万人曾经是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工人,占31.2%。这进而使得灵活就业方式构成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
表面上看,这种灵活就业的确为从业的劳动者提供了某些自由,但其实劳动者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技术上更加依赖资本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弹性工作制有利于员工进行工作—闲暇平衡(work-leisure balance,WLB),从而提高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管理与运营的灵活性,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企业在日益复杂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因时而变的动态竞争力。”④刘剑:《实现灵活化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对雇佣关系的影响》,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年第14期,第77-83页。因为任何新技术包括网络技术都是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不同的是,以往劳动者受雇于实体化的雇主,在固定的时间、场所从事劳动工作,“互联网+”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劳动者与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客户建立了交易平台。但吊诡的是,平台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雇主,而只肯承认与劳动者存在某种“合作/伙伴关系”,这也就规避了传统劳动关系要求雇主(资本)对雇员(劳动者)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大多数灵活就业劳动者似乎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劳动者身份。
“互联网+”灵活就业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他们更愿意接受平台提供的就业机会,他们看好比较自由的工作状态和多样化的工作体验,年轻人尤其如此。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工厂车间流水线,选择网约车、快递、外卖等灵活工作。据美团点评研究院报告,美团骑手的31%来自去产能产业工人,16%为餐饮业从业人员,13%为个体户和小生意人;这些骑手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66%,其中大学生的比例为16%;高达24%的骑手还保持着学习和阅读的习惯。①《钱和自由一个也不能少,这届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614.问题是,“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及其主体该如何确定呢?近年来,不少有关争议就是在灵活就业劳动者究竟是“雇员”还是“自由职业者”或“独立承包者”问题上产生的。首先要确定被雇佣的劳动者身份,才能进行包括法定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失业和工伤救济资格、退休金领取,乃至集体谈判等活动;否则,所谓“标准劳动关系”②我国劳动法规有关“标准劳动关系”的理解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劳动者与《劳动法》规定范畴内的用人单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二是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以劳动力和相应的报酬作为对价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三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权,双方形成人身隶属关系。还有更简洁的表述:全职工作、隶属单一雇主和工资形式的收入。要求的劳动立法、集体协议、司法裁决便无从谈起。这种“对企业来说是弹性用工,对劳动者来说是灵活就业,对劳资双方来说则是非标准劳动关系”③董保华:《论非标准劳动关系》,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第50-57页。的就业方式,传统的劳动关系已不好说明。
灵活就业减少了对资本的管制,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配置资源,不但节约了劳动成本,还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何乐而不为?从业者只需在平台注册就能揽活成为事实上的“雇员”,但也因此出现了平台对这些人员的行为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以及有关风险分配等问题。按照国际劳工大会会议报告(2006年)的说法,非标准的新型劳动关系“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也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的就业身份变得不明确,并因此而处于通常与一种雇佣关系相联系的保护范围之外”;也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应该被劳动和就业法律保护的劳动者没有受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保护”。④国际劳工大会第95届会议(2006年):报告五(1)《雇佣关系》,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2005/105B09_8_engl.pdf.
三、劳动从属性非标准化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一开始就是劳动成为资本对立面的“形式条件”。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来获得生活资料,而且这正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理由,资本通过货币形式与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力即雇佣劳动进行“交换”。劳动者所提供的就是对象化劳动,由于“劳动的对象条件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而如果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考察这些条件,它们就只是对象化形式的劳动时间”;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劳动者只有在付出劳动之后得到工资,同时创造了超出这份工资的“剩余”,“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马克思因此是第一个揭示资本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占有“剩余”的思想家。
事实上,所谓劳动关系就是建立在劳资关系这个现实基础上,即劳动者通过与作为劳动使用者的资方、雇主或用人单位(Employers,“用人单位”是我国的特有概念,还包括非企业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劳动(或生产劳动)而产生利益;资方、雇主或“用人单位”占有这些利益再从中支付一部分给劳动者作为工资、补贴和各种福利。这种劳动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中普遍存在,一百多年来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显然,劳动关系的关键是劳动者对于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的从属性。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为一方,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作为另一方。在传统劳动关系中,作为劳动者对方的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具有排他性即单一的,劳动者的劳动是为了实现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的利益,然后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表现为工资等形式的其中部分收益。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从属于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的。“‘从属性’构成了劳动关系的独有特征,是劳动关系与其他领域的法律关系相区别的关键点……无论是人格从属性还是经济从属性,都外在地表现为劳动者对雇主构建的生产组织的依赖。”①董保华:《论非标准劳动关系》,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第50-57页。
现在,从事“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从平台那里接单,为下单的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其工作时间、场所往往比较自由,其报酬也并非来自单一的雇主而是来自客户,那么这里还有没有从属性?或者从属性如何体现?如果说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工作内容及履行方式服从平台的指挥,平台还可以对其工作进行监督,这是劳动者的个人从属性;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及其所进行的工作仍然来自雇主业务包括外包业务的组成部分(如果可以这样认定的话),这是劳动者的经济从属性;但灵活就业不但工作时间、场所多样性灵活化了,而且根据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这相当于承认多重即非单一雇主的劳动关系),此外还有以劳务派遣机构作为第三方的三方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与派遣机构之间是民事关系,派遣机构与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则是用工关系;这样,劳动者的组织从属性的确弱化了。
“互联网+”灵活就业的用工方式,工作时间、场所比较灵活、支付报酬多样化,已不具备传统劳动关系的某些要件,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改变劳动者受雇佣的实质,“用工者利用网络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技术控制,就是劳动过程中出现以网络信息技术主导下的新型控制方式,企业对劳动者的管理策略由传统的考勤考绩开始转向对劳动者劳动信誉、服务质量、实际业绩的评价与分配,网络技术与传播使得企业对劳动者管理呈现出越来越细致和严格的趋势。……换言之,网络用工条件下,企业用工的身份性不断淡化,而控制性逐步强化”。②秦国荣:《网络用工与劳动法的理论革新及实践应对》,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4-61页。平台信息被用于劳动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资本通过拥有生产资料占有利益的基本事实似乎被隐蔽了,但无论信息供应还是收入报酬,都只能由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利润部分来实现。恐怕谁也不能否认,“互联网+”灵活就业使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更方便更自主地安排工作时间、场所,作为一种非标准就业,③参见王永洁:《国际视野中的非标准就业与中国背景下的解读——兼论中国非标准就业的规模与特征》,载《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第95-115页。作者认为,“非标准就业,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多方雇佣关系(典型的是劳务派遣)、临时性雇佣(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和季节性用工)和非雇佣关系用工(隐蔽性雇佣或依赖性自雇)等”。最后一种非雇佣关系用工主要出现在网络平台经济活动中。他们可以拥有较多的灵活工作和兼职机会,甚至还可以拥有如网约车、SOHO作坊这样的生产资料,但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的劳动,所提供的是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这还需要认定)的产品和服务,并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利润中获得报酬,这一切还是要受控于资本、雇主或用人单位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当今世界,各国劳动关系都呈现出不可逆转的非标准化趋势。灵活就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张,新的业态还在涌现,发展情况也变化多端;从业者的人事管理、报酬待遇和劳动保护都与传统劳动关系很不一样。不过,“劳动关系认定与否并不取决于业态或商业模式,即使在‘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中,仍然有从属性劳动与独立劳动及中间类型之分,尽管由当事人双方选择签订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但劳动关系认定所看重的依然是劳动用工事实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而不是双方签约时的‘认识’”。①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载《法学》,2018年第4期,第57-72页。必须承认,仍然沿用标准劳动关系来认定“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已经捉襟见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适应“互联网+”的新型劳动关系,就难以推进适用灵活就业的劳动法规,无论对于灵活就业的健康发展还是从业者的法律救济和社会保障都是很不利的。正如有研究注意到,“我国现有劳动立法过于突出劳动者的外在身份性,而忽略了判定劳动者标准的实质控制性;过于强调书面劳动合同的象征性证据意义,而忽略了劳动用工关系的实际内涵及判别标准,导致了现有立法难以对类似网络用工这种劳动关系进行判别与调整”。②秦国荣:《网络用工与劳动法的理论革新及实践应对》,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4-61页。我国劳动主管部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③根据这个《通知》,劳动关系成立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已提出劳动者的工作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条件之一,但网络平台是否属于业务组成部分就是因“互联网+”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这也是网约工是否适用劳动关系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理论上,作为劳动者,每一个灵活就业的从业者都应享有劳动权利,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因此很有必要对现行劳动法规的解释空间做出相应调整,并进一步确认典型判例,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复杂多变的劳动关系标准化。
四、重要的是“灵活安全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劳动的确定形式无关紧要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从而引起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灵活性”。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0页。这就意味着劳动关系的实质是资本使用劳动力,而不在于其形式多么灵活。由于资本在劳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劳动法规就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劳动关系的结构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是资本流动性增强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表明劳动的灵活性进而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指面对经济的变化,就业量或工作时间(劳动投入)或工资(劳动成本)进行相应调整的灵活程度。”①〔德〕桑德林·卡则斯、伊莲娜·纳斯波洛娃著,黄安余译:《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平衡灵活性与安全性——中东欧的经验》,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而且劳资双方都有短期化的机会主义意向,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契约正在快速向交易契约(劳务关系)转变。
我国政府也早在“十五计划”(2001-2005年)时期就提出实行灵活的就业形式,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更明确要求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以往的灵活就业主要是指劳动密集型的非正规就业,吸收了一大批技能不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而在“互联网+”灵活就业活动中,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劳资双方均感到所谓稳定的劳动契约已变得无关紧要与不经济,因为这种‘稳定’对用工方而言会束缚资本流动,减损市场竞争力;对劳方而言会束缚契约与择业自由,减损其预期收益”。②秦国荣:《网络用工与劳动法的理论革新及实践应对》,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4-61页。从业者基本不签劳动合同,劳动者与平台公司的合约(协议)也是通过注册实现的,他可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如网约车、民居),自己来安排工作时间和场所。这种就业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的博弈及其结果,双方甚至多方的权利和责任都越来越模糊了,无论是平台公司还是灵活就业劳动者如果只肯签劳务协议而不签劳动关系合同,就带来了有关劳动法规缺失的各种风险,并大大增加了劳动保护的难度。
网络平台通过信息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者可以用比较灵活的方式获得工作,事实上平台也因此拥有了更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而且作为劳动的对方或资方,它不再需要对劳动者的福利、保险、培训等负有责任。这就突破了基于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法规约束,出现了劳动保护的灰色地带。“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属性’标准已经不足以界定和诠释这种新型劳动关系呈现的新特点,也不能有效防范和规避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风险。”③魏益华、谭建萍:《互联网经济中新型劳动关系的风险防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第84-90页。我国目前有关劳动法规的调整主要针对劳务派遣和临时工,而未涉及“互联网+”灵活就业情况;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灵活就业劳动争议已明显暴露了有关制度法规供给不足,既无法实现劳资利益的平衡并保护劳动者,更可能危及互联网企业的健康发展。④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标准工作缺少的基本保障概括为:劳动力市场保障(由宏观经济政策保障的充分就业机会);就业保障(对雇主单方解雇的保障、有关解雇和雇佣的规定、与经济变动相应的职业保障);工作保障(包括合适的职业规划、有机会通过提升能力来发展职业意识);劳动保障(职业安全卫生保障、全面的职业安全卫生规则、对工作时间的限制);技术再生产保障(获取技术与保持技术的全面机会、全面的技术更新手段、全面的学徒和就业培训);收入保障(收入受到法律的保障);代表保障(可以通过工会以及社会对话机制发出集体声音)。参见国际劳工大会第90届会议(2002年):报告六《体面劳动与非正规经济》,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90/pdf/rep-vi.pdf.特别是考虑到“互联网+”灵活就业劳动者即便在同一平台也很少有交流,身份认同度很低,他们对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劳动争议权都很陌生,集体谈判更遥不可及,一旦发生规模纠纷就很容易引发无序乃至失控的激烈行动。
20世纪末,欧盟峰会(EU Summits)已就如何协调就业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关系问题提出“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概念,并将灵活安全性作为促进21世纪欧洲就业的一个战略目标。2006年,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发布绿皮书将灵活安全性列为制定劳动力市场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里的灵活性主要指劳动力市场适应经济变化而减少管制,而安全性则表现为充分就业,包括获得合理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免遭不公平的歧视,以及失业后能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等各种保障措施。为企业提供更大灵活性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趋势,但同时还要求在企业之外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也不可忽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保障劳动力雇用与解雇、工作组织、薪酬安排等方面所涉劳动关系的适度灵活化,而且提高工作安全、就业安全和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提高弱势群体在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安全性。”①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in Europe 2006, Luxembourg: Office for Publication, 2006.转引自谭金可:《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法制平衡》,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第53-59页。灵活安全性就是要体现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某种平衡,在鼓励增进劳动力市场、企业组织和劳动关系灵活性的同时,加强弱势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性和社会保障,通过一定的社会补偿来抵消灵活规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综合提高工作质量和企业竞争力。当然,推进灵活安全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有相关制度及其保护政策配合,还需要来自立法机构、政府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为此,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实现体面劳动的政策干预,也包括使非标准工作体面化,政策应支持和保护所有劳动者,不论他们以何种方式工作。具体内容包括:(1)填补政府规制的漏洞,对多方参与的工作需要明确责任和义务,保证所有劳动者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2)加强集体谈判机制,培养工会在组织非标准工作者方面的能力,使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对非标准工作作出集体性回应;(3)加强社会保护措施,消除或降低获得社会保障资格的门槛,提髙社会保障项目的可随身转移性,利用补充社会保险项目为所有就业者提供最基本保障;(4)制定应对社会风险和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就业和社会政策,支持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重新设计促进技术与职业发展的失业保险政策。②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世界范围的非标准就业:了解挑战,塑造愿景》,http //www ilo 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34326.pdf.从各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实践看,促进灵活性与安全性平衡的重心是向实现体面劳动而不是标准劳动关系方面转移。
促进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或灵活安全性,既有利于资方、雇主或用人单位的灵活用工需求,盘活资源,提高效率,又要尽力满足劳动者的安全愿望,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适应“互联网+”灵活就业新型劳动关系必须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各种灵活就业及其非标准劳动关系还不适应,大多数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待遇还没有纳入现行劳动法规调整范围,进而也被排除在基于现行劳动法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可以从各地灵活就业劳动者参保比例明显小于他们的实际就业比例情况略见一斑,越是发达和经济活跃的地区这种结构性反差越明显。由于我国劳动法除了保护劳动者权益还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单靠劳动法规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越来越吃力,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劳动法、民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共同支撑;还要尽快改变“个人—单位—社会保障”模式,早日实现“个人-社会保障”模式;并利用“互联网+”条件,提高包括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质量,对社会保险的缴费方式和缴费基数、比例、年限等制定适合灵活就业特征、有利于灵活就业劳动者缴费的办法。
“互联网+”新型劳动关系对我国工会组织依法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更好地为各种就业形式的劳动者服务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包括为灵活就业劳动者提供有法可依的组织性保护,帮助他们在发生争议时能够有效取证和维权;建立线上线下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机制和维权途径;支持与各级工会合作的各种行业联合会,探索适合灵活就业的代表诉讼和集体谈判方式;还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挖掘服务资源,创新服务与维权相结合的组织形态和工作机制,利用网络集思广益,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维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