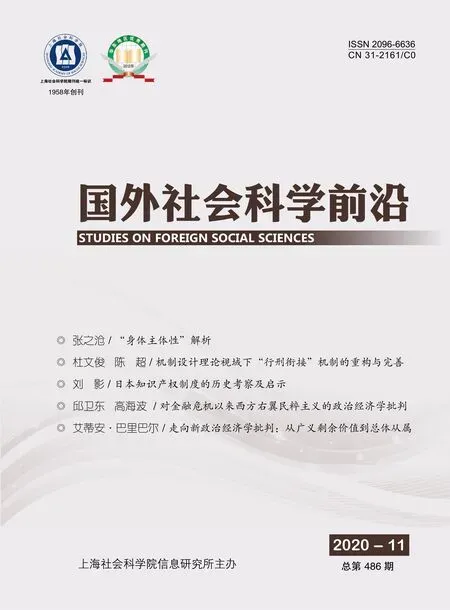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广义剩余价值到总体从属 *
艾蒂安·巴里巴尔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分析了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是如何支配日常生活的。作者首先讨论了剩余价值范畴,提出“剩余健康”概念,其利润不是来自增殖过程,而是直接将创新与增加的消费联系起来。作者称之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广义形式。同时,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价值论的倒置,它否认资本最终缩减为劳动,反而认为劳动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其内在意识形态是将劳动者等同于企业家,目的是蒙骗劳动者。而后,作者提出金融资本创造新“虚拟商品”的过程是维持积累过程的关键,它使再生产过程纳入增殖过程之中,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剥削。作者进而提出“总体从属”概念,即任何未包括在内的东西必须表现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整合的领域。
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架构中,需要重新讨论所有问题。①作者正在研究一个相关项目,这篇文章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有关研究的更广泛背景,请参见Étienne Balibar,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and Religion Again, Radical Philosophy, no. 200, Nov./Dec. 2016, pp. 11-21。这一理论框架明显地与马克思相联系,与其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理论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不谋而合。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有一些差异,甚至是基于对立的假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政治经济学”一词被赋予更专业化的内涵。比如“经济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并不能确保更强的科学性,而是涵盖了特定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一概念隐藏着相当大的谜团,特别是关于它研究对象的界限。这一概念是指向一种辨析吗?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区分和辨析。前者成为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论来源,后者实际上是他对20 世纪的主流经济理论进行的预见。如果不是辨析,那么这一概念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总体上的政治经济学吗?在这种情况下,马
克
思主义本身可能同时成为批判的主体和客体。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庸俗经济学”虽然被马克思否定了,但还是幸存至今。这不仅是由于学术界权力关系的原因,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重视研究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调控机制。通过观察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失败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吸取了其中的教训。但在这里,再一次,我们应该记住,情况远比做一个有倾向性的选择要复杂得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非正统的”流派实际上研究了后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范畴。由此可以表明,主流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回应了马克思,因此以一种辩证的方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新”这一形容词的使用潜藏着一些问题。“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是批判某种马克思都不了解的新的(或相对较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因为马克思论述存在内在的模糊性,让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确切地表述某些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倾向?这样一种新的或经过更新的批判,作为经济理论话语的延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种延续?或者,尽管它在与当代经济学话语的关系上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相似之处,它实际上正尝试创造一种不同的批判理论?再或者,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依赖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已经成为被批判问题一部分,它应该代表一种全新的批判?最后,在这个“新”批判的核心理论中,批判各种论述的关键点在哪里?批判各种制度、社会结构、历史趋势的维度有哪些?
这些困境是抽象的,也不是详尽的。在我提出辩论和条件所涉及的一些内容时,我将牢记这些内容。我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其自身的弱点或难点,而且这些弱点总是和其闪光点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优点比邻而居,①作者借用了大卫·哈维(Daivd Harvey)提出的“承压点”(points of stress)这一概念,他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A Companion to Marx,London: Verso, 2010 and 2013)中广泛使用了这一范畴。好像这些真理的影子一样,在很多的情况下使一切内容都变得晦涩模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首先要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核心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正是它将对剥削分析与积累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我将提出一个广义的剩余价值概念,解除了马克思设定的、来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理论基础的局限,涉及到“总体从属”(total subsumption)的问题。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一问题更好地了解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是如何支配日常生活的。
一、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
正如我们所知,20 世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各种批判解读中有一个“共识”,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引入了社会关系这一“结构性”范畴,而不是对商品和人的拜物教分析。“资本”不是“物”,甚至不是资本家和其他代理人处理和加工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件表面“象征性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物”,比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处置和投资的一笔钱、一笔存款或一个银行账户。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它是一种社会主体、个人和所有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扮演特定的角色,这些角色既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对立的。这直接表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与过程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是在一个过程中形成的,由几个相互交织的过程构成,其中交换过程与消费和生产过程交替出现。这个过程应该是永续的,更严格地说是对应物质的、金融的、制度的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条件进行不断地再生产。但是,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也必须是一种转型。资本是这样一种过程,只有通过自身的转型,才能使自身社会地、历史地得到实现。
为了研究资本这一“过程”及其目标导向和驱动力,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谈论的那种关系、那种“社会效应”,这样所有的一切才能变得清晰起来。这一过程的目标是积累,而这一结果在整个过程再次开始时总是被设定为先决条件,其表现的形式是货币资本寻找投资地点和投资方式。同时,资本关系的具体性质特点是,虽然它们可能广泛地出现在多个社会的层面上,受积累规则控制的社会依赖关系最终归化为或简化为一种敌对的剥削关系,即在生产流程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解释为何对立关系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虽然这种剥削关系会或多或少产生动态冲突,但是没有这种剥削关系就无法维持生活和社会的再生产。我们还需要解释我们如何描述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在这种社会关系中,雇佣劳动者的对立面是资本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种社会阶层是具有全球联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关系、总体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形式、权力的分配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存在许多社会功能和区别:它不再表现为剥削和支配“主体间”的关系,而是不断演变的“社会”与其自身的一种“客观”关系。
我同意路易·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说法,他认为这是马克思认识论决裂点的哲学核心。这种“决裂”是对以往资本意识形态表征的决裂性否定。在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中,这种否定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表征是必要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用的。换句话说,它们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一部分。这种“决裂”更是一种突破,它所指向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发展前提来解决。这一套理论表达了同样的创新。但是在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变革的对抗过程中,这一套理论包含的障碍逐渐明显起来。这里体现了解构策略的必要之处,由于解构策略是通过解构障碍“基本概念”的定义方式来追溯它们的起源,它确定了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中所包含的障碍和困难。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但是当否定或修正某一概念时,必须理解其解释的内涵,必须了解修正这一概念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尤其是什么样的政治影响。
二、关于马克思认识论干扰因素的研究
马克思通过两种伟大的方式定义“资本”这一概念。从我们当代的观点来看,关于马克思认识论的主要干扰因素正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汇点。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互补的,实际上是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资本是一个剥削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依赖于对劳动力的雇佣。马克思有时会借用黑格尔的说法,称这种关系为“本质关系”(essential relation)。①黑格尔用德语称之为“das wesentliche Verhältnis”,这是《本质的逻辑》(Logic of the Essence)第二部分第三章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9 章论述“劳动力的价值(以及相应的价格)转化为工资”时使用了这个词。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剩余价值时,对作为“形式”关系和“本质”关系的“资本”作出了界定,作者对这两种关系进行了分析,具体请参见W. F. Haug (ed.),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erlin: InKrit,Das Argument Verlag, vol. 9, 2018。另一方面,资本又是一个积累过程,这一无限循环的过程是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利润必须通过重建其自身的主要部分才能实现最大化。当然,利润是否可以得到实现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和潜在的矛盾。这两个概念远远不是同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指的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机制的不同方面,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严格相关的。如果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如果有第二个,就有第一个。为什么在二者的交汇点会出现问题?问题的来源有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最终不过是资本化的劳动,因此,“劳动”并不是主流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第二,马克思通过何种方式把劳动与货币形式联系起来;第三,马克思通过何种方式将“生产力”归因于劳动。①作者指的是所谓的“三位一体公式”(Trinity Formula,土地、劳动力、资本共同作为收入/利润的“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 章中批判性地讨论了这一公式,其源自亚当·斯密,至今仍被主流经济学家用作“生产职能”中“主要的生产要素”。自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在1935 年的《竞争伦理》(Ethics of Competition)中使用了“三位一体公式”这一术语以来,芝加哥学派就将“人力资本”作为“第四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职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和积累的论述完全依赖于“价值增殖”(valorization)这一核心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德文文本,就会看到该词对应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②请参考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词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中对“剩余价值”(Mehrwert)条目的具体论述。当然,它们是相互交织的,但问题是结合方式是怎样的。一种内涵得字面意思是“价值的形成”(Wertbildung)。其隐含的概念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生产的产品都采取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必须由某种具有共性的“物质”来决定,而共性“物质”通过产品的交换价值来得到表现。马克思延续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认为这种物质是劳动力,但他进一步限定,这里的劳动力是“抽象的社会劳动”:其数量不能被直接观测到,而是作为交换本身的结果,隐含于或“内化于”市场背后或空隙间形成的“均衡”之中。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循环,抽象劳动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商品交换的比例直接取决于它们所体现的抽象劳动的数量。然而,主要的难点,出现在如何在从价值形成(Wertbildung)的角度阐明“价值增殖”的同时,从资本主义角度来阐明“价值增殖”。剥削(Verwertung)代表着“价值的增殖”,换句话说,代表着增长出来的新价值或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的附加价值。③马克思使用的准数学术语“微分”(“Das Inkrement”或“differential”)是受到19 世纪早期微分学论述的启发。参见D. J. Struik, Marx and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Society, no.12,1948, pp. 181-196。资本家投资并测算价值或计算价格,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将“剩余”进行最大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表面看起来,价值是在市场上“形成”的,是在价值进入自身增长的过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实际上,正确的过程恰恰相反。从第一重价值形成的意义上看,增殖已经存在,因为从第二重含义即产生剩余价值的意义上看,增殖同样存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已经是资本主义市场,最终,“抽象的”社会劳动是通过雇佣劳动的形式表现的、被剥削的社会劳动。正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主义,使劳动同质化和“均等化”。
其他困难与这个公理循环有关。为了解释“盈余”(increment)如何产生,马克思必须解释生产资料的价值已经存在,比如由“过去”的“物化”劳动力构成的财产或股票。由当前劳动力形成的“活”劳动,将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在生产资料价值上添加新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秘密”有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具体”劳动,它保留或重新创造了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的价值;二是作为“抽象”劳动,它创造可衡量的新价值。但事实上,这一切都不是确定的:只有当对价值的预期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以后,也就是说当产品以一种完全随机的方式出售并转换成货币时,一切才有意义。因此,这里遇到相当大的难题:马克思主张价值只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同时他也倾向于将货币的功能中性化,并回归对经济循环的“真实”表现。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在经济循环中,并不是货币控制商品的流通,商品以货币运作的拜物教形式联系和表达它们本身之间的关系。④大卫·哈维和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米歇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其他一些学者坚持了这一观点。具体参见Riccardo Bellofiore, A Monetary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1,no. 1/2, 1989, pp. 1-25。这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未完成的第三卷第25 章中,将信贷的运作以及整个金融过程称为“虚拟资本”。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可能使人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通过使用“虚拟物品”来运转,即使用建立在传统和制度基础的象征性工具来运转。它也可能使人认为,“真实”的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历史趋势和转换,必须纯粹通过劳动关系来解释,即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因为这两种劳动都是受到“价值实现”的货币约束。①“ 虚拟”一词是与马克思的双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即在这两种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第二种循环只能用“倒转的形式”来表达第一种循环。信贷的自治在本质上是“投机性的”,这开启了危机的可能性。一些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凯恩斯,也广泛认同这一观点。
当讨论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这引发一个巨大的难点,它有可能把我们引入相反的论述:即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纯粹的金融过程,仿佛信贷货币及其衍生物可以发展出自己独立的生产力来创造利润,可以完全脱离生产过程,或者更广泛地说,完全脱离促使价值从货币形式有序转型为商品形式的社会关系。没有这种有序转型蜕变,就无法实现两重意义上的增殖。要实现价值的增殖,价值必须实现形式转换。正如马克思所说,它甚至必须永久不停地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从货币交换领域转移到生产和消费领域。②这基本上是苏珊娜·德·布伦霍夫(Suzanne de Brunhoff)在她1973 年的开创性著作《马克思论货币》(Marx on Money, London: Verso, 2015)中的立场。这一观点后来在1979 年 的 著 作(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PUG, 1979)中得到扩展,作者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这本书。
劳动方面也有同样的难点。“劳动的二重性”解释了“增殖”的双重性。从“劳动的二重性”的观点出发,马克思的论证中仍然存在两种对“劳动”的认定方式。这种局促之感通过对“生产力”(Produktivkraft)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使用而变得明显。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描述的是转化为资本投资领域的一切活动:在我之前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通过将货币价值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表达形式,都将产生剩余价值。这一转化产生一种可以资本化或积累的增量,这种增量在资本主义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是指在工业和农业这些物质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具体活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资本“周转”过程中生产与流通之循环的相互渗透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当然可以把运输、通讯等纳入生产领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正式地”与货币资本投资的各种领域相联系的含义,这里的“生产性劳动”是狭义的。这一限制的原因显然是政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被视为产业革命的一种社会产物,而产业革命同时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并潜在地动摇了资本的统治,因此破坏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连续性。③“ 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问题的争议始于重农主义者,他们认为,生产劳动仅限于农业生产,这一争论在亚当·斯密这里得以延续,斯密将生产劳动泛化为每一个增加价值的活动,马克思在以上基础上对“生产性劳动”进行了重新定义,即任何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虽然马克思知道“生产阶级”“无产阶级”和“雇佣工人”这三个类别在分析上是不同的,但他仍然倾向于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确定它们。但我坚持,这是一个对“增殖”来源的狭窄定义:它没有包含所有受雇佣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包含所有受剥削劳动力,特别是那些根据定义不能通过货币来支付工资或补偿的劳动,即通过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历史结合的手段被剥削的、基本上由妇女进行的家务劳动。④参见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哈里特·弗拉德(Harriet Fraad)、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的女性主义批判。并参见作者在《政治概念:一个重要词汇》(Political Concepts: A Critical Lexicon)中对“剥削”的讨论, www.politicalconcepts.org/balibar-exploitation。最后,它没能包括其他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劳动”,但获得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增殖功能,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生产性的”。
在这里,我将通过实验的方式讨论一些例子,而不是从纯粹的概念论证中推导出任何东西。我将研究两个这样的过程,当然,它们可能依赖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是,给人类生活和消费的其他方面“赋予价值”,这些方面在“广泛的意义”上也产生了剩余价值。在讨论这些例子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货币不转变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有生产力”的商品,那么资本就不能存在,也就没有货币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劳动并不是1857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描述的“生产性消费”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必须重思马克思对剥削的某些本质分析,并正视这种矫正带来的所有政治后果。然而,我提出的结果并不一定等于消除资本主义的对抗维度。
三、剩余健康与生物资本的积累
这里提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剩余健康”(surplus-health)。我认为该词是约瑟夫·杜米特(Joseph Dumit)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创造出来的,并在其著作《生命之药》(Drugs for Life)①参见Joseph Dumit, Drugs for Life: Ho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fine Our Health,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这与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的作品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但在这里不做讨论。参见Melinda Cooper, Family Valu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w Social Conservatism, New York: Zone Books, 2017。中做了总结。这个概念仿照了“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力”,将研究角度从生产转到某种消费领域,这一消费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个人生存的能力,决定着是否可以在给定的环境中享受“可接受”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目前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引入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能力相类似的“幸存”能力,一种能够获取药物和医疗服务的能力。②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有两个术语描述这个概念的不同方面和功能:“劳动力”(Arbeitskraft)和“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前者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后者指社会公认的工作能力或专业就业能力。参见Pierre Macherey,Le Sujet des normes,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14。杜米特追求的是,从现象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三重角度对健康和疾病定义的变化、人均药品消费的持续增长以及医药行业健康成本和利润的相关增长进行调查。
第一方面,“疾病”的定义逐渐在变化。从前,疾病意味着医生在临床上对病人做出一种病理学上的诊断,分析病人主体经历的某种痛苦、病理障碍或紊乱。现在疾病逐渐用来形容一种虽然看不见但可通过“生物指标”测量或表示的某种客观条件。比如胆固醇水平的量化定义会定期修订,这或多或少会相应要求医生开具需要终身服用药物(如他汀类药物)的处方。疾病作为一种生活的体验,也可以成为某种被剥削的对象。第二方面,人们面临的疾病从一种不连续状态进入持续状态。现在大多数的疾病是慢性疾病。而且统计学表明,存在一种内在的趋势,随着年龄增长,个人倾向于尽可能频繁、尽可能长时间地消费最大数量的、不同的药物。③这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将生产率的提高与集约化联系起来的做法惊人地相似。因此,《生命之药》这一书名本身就具有讽刺性,吃药是为了活着,抑或为了生存,因此,终生依赖药而活命。无论如何,生命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假体生命”(prosthetic life),也就是依赖性生命。④诚然,每个人的生命总是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依赖于条件,依赖于技术。但是,这是一种新型的依赖,与此同时,这种依赖更加被动,并受到制药行业中经济技术综合公司的力量的控制。第三个方面是:根据市场的“自由”法则(萨伊定律),供给先于需求,实际上创造了供给。至少在“发达”国家,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能够持续增长。这些费用通常由社会保险和个人分摊负担,因此涉及到信用。这种增长是符合制药行业利益的,制药企业可以通过核算投资和回报来决定实验室如何设定“风险的条件”,选择优先开发哪些药物。
马克思认为利润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增殖过程,但这里的利润本质上不仅仅来自生产过程。利润还来自另一种不同的增殖,即直接将创新与增加的消费联系起来。这正是“剩余健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广义形式。考希克·桑德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它阐明了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层面上的人口法则,因此这对于理解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联非常重要。①Kaushik Sunder Rajan, Pharmocracy: Value, Politics and Knowledge in Global Biomedicin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一些药物主要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销售,它们是为这个市场设计的;但是它们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测试。这不仅是因为在印度,制药业可以找到“志愿者”,即提供“知情同意书”的合同病人,更是因为印度有大量的失业贫困人口以这种方式谋生。受测试的人群要符合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某些科学标准,因为只有在某个地区大部分人口还没有开始使用慢性药物,才会发现所谓的药物实验“优质的受试者”。这要求受试者的生物机能还没有改变,他们的生理反应才能为理解和调整药物的影响提供实验模型。通过这一系列重要的新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义剩余价值是一种同时作用于本地市场功能和全球系统条件的社会关系。
四、人力资本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倒置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它的作用不同。正如我们所知,这一范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具有战略性的功能,它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延伸,延伸到一些按照“性质”应该位于经济演算领域之外的领域:包括教育、婚姻、法律和刑罚、慈善事业等。教育与我们的学科特别相关。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建立了相互关联的模型,一方面研究了哪些个人能力中的关键能力可以使人在受雇佣后为雇主实现最大盈利程度,另一方面也研究了生产这些关键能力的成本公式,是如何通过向社会和劳动者家庭内部摊销成本,从而使雇主在获得最大化收入的同时,尽量缩减成本。②参见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19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Gary S.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n Arbor M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研究评估了投资和回报之间的经济相关性,证明经济战略可以实现“理性期望”,也就是说可以将个人能力定义为生产函数。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指定一种最优策略,通过这种策略考量以下三个变量:形成劳动能力的耗时,即需要多少年学习和在哪里学习;个人或集体耗费的成本;通过个人一生收入反映的收益。我并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些模型是否真的“有效”或“具有预测性”。但是,我想坚持我认为应该阐明的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这一范畴并不是在个人主义的视角下产生的。事实上,它出现在20 世纪50 年代,其产生伴随着对于新独立的殖民地如何发展的讨论和计划。位于亚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国家,那时刚刚获得民族独立,面临经济层面的各种问题。它们需要通过自主发展教育、科学和医疗资源,提升“生产力”和扩充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人口。③参见D. Cogneau et al., Développement des pays du Sud, 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developpementeconomique-et-social-developpement-des-pays-du-sud/.这项原则与个人之间的竞争无关,而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关,它与去殖民化和发展方面某种“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关。新自由主义在这里对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一种挪用,将一种具有社会内容的概念转变扭曲为内涵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概念。规划理念走向衰落并被普遍的竞争模式所取代,与这种扭曲紧密相连。
其次,贝克尔的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精英”个人计算成本和收益时,提供定量评价各种优点的理论工具,以及为实现“平等”提供可选的教育策略。实际上,他所谓的“精英”,之所以被预测能更加出类拔萃,是因为进行了更多的投资;他所谓的“平等”就是向教育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其能向所有人提供不同的服务,根据个人能力、野心或坚定程度不同,使个体获得不同程度的“增殖”。①参见Gary Stanley,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n Arbor MI: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这显然是一场政治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其结果是,精英主义制度比平等主义制度更有效,这并不令人意外。不止于此,该模型的一项正式结果表明,只要保持一个普通教育与专业化教育之间的“最优”比例,教育服务私有化将被认为更有效率。由此,公共机构要么被卖给私营企业,要么参照私营企业相同的管理策略来运作。这似乎有一个明确的阶级意图,我们尤其需要考虑到,对孩子教育的个人投资需要已经存在的资本作为支撑。于是,人力资本理论家引入信贷,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投资,以帮助那些无遗产可继承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这被认为是一种民主的纠正措施。然而,与民主相伴的,是大量的债务。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而且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训练参与增殖的进程。
最后,这样的理论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的趋势,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论述有着一种有悖常理却非常容易理解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最终可以缩减为生产性劳动,或者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劳动。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的理论则将劳动称为“人力资本” (Arbeitsvermögen),认为劳动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并可以采取信贷、投资和盈利能力这些资本的方式来进行运行。当然,这里潜在的意识形态,是将个人视为自我雇佣者或者企业家本人。这与正如马克思将不同强度的社会劳动以不同倍数比例缩减为无差别“抽象劳动”的理论非常有效一样,基于相同的原因,这种意识形态也非常有效。如果资本主义需要永久保留大量流离失所、处处逃不过剥削的劳动力储备军,那么必须永远维持对人类能力的差异化并且等级化。这种人类的能力不是通过传统的学科或职业来塑造,而是被组织和标准化,成为资本主义形式。
五、资本主义再生产或“总体从属”
在我向尝试定义“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的方向展开研究时,出现一个转折点:一个稳定的商品化过程,或者创造新的“虚拟商品”的过程,这是维持积累过程的关键。它导致将包括生物、知识或符号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纳入增殖过程之中。这一增殖过程将人的活动“转变”为能通过货币衡量的数字,这一过程也使得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承担的信贷和债务大幅提升。由此,须将生产过程和增殖过程纳入资本本身的定义之中。
我已经讨论了增殖的问题,这一过程即包括价值的形成过程,也包括向现有的资本中增加新价值的过程。增殖的过程包括积累、商品化、金融化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一过程不是纯粹依赖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即“生产性消费”),它更包含了对某种生活能力的剥削。我同意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坚持的,这并不是说增殖不涉及剥削或剥夺,就没有潜在或公开的对抗。①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Socialist Register, vol.40, 2004, pp. 63-87.恰恰相反,无限积累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推动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每项投资都必须事先计划价值的实现。由于私人资本尽可能保持其“流动性”,以便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来攫取利润最大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情境下,是追求股东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所谓的“理性的期望”是包含在银行和对冲基金的决定中,是他们决定支持哪一项投资。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冒险提出一个额外的假设: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用来描述现有产品市场的增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市场的范围超越传统意义上“生产领域”的限制,如何为永不枯竭的额外剩余价值开辟新的来源。资本的增殖不仅在“客体方面”需要劳动和生产,也需要“主体”方面的消费和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强调稳步进行商品化过程的重要性。最终,“商品化”是一种对生命的商品化,通过将其目标、行为或爱好商品化实现的。这个过程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但它在资本主义内部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存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虚拟商品”类别分析在这里是非常宝贵的,虽然我并不赞同有类似自然给定的“虚拟商品”列表存在。相反,“虚拟商品”这种新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健康、教育、知识、娱乐、艺术、护理和情绪等,这不仅为生产部门本身生产“工具”,或为人类主体的“生存”提供物资(参照马克思的两个部类的“有计划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虚拟商品在“制造”自己的主体。然而,我们也必须牢记在波兰尼的理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即是否存在阻碍商品化无限进行的障碍:内部或外部存在的矛盾效应,使增殖无法通过更新的商品化顺利进行。
正是这些客观和主观维度的结合,促使我提出了一个“总体从属”的准马克思主义范畴。我参考了“总体异化”(total alienation)的理论,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再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很多学者阐述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是,我想延伸一个由马克思开创的思想,尽管他留下了一些未出版的晦涩文本。在英文中,“从属”(subsumption)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和哲学范畴。它的意思是某物或某人“服从”(subjected)一种“规范”“法律”或“规则”,因为它是这些规则的一部分,或受该规则的指导。那么问题是:什么从属于什么?人们也许会认为是“某物”或“某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引入第三个本体论范畴时,这个范畴既不是“物”也不是“人”,也不能包含两者,而是“行为”(actions)或“代理”(agency)。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从“形式上的从属”(formal subsumption)到“实际上的从属”(real subsumption)的转变时所使用的方式:一个工人的生产性活动,在这一生产性操作过程中,人利用工具把一项给定物质塑造成一个可用的对象。正是工人的活动被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革命变形为一种集体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操作,而这一集体过程的内容和节奏则被视为机械本身。所以工人只有在工厂的环境下才可以生产或才有“活动能力”,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增殖的“法则”。工人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接受”资本家给他的工作,而且一旦脱离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形态,工人就无法通过自身体力或智力进行生产操作。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仅成为“抽象劳动”,它还被分离为一个过程的“部分活动”(partial activities),失去主体性。当法律上以工资形式表现出来的“形式上的从属”充分“实现”或转化为“实际上的从属”时,剥削就不仅仅是一种支配手段,而是被整合到人类身体和思想之中,或者被彻底地个体化。但是,这种“个体化”还是个性的完全丧失,丧失了个人的身份特性和自主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所希望的解放只是从另一场工业革命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可以用当前的个人活动形式取代集体能力,或者说是集体分配的能力。
然而,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称之为“总体从属”。有迹象显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总是想从两方面进行剥削: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力,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剥削。包括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被认为是“他们自己所有者”社会个体在内,他们消费商品只是为了“再生产”或“恢复”他们的劳动力。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样一个将家庭与市场条件具体地联系起来的再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额外形式的无报酬的家庭劳动。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约束或市场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控制工人消费的质量和数量,以使其对资本来说更加有利可图。例如,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住房或城市的发展以及商品的大规模分配也反映了上面的事实。然而,这只是消费领域的一种“形式上的”从属。随着商品化到达新的阶段,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所描述的,在剩余健康或人力资本方面,资本主义投资已经渗透到护理和教育过程本身之中。
这显然意味着两件事:(1)工作与生活之间、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界限已然消失,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正在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领域;(2)不被商品化影响的个性的维度已然消失,即个体之间没有了主体间性、脆弱性或依赖性。任何形式的生命作为参与者,不论是积极还是被动,甚至痛苦或濒死,都不能脱离其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而存在,而这种价值形式实际上只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瞬间。这并不是将个人的生活缩减为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相反:虽然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是某种“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但是生命的变性,或由此产生的“第二天性”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就是我所说的总体从属(它出现在“形式上的”和“实际上的”从属之后),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外在的东西(没有给“自然的”生命留出任何的空间)。或者,任何未包括在内的东西必须表现为一个残余物,一个有待进一步整合的领域。必须如此吗?整个问题当然如此,道德问题就像政治问题一样:商品化有限度吗?是否存在内部和外部障碍?拉康主义者可能会说:每一种这样的总体化都包含一种不可能的元素,它属于“实在界”(the real);它必须是“并非全部的”(pas tout),或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异质的元素——总体从属的内在剩余——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表现形式明显是个人行为,如病态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活动;有些表现形式则是大众行为,还有一些甚至采取政府行为。或者,它们可能会成为一种展示,在实施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某些困难中表现出来,例如,一旦一种医疗保险制度被合法化,就很难废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