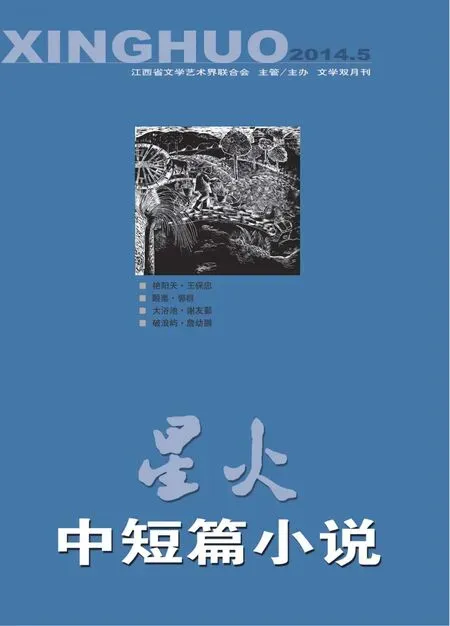敲山公
○冯祉艾
表妹毕业工作后,为了方便照顾姨妈和姨父,带着他们住到了长沙。因为工作繁忙,加上姨父的身体吃不消几个小时的回乡路程,他们这些年很少再回乡下。
姨父说县里已经拨了一笔改造费给村里,等村里人回来得差不多,老家那一片旧房子就要被推倒,之后再按照新农村的蓝图重新打造一个傍山农村。
姨父家的村子靠山,怀化农村独特的山水造就了这片物资丰富的土地,可是也限制了这块土地上农民的发展。村子靠近沅江,三面环山,只有沅江在南面留出一道通风口。村子建在大山脚下,沅江的分支流经村子,给这里的水田发展带来了天然的资源。村里人口多,家家户户都在村口下面的平坦地区开拓田地,河里的水顺着一条条有序分开的田埂流到田里。人们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在水里养起了禾花鱼和田螺,等到夏秋季节就打捞去集市上卖。村里人依靠山水吃饭,但是大自然回馈他们的仅仅是维系温饱。到了表妹上大学的时候,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走出了大山。
去年,表妹家所在的村子列入了新一批农村改造计划中。村子贫穷,留在村里的人多为孤寡空巢老人和儿童,如果没有这个新农村改造计划,这样的农村很快就会慢慢流失掉最新鲜的血液,骨子里的文化和传承也会随着时间枯败。
山里的老房子地基不稳,改造新建残破老旧的屋子是第一步。听说等到老房子拆掉,新房子建好,城里的开发商还打算在这里建造生态度假区。留守在村里的人都渐渐老了,水田的农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吃不消,建设生态区是山里最好的一条出路。
晚上,表妹请我去家里吃饭。饭后,将头顶散射下来灯光融入浑浊的酒水,透明的玻璃瓶上沾着许多细小的米酒沫,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的破碎,酒沫炸开的声音在姨父长时间的安静中格外明显。一瞬间我觉得恍惚。
建设和改造对掩埋于茂密山林里的村子来说是新生的喜悦,可对于已经离家许久的表妹一家人来说,是割舍不下的乡愁。
姨父很是感慨。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农人自家盖的,这些风雨里依靠山水吃饭的庄稼汉,一辈子其实就只是祈愿可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老家的房子没了,心里就总觉得空落落的,仿佛置身于无边大海,瞬间没了寄托。
表妹突然提起了敲山公的土坯屋子。
我听姨妈说过,敲山公是村里的流浪汉,他年轻时有儿有女,可惜人到中年后没有一个愿意赡养他,子女年纪轻轻的就全都跑出了大山,之后便再无音讯。他一个人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因为他常年在村子后面的大山上走动,村里人就喊他敲山公,久而久之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表妹有记忆以来,敲山公没有房子,只在山脚下的一棵大柿子树底下用瓦楞铁皮搭了个简易的小屋,后来倒卖山货换了些钱,他就自己慢慢地盖了一间土坯小屋。
敲山公的屋子和表妹家离得不远,我和表妹幼时经常找他玩耍。
村里人除了种植水田之外,还在半山腰平缓地区种植一些果树。可是因为农活繁忙,加上村里人不懂生态种植,山里的果树结的果实又涩又小,大多成了野树。姨父之前也随着村里人在山坡上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了几十棵猕猴桃树,之后将它们随意荒废在山坡上。我和表妹都是独生子女,为了有个玩伴,母亲把我放在姨妈家住过一段时间。我记得,第一次见敲山公是在八岁那年的秋天。那段时间大人都忙得团团转,他们只好将表妹留在家里看家。敲山公在早上八九点钟敲响了表妹家的铁门,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水桶,水桶没有盖子,只用一块蓝色的破布盖在上面,一条草绳缠绕在桶口,将桶里的东西遮挡个严实。他穿得破旧,上面是一件灰黄色的衬衣,说是灰黄色,其实是衣服上面沾染的泥垢让本来的颜色看不清楚,隐隐约约只能瞧见个大概。衬衫中间少了两颗纽扣,他用路边成熟的草珠子串绳绑在纽扣的位置,制成了简易的纽扣。裤子倒和姨夫一样,是乡下农民常穿的迷彩布裤子,这种裤子耐脏耐磨,非常适合干农活的时候穿。敲山公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村里的男人有些老旧衣服不要的,就会送给敲山公穿。敲山工将这些破烂的衣服剪开再缝补,缝补好的衣服总要穿到缝补不了的程度才肯丢掉。多余出来的边角料用来充当家里的抹布,塑料桶上面盖着的蓝色破布就是从衣服上裁剪下来的。他五官长得周正,两只眼睛看着你时格外精神,眉毛尖尖有几根长寿眉随意地耷拉在眼睛上面,显出几分憨态。皮肤宛如潮湿的黄泥土,枯黄又冒着油光,嘴唇颜色像极了山里的紫黑色野葡萄,除非他咧嘴一笑,露出里面黄黑色的牙齿,不然你都看不太清他嘴巴在哪里。
这个季节,山上的猕猴桃都熟了,姨父没有时间上去采摘,敲山公这个时候就会挑着担子,带着两条大麻袋上山采摘,也叫“敲山”。他过得凄苦,可是却不肯接受别人的施舍,山坡上的果树大多成了无人照管的野树,姨父同意敲山公去采摘,敲山公却时刻记着别人的好,今天早上就送来一桶自己烫的柿子。
敲山公没有财产,陪伴他的只有几片遮风挡雨的瓦楞铁皮和一棵柿子树。秋天柿子成熟,熟透的柿子软软地挂在枝头,这个季节的柿树叶子稀少,鸟雀很容易看到鲜红的柿子,所以挂在枝头的熟柿子很容易被这些飞鸟抢先品尝。有的刚刚开始泛红,果肉还是生硬的,敲山公便爬上树将它们摘下。这种半生半熟的柿子在阳光下晾晒几天,表皮就会慢慢地松软,果肉虽然不及挂在树上的熟柿子,但是里面的柿子核夹杂着旁边成块的果肉,一口下去是嘎吱嘎吱作响,清脆的声音和绵密的口感混合在一起,完全冲淡了生柿子的苦涩感。一棵柿子树可以结很多果实,敲山公一个人吃不完,便采摘了很多青柿子下来制作烫柿子。青柿子是完全没有熟的柿子,这些柿子的柿托还是鲜活的青色,表皮带有一层白白的果霜,一个个地被敲山公提前摘了下来。烫柿子制作简单,将生柿子搁在塑料桶里用滚烫的热水浸泡,之后用一层塑料袋盖在桶口,再用一块布紧紧封上。这样的烫柿子一般隔一天就可以食用。烫好的柿子从水桶里面拿出,原本青涩的表皮已经微微发黄,凑近一闻,扑鼻而来的是一种烫柿子独有的清香味。
敲山公送柿子来的时候姨父他们已经出门收稻子了,他就把满满一桶柿子放在院子里。烫柿子对于农家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姨父他们总是早出晚归,敲山工这时送来的柿子对表妹来说就是极大的诱惑。敲山公见表妹心急,冲我们招招手,然后和她一起围着塑料桶蹲在地上。他把水桶上面的破布掀开,蓝色的破布被他叠好塞进兜里,之后再揭开里层的塑料薄膜。桶外边的遮挡物一揭开,我就猴急地探着脑袋去看。敲山公在里面挑出一个大柿子,搁在手心里变着花样地展示,脸上深褐色的褶子从嘴角往外扩散,骄傲地冲我们炫耀他的劳动成果。烫柿子需要削皮吃,敲山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削竹签的小刀,手指灵活翻转,还不待看清楚,青黄色的柿子肉就被他削好放到表妹手里。小孩子牙齿稚嫩,清脆的柿子肉被牙齿从中间咬断搅碎,果肉里的汁水顿时溢满了整个口腔。
此后我和表妹便经常去找敲山公玩。敲山公是这片村子里最懂土地的人,跟在他身后上山下山,总是会有不同的新玩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而我们也恰好见证了敲山公房子的建成过程。
敲山公五十岁之前没有房子,但是他用自己的双手赶在五十岁那年的冬至之前,终于搭好了一个土坯茅草屋。
第一次制作黏土胚,敲山公花掉了他两年里卖茶果油赚的钱。怀化融水这片土地肥沃,适合茶树生长。敲山公每年秋天就背着麻袋上山去摘野生茶果。山上之前有人种植过茶树林,后来收益不好,一整片茶林就都荒废了。荒废的茶林里面已经长满了荆棘和野树,脚底下的茅草长至腰高,很容易在里面受伤。敲山公腰间别着一把弯刀,手上拿着一根一指粗的木棍,行走时木棍先在草丛里敲打,遇到茅草荆棘拦路,就用弯刀把两旁的荆棘劈开,之后把掉落下来的碎枝整齐地放好堆在一处,这些树枝荆棘晒干后可以背回去当作柴火。
那时我们的个头刚刚超过茅草,跟在敲山公后面像两条甩不掉的小尾巴。敲山公给表妹背了一个用两件破T 恤改成的背包,茶树果子刚好长在我头顶,我需垫着脚尖才可以够到一两个红色的小果,茶果和茶树连接紧密,我借着蹲的力气往下一扯,两个茶果便落到了表妹的小背包里,同时身上也落了不少枯茶叶。敲山公的采茶果技术明显比我们高超,他的手掌很大,一手伸进茶树里面,用力将茶树枝杈分开,另外一只手飞速地在枝条上穿梭,手背划过树叶的“沙沙”声和扯下茶果时清脆的撕扯声融为一体,一套动作下来宛如一幅立体的艺术画。他采茶果的时候不喜欢说话,我们对这件事的好奇心慢慢耗尽,之后就钻进林子里面自己玩去了。等太阳稍稍隐没余晖,敲山公便收拾收拾准备下山,他将表妹兜里的几个小茶果抖落进自己的大麻袋里,之后从怀里掏出两根麻绳系上口,分别挂在扁担的两头。那两袋茶果估摸着比我们两个都重,看他半蹲在地上,咬着腮帮子大喝一声,之后颤抖着身子慢慢直立起来。他将肩头的平衡位置调整好,一手搭在扁担上面,一手牵着表妹慢慢下山。茶果袋子在他身体两侧一高一低来回晃动,敲山公牵着表妹走的步伐与之一致。有些下山路坡滑难走,他的呼吸声也急促起来,嘴边却一直轻哼着山歌。我们诧异一条细窄的竹扁担竟然可以挑起一百来斤的重物,也诧异敲山公身体里面隐藏如此巨大的力量。
敲山公采摘茶树果之后,再一担担挑去镇上卖。茶树果榨出来的油炒菜极香,而且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可以卖个好价钱。敲山公留下一小部分茶树果榨油,之后用塑料瓶装着分给村里帮助过他的人。姨父也收过敲山公的茶油,他曾和姨妈在灯下谈及敲山公这个人,言语间都是对这个人的同情与感慨。
敲山公是一个孤独的人,村里的人都这样说。
敲山公攒了两年的卖茶树果的钱,一部分用来在别的村子租了一台搅拌机,剩下的钱在镇上买了水泥。他在山里挑了一堆黄土回来,那时正值暑假,我和表妹便从家里偷偷跑出来,蹲在他身边学着怎么把黄土里面的杂物清除干净。家里没有小板凳,敲山工和我从河岸的石堆里搬来一大一小两块石头,三人裤缝对着裤缝,手臂碰着手臂,并着身子稳当地坐在石头上,弓着脊背埋首翻动着黄土里的杂草,三人宛如复制般的动作透着一种莫名的诙谐。
拣好的黄土之后用搅拌机打碎,我照着敲山公的指示,把小山似的黄土刨出一个“火山口”,等到敲山公往火山口里面倒水,我和表妹就拎着裤脚赤着脚丫在坑里狂踩。这种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个游戏,黄土里的水被我们踩得飞起,纷纷溅到敲山公的脸上。他也不生气,拿着木铲不断地翻着被我们踩出的黄土。等到黄土变黏,还要再往里面加一些稻草秸秆捶揉一番。剪碎的秸秆轻飘飘的,从麻袋里面一掏出就飞得我满身都是。我干脆捧着满手往天上一撒,看着漫天乱飞的秸秆哈哈大笑。
我们在闹,他在干活,明明是小半天就可以完成的活计,愣是被我们给搅和到了傍晚。
黄土揉成的土砖块需要在太阳底下晾晒半个多月。最早一批土砖晾晒了一个多星期,夜里突然下了暴雨,土砖一碰到水就开始融化,敲山公几天的心血就都打了水漂。我知晓敲山公心里难受,又陪着他重新踩了一堆黄土。等到晾晒好的砖头成型,敲山公便在他的柿子树底下拉了一块简易雨棚,那里成了土砖暂时的容身之处。
冬天敲山公基本是不出门的,他那间土坯小屋还没有封顶,上面被他用农家种菜的塑料薄膜盖着挡雨,他自己钻进那个矮小的铁皮屋子里睡觉。那间铁皮屋子里只有一块宽木头放在地上当作床板,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和一些破旧衣物。门口的位置摆着一个烧炭的炉子,那是他为数不多的财产之一。冬天山上没有多少东西,敲山公就用之前从山上拾来的一些树枝点火取暖。湖南的冬天湿冷难耐,下雨时雨水浸湿小屋的稻草,人睡在上面宛如直接躺在冰冷坚硬的地面。村里人心善,有时会邀请敲山公来自家吃顿晚饭,走的时候还会给他些棉质厚衣物。大山里的人有着骨子里的质朴,即使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贫苦,却把照顾敲山公当成了自己责任。
第二年春天,村子里面第一个被唤醒的人是敲山公。那时候农家还没有在水田里撒鱼苗种水稻,敲山公就已经早早上了山。冬天山上气温低,流水将一些碎石挟裹而下,到了浅水区就停留在那里。敲山公喜欢去一处河床捡石头,山泉水将山坡碎落的石头打磨成各种形状,清澈透亮的泉水被成堆的碎石阻拦,一股股地从缝隙间和头顶流出。那里的石头大多为大湾石,有的浓绿中夹杂着金黄,有的淡绿底色上面微微泛白,形状多为鸡蛋般的圆润,大小如小孩的拳头。敲山公将这些石头洗干净丢到背篓里,背下山后就放在柿子树底下摆着。敲山公一生没有积蓄,我问敲山公藏着这些满山见的石头做什么,老人的眼里包着泪,叹着气说留着当作念想。
秋季是野生猕猴桃的成熟期,那是敲山公最忙碌的时候。我喜欢跟在他后面去山上摘猕猴桃。我和他腰间各别着一个麻袋,他肩上扛着一条扁担,上面勾着的麻绳一甩一甩的,我紧跟在他后面,欢快的步伐随着绳子一起摆动。路过他家的猕猴桃林,此时上面已零零散散地挂着一些小猕猴桃,模样娇小,颜色发黄,摘下来闻着味道就觉得满口酸水。敲山公挑了手里最熟的递给我,我学着他用两指将猕猴桃从屁股中间对着挤捏,来回两下后手指用力一扯,猕猴桃就被分成了两半。没人照管的猕猴桃算是野生,入嘴的味道是酸中带着微甜,引得我口水直冒。山坡上面有几棵粗壮的杨梅树,这几棵树年代久远,最顶端的枝叶已经高出旁边杂树一大截,遥遥地在高空舒展着。此时地上已经掉落了许多杨梅,鲜红的杨梅果落在灰色的枯枝落叶上面,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敲山公将扁担靠在树下,两手抱树,双腿攀附在树干上,手脚灵活地往上一蹿,宛如常年生活在山林里的猿猴,手脚蹬在枝干上面行动灵敏;到了分叉的位置,单手勾住上面突出的树枝,一脚踩在另一段枝干上,宛如一个身子柔软的空中柔术表演者。敲山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山林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大树攀爬的技巧。我在杨梅树下等着,没过一会儿敲山公就爬到了最顶端。他朝表妹呼喊,然后两手抱稳树枝,一脚蹬在树干上。我仰着头往上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透出,无数个青的红的杨梅如雨点一般从天上落下,表妹的额头被砸个正着,杨梅的汁液在脸上溢开,顿时空气中充满了杨梅香甜的气息。这场杨梅雨来得急促,果实落在枯叶上发出“砰砰”的声音,我弯着身子还没有来得及捡起地上落的,天上又落下一批,转眼间地上被青红色的杨梅铺了个遍。
下山的路上有几棵拐枣树,三四片宽大的树叶中间长着一团拐枣,敲山公用镰刀勾着枝条割下一段,摘干净上面的拐枣装进口袋里。他知道姨父爱喝米酒,将拐枣用塑料袋装着让我们带回去给他泡酒。
山上的杨梅采摘季节并不长,敲山公这阵子需要频繁地上山。摘回来的野生杨梅倒进竹筐里,之后再挑去镇上卖。野生的杨梅虽然味道不及人家专门种植的鲜美,但这种酸甜的杨梅最适合泡酒。等到山上的杨梅完全落完,敲山公已经攒好了给土坯小屋盖瓦的钱。
我能感受得到,那是敲山公最开心的日子。镇上买来的瓦片被人用车拉到村口,敲山公再一担一担挑到自家门口。小屋的屋梁用山里的杉木架在屋顶,敲山公问村里的人家借了梯子,之后就自己爬上爬下给土屋盖顶。那间土坯小屋不过四十平方,他将那块木板小床搬到屋子里面,给自己换了一层新的稻草,上面铺着一床略微破旧的褥子,那是他在一户人家买来的,算是给自己新屋的一个贺喜。柿子树下面的大湾石被他挪到屋子拐角处,一个个擦得透亮,彰显着主人对他们的喜爱。
村里人知道敲山公的房子建好了,趁他白天不在家就送去一些食物放在桌上;他们和这个古怪的老头相处了这么多年,知道了他骨子里爱面子,所以不想给他增加负担。敲山公在人生的后半辈子好不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本以为好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谁知道第二年就出了意外。
姨父告诉我,敲山公在一次去采摘杨梅的路上,因雨后山路松软,他踩滑了松石连人带着麻袋滚下山坡摔断了腿。因为拖着没有治疗,等到好了之后敲山公已经瘸了。放假了,我们再去找他,他大多是躺在床上休养,一条腿笔直地搁在床板上,一条腿垂在地上。敲山公看得开,他知道自己以后都不能再爬树了,这对于他来说几乎是断了谋生的途径,但是家住物资丰富的大山,树上长的东西索取不得,地上的东西依然可以获取。敲山公好了之后便上山采起了草药。
后山上的一处山坡上长着不少白毛夏枯草,村里人很少知道它的功效。敲山公白天瘸着腿爬山,到了晚上才慢悠悠地回到土坯屋里,他将夏枯草晒干,之后拿去镇上的小药房卖,赚来的钱也可以管个温饱。
姨妈一家知道敲山公老实厚道,每年秋收时节都会喊他去田里帮忙。稻田里杂养着一些禾花鱼和田螺,农家人需要赶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它们打捞起来。禾花鱼不大,身子细长宛如泥鳅一般滑溜灵活。村里人捞鱼的时候,卷着裤脚,赤着脚站在稻田里弯腰摸索。相比狡猾的禾花鱼,不会动的田螺倒是方便打捞,有时候他们在水里捞上半天,也只是捞了大半桶的田螺。
敲山公善于捞禾花鱼,他到姨妈家帮忙,先将脚下徙着的解放布鞋搁到一旁溅不到泥水的地方,之后再朝四周的村民略显幼稚地显摆,好像戏台上耍着拳脚渴望得到台下喝彩的武生。他一下水,先趁着田里的水没有浑浊,定着神在水稻的根部搜寻一番,之后倾着身子一点点往前探。敲山公的脊背可以弯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弧度,他两只脚稳稳地扎在淤泥里,只依靠前倾的身子和浸入水中的手来摸索禾花鱼。也不知怎的,敲山公半浮在水面上的手猛地往下一夹,两只手像是握拳一般合拢在一块,等他双手出水,一条青黄色的小禾花鱼就在掌心翘着尾巴挣扎。活的禾花鱼可以送去集市上卖钱,农家的水田里都会杂养一些鱼苗。敲山公帮他们捞上几天,基本上一块水田里的禾花鱼就打捞得干净。
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学着模样动作,小孩子没有定性,半天没有捞到一条鱼后,便卷着裤脚在水田里乱踩一通,惹得敲山公乐好半天。
晚上姨父会邀请敲山公吃饭,田螺泡水洗干净加辣椒爆炒,禾花鱼改上花刀后只加点葱花酱油放铁锅里蒸,再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小酒杯倒上一盏,敲山公就这样吃着百家饭喝着百家酒。敲山公帮村里人打捞禾花鱼,不需要工钱,村里人过意不去,晚饭过后还会送上几条禾花鱼,禾花鱼的嘴用茅草穿过结成一个圆环,敲山公提溜在手里,只需掂一掂就清楚这些鱼有几斤重。要是遇到出手大方的,他心里过意不去,之后总会带些山货给他们送来。自从敲山公摔断了腿,因为不能长时间浸水,他也就再没有下水捞过禾花鱼了。
那晚之后,我陪表妹请了两天假回乡下看看老屋。
现在的交通比以前方便,表妹说上次回家还需要颠簸辗转七八个小时,这次却是五个小时就到了村子附近的镇上。下车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我们在附近的餐馆随便对付一顿,之后便坐上通往村子的大巴。
村子建在大山里面,从镇上到村子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许多村子的路已经被拓宽成了可供两车行驶的水泥路,为了节省资源,蜿蜒的旧山路被废弃在一边,几条笔直的水泥路将旧山路中间截断,径直连接附近的村子,形成了一张简单的乡村交通网。马路两边的杂树被砍干净,透过车窗往外看,乡下秋日的风景全部跑进眼里。水泥路两侧是分割工整的水田,此时正是农家收割水稻最忙碌的季节。水田形状各异,但是又像拼图一般恰到好处地拼合到一处。农人正在地里忙着割稻,他们身上穿着深灰色的麻布外套,这种暗沉且耐脏的颜色在稻田的一片金黄中格外突出。几个妇女头上戴着圆顶宽檐的草帽,低头弯着身子时头上的草帽和半人高的稻子融合在一起,好似本身就长在那里一般。有些广阔的稻田需要机器来收割,收割机的履带压平田埂,一点点地在地里来回移动,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大巴车的玻璃都可以听得清楚。
路上还有一些男人敞着衬衫,肩上挑着一担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稻穗。大巴车很快就在他们身边驶过,我回头去看,男人们的肩被压得有些垮,身子前后两座小山似的稻穗在两边摇晃,他们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还有说有笑,好像身上没有压着一百来斤的重物一般。
前面的水田一过,表妹家所在的村子就慢慢出现在眼前。村子靠近山脚,除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从外围通过,其余的除了成片的水田就是连绵的大山。我拎着箱子从大巴车上下来,车门在我眼前闭合,之后又慢悠悠地往下一个村子驶去。
村子变化挺大,可能是我们来得已经有些晚,靠近村口的房子已经被拆除干净,只留下地上成堆的砖头和破旧杂物。因为是挖土机施工,一些阻碍道路的柿子树从根部被砍断,倒下的枝叶上还挂着一些橙黄色的柿子,施工队将它们丢在一边的水沟里,成熟的柿子便一个个摔进水坑,新鲜的果肉一下子成了一坨,只留下一个个灰色的柿托盖在上面。施工队是县里派来的,为了加快速度,村里新拆除的房子清理干净后就开始了新社区的建造,喜悦的力量催动着工程前进,在村口的左侧,以前高矮错落的农村旧房已经变成一排排新房,立在村口最打眼的位置。
挖土机在村子里的水泥路上留下两行痕迹,我顺着它往前走,在水泥路的拐弯处发现了它的踪影。
一辆挖土机停在水泥路下面的空地上,路面和下面的连接处用碎泥沙和砖头堆成一个简易的台阶,松软的泥土已经被挖土机压成了板实的路面。挖土机吊臂高高举起,宛如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型怪物,爪子贴在墙壁上往前推动。随着轰隆巨响,老旧的屋顶就被掀开推翻在地,碎成了一坨一坨的砖块。地面的灰尘被震荡飞起,空中两三米被黄色的灰尘掩盖,我们不得不捂着鼻子离开。
表妹家离那栋刚被掀了顶的房子不远,那里还零散着几栋房子没有施工,不过房子都已经搬空了。我们往回走的路上碰见几个村里的人,表妹和其中几个人打了招呼。见我们回来,寒暄几句,他们说了一件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敲山公怎么都不肯搬出去。
村里人见我和表妹回来,因为幼时我们天天跟在敲山公屁股后面转,他们提议让我们去敲山公那里当个说客。
敲山公的土坯小屋离表妹家不远,从表妹家门口越过中间的一片杉木林,那间土黄色的小屋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土坯的外墙已经开始掉落碎土,黄色的土块成堆地落在墙角。侵蚀严重的还露出了里面的稻草秸秆。土坯之间存有缝隙,有的缝隙里还插着木棍,上面挂晒着一些笋干。土坯屋四周空荡荡的,不远处一栋水泥砖房拆了一半,破碎颓败的墙壁和矮小的土屋形成对应,心酸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土屋的门是两片木板改的,木板下面裁成圆柱形杵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球形凹槽。木门虚掩着,敲山公不在家。我们有些遗憾,正打算往回走,迎面一个瘸腿老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喊他几声,他都没有回应,大概是耳朵有些不好使了。他佝偻着背弯成山群驼峰的模样,上半身完全支撑在一根原木拐杖上面。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的皮肤宛如山上松软的泥土,眉毛两侧的长寿眉硬挺挺地竖立在眼皮上方,眼睛被耷拉下来的眼皮遮挡了大半,依稀露出一点湿润的光。他还穿着我们小时候见他时那般破旧的衣服,一条裤子几经缝补,看不到一丝原来的模样。腰后面拴了个麻袋,里面露出几个新鲜竹笋的尖头。
驼背让他不得不仰着脖子看我们,目光是带着几分陌生的打量,后来仿佛一下子认出了我们,眼里的陌生感变淡,嘴角慢慢地咧开一个笑容。敲山公已经七十多岁了,嘴巴抿在一起时四周蔓延着褶皱,等到他朝我们张着嘴缓慢地笑,泛紫的嘴唇中间只剩下一颗门牙。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左手杵着木拐,右手缓慢且有些迟钝地在表妹身上轻轻拍打,像极了小时候他帮表妹拍打干净衣服上的泥土。见他背着麻袋吃力,我把他腰后面拴着的麻袋解下,里面只装着三四个毛笋尖,这个季节的毛笋尖皮厚肉老,很少有人会去采挖。他说他年纪大了,大山爬不上去,只能在山脚下的竹林里寻些笋子来吃。他为了这几根毛笋大概费了不少心力,膝盖上和屁股后面沾了一些泥土和碎草。我们弯着腰帮他拍干净,他摇手拒绝,笑得有些许羞涩。
敲山公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一般外出也不锁门,只将两片木板合在一处,虚露出一条缝隙。表妹说,以前村里有人找他帮忙,若是看到门掩着,就知道他上山去了;若是在家,隔着一条门缝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木板门有些沉,需两手扒拉着两边才可以推开,等敲山公彻底推开木门,他的额头已冒出一些薄汗。
小屋里没多少东西,东墙拐角堆着一些大湾石,那是敲山公舍不得扔的宝贝。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床褥子,敲山公说是村里人拆迁后送给自己的。他身子骨行动不便,让我帮他铺展到床上去。我用手在床板上摸了一把,下面的稻草有些潮湿发霉,即使我把棉被对叠铺在上面,那股黏腻的潮气仍然可以感觉得到。
掌心潮湿的触感让我打好的腹稿顿时堵在喉咙,说客的身份和土坯屋见证者的角色矛盾争夺……最后我没有将话说出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陪伴他的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把屋外墙缝里晾晒的笋干用塑料袋装着塞到我们手里。回去的路上,表妹说,他还惦记着以前上山时从人家废弃的猕猴桃林里摘的那些果子,这些小事对于村里人来说可能早已忘记,但他却始终惦记着,这么多年过去仍要我们带些他自制的山货回去。
晚上收拾东西,老屋的东西之前陆陆续续被表妹带走了不少,大物件之前都送给了邻近的亲戚,屋子里一眼看过去空荡无物。在厨房的橱柜里翻到姨父以前喝米酒时常用的竹碗,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尘。表妹打算将它带回去给姨父做个念想。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透出亮光,村里的挖土机已经开始工作。我们被震耳的轰鸣声吵醒,索性不睡,收拾好东西打算离开。我们没有再去看那个年迈的老人。
出村时一路看过去都是破碎凌乱的砖石,挖土机已经开到表妹家附近了。我们不忍心再看,坐上大巴车径直离开。村里这些房子都比敲山公自己盖的土坯小屋坚固,可现在却只有他的屋子还留在山脚。
回去之后我很久没有听到关于敲山公的事情,只知道村里的房子已经施工完了,也不知敲山公之后发生了什么。后来家里几个还联系的邻居告诉我,敲山公在屋子改造前就去世了……我沉默许久,心中仿佛有无尽的惋惜和感慨,却又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