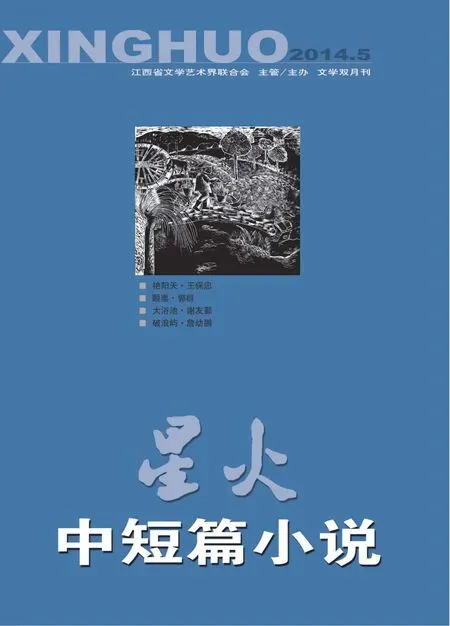春风十里黄冠村
○胤忠
天微蒙,星光渐次退场。公鸡挨个打鸣,划破整夜的沉寂。当都市的细胞才彻底安静,村庄已经苏醒。孩子们迫不及待闯进鸡窝,揣上几只温度尚存的鸡蛋,笑脸盈盈。
我又回到了家乡,一个窝在赣南山峦里的小村庄。每逢春节,回乡就成了家族的首要命题。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微信视频了多少次,也无论旅游团如何火爆,亲人们必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共同守岁。就像一个个零件重新嵌入失散的母体。仿佛只有站在老宅前,让库存的方言脱口而出,心才能真正定了下来。
年,似乎没有隐退分毫。小年前后,年味就浓烈起来。壮劳力纷纷返家,拎回大包小包的年货,羊肠小道上满是车轱辘印。大家贴春联,扫灰尘,包饺子,酿米酒,卤猪肝,煎豆腐,做米粿,忙得不亦乐乎。忽然间,星星点点的红在山林间铺开,胖瘦不一的香肠、腊肉随处可见,米酒醇香四溢,平日素颜的村庄迅速红火起来。
三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景象可要灰暗得多。
凤凰岽乡,黄冠村。无论名字多么优雅,地理距离却骨感至极。一整天的班车,从省会南下赣州,住上一晚,再转车到会昌县城,搭顺风车进村。泥泞的羊肠小道急剧颠簸。山伟岸雄浑,仿佛被它们包裹进来,便永无出头之日。土坯的宅院,这儿两家那儿三户地散落着。
两层土坯房,楼梯咯吱作响,一张木纤维凹凸不平的圆桌,几张床,两条长板凳,三把小藤椅,满是划痕的锅碗瓢盆,是爷爷家的全部。除七叔、八姑、九叔尚在读书外,家中只剩爷爷奶奶。依然入不敷出。还没有通电。夜幕降临,除了几支蜡烛的微光,整座村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聊天,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几乎每个人都是陌生的。我蜷在妈妈腿上,听着分贝不一的声响,默默熟悉村人村事。
衣服上密集的补丁,是罗文堂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我们的近亲,和爷爷同辈。媳妇给他生了两儿一女,一家五口相濡以沫。与祖辈和乡邻一样,他的生命似乎也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一望到头。
罗文堂屋后,住着罗北京一家,同样是爷爷辈的近亲。房子四处渗水,屋顶随时要塌下来似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用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仅剩几亩耕田,守着一儿一女。孩子们整天挂着一串鼻涕,四处闲晃。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担忧。
随着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多,脚底沾上越来越多的泥土,家乡的草木虫鱼和故人旧事也就不自觉间耳熟能详。
文堂爷爷是吃过苦的。打小家里穷,八九岁跟长辈上山砍柴,下地耕种。没过多久,作田、放牛、烧火、喂猪,都成了行家。年复一年,生活照例轮转。成家后,当仁不让成了顶梁柱,躬耕之余养鸡饲猪,又在山上的鱼塘圈了大量鱼苗,打理得有条有理。关键是学精了裁缝手艺,别看他手掌粗壮,织起针线来却精细得紧,外套也好,内衣也罢,像模像样。
有一次,爷爷带我找他做身衣服。正准备把身子凑上前量尺寸,他摆摆手,“我瞅两眼就行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打发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都犯嘀咕。直到交货那天,大小正合适,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后来我才知道,全村老少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或许是太累了,他要寻找一种发泄方式。不知怎地,他选择了唱歌。耕田累了,把锄头往地里一顿,“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就吼上了。下工回家,也随兴喊上两嗓子。睡觉前,抽支烟、唱支歌是他的两个固定动作,从来不曾失眠。他的歌库很丰富,隔几天又有新曲目。山歌,劳动号子,各式小曲,样样精通。谁也不知道是哪学来的。“山歌来自心中,有灵气的人才唱得出。”乡亲们都听过他的这句名言。他最喜欢唱的,还是红歌。《北京的金山上》《咱们工人有力量》出镜率最高。尤其是《北京的金山上》,每每唱到最后—“哎,巴扎嘿”,就使劲跺一下脚,拍一下掌,再定几秒钟,仿佛飘飘欲仙。
他爱拉人对唱,谁陪他唱两首,简直比喝了小酒还痛快。实在没人唱,他就会哀求我奶奶。“三秀嫂嫂,陪我唱一首吧?”从小孤苦伶仃的奶奶也爱唱几句,拗不过劝,就边洗碗边和上几句。
还有军歌。他太想当兵了,说梦话都喊“一二三四”。可惜没机遇,只能用军歌聊以自慰。《咱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游击队歌》,唱着唱着,好像自己真的当了兵,在上工下工路上雄赳赳气昂昂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件墨绿色凡尔丁料的外衣,可像军队的作训服了,天天套在身上。哪里磨破了,打个补丁继续穿。配双解放鞋,倒真有几分军人的模样。
北京爷爷直到知天命之年,也没能踏上北京半寸土地。我每次见他,他仿佛只有一身装束—草绿色夹克,咖啡色裤子,黑色套鞋。都泛着白。实在可惜了他的大帅哥胚子—一米八的个子,身板直溜,标准的国字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若是哪家经纪公司包装一番,没准能捧出个大明星来。
本来日子尽管艰辛,但两口子耕田做工,勤俭持家,倒也自得其乐。可是早些年,媳妇忍受不了穷苦,突然没了踪影,只留下嗷嗷待哺的幼童。北京爷爷消沉了好一阵子,那几年连互相拜年,面容都憔悴得紧。好歹是走出来了。可生计在哪?想来想去,他把目光投向了盖房的各项工艺。他陆续学会了泥工、木工、漆工的活儿,这些手艺里,又对制砖情有独钟。他曾对我解释过缘由:“每家每户都得盖房子吧,盖房子就得用砖吧,有了这门手艺总不会饿死。”他抱着最原始的生存理念,往一块块砖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曾见过他制砖,从做好模具,到填多少土,到每层刷多厚的水泥,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一会儿猫着腰,一会儿蹲个马步,一会儿跪在凳子上,以防失之毫厘。“慢工出细活”,他的嘴里不只一次嘟囔着。夜晚的时间也不放过,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他孜孜以求的身影孤独而坚毅。
他要争口气。
日积月累,凭着一股狠劲,北京爷爷制砖用砖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刚开始没人发觉,“不就是几块砖么?”大伙心里都认为,这点事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了。但每每三五乡亲共同帮忙,只有北京爷爷负责的部分平平整整,其他的总是凹一块、凸一角。大家这才陆续领教到北京爷爷的功夫。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哪家要修缮房屋,总是邀请他担纲主力。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村民手头都没几个钱,倒也赚不了多少,只能管餐好饭。他自己从来不吃,全部带回去给孩子们。
慢慢的,砖成了北京爷爷生存的法宝……
大叔的一声吆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该去走亲串户了。上次回来,文堂爷爷家的小洋楼才建了一半,这次不仅竣工了,连原先的老屋也翻修一新。我满怀好奇前去参观,嘿!站在院坪上,眼前绿油油一片,村路隐隐约约,远处山脉绵延,尽收眼底,偶尔三两只鸟儿啾啾飞过,颇有桃源仙境的味道。一进客厅,豁然开朗,墙高五六米,白得发亮,一张圆桌立于中央,空间富余得可怕。哪怕城里最精贵的别墅也难以媲美。我们在啧啧赞叹的同时,也感慨文堂爷爷的眼光。
“如果不送建华两兄弟去读书,今天哪里住得上小洋楼啊?”听了二叔的话,文堂爷爷哈哈大笑。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文堂爷爷还是经历了一段摇摆期。“我自己没什么文化,连歌词都认不完整,不能让儿子也当文盲啊!”但条件的确艰苦,常常入不敷出,“索性不读了,罗贵生家不就没送去读嘛!”乡邻们这两天听了这个版本,过两天又听那个版本,莫衷一是。但看到我爷爷把几个儿子都送进学堂,他最终还是坚定了信心。他特地添置了猪仔和鱼苗,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开辟出来,收入勉强凑合。
他有个毛病,馋酒。一到冬至,就要酿上一大缸米酒,作为下一年的储备。自己时不时就一小碟花生米,喝上几碗。这米酒后劲不小,两三碗下肚,人就轻飘飘起来。但孩子上学后,他明显收敛了。孩子做完作业前,他滴酒不沾,充当“监工”。谁考试没考好,他会厉声批评,蹲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扭头抽闷烟,酒也提不起兴趣。谁的成绩提高了,他会开怀畅饮一番,边喝边哼上几句。
事实证明,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富前瞻性的决断。儿子们很争气,学了门手艺,跟随外出大军赴闽打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挣了不少钱,每月寄些回家,家境日益殷实。日积月累,攒够了两栋小洋楼的资本。
才坐了一会儿,北京爷爷又来邀约。他的新房,与文堂爷爷家比邻而居。没来得及打量,只见他瞬间从橱子里端出十几个果盘,盛着米粿、瓜子、糖果、红薯干、腊猪肝等年货,再给每人筛满一碗米酒,五颜六色的食物眼花缭乱。仔细打量,墙壁刷得雪白,水龙头取代了大水缸,卫生间的瓷砖若隐若现,一辆摩托车倚在角落。装饰虽谈不上豪华,却也干净整洁,有模有样。北京爷爷身上的夹克衫一尘不染,绿得纯粹。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盖的。”北京爷爷眼里泛着自豪。
旁边还搭了个车库,一辆白色斯科达优雅地停在里面,像是奔入小康的证明。这幅场景,谁能想起它破旧的前身?
改变这一切的,其实是不起眼的“砖”。
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释放。村民的经济条件陆续好转,外出打工捞到第一桶金的年轻人,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翻修老房子。尽管土砖、青砖逐渐被红砖、水泥砖取代,盖房的时间成本大大下降,但乡亲们对房屋质量的要求反倒更高。毕竟红砖的墙壁砌歪了,比土砖的结构更突兀。乡亲们挑来拣去,还是打心眼儿里认为北京爷爷最合适,不仅是手艺,更是做事的钻劲和韧劲。北京爷爷与时俱进,村里通水通电后,又学会了水电工的技术。于是,村里的小洋楼越来越多,北京爷爷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家中陆续添置了一些物品,肉也成了案上的常客。孩子大了,读书的同时还能帮衬田事和家务。日子,终于好了起来。
周边的壮劳力纷纷进城务工,但北京爷爷并没有被诱惑,而是反其道行之。“您不想出去赚钱吗?”我问。“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意思。在家多自由啊,赚的钱还不比城里少。”北京爷爷毫无隐藏。他告诉我,盖一栋房子,工期一般两个半月至三个月,每天可赚三到五百元,再加上承种了撂荒的二十多亩田地,化肥都由政府补贴,一年下来,一亩能净挣六百到一千元。我大致一算,哎呀,都奔小康了!
在黄冠村,罗文堂和罗北京只是脱贫的两个缩影。这个有着两千人的“十三五”贫困村,村容村貌早已焕然一新。十八弯的村道硬化平坦,蛛网似的串连起整座村庄。拐进村口,小洋楼一幢接着一幢,不少大门刷饱油漆,鲜红、阔气。有的砌出单家独院,两座石狮子守门,霸气十足。自来水管架起来了,穿村而过的小河终于可以睡个懒觉。站上去摇摇晃晃的茅厕,也纷纷改头换面。前不久,上海援建的幼儿园刚刚落成,教室、宿舍、餐厅宽敞明亮,我六岁的儿子惊呼“比城里的还要好”。小学、卫生室、便民中心都披上了新装。夜幕降临,年轻的光伏灯发出饱满的光芒。
一股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在全村上下升腾。
“新建了五十亩蔬菜大棚培育贝贝小南瓜,又种了六十亩烤烟,村集体经济达到十二万元。”村支书老钟说起这些语气简直有点嘚瑟。他背后那栋贴满米黄色瓷砖的新楼,正是村委会的办公楼,比起百米开外的旧址,简直天壤之别。
“二○一四年脱贫三户、二十人,二○一五年脱贫十九户、一百○一人,二○一六年脱贫十七户、七十三人,二○一七年脱贫十五户、七十人,二○一八年脱贫二十户、七十九人……”老钟拿出七十五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三百四十八个贫困人口的台账,如数家珍。这一户加入了村合作社,那一户的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就连嗜酒如命、打了一辈子光棍的罗长生,也在花甲之年被安置进敬老院,颐养天年。
正说着,村道上粤B、粤E、闽C 等外地车牌频繁出镜。老樟树下,文堂爷爷又在跟村民谈论村里的一些新规划。虽然他不是村干部,但对国家大事比谁都关心。老樟树下的浓荫,就是他的讲台。一有什么政策下来,文堂爷爷就要召集大伙“传道授业”。说到兴奋处,还会猛地站起来,唾沫星子横飞,有时手上的烟头都甩飞了。当然,有些政策他也没完全理解透,乡亲们一提问,就卡壳了。但这样的尴尬一点也不打击他的积极性,下次照样滔滔不绝。
一缕缕炊烟掠过屋顶在村庄上空弥漫开来。“开饭了!”二姑清脆的喊声在山里打着转。六岁的儿子和兄弟姐妹扑向饭桌,狼吞虎咽起来。奶奶愣愣地盯着这群第四代的孩子们,嘴角泛起微笑。她是否又回忆起和爷爷白手起家的苦中作乐?她的皮肤褶皱密布。这些深纹里,潜藏着一个农村妇女的奋斗史,乃至一个村落的变迁史。前段时间,父亲和叔叔们给老屋刷了墙,改装了屋顶,让北京爷爷又多了一件引以为傲的工艺品。
昨天晚上,星光斑斓,文堂爷爷和北京爷爷凑过院坪聊天。聊着聊着,文堂爷爷又唱了起来,我赶忙拿出手机,录下了《浏阳河》和《七律·长征》。
北京爷爷又接了一单新活。此时,“砖艺”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乐趣,一份坚守。本村小组三分之二的新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也学会了微信收款追赶着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