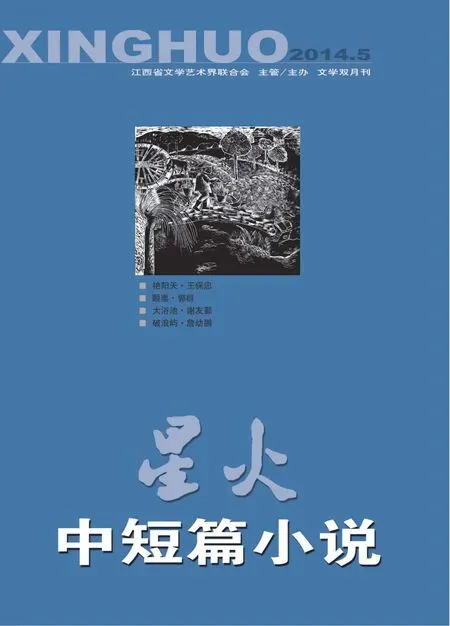昙花
○陈小虎
从伯顿西餐厅出来,石牌东路安静了。这条从一大早就高潮到深夜的马路,此刻,困乏了。其实,路也和人一样,总有累的时候,也会死。没有一条道路能够从古伸延至今,也没有一条道路能够从现在直抵未来。石牌东路上除了白晃晃的路灯,还没长高的树,就空空荡荡了。我们在路边站了好一会,依然没有见到一辆出租车。她说,走吧!走?我重复一句。她看着我,点点头。我却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我想问去哪,但忍住了。我就住在石牌村,从站立的地方往左,走上十五步,就是石牌村的一个入口,再沿着巷子往前,就可以到我的住所,而她,却住在龙口西路。那么远的距离不是依靠双脚可以到达的呀。
她看着我,笑。两边的酒窝露出来,很深,深得我望过去就头晕不知所措。我努力把目光移开,不能掉进去。走吧!声音很轻,也很坚决。这两个字还没坠在地上,她就迈开了双脚。
我们沿着石牌东路,从南走向北。路上就只有我们的影子在晃动,经过石牌村的一个村口,烟草专卖店,饭馆,旅馆,内衣专卖店,五金店,凉茶铺,窗帘店,我知道,又要到石牌村的又一个入口了,再往前走两百米,就到中山大道了。那是这座城市最为热闹的马路。在广州城,如果让我说出最熟悉的马路,我一定指向这条现在就在脚下的路。上学的时候,学校就在石牌。那时,经常就会在这路上闲逛。我曾在楼与楼之间的空隙把一泡尿撒在村民还保留的菜地上,也曾在这路上逛过夜市的每一个摊位。后来,搬进石牌村,这路更是我不时出没的场所。在我关于广州的系列散文中,石牌东路是出现最多的马路。
就那样并排走着,我以为她会开口说点什么,但没有。她只是不时扭头看我,在遇到广告牌时往我身上靠,然后又很自然地离开。在伯顿西餐厅,我已经说了太多的话,她就只是听,在我的话像断线的风筝那样摇摇晃晃时,她才巧妙地把线接上去。一个晚上,我在说,她在听,不时穿针引线。我终于硬硬地刹住话头,那种滔滔不绝的感觉让我好像在她面前脱完了衣服。这让我不舒服。可是,即使我选择了少说,她还是听,终至两人默默。奇怪的是,我以为因此就结束了这个晚上的见面,但在沉默中,我反而觉得自在和心安。这样的相处方式,我一直认为只有在默契的朋友间才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中,也仅有那么一两个可以默坐一个下午而不心烦。而我和她,远远没到那样的程度。
一个小女孩从屋旁的暗角跑出来,拦住我们。我把她拉在身后,问小女孩,干什么?话音刚落,又一个女孩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长得特别像,一般高,一样的衣服。我估摸是双胞胎。后来出现的女孩,拎着一个篮子,里面斜立着玫瑰花。她拿出一枝,大哥哥,给姐姐买一枝吧。我回头看她,她没说话,也不看。买一枝吧!小女孩抽出一枝,递到我面前,仰着脸。我说,全部买了。小女孩一脸惊讶,然后欣喜。她们手忙脚乱地归拢篮子里的玫瑰花,用报纸包住,双手捧着伸到我面前。我付了钱,她们一齐向我们鞠躬,牵着手消失在拐角处。
这么多?她又和我并排。嗯!我点了点头。送我?她的双眼亮亮的。当然。我笑了笑,并且把那束玫瑰花递到她的面前。就这样?她笑着问。那,要怎样?我一头雾水。难道要单膝跪下?她又笑,算了,免礼!喳!我不知怎么,就这样蹦出这个词。俩人就都笑了。
十一月。北方已经是深深地秋着,广州还是燥燥地夏着,但早晚已漫出如水的凉意。风迎面而来,缓缓地,滑过裸露的肌肤,水般沁凉,一种挣脱了酷热后的清爽和通透。我喜欢这样的时候,喜欢这样的时候独处或者和喜欢的女子安静地待在一起,不言不语,默默相望。或者,就如这一刻,两个人就这样走在石牌东路上。
为什么买这么多?她还是开口了。不多呀,送不了你一亩一垄,就一束。我看着她,她把头靠近玫瑰花瓣,吸了一口气,仰起头,向着天缓缓呼出,然后,望向我,脸笑得像玫瑰花。是不是觉得姐妹俩可怜?她很认真地问。我避开她的目光,轻声说,走吧!
你真是一个好人!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神情严肃认真。那束玫瑰花在路灯的映照下,花瓣上的水珠晶莹剔透。我没有说话,我想用干笑糊弄过去,但还是忍住了。这一刻,我相信她是正经的,我的想法就显得儿戏。但是,一个人的好坏与一束玫瑰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买与不买,仅仅只是刹那间的想法罢了。我若不买,难道我就成了坏人?我相信她是被感动了,人在感动的时候理性会躲在一边。
走吧!我边说边往前。这个时候讨论一个人的好坏是没有意义,而且,人的好坏只是对于他者的一种感觉,实在证明不了什么。在她眼中,因为我有怜悯所以是好人;在另一个人眼里,我为了一个女子而买下这么多的玫瑰花,是一个败家子。生活中,我早已放弃了评判和下结论,因为我被事实无数次地嘲笑过。
我们又并排走在一起,她的右手挽住我的手臂,左手举着那束玫瑰花。风吹拂她的长头,扬起的发梢划过我的脖子,微微地痒。宁静,自在,温馨,充满美的想象。一辆黑色的私家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钢铁在灯光下闪着冷冷的坚硬。石牌东路更静了。
在人行天桥的旁边,我们停下了脚步。在一篇《石牌东路》的散文中,我曾经写到这个地方——“石牌东路口是个十字路口,五山路,中山大道,石牌东路的车辆和行人在这里交汇……这路口建起了立交桥,还有像章鱼一样的人行天桥。”
但是,这天桥与石牌东路西侧相连接的地方一直没有修好,就1 米的路程呀!我领着她穿过石牌东路,从东侧上天桥,跨过依然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在靠近五山路的路口停下。等待一辆出租车的出现。
送我回去。她转过身子说。我看着灯火通明的中山大道,没有说话。已经是凌晨一点,此刻的前行,对于我和她意味着什么,彼此都清楚。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了内心的忐忑和犹豫。这本不应该出现。我不知道自己在顾虑什么,担心什么。
不敢?!她的语气带着挑衅。不会有哪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承认自己的胆怯。笑话,难道你会吃了我。我回敬她。我就吃了你,怎么啦,怕啦?她仰着脸,嘴角往上翘,两个酒窝又出现在脸上。我知道这一次的对话我又处于下风。“吃”在这一刻是个鲜艳的词语,在暗黑中金子般闪闪发光。她若胆大,我无处可逃。
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为她打开车门,侧着身子。她就那样看着我,走过来,稍稍弯腰,进车里,落座时把手伸出,手心向上,五指分开。这是邀请的信号。我的手抓着车门边上的铁皮,那种沁凉从手指蔓延过来。去,还是不去?我的心里在挣扎。上车,到她楼下,然后上楼,进她的家门。她已离异,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住校。随后将会发生什么,一清二楚。天亮后,我将从那里出发去办公室。但是,在我和她之间,我好像还没有做好迈出这一步的心理准备,我无法看到天亮之后对我生活的影响。而我,一直都在躲避一团团的浓雾。那些看不清前程旧路的雾团让我心生恐惧。这与胆小怕事无关,我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地活得明白一些。可是,若不去,对她可能的伤害暂且不说,她的美丽和性感对我有着无尽的吸引力,不然,我也不会与她相识,也不会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经常和她见面。那时,一场爱情刚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像一朵花的枯萎,日子再也没有了鲜艳的色彩和醉人的芳香。
她应该是看出我内心的挣扎。也许,就是这样的挣扎让她放心。她抓住我的手,一拉,我就到了车门边。她往座位的那边挪,拉着我。我还是弯下了腰,进到车里去了。呵呵!我听到司机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也笑了,她跟着笑得比我还欢。
一路上,两人倒坐得规矩,车的拐弯会把她的身体甩向我。龙口西路是那些年我常去的地方,几乎一周两次。记忆中,这路不至于转弯那么多。司机是在给我们制造身体接触的机会,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嘲笑我?也许,在他眼中,我的犹豫不过就是一次装模作样的推托,这世上,没有不吃腥的猫。
我的手撑在座位上,竭力让自己保持端正。车到了天河北路,速度快了些。夜深车少人稀,我真怕他把这辆捷达开成波音。还好,很快就到进入龙口西路的拐弯处,车还没拐过去,她把我抱住了。这司机是成心开玩笑的,这个时候,他把车速放得很慢。车方方正正地拐过去,一点都不甩。我以为她会松开手,但没有。
她住的小区看不出大小,我第一次到那里。夜晚,每一栋楼房在我看来都是一模一样,冷漠,无言。那些窗户都关了,都熄了灯。树木中间的路灯,把树的影子塑出奇形怪状,怪兽一样。她抬起手指着前面的一栋房子,说,我家就在那里,顶楼。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以为很快就到,她却领着我绕了一圈。这样的夜晚,我想不出有什么景色可以观赏的,实际上,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就听她说这小区的建筑史,哪一年卖第一栋房子,她买了,然后,把房产证拿去银行抵押,贷出来的钱在第二栋楼里又买了一套房子。又把这套房子拿去贷款,再用从银行借到的钱买房子。用这个办法,半年的时间在这小区里拥有了五套房子,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日子过得特别逼仄。老公因此离开了她。她把其中的两套房子卖掉,还了银行的一些钱,又继续抵押买房,房子的数量到心中的目标,就卖,又继续买。几年下来,她在这座城市拥有的房子数量已近三位数。我像在听一个神话故事,我从未想过我认识的人中居然有人有这样的思路、胆魄、手段和财富。在广州城,差不多一百栋房子呀,我用五百辈子也不可能得到。我看着她婀娜的身段,实在无法想象她怎么就能扛得起那么多的房子。我相信内心的惊叹肯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了,尽管我没有直接说出赞美的言辞,她的笑声即使克制,还是扇着翅膀往上飞扬。
我是真诚的。在生活中,我一直对自己做不到而别人游刃有余的行为保持敬意。一个锁匠花一分钟就能打开让我束手无策的大门,电车司机在那么拥挤的人群中稳稳地把车停好,诸如此类,我都会向他们亮出大拇指,更何况像她这样,短短的几年就合规合法地积攒了这么巨大的财富。我几乎就要拜她为师了,只是那时,我在心中还没有把金钱放在第一的位置。
灯打开的那一刻,我恍若进了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皇宫。这和我在石牌村租住的小房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住的是尘埃里的凡间,她在金碧辉煌的仙界。我站在进门处,迟迟没有迈出脚步,唯恐那双穿街过巷的鞋子脏了那一地白绒绒的皮毛。那皮毛云朵一样,我想,踩上去一定会腾云驾雾。
她蹬蹬蹬地往前,进了房间,一会,又出现在客厅。我就一直站在进门的位置,进退两难。退,当然是说不过去;而进,我担心踩脏了她家的那些白绒毛。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潮湿的回南天,难见蓝天白云的污染,不时倾盆而下的大雨,怎么就会用这样易脏易湿的东西来作为客厅的地板?也许,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样让人惊叹。
她递给我一双拖鞋,也是绒的,软绵,舒适。我可是连袜子都脱了的,脚趾头像踩在一堆棉花上。在墙的边上,是一张矮矮的桌子,两张矮矮的靠背椅,颜色全都是乌乌的,我挪了一下,沉甸甸的。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巴西乌木做的,价格不菲。桌子和椅子手感极滑,在壁灯的照射下泛着金属般的冷光。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她从厨房端出的冰冻饮料,瓶子像钥匙扣,设计奇妙。我猜想是进口的,果然,标签上除了那只切开的黄色番石榴是我认识的,其他的文字全是字母,但,不是英语。我放下已打开盖的瓶子,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番石榴味道。小时候,我家屋前有一棵番石榴树,当然,是别人家的。番石榴黄了,我就总是想着去偷。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水果,芳香之浓郁让我对别的水果少了许多兴趣;甚至,番石榴叶子的清香也让我念念不忘。有些年,我的书签就是一枚枚番石榴叶子。我忘记了是否跟她讲述过我的这些喜好,这瓶饮料无疑让我想到她的关心。
我以为她也坐在椅子上,但,不是,她就坐在那些白绒绒的毛上面,一边褪去肉色的裤袜,一边对我说,她不仅喜欢这样坐着,更喜欢光着身子在这些毛上面翻滚,那种毛茸茸的触觉特别让她兴奋。我只能笑了笑,不知道怎样接她的话。在我面前,她要么不说,要么说出的每个字都能让我浮想联翩。和她往来,我总能感觉到自己的语拙,和不知所措。
她随手把裤袜揉成一团,捏在手里,然后,睨我,两只手握在一起,搓了搓,把裤袜一点点拉开,又成了一双完整的袜子,在我的目光中弹拉。我笑了笑。我咧开的嘴还没合上,她把裤袜往上一扔,落下来,掉在她的头上,不知是左还是右的一边从她的脸上耷拉下来,盖住鼻子和嘴巴,直达高耸的胸脯。我以为她会拨拉好,但她理都不理,反而笑起来。那笑没了以前的羞怯,多了一份放任。我没想到,她居然就那样笑得倒在那些毛上面了。
我想去扶起她,但还是没有动。也许,这就是她喜欢的方式,放纵,为所欲为。这是她的家。她微微仰起身子,张开腿,把一只脚伸向我,举起,落下,搭在我的腿上。我的脑袋一阵发蒙。这就开始了?
五个脚趾头都涂上指甲油,玫瑰红,肉嘟嘟的,像五朵绽放的花,但我不敢去触摸。很多年了,我一直对把脚趾头当成画布的女子保持警惕。在石牌村,那些在巷子里游荡的女人,她们拖鞋里的趾头全都色彩斑斓。
我僵硬地斜坐着,半个身子倚着那张椅子。还好,椅子重,而且靠近墙壁。我能感觉到她的脚在用力。这样的场面对我不利,我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权,像刀俎下的鱼肉。我四处张望,想寻找一个可以转移的话题。没有看到书,没有看到报纸,没有看到CD。我怎么就不会在自己的爱好之外再找些爱好呢?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活得如此狭窄,这个世界,除了读书和听音乐,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可是,我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窘态,抬起腿,用脚趾头顺着我的裤子往下撩,到脚底。痒!我实在忍不住,笑着抖脚,顺势把脚收回来,盘着。她也笑了,笑得前翻后仰的,衬衣上的扣子已解开了三个。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解的。我的目光迅速从鼓胀的地方移开。我必须承认,她之所以能够攒到那么多的财富,一定与她的聪明和敏锐有关。聪明并不仅仅就体现在读书上,更不仅仅与考试成绩相关,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如鱼得水。她笑嘻嘻地问,紧张啦?害怕啦?你该不会是……我明白她想要说什么。我拦住她的话,大声回答,是!
不知道是我的声音还是回答的内容在她的意料之外,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坐直,很认真地看着我。我看到她嘴角轻轻的抽搐,然后,又对我露出那两个酒窝,山洞一样望不到尽头的酒窝。
我并没有读懂她脸上那种表情的意思。看着她,我觉得迷惑,相识大半年,好像了解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是谜团。人和人之间,本来简单,一旦有了目的,就变得扑朔迷离。像这个晚上,如果在伯顿西餐厅门口拦到的士,她回她的小区,我进我的石牌村,那关系再怎么绕也是一条直线。
她举起酒瓶,那是一种进口啤酒,我曾经在酒吧里见过。两个瓶子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把瓶口对准嘴巴,咕噜三下,一张纸巾递到我面前。我才知道,她没有喝,她一直就在看着我。她在想啥呢?我晃了晃脑袋,想不通,那就不想。这也是我与人来往的原则,我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复杂,我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复杂。
但,今晚……
番石榴的香不仅浓郁,而且独特,唤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那个瓶子,很快就见底。当两人的话题难以形成共识,我习惯于用抽烟喝茶来打破僵持。这个晚上,在她的步步进逼面前,我用番石榴汁构筑防线。
洗手间在那边。在我第二次抬头张望的时候,她往客厅的一边指了指。我无奈地笑了笑。她已经能够从我的表情和动作中读出我想要干什么想要说什么。和她在一起,我越发觉得自己的无能和裸露。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时,她已一跃而起。这令我惊讶。她扭着腰,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一片光亮从那里倾泻而出。我站起来,等着。我突然想到,也许是那里摆放了什么不宜被我看到的物什,她赶着去收拾放好。不然,我真想不出她为什么这么紧张。卫生间的门却一直敞开着,一会,我听到她叫唤我的声音。
卫生间真大,比我租住的那套房子的客厅都大。一个四周缕金的白色浴缸摆在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个两层的木架子,木架子的上层摆着两个高颈酒杯,下层是酒瓶,好像是四支。一面几乎占据一堵墙的镜子。一个不知是仿古还是真古董的褐色衣柜。宽大的洗脸盆,金色的水龙头。琳琅满目的化妆品。洁白如玉的壁砖,被两条黑金的波浪腰线分成三个层次。我站在中间,一股香水的味道袭来,淡淡的,恍若檀香。就在洗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化妆盒上面有两把男士用的剃须刀,吉列牌。我以为眼花了,凑近,是的,两把!
我努力压住心中的好奇和些许的愤怒,我又不娶她,她也不会嫁给我,在意这些干什么呢?都是逢场作戏!可是,我不是一个逢场作戏的人呀,我也从未喜欢过逢场作戏。能开口问吗?不能!能旁敲侧击吗?不能!能表现出内心的疑惑吗?不能!在洗手间,我把手洗白了,还是找不出稳妥的办法。我能感觉到欲望的生长,但我又不愿意让欲望遮住了内心的感受。也许,那是她前夫留下来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回到客厅,我又看到一瓶番石榴汁的饮料摆在黑色桌子上,瓶盖已经拧开。她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这么久,不会是耐不住自己解决了吧?!我再一次陷入无语,想不出怎么去回答她。好啦,开玩笑的。她拿着睡裙,侧过身,一脸妩媚地说,等我。我说,抽烟。阳台。她边走边回答。
我听到她放水的声音,我听到她在卫生间的歌声,轻柔,悦耳,充满磁性和魅力。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如果在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她一定可以成为百乐门的当红歌星。
阳台很大,花草不多,倚着栏杆,我闻到了花香,淡淡的清香。我看到了八朵白色的、盛开的花。噢,昙花!我凑近去,在花盆边上,并排放着两个烟灰缸,都是半缸的烟头。烟头有长有短,烟蒂颜色不一,或红或白或黑或黄,有细的,有粗的。也许,不应该仅仅是两把剃须刀。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站起来,碰到晾晒的衣服,长长的裤脚,男式。我仔细看了看,那些裤子胖瘦不一。
我成了什么?我算什么?我在心里问自己。没有答案。我可是连一把剃须刀的位置都没有呀!
我折了一朵昙花回到客厅,把它摆在桌子上,从随身带的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在纸上写下“谢谢!再见!”然后,放在昙花的下面,穿好袜子,套上鞋,打开门,再把她家的两道门关好。
从此,我们之间再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