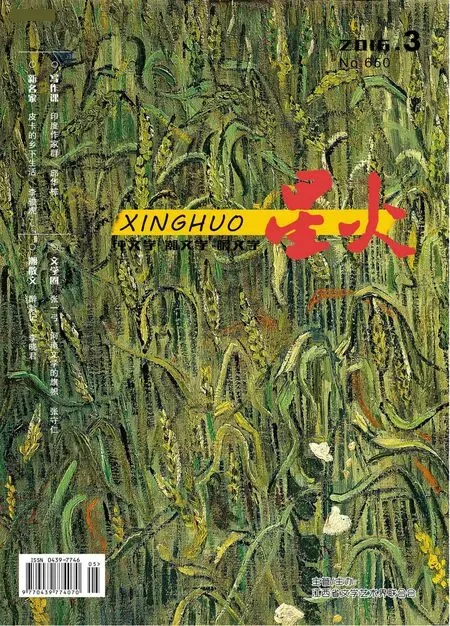孤独的春天
简 儿
1
从白玉兰开得闹哄哄的一刹那,就觉得春天真切地来了。草木的情意,远比人来得热烈。
春天总是教人忍不住生出欢喜之心。想要跑到一处无人的旷野,一个人撒撒野,发发疯。想要去折几枝柳、一束花,掬一缕风的柔情。想要去爱一切可爱的,去拥抱一切可拥抱的。想要去开辟一片新天新地……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有一个声音在吱吱叫。
每年春天,总要被感冒君缠上。且这感冒症状也很是离奇。有一次,我觉得腿酸,走着走着就想躺到地上去。两条腿实在酸得不行,就像踩在棉花里。我恹恹地来到医院,医生一量体温,惊诧道:四十度。你怎么还能走到医院?我也诧异起来,说起来,除了腿酸,脑袋也不昏,头也不疼,什么症状也没有。
那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要不挂两袋水。我说,没事,配点蒲地蓝吧。蒲地蓝,成分是蒲公英、苦地丁、板蓝根、黄芩,清热解毒。气微香,味甜,微苦。一盒十支,喝了两盒,便觉得脚酸得没那么厉害了。
一颗心遂欢喜起来,原来欢喜这么简单,脚酸的人,忽然不脚酸了。病着的人,忽然病好了。沉郁的人生,忽然有了一点色彩。冰封的大地,忽然春暖花开。
肉体凡胎,生老病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时想,人迟早总有一死,未免会深深地沮丧。记得我在乡下教书时,有一天,有个孩子忽然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好不容易等她平息一些,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抽噎道:人原来是要死的啊。我一直记得这个孩子悲伤的神情。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并不知人会死,还以为会活到永远。既然要死,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风和日丽,令人想要永远活下去。”素来多愁善感的我,有一天,读到这句话,忽然豁然开朗,灵魂宛如被雨水洗过的树叶。一束光,带来神谕,一颗焦躁不安的心,渐渐安顿、平静了下来,不再悲伤、忧戚、迷茫、郁郁寡欢。
诚觉世事皆可欢喜。
黄昏时去小区楼底下的园子走了一遭。五点三十分,天光仍是亮的。回首看那一轮斜阳,咸鸭蛋黄似的,挂在树梢上。温柔得令人忍不住想要掉眼泪。我痴痴地目送它,渐渐坠入黑黝黝的湖水中。
湖畔,伫立着一株红叶李。那一朵红叶李花,教人忘了世上还有忧愁。
2
忽然想起一个朋友。年少时我们曾在一起,好得须臾分不开。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彼此竟杳无音讯。电话号码早就没有了,qq 里倒是还有她的头像。翻出来,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好久不见,一切好吗?过了一会儿,她回过来:甚好,三月念故人。
隔着键盘,仿佛仍能窥见旧光阴。旧光阴里的春天,我和她徜徉于油菜花田里。穿了一袭棉布裙,小仙女似的,捧一束油菜花,站在花丛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得走过的人纷纷侧目。
晚上,两个人钻在一个被窝里。小孩子总是希冀有人作伴。小时候去表哥家,表哥总央求我留宿。我一答应,他高兴得什么似的,把好吃的,好玩的统统都拿来给我。
不晓得为什么,长大了,和表哥渐渐生疏起来。甚至于一年才见上一次,说的也无非是客气话。
我的这位旧友,亦是如此。从前两个人好得似一个人,忽然有一日,彼此生分了起来。
并非是有嫌隙、吵架之类。不过是人生的境遇不同了。她去了杭州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开辟疆场,自由飞翔。我呢,仍蜗居在这一座小城,浑浑噩噩度日。
她说,下个月要飞成都,再下个月去深圳;在杭州买了新房子,刚开始装修。噢,别太累了。我说。不会,装修是学生家长在弄,无需自己费心。一时,我竟不知说什么好。我和她终究已经相别太久,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曾经依恋过的一个人,有一天会变成陌生人。曾经亲密的朋友,再见时亦只有客气寒暄。想来,人生终究是孤独的行程。
至今仍记得她曾为我两肋插刀。有人欺负我,她摩拳擦掌,冲那个人扔过去一把剪刀。那个人吓得抱头鼠窜。她走过去,笑嘻嘻地把剪刀捡起来。我仍心有余悸地说:“要是扎到人怎么了得?”
她笑嘻嘻地说:“不会啊,我看准了才扔的。”
忽又恨恨道:“扎到了也活该,谁让他欺负你。”
那一刻,她说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世上有哪一个人抵得过她对我的义气与深情——怕是这一生,再不会遇到了。
她离开小城的那一天,我去送她。她扎了马尾辫,笑眉笑眼,仍是我熟悉的神情。她说,回去吧。有空回来看你。
有一年,她回来打我电话,见了一面。不知怎么,说的都是些客气话。我生她的气,遂不理她。她也不再理我。就这样,一晃又是好多年过去了。
原本以为,一生一世都会这样好下去的,不知怎么就渐渐走散在人海。
想起旧时春天,我们在一株白玉兰底下。她穿了白衣白裙,手里擎了一朵白玉兰,窃窃地笑。
我揿下一张照片。去暗房冲照片,冲出来,走到秋千架旁,笑嘻嘻递给她。她亦笑嘻嘻地看着我。
那真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了。
白玉兰又开了。人伫立在白玉兰树底下,心底会滋生出几许柔情——草木的情意,实在比人长久。人早已离散了,草木仍伫立在那里。痴心的,把春天一年一年送给你。
3
我一直记得那个春天的黄昏。
我在田埂上骑自行车,我把自行车骑得像摩托车一样,像火箭一样。我想,也许我会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那时的我,对世界怀着无尽的好奇心。
我把柳树枝折下来,缠在铁丝上,绿绿的铁环滚啊滚的,滚到了造船匠的家里。
我去看那个造船匠造船。那个造船匠,一直嚷嚷着要造一艘诺亚方舟,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铁钉都已经快要烂掉了,那艘大船仍连个影子都没见,那个造船匠,也早已不见踪影啦。
只有故乡的大槐树,一座北宋的寺,粮站,步云桥,桥堍底下阿庆嫂的馄饨店,阿四的理发店,茶馆店,金子铺,剪刀铺,唱越剧的老人,依旧还在。
可是我的旧时光,它去了哪里呢?
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绿绿的铁环,去了哪里呢?
我再也回不到少年时,春风里了。我只能怅惘地回首,望一眼故乡,望一眼春天。那个孤单的,像一朵云一样飘来飘去的小女孩。那个在脖子上挂了一把铜钥匙,走起路来叮当叮当作响的小女孩。那个在河滩上拣石子,看着夕阳骨碌骨碌地从青龙湾的草坡上掉下去,饱含热泪的小女孩。
故乡,始终是她情之所牵,梦之所系的地方。哪怕那里的小河、青草、牛羊、炊烟,再也不认识她。哪怕那条蜿蜒如白蛇的小路消失了踪影。哪怕故园的灯盏黯淡,破旧的屋子里,挂满了蛛网与灰尘。哪怕,她的祖母,再也不会伫立在门口,等候她回家。
似乎只有那一片土地,才是我们一生的眷恋。我们的灵魂,从未远离故乡,城市的高楼,禁锢不住它。它总是随着春风,一年一年回来。回到青青河畔,回到童年,回到昨日,大槐树底下暖融融的春光中。
十六岁,我提着一只大红色的行李箱,离开了故乡。祖母伫立在村口,冲我挥手。我一直记得祖母的白发,在风中闪烁。
我的祖母,一个慈悲的老太太,一生信奉“人在做,天在看”,晚年,身体仍十分康健。有一天早上,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春天的黄昏,祖母坐在大槐树底下的一只藤椅上。一只老猫蜷缩在她脚旁。远远的,算命的王瞎子晃晃悠悠地走来,手里提着一只鸟笼,鸟笼里有一只翠绿色的小鸟。
祖母端出云片糕、龙井茶请王瞎子吃,央求王瞎子替我算一命。王瞎子让翠绿色的小鸟,衔出一张牌。
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坐办公室的。祖母摸着我的头,吃吃地笑了。果然,我后来坐了办公室。
祖母永远不知道,大槐树底下的春天,是我一生中最温柔的时光。
4
女神节,学校组织去公园健行。那个公园,虽与学校只隔一条马路,却从未去过。每日如困兽一般,囚在一个格子间里。抬头只看到高耸的楼群。这几年,城西的楼群愈来愈高,把天空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
四季流转,竟惘然不知呢。
日子走得忒仓促了些。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前疾驰,人生究竟会走到何处去呢?这平淡、庸常的岁月,究竟又会发生些什么新鲜的事情呢?
也许司命早已把剧本写好,舞台、布景亦早就搭好,只差你登台,咿咿呀呀地唱。观众寂寥,掌声寂寥,甚至有人喝倒彩。可是不管呢,照旧咿咿呀呀地唱。莫辜负了这大好春光呀,这素年锦时。
有时,未免会觉得深深地疲惫,想甩一记水袖,不管不顾,走到幕布后面去。一个人独自待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这样发着呆,看斜阳染红天际的微云。
在春天,孤独会发芽,心中仿佛翻涌着什么,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想说什么话。就让那些话烂在心里,谁也不告诉。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这里的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
“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如此痴情、缠绵的情书,应是在春天里写的吧。
这几天在看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这个莎翁的译者,小城有他的故居,就在梅湾街东侧。故居门口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两行字: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中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朱生豪的儿子尚刚先生,倒是见到过一回。朱生豪去世时仍是一个年轻人,我见尚刚先生的时候,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春天,我们说起海子、顾城,说起朗读者里的一个男人,卖掉了广州的房子,买了一个山谷,种了一山坡的玫瑰花。
亲爱的,当我说起春天,不知怎么,我闻到了玫瑰的芬芳。
此刻,天朗、气清、花红、柳绿。万物静默如谜。
一个人的春天,和许多人的春天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的孤独,与这个春天的孤独,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