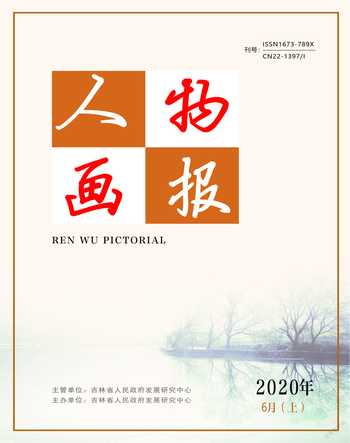行政协议判定标准问题研究
摘 要: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方式之一,随着公共行政理念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建立在协商互利上的新型行政关系。因此,如何更好地完善行政协议的判定标准,使之能够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帮助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更加顺利地进行、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协议;判定标准;公共利益
纵观全人类的发展史,合同作为人类商品经济萌芽的产物,它具有着极其古老的生命,同时也是见证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着的重要交易制度。在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会存在着“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界定,而“合同”这一名词就自然而然的被归入到“私法”的范畴之中。可从现实中看,“合同”这一交易制度在“公法”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与合同中的主体所不同的是,行政权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象征,向人们呈现的大多都是不容置疑、高高在上或是不需协商便可作出某些决定的形象,而随着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往“高高在上”的行政权也需要以更合适的面貌去实施国家管理。善治是现代民主国家贯彻的重要理念,国家的治理不仅需要强硬的国家行政权力,更要求非权力手段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行政协议也称为行政合同,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便产生了。
一、行政协议的概述
(一)行政协议的定义
行政协议作为一个“舶来品”,在我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国学界也将其称为行政合同,行政协议与行政合同只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实质上,从当前的立法实践及司法实践活动来看,我国对于行政协议这一法律概念仍处于不断地探讨之中。早在2015年就作出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及后续推出的司法解释中,对行政协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而在新《行政诉讼法》 实施数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其中,指明了: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1]
(二)行政协议的特征
第一,行政协议具有鲜明的行政性。显而易见,行政协议拆分来看便是“行政+协议”,是为了满足国家行政管理需要而订立的某种协议,本质上是为公权力所服务的。在我国,存在着“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界定,合同本应出现在民事法律领域,民事法律则应划分到“私法”的范畴之中。而随着现代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不同需求,公法与与私法之间的结合愈来愈密切,传统的“干预政府”也逐渐向着“服务政府”发生转变,产生一种能够迎合私法与公法领域的新型行政管理手段就变得十分重要。这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便是行政协议,它巧妙地运用了私法领域的“合同”的形式作为其基础,体现了行政机关与另一方相对人所形成的合意,行政机关可以在减少运用行政强制力的同时,可以通过协议这种相对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而这其中,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行政主体及授权组织可以自己名义签订行政协议。[2]在我国,一个行政机关的组成部门在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时,即便是在并不具备其主管部门的许可或是授权的情况下,也应当由签订该行政协议的主管部门来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与之相区别的是,民事合同只是约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往往对未参与合意的第三人不参生约束力。其次,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并非单纯的实现个人或者组织的利益,因此是具有十分明显的公法性质的。最后,行政协议双方具有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某种程度上说行政协议相对人处于行政主体的管理之下,行政相对人需要服从。[3]
第二,行政协议具有合同性。在传统视角下,行政权在实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不需经过行政相对人的同意便可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不平等主体地位的。而行政协议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固有的地位,双方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能是受到一定约束的,通过采取行政机关与另一方相对人所形成的合意,这种合意能够平衡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对等,可以使行政机关更好地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而后经由协议这种相对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而行政协议的合同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行政机关有权订立或是拒绝订立行政协议。对于行政协议的内容,相对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寻求与行政机关进行协商讨论,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地修改,直到行政协议签订双方形成合意为止;行政主体的让步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不能突破订立之时所要实现的目的。
二、行政协议判定标准所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协议的成立与合法条件未区分
翻阅我们现行的法律与司法解释来看,《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对于行政协议概念的界定,是增加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这一限定条件的。从这一规定上看,判定行政协议成立的要件与行政协议合乎法律的要件之间,没有做出相应明确的区分。简单来说,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机关是时刻需要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因此行政机关其职能的实现也有赖于具备相应的行政权能。根据传统理论而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通常表现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行政机关在自身行政权能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可以不经过公民的许可从而做出一定行政行为的。与之所不同的是,行政机关为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在其行政权能的范围内与行政相对人订立的协议是归属于行政协议范畴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反之,行政机关同样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但与行政相对人订立的协议超出了其行政权能的范围,那么此类协议就必然不属于行政协议的范畴吗?这在实务中明显是不合理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订立的此类协议虽然超出了行政机关相应的行政职能范围,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就算行政机关不具备相应的行政职能,也只是产生行政协议的效力问题而不是行政协议的性质问题。所以说,行政机关超出了其相应的行政职能范围与行政相对人订立的此类协议是必然归属于行政协议的范围之内的,不仅如此,简单的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的限定条件“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为判定行政協议的标准之一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讨论的,这会导致会不合理地使部分行政协议纠纷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合理审查与裁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也就无从谈起。但法律实践的过程中,要求每一位法官都要熟读立法者的书籍以达到知悉立法者的明确意图是比较困难的,绝大多数法官在审理案件之时主要还是依据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表述可能非但无法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反而会使司法实务对于行政协议的认定陷入混乱。
(二)行政协议目的含义未明确
判断行政协议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目的上的公益性。实质上,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实际上,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不同背景下是具有诸多不同含义的:广义上的公共利益可以分为普遍的公共利益和特定的公共利益,前者是指处于同一社会关系中的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等; 后者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特定群体的利益。狭义的公共利益仅指普遍的公共利益。诚然,立法者在法律文件之中采用这样不确定的概念有利于增加法律的适应性,但也会给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活动时徒增不必要的的困难。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目的获取某种利益、侵害相对人权益的例子比比皆是。[4]所以说,将行政协议中“公共利益”的含义加以明确,对于在实务之中更好的界定行政协议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政协议判定标准的完善对策
(一)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
作为行政协议的目的标准之一,公共利益在界定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之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更好的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就变得十分重要和急迫,想要明晰公共利益的含义应从几个方面出发。
第一,公共利益的内容是处于一种不断拓宽的状态。如上所述,公共利益可分为普遍的公共利益以及特定的公共利益,这其中就包括了国家安全、自然环境或者是特定群体的合法利益等等。但实质上,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不同背景下是具有诸多不同含义的,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之下,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时代,公共利益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第二,公共利益本身具有不特定性。公共利益的不特定性主要表现在,其内容的不特定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公共利益这一内容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其自身也在不斷地拓宽之中。即便是学界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对公共利益作出了相应的界定或是定位,但也并不能完完全全的准确划分出公共利益的范围。第三,公共利益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前面说到,公共利益包括特定的公共利益,也就是某些特定群体的利益。而实质上,公共利益也可以看作是一大群人的共同利益,这是由众多人的利益所共同组成的。人是具有鲜明社会性的,而公共利益必须是依附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而存在着的。第四,公共利益是不以盈利作为其目的的。这一特性就意味着,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或群体并不能从中获取到任何的非法利益,即使这个服务本质上是能够帮助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也不应当被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最后,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遵循一定的行政法原则。合理性是行政法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之所以进行行政管理行为,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如何更好更合理的行使行政权能是行政机关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合理性原则的切实遵守。
(二)明确“行政协议”的判定标准
第一,为了更好地实施行政管理而签订行政协议的主体,一方必须是具备一定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而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民事主体与另一方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并不能被认定为行政协议,在这其中双方是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来开展民事活动的。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行政主体呢?行政主体首先是指行政机关,即乡镇至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对外管理职能的部门。[5]不仅如此,行政主体的范畴内还有其他的主体,分别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 ( 居) 委会等社会组织,基于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而行使行政职权,从而成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
第二,签订及履行行政协议需要有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切来说,行政主体应该具备相应的行政权能,其行政权能是由法律、行政法规或是规章所赋予的。与此同时,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之一是通过行政协议的履行得以实现,但法律之中如若存在严禁行政机关经由签订行政协议此种行为来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相关规定,行政主体就不能作出类似的行为。而在行政协议履行的过程中,不仅要按照合同本身的约定进行实际履行,还应当遵从行政法的基本程序性原则。
第三,对于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签订的协议的属性判定,核心就在于就在于协议的内容是否包含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简而言之,当协议的内容包括行政权能内容之时,此类协议的行政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行政协议的履行体现着十分突出的行政性。上面谈及到,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是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与行政相对人所订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能无法得以施展。首先,在行政协议订立后,行政机关有权对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协议的工作进程或是具体方式进行监督和指导。其次,在面对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协议不当之时,有权对其进行指导或是纠正,以便公共利益的更好更快实现。最后,如果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法律赋予的强制手段,强制对方履行协议,以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行政机关如何更加高效更加效率的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如何促使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已然成为各国学界所热议的话题。我国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建立中国的行政协议制度更加具有现实必要性和规范紧迫性。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行政协议制度一定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不断发展完善。
注释:
[1]参见《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2]朱新力:《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版。
[3]步兵:《行政契约中的特权及其控制》,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版。
[4]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政法论坛2016年版。
[5]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沈福俊:《司法解释中行政协议定义论析——以改造“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表述为中心,法学2017年版。
[3]江必新:《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法学2012年版。
[5]何海波: 《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简介:
蔡佳朋(1996.01-),男,汉,海南海口,学生,研究生,宪法学与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