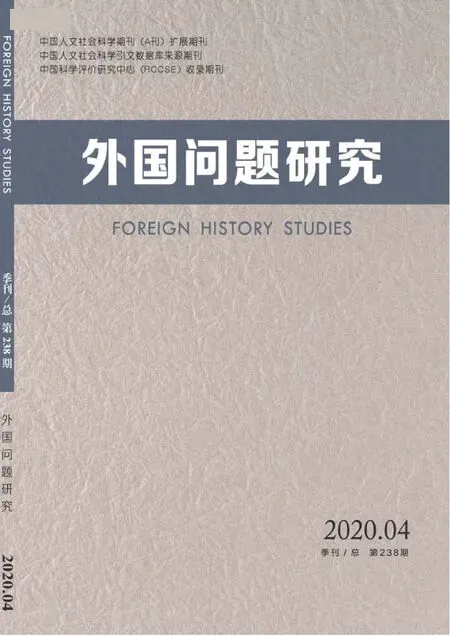唐、日陪都布局与建置原因比较研究
——以洛阳、太原、难波京、恭仁京为例
韩宾娜 王艺深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国内的中、日都城比较研究可以以2000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研究以考论日本古代都城渊源为主要话题,主要观点认为日本都城的形制来源于唐长安城与洛阳城,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宿白、王维坤、王仲殊。(1)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考古》2000年第7期。后期,学界观点呈现多样化态势,关于日本都城源流,出现了邺城说、(2)牛润珍:《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魏晋建康台城说。(3)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研究也不断细化,出现了以都城内部某个要素,如条坊、建筑形式为中心主题的研究,代表学者有王仲殊、王晖等。(4)王仲殊:《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考古》1999年第3期;《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考古》2004年第10期。王晖:《日本古代都城条坊制度的演变》,《国际城市规划》2007年第1期;《日本中世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城市空间的变迁——以京都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2期。王海燕所著《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5)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较早系统讨论日本都城的中文专著。
日本学界的都城研究通常以中国都城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较早从事都城研究的有喜田贞吉、泷川政次郎、岸俊男等人,观点影响力大,常被中国学者引用。(6)喜田貞吉:《喜田貞吉著作集·第五巻·都城の研究》,東京:平凡社,1979年。瀧川政次郎:《京制並びに都城制の研究》,東京:角川书店,1967年。岸俊男:《日本の古代宮都》,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涉及陪都的部分可参阅仁藤敦史与小笠原好彦的著作。(7)仁藤敦史:《都はなぜ移るのか遷都の古代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年。小笠原好彦:《聖武天皇が造った都——難波宮·恭仁宮·紫香樂宮》,東京:吉川弘文舘,2012年。目前已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都城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下,都城制度的研究本质上是希望将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态史归结为相互联系、前后影响的历史,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问题具体在于缺少比较标准,相似要素之间的内涵、产生原因不同,无法直接证明有前后影响关系。(8)成一农:《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本文都城布局的比较研究不仅以样本城市为例且更多考虑都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与线索;另一方面也不仅限于布局的对比,建置原因、城市体系等问题都被列入了讨论范围。谨为文,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布局原则异同
(一)中轴线
日本律令制下诸京无论首都、陪都,除藤原京外均采用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主要宫殿轴线与宫城轴线重合,宫城轴线与京城轴线重合,宫城南端与朱雀大路相连,(9)大阪市博物館協会、大阪文化財研究所:《難波京朱雀大路跡発掘調查報告》,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12年,第8頁。这显然与唐代都城制度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京城建筑基线可能并不仅限于京域范围之内,如平城京朱雀大路向南为古代下津道、难波京再向南为难波大道。千田稔认为,在藤原京南北中轴线的南延长线上,分布着诸多古坟。持统天武合葬陵(桧隈大内陵)即在都城中轴线的南延长线上,这可能是附会道教中的“朱火宫”而有意进行的布局。同样恭仁京虽然因山地分为左右两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左右京即以此为划分,并且京域中坡度起伏较大,恭仁京大极殿的中轴线可能并不是全城轴线。除了现大极殿正南方的道路可以作为城市轴线外,都城左右边界的正中是形式上的轴线,向南正对元明天皇陵。这一布局形式与藤原京南侧正对古坟相同。(10)千田稔:《古代日本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第26—49、261—270頁。朱火宫思想即《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陶弘景注所记载:“在世行阴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浅深轻重,故其受报亦不得皆同。有即身地仙不死者,有托形尸解去者,有既终得入洞宫受学者,有先诣朱火宫炼形者。”即死后,灵魂先于朱火宫修炼,而后才能成仙。

图1 恭仁京复原图(11)足利健亮:《恭仁京域の復原》,《社会科学論集》1973年第4·5期。
唐代洛阳城市轴线北起邙山,南对伊阙龙门,将周围“川原形胜”也纳入城市设计之中,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日都城陪都建设的共同特点。《元和郡县志》记载:“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12)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可见隋炀帝亲自考察地形对洛阳城微观选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隋唐洛阳城宫城居于西北部的城市布局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将整个都城的核心与伊阙龙门相对。(13)关于隋唐洛阳城为何采取宫城位于西北部的布局形式,有不同的意见,俞伟超即采取正对伊阙龙门的看法,参见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将城市轴线与自然地形相连接的做法最早见于秦咸阳宫,《史记》记载秦咸阳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14)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这两组界标提示着都城直接控制范围与国家范围这两个空间层次。而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汉代长安城则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都城选址时通过结合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来构筑跨越城墙的城市轴线,城市不仅与周围自然融为一体,也凸显出城市——地域——全国的控制层级。(15)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
隋唐洛阳布局以及城市轴线的生成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完成的,同样也可以认为日本将都城建立在古道节点的做法是受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超长轴线”的影响。唐代洛阳城延续隋代布局,所不同的是唐代又在洛阳城南北轴线的延长线上新增了宗教建筑,于北邙山上建上清宫,在伊阙龙门建天竺、奉先寺。(16)“高宗龙朔二年,诏洛州长史谯国公许力士,于邙山建上清宫以镇鬼。”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转引自赵荣珦:《洛阳上清宫考略》,《中国道教》2001年第1期。“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涨,毁都城南龙门天竺、奉先寺,坏罗郭东南角。”刘昫:《旧唐书》卷37《志第一七·五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7页。不排除轴线上宗教建筑具有重大意义的可能,因为李唐尊老子为祖先,上清宫即供奉老子,而奉先寺在开始修建时很可能是为供奉皇室祖先。(17)富安敦:《龙门大奉先寺的起源及地位》,《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二)“洛水贯都”与“斗为帝车”
唐代洛阳城整体布局特点有二:其一,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与首都长安同属“北阙型”都城;其二,河水穿城而过,“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这两个特点其实是同一布局思想的两个方面。
以北为上的布局理念则是出于古代天文学知识与“紫微”“北斗”崇拜,如:
“宫者,天有紫微宫,人君则之,所居之处故曰‘宫’。”(18)长孙无忌等撰:《故唐律疏议》卷1《十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年,第24页。
“紫宫为帝皇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谓之北斗,动系于占,实司王命。”
“紫宫垣下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19)魏征等撰:《隋书》卷19《志第一四·天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04、530页。
其核心为:天文中的紫微宫为天帝居所,紫微宫与人间之皇宫相对应,地上的太极殿作为皇宫的核心被认为与天上星宿的北斗相对应。由此通过宇宙论将都城神圣化,王朝的正统性也借此建立起来。(20)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计划》,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41—145页。不仅首都长安如此,洛阳也在同一思想体系下建成:“(皇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2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8《志第二八·地理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82页。
而隋唐时这一对建都布局造成重要影响的宇宙论在秦汉时已经形成,两个时期的思想并无本质区别: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22)《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第1289页。班固撰:《汉书》卷26《天文志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74页。
将宫城建于都城北部与河水穿城而过的设计,都是中国古代宇宙论在都城实践中的反映。《周礼·匠人营国》记载了中国最早的都城规划思想,其中所体现的“天圆地方”“四方”“四时”等象征意义以及十二座城门将“四时”细化为具体时间,与中国古代以十二地支对应,并运用于纪年、计时。数字“九”象征最高等级,都城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相对应,地方城市的等级包括道路、城门数量,占地面积都应该等低于首都规格等象征手段,(23)武廷海、戴吾三:《“匠人营国”的基本精神与形成背景初探》,《城市规划》2005年第2期。相比于秦汉时“象天法地”的布局原则显得相对简单、原始。秦汉时所产生“象天法地”的建都思想是都城布局理论上的创新,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只是在具体布局上,秦咸阳在渭水两侧均设置宫殿的做法被省略,(24)徐斌、武廷海、王学荣:《秦咸阳规划中象天法地思想初探》,《城市规划》2016年第12期。所剩只有以宫城象北斗,以洛河象银河的具体表现。
日本都城除藤原京外,首都和陪都都采取“北阙型”宫城布局,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同一制度,在日本不仅体现了天皇的崇高地位,也是为了给外来使节留下积极印象而采取的行动。(25)瀧川政次郎:《京制並びに都城制の研究》,第324—325頁。日本都城中恭仁京对这一思想体现最为充分。恭仁京不仅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也有木津川穿城而过,与洛阳异曲同工,在河上建天津桥也是其例证,《尔雅》云:“箕、斗之间汉津也。”(26)郭璞注:《尔雅》卷6《释天第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8页。故而洛水之上有桥名为“天津”,恭仁京木津川桥两次刻意修建应当与此有所联系。(27)菅野真道等撰:《続日本記》巻14,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第237、240頁:“(天平十三年十月)癸巳,贺世山东河造桥,始自七月至今月乃成。”“(天平十四年八月)乙酉,宫城以南大路西头与甕原宫东之间令造大桥,令诸国司随国大小输钱十贯以下一贯以上,以充造桥用度。”另外,恭仁京分为东、西两部,中为山地,可能是受到太原分为东、西、中三城的影响。
(三)三朝制
“三朝”即内朝、中朝、外朝。据《唐六典》记载:
“承天门,隋开皇二年作。初曰广阳门,仁寿元年改曰昭阳门,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曰承天门。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盖古之内朝也。”(28)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7页。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第一,在唐代官方记载中认可“三朝”的说法;第二,唐代“三朝”为南北直线分布,分别为外朝承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第三,“三朝”各有职能,外朝主要负责各种仪式的举行,中朝为半月常朝的场所,内朝为皇帝日常办公场所;最后,唐代对前代三朝制具体情形甚至是否实行三朝制并不肯定,只能以“盖”来推测,三朝制在陪都中也没有严格实行,洛阳正殿乾元殿与日常处理政事的宣政殿并非南北对应关系,而是东西并列。由此便产生了三朝制产生于何时、实行于何时、三朝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唐代的三朝制影响有多大等问题。
首先,三朝制的实际运用可能最早只能追溯到东魏邺城,不仅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都城外朝、中朝、内朝,而且东魏邺城不仅建有南北排列的宫殿建筑,同时太极殿两侧东西堂仍发挥非常大的作用。(29)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84页。
其次,郑玄《周礼》注最早对三朝制作出描述,(30)贾公彦疏,黄侃句读:《周礼注疏》卷35《朝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31页:“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内者,或谓之燕朝。”而对三朝功能的解释《周礼》正文中只有对外朝的解释,且可能并非三朝制之“外朝”。唐代贾公彦《周礼》疏中更为详细,(31)《周礼注疏》卷35《小司寇》,第522页;卷16《槀人》,第253页:“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天子三朝,路寝庭朝,是图宗人嘉事之朝,大仆掌之;又有路门外朝,是常朝之处。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皋门内,库门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断狱弊讼之朝,朝士掌之。”到唐代晚期杜佑撰《通典》看法则融合以上多种观点,形成“天子有四朝”的看法。(32)杜佑:《通典》卷75《礼三十五·沿革三十五·宾礼二·天子朝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39页:“周制,天子有四朝。恒言三朝者,以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因此,三朝制在都城建设的实践中比较完善的时段可能要晚至隋唐时期。(33)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将三朝制分为注重思想的“儒学三朝”与实际运用的“匠学三朝”,参见庞骏:《东晋建康城权力空间——兼对儒家三朝五门观念史的考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241页。
唐代三朝制的影响及于周边,(34)渤海上京的三朝制与唐代制度相似度最高,参见刘晓东、李陈奇:《渤海上京城“三朝”制建制的探索》,《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日本都城中即受到三朝制的影响,岸俊男指出平城京中内里正殿相当于内朝,大极殿相当于中朝,大极殿院门则相当于外朝。(35)岸俊男:《日本の古代宮都》,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第173—174頁。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都城中的朝堂院与唐代都城制度稍有不同,不像《唐六典》中记载的承天门仅作为礼仪空间,也不同于长安城皇城内排列各处政府机关的做法。一方面,朝堂院中朝堂具有一部分礼仪空间的职能;(36)根据王海燕的研究,唐代的宾礼根据对象国的地位来决定。对等国关系常在内朝或外朝空间接见使节,附属国常在内朝接见使节;日本在接待新罗、渤海使节时常在朝堂设宴,并有要求入京使节参加元日朝贺礼仪。元日礼仪方面日本以射礼为代表,通常举行于南庭(大极殿院南门)。参见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130、140—148页。另一方面《延喜式》等文献记载:“凡百官庶政皆于朝堂行之。但三月、十月旬日着之。正月、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并在曹司行之。”“凡京官五位以上先参朝堂。后赴曹司”(37)經濟雜誌社:《延歷交替式·贞觀交替式·延喜交替式·延喜式》巻11《太政官》,東京:經濟雜誌社,1900年,第421頁、巻41《彈正臺》,第1060頁。可见朝堂并不等于各部门办公地点,而应是议政之所,因此可视作“中朝”的延伸,固定的办公地点为引文中曹司,前期难波宫中的东方官衙遗迹可能即是如此。因此,朝堂院相当于唐代三朝制中的外朝而稍有不同。
另一方面日本古代的宫城布局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大极殿院逐渐与内里分离形成三个独立院落,内里逐渐与大极殿院朝堂院分离的过程,前期难波宫内里(天皇居住空间)、大极殿院、朝堂院连为一体,到后期难波宫时难波宫大极殿院连接朝堂院,并与内里分离。(38)大阪市文化財協会:《難波宮址の研究·第十三》,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05年,第20—35頁。大阪市文化財協会:《難波宮址の研究·第十》,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1995年,第70—89頁。日本都城宫城内空间变化的动力是官僚制度的发展,而唐代三朝制无有定制则为周边国家都城的建设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因此可以说唐代将中国古代经典中理想的布局方式予以实施,实行了对宫城中枢部空间划分并对各区功能加以分别的特殊制度,且已经对周边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但各国接受程度也并非完全相同,日本宫城中枢部分空间尚在不断变动,各国对三朝制有着不同的理解。

图2 后期难波宫遗迹分布图(39)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日中古代都城図録》,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09年,第17页,改以中文标注。
二、陪都设置原因与类型对比
(一)都城建设中的促进交流融合因素
唐朝延续前代的“关中本位政策”(4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页。并建都关中。虽然王朝已经建立,并且稳定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势力已经融为一体,将洛阳设为陪都有沟通关中与山东、江南并控制后二者之意,或者说洛阳即是经济、文化交融的前沿阵地。
魏晋南北朝以来全国氏族大约可以分为五个地域性集团,唐人柳芳将其分为江左“侨姓”、东南“吴姓”、山东“郡姓”、关中“郡姓”、代北“虏姓”五大集团,(41)《新唐书》卷199《列传一四二·儒学中》,第5677—5678页:“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在唐代氏族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唐代曾多次官修谱牒如《大唐氏族志》《姓氏谱》《大唐姓族系录》即说明了这一点。(42)《旧唐书》卷46《志第二六》,经籍上,第2012页。刘知几也主张作“氏族志”来对诸姓人物作以标识:“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土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刘知几撰:《史通》内篇《书志第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安史之乱后所成《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以地域为划分标准记录了大量望族姓氏,现仅举河南、江东两例作一比对:
“洛州河南郡出廿三姓:褚、穆、独孤、丘、祝、元、闻人、贺兰、慕容、高、南宫、古、山、方、蔺、庆、闾丘、利、芮、侯莫陈、房、庸、宇文。
……苏州吴郡出五姓:朱、张、顾、陆、暨。”(43)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3—518页。王仲荦先生认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成书于大历十四年后元和元年以前,华林甫先生认为前一观点有误,该书应成于天宝初年(742)至肃宗至德二年(757)之前。参见华林甫:《〈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从中可以看出唐代仍延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氏族以地域为单位集结的趋势,洛阳鲜卑姓、东南吴姓势力未减,更不用说史书中明确记载与皇室摩擦不断的山东望族。在此情况下,洛阳作为“天下之中”,融合各地氏族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一方面,在隋代兴建东都洛阳时,大业元年三月下令营建东都,同年七月又发布劝学访才诏书,(44)“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3《帝纪第三·炀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4页。东都营建与促进全国文化融合应有所联系,唐代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唐代洛阳地区的鲜卑望族也不断向外乔迁,以东都为起点融合于各地,如河东道泽州高平郡有独孤氏、并州太原郡有尉迟氏、徐州兰陵郡有万侯氏等。
而太原无论是在资源占有方面还是在军事险要方面都十分重要,足以对天下形势产生影响。对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隋唐以前便已记入史册:“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带甲五万,北阻强胡”。(45)陈寿:《三国志》卷26《魏书·满田牵郭传第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0页。因而唐代除在太原设置北都之外,还以太原府为治所设置了河东节度使,统御军队以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46)《旧唐书》卷38《志一八·地理一》,第1386—1387页。
另一方面,既为军事重镇,目的在“御北狄”,则说明太原府是中原同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舞台之一,自秦汉以来即是如此。“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47)《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第2633页。到唐代,虽然太原府并不处在农牧交错带上,但自北到西再至西南临近诸州均为半农半牧,(48)根据韩茂莉先生的研究,隋唐代农牧交错带向北有所扩展,其中断河东道内农牧交错州为慈、岚、忻、云、隰、石、代、朔。参见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4页。再加上突厥内附后,太原及周边诸州多作为降户驻地,“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朔、代二州即在太原府之北。“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49)《旧唐书》卷194上《列传一四四上·突厥上》,第5168页。《旧唐书》卷99《列传四九·张嘉贞》,第3090页。其促进民族融合的功能是明显的,《通典》中记载并州风俗为:“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50)杜佑:《通典》卷179《州郡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45页。同时在唐人心目中也以并州为中原文化的北方“边塞”,(51)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李晓聪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20—321页。有诗为证,如“并州近胡地”“县属并州北近胡”“汾河流晋地,塞雪满并州”。(52)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271页、第2992页、第6877页。虽然唐代设置北都太原的直接原因是控制战略要地、防御游牧民族,但正像边境摩擦、暴力冲突也是融合的方式之一一样,无论统治者主观上情愿与否,北都太原的设立都促进了民族融合。
古代日本本土也存在少数民族,即史籍中记载的虾夷、隼人。隼人也有部分迁入京城,在律令制下,日本在兵部省下设隼人司管理事务。(53)根据《延喜式》记载,隼人司主要负责调集京城内的隼人参加元日等国家礼仪活动,并颁给粮、服。《延歷交替式·贞觀交替式·延喜交替式·延喜式》,第854—857頁。但融合民族的功能在日本都城发展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隼人主要集中于九州岛南部,虾夷主要活动于本州岛东北部的陆奥国,两个民族分别位于日本东、西两方边缘地带,离建立都城的畿内地区较远,影响微弱;另一方面,日本西部有大宰府,东部筑有多贺城是应对少数民族事务的前沿要地。(54)《続日本記》,第120頁:“(养老四年,二月)壬子,太宰府奏言,隼人反,杀大隅国守阳侯史麻吕。三月丙辰,以中纳言正四位下大伴宿弥旅人为征隼人持节大将军。(同年八月诏还)。”第124頁:“(养老四年,九月)丁丑,陆奥国奏言,虾夷反乱,杀按察使正五位上毛野朝臣广人。戊寅,以播磨按察使正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为持节征夷将军。(翌年四月归还)。”日本常将本土少数民族虾夷、隼人与新罗、渤海置于同等位置,其原因是受到中国华夷观念的影响,企图在中国之外再行塑造中心国家,建立“东夷小帝国”,但是随着虾夷、隼人不断内化,新罗外交亦不稳定,“夷狄”不再存在,“帝国”自然无存。(55)佐藤信:《律令国家と天平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270—307頁。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将唐朝、日本作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而非两个毫不相关的国家来看的话,日本都城的建设,尤其是难波京的建设,也可以看作是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交流的重要舞台,文化吸收的前沿阵地。4世纪所开凿的运河难波堀江,(56)“故群臣共视之。决横源而同海。塞逆流以全田宅。”“掘宫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日本書紀》巻十一),“又掘难波之堀江而通海。”(太安萬侶:《古事記》下巻,東京:經濟雜誌社,1898年,第127頁),“今山崎河通海是其堀江也。”(藤原緒嗣等:《日本逸史·扶桑略记》,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第460頁)。也成为难波地区发展的优势条件。一方面难波堀江的开凿打通了从大阪湾到飞鸟、山背地区的水路运输,将海运与河运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从祭祀与管理模式来看,难波津(港)南面的住吉津原本更为繁荣,神社数量庞大,很可能是地方豪族津守氏管理,而难波津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在管理体制上更加进步。(57)直木孝次郎:《難波宮と難波津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第21—24頁。水运与仓库的修建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也使其成为外交上重要的港口,推古十六年六月隋使裴世清、舒明四年十月唐使高表仁、皇极元年高丽使人、同年五月百济使者都从难波港登陆,可见其不仅是国内的重要经济枢纽,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节点。
(二)“辅助”含义的确定与中日陪都制度
“陪都”是指在首都以外另设置的都城。设置多个都城的做法起源很早,先秦时期就已经运用于国家治理,但是“陪都”这一词的出现时间晚于陪都制度的实行。据考证“陪都”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白的诗句“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陪都”。(58)吴立友:《“陪都”词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8期。除了“陪都”之外可以相互替换的名词还有“陪京”“下都”等,每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早期通常以方位与“京”“都”连称的方式命名陪都,如“西京”“东都”,到唐宋时期陪都等相关称呼才广泛使用。(59)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换句话说,陪都中表明等级、确定辅助地位的语义可能在唐宋时期才最终形成,这与早期两京并列、不分主次的都城制度是不同的。而其变化可能是宋代维持复都制的王权思想由“天”向“理”转变的体现。(60)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兵兵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3—294页。先秦至秦汉时两京并举不分高低的观念直到隋唐时期仍有存留,如唐高宗即认为“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61)李昉撰:《太平御览》卷156《州郡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版,第760页。
日本都城方面,在原始文献中并没有“陪都”的提法,即使在比较明确的天武天皇“建陪都诏”中也只是说“必造两参”,其他记载中通常的记录是“行幸”或“迁都”。直到8世纪中叶保良宫、由义宫的兴建才有“北京”“西京”之名,这时首都、陪都的含义才相对明确,在此之前并无法说明都城有主副之分。究其原因,日本陪都兴起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陪都制逐渐定型、含义逐渐明晰、影响逐渐扩大的时段,而日本都城没有完成主次序列分离这一过程,可能与其存在时间短暂相关。另一方面,在古代日本都城通常建于畿内(紫香乐宫除外,这也可能是其初始仅为离宫的原因),即大和、河内、摄津、和泉、山背五国,而“畿内”换言之即是王畿,在空间尺度上类似于秦汉时的三辅,隋唐时的关中,换种眼光来看很类似于后世的“首都圈”概念。(62)首都圈是一种以首都城市为中心城市的特殊都市圈,不只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参见张召堂:《中国首都圈发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同时首都圈内行政管理与职官设置也通常具有特殊之处。参见叶骁军:《都城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38—49页。日本畿内的特殊官职有京城左右京职大夫、摄津国摄津职、河内国河内职。圣武天皇以后畿内水路逐渐完备,寺院增多并形成系统,离宫建设逐渐延伸至五畿之外,这一过程,也许可以视作首都圈的发展。参见吉村武彦、山路直充編:《都城:古代日本のシンボリズム》,東京:青木書店,2007年,第307—308頁。也就是说都城不仅在畿内迁移也有同时设都多处的现象,但因为所限范围不大,再加上道路体系的连接,所以首都、陪都的功能、属性非常接近。
(三)日本陪都建设中的贵族影响
明确的贵族制度是唐代政治制度中所不见的。天武天皇十三年“冬十月乙卯朔,诏曰: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弥;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63)舍人親王等撰:《日本書紀》巻30,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第533頁。根据与皇室血缘关系的远近对贵族作出了划分,明确了高级官僚与低级官僚、中央与地方官僚差别,提高皇族近亲地位。(64)徐建新:《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确定也使得权力并非集中于天皇一人,都城的迁移新建、陪都设置都受到高级贵族的影响。
天平九年(737)平城京爆发疫病(天花),在朝廷中枢担任官职的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相继病逝,(65)《続日本記》巻13,第240頁:“是年春,疫疮大发,初自筑紫来,经夏涉秋。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继没死,不可胜计。近代以来未之有也。”中央职位空缺,橘诸兄势力膨胀,进而激起藤原氏反抗,藤原广嗣之乱爆发。这一阶段中提及恭仁京建设的史料多涉及橘诸兄,如:“十二年十一月戊午从不破发至坂田郡横川顿宫。是日。右大臣橘宿弥诸兄。在前而发。经畧山背国相乐郡恭仁乡。以拟迁都故也。”“十一月戊辰右大臣橘宿弥诸兄奏:此间朝廷以何名号传于万代。天皇敕曰:号为大养德恭仁大宫也。”可见其在恭仁京建设中的主导地位。(66)橘诸兄本为皇族后裔葛城王,后请将为臣籍,赐姓橘氏。事见《続日本記》巻12,第203—204頁。喜田贞吉认为,相乐郡有橘诸兄别业,迁都恭仁京即橘诸兄一手策划,其兴废均与橘诸兄势力消长相关。喜田貞吉:《喜田貞吉著作集·第五巻·都城の研究》,東京:平凡社,1979年,第117—125頁。
由此可将迁都恭仁京的过程简化为:前任权力者(藤原四子)失势——新任权力者(橘诸兄)崛起——前任权力者继承人(藤原广嗣)叛乱——在新任权力者势力范围内建立陪都。这一模式也在后来建立保良宫、由义宫时再次重演,(67)其过程分别为:橘诸兄失势——藤原仲麻吕崛起——橘奈良麻吕叛乱——在藤原仲麻吕曾任近江国守的近江建立保良宫;藤原仲麻吕失势——道镜崛起——藤原仲麻吕叛乱——在道镜家族弓削氏势力范围内建立由义宫。这或许也是除难波京外日本古代陪都使用时间短暂的原因之一。
(四)发展指向与陪都类型
学者丁海斌曾将中国古代陪都分为十个类型,(68)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第16—27页。基本涵盖了中国自先秦至清代所有陪都类型,例如唐代洛阳可以认为是东西平衡型陪都,古代典籍中将洛阳描述为“天下之中”,若从空间上理解即是此意;太原可以看作“龙兴之地”的留都型陪都;成都、蒲州等其他陪都则是出于分区治理目的的多京制陪都。将这一分类方法运用至唐代陪都的研究十分贴切,但是以上分类中多偏重于对内安全指向,却没有对外发展指向。“国都定位属于区域空间现象”,都城选址必须满足对内安全指向与对外发展指向两个指标。(69)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1—170页。也就是说,陪都功能与类型,可能并不单一,除去主要职能之外还有次要职能,其分类也并不能只依据主要职能,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及首都、陪都的联系之后再做具体讨论。以上分类中,中国古代陪都并非没有起到守卫疆土、融合民族的作用,只是这些功能并非中国古代陪都建设的首要目的。那么是否有外向型陪都?除了前文所述唐代洛阳、太原有融合东南氏族与塞北民族的功能之外,日本陪都是很好的例证。首先,日本皇族起源于大和地区,飞鸟——大和地区的都城才被视为正统都城。其次,从功能上看立都时间最长的难波京主要功能即是外交,史籍中记载“难波馆”“高丽馆”及大、小郡等外交设施说明了难波地区不仅是古代中、日交往的舞台,更有朝鲜半岛使节在此登陆日本;第三,从地区分布上看,日本古代陪都均不在大和地区内,难波京位于摄津国,恭仁京位于山背国,紫香乐宫则位于更远的近江国。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末桓武天皇将首都迁移至平安京,平安京即位于山背国,迁都后改名山城国,日本首都自此结束了不断迁徙的历史,不动之都建立在大和地区之外。
因此日本陪都可以称为“外向型陪都”,不仅因为其功能在于外交,也在于将都城设置于大和地区之外的前沿位置。对比中、日7、8世纪都城建设不难发现,中、日两国首都、陪都建设的目的相反,唐朝以龙兴之地为陪都,建立留都型陪都;日本以皇族发祥地为首都,建立外向型陪都。唐朝首都、陪都均有对外发展的战略目的,日本这一目的更集中地体现于陪都建设。
结 论
总之,从城市布局上来看,唐、日陪都之间同大于异。唐代都城建设吸取了秦汉以来的建设经验,城市布局方式日臻成熟,并影响到周边国家,可以认为日本都城布局中的特点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建筑基线跨越城墙与周边相融合、将宇宙论或天象崇拜融入都城布局中是自秦汉以来积累而成的布局方式;三朝制构想以用途为标准,将宫城内部核心空间再次划分,将《周礼》中古典的都城建设思想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在建置原因上,唐代洛阳、太原促进交流融合的功能更加突出,日本难波京也可看作交流的舞台,只是其面向的是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从陪都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唐宋时期经历了“陪都”及同类词汇语义确定的过程,日本因陪都发展过程短暂而变化并不明显。贵族制度是日本陪都建造的特殊影响因素。从陪都类型上来看,唐代陪都设置更注重防御、控制等“内向型”功能,日本陪都则对非传统建都地区作出开拓。从这些方面来看,唐、日古代陪都的建设异大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