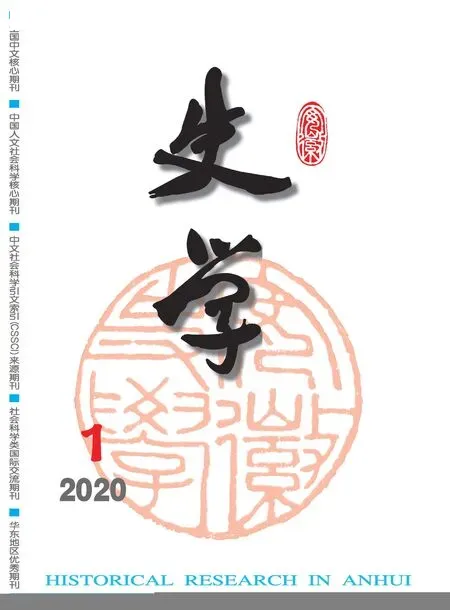国外陈独秀研究述略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第一任总书记。一直以来,国外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从未停止,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外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研究广度,亦或是研究深度,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值得国内学者加以了解、关注。
一、研究概况
国外最早对中国文学革命进行报道,并对陈独秀进行分析研究的论文是1920年11月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发表在『支那学』第1卷第3号上的「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学革命」一文。同一时期,联共(布)中央代表维经斯基、维连斯基,他们在1920年给苏俄国内的报告中都对陈独秀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点评。改革开放以降,欧美学者、日韩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日渐增多,并涌现出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目前来看,欧美学者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宏观上的把握和分析,如:美国学者李芾甘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建者》(1)[美]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美籍华人郭成棠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美]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英国理查德·C·卡甘的《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3)[英]Richard C.Kagan, Chen Tu-hsiu’s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The China Quarterly,No.50,Apr.—Jun.1972.和西班牙学者费南德·克劳丁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4)[西]费南德·克劳丁著、方光明等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
日本学者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则更为微观细致,侧重于横纵向的对比研究。如:横山宏章的《陈独秀》(5)[日]横山宏章:『陳独秀』.朝日新聞出版社1983年版。、佐佐木力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永久革命家陈独秀》(6)[日]佐佐木力:《彻底的民主主义永久革命家陈独秀》,奚金芳编:《陈独秀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和《吉野作造与陈独秀》(7)[日]佐佐木力:《吉野作造和陈独秀》,奚金芳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中屋敷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关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基础的考察》(8)[日]中屋敷宏:『「五四」新文化運動と陳独秀 :中国近代文学の思想的基礎についての考察』,文経論叢,1980,15(1)。等。

苏俄学者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成果则更偏向于政治上的分析、评价,例如:B·阿斯特洛夫《论中国革命》(13)[苏]B·阿斯特洛夫:《论中国革命》,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索波列夫的《共产国际史纲》(14)[苏]索波列夫著、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马诺夫的《杜亚泉和1910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确立》(15)[俄]А.В.Ломанов,Ду Яцюань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в 191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6,2017 г.以及维尔琴科的《“新文化运动”前期和最初中国对俄罗斯的理解》(16)[俄]Алла Леонидовна Верченко,Вослри ятие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Наканунеи в Пеовые Годы Движения За Новую Кулътуру,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等。
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各有侧重。欧美学者和苏俄学者的研究更为宏观,偏向于从整体上和技术上对陈独秀进行分析研究。相比之下,日韩学者则更偏向于从微观上对陈独秀的思想进行把握,以小窥大,进行细致的比对研究。
二、研究热点及研究方法评析
国外学界对于对陈独秀的研究,领域广泛,成果颇丰,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对陈独秀的历史定位
1920年,联共(布)中央代表维经斯基给苏俄国内的报告中多次评价陈独秀,将其称为“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将陈独秀介绍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页。后期,受政治和其它因素的影响,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开始大肆批判其“右倾机会主义”及“家长制”作风。如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其回忆录中称,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家长’。对于普通中共党员来说,他的威望和决定是无可置疑的”。(19)[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驰译:《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格鲁宁批判陈独秀带有典型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阶层的“探索精神、动摇性和错误倾向”,“‘左’的革命急躁情绪同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估价并存”。(20)[苏]格鲁宁著、黄东兰译:《二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奚金芳编:《陈独秀与20世纪中国》,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和实证主义研究的发展,国外学者对陈独秀的评价“被从过去教条主义的批判中解放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21)[日]江田宪治:《第一任总书记的功与过》,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南京会议)筹备处编:《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陈独秀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文化》,南京会议筹备处2002年版,第57—58页。英国学者高里戈·本顿毫不吝啬地称赞道,“他是伟大的多才多艺者:他是诗人、作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最重要的是,他是大无畏的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22)[英]高里戈·本顿:《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奚金芳编:《陈独秀与20世纪中国》,第271页。日本学者佐佐木力也认为,“像陈独秀那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在革命家、思想家和文人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23)[日]佐佐木力:《彻底的民主主义永久革命家陈独秀》,奚金芳编:《陈独秀研究文集》,第56页。
笔者则认为,日本学者横山宏章对于陈独秀的评价更为中肯贴切,即:陈独秀“最早地洞察了时代的趋势,理清了混乱的思想,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陈独秀一心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从前近代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直在探索新的运动与思想,他是时代的旗手。”“时代改变了陈独秀,同时陈独秀也改变了时代。”(24)[日]横山宏章:『陳独秀』,第7—8页。
(二)对陈独秀生平问题的研究
陈独秀生平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国外学者研究兴趣最为浓厚的区域,也是目前国外学者争议最多的区域。
1、对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研究
关于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国外学术界普遍认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所做的贡献,并将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儒教传统的自由旗手”。(25)[日]横山宏章:《从日本看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2008年版,第254页。美国学者格里德尔指出,“陈(独秀)在北京出现意义深远,不仅由于他的言论——正是在这期间他从一个进步人士转变为政治积极分子——而且也由于他为不断壮大的北大文化叛逆团体发出了第一声呐喊。”(26)[美]杰罗姆 B.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19页。格里德尔盛赞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肩负起了梁启超十年前未能完成的巨大思想启蒙任务”。(27)[美]杰罗姆 B.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19页。美籍华人郭成棠称赞“陈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平凡的角色”。(28)[美]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91页。
但美国学者史华慈却认为,虽然陈独秀以五四运动领袖而闻名,然而“就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陈独秀称不上是领袖”。(29)[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史华慈认为,“正是他的学生们的行动最终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拿起列宁的武器。”(30)[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对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研究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共产国际的帮助,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关系不大。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就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时,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和列宁主义的认识仅仅处在小学生的水平”,“共产党的成立并非建立在对中国未来前途的透彻分析与清晰的构想之上”(31)[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译:《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而是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直接输入。前苏联学者舍维廖夫也认为,在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之前,陈独秀“实际上都还没有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32)[苏]K·B·舍维廖夫:《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主要来源于苏联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组织和物质方面对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帮助。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和舍维廖夫观点类似,他认为来自苏俄方面的推动“才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转变为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33)[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而非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
另一派国外学者在考虑共产国际帮助的同时,对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物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美国学者李芾甘分析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背景,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人能像陈独秀一样在青年之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若无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那样快或那样早地建立”。(34)[美]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137;p.164.但李芾甘也很客观地指出,虽然陈独秀有志建立一个新型政党,“但若无共产国际的帮助,他未必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组织”。(35)[美]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137;p.164.美籍华人郭成棠也认为,“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和凡尔赛和平会议的历史事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在当时有可能成立起来,主要是由于列宁的中国政策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概念吻合的结果。”(36)[美]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33、143页。郭成棠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成为事实,就应归功于陈独秀的思想、性格、热诚、努力和领导能力了。”(37)[美]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33、143页。
3、对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国外学者最主要的的争议点。目前国外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就极力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遵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公然解散所有武汉职工会的纠察队及武装,正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错误,“乃成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38)[苏]米夫著、攸丽译:《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北方文化出版社1938年版,第44页。苏联学者索波列夫则刻意地夸大共产国际五大以后的统一战线政策,忽略其过失。索波列夫认为,“早在1921—1924年,陈独秀就曾经企图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今他又表现出强烈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从而放松了对国民党右派领导的警惕性。”(39)[苏]索波列夫著、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第258页。1927年7月,苏联《真理报》相继刊发了H·布哈林的《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T·曼达梁的《中共领导为何失败》和B·阿斯特罗夫的《论中国革命》等多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严厉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陈独秀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是大革命失败的关键,并称“将这些错误归罪于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这是反对派的恶毒中伤和无耻诽谤”。(40)[苏]B·阿斯特洛夫:《论中国革命》,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531页。此外,英国学者方德万也不同意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干涉的理论,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没有能力建立稳固的基础及缺乏必要的组织技能的结果”。(41)[英]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43.
持第二种观点的国外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美国学者费正清明确地指出,陈独秀完全“沦为斯大林错误判断的替罪羊”。(42)[美]费正清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在1927年的危机中“莫斯科仍指令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执行斯大林的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路线”,并在大革命失败后“指责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采取导致失败的‘机会主义’”。(43)[美]费正清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甚至讽刺道:“斯大林是宽宏大量的,他只找了一个替罪羊;同陈独秀不相上下的其他中共领导人这次得以幸免。”(44)[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西班牙学者费南德·克劳丁批判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认为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是共产国际为了摆脱斯大林困境局面的“遮羞布”。他毫不掩饰地嘲讽道:“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直到1927年所遭到的一些灾难,统统用一个奇妙的公式加以说明:即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45)[西]费南德·克劳丁著、方光明等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294页。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并不是陈独秀或者共产国际单方面的原因,而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日本学者中西功便提出,“有人辩解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的责任,陈独秀没有责任。这是徒劳的。”(46)[日]中西功:『中国革命と毛沢東思想』,青木書店1969年版,第145页。他进一步分析了当时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国内体制和对工人阶级认识方面的思想缺陷,认为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共产国际的判断失误外,与陈独秀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也是密不可分的。日本学者岩村三千夫对国民革命中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统一战线的错误根源在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了“党内合作”。但他认为“党内合作”并没有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也不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央的错误。“在这个错误里,不仅陈独秀有责任,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47)[日]岩村三千夫:『中国革命史』,青年出版社1974年版,第133页。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提出,蒋介石的屠刀轻而易举地落到共产党人的头上,不应该归咎于陈独秀的幼稚,但也不应该归咎于共产国际的傲慢无知。当时的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都没有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建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中国根本没有独立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任何现实机会”。(48)[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译:《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第229页。
4、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马忠行在《托洛茨基主义》一书中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的学说,回顾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认为陈独秀是“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的中国左翼反对派”。(49)[日]对马忠行著、大洪译:《托洛茨基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著作《双山回忆录》中以“自传”的形式回忆了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王凡西叙述了陈独秀与托派联系的过程,认为所谓的“托陈取消派”是对陈独秀的诬蔑和诋毁,“无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他那时都还是最有声望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50)[英]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5、319页。但是作者自身也承认,这篇著作是以其“个人视角来看的一面”,“不曾与不可能将它们用真实的文献来作检核和比对”(51)[英]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5、319页。,因此需要辩证地参阅书中内容。美国学者彼得·库弗斯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回忆录和各种参与者的报告以及当时新闻报道等资料,论述了陈独秀是如何与托洛茨基联系到一起,以及二者的具体关系等问题。库弗斯认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不应被归类为完全根据意识形态层面,也不能仅仅是‘机会主义’的融合,而是以基本意识形态认同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目的的互补”(52)[美]Peter Kuhfus ,Chen Duxiu and Leon Trotsky:New Light on their Relationship ,The China Quarterly,Vol.102,June,1985,p.275.,即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包容意识形态分歧的灵活关系。
(三)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陈独秀研究成果最为深入的要属对陈独秀相关思想的研究。
1.对陈独秀思想演变的研究

2.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
关于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研究,美国学者郭成棠认为,“陈似乎忽视了或者没有懂得列宁主义成果的原则——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纪律严格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主义政党将会代表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因此,郭成棠批评道,“陈不应该用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公式来解决他们在二十世纪里面临的问题,他也不应该把马克思观察欧洲社会的结论运用到中国复杂的情形中来。”(63)[美]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97页。日本学者江田宪治则认为陈独秀并没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江田宪治认为,“1923年4月陈独秀所发表的有关向革命的资产阶级寻求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的观点,决非主张阶级妥协,只不过是希望资产阶级参加联合战线。”“1923年12月的论文中对资产阶级评价较高,对无产阶级评价较低的情形,是由于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他需要作这种舆论上的准备。”(64)[日]江田宪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功与过》,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南京会议)筹备处编:《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陈独秀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文化》,第67页。

在对陈独秀国家思想的研究方面,美国卫斯里安大学的托万·卡多特伍德认为,1914年之前,陈独秀的国家思想主要围绕“人民、领土、主权”三点。1914年之后,陈独秀的国家思想发生了转变,侧重于国家对人民的亏欠,认为土地、人民和主权只是一个国家的形式,“一个真正的国家是由人民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维护他们的权利,为他们的繁荣提供保障”。(68)[美]Antoine Cadot-Wood,Striving Toward a Lovable Nation:Nationalism and Individual Agency in the Writings of Chen Duxiu,Wesleyan University,2010,p.55.澳大利亚学者艾德里安分析了陈独秀对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看法。在他看来,陈独秀期待一个“可爱的国家”,并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为国家的必要责任。如果国家做不到,“它就不能指望它的人民在智力上和情感上的忠诚”。(69)[澳]Adrian Chan, The Liberation of Marx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5,No.1,1995,p.102.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汉斯·方德万指出,陈独秀“对共和国历史的看法是,它的体制受到了那些为了纯粹的私人目的滥用共和党的政治机构。”(70)[英]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 ,p.20.方德万认为,“在这一点上,陈受传统的政治服务标准的影响,而不是受西方民主标准的影响。”(71)[英]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 ,p.20.
3.对陈独秀哲学思想的研究


4.对陈独秀文化思想的研究
在对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研究方面,法国学者谢和奈认为,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类似于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宣战,“因为中国的伦理与西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创业精神处于全面的对立中”。(8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页。美国学者纪文勋细致地分析了陈独秀思想中东西文化对立的表现,即“东方文化主张仁爱、安息,西方文化则健斗、好战”;“东方主张家族主义,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主张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东方主张感情、虚文,西方则主张法治、实利”。(82)[美]纪文勋著、程农等译:《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第229页。美国学者周策纵十分赞同纪文勋的观点,“在他(陈独秀)看来,东西方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西方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以虚文为本位。”(83)[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16页。美国学者余英时则认为,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时代学者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解释。”(84)[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美国学者艾凯明确指出,“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政体,则必须也引进西方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国人必须从整体上根本的采用西方文化,改变意欲的基本方向。”(85)[美]艾凯著、王宗昱等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在对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中屋敷宏从陈独秀在《甲寅》发表的文章入手,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中屋敷宏表示,陈独秀认为西方富强、东方积弱的人性基础在于国人的国民性,因此他将“中华民族的品质”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宗旨,“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中国绝对不能和世界列强并肩作战,在国际世界中生存下去”。而“所谓‘中华民族的精神改造’,则是指‘西欧精神改造’”。(86)[日]中屋敷宏:『「五四」新文化運動と陳独秀 :中国近代文学の思想的基礎についての考察』,《文経論叢》,1980,15(1),第210页。
(四)对陈独秀的比较研究
时任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非常勤讲师周程以福泽谕吉与陈独秀为焦点对近代东亚科学启蒙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解读。周程在分析了二者启蒙思想的内容、形成、特点及当代价值后认为,陈独秀坚持“根本的民主主义”,自始至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并最终死在了“民主”与“科学”的大义之下。虽然“两人都提倡国家独立和个人的精神独立”,“但是福泽谕吉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本义,改变了自己”。“与此相反,陈独秀始终没有改变方向,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下进行着思想斗争,贯彻了思想批判的传统思想。”(87)周程:『福澤諭吉と陳独秀 :東アジア近代科学啓蒙思想の黎明』,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第381页。韩国研究院的朴永臻以20世纪初的反儒学运动为中心,对比了陈独秀和鲁迅在这一运动中的思想异同。朴永臻认为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保守传统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二者的不同在于,“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和伦理”,“鲁迅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了对儒学的文学批评”。因此,朴永臻认为相比鲁迅,陈独秀反儒学的立场更为坚定、直接和抽象,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而“鲁迅对儒学的批判则更为具体,对普通大众的影响更为深远”。(88)[韩]Bahk,Yeong-Jin,A Study on the Anti-Confucianism Movement inEarly-Twentieth Century Focus on Chen Duxiu and Lu Xun.Journal of Korean Ethics Studies,2013.Vol.89,p.32.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力将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从二者之间的交流、民主观的异同等方面作了对比研究。在佐佐木力看来,“与只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阶段的吉野相比,陈独秀值得称作为‘终级的民主主义的不断革命者’。”(89)[日]佐佐木力:《吉野作造和陈独秀》,奚金芳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第58页。日本山梨县立大学的平野和彦以陈独秀、梁启超、中村不折、坪内逍遥等为中心,对日中近代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两面性进行了研究。平野和彦对陈独秀和吕澂的“改良”或“改革”的中国传统书画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正如康有为是依据儒家经典一样,陈独秀和吕澂的讨论,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剽窃了欧洲的艺术运动和其相关理论。但是如果不能认识到它这种强烈的两极性,并且超越它的话,就不能认识到,中国传统色彩是不容易被淡化的。”(90)[日]平野和彦:『日中近代における伝統芸術解釈の二面性(上)——「画」と「美術」の認識をめぐって』,山梨県立大学國際政策學部紀要,No.4,2009,第31页。俄国学者罗马诺夫对比了陈独秀和杜亚泉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态度差异。罗马诺夫指出,“杜亚泉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有其独特的特征,它们相互补充,并且应该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寻求协调。他并没有否认借用西方文明成就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反对普遍的西化和完全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陈独秀则不然,主张“有必要彻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91)[俄]А.В.Ломанов,Ду Яцюань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в 191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6,2017 г,pp.106—107;p.110.在罗马诺夫看来,“关于东西方文化讨论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杜亚泉‘叛国罪’的指责,和君主制的恢复计划是‘肤浅的’。”(92)[俄]А.В.Ломанов,Ду Яцюань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в 191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6,2017 г,pp.106—107;p.110.
(五)其它问题研究
国外学术界还有许多有关陈独秀其他问题的研究。如在对陈独秀女性主义思想研究方面,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盖尔·赫什蒂特认为,陈独秀将家庭和习惯上对妇女的束缚看成是阻碍公平和民主国家建设的重要障碍,陈独秀所倡导的“关于妇女和家庭的新文化叙事很快在年轻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而愚昧的、无知的、封闭的受害者只有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政治行动才能解放的女性形象,成为小说写作、论战和新闻报道中的标准形象。”(93)[美]Gail Hershatter,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p.95.美国学者安敏成对陈独秀的文学写作特点进行了研究,对陈独秀文学著作中形容词的运用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安敏成称赞道:“在形容词的跳跃间,陈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勾画出可能的方案”;“陈的措辞中充溢着那个时代年轻革命者的热情,一种崭新的民族同一性也蕴含其中。”(94)[美]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 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美国莱斯大学的赵沈允利用数字化图表软件和编程语言立体化地构建了陈独秀早期的安徽关系网络,分析了早期社会群体或社会网络对陈独秀关系网的重要作用。赵沈允认为,“他们为他(陈独秀)提供了早期组织锻炼、出版和演讲技能的机会。当他走到国家舞台上的时候,他利用安徽的关系网创办了期刊,启动了文化改革。”(95)[美]Anne S.Chao,The Local in the Global:The Strength of Anhui Ties in Chen Duxiu’s Early Social Networks,Twentieth-Century China,1901—1925,Volume 42,No.2,May 2017,p.136.
三、国外陈独秀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一)拓宽研究领域及视角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基本以建党前后及大革命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为主,对于陈独秀早期活动及晚期思想研究较为薄弱。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和全面,覆盖了陈独秀活动早期、中期、晚期的各个时期。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也更为多样。从陈独秀的文学艺术理论到社会关系网络,从宗教伦理到语言文字,从专题研究到交叉研究,可谓是十分新颖齐全。因此,今后国内学者对于陈独秀的相关研究应该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打破现有的自我禁锢,突破传统的集中“热点”,改变传统的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代之以系统的网络联系,从整体上完整地对陈独秀进行把握和研究。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应该积极地借鉴、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摆脱传统视角的拘泥,更新研究观念,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对陈独秀文化、学术等新视角的研究,推动陈独秀研究的立体化、系统化和多样化。
(二)加强史料的挖掘与整理
对于陈独秀及其思想的研究必须不断深挖新史料、整理旧史料,这是对陈独秀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国外学者取得诸多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内学者目前对陈独秀的研究大多依据传统的相关文本资料,甚至二手资料,忽视了对陈独秀相关原始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导致研究成果重复,研究进程缓慢。因此在史料的利用这一方面,国内学者一方面要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料,加强对现有史料的整理研究,强化文本资料的解读剖析。另一方面,要突破空间、地域上限制,加强对新史料的挖掘与发现,缩小学术需求与史料匮乏之间的缺口,推动陈独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互动
之前,由于现有条件及外部环境的限制,国内学者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多是“关起门来”研究,导致国内外学术界的信息闭塞,无法实现国内外学术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在陈独秀及其思想的研究上也产生了诸多分歧。近年来,国内、国际学术环境的逐步开放,国内外学者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国内学者应借此加强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开拓视野,博采众长。在了解国外学者研究动态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积极地让国外学者了解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观点,避免研究成果的片面化、主观化。
(四)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日益改善,国外学者在对陈独秀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不少国外学者由于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其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违背客观事实,存在一些歪曲、丑化或污蔑的内容。对此,国内学者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要提高自我甄别能力,对于不符合“史德”的内容必须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今后对陈独秀的研究应该在深入研究和系统整合文献资料的同时,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联系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辩证发展的历史中去研究。
总之,我们了解和借鉴国外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国内研究视野,丰富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推动陈独秀研究的深化、全面化与系统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亚细亚文库’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1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北抗联国外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5ADJ005)、吉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MYL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