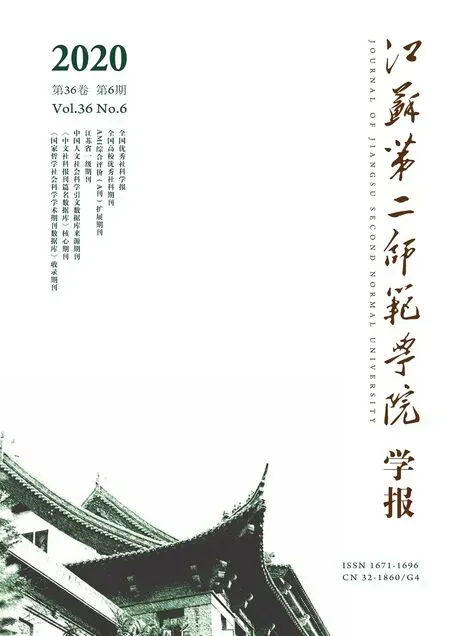从大清律例看《红楼梦》薛蟠案的文本叙事*
庄 怀 芹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在几百人的《红楼梦》人物画廊里,薛蟠并非重要人物。但他的出场和落幕却有些异乎寻常。他凭借一起人命官司被告人的身份登场,看起来心惊肉跳,最终却是风平浪静。结局是他又惹一起人命官司,读者以为他自是安好,谁知竟是百转千回,多方打点,才保住卿卿性命。通过考察,薛蟠两次人命官司的审理和判定基本上都适用大清律例规定和要求,但两次引述法律条文的详略截然不同,值得深入加以分析。
一
薛蟠第一次人命官司在书中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情郎,葫芦僧乱叛葫芦案”[1]56-61,篇幅大概半回,笔墨简洁,省略了具体诉讼审理过程。贾雨村补授应天府,“一下马便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冯渊家下人说自己“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大清律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2]869但若是“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2]869。冯渊家下人在官司发生地告状,没人管,就告到其上级应天府来了,诉求是“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1]56。应天府前任知府估计是知晓这场官司棘手,一直拖着没有正式接案,直到贾雨村上任。贾氏听说该案后大怒,按律按理杀人均需抵命,哪有“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1]56
清朝审理案件规定:“寻常命案统限六个月完结,州县三个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解司,司一个月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咨题。”[3]78根据规定层层转详,直到刑部,上达天听。贾雨村徇情处理,快速结案,跟“护官符”密切相关。据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1]57。薛蟠是薛家之嫡后,王家外甥,贾家姨侄,是“护官符”里牵一动四型的人物。门子对“护官符”作用有清楚认知,他现在亟须将“护官符”的功能传递给新知府贾雨村,让他合理避让“护官符”里的目录人物。门子的话可以看出“护官符”是做官必备指南,在当时非常流行,是地方官员和地方权贵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护官符”对地方官员如何做官以及处理事务有极大的指引作用,地方官行为的避让又强化了“护官符”的威力。
地方官做官要自保,“护官符”里的权贵不能得罪,为政一方又不能完全不顾为官声誉,所以只能搞些权术愚弄百姓。门子建议贾雨村让薛家族人以及地方官出具薛蟠暴病身亡保呈(相当于今天的死亡证明),以此瞒天过海,诈死脱身。“斗殴及故杀人第三条”规定:“凡审共殴下手应拟绞抵人犯,果于未结之前,遇有原谋及助殴伤重之人监毙在狱,与解审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若系配发事结之后在家病亡者,不得滥准抵偿,仍将下手之人依律拟抵。”[2]795“诈病死伤避事第二条”又规定:“凡未经到案之犯报称病故,该抚严饬地方官悉心确查,取具甘结报部。倘有捏报等情,日后发觉,将该地方官与该抚一并严加议处。”[2]948上述条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案件审判期间,犯罪嫌疑人突然病故的,允许以此抵命,也就说官司可以随着犯罪嫌疑人的病故而自然了结,但须出具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的保呈(死亡证明)。“保呈”的内容大体上要写明薛蟠因何事犯案应判何罪,在未定案之前,因何病何时而身死,然后再由薛蟠族人和当地官员签名确认情况属实。其中得何种病显然是保呈的关键内容。然而小说中薛蟠得的却是“无名之症”,保呈信度可见一斑。在此,脂砚斋点评说,“无名之症确是病之名,而反曰无,妙极!”贾雨村就是利用这个律例条款让薛蟠人命官司快速结案的。虽然《大清律例》也明确规定捏造事实,帮助犯人诈死脱罪,相关官员要受到严处。但贾雨村“朝中有人”,案件一了,便急忙向“朝中人”贾政、王子滕表忠心邀功去了。案件到此应该算圆满结束了。但在小说中,结案后贾雨村还有一个动作值得深思,那就是他把门子充军发配了。“官吏受财第三条”规定:凡衙门蠹役,恐吓勒索,十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2]908。“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衙门蠹役都是专门敛财高手,十两实在微不足道,贾雨村是随意“寻了不是”,都不需要证据确凿,就轻易地打发了门子。脂砚斋点评,“瞧他写语村如此”,贾雨村的形象塑造在薛蟠第一次人命官司基本成型。
二
薛蟠第二次人命官司是从第八十五回开始,断断续续,绵延到第一百二十回,历时弥久。第九十九回,贾政任江西粮道时,在省里邸报上看到的刑部题本贴黄[1]1365-1366,是对这次官司曲折反复过程的全面概述。
花朝节(二月初二),贾政升郎中庆贺之日,筵宴繁华,高兴欢闹之中,薛蟠祸事犹如晴天霹雳,打散了欢喜氛围。薛姨妈战战兢兢,和宝钗只是哭,薛家下人建议:“打点银两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许他些银子,先把死罪撕掳开,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1]1202。薛姨妈派薛蝌立即起身去太平县打点,过了两日薛蝌就寄回第一封信[1]1203。这封信的信息量很大,但是信息具体内容却含糊不清:薛蟠要翻供,怎么翻供没交代;薛蝌写了呈文,写了什么不知道;钱花在哪里也没说,但要再来五百两急用;馀什么事问小厮,也不清楚。但薛姨妈得了信后,就亲自去找王夫人,再找贾政说情,贾政含糊应了,说等薛蝌递了呈子看知县回复。
第八十六回薛蝌送回第二封信[1]1206-1207,第一封信内容不明的四个问题都得到了补充。在这封信里薛蝌说翻供方法和操作流程是他请的好先生帮忙策划的,详情在薛蝌第二次呈文的呈底上。这个呈底不仅补充了薛蟠翻供的具体内容,推动薛蟠命案审理过程的进行;也与前文贾政说要视薛蝌呈文后批复情况再去托人的说法呼应。呈底后批文进一步补充前面没厘清的薛蟠人命官司真实情况,回答了前文薛姨妈疑问“到底是和谁?”以及薛蝌第一封信里小厮没说清的“馀事”。
太平县知县批文基本认定薛蟠“自认斗杀”,“证据确凿”,明确表态“不准”。这并非故意吓唬薛家人,从下文重审翻供言辞中发现先前太平县知县给薛蟠量刑完全符合大清律例规定这一点即可看出。“保辜限期第一条”:凡京城内外及各省州县,遇有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或俱控到官,或经拿获及巡役、地保人等指报,该管官即行带领仵作追亲往验看,讯取确供,定限保辜。不许扛抬赴验,如有违例抬验者,将违例抬验之亲属与不行阻止之地保,各照违令律笞五十。因抬验而致伤生者,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倘内外该管衙门遇有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仍令扛抬听候验看者,各该上司察实指参,交部议处[2]822。但太平县知县仍然允许薛蟠翻供,是因为薛蝌第二封信送来的同时,还带了县里口信,说“须得在京里谋得一份大情,再送一份大礼,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1]1207。薛姨妈得知后,又立即又找了王夫人托贾政去跟知县说情,还找了王熙凤托贾琏给太平县知县送了几千两银子。这为后文太平县知县被革职查办埋下伏笔。“官司出入人罪第一条”规定:承审官改造口供故行出入者,革职[2]1070。翻供以后,薛蟠犯罪情节从先前的“自认斗杀”变成了“过失杀人”,斗杀量刑是“绞监候”,而“过失杀人”的绞罪可以收赎。关于斗殴杀人,大清律例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余人(不曾下手致命,又非原谋者)各杖一百[2]794;凡审理命案,一人独殴人致死,无论致命不致命,皆拟抵偿[2]795。若过失杀伤人者,(较戏杀愈轻)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2]800,收赎过失杀人绞罪,与被杀之家营葬,折银十二两四钱二分[2]801。又规定:应该偿命罪囚,遇蒙赦宥,俱追银二十两,给付被杀家属[2]800。
过失杀人情节认定的关键在于要排除意图和行为上的主观故意。“过失,谓耳口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如弹射禽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驾船使风、乘马惊走,驰车下坡,势不能止,或共举重物力不能制损及同举物者,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2]800。薛蟠翻供后的具体供词,刑部题本贴黄有明确摘录,说“行过太平县,李家店歇宿,与店内当槽之张三素不相认”,这是排除主观意图的故杀;“因酒不甘,薛蟠令换好酒。张三称酒已沽定难定。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不期去势甚猛,恰值张三低头拾,一时失手,将酒碗掷在张三囟门,皮破血出,逾时殒命”,这在表明客观上“势不能止”。虽然薛蟠翻供成功,但是过失杀人罪的认定才刚刚开始。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徒罪以上通详,杖枷等罪均听州县发落[4]卷七。可见,地方量刑定罪的权力很小,大多是提供量刑定罪的建议。所谓通详指徒刑罪以上的罪须从地方上报其所有上级部门,若命案在县级发生须详文上报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道(道员)、宪(知州、知府)。“多一重衙门,便多一重费用”[4]卷七,“且详之其行与否,均关有司体面。故事,非不得已,亦不可轻易动详”[5]4019,当事人和有司一般不会轻率选择通详。这里是使用常规详文上报,从县—州—府—道—刑部—皇帝。此后薛蝌便差人送第三封信回家,说“等批详回来,便好打点赎罪,且住着等信”[1]1209。因为讹传贾贵妃薨,薛蝌返回都中。
直到第九十一回,薛蟠寄信回来,说,“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反驳下来。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饬。现在道里要亲提,若一上去,又吃苦。必是道里没有托到。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火速,火速”[1]1265-1266。薛蟠信来,宝钗急得病倒,薛蝌立返太平县,不久寄回第四封信,但小说对薛蝌第四封信内容完全没有交代,猜测这封信内容应与薛蟠信内容大体相符。薛姨妈收了信又找王夫人,已是第三次找王夫人托贾政。贾政说:“此事上头可托,底下难托,必须打点”[1]1267。贾政的说法和第九十九回他看了刑部题本贴黄后的状态是矛盾的。文中说他不放心,他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担心革审起来牵连自己,表明贾政只托了县里。但刑部题本贴黄和薛蟠来信都明确表示州里府里都批了太平县对薛蟠的量刑定罪建议。州里府里的情是托谁呢?除贾政外,薛家可托之人还有王子滕和贾赦。第四回交代王子滕在薛蟠将入都时,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第九十五回王夫人听说哥哥王子滕升内阁大学士,奉旨回京,欢喜非常,因为薛姨妈衰败了,王子滕外任,照应不着,这次回来又有了依靠。王子滕在外,对薛蟠这次官司是鞭长莫及。排除贾政和王子滕后,受薛姨妈之托去讲情的可能就是贾赦。一般贾赦有事须打点,基本上都是委派贾琏出面处理。第八十六回,薛姨妈托了贾政后,恐不中用,又托凤姐与贾琏说了。第九十九回李十和贾政讲到薛蟠官司时说,“不但托了知县,还求琏二爷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不知怎么部里没弄明白”[1]1367。第一百○五回贾赦被弹劾的一款罪状就是“包揽词讼”。在薛蟠案中,贾琏应是打点县、州、府、道各层级。李十打听到的信息说刑部不领情,出了问题。
实际上细阅刑部题本引述的京营节度使咨文会发现真正出问题的环节是在京营节度使,也就是在都中,不在地方,也不在刑部。京营节度使咨文说,“前署县诣验,仵作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详府审转”。京营节度使之所以能看出张三尸格改轻,主要是因为前后供词不一致。“凡初次供招,不许擅自删改。俱应详载揭帖。……倘遇有意义不明、序次不顺,与情罪并无干碍,即就近核正申转,将改本备案,不得发换销毁。违者,依改造口供故行出入例议处。”[2]1071这里的揭帖相当于今天的附件,供词是重要案情材料,在详文转申时须作为附件一起转送,不管是更改前的还是更改后的都须附录。前后对比,京营节度使向刑部明确指出薛蟠案问题之关键所在。刑部官员也就发现了同样问题,“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着张三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门深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其中“该”是对下级机关的称呼,“今据该节度疏称”,是对下级机关文书的引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节度”和“京营节度使”不是同一个机关长官,京营节度使应是京都最高军政长官,“该节度”是地方军政长官。刑部引述京营节度使文书时用“咨称”,它们之间用平行文“咨”;引述地方节度文书说“该节度疏称”,“该”是引用下级机关来文的惯用语。大体情况应是太平县所在的地方道节度将薛蟠案上报刑部的同时,也上报了京营节度使,京营节度使得知案情后,行咨文给刑部专门来干涉。贾琏应是将太平县及其所在的州、府、道都打点了,没有想到京营节度使会出面插手该事。薛蟠第一次犯案时,舅舅王子滕任京营节度使一职,权势重,随便花几个钱就了事了。这次京营节度使却专门来揭发薛蟠捏供,基本可以断定现任京营节度使和前任京营节度使王子滕是政敌,互不对付,所以才会横加干涉此事。刑部得到京营节度使咨文后,驳回太平县量刑建议,要求其重新审定事实。这个情节薛蟠信中也有描述,说“道里反驳下来”,“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但“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饬”。刑部题本的最终结果是薛蟠仍旧被定为斗殴故杀人罪,被判绞监候,帮助薛蟠故意捏造供词的太平县知县被革职。
三
从以上两起官司的审理过程和判定依据来看,不难发现小说对薛蟠两起案件的审理是完全符合大清律例相关条款规定的。但第一起官司审理过程叙述相当简略,篇幅很短,全部事件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大约占半回,这半回文字又大多在描述门子出示“护官符”的场景及其连锁反应,正面叙述案件的文字非常少,对条款依据使用并不显著。关于这次判案,甲戌本有两处很有深意的批语:一处是关于贾雨村点评冯渊和英莲的一段,眉批曰:“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省中实也。”[6]155所谓的“繁中虚”可以理解为愈加枝蔓的故事愈不能面面俱到,而是大量留白。所谓“省中实”指的是虽然故事呈现得非常简略,但是确实符合事实上的情理和真实。掌握事件梗概后,在留白的空间内,根据事实,读者可以进行自觉联想补充。另一处是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侧批曰:“实注一笔,更好。不过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细写。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盖作者立意写闺阁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6]156“如此等事,又何用细写”的意思是说不用特意写明,意思自然明了;而不是说不写,读者就不知道。“莫谓写之不到”实际上已经写到,因为“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又“将真事隐去”。这似乎曹雪芹一直要表达的思想相一致,因为他在《红楼梦》多次强调自己创作的《红楼梦》是“闺阁昭传”“假语村言”“敷衍荒唐”,“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是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希望各位看官不要像空空道人那样“寻根究底”,但是又说“真而不真,假而不假”,“假做真是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王希廉说,“《红楼梦》一书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需知真即是真,假即是真,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要明此数意,知作者匠心”[6]537。“假语存”可能只是一种不得而为之的表象,“真事隐”才是其真实内核。这种强调是否意味着规避该书面世的一些现实压力或不得已的苦衷,特别是要“掩护作品所赋有的尖锐的指斥、针刺的性质”[7]560。脂砚斋说曹雪芹避嫌,不干涉朝廷,“但不能说它(指《红楼梦》)没有自己的倾向,不能说它没有概括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不能说它缺乏历史性的内容”[7]560。总体而言,薛蟠第一次官司对《大清律例》的适用非常隐晦,除了少数文体名称之外,很少出现大片司法专门用语。
薛蟠第二次人命官司在《红楼梦》第八十五回到第一百二十回。薛蟠第二次人命官司写法比较张扬,不怎么含蓄,对官司叙述基本都是正面叙事,直接描写交代案情状况,显著的集中叙述有:第八十六回薛蟠在太平县府衙翻供时,各方对案件事实细节的重现;第八十五回、第八十六回、第九十一回薛蝌薛蟠两人给薛姨妈信件,对案件审理过程的跟进;第九十九回刑部题本所体现的清代司法系统对薛蟠量刑建议的认定及最终审判。这次官司的语言表述中出现了大量的清代司法专用词语,甚至出现了篇章式的司法文书文稿内容。这种写法与第一次大不相同,甚至在对薛蟠量刑定罪时,明目张胆地直接引用刑部题本贴黄,直接表明判定薛蟠“绞监候”是依据《刑律》之“斗殴及故杀人”条款,说,“臣等细阅各犯证尸亲前后供词不符,且查《斗杀律》注云‘相争为斗,相打为殴。必实无争斗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过失杀定拟。’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着张三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门深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是张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宛砸伤深重致死,自应以薛蟠拟抵。将薛蟠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吴良拟以杖徒。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1]1366
薛蟠两次打死人,事实既定,证据确凿,按规定理应抵命,造成薛蟠案件审理曲折的原因,小说第八十回中有明确表述:“谁还不知道你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1]1132。这是夏金桂跟薛蟠吵架时说的话。这句话对薛蟠打死冯渊案进行了准确概括,也为下文再打死张三进行伏笔。这个意思在薛蟠第二次人命官司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如第八十五回薛蟠打死张三事情刚传回薛家时,薛姨妈惊慌失措,薛家下人出主意说:“打点银两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许他些银子,先把死罪撕掳开,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1]1202夏金桂嚷道:“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一点事也没有,就进京来了,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这时我看着也唬得慌手慌脚的了”[1]1202。第八十六回薛蝌第二次寄信回家,下人带了县里口信,说“须得在京里谋得一份大情,再送一份大礼,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1]1207。第九十一回薛姨妈庆幸“亏得家里有钱,贾府出力,方才有了指望”[1〗1264。一日薛蟠又写信说:“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火速,火速”[1]1266。第九十七回王夫人和薛姨妈说,“一面这里过门,一面给他变法儿撕掳官事”[1]1334,薛蝌回复薛姨妈说,“一过堂就题本了,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1]1335。第九十九回李十对贾政说,“奴才听见不但是托了知县,还求琏二爷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1]1367。第一百回宝钗劝薛姨妈说,“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尽心的了,花了银钱不算,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1]1369。前面百转千折,在第一百回,薛蟠打杀张三案有了最终审判结果,“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薛蟠依旧被定死罪并不能说明当时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薛家所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在干扰司法系统的审判工作,薛蟠被判罪的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严明的结果,而是现任京营节度使横加干涉的结果。
复有可说者,薛蟠第二次人命官司的情节叙事中使用了大量清朝司法审判专用名词以及篇幅型司法文书文本,对条款的适用十分具体、频繁,对薛家用花钱和托人来干扰审判结果进行反复描述。这些是不是可以为后四十回作者不是曹雪芹的成说提供一点点线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