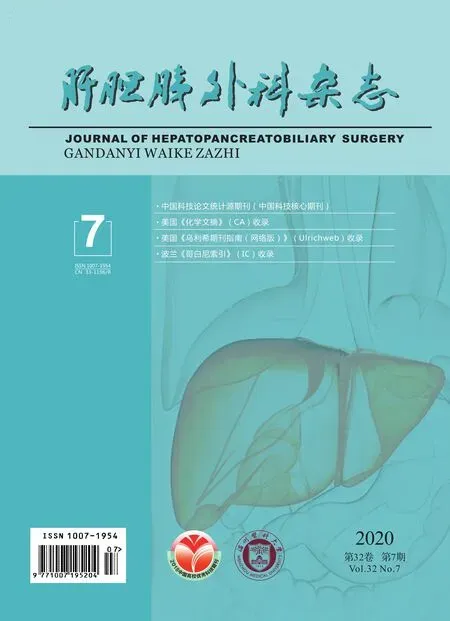晚期不可切除肝癌降期治疗的研究进展
马志坚,焦作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普外一科,甘肃 兰州 730000)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居第六位和第四位,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1-2]。据2018年统计,全世界有85万肝癌新发病例和78万死亡病例,新发病例中,我国占了46.71%[3-4]。近年来,随着乙肝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普及,肝癌的发病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依然是我国病死率排名前三的恶性肿瘤。肝癌是一种侵袭性肿瘤,常继发于慢性肝病和肝硬化,但由于发病隐匿且无特殊临床症状,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处于病程晚期,中位生存期约为6~20个月[5]。尽管根治性肝切除术是肝癌的最佳治疗方法,但多数患者由于肿瘤巨大、肝内外多发转移、肝内肿瘤的解剖限制或肝功能较差等原因,而失去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能获得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不足20%[6]。此外,根治性切除术后,局部复发率仍然很高,故如何将不可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转变为可以手术切除,提高肝癌患者预后,是近年临床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就近年来有关不可切除肝癌降期治疗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肝脏的血供主要来源于肝动脉和门静脉,正常肝脏由门静脉提供75%的血供,而肝细胞恶性肿瘤主要由肝动脉供血。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法(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通过破坏肿瘤血供从而诱导肿瘤缺血,同时化疗药物被直接通过肿瘤血管注入肿瘤组织,形成肿瘤局部高浓度化疗药物环境,起到抑制肿瘤的效果,已成功应用于治疗不可切除和复发性肝癌。Llovet等[7]与Lo等[8]进行的两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结果表明,TACE对于不可切除的肝癌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生存获益,且效果显著优于单纯经动脉栓塞,可提供潜在手术切除机会而达到降期治疗的目的。而对于临近大血管或血管丰富的肝癌,高飞等[9]的研究表明,使用TACE联合经皮射频消融(radio frequency ablation,RFA)比单独使用TACE和RFA,可显著提高肿瘤完全坏死率,延长患者生存期。但由于TACE可导致肝脏失代偿,良好的功能性肝储备是TACE治疗的前提[10]。因此TACE最常用于治疗不适合手术切除、无周围血管侵犯及肝外转移且肝功能尚可(Child-Pugh A或B级)的肝癌患者,且通过与RFA的联合治疗也可以提高TACE治疗效果,使一部分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在序贯治疗过程中获得手术机会。此外,TACE也常作为“过渡疗法”被应用在肝移植手术之前。尽管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中未做明显推荐,但目前大多国际指南都推荐TACE对无法切除肝癌进行降期治疗[11-13]。
2 选择性门静脉栓塞
术前门静脉栓塞(portal vein embolization,PVE)是肝切除术前很有价值的辅助治疗手段,尤其对于肝右叶肿瘤。PVE可以促使残肝体积增大,给手术提供潜在的扩大切除范围。Abulkhir等[13]通过Meta分析评估了肝癌患者行PVE的临床获益,该Meta纳入37篇PVE系列研究,共计纳入1 088例患者(265例肝癌,其余为胆管癌或继发性肝转移),PVE治疗4周后患者肝脏体积总体增加10%~12%,其中85%的患者如期进行了肝部分切除术,有效防止了因残肝不足而导致的肝衰竭的发生。另一项回顾性研究进一步展示了术前行PVE的临床获益,该研究比较了接受PVE(n=21)和不接受PVE(n=33)的肝癌患者在肝部分切除术的临床结局[14]。在PVE组中,PVE前后标准化剩余残肝体积(FLR)的中位数分别为23%和34%,行PVE患者的并发症较少(10%vs36%),且90 d病死率为0(而无PVE组为18%)。另外,TACE也被推荐作为肝癌患者行PVE之前的补充治疗方案[15-17]。TACE可阻断肿瘤的动脉血供并栓塞潜在的动脉门静脉分流,因此也可减弱PVE在肝硬化肝脏中的不利影响[16,18]。在肝切除术前联合TACE和PVE治疗,可提高手术安全性,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这也引起了对肝硬化患者肝右叶切除术前治疗顺序的进一步关注。而对于较大的肝脏肿瘤,如果直接切除会使剩余肝脏体积不足,导致严重的术后肝衰竭,因此可先采用PVE促进剩余肝脏增生然后再切除肿瘤的二步肝切除术,从而极大地改善这部分患者的预后。
3 经肝动脉放疗栓塞
经肝动脉放疗栓塞(transarterial radioembolization,TARE)是将载有发射β射线的钇-90(90Y)玻璃微球选择性地注射到肝动脉,放射性微球因无法通过肿瘤的毛细血管床而聚集在肿瘤组织,其发出的射线对靶肿瘤具有细胞毒性作用。射线在肝组织内的穿透能力只有2.5 mm,在杀伤肿瘤的同时对正常肝脏组织的损伤较小[19]。然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其对生存的影响,国际上就该疗法的最佳应用方案也未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治疗无法切除肝癌患者时应选择TARE还是TACE方案。Salem等[20]开展的一项小型随机II期临床试验表明,相比于TACE,TARE与更长的肿瘤进展时间相关,但治疗反应率和存活率无明显差异。多篇文献已证实使用90Y标记的玻璃(TheraSphere)或树脂(SIR-Spheres)微球进行TARE对于无法切除肝癌患者(包括门静脉血栓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1-23]。Salem等[20]使用TheraSpheres治疗291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试验证明了90Y TARE的长期疗效,其中位随访时间为31个月,中位进展时间为7.9个月,且二维测量肿块的垂直径线(WHO评判标准)结果显示,TARE后42%的患者肿瘤负荷减小;而增强CT(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23]标准)结果显示,TARE后57%患者的肿瘤缩小[24]。TARE的主要的临床毒性反应是恶心、腹痛、疲劳和短暂的高胆红素血症,但其对于门静脉癌栓的治疗具有显著作用。因门静脉癌栓对放疗较为敏感,癌栓内的癌细胞可被射线迅速杀灭,即使术中癌栓内癌细胞脱落到正常肝脏,由于癌细胞活性降低,难以增殖存活。因此,TARE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局部治疗,毒性作用相对较小,并且更加适合于肿瘤负荷较高的患者。然而,其昂贵的费用以及肿瘤位置的的解剖学限制也降低了这种治疗方法的实用性。
4 射频消融术
经皮肝穿刺肿瘤局部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被认为是治疗肝脏恶性肿瘤的一种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法。目前对于可切除肝癌患者,射频消融术相对于直接手术切除的临床获益仍存在争议[25]。Maeda等[26]的研究显示,RFA治疗肝癌后,其病死率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0.038%和3.540%,且相较于手术切除,RFA在降低患者病死率方面并无明显优势,但可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彭莉晴等[27]进行了一项RCT实验,将165例肝癌患者分为保守治疗组(52例)、手术组(55例,60个病灶)和射频消融组(58例,64个病灶),治疗3个月后发现手术组与RFA组的有效率无差异,但明显高于保守治疗组,且治疗后肝功能、AFP、CEA均明显改善。因此,对于肿瘤直径小于5 cm的肝癌患者,RFA不仅可以取得与手术治疗相当的治疗效果,也可一定程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可作为治疗原发性和转移性肝癌的一种安全、有效且低成本的治疗手段。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通过对189例肿瘤直径小于7 cm的肝癌患者接受RFA或RFA联合TACE(使用卡铂、丝裂霉素与脂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联合治疗可以显著改善4年生存率(62%vs45%)和无病生存率(55%vs39%),且没有发生治疗相关死亡[28]。目前,TACE和RFA常作为序贯治疗方案应用于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降期治疗。TACE和RFA联合应用可以克服单独应用时的限制。两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TACE联合RFA较单独RFA或单独TACE相比,患者存活率更高[29-30]。因此,对于肿瘤直径较大,无法进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TACE联合RFA可作为其治疗的有效手段之一。
5 经皮无水乙醇或乙酸消融术
经皮无水乙醇消融术(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PEI)是将浓度95%乙醇直接注入肿瘤,诱导局部凝固性坏死和纤维化反应,导致肿瘤微血管血栓形成,使癌组织发生缺血、失活。多项研究表明,PEI可显著改善小肝癌患者的长期预后[31-35],肿瘤小于3 cm患者经PEI治疗后5年生存率由40%提高至54%,而肿瘤3~5 cm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32%提高至37%[33]。Pompili等人[32]对4 037例接受PEI治疗的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单发且直径<2 cm 肝癌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54%,而肿瘤直径2~5 cm的则为39%。据报道,Child-Pugh A级肝硬化合并单发且肿瘤≤2 cm的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高达78%[34];相比之下,直径5~10 cm的单发肝癌 3年生存率仅为42%[36],而潜在肝功能不全患者的长期疗效更差[32-33]。Okuda[37]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在纳入的125例肝癌患者经PEI治疗后,Child-Pugh A级肝硬化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44.5%,而Child-Pugh B级和C级的肝硬化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34.3%和8.1%。此外,经皮注射乙酸效果与乙醇相似,但副作用相对较小[38-39],Weis等[40]比较了经皮注射乙酸与无水乙醇的临床获益,但不足以说明两种方法的相对益处和危害。Majumdar等[41]通过Meta分析认为,与RFA相比,经皮乙酸注射与达到最大随访时间时的病死率显著相关(HR1.77,95%CI1.12~2.79)。
6 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
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是术前PVE的替代疗法[42-46]。此方案会使患者手术风险增加,并且ALPPS的手术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仍然较高,因此应对患者肿瘤分期及全身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谨慎选择。目前支持ALPPS的数据并不多,并且术前PVE仍然是FLR不足患者的首选方案[42]。与PVE相比,ALPPS可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正常肝体积快速增加。一部分接受ALPPS的患者的平均肝脏体积增大率为85%,而其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35%和6%[44]。Schadde等[43]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ALPPS与PVE/PVL的结果,ALPPS组中的更多患者实现了降期治疗并完成肝部分切除术(83%vs66%),且ALPPS组肝脏生长速度提高11倍(34.8 mL/dvs3.0 mL/d),1年内肿瘤复发率无明显差异(54%vs52%)。
7 分子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是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在肿瘤中特异性表达的分子靶点而设计的抗肿瘤药物,药物进入体内会特异性的与靶点结合,使肿瘤细胞的生命活动无法进行而发生程序性死亡。多项研究表明,肝癌组织中VEGF受体(VEGFR)、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DGFR)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等相较于癌旁组织呈高表达,一些信号转导通路如络氨酸激酶受体下游的主要信号通路Ras/Raf/Med/ERK、P13K/Akt/mTOR也均在肝癌中呈高表达,与肝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是分子靶向治疗的分子基础[47]。索拉非尼是近十年以来FDA唯一批准的全身治疗晚期肝癌的药物,其通过抑制肿瘤细胞表面的络氨酸激酶信号通路,同时使原癌基因flt-3、c-kit和细胞内丝/苏氨酸激酶表达降低,进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心血管生成[48]。在第三期索拉非尼肝癌评估随机方案(Sorafenib HCC assessment randomized protocol,SHARP)[49]实验结果表明,索拉非尼可有效提高晚期肝癌患者3~5个月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子靶向治疗具有高度的特异性,疗效显著且对正常组织损伤较小的特点。仑伐替尼作为第二个被批准用于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药物,其III期临床研究—REFLECT结果表明仑伐替尼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且在亚太地区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优于索拉非尼[50]。瑞戈替尼和卡博替尼被用作是晚期肝癌患者索拉非尼治疗失败后的二线用药,相较于索拉非尼可有效提高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51-52]。分子靶向治疗具有迅速、高效且不良反应小的特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作为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但晚期患者对于分子靶向治疗的总体应答率较低,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特异性分子靶点或者通过联合用药提高其应答率是目前分子靶向治疗的难点所在。
8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癌症治疗手段,其主要通过诱导或增强现有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来选择性地靶向肿瘤细胞,打破免疫耐受,以达到延缓肿瘤进展,延长肿瘤患者预后的目的。从而发挥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目前,肝癌的免疫治疗主要包括过继免疫细胞(adoptive cell transfer therapy,ACT)治疗、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和肿瘤疫苗治疗。ACT治疗是通过收集患者外周血中的免疫效应细胞进行体外培养,使之具有抗肿瘤活性,后回输到患者体内从而发挥肿瘤杀伤作用。Katz等[53]的研究表明,使用抗CEA-CAR-T细胞治疗肝转移癌后,患者肝组织活检发现转移灶有明显坏死或纤维化,且患者血清中CEA水平均明显下降,其抗肿瘤效果显著。树突状细胞疫苗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肿瘤疫苗[54],Palmer等[55]进行的肝癌树突状细胞疫苗II期实验结果显示,患者在使用树突状细胞疫苗后,体内的IFN-γ水平升高,AFP水平下降,生存期较对照组延长且复发率显著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通过阻断T细胞活化第二信号的传导来加强免疫反应,程序性死亡1因子(PD-1)及其配体PD-L1的相互作用是肿瘤微环境中重要的免疫检查点和免疫抑制的主要机制[56]。研究表明PD-L1的过表达与肝癌患者的肿瘤侵袭性和术后复发相关[57]。卡瑞利珠单抗作为首个中国自主开发的PD-1抑制剂,也是唯一一个目前被获批用于肝癌治疗的PD-1/PD-L1类抑制剂。在一项多中心二期随机试验中[58],217例肝癌患者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其中位随访时间为12.5个月,总体客观缓解率为13.8%,6个月总生存率为74.4%。此外,卡瑞利珠单抗与传统的PD-1药物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相比,其治疗效果相似,但副反应更小,价格相对较低,且受试对象多为亚洲人群,因此有望成为国内肝癌患者的有效治疗药物之一。
9 总结与展望
晚期肝癌的降期治疗,指通过局部、全身或综合治疗,将晚期肝癌转变为较为早期的肝癌,使得一部分肝癌由不可切除变为可切除。肝癌降期治疗的目的是使肝内外部分肿瘤、静脉癌栓缩小消失或者使未受侵犯肝脏代偿性增大。目前,临床上对于晚期肝癌患者使用介入治疗联合分子靶向治疗可取得较为显著的治疗效果。而对于大肝癌有时候完整切除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同时也可先进行介入治疗,使肝癌肿块缩小,然后再进行手术切除防止其复发,从而提高巨块型肝癌的术后总生存率。此外,通过降期治疗观察肿瘤生物学特性,从而判断是否适合手术切除而不引起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降期治疗最值得被关注的特点。虽然肝癌降期切除给不能手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带来希望,但目前仅有11%的患者能达到降期切除的目的[59],而且肝癌降期治疗方案在临床应用中尚存争议,比如肝癌巨大且不能切除的标准、降期后再予以手术切除的指征等问题尚有待于临床进一步实践与探讨。目前仍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以明确各个治疗手段单用或联合使用对于具体类型、具体阶段肝癌的治疗效果,从而优化肝癌降期方案,进一步提升降期后手术切除率,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