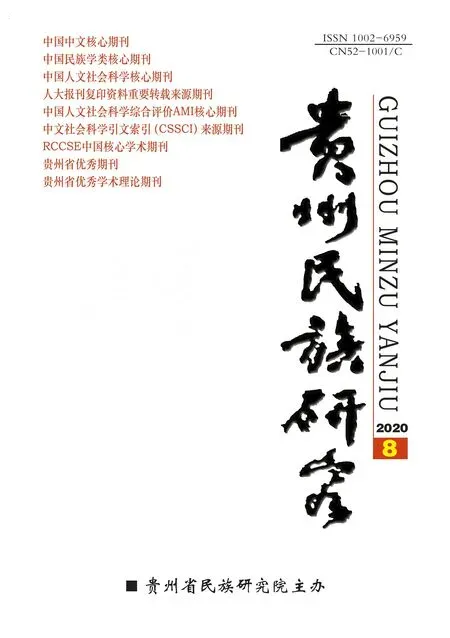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的瘟疫恐慌与应对演变研究
崔 阳 沙丽娜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瘟疫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由来已久,危害甚巨。故遍布于世界各地的族群都围绕其形成了相应的认知观念和防御策略,或退避三舍,或欲除之而后快。然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人类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今之瘟疫已演变成了一个“亿众瞩目”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在发轫于西方的科学语境下,当今世界对“瘟疫”的主流认知是一种“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并将其病源归结为由各种微生物、寄生虫等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1]。中国古代医学关于传染病学说的观点大致有时气说、瘴气说两种。“所谓时气,即非其时而有其气,古人谓之四时不正之气。瘴气说,即认为尸体腐烂或其他一些山岚瘴气等,弥漫在空气中,人在吸入这些恶毒之气后,便会导致疫病的发生。”[2]
查阅史乘,各跨境民族聚居的中缅北界地区常被表述为“疫疠横行”之地。“潞江边,阻瘴烟”“疫疠时行,死亡甚众”等词语不绝于书。19世纪末曾探险游历于怒江峡谷的法国亨利·奥尔良王子也发出了“中国人说萨尔温江谷地是瘴疠之地,这个恶名大概不是无中生有”[3]的感慨。从纬度分布上看,该地区属亚热带,河谷地方气候炎热。全年雨量丰沛,春夏季易发生洪涝、滑坡等自然灾害。全域处于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的群峰环峙之中,故又于亚热带的大气候中形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局地气候。独特的地貌和气候条件创造了种类纷繁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并为生活在其地的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使其可以通过采集、狩猎等非农耕手段更高效地获取食物,但也应看到,缩短食物链的努力势必将伴随着时常感染疾息的高昂代价[4]。
人类在怒江峡谷的活动踪迹可溯及新石器时代。长时间以来,怒族、独龙族、景颇族、傈僳族、白族支系勒墨人等跨境民族咸集于此,即便是稍晚徙居而来的傈僳族和白族支系勒墨人,也至少有四百年以上的怒江生活史。诸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在生态环境、生活起居、宗教信仰等方面业已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性认知,并表现为文化观念上的相互濡染和趋同。《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中说:“上帕夷民,虽分三种,而性质则互相传变,习染成风。”[5]在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的区域性认知中,当然也包括构成其苦难社会记忆的“瘟疫”。不同于其他学科对瘟疫的研究,人类学则将之视为一种人类社会处于危急情境下的文化现象,旨在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得基于研究对象立场上的主位视角,并进而理解和阐释其围绕“瘟疫”所形成的观念体系和藉此而做出的因应策略。本文正是遵此思路下的一种研究尝试,笔者将以基督教信仰的传入为分水岭,分别探讨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究竟是何种观念体系构成了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对瘟疫的区域性认知,以及由此观念产生出的应对方式,并进一步讨论其“瘟疫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情况。
二、前基督教时代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之瘟疫观、瘟疫恐慌的历史回顾
在源自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传入之前,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皆笃信以“万物有灵”(Animism)为核心观念的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观”亦称“泛灵崇拜”,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 (1871年) 率先提出。在其理论表述中,“人是具有灵魂的人”无疑是该观念体系的基石,也是人类诸宗教信仰得以发端和存在的核心内容。“万物有灵观”认为灵魂和生命共同构成了人类本身,二者同身体有着密切联系:“生命给予它感觉、思想和活动的能力,而幽灵则构成了它的形象。由此看来,两者跟肉体是可以分离的:生命可以离开它出走而使它失去感觉或死亡,幽灵则向人表明远离肉体。”[6]所谓“灵魂”是指附着于肉体之上,却又摸不着,看不见的“气”,可类比人类呼吸活动中的气体交换。它是个体生命和思想的源泉;能独立地支配着肉体所有者过去和现在的意志;也能离开肉体从一个地方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6](P351)。当人类把“灵魂”这一概念投射和泛化到自身以外世界的时候,万物有灵的观念就产生了。那些有“生命力”的物质自不必说,就连没有生命特征的自然事物和人造物也被视为“属灵”的存在。于是,物质世界变成了人性化的精灵世界[7]。
上述关于灵魂的表述被泰勒认为是“万物有灵观”最主要的信条之一,它在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也能获得相当的证实,并因民族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怒族人相信不论生死,人都有灵魂,且拥有灵魂的数量视性别而定,“男人有九个灵魂,女人则有七个灵魂。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不同的时候可以看见人不同的身影,这些身影便是人不同灵魂的体现。故怒族忌别人踩踏自己的身影”[8]。人之灵魂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不依赖于肉身出游。当其离开人体又呼唤不归时,这个人要么死去,要么徒有奄奄一息的躯体。独龙族也相信灵魂是包括人在内诸事物活动的动力和主宰[7](P105),并认为人死后灵魂有“息托” (变人的鬼、人类的祖先) 及“排勒”(家鬼、祖先的鬼) 两种[9]。傈僳族中也有与“灵魂”相对应的词汇——尼(Ne),他们信人死后,及山石水树均有尼,“人死后之鬼,颇像汉人的鬼、精、妖等的有恶化的人形,而山石树泉之灵,则并不具有任何形象,它是看不见,但是觉得着的。它同时必需有一个实物在那做介物,才能发生。这种‘灵’不是那个实物(如石,树,水)自己,好像是他的生机力(Vital Power or Seelenstoff)。此生机力可以脱离物体而存在,但必有其物,始能发生作用做出事故”[10]。
由上可知,若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民众将周遭世界皆视为有灵存在的话,那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疾病”与“瘟疫”这一人类社会的普同现象呢?这就要提及“万物有灵观”的第二要义:即“神灵”的力量应足以影响或控制自然万物的运转,以及人的生死存亡。神灵与人亦能交互感知。人在世间的言行暴露于神灵的注目之下并可激起其喜悦或愤怒的反应。于是就导致出现了对神灵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并集中表现为对祈求神灵赐福的期许和祈祷神灵免除灾祸的哀求[6](P349-350)。
对于虔信“万物有灵”的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民众来说,由于其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对各种“神灵”充满畏惧,它们不仅拥有人所不具备的超凡能力,也因其与人相通而具有人的品格。因此,自然界常常被人想象为异己的,可以在人身上施以无限威力和惩罚的存在,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二者间的对立。此外,在历史上随着各民族相继徙居怒江流域,就连他们彼此也被想象成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属灵的存在。于是在人与灵之间,始终处于既屈服又敌对的地位,由此也产生出人的一切灾病危难完全是由于世间的“灵”作祟的思想,而身体之病痛只是灵魂受到戕害或诱骗的表象。所以人若想免除灾病祸难,必须和“灵”妥协,抑或搏杀,以祭品取悦于他,或彻底将其驱逐。其间能同时沟通人与灵者唯有巫师。这也证实了人类对于“灵”想象颇具人格化特点,人与灵之间亦是人人关系的投射。
在各跨境民族民众的传统观念中,对瘟疫并没有形成单独的认知体系,他们之于瘟疫的诠释仍处于对疾病的整体认知当中,因此,导致出现瘟疫的“灵”与其他疾病在类属上是相似的。林林总总,名目甚繁,且因族因地而异。总括之大致有三:其一,自然神灵,即日月山川、花鸟虫鱼、风雨雷电均有恶灵。比如独龙族信仰的神灵中有“几卜郎”一种,“它是山崖、洞窟中的崖鬼,善于变成各种的东西,附在人体上,作祟其灵魂‘卜拉’(人的生魂——笔者注),对人危害极大,能让人患病死亡。”[11]除“几卜郎”外,崖灵“瓦江卜郎”,藏匿于山林的恶灵“墨里”,以及崖峰之灵“南木郎”等都被独龙族视为与瘟疫相关的自然神灵。其二,“民族”神灵、氏族神灵,这两个神灵均产生于社会,对于多自社区外传播的瘟疫来说,“民族”神灵又成为重要诱因之一。其三,人之灵魂,其中包含“亡魂”和“生魂”。
然而,瘟疫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与其他疾病不同,在医药知识阙如的年代,人们很难断定病源的出处,在瘟疫所造成的极端恐慌心理之下,“病毒源于社区之外,或是有人蓄意谋之”便成为最合理之想象。为了克服此种恐惧心理,以及对病患进行有针对性治疗,在信赖“万物有灵观”的前提下,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往往会急于寻找被错置为病源的“替罪羊”。常被视为疫源的替罪羊主要有两类:分别为来自异族的邪祟鬼灵和社区中的善事巫蛊者。
在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中均流传着一种“异族”神灵观念,该观念系典型的替罪羊思想,即认为包括瘟疫在内的病源来自异族的鬼灵,其实质是历史上各民族不平等关系映射于宗教观念的体现[12]。比如居住于福贡县匹河乡的怒苏人过去就认为“痢疾”“荨麻疹”“肺结核”等症与邻近白族支系勒墨人的鬼灵有关,一旦占卜到是勒墨人的灵作祟,就要视症状举行“磨曲于谷”“尼白于”“享北于”等仪式。怒苏人对待异族鬼灵多采取驱赶的方式,但仍需施舍祭品以确保鬼灵不会恋栈不去。祭词使用“鬼灵”通晓的勒墨话,祭祀的场所多在村寨外的旷野,通常有固定地点,如祭“尼白于”就要到名叫“洛霍”的岩洞中进行[13]。对于这类祭祀场所,民众都十分忌讳,往往绕道而行。祭品一律由巫师和病患分食,决计不能带回家中,吃不完的需现场烧掉。这也体现了怒族人对瘟疫具有传染性的认知。整个祭仪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鬼灵送至其居住地方。如在“磨曲瑞谷”中,巫师要将鬼灵从福贡匹河的老姆登村一路遣送至勒墨人居住的大、小格拉(今兰坪石磴、中排等地),其间还需监督其翻越碧罗雪山的垭口。
另一类被想象成为替罪羊的是社区内部的善事巫蛊者。在瘟疫流行之时,他们经常被当作“我群内部或边缘的‘非内部人亦非外人的他者’,并因其通灵属性而构成‘与恶灵内外勾结的虚构想象’,”[14]进而受到攻讦和驱逐,有时甚至还有丧命之虞。“在集体恐惧与焦虑下,人们猜疑并施暴于内部或身边敌人的‘猎巫’找寻替罪羊的行动从未消失。”[14]常被怒江中缅北界各族视作“猎巫”对象的有两种,其一是所谓的放蛊者,其二则是精通攘灾祛病之术的巫师。
先说第一种,怒江的傈僳族、怒族都笃信蛊术,认为畜蛊是一门代代传习的巫术,男女皆有,但妇女为此业者居多。部分村寨有公认的养蛊之家,虽可生财,“但因其名誉不好,社会批评太坏,村邻亲朋且不愿与之发生婚姻关系……傈僳对放蛊者甚为畏惧,亦甚信仰,对有养蛊嫌疑之家,多所忌避”[15]。然而,一旦尼帕认定瘟疫祸起于有人放蛊,则必求诸于神判。该方法也被傈僳称为“翻药”。其最普遍之法“是使他攫取在盛满了滚水或热油的铁锅底上放着的银片。如无灼坏事实,即认为无罪”[10](P278)。如有罪,轻则阖家被驱离,重则遭来杀身之祸。对于有的社区来说,施巫蛊者是明确的,但有时则是模糊的,若不能明辨就需要巫师来占卜,然后借助巫术来驱杀被神谕为施巫者的灵魂,谓之杀魂。怒族把这种于私下勾魂摄魄,致病降灾的人称为“衣苏”。
除放蛊和勾魂者之外,巫师在疫情严重或病患久治不愈,乃至死亡甚众的情形下,也会成为民众驱杀的对象。因为能沟通人、灵双方的巫师,本身就足以令人忌惮。福贡县木古甲乡有怒族巫师而被称为尼帕者,“除能给病人看鬼‘治病’以外,也会替病人到死后的世界去招魂。尼帕并能祸人,即把别人的魂收去,致人于死。一般人对尼帕都比较惧怕,过去因怀疑‘尼帕’杀魂而曾有赶走或杀死尼帕的事情发生”[16]。
在前基督教时代,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应对瘟疫均以举行祈神禳鬼的仪式为主,并兼以“翻药杀魂”等巫术治疗方法。疾病多系出于神之谴责或鬼之作祟,对神祈祷祭祀,对鬼则请巫师禳除。虽然各族中亦有极少数求医问药者,但“此辈医师之药品多系以山野所获之草木花卉配制而成,且多系外科之伤药,”[15](P346-347)不堪大用。至于集中表现为“杀牲祭鬼”的献祭仪式,则不仅无法救人于水火,而且动辄致病患所在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绝境。 《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 中说:“上帕夷民信仰祈祷,牢不可破……一有疾病,不信医药,即请巫人于郊外择树一株,系以白纸少许而祭之。初则用鸡猪,不愈则祭之以牛羊。怒族家产,唯恃牲畜。故一人有病,所祭牲畜,几至破产,一家均受其害,且一经死亡,房产器具,尽皆抛弃,另行择地徙居。其房屋构造甚易,然因赤贫已极,若死伤甚重,其后裔必至贫无立锥。”[5](P64)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中缅北界各族不惟在遇瘟疫或疾病侵袭时,才举行攘灾驱鬼的仪式,在其重要的传统节日当中,也有以驱邪除秽为目的的仪式活动,如傈僳族刀杆节、怒族如密期、独龙族卡雀哇、勒墨人尚旺节等等。在如密期中,怒苏人更是以生长在不同海拔高度的野禽来向神灵献祭,祈求“血鬼”在享受过美味之后尽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这些都表明各跨境民族民众苦瘟疫久矣,他们有攘灾驱疫的迫切需求,但在前科学时代唯有依靠巫术和仪式。
三、基督教传入之后的瘟疫观、瘟疫恐慌及其应对
(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民间巫医与基督教医疗并行
基督教本系外来宗教,它于20世纪初才传至位于中缅北界的怒江流域。在其之前,早有天主教捷足先登,“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 法国传教士壬司铎开始到贡山传播天主教,在白哈罗建立教堂”[17]。但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有限,信众也仅限于怒族的阿怒支系和少数藏族,未成为怒江各跨境民族之普遍宗教信仰。与之相比,基督教虽然传入时间较天主教晚,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传播,牧养了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支系勒墨人等大批信众。1949年以前,其信众比例占怒江总人数的1/3[18]。同时基督教信仰还呈现出区域性,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特质。
传至怒江的基督教派均属经过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且各差会都成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比之基督教传统,其传教方式和宗教理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与其成立的社会历史场景和宗教使命不无关联。皈依了基督教的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民众在对于瘟疫的认知和应对方面亦受此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于19世纪陆续来华的新教各教派传教士,其目标均为牧养信众,传播信仰。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在怒江传教的内地会、神召会等差会与其他早期在华传教的差会在传教模式上基本一致:它们将文字布道与医药施治等社会公益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在传教对象中建立了信任[19]。这当然于客观上也为怒江边民带来了科学意义上的医疗卫生观念。据傈僳族学者史富相回忆:(原) 碧江县传教士杨思慧之妻阿子打不仅从事传教活动,而且还兼做医师,每逢礼拜其门前就聚集了众多来求医问药的傈僳族群众。凡遇信众患病,她总要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地去逐一诊治[20]。另有《福贡县卫生志》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年) 美国牧师马道民进入福贡上帕地区后,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将携带的部分西药,偶尔给患病的教民施用,以笼络民心,当时给患病教民服用的西药主要有两种:群众俗称黄药片(阿的平),白药片(磺胺类),主要用于治疟疾和痢疾。”[21]
其次,虽然外国传教士在有限的程度上传播了科学意义上的医疗卫生观念,帮助贫苦的怒江边民于身体上缓解和消除了病痛,但他们灌输给信众的有关“疾病”与“瘟疫”的观念却是神学和宗教意义的。民国时期,怒江地区分属四个差会,各差会的布道范围互不统属。今泸水市和福贡县南部属内地会;福贡县中、北部属神召会;而在贡山县传教的则先是联合基督教会中华传教会,后析出分立为“滇藏基督教会”。尽管各差会在宗教理念和仪轨上不尽相同,但均表现出对“属灵”这一神学观念的重视。它们在宗教理念上的共通点是:第一,坚持《圣经》原典的权威性,凡事必依循经典。第二,保持信仰的纯真与坚定,倡导内省,并注重“圣灵”的开动,从而将“属灵”置于中心地位。所谓“属灵”,“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接受基督或被圣灵充满,这需要将自己完全奉献,并且不管结果如何都完全依靠上帝。在此属灵境界中,祷告成为最有效的方式[19]。
基督教信仰传入后,外国传教士向信众宣称,上帝是唯一且万能的神,有病禁止向其他鬼神献祭,只需向上帝祷告,除祷告外还赠予药品。故表现为“杀牲祭鬼”的原始宗教活动有减少的趋势。但面临来势汹汹且蔓延迅速的瘟疫威胁,单凭祈祷上帝和维持仅限于信徒中的施药救济,显然无法彻底有效地应对瘟疫。因此,“杀牲祭鬼”“驱杀巫人”等传统观念下的应对方式仍然是各族民众消灾祛疾的重要选择。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健全的医疗体系与疾控措施在中缅北界的怒江尚未建立,故从基督教传入至20世纪50年代的三四十年间,基督教医疗与民间巫医并行一直是各族应对瘟疫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鉴于瘟疫所引发的心理恐慌,部分民众还会抱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矛盾心态,交替举行“祷告”与“祭鬼”仪式,以期病患能够痊愈。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碧江县第二区俄科罗村村民黑阿妹的调查,“1953年7月他父亲生病,请教会挖苦(祷告),给晚上挖苦的人吃肉,杀2头猪,合10元,合包谷2斗8 升6合,还用去包谷1斗、大米5升、茶2元。病情未见好转,又祭鬼,用去羊两只,24元,合包谷6斗8升6合。鸡5只,10元,合包谷2斗8升6合。杀猪2头,20元,合包谷5斗7升2合,还用去包谷1斗”[17](P41)。由此可见,在没有建立现代医疗和疾病防控体系的时代,如何有效地应对瘟疫依旧是怒江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体系下的医疗卫生与仪式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在包括怒江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着手组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各级政府曾多次向位于中缅北界的怒江地区派驻民族工作医疗队,他们一方面宣传卫生科普知识,一方面选拔和培训当地的民族医疗工作者。面对怒江各族经济欠发达,交通闭塞,山高坡陡,人口居住分散的艰苦环境,外来和本地的医疗工作者常常送医送药下乡,并鼓励各族民众转变观念,于生病时积极寻求医疗救助。至20世纪80年代,怒江地区的疾病防治取得了显著成就。因病求神祭鬼而导致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境,已鲜有所闻。随着怒江城镇农村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各族人群的免疫力得到了明显提高,曾经肆虐于怒江各跨境民族的各类传染病均已得到抑制并不再复发。
长期以来,由国家致力倡导、推广的基于科学理念下的现代医疗卫生观深刻地影响了怒江各跨境民族民众对于传染病和瘟疫的认知,也使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各族信众于传统认知中丰富了对瘟疫观的表述,虽然其对瘟疫的理解和阐释仍然囿于神学和宗教观念,但对于“出现疫情需要及时求助医疗”,以及“瘟疫具有传染性应避免聚众祷告”等认知则是在国家卫生防疫观念下所产生的新内容。怒江各跨境民族信众现在对于“瘟疫”的一般性认知是:第一,溯自《圣经》,瘟疫当是人违背神的戒律及其所限定的人类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人犯下的罪行是瘟疫之祸源;第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于瘟疫未起时就已预知了它的发生,其策动瘟疫的目的是惩罚那些不知有神存在,作恶而又不知忏悔的人类,同时也是为了试炼神之儿女的信心;第三,若信众中有感染瘟疫者,不能证明其有罪,亦不能证明其无罪;第四,神因人类的罪孽而发怒,但他的慈爱远胜于怨恨。只要人类认罪悔改,神就将出手相救。由此种“赎罪”观念所导致的结果是,信众尽管认为医疗层面的救助措施对瘟疫防治至关重要,但人若想彻底获救,必须赢得上帝的赦免与宽恕,其悔过认罪之心要能为上帝所闻,只有感动了世上唯一的神,人类方能获救。对基督徒而言,实现救赎的途径唯有向神祷告,既为自己,也为那些不信神却犯下罪行的人。
然而,当上述“瘟疫观”遇到村寨中出现疑似传染病这一危急情形时,就会发现于社会恐慌的心态下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依然存在。福贡县娃底村的个案说明了作为社会排斥形式之一的“驱巫行为”是如何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傈僳族村寨中被再次实践的。“2006年下半年,娃底村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去世,且去世的大多为中青年,这种与正常有异的死亡概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后来村里人认定事情的起因是:村里来了一个与“尼扒”一样的女人。村里人传说,这个女人法力很高,曾变成老鹰与人搏斗;也传言说她在家中与人斗法致人非命等。村里人认为单凭个人难以与她抗衡,因而就在教堂里组织了三次集体祷告会,全村人共同参加,并把村里所有被认为有灵力的人,集合起来手握手共同祷告,以求形成最强大的合力。后来这一事件以那位被称为‘尼扒’的女人离开村子而告终,但娃底人认为教会组织的集体祷告会把她镇住了,她才会离开的。”[22]由上可知,尽管有了现代医疗观念的介入,怒江各跨境民族信众对“瘟疫”“传染病”等疾病也有了新的认知,但当其面对不确定性加剧和使人陷入极度恐慌的“瘟疫”时,“驱蛊”“排巫”等原有的“替罪羊”观念就会借助基督教的仪式形态以新的面目出现。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应对瘟疫和传染病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国家层面来说,以国家为主导的构筑于现代医学观念体系的疾控防御和治疗已成为最重要的应对方式。它包括在基层政府和医疗单位的组织下,普及和宣传防疫知识,派发防疫药品,村寨消毒,封闭村落交通,派专人值守村口等等。从民众层面而言,以祭鬼和祷告为主的仪式治疗方式仍然存在,尽管前者目前已十分少见。而祷告则是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于国家医疗体系之外,最常见的应对方式。
祷告被认为是基督教灵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人与上帝交通的主要途径。它不仅是人求得“神启”以应对日常及突发事务的主要方式,也是在面对不确定事项时非常重要的自我安慰形式。马塞尔·莫斯更是认为:“在开放的新教主义中,祷告实际上已经成了宗教生活的全部。”[23]与疾病和瘟疫相关的祷告,有个人和集体祷告两种形式。当遇到久治不愈的重症或是瘟疫出现,常举办集体祷告。据主持祷告活动的教牧介绍,在社区或是家庭遭遇严重危机时,还会举行禁食祷告和守望祷告。
与原始宗教信仰不同,基督教信仰观念强调,人人皆可向世上唯一的神上帝祷告,且无需通过灵媒,亦无需宰牲献祭。信众只要凭借上帝所赐予的信心,并真诚地向其祷告,就可以期待灵验的出现。然而,在以祛除疾病和瘟疫为目的的祷告活动中,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又表现出与上述观念的差异。虽然教牧人员声称“属灵”并没有高低大小之分,在教会中职分高的人并不比一般信众虔诚祷告所得的灵力更高,但在田野调查中,笔者经常发现信众总因担心自己不会祷告,而希望能在祷告活动中邀请到那些他们所认为的“会祷告的人”。所谓“会祷告”实质上是一种藉由灵修和不断学习而产生的,并非来自天赋或神授的灵力属性。正如马塞尔·莫斯所指出的:“祷告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神圣事物的口头宗教仪式,其所用的仪式语言必须为其宗教群体所接纳。不管是个体化的,抑或集体化的祷告,其本质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23](P167)因此,通过学习而熟稔宗教文本和仪轨的传道人、教会长老、礼拜长等教牧自然地被信众视为“信得好”或者是“有灵力”的人。由此可见,虽然基督教观念认为“凡信徒皆可由信心祷告属灵”。但对于一般信众来说,其心中“得灵力必请有灵力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下,经过神学灵修和研习的教牧便成为新的“灵力持有者”。这不得不说是对原有信仰观念的延伸和发展。
三、结论
中缅北界的怒江峡谷历来瘟疫频仍,生活于其间的各跨境民族长期与之共存。瘟疫不仅为峡谷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也于其历史记忆中留下了苦难的回忆。回顾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与瘟疫的博弈史,他们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对“瘟疫”的区域性认知,而且这些认知与应对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在前基督教时代,瘟疫在“万物有灵”观念模塑下被解释为附着于自然、族群,以及个体上的鬼灵作祟,以祭祀神灵与驱杀巫人为主的仪式与巫术,构成了各族应对瘟疫危害与恐慌的最主要方式。基督教传入之后,基于传教的目的,外国传教士在极为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了现代医疗卫生观念及其治疗技术,其与基督教祷告仪式,民间巫医共同成为这一时期的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民众应对瘟疫的并行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降,以国家医疗体系为主导的疾控防御机制已成为应对瘟疫的最重要力量,并有力地消除和减少了瘟疫对怒江各跨境民族民众日常生活的威胁。然而,国家医疗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导致民间巫医与基督教仪式治疗的消亡,后者还于当下的历史情境中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构筑于西方微生物病学基础上的科学瘟疫观无疑是现代社会应对瘟疫的主流方式,也主导着当今人类对瘟疫的话语表述。但应看到,人类对瘟疫的认知绝不仅限于19世纪末才开始成形的现代科学卫生观。从中缅北界各跨境民族的案例可知:在前科学时代,人之瘟疫观与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有关。危险性极高的瘟疫被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失序所致。几乎所有的应对措施都是以恢复正常秩序为要旨。对于前者,主要以祈祷献祭的方式来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于后者,则由发生瘟疫的社会于自身文化中建构出一个危险制造者的“他者”形象,通过攻讦和驱逐“他者”来缓解瘟疫恐慌及回归社会的正常秩序。所谓“他者”既包括异己的族群,也包括社区内部的“边缘人”。这些颇具替罪羊意义的责难者因文化界定而被赋予了道德伦理色彩,因而也被塑造成为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普世性的基督教信仰传入中缅北界地区,其系统的神学教义和宗教观念为各跨境民族信众提供了关于瘟疫的新解释体系,并同时带来了瘟疫肇始人类自身罪孽的赎罪观。由此,指向内省的虔心祷告和从外部找寻“替罪羊”共同构成了当今各族面对瘟疫恐慌时的宗教经验。
人类学的个案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在经历疾病、瘟疫等重大灾难时,将病源归咎于社会中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案例屡见不鲜,并常表现为社会的歧视与排斥。此举的目的表面上看是借助对部分人群的污名化和迫害来缓解瘟疫所造成的恐慌焦虑,实则借以强化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污名化的建构表征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抑或族群间的冲突与对立。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致使数十万的“女巫”被指责为瘟疫的祸源,她们大多都不具备通灵能力,仅以替罪羊的身份被无辜地凌虐处死,从而成为了巩固上帝之国的牺牲品。医学人类学家法默以大量流行病数据为立论基础,确证艾滋病病毒实际上是从美国输入海地,病毒的携带者多是以游客身份来海地享受性产业服务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海地裔美国人。然而,受害者海地人却一直承担着艾滋病毒传播者的恶名。再联系当前疫情,蔓延全球的疫情向人类社会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于此危难当头本应强化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互信,共克时艰,但原本毫无“政治倾向”的瘟疫却被西方各国加以政治建构和污名,并被贴上了病毒专属于某一国或某一族群的标签。争讼病毒来源,赋予病毒以污蔑性称呼等行为均表明了西方各国企图嫁祸于人,掩盖其社会内部失序的窘迫,这与面对瘟疫驱杀巫蛊者的行为是何其类似!由上可知,作为一项关于瘟疫恐慌与应对的人类学探究,必须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出发,同时还需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历时性的维度。唯其如此,才能挖掘出人类行为实践所表达的丰富社会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