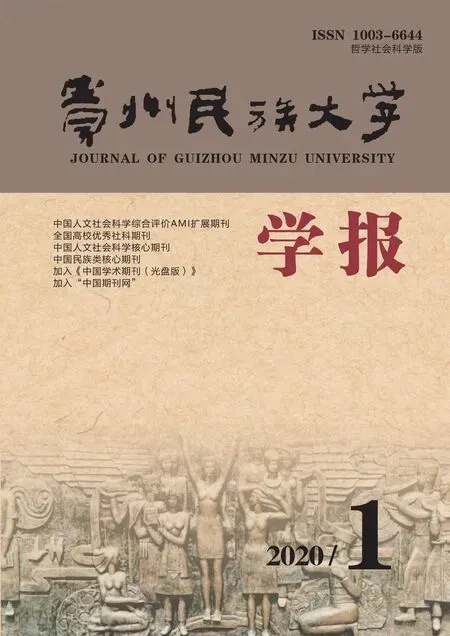苗族史诗研究若干问题述论
杨正文
苗族史诗(1)本文使用的“苗族史诗”涵盖“苗族古歌”“苗族古经”等概念,后文将辨析。研究是苗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自19世纪末发端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间,在中外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苗族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完成了苗语各方言史诗采录、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若干代表集册,在研究层面更是关涉史诗、民间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成果丰硕。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不论是搜集整理还是研究,存在“苗族史诗”“苗族古歌”“苗族古经”等概念交叠或混用现象,因此,对之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同时,在苗族史诗本体研究方面存在着音声研究不足等问题,亦需要深入探讨。
一、“苗族史诗”研究回顾
近二十年来,已有多位学人对苗族史诗研究做了学术史梳理。李炳泽、邹玉华在世纪之交就开始了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苗族史诗搜集整理及研究进行梳理[1]。之后,李炳泽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口传诗歌中的非口语问题:苗族古歌的语言研究”研究中,对苗族古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进行了回顾,不过较为简约,基本把关注点放在搜集、翻译与语言研究上,且以20世纪90年代为下限。[2]21-29同样,吴一文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3]研究中,也对苗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进行了回溯,其中包括了对苗族古歌概念、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以及相关搜集整理的版本进行了评述,但从所涉内容看,基本上是以苗语中部方言区即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史诗为研究对象。相较于前两位学者,龙仙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作者基本以李炳泽首提的1895年为上限,分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两个部分,并将国内研究分为“萌芽期”(1912-1949年10月前)、“低潮期”(1949-1979)、“繁荣期”(1980至今)[4]49-67,且把每一时期所研究的基本重点做了详细的述评。曹端波等在《苗族古歌演唱传统与地域社会研究》的第一章里也专辟一节对“苗族古歌”相关研究中结合问题有针对性进行了梳理[5]29-42。这些学术回溯无疑对苗族史诗研究学术史的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仍有进一步梳理廓清的必要。
在苗族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使用“苗族史诗”概念进行苗族口头传统的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但关涉到苗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及学术研究起步要早于此,几乎与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引介与发展同步。文献检索显示,中外学界开展对苗族的学术研究是比较早的(2)参见王慧群,《关于外国苗族研究的情况》,载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编,《民族史译文集(8)》,1980年;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但有明确对苗族史诗的搜集或研究的记载,是以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Clarke)与贵州黄平籍苗族布道员潘寿山的合作为开端的,他们在1895年前后记录了包括《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等在内的苗族史诗。[6]22-32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902年从湖南常德经由贵州到云南的一路调查中,在贵州安顺一带搜集了涉及苗族史诗内容的口传资料,在他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里专辟有“苗族之神话”一节,记载安顺地区苗族有关兄妹通婚与苗族各支系起源的史诗资料。[7]32-33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萨维纳(F. M. Savina)1924年在香港出版的《苗族史》中,于第四章“苗族的信仰”里记载了其“根据苗人的口述而记录下来的”“未做任何改动”的关于“创世”“造人”“洪水”[8]243-283等歌谣。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早年以传教士身份在四川宜宾工作时,于1921年前后接触了珙县等地的苗族,开始搜集一些苗族的歌谣与故事。1932年被任命为(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后,更潜心研究川苗文化。他采用的方法是,请当地苗族当面唱歌或讲故事,他用国际音标一字一句将苗语记录下来,再进行翻译。后在通晓汉语的苗族人项朝嵩的帮助下,先后搜集到752篇苗族歌谣、传说和故事。其中有近60篇故事、神话、歌谣被翻译整理,以《川苗习俗》《川苗传说》为题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1937年第9卷,1938年第10卷)。更重要的是葛维汉的四川苗族神话、故事研究还得到了他的好友——《中国民间文学分类》作者,《民间文学分类》作者S·汤普逊的帮助予以分类研究。[9]147-162葛维汉的研究工作在史诗学或民间文学界内具有一定价值,值得重视。
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三人受蔡元培的委托赴湖南湘西调查,其间搜集了苗族大量的口头传统资料。在1941年出版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凌纯声等把所搜集到的故事资料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含有宗教性的,在民间文学的术语上叫做神话(myth);第二类是含有历史性的,那就是传说(legend);第三类是含有伦理性或道德性的,那就是寓言(apologue);第四类是含有滑稽性或诙谐性的,那就是趣事(droll)。第三、第四两类本来都是说来消遣而具有娱乐性的,普通都总称为民谈或民间故事。”[10]164该书记载了篇幅较长的翻译为汉语的“洪水神话”“自然神话”“事物起源神话”“神仙神话”“龙王神话”“鬼怪神话”“阴阳界神话”等文本,这些神话无疑是本文言之史诗的范畴。这些资料除一部分是凌纯声等人在湘西亲耳聆听苗人讲述随时记录外,大部分是协助他们的几位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吴文祥、吴良佐等人)请苗族中耆老或能讲故事者讲述,经他们记录下来并进行翻译的。可贵的是,这些资料完全由苗族人用苗语口述,调查记录者用国际音标或汉语辅以记音,并附记有每篇故事讲述人的姓名信息等。这样的民族学资料采集方法,在苗族史诗早期搜集中是难能可贵的,所获得的史诗资料无疑具有较高可信度。
吴泽霖受其老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鲍亚士(Boas)从神话入手研究印第安人历史的学术路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夏大学迁黔期间,他所领导进行的苗族社会调查中十分注重对苗族神话传说的搜集。他在1938年发表的《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3)吴泽霖,《苗族中的祖先来历的传说》,先发表于《贵州革命日报·社会旬刊》第四第五期,1938年5月19日,后载《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再版,民族出版社,第94-105页。一文中,完整引用了苗族学者杨汉先整理翻译的“洪水滔天歌”,并采用人类学方法比较了几个不同苗族支系关于洪水滔天、兄妹通婚的神话故事。1941年3月出版的《社会研究》第20期,发表了时在大夏大学执教的陈国钧《生苗的人祖神话》一文,引入了他在今贵州省从江县记录的所谓“生苗”(指今分布在月亮山区的苗族)的三则被他称为“最为普遍的”“人祖神话”,其中第三则共有488句长,是陈氏用国际音标记录了苗语的“全生苗区已几乎没有几个老者能唱”的“人祖神话”,文中称之为“生苗语原歌”。[11]114这被认为是发表最早的苗族古歌汉文诗体译本。[3]2
罗荣宗在20世纪40年代也对贵阳高坡一带苗族歌谣进行了搜集,20世纪50年代陆续推出成果,于1957年出版了《苗族歌谣初探》,将苗族歌谣分为历史古歌、英雄歌、苗族情歌、苗族酒歌等。其搜集整理的贵阳高坡苗族歌谣文稿由后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编辑为《苗族歌谣初探·贵阳高坡苗族》一书于1984年内部印刷流通。[12]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苗族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及研究与现代苗族知识分子的成长、掌握文字书写有密切的关联性。在上述中外学者的研究中不乏苗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如潘寿山、杨汉先、石启贵等,他们对相关工作的开展做了不少贡献。早在20世纪20年代,贵州威宁县等地的苗族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基督教的传播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如果不及时将苗族传统歌谣记录下来,基督教传来之前的民族文化将有失传的危险,于是开始用柏格理苗文记录苗族的传统歌谣,尤其是当地苗族的一些“史歌和历史传说”[13]。20世纪80年代,杨光汉等将20世纪30年代滇东北、黔西北苗族歌手用“老苗文”记录的“古歌”编辑成书,以《西部苗族古歌》[14]为名纳入“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丛”出版。该书所编选的内容包括从“开天辟地”到民族迁徙,以及流传于该区域的一些故事、习俗等。贵州威宁县出生的杨汉先是最早独立进行苗族歌谣研究的本民族学者,他写于1937年前后的《苗族述略》《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等文,均有史诗资料的研究和运用,他还将“花苗故事”划分为神话、传说、故事三类,且进一步将传说区分为“战争的传说”“历史的传说”“英雄的传说”三类,把故事进一步分为“爱情的故事”“愚人的故事”“动物的故事”“教训的故事”等四类。(4)李文汉主编,《杨汉先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4-15页。《苗族述略》《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二文最早刊于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0集,内部刊印,1983年)湖南湘西的石启贵于20世纪30年代在凌纯声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用汉字记音的方式搜集整理“苗觋神辞”有百余种,“汇编数十厚册”[15]4,由麻树兰等翻译整理于2009年出版的有8卷之多[16],包括了椎牛、椎猪、接龙、祭日月神、还诺月傩愿等内容。
在苗族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百余年间,大致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成为推动各民族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引擎”。之后,《民间文学》创刊(1955年),依托研究会开展收集民歌运动,从1959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各地歌谣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在此背景下,贵州、湖南等省的苗族史诗陆续被搜集整理。此外,以全国人大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肇端,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各调查组在深入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苗族地区调查时,也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苗族史诗(古歌、故事)。此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于1950年至1955年先后对西南、中南、西北一些省区进行的民族语言调查,在收集民族语言素材同时搜集了不少的民族口头传统资料。马学良带领苗族学生邰昌厚、潘昌荣等前往贵州台江、黄平等地搜集苗语资料,张永祥带着中央民族大学苗语班学生到凯里实习,搜集苗语资料。他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各种民间口头传统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史诗。[17]250龙正学等带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到贵州松桃、湖南花垣等进行苗语调查[18]1,也搜集了不少的苗族史诗资料。今旦、马学良等搜集编译的《金银歌》全文及《蝴蝶歌》片段,曾分别在《民间文学》1955年8月号、1956年8月号发表[19]59-108。在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集内部刊印的唐春芳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以及第十七集《苗族婚姻歌》等是这一阶段标志性成果之一。在研究方面,前述马学良、邰昌厚、今旦等1957年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关于苗族古歌》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代表作。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的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工程,成为推动苗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再次高潮的契机。1979的田兵编选《苗族古歌》正式出版,之后马学良﹑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1983),西部方言《苗族古歌》(1986),张应和、彭德荣整理译释《苗族婚姻礼词》(1987),龙炳文、龙秀祥整理译注《古老话》(1990),石宗仁编译《中国苗族古歌》(1991),清镇市民委编《苗族十二组主歌》(1991),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西部苗族古歌》(1992),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1993),龙岳洲等编《武陵苗族古歌》(1994)(5)张应和、彭德荣整理译释,《苗族婚姻礼词》,岳麓书社,1987年;龙炳文、龙秀祥整理译注,《古老话》,岳麓书社,1990年;清镇市民委编,《苗族十二组主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龙岳洲、罗正铭、欧秀昌编,《武陵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其他参见另页注释。等苗语不同方言区的代表性史诗整理翻译陆续出版。此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民间文学资料》中,第五十九集“苗族开亲歌”“巫歌巫词”,第六十集“苗族古老话”,以及黄平、施秉、镇远三县民委编《苗族大歌》[20]等的史诗资料刊印。这些史诗资料的公开出版、刊印流通,推动了苗族史诗研究的发展,这阶段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涉及民间文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度、广度比第一次高潮有了较大的拓展。大批本民族学者参与其中,不少成长为研究的中坚力量,是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
第三次高潮是在21世纪以来,尤以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为引擎。早在世纪之交,回归传统逐渐成为主导文化的国家主流意识,不少地方的苗族史诗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的旗帜下得到搜集整理。如在四川省古籍办支持下,1999年出版的《四川苗族古歌》(三卷本)[21],今旦译注的《苗族古歌歌花》[22],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等编的《苗族古歌》等。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2005年“苗族古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苗族史诗《亚鲁王》“被发现”(冯骥才语),成为这一高潮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这一阶段先后被整理、翻译、编选出版的苗族史诗版本有《王安江版苗族古歌》,吴德坤、吴德杰搜集整理翻译《苗族理词》《西部苗族古歌(川滇黔方言)》《黔西苗族古歌》,韦秀明、贺明辉主编《苗族古歌(融水卷)》,石如金搜集翻译《湘西苗族传统丧葬文化〈招魂词〉》,石如金、龙正学搜集翻译《苗族创世史话》,龙正学搜集翻译《苗族创世纪》,胡廷夺、李榕屏主编《苗族古歌》(系列),杨正江编译《亚鲁王》(6)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编,《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吴德坤、吴德杰搜集整理翻译,《苗族理词》,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王安江搜集编注,《王安江版苗族古歌》,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等编,《黔西苗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杨照飞编译,《西部苗族古歌(川黔滇方言)》,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韦秀明、贺明辉主编《苗族古歌(融水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16年;杨正江搜集整理翻译,《亚鲁王》,中国书局,2011年;龙正学搜译,《苗族创世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胡廷夺、李榕屏主编《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黄平、施秉、镇远三县民委编,《苗族大歌》(内部刊印),1988年。,还有20世纪80年代一些史诗版本的再版或作为民间文学作品选出版(7)《中国苗族文轩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苗青主编,《东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中部民间文学作品选》《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系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前文提到的石启贵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的出版。还有吴一文、今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本德尔合作的三语版《苗族史诗》(苗文、英文、汉文)的出版[23],等等。
在研究方面,第三次高潮除了延续第二次高潮在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深度外,还显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苗族史诗本体研究的系统深入。以吴一文、今旦的《苗族史诗通解》,吴一文的《苗族古歌叙事传统研究》,肖远平、杨兰、刘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形象与母题研究》,曹端波、曾雪飞的《苗族古歌演唱传统与地域社会研究》,龙仙艳的《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8)吴一文著,《苗族古歌叙事传统研究》,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肖远平、杨兰、刘洋著,《苗族史诗〈亚鲁王〉形象与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曹端波、曾雪飞著,《苗族古歌演唱传统与地域社会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龙仙艳著,《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等为代表。二是围绕《亚鲁王》形成的研究群体和系列成果。《亚鲁王》“被发现”时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初期,引起了国内学界高度重视,《亚鲁王》整理文本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围绕“亚鲁王”召开多次高端学术会议,乃至提出“亚鲁学”等[24]。三是苗族史诗研究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9)据不完全统计,国家社科课题立项资助涉苗族史诗课题:“口传诗歌中的非口语问题——苗族古歌的语言研究”“苗族古歌通解”(2000,李炳泽)、“苗族古歌通解”(2008,吴一文)、“苗族巫文化经典研究”(2011,麻勇斌)、“苗族古歌民间叙事传统研究”(2012,吴一文)、“中国苗族古经采录整理与研究”(2013重大,刘峰)、“中国苗族古经专题研究”(2013重点,杨正文)、“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2013,龙仙艳)、“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2013,吴正彪)、“《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2013,蔡熙)、“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英译及研究”(2015,李敏杰)、“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2015,杨兰)。,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苗族史诗为研究选题等,为促进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苗族史诗、古歌、古经等概念辨析
目前,在苗族史诗研究中,被使用的概念还有苗族古歌、苗族古经等,一些学者认为含义相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涵盖的意义是不同的,不能混同使用,因此有必要进行简约的界定与梳理。
“苗族古歌”这一学术用语最早见于公开出版物的是1956年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关于苗族古歌》[25]一文,文章没有指明“苗族古歌”概念源于苗语的直译或是意译,而是直接表述说:“古歌也称大歌。古歌是指其内容古老而言,大歌则指篇幅的巨大而言。古歌一般都是几百行以至几千行,远非其他类型的民歌可比。”1958年中国民协贵州省分会筹备组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集时,直接用《苗族古歌》(10)唐春芳,《苗族古歌》,《民间文学资料》(内部印刷)第四集,第2-3页,中国民协贵州分会筹备组编印,1958年。田兵在1979的《苗族古歌》前言中说黔东南苗族地区流传的《开天辟地》等民间长诗,“习惯上称为‘古歌’,因为苗族人民把它看成历史,所以也称为“古史歌”。名词刊发了唐春芳整理的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唐春芳在前言里说,“有的以时间比较古老,内容意义比较重要,篇幅比较巨大,作为衡量古歌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合理。”(11)本文在此沿用我国民俗学知识谱系中把民间歌谣等归为“民间文学”的传统分类。自此,“苗族古歌”逐渐为苗族民间文学界所接受。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田兵、燕宝等(12)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田兵编选,《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人整理出版的苗族口头传统作品依然沿用“苗族古歌”的概念,尽管这些“苗族古歌”在整理出版中同样没有清楚交代其概念源自苗语音译或意译,但其共同点是这些早期被整理出版的苗族口头传统资料多是来自苗语中部方言的黔东南地区。且燕宝翻译的《苗族古歌》(1993)的苗文标题是HxakLulHxakGhot。今旦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苗族古歌”苗语称HxaklulHxakGhot或HxakHlieb等,[26]无疑,“苗族古歌”是对流行在黔东南苗族中的“老歌古歌”(HxaklulHxakGhot)或“大歌”(HxakHlieb)的意译。部分年轻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吴一文、覃东平认为,“苗族古歌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歌谣的泛称。狭义的‘苗族古歌’严格来说是‘苗族史诗’是专指叙述开天辟地、人类产生,洪水灾难、民族迁徙等内容的这组内部各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苗族民间文学作品。”[27]6吴一文认为“古歌是流传于苗语黔东方言区,以五言为基本句式,以插有歌花的问答句对唱为主要演唱形式,以创世、祭祖、民族迁徙为叙事主题,内部篇章之间有紧密逻辑联系,剧本史诗性质的苗族民间活态押调口头传统。”[3]37该定义显然将“苗族古歌”局限于黔东方言区内,当延展对其他苗语方言区同类文化事象研究时显示出某些不对称。李炳泽也持“广义”“狭义”之分,他认为综合这些前辈学者的看法,他们所指的是狭义“古歌”。如果是广义的古歌,可以换一句话说,内容涉及“古代”,追溯事物起源、发展和变化的歌,都算是广义上的古歌。他接着说,古歌的曲调与酒歌中的一种曲调浑为一体,只是各地的酒歌曲调不同。[2]34-35之后李炳泽给的定义为:“苗族古歌,是苗族人用苗语构筑出来的人类(苗族)早期的历史。”[2]38不难看出李炳泽在比较唱述古歌与酒歌曲调时也是基于其所熟悉的苗语中部方言区雷山县一带来说的。持苗族古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观点的还有龙仙艳,她说:“广义而言,所有的苗族古歌的歌谣皆可称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特指篇幅宏大的苗族古歌;狭义而言,苗族古歌指在苗族聚居地流传的有关开天辟地、万物起源、战争与迁徙等缘故性题材的韵文体口头传统。”[4]260她对苗族“古歌”概念是否存在于苗族文化“本文”之中提出了质疑,认为“苗族古歌”是他称而非苗语专有名词,“从苗族民间自称而言,除了西部方言区之川黔滇次方言的本土称谓‘hmongbngouxloul’(蒙歌老)可直译为苗族老歌或苗族古歌之外,东部方言区之‘dutghotdutyos’(都果都谣)直译为古言古语,中部方言区‘hxaklulhxakghot’(夏鲁夏个)直译为老歌、根古歌。通过苗语直译可见,在本土自称三大方言都凸显其‘古、老、长’,但民族性(苗族)显然是翻译者意译后所加。换而言之,在本文里,没有苗族古歌”“苗族古歌是文本化名词”。[28]
笔者认为,尽管在一些地区存在类似李炳泽所说的古歌唱述曲调与酒歌曲调相同的情况,乃至在黔东南巴拉河流域把酒歌称为“Hxaknaillul”(老人的歌或古人的歌),但也不尽然,同样在李炳泽所赖以为据的雷山县境内,人们既用酒歌调唱述古歌(史诗),也用“噶别福”调唱述,在仪式过程中还交替使用接近念白的吟诵,不应忽略了“古歌”唱述的场景以及唱述的内容,用“古歌”对译苗族口头传统中那些具有神话性或历史性题材,关注苗族对于世界源起、祖先历史的解释体系部分是切中其意涵的,且苗语中确有“古歌”(诸如hmongbngouxloul或HxakLulHxakGhot)的概念,是对译词而非他称,更何况用以称呼古歌中有关“古”“老”“大”等苗语的意义不完全等同口语中的意义。并非苗族“本文”里“没有苗族古歌”。至于龙仙艳所认为的民族性是添加的,这是没错的。但试想不加“苗族”定语,黄平、施秉等地直译史诗为“大歌”(Hxakhlieb),且“侗族大歌”也去掉侗族的定语,可能会导致学术表述无所适从。
毋庸讳言,“苗族古歌”概念的出现首先源自对苗语中部方言(黔东方言)民歌的搜集整理,是一个基于苗族本土语言翻译的学术概念。但“苗族古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并非局限于对苗语中部方言区史诗的表述,它已成为各方言苗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中常被使用的概念。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出版的苗语各方言区的口头传统资料中,还不乏“苗族古歌”的使用。如,先后出版的石宗仁整理译注《中国苗族古歌》(东部方言),古玉林等翻译整理《四川苗族古歌》(西部方言),杨照飞编译《西部苗族古歌(川滇黔方言)》,夏杨整理《苗族古歌》(西部方言),贵州毕节市民族事务局等编《黔西苗族古歌》(西部方言),韦秀明等主编《苗族古歌》(融水卷),胡廷夺等主编《苗族古歌》(多卷本)(13)《中国苗族古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四川苗族古歌》(三卷本),巴蜀书社出版社,1999年;《西部苗族古歌(川滇黔方言)》,云南民族出版社;《苗族古歌》(西部方言),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等编,《黔西苗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韦秀明、贺明辉主编《苗族古歌(融水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16年;胡廷夺、李榕屏主编《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在研究层面上使用“苗族古歌”一语就更为普遍了。(14)诸如:段宝林,《苗族古歌与史诗学分类》,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1期;杨正文,《论‘苗族古歌’神体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吴一文、覃东平,《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等等。在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苗族古歌》被列其中。说明“苗族古歌”本土概念在国内民间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苗族史诗”在苗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中使用的时间尽管比“苗族古歌”稍晚,但使用较为普遍,而且近年来增量明显,特别是在研究领域。同样是最早使用“苗族古歌”翻译整理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的马学良、今旦等前辈学者,早在1983年以《苗族史诗》书名出版了他们整理翻译的苗族民间文学资料,且在马学良为该书写的代前言中指出,“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这些诗歌详尽地记载了苗族族源,古代社会状况及风俗人情等等,苗族人民把诗歌看成自己形象的历史,所以我们称之为《苗族史诗》更为恰当。”[29]1-9之后,段宝林在《苗族古歌与史诗分类学》一文中说,他之所以用“苗族古歌”探索中国史诗学分类问题,“因《苗族古歌》是神话史诗最长、最完整、最有代表性典型作品。”[30]23今旦在《马学良先生与苗族古歌》一文中也指出,“《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苗语称HxaklulHxakGhot或HxakHlieb等,是一部无言押调,含创世神话和祖先迁徙的长篇史诗。”[17]
由此不难看出,不论是搜集整理者还是研究者,在面对苗族有关创世、历史等“诗化”口传文化部分时交叠或混用“古歌”“史诗”等术语表述时,也在强调“史诗”概念的“恰当性”。吴一文专门对苗语中部方言与“苗族史诗(或古歌)”关涉的HxaklulHxakGhot或HxakHlieb等几个苗语词汇从语义上进行梳理和解释,之后他认为“苗族史诗”在民间具有其特定的名称,且史诗的篇章构成也有一定的界定,表明民间对“史诗”的整体性有一定的认识。田兵、马学良、今旦、燕宝等老一辈学者整理出版的几个重要版本,体现出权威学者对苗族史诗整体性认识与民间认识是相同或相似的。[31]17最后他定义说,“苗族史诗是流传于苗语黔东方言区,以五言为基本句式,以穿插歌花的问答式对唱的主要演述形式,以创世、敬祖、民族迁徙为叙事主题,内部篇章之间有着紧密逻辑联系,具备史诗性质的苗族民间活态押调口头传统。”[31]21该定义强调了叙述主题、语言特点、结构形式和活态特点,并指明了流传区域。也正因如此,该定义用于苗语其他方言区不能完全符合其史诗存在的状态,就是在黔东方言区内,仿佛也给那些专用于祭祀或其他民俗场景中的口头传统作品留下了“古经”定义的空间。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苗族史诗”特别伴随着《亚鲁王》“被发现”再度成为中国史诗学界的热词。仅以“亚鲁王”作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有160余条,以“亚鲁王史诗”研究为关键词检索有79条,博士学位论文有2篇,硕士学位论文有8篇之多(截至2018年)。在万方数据知识脉络网的检索显示,自2003至2017年之间,苗族史诗论著呈现明显增量。
相较于“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而言,“苗族古经”概念出现很晚。文献检索显示,“苗族古经”概念在苗族文化研究领域或我国学术界公开表述始于2009年。是年,余学军、潘明修正式以《苗族古经》为书名编译了他们在贵州丹寨县采录的苗族口头传统资料,以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内部资料方式刊印,2010年4月余学军在第三届“中国传统节日(清明·寒食)论坛”提交的题目为《清明节苗族“嘎熙”祭仪的文化解析》的学术论文中(15)余学军,《“清明节苗族“嘎熙”祭仪的文化解析”》,载冯骥才主编,《清明(寒食)文化的多样和保护——文集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第165-175页。另见余学军、潘明修《苗族古经》(内部刊印),贵阳: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2009年。,使用“古经”“祭仪古经”等词汇称谓祭司在“嘎熙”仪式中的唱述词。他认为,苗族的“祭仪经”“是苗族古代文学最早的表现形式。”“苗族古歌、苗族贾理经都是从苗族祭仪古经中渐渐分离出来的”,且对“苗族古歌”和“古经”之间的关系做了解释,他说,“苗族古歌是祭仪古经世俗化的结果,贾理经是祭仪古经理性化的结果,而贾理经的再次世俗化,乃是理歌。”“祭仪古经中除了神圣不可世俗化的内容继续由祈禳长老掌控外,可以在所有社会成员中传唱的部分则脱胎而成苗族诗经,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苗族古歌’”(16)同上。。据余学军介绍,之所以提出“古经”概念,也是基于在田野采录苗族口头传统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仿佛“古歌”太过宽泛,难以精准表述苗族口头传统中经典的部分,因此,他认为“祭仪经与贾理经和古歌一道,成为苗族经典文化中三颗璀璨的明珠”。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选题(第二批)研究方向第97号将“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列入,标志着“苗族古经”进入了国家学术话语殿堂。随着“苗族古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资助(项目编号13&ZD137)后,2014年发表了阶段成果,[32]“苗族古经”研究话语逐渐出现在学术期刊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开设了“苗族古经研究”[33]栏目,进一步推动“苗族古经”学术概念的普及。
从发表的有关讨论“苗族古经”概念的文章看,“苗族古经”概念的倡导者是基于过去使用“苗族古歌”或“苗族史诗”等概念的反思,力图从“经典”层面强调“古歌”或“史诗”等在苗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意欲将之提升与国家主体民族传统“经典文化”同等地位。比如,刘峰在论证为什么提出“苗族古经”概念时指出,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包括古歌、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将苗族古经降解为文学文本,暗中预设苗族古经为相对于‘经典’的‘他者’”;民俗学研究“主要包括风俗民俗、宗教民俗、物质民俗等方面的研究。”“无视古老苗族社会的生存智慧,暗中预设苗族古经为相对于‘非民间性’的‘他者’。不自觉地站在‘国家’‘文字’为‘文明’的立场,暗中剥夺苗族文化文本之为‘文明’的资格,同时也遮蔽了苗族文化自足系统的存在。”民族学研究则“主要包括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社会控制、社会结构、社会伦理、文化变迁以及信仰与地方性知识等方面的研究。”[33]因此,将“古经”视作苗族“文化元典”,突破对无文字民族口传文献的“民间文学”“民俗研究”定位,进而反思“文明”“民族”“国家”等基源性概念,以新的视角,研究苗族文化元典体现的自然、社会与精神文明。[33]也有学者认为“苗族古经”指的是苗族“口传经典”,如曹端波认为,“苗族古歌是一种口传艺术的经典文本,可以说为苗人社会的‘古经’,如同汉人儒家社会的四书五经,西方欧美社会的基督教经典文本‘圣经’等,当然,作为口传经典的文本与文字经典文本不同,苗族古歌是口传文本与仪式行为相结合的一种具有场域性的文本。”[34]
有学人指出,“苗族古经”提法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及文化相对性理念指引下,苗族知识分子表达“追寻和重塑‘民族之根’‘民族之魂’的诉求,是对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价值反思后的一种再认识和再定位,是将苗族传统口承文化从苗族民间文学视野中提升出来予以重新审视的一种历史实践。苗族传统口承文化实体研究中经历了较长的酝酿和演化过程,它经历了从苗族民间文学经典走向苗族世代遵循的一种‘常道’和行为法则再定位的质变过程。”[35]无疑,“苗族古经”是部分苗族学者基于建构民族“文化元典”[36],重塑“民族之魂”诉求而使用于苗族口头传统领域搜集整理与研究的一个新概念,是在国家回归传统大背景下对苗族文化认知和自觉的某种体现。
关于“苗族古经”概念的意涵,除了前面所引余学军的表述外,刘锋认为“古经”“是苗族‘经师’在排解纠纷、祭祀大典与丧葬、巫事、庆典、动工等仪式场合吟诵的长篇说理、叙事、对话(人与神、人与人)等作品的统称。”[33]尽管刘锋积极倡导“苗族古经”的使用,但在他所申报并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中,仍然设定有“史诗与史实:苗族古经中的历史研究”[33]的子项目,足见“苗族史诗”与“苗族古经”是交叠的,仿佛也是难以界定清楚其各自界限的。
在研读有关“苗族古经”论著发现,“古经”一语的提出多是基于苗语中部方言区口头传统的资料基础,特别是对已经整理出版的“贾理”(或“佳”)内容和性质的界定上。于是,有如余学军所说的“古经”由少数的经师传承,普通民众多不能承袭,禁忌运用,而“古歌”可以由大众传承,可以家传,也可以师传。“古经”经由民众化、世俗化、演绎化后可以变成“古歌”。“古歌”歌师经常有改动,而“古经”稳定性强,经师严格遵循古制。“经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多为家传世袭。“歌师”地位也很高,既有世袭也有师承,但没有“经师”传承与践行的神圣场域。[33]如此等等。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落地于苗语西部方言区、东部方言区去考察同类文化现象时会发现,“古歌”或“史诗”基本上是与民俗仪式难以分离的,极少出现“古经”经由民众化、演绎化后可以变成“古歌”的情况。如已经出版的为史诗学界瞩目的《亚鲁王》就是离不开当地苗族丧葬中砍马祭祀。[37]从此点而言,“古经”概念或许难以胜任对所有苗族同类文化的解析,特别难以解释“异文”出现的合理性。
综上,“苗族古歌”是基于苗族本土语言翻译的学术概念,“苗族古经”是部分苗族学者基于建构民族“文化元典”(如麻勇斌、龙秀海、吴琳等编辑的“苗族口传活态文化元典”丛书等),重塑“民族之魂”诉求而提出来的概念,“苗族史诗”则是依从国内外史诗学界、民间文学界规范的学术用语。三者所指涉的基本是苗族同一文化“文类”。因此,统一使用“苗族史诗”概念,既涵盖了“苗族古歌”“苗族古经”等所蕴含的苗族口头传统内容,又避免三个概念交叠使用带来的学术表述含混,还利于同国内外学界对话交流。
笔者认为,“苗族史诗”可以定义为流传于苗语各方言中,使用苗语的韵体句式,以对唱、唱述或吟诵为主要形式,以创世、祭祖、祈禳、民族迁徙互动为叙事主题,在社会交往、婚姻、丧葬、其他祭仪等民俗场景中演述,具备史诗性的苗族民间活态口头传统。
三、苗族史诗的本体研究
有学者认为,“文学本体论不仅研究文学的本质,而且研究文学的本体和存在。”[38]在笔者看来,从史诗内容结构、母题、语言形式、声率韵律、传承人与传承谱系、唱述环境、唱述方式与音声音乐、采录整理与翻译等的研究都是对史诗的本体研究。从前面的概念界定所引述的研究成果显示,对苗族史诗本体研究无疑是主要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学良、今旦等学者就针对其所搜集的中部方言区苗族史诗的有关内容结构、语言风格、唱述方式等进行了分析,当时他们注意到流行于贵州台江等地的史诗(古歌)由四支歌组成(17)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搜集整理比较成熟的黔东南苗族史诗版本多由《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和《溯河西迁》五个部分组成(参见马学良、今旦《苗族史诗》),或由十二大歌组成(参见黄平等县编《大歌》),但50年代的四个部分划分仍然在延续,表明史诗版本是存在争论的。,它们“可以成为独立的歌,连贯起来,则自成一个系统,每一支歌又分为几部分。”[25]并指出史诗的语言风格多是五言体(即每句五个音节),押调而不押韵。最理想的是前后各句每一个相对的音节的声调都相同,便利于唱述顺口。唱述的方式最明显的特点是设问和作答。唱古歌多为四人,两人为一组,分为甲乙两方。甲方提问,乙方作答;乙方回答完后再问甲方,甲方再回,再设问,这样辗转反复地唱下去。苗语把设问叫作“打结”,把回答叫作“解结”。“打结”和“解结”之间可以加“花”。[25]92潘定智认为苗族各支系都有自己丰富的反映民族历史的古歌,且他认为苗族古歌内容包括(1)酒席上对唱的问答式;(2)理老(说理判案人)、巫师和歌手单独演唱的叙事的;(3)丧葬和祭祀的;(4)结亲嫁女酒席场上唱的;(5)生产劳动歌,诸如“造酒歌”“造船歌”“造鼓歌”等;(6)长寿歌,诸如《榜香由》等。[39]其实,较早参与搜集整理苗族史诗的学者,不可回避要涉及苗族史诗构成的问题——即什么样的苗族口头传统才是苗族史诗(或古歌)?前述杨汉先对黔西北苗族歌谣进行的四种分类中,古诗歌、叙事歌和历史歌三类以及故事中的神话视为黔西北地区苗族史诗的基本结构[40]14-15。马学良等(1956)首先从史诗语言进行判断,指出“从其中所反映的生活,以及一些现在已经不用了的古老的词儿和特殊的语法形式来看,可以知道,它的最初产生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是相当久远了”,而且从内容而言,篇幅巨大。[25]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对苗族史诗本体的关注大多基于整理角度,即重点关心什么样内容的口头传统可以放到“史诗”或“古歌”的篮子之中。而从这一角度对史诗本体的研究实际上又直接影响到搜集整理者关于史诗的概念界定与史诗的实际编译整理。唐春芳不仅参与黔东南苗族古歌的收集、整理、翻译,而且在论及“苗族古歌”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唐春芳认为“苗族古歌”是“以时间比较远古,内容意义比较重要,篇幅比较巨大”作为衡量古歌的标准,并指出了黔东南清水江、雷公山一带苗族古歌有以下七种:(1)叙述天地来源的歌:如“开天辟地”“铸撑天柱一造日月”及“运金运银”等;(2)叙述万物来源的歌:如“枫木歌”等;(3)叙述人类来源和民族迁徙的歌:如“兄妹开亲一爬山涉水”等;(4)反映古代社会历史变革的歌:例如“姐妹歌”就是反映苗族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变化,又如“阿娇与金丹”这首古代爱情叙事诗,就是反映苗族由族外婚制转入族内婚制的婚姻变革斗争;(5)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歌:如“祭祀歌”和“开山辟土”,前者一般译为“鼓藏歌”;(6)反映古人事迹的歌:如“榜香由”这首歌,就是叙述榜香由这个活了九千岁的老人劳动上、爱情上许多有趣的事情;(7)反映古代的创造发明的歌:如“造酒歌”“造船歌”“造纸歌”“造鼓歌”等等。唐春芳据此还分析了“苗族古歌”演唱的特点:“苗族古歌的语言形式都是五言体。句与句之间协调而不押韵。句与句前三字不协调也可以,但后两字必须协调,否则就不能唱。”[41]3且他注意到史诗传唱中的“歌骨”与“歌花”之分:“苗族古歌的结构一般是问答体。唱古歌时,由四人分成两组进行对唱。先是甲方设问,乙方解答;乙方解答完后,紧接着又提出设问,再由甲方解答。这样辗转唱下去,一直到唱完一首歌为止。每一个设问和每一个解答,是全歌的一小段,苗族叫它为歌的‘骨头’。每一段的句子多少不拘,少有五六句,多有十至三十句。除‘骨头’外,还有‘结子’和‘花’。”[41]4-5黔东南苗族史诗的重要搜集整理者之一今旦较早对“歌骨”“歌花”展开研究,他在《苗族古歌歌花》序言中说,苗族古歌是篇幅宏大、内容精深,它的基干,即苗语称为“hsongdhxak”(意为歌骨)的部分,歌骨是表现一支歌主题的部分,在古歌中具体指问和答的内容。歌花(苗语称为“bangxhxak”)是游离于歌骨之外的部分,内容与主题无关,主要以营造环境、活跃气氛、激发情感为目的,以邀请、赞美、自谦、挑战、评说等为内容,也可以包括那些表示交代、承接的套语。歌骨重在叙事,歌花重于抒情;歌骨严肃庄重,歌花活泼风趣;歌骨传授知识为主,歌花娱乐身心为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伴而行。[22]新近研究成果中,吴一文认为,“界定苗族古歌的主要因素”包括“演述方式、叙事主题、整体性与逻辑性、演述传统与口头传统。”[3]30-37当然这是针对中部方言的部分地区史诗而言,比如他指出的“古歌的演唱是一种比较特殊、仅为古歌所特有的演唱方式——歌骨、歌花、套语、插唱等交错一体的提问和回答交互并行的演唱。”[3]30从目前苗语西部方言、东部方言搜集整理的史诗材料显示,他们没有歌骨和歌花之分,且演唱方式也不尽然。
从早期公开出版的苗族史诗(或古歌)文本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苗族史诗的内容结构理解存在差异。田兵选编的《苗族古歌》全书内容分为《开天辟地歌》《枫木歌》《洪水滔天歌》和《跋山涉水歌》四大部分;马学良、今旦译注《苗族史诗》全书内容为《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和《溯河西迁》五大部分;吴一文、今旦著《苗族史诗通解》所引史诗内容也是《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和《溯河西迁》五大部分;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全书内容分为《创造宇宙》《枫木生人》《浩劫复生》和《沿河西迁》四个部分;力士东坡等翻译整理《苗族十二路大歌》的篇目将民间所谓“十二路大歌”篇目全部搜列举齐全,即《掘窝》《十二宝》《扁瑟缟》《五好汉》《洪水滔别》《运金银》《铸造日月》《仰欧桑》《扁香尤》《斩龙》《嘎尼拉》《香简马》等。总体上说,中部方言的黔东南地区史诗版本,或四个部分、五个部分,或“十二大歌”的结构居多。该方言区目前所见已出版的史诗(古歌)中,只有《苗族古歌(融水卷)》[42]例外,其内容包括创世纪、天灾歌、迁徙歌、埋岩歌、婚姻埋岩歌、蛇郎歌、英雄歌、哈梅歌、友荣配衣歌、配烈亨兄歌、波麻歌等十一个部分。东部方言区的则明显不同,石宗仁收集整理翻译的《中国苗族古歌》,内涵是最广的,共分十一部分:(1)远古纪源;(2)傩公傩母;(3)除鳄斗皇;(3)部族变迁;(4)部族迁徙;(5)辰州接龙;(6)崇山祭祀;(7)婚配;(8)纠纷;(9)丧葬;(10)招魂;(11)赶秋节等。[43]西部方言又略有差异,古玉林等编译《四川苗族古歌》由(1)创世纪;(2)洪水滔天;(3)杨娄古仑;(4)婚姻礼辞;(4)丧葬礼辞等。以杨照飞编译的《西部苗族古歌(川黔滇方言)》看,内容由(1)创世纪歌;(2)婚姻礼辞;(3)丧葬礼辞;(4)祭神礼辞等四个部分组成[44]。吴秋林等搜集整理的“蒙恰”苗族“古歌”[45],内容庞杂,把一般故事也囊括其中。此外,还有一些文本是单体的史诗整理文本,如《焚巾曲》《亚鲁王》《鼓藏辞》等。
如果说从整理角度对苗族史诗本体的理解尚显零星的话,21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史诗理论层面上关切了本体研究。内容几乎关涉到了史诗结构、母题、语言形式、声率韵律、传承谱系、唱述方式与音声音乐等本体要素。其中结构、语言形式、声率韵律等延续在前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较大拓展。吴一文、覃东平认为不论是苗族史诗还是苗族古歌,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点:第一是反映了黔东南苗族历史与生产生活大概情况;第二,各篇章之间脉络清晰,排列有序,逻辑关系缜密;第三表达手法多样[27]5-6。吴一文围绕中部方言苗族史诗叙事传统研究指出,苗族史诗的语言形式是以五言为主的叙事句式且递接句式为核心,以押调为主的叙事格律,在表示角色名字、行为及时间与空间等方面呈现出的格律特点符合帕里-洛德理论揭示的史诗“程式”风格。[3]229-252李炳泽从语言学层面关注到了史诗中保留有的大量的“非口语”苗语(古苗语),还有一些在口语中不能搭接的词汇在史诗里为修辞需要而可以搭接,他把这种语言现象视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意义上的史诗,通过语言的超常组合达到了“狂欢”。[2]48-49苗青从语言、声律、韵律等角度集中对史诗在内的东部方言区苗族歌谣本体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该方言区的歌谣(包括史诗)的声律上有奇偶对称谐声押调、三脚押调以及通声、插花声等特点,相应地有奇偶复沓韵三脚复沓、韵连绵复沓、间隔复沓韵等韵律特点。[47]220-269肖远平等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为研究对象进行史诗母题研究可谓是苗族史诗母题研究的代表,他们将搜集于贵州麻山地区的《亚鲁王》史诗分解为英雄“特异诞生成长”“婚姻”“被骗”“征战”“对手”“战争禁忌”“心脾禁忌”“杀子”“考验”等九个母题来研究[47],或许有一些母题的归纳解析不一定吻合汤普森(Stith Thompson)分类[48],但这是目前苗族史诗中关注母题研究较系统的论著,较过去有关母题的零星研究深入一步。在苗族史诗本体研究中,龙仙艳《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4]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她在具体的还傩愿、婚礼、鼓藏节田野采录基础上,力求结合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对三个大的苗语方言区史诗的歌词与唱述民俗环境、唱述者与听者、功能与传承等多维度剖析研究。
苗族史诗本体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受21世纪以来我国史诗学引介的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史学、表演理论及本土化改造,借鉴人类学理论、口述史理论思潮的影响,重视对唱述人或传承人、唱述民俗环境记录与研究。“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有效地揭示了史诗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49]尽管苗族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起步较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搜集整理形成的版本至多仅见到唱述者的姓名,有关唱述民俗环境及场景下的演述记录极少。《亚鲁王》“被发现”,如李云兵所言,“不少人嗟乎,争前恐后,纷至沓来”[50]59-72,“亚鲁王”的唱述者被研究者关注,完成了一批歌师的口述史以及仪式过程田野报告。[51]稍显遗憾的是这些歌师口述史资料、仪式田野报告与出版的《亚鲁王》综合版本没有对接和呈现,不仅多少影响了研究者对文本的完整性理解,且对作为仪式组成部分的南方史诗来说也是不完整的。如吴晓东所指出的“文本的制作者不能只是一部‘照相机’或‘摄像机’,而应当承担起阐释的角色。”整理者在整理演唱《砍马经》与《开路经》的时候,应该将其间很多仪式细节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知道每一部分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演唱的。[52]87
文化部(现文化与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实施的“中国百部史诗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苗族史诗唱述人的演述场景性记录工作,该课题任务要求必须对史诗唱述者进行个人生活及传习史诗的口述史、一部史诗的完整唱述和史诗在民俗环境中的演述等进行影像记录和文字整理及汉译。吴一文、龙仙艳、吴晓东、杨正文等分别承担了不同苗语方言区的苗族史诗子项目,目前见诸公开出版的文献仅有吴一文在《苗族古歌叙事成天研究》一书附录中所列两位唱述人的采访录音资料。期待着更多的有关唱述人及其民俗情景式唱述文献资料的问世。
苗族史诗包罗了苗族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代表了苗族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秩序的一种理解与解释,被一些学者誉为苗族“百科全书”或“圣经”。因此,在苗族史诗领域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非常丰硕,截至2012年前的成果已由龙仙艳做了很好的综述[53],在此不再赘述。
四、整理、翻译与音声等问题
史诗的整理、翻译及音声等也是史诗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如果说民俗环境情景式田野采录的不足是过去苗族史诗采集方法的问题,那么整理、翻译及音声研究不足的问题更多是认知与关注度层面的。
史诗的整理是关切到史诗文本质量的重要环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史诗学界存在着两种关于搜集整理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准确忠实、一字不移”,另一种是主张“综合整理、删除糟粕”(特别针对出版时)。如钟敬文指出要区别提供于学术研究还是给一般读者阅读,两种的整理目标有不同,他说“作为多种人文学科研究材料的故事、传说的记录,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且不加任何改变地提供出去(当然,它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整理过程)。即使原讲述中有形式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内容等,也不要随意加以删除或改动。最好把对它判断和弃取之权留给它的各种研究者。这种资料,虽在性质上十分宝贵,但是,一般作为普通读物大量印行,是不大适宜的。”[54]144尽管刘魁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文主张对民间文学作品记录要“不加任何窜改、歪曲、扩大或缩减,如实地提供有关人民创作和生活的材料”,而且“尽可能把那些‘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部分’(如手势、音调、表情)也标记出来”,还要求“必须对听众(如果有听众的话)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观点。[55]但刘魁立所主张的忠实记录原则与方法并没有成为主流,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人民性、革命性是当时评价民间文学的重要标准,学人多秉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在进行各民族史诗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有重点、有选择地记录和整理进行“适度”的增删,这直接导致了史诗歌手的相关情况以及演唱环境等诸多资料的缺失,导致许多搜集者在记录、整理与出版过程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做出增添、删除、改动等不科学、不规范的学术行为。[56]此种大环境下苗族史诗的整理存在瑕疵在所难免。前述的不同学者由于搜集整理的取舍方法未能达成统一,造成了在同一区域采录整理的苗族史诗版本不同、结构不一的状况。
纵使引人注目、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亚鲁王》史诗,在整理方面仍然存在让人诟病的地方。杨杰宏认为,“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翻译整理中存在着文本选择不完整、翻译不准确、演述语境失真等问题。”进一步说,现出版的《亚鲁王》版本,表面上看是根据不同东郎演述整理而成的史诗文本是目前字数最多、史诗规模文化体积最大的一个“范本”’,但其实质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即经过整理者二次编辑而成的史诗残本。”[57]吴晓东指出,出版的《亚鲁王》,其实是紫云、望谟一带苗族丧葬仪式中所唱的《砍马经》与《开路径》中的某些部分,是祭司东郎对亡魂的吟唱。这部分追述了苗族祖先亚鲁的征战和率领部族迁徙的历史,也追述了其子孙的历史。把这部分抽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篇章,即现在看到的《亚鲁王》版本。要真正了解该史诗,必先大致了解《砍马经》与《开路径》的概貌和唱述它们的丧葬仪式过程。[52]84吴秋林说,“亚鲁王”有一个坚实的民间形态,但这个形态只是“亚鲁”,而不是“王”,“王”是收集整理出来的,因为这个“伟大的发现”的最初“定义”是英雄史诗。[58]264-280这的确是史诗整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有“王”与无“王”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差异实在很大,倘若采用人类学或政治学有关“王权”理论去研究“亚鲁王”下苗族社会将是怎样的结果?
影响苗族史诗整理或文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问题,这也是所有少数民族史诗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所说语言有不可翻译性的一面,史诗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还是文化的翻译,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也曾经尝试着所搜集的苗族史诗翻译,各种艰辛深有体会。目前国内常见的史诗翻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为汉语文)有两种文本,一种是直译,另一种是意译。在出版的苗族史诗中,有好些版本既有直译也有意译,保留用苗文或国际音标记录了史诗的“元态”,这是非常宝贵的。笔者在翻阅一些史诗版本中发现有些翻译(主要指意译)值得商榷,好在有苗语版可以参考并纠正一些可能的误译。因此,出版保留苗语史诗的“元态”记录,既是让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减少误读苗族文化的保障,更是有利苗族史诗在传承与传播中最大限度降低“失真”的基本条件,是一种较好的非遗“固化”保护形式。
搜集整理、翻译势必涉及成型的史诗文本问题。“异文”在史诗学界讨论较多,笔者以为讨论“异文”只能是相对的,“异文”的存在隐含着某一文本为“中心”或“正本”的逻辑前提。有学者注意到了因为时代的变迁,苗族语言发生变化对口头传承与唱述的史诗语言唱述产生影响,以及民族交往带来的语言影响,诸如苗族史诗中的汉语借词等,还有不同的唱述民俗环境。此外,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所追踪的史诗说唱歌手阿夫多在不同场合唱述所获得的版本有差异一样,口传史诗在唱述中有细微变化不可避免。这里想强调的是苗族史诗“异文”的出现是必然的,其一是因为苗族史诗乃至南方各民族史诗唱述大多与仪式紧密相连,这是区别于艺人表演的国内三大史诗的不同特征,在史诗唱述者在仪式中唱述势必有一部分内容是要结合“事主”的家事来唱的,在此语境下记录获得的史诗哪怕是同一个唱述人所唱,两次或两次以上所唱述的内容必然有不同的成分。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说“仪式也很难在时间流逝中保持不变,尤其当这类仪式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表演一次的话。”[59]63其二是在一些苗族史诗流布地区,仪式中的唱述人具有“家族性”特点。龙正学记录于20世纪50年代材料显示,“凡要举行祭仪的人家,一般都必须请同姓氏的祭司来帮忙做,”“只有举行大典,如‘吃牯脏’‘引龙’需要祭司两名以上,才去请异姓氏的祭司来帮忙,但必须相识,或由族中介绍才去请。”[18]311四川凉山彝族毕摩在仪式中唱述的史诗其家支特性至今仍较突出,足见这是南方各民族史诗的某种共性。由于篇幅所限,有关苗族史诗“异文”问题另文再探讨。
音声是苗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中较为缺乏的。“音声”是曹本冶在仪式音乐研究中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仪式中的“音乐”及诸多声响,他认为作为仪式行为的一个部分,音声对仪式参与者来说,是增强和延续仪式行为和氛围的重要媒介。[60]不论是在婚丧及其他祭祀仪式上唱述还是如黔东南部分地方的主客对唱中,作为“唱本”的苗族史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始终与音乐或“音声”相伴,但在苗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有的零星音乐研究又多是与史诗文化脱节,大量被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史诗成为无声的史诗。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苗族史诗的音乐开始有了一定进展,但文献检索显示,还是仅仅寥寥几篇。围绕“亚鲁王”史诗的研究,如孙航、梁勇,[61]其中梁勇的硕士论文《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的音乐文化阐释》[62]是基于麻山田野基础完成的,较好兼顾了音乐本体研究和史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龙仙艳尝试着对苗语三大方言区的史诗音乐进行分析,并努力归纳了三大方言史诗音乐的共同性和差异性。[4]132-134但毕竟没有足够的田野资料支撑,难以将各地苗族史诗音乐相关特色呈现出来。音乐风格特色与方言土语有很强关联性,各地苗族史诗唱述中有乐器使用的,有完全用声腔的,有用单一乐器的也有多种乐器混合的。诸如笔者在川南田野调研时发现丧葬仪式上的史诗唱述与木鼓声、芦笙、钹、锣等“音声”交替杂糅,没有专业音乐人员参与实难以完成田野记录。史诗“音声”的缺乏使史诗传承和研究失却了很多色彩,史诗音乐研究任重道远。
五、结束语
苗族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经过百年发展,取得了毋庸置疑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成为进一步前行的坚实基础。回溯过去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不足,目的在于坚定前行。苗族史诗学界前辈们在过去的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如吴晓东所推荐的使用苗语文、国际音标和汉文出版《四川苗族古歌》及近20年来贵州等地出版多语史诗版本可供参照。还有中国史诗学界前辈们的探索,前文提到的刘魁立倡导的原则,再如一直致力于蒙古史诗研究的仁钦道尔吉秉持的完全忠实于原始文本,不对所记录的文本进行改编;对田野记录文本未加以增减,对不完整的演述、内容明显残缺的文本,也都按原样记录,不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补全;认真记录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演述文本,没有试图把它们整编到一起,通过互为补充,改编出所谓的“理想文本”等的史诗记录工作原则[63]。还有杨杰宏在反思《亚鲁王》搜集整理后提出的在整理、研究口头传统文本中要遵循“文本的完整性、翻译的准确性、语境的真实性”三个重要维度,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整理工作中的诸多失误,而且对于有效推进口头传统理论和方法论创新也有着积极的意义。[57]
不论从事苗族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抑或从事苗族社会文化研究,不能祈求通过某一局部的研究来概括所有苗族社会文化的共性特点,也千万别企图以自己熟悉的苗族文化现象否定或替代别处的苗族文化。[64]毕竟近千万苗族人口世居在南方七个省市自治区中,在没有统一文字整合的背景下,又长期与各民族互动交往,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明显,这些差异是苗族文化丰富多样性的标志,也是苗族史诗滋长的文化沃土。[65]
——以凯里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