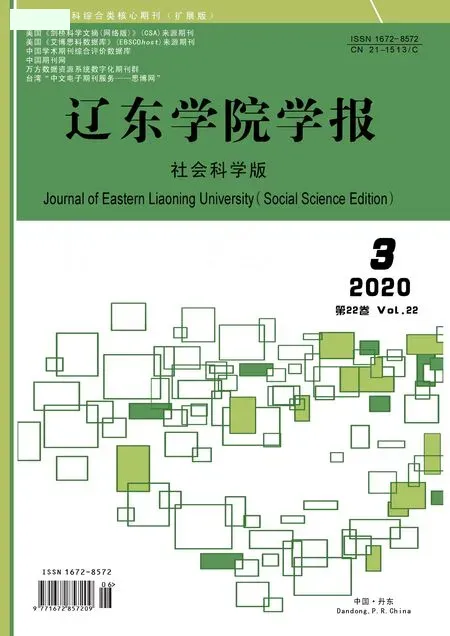论爱罗先珂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碰撞
贺雪琴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3)
爱罗先珂是著名世界语诗人。因为政治原因常常需要漂泊异国。1921年,俄国白银诗人华西理·爱罗先珂从日本来到中国。此前,他曾在暹罗、缅甸、英国、印度等地漂泊。爱罗先珂受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一分子主义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反映着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怜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个国家间紧张的局势,这位世界语爱好者曾多次获“思想罪”而被驱逐。1922年,在胡愈之,鲁迅等人的努力下,爱罗先珂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课程,与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激烈碰撞。目前,学界对于爱罗先珂的研究略有关涉,主要集中于爱罗先珂对鲁迅的影响和爱罗先珂对巴金文学创作的影响上。如熊鹰《世界语文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以鲁迅“一战”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为例》[1]、孟庆澍《铁屋中的“放火者 ”——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2]、贾蕾《巴金与世界语文学》[3]等。然目前学界并没有关注爱罗先珂对现代中国文学家的影响及爱罗先珂在现代中国文学界激起的水花。故而笔者试图论述爱罗先珂来到中国对当时中国文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梳理爱罗先珂与中国现代代表性文学家的碰撞。在爱罗先珂访华期间,联系最密切的当属同住八道湾胡同的周氏兄弟。鲁迅和爱罗先珂不仅是生活上的好友,文学上也联系密切。爱罗先珂与胡愈之因世界语运动结识,胡愈之积极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对于爱罗先珂文学作品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一生推崇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深受爱罗先珂政治观点的影响,其创作的童话作品也与爱罗先珂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笔者便以胡愈之、鲁迅、巴金为考查对象。
一、世界语运动下的爱罗先珂与胡愈之
当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为了推进华夏语言文化进步和社会变革,近代知识分子加紧学习西方的知识文化。1916年陈独秀首先介绍了世界语发展现状,然后就有读者致信认为学习世界语有损无益。陈独秀回复读者:“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4]。因而引起当时学界的激烈讨论。蔡元培在1917年于北京大学就开设了世界语课程,由孙国璋担任教师。
近代中国社会最早了解爱罗先珂,是因为胡愈之。胡愈之除文学家身份外,一生都是世界语的理想主义者。陈原在《胡愈之与世界语》序言中提及“我们世界语界称他们是世界语的化身”[5]2。胡愈之相信:“全人类语言统一的梦想,在将来,至少最近的将来也许不会——但不是绝对的不会——有实现的希望。”[5]34他认为世界语主义事业是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的普泛的交易”。怀揣着这种“高尚的理想”,胡愈之注意到了世界语诗人爱罗先珂。
胡愈之与爱罗先珂因为世界语运动这一媒介产生了联系。1921年5月,爱罗先珂在日本因参加政治运动被捕,后被驱逐出境。胡愈之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文,第一次介绍了爱罗先珂并对其遭遇深表同情。此后,胡愈之收到日本世界语协会信托,请其帮助这位被驱逐的世界语诗人。在爱罗先珂辗转到了上海之后,胡愈之作为上海世界语协会成员,第一个前去探望,并邀请爱罗先珂在上海世界语协会讲习班授课。当年9月,胡愈之信托鲁迅,帮忙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这是鲁迅第一次与爱罗先珂发生联系。后来,在胡愈之与鲁迅的共同介绍下,蔡元培聘任爱罗先珂在北大教授世界语,理想主义者胡愈之于是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爱罗先珂的戏剧和诗作,其中鲁迅、胡愈之翻译的较多。二人一起翻译了一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发表于胡愈之工作地上海商务印书馆,这是爱罗先珂作品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后来逐渐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如《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晨报副刊》等报刊纷纷刊载爱罗先珂的作品及对其作品的评论。
翻译爱罗先珂的作品对于胡愈之进一步推进世界语运动无疑是有助益的,胡愈之在《为跌下而创造的塔》译者后记中写道:
译了爱罗先珂君的几篇作品之后,使我对于世界语更得以坚信。如果他用了别种国语来作,思想和情绪自然——也像他的日文著作一般——也能够一样表现出来的,可是文章的音节可再不会像这样的华美了。[5]20
胡愈之认为爱罗先珂世界语写作的作品充满了音节的华美。可以说,爱罗先珂在胡愈之眼中就是一个推广世界语运动的极好的榜样。
1923年4月,爱罗先珂回到革命后的俄国,之后就再没有再踏回这片尊敬他、关爱他的土地。但爱罗先珂与中国的联系没有随着他的归国而消失。爱罗先珂译介热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渐渐褪去。爱罗先珂与胡愈之的最后一次联系还是因为世界语协会。胡愈之出游莫斯科时,胡愈之记道:“在苏联世界语会内,遇见五六位世界语同志,并且得到了七八年前来中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确实消息,这使我意外的喜悦。”[6]45可以说,世界语协会是爱罗先珂和胡愈之之间联系的牢固纽带,他们因同样的理想相识,因世界语协会而互帮互助,这也正体现了世界语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人类爱。
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中详细记述了1931年胡愈之“跨进普罗之春”,进行的七天旅行中发生的事。观其当时之社会政治背景,这本书得以出版并深受读者欢迎,是很不容易的。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在莫斯科的所见所感,其中有一篇短文《盲诗人的消息》[6]45,介绍了爱罗先珂的近况。“在法国,我用了种种方法,托在俄友人设法探听,可是不曾接到过一个确实的答复。”“要是我来莫斯科早了五个月,还能和他见面。”[6]45“可惜路太远了,我不能去看他,不然,我可以和他诉说七八年以来的事情,而且可以知道他最近的生活感想。无论如何,我相信他现在不会像在北京的时候那样,天天嚷着住在沙漠中的悲哀呢。”[6]45从胡愈之的写作可以看出,虽然爱罗先珂已经离开了中国,但胡愈之对他还是十分挂念的。胡愈之来到莫斯科,也期待和爱罗先珂能够老友相见,一番彻谈。这种挂念,是世界语协会之外的单纯的异国文人友谊,虽然许久未见,但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消息,还是触动着胡愈之的心。
总的来说,胡愈之与爱罗先珂因世界语运动结缘,作为翻译家和报人,胡愈之积极传播爱罗先珂的文学作品,促进了当时国内爱罗先珂热的产生。
二、爱罗先珂与鲁迅的情感共鸣
鲁迅先生对世界语运动也是支持的。在世界语运动刚刚兴起的中国,鲁迅就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的赞成Esperanto的理由,十分简单……。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赞成Esperanto。”[7]36在1936年8月《答世界社信》上,鲁迅又再次重申了自己对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态度:“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7]36在爱罗先珂在北大教授世界语时,鲁迅也常常抽空去听爱罗先珂的讲座,但爱罗先珂和鲁迅的联系与世界语运动关系不大。
鲁迅是中国最主要和最早的爱罗先珂作品的译介者。《鲁迅全集》中收入的爱罗先珂童话共13篇。在当时,鲁迅先后把爱罗先珂童话译作发表到《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中,促进了当时文学界对爱罗先珂作品的认识和理解。
“鲁迅翻译选目,往往首要的不是从文学的标准出发,尽管文学往往是他表达思想的主要载体。”[8]101当时鲁迅先后译介了武者小路的《一个青年的梦》这一含有世界主义思想的剧作和爱罗先珂的童话,符合当时鲁迅借译作传达思想的目的。鲁迅的译作选择从来不考虑原作者的文学史地位,往往是从主观的喜好和文学思想出发,而爱罗先珂就这样进入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选材中。
鲁迅译介爱罗先珂童话,与爱罗先珂童话作品中所表达的“泛爱主义”有很大关系。爱罗先珂的“泛爱主义”与鲁迅作品中的反抗精神在其批判意味上是很相似的。在鲁迅译介爱罗先珂的作品中,《池边》[9]77里曾写道,蝴蝶因为不忍目睹世界的黑暗,想救世界,想恢复太阳,飞向太阳,结果葬身大海,而蝴蝶的大爱没有人理解。在《狭的笼》[9]89中,老虎想救出山羊、金鱼和金丝雀,但动物们并不感激,而老虎想要救出的女人最后自杀了。其他人和动物们不能理解老虎的拯救,而老虎也得不到对于它的爱的任何回应。爱罗先珂的跨种族的无区别的爱尤其受鲁迅珍视。这些作品里的人物与当时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夏瑜等人物形象很有相似之处。蝴蝶和老虎的牺牲和拯救对于当时的国民来说是无用的,得不到回报,但它们不会考虑得失,它们只是专心把自己的志向完成。而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和夏瑜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们都曾站起来与封建势力斗争。然而在广大民众眼中,他们不过是狂人和死刑犯。他们是清醒的人,却也是民众眼中不正常的人。同样是描绘无谓的牺牲,爱罗先珂的牺牲更富唯美意味,而鲁迅则更具批判意味。鲁迅创作《阿Q正传》与翻译爱罗先珂童话的时间大体相当。一面是针对现实进行历史的批判性地写作,一面是“泛爱主义”似梦一样的诗意翻译,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性格中的两极性。“他一方面是乐观的,相信进化论,总是抱着希望;另一方面又是悲观的,现实中种种黑暗和腐败让他悲愤。”[10]
爱罗先珂的文学常被鲁迅称为是梦,鲁迅深知梦的美好和梦的虚幻的双重性。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说道:
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着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11]214
鲁迅在爱罗先珂的作品中看到了很多乌托邦的、天真的梦的理想,但鲁迅也是清醒的卫道士。爱罗先珂童话作品中的对当权者暴政的批判,鲁迅是支持的;而爱罗先珂对人类一分子主义体现出的未来美好幻想,鲁迅是以一种情感上的赞扬为主。鲁迅在评论《春夜的梦》时曾说:“作者曾有危险思想之称,而看完这一篇,却令人觉得他实在只有平和而且宽大,近于调和的思想。”[11]222鲁迅评论的爱罗先珂作品中“调和”,正是与鲁迅本人思想的最大差别,鲁迅作品中常常是掩不住的愤怒的情绪。可以说,鲁迅也曾做梦,但鲁迅大多数时候却是清醒的。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认为鲁迅是把爱罗先珂意象化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来说,爱罗先珂被当作从正在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国来的预言者。”[12]141
关于情感上的赞扬,鲁迅在1922年曾创作了一部小说《鸭的喜剧》。“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13]176小说写了爱罗先珂的寂寞感,其实也暗含着鲁迅自己的寂寞感。鲁迅和爱罗先珂是有着情感上的共鸣的。爱罗先珂在讲座中常常直白地批判当时的中国,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在一次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中,爱罗先珂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14]201这种直白的痛骂和鲁迅性格中的怒目而争很有相似之处。
而爱罗先珂对鲁迅的文学作品也是兴趣极大的。日本记者清水安三认为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发出“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的呐喊,使“不及周作人著作稿费一半的鲁迅的稿费,蘧然上涨了三倍。”[15]173这位日本记者还说,他受爱罗先珂之邀,走访爱罗先珂,为他读鲁迅的小说,边读边译,爱罗先珂对鲁迅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阿Q特别感兴趣。可以说,正是两位文学家的惺惺相惜和心灵相通,才让五四时期的这场文学碰撞激起更大的火花。
三、无政府主义旗帜下的爱罗先珂和巴金
如果说爱罗先珂与胡愈之、鲁迅二人的文学联系,是基于爱罗先珂在华期间与二人的文学交往,那么爱罗先珂与巴金的文学联系则更多的是巴金和爱罗先珂在思想上的契合。
爱罗先珂在华的三年间(1921—1923),巴金还是文学新人,是鲁迅狂热是追随者。巴金曾三次说过愿追随“鲁迅的道路”。通观巴金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延续了鲁迅的启蒙立场。王元化在《讲真话》中说:“无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激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着多少差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16]
爱罗先珂并未与巴金有直接交往,但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使青年巴金也深受爱罗先珂影响。巴金曾自言:
说实话,我是爱罗先珂的童话的爱读者,二十年代爱罗先珂的童话通过鲁迅先生、夏丏尊先生和胡愈之同志的翻译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他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17]
这既是爱罗先珂译介热产生的文学影响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巴金对爱罗先珂文学思想的心慕手追。巴金同爱罗先珂一样,深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都是坚定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上都有着坚定的人道主义内涵。无政府主义要求打破一切国家机器,追求绝对的平等和自由。巴金一生都推崇无政府主义,爱罗先珂在其童话作品中反映出的“人类爱”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体现。正如日本作者江口涣评论:
爱罗先珂君是无统治主义者;是世界主义者……然而他所住的世界,却全然不是现实的世界;是美的未来的园,是乌托邦、自由乡,是近于童话的诗的世界。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也无非就是从这美的诗的世界所产生的东西罢了。[18]506
爱罗先珂在印度,日本等地宣扬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辗转来到中国之后,在自己的讲座中也常常是大骂剥削人民的政府。青年巴金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旧剥削的先进青年,他在爱罗先珂的童话中看到了自己向往的无政府主义世界,然而现实往往是黑暗的。他的作品《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就是一位对现实世界充满憎恶的革命青年,他为了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拼死抗争,最后以生命殉理想。这正如巴金自述:“忠实地生活,正直的战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需要恨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19]
巴金和爱罗先珂的文学联系还反映在巴金对爱罗先珂童话的借鉴和再创造上。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编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随后巴金创作了四篇童话,其中《长生塔》以父亲叙述故事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残暴的皇帝为了追求长生,奴役百姓,建造长生塔,最后塔倒塌皇帝也从塔顶坠落的故事。巴金在《关于〈长生塔〉》——《创作回忆录》之二一文中说到了创作这篇童话的最初动机:“读了欧森外的《沉默之塔》(鲁迅先生译),忽然想起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1899—1952)的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译),我对自己说,写篇童话试试吧。”[20]383这就是巴金写作这篇童话的最初动因。而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讲述的是互为仇敌的富家小姐和富家少爷为了炫耀彼此的财富,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互相建起高塔,结果同时摔下来的故事。巴金借鉴了爱罗先珂塔的意象和剥削方随塔摔下去的情节。这两部童话都是揭露剥削阶级的无耻,暴露他们对穷人的残忍,最后都以塔倒塌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局,表达了对富裕者的诅咒和对平民的怜爱。巴金的《长生塔》创作与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高压统治下的中国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除却吸收爱罗先珂作品中的“人类爱”的主张和人道主义悲悯情怀之外,巴金更有对理想未来社会的美丽梦想。“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是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完完全全的自由”[20]380,这段《长生塔》序中的文字,可谓表达了巴金在那个压抑时代的心里话。
虽然巴金和爱罗先珂的作品有很大相似之处,但巴金比爱罗先珂的童话更多了一层积极的含义。巴金曾评价爱罗先珂的作品:“在他的苦人类之苦,憎人类之憎的心上,永远刻印着一条悲哀的伤痕。”[20]4在母亲的关爱下长大的巴金,作品中常常透露出一种对热情和对革命的期望,而流浪诗人爱罗先珂则是在幻想建立一个乌托邦世界。巴金在《生之忏悔:〈幸福的船〉》序中曾说:“这个俄罗斯盲诗人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自身,他象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人类的爱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恨潜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20]4可以说爱罗先珂停留在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和对乌托邦世界的幻想里,而当时中国的文人则是有着追求光明的勇气和更加现实的考虑。巴金的童话没有了爱罗先珂的“伤痕”,写出了更加积极的革命力量。巴金发展了爱罗先珂的“人类爱”,转化为更为确切的百姓爱。正如巴金的童话《能言树》中所说:“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镣铐、皮鞭、地牢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他们最终会失去幸福。”[20]50巴金敢于通过童话直接表达他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期待。
余 论
爱罗先珂的访华给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带来了很大影响,通过当时文化界对其作品的翻译,爱罗先珂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泛爱精神,都被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很好的学习吸收下来。通过梳理文献可知:
其一,胡愈之与爱罗先珂的交往是基于世界语运动,胡愈之对爱罗先珂的作品产生了极深的共鸣,因而胡愈之不仅积极翻译爱罗先珂之作品,亦与爱罗先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其二,爱罗先珂与鲁迅之交游亦深,二人不仅在生活上交往颇密,更主要是鲁迅在情感上极力赞扬爱罗先珂,同时爱罗先珂也对鲁迅的作品极力称赞,二人之间的情感产生了极强的共鸣,此二人之情感主要是基于对彼此作品的欣赏。
其三,巴金作为青年后学,未与爱罗先珂有实质上的交游,更多的是对爱罗先珂的心慕手追,二人之交游主要是在于二人之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爱罗先珂对巴金的童话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同时巴金也发展了爱罗先珂的思想义涵。二人之间的碰撞影响主要是在于其巴金对爱罗先珂的思想接受。
要之,中国文学家对于爱罗先珂的文学思想并非盲目吸收,而是带着一种批判学习的精神,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可以说,爱罗先珂和当时中国文化界用碰撞一词更为合适。爱罗先珂的“人类爱”丰富了中国文化界的文化知识宝库,同时也给了当时文人们创作带来了启发和灵感。虽然世界语运动以成为过去,但这位世界语诗人在中国文化界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